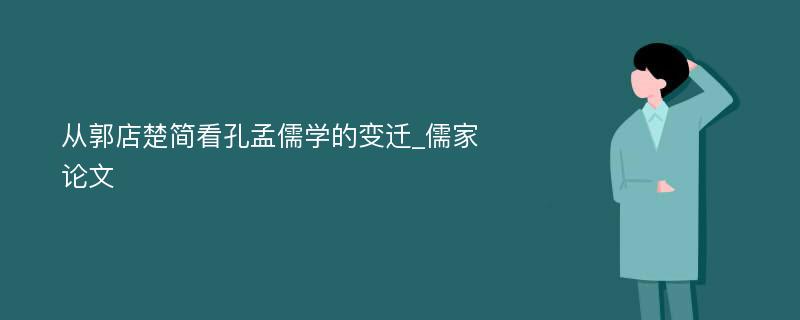
从郭店楚简看孔、孟之间的儒学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郭店楚简看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店所出楚简,包括儒家思想文献十篇。这十篇文献,按照其内容划分,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探讨儒家思想范畴、义理,包括《五行》、《性自命出》;另一类侧重于政治哲学,即为君、治人之道,包括《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不过,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儒家传统中,“德”与“业”总是相互关联、融合的,而郭店楚简的篇目也显现出两者杂糅的特点,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注:竹简中《忠信之道》、《尊德义》两篇是德、业两者并重。)这十篇楚简,据专家推测,出自楚太子之师的墓葬,且有可能是太子师用以教授太子的教本,其内容可能是从流行的儒家文献中选编出来的。(注: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陈来《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若果然如此, 则这一选本必然有其强烈的目的倾向性。郭店楚简中探讨治人之道的儒家理论占有多数,这正符合太傅教授太子以成治人之材的目的。这样说来,这十篇文字便不足以代表当时儒家思想的全貌,而且十篇文献非出自一派,有可能是儒家多个派别思想文献的混合。各篇文字写定的时间早晚也不相同,因而从整体方面看,缺乏系统性,并不能代表当时儒家发展的全貌。以这样稀少且问题重重的资料论析往古思想的轨迹,自然不易得出具体的结论。但若抱着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态度,是否也可约略探知儒家思想演变的一些蛛丝马迹?
这批竹简所出墓葬的时间在公元前350—300年之间,(注: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8日。)这正处于孔孟之间的儒学发展期。对于郭店楚简所反映的儒家思想,专家曾经提出不少精辟见解,(注:郭店楚简出土以后,除了整理小组的释文以外,专家也有不少研究论文问世,如庞朴《孔孟之间》(《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初读郭店楚简》(《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等。 )给我们以很大启示。本文主要从儒家义理(即思想概念、理想人格与修身途径等)方面来考察儒家学派在这一阶段的发展状况。
一
儒家学派讨论义理,往往着重于人生诸问题,因此又被称为人生哲学或伦理思想。在人生哲学的探讨中,原始儒家如孔子往往就儒学思想范畴(如仁、礼、义、忠、信等等)理想人格及修身途径展开阐述,对于有些问题虽未上升至本体或逻辑的高度,但基本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发展格局。诚如学者所云,后世儒者的思想,均是以未展开的形式孕育在孔子的思想当中。(注:请参考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古代中国与世界》第377—398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郭店楚简正是在孔子思想基础上所进行的发挥,但却又体现着浓厚的儒家别派的思想特点。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它博大精深,体现着孔子最高的人生境界。在孔子“仁”的思想当中,包含着“爱人”的意蕴,如孔子谓“仁者爱人”,这一思想在郭店楚简中也有反映,如:
爱,仁也。(《语丛》三)
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五行》)
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五行》)
在这里,“仁”所展现的是“爱”之情。又如《五行》篇云“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人,仁也”,由爱己而扩展到爱人,这可看作是儒家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思想的直接反映。“仁”之所以能够成为孔学的骨干,关键在于它是内心之德,它要求人们立于己、立于内,而非立于人、立于外,从而肯定了人的独立性和人在道德面前的主动性。孔子称许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以为颜渊达到了“仁”的境界,原因在于颜渊能够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颜渊在窘困的环境中仍以追求仁德为务,内心充实,因而一切行为均无待于外物。“仁”成为“心之德”这一命题,在郭店楚简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述。《缁衣》篇记载孔子曰:“轻绝贫贱,而厚绝富贵,则好仁不坚,而恶恶不著也。人虽曰不利,吾弗信之矣。”(注:《缁衣》篇的作者不详,篇中以此句出自孔子,无论是否事实,都可以表明这一思想是受到孔子之后某一学派的儒者重视和赞赏的。)由于外物所诱而轻率地脱离穷困、追求仁德却不肯割舍富贵的诱惑,这样的人,便称不上具有仁德,事实上这是讲求将仁德根植于内心,不以外在环境的变迁而动摇内心之德。关于“仁德”的实践,孔子曾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还谓“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强调倘若能从身边的善事做起,则欲仁而得仁。简文对于实践仁德的方法,曾有几处说明,谓“匿,仁之方也,……柔,仁之方也”(《五行》),“笃,仁之方也”,“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慎,仁之方也”(《性自命出》),简文认为匿、柔、笃、性爱、慎等是实践仁德的方法。慎(或“慎独”)是可以在儒家文献中见到的,但将笃、性爱与仁联系起来,并且以柔说明实践仁德的方法和仁的特征,则是郭店楚简的发明。这说明,孔子之后,儒家学派在以不同的方式探讨实践仁的途径。“仁”,运用到政治当中,便成为仁政。孔子将仁贯彻到政治当中去,包含着许多方面的内容,其基本点则是要求为政者修身而为天下的表率,使民众有所仿效,自然而然地归心于“仁”,正如孔子所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郭店楚简论述为政的内容较多,而其相关思想与此完全一致,如谓“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道”(《缁衣》)“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含德者,未之有也。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导之,其所在者内矣。”(《成之闻之》)“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尊德义》)可以说,为政者应当成为天下民众的表率实为简文的重要思想。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体现着至深至远的精神境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从不将仁与其它道德范畴并列。孔子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等,这些都说明孔子有时是将“仁”作为诸种德行中的一“德”而与其它思想概念并列的。但在孔子的总体思想中,仁却是最高远、最具包容力的思想概念,甚至成为道德总和。(注:如孔子谓“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以为“仁”超越于勇,其他如“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恭、宽、信、敏、惠”为仁(《论语·阳货》),可见这些德行是综合地包含在“仁”之中的,“仁”堪称道德总和。)郭店楚简中“仁”出现的次数很多,表明了其作者对于仁的重视,不过简文中的仁,其内涵有与孔子思想相异之处。其中,值得注意处有下面几点。
首先,郭店楚简中,“仁”不再具有道德总目的意义而多与其它道德范畴并列,如《五行》篇谓“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而畏者,好义者也;闻道而恭者,好礼者也;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在这里,仁与义、德、礼等并列。《六德》篇谓“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将圣、智、仁、义、忠、信固定为六德。这些都标志着,在郭店楚简中,仁并未获得思想核心和道德总和的地位。其次,简文中,仁不是最高的道德境界,而只是道德逻辑序列中的一环。《五行》篇谓“见而知之,智也;智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仁,义、礼之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注:文中“四行之所和”,其内容不知确指,若以仁为知、义、礼之和则只有三行,若以“知、安、行、敬”为之,则其中的安、行又不具备道德含义,仁便只是四种行动的总和。)按照其所云,“仁”来源于智,而义与礼导源于仁,智与仁、仁与礼义环环相扣,构成有序的递进。《五行》篇又说“不聪不明,不圣不智,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这里认为仁源于智,但是抵达仁德之后,并非最终的完善,而是直到“德”方是道德递进中的大善。许多专家指出过,作为孔子思想体系核心的“仁”虽然上承周公“德”之思想而来,但又超越了德的内涵。不过,我们发现,在郭店楚简中,“德”’却体现着道德的最高境界,《五行》篇谓“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说明德是其他德目如仁、礼等的总概括。《五行》篇又谓“德,天道也”(《五行》),“德”代表着最高的天之德行,从而与人道相区别。显而易见,这里所凸现的是德而不是仁。再次,就仁的具体运用而言,简文中曾以六德配六位。如谓“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将仁固定为子对父的伦理准则。其实,简文的这一配位方式,并没有多少根据,而且降低了孔子思想当中仁所固有的理想高度,缩小了仁的博大内涵。
可以看出,郭店楚简中仁的地位并没有凸现出来,这是否意味着在那个时代,儒学别派对仁虽然重视,但将其作为儒学的核心这一原则却尚未固定下来?此外,孔子之后的儒家不再像孔子那样突出仁,因此,儒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了凝聚与感召的力量。这是否与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分化也存有某种关联?
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礼”的含义,同孔子有关思想基本一致。孔子曾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要求为政者以礼治国。郭店楚简继承了这一思想,谓:“尊仁,亲忠,敬壮,归礼,……君民者,治民复礼,民余害智”(《尊德义》)。简文倡导礼治,认为“为邦而不以礼,犹口之亡口也。非礼而民悦口,此小人矣。非伦而民服,世此乱矣”(《尊德义》),强调了以礼治国的重要性。不过,这种治国之礼,终究是外在的行为规范。相对于外在之礼,孔子业已转向内心寻找礼的内在根据,重视行礼时人的内心真实情感,所以他才发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的感慨。简文所说的礼,也体现了内心道德情感的因素,谓“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恭,不恭无礼”(《五行》),礼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的是出自内心的对于他人的礼貌之情。简文曾经明确指出“礼作于情”(《性自命出》),将礼与情联系起来,这可以看作是简文对于孔子礼学思想的发挥,标明礼已经完全内化。简文还谓“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性自命出》)。“浅泽”与“深泽”的区分,蕴含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笑是人之情感的外在的、浅层次的表现,内心的喜悦则为根本,它是外在之笑的支配者。简文将外在、表面的东西看作是浅层之礼,而将内在的、由衷的东西视为深层之礼,说明简文十分注重礼的内在依据。
与孔子思想相比较,简文关于礼的论述,其间最大的变化在于它对于礼仪、仪节之礼几乎没有涉及。孔子所生活的历史时期,尽管已经“礼崩乐坏”,但贵族间的礼仪并没有废弃,孔子对于各个社会等级间的礼仪,仍然十分重视。孔子与简文间礼之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时代使然。简文写定的时代下限(公元前300年)正值各国变法运动的尾声, 就是商缺变法也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之久,各国变法运动给宗法制和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以猛烈冲击,与宗法制和传统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各种礼仪也就无可挽回地凋落了。再从地域特征看,楚国历来对于春秋时期以鲁、晋、齐等北方诸侯国为主而形成的礼仪不感兴趣,这是否也是简文不出现关于仪节之礼的重要原因?
在考察了郭店楚简所反映的孔子思想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仁与礼——的变化情况以后,我们需要简略地分析一下在儒学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圣”的变迁情况。“圣”之有特殊地位,是因为在孔子所设计的伦理层中,“圣”实是空悬一格,孔子从不许人(甚至包括尧、舜)以“圣”,“圣”是最难企及的境界,“圣”不仅包括个体修身以至尽善尽美的因素,而且包括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从而普惠天下的意蕴。这样,只有那些为政治国者方可成“圣”,一般的修行君子可以达到仁的层次,但却无缘臻于“圣”的境界。换言之,可以说成“圣”的范围十分狭小。郭店楚简中出现许多关于“圣”的论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儒学的某些变化。
首先,简文将“圣”与天联系起来,谓“圣人智(知)而(天)道也……圣,知礼乐之所由生也”(《五行》),圣人体察天道而制定礼乐,显然这里蕴含了天人相通的意义。《成之闻之》篇还探讨关于“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的问题。显然,这在孔子思想中并不突出。其次,简文将“圣”赋于尧、舜,谓“尧舜之王,……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始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唐虞之道》)。简文的作者认为,尧舜尊贤而让贤,不以亲亲碍于尊贤,因此尧舜堪称圣人。这虽然与孔子思想大体相符,但孔子并未许尧舜以“圣”,而是说“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再者,简文中的“圣”已经不单纯是对于德行高尚者的称谓,而是衍变为道德范畴,与仁、智、义、忠、信等并列(见《六德》),《五行》篇还说:“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将“圣”也作为一种内心之德。是篇还谓“未尝闻君子道,谓之不聪;未尝见贤人,谓之不明;闻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谓之不圣。见贤人而不知其有德也,谓之不智;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隙隙,(注:简文中的这两个字不从阜而从虎,见于《广雅·释训》为叠语,与战战、栗栗等意同,释为“惧也”。简文此字今以隙代之。)圣也。……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这里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何以为“圣”的问题。认为凡是善于见贤思齐,且闻斯而行者便具备了“圣”德。简文以“圣”为道德概念,无疑将成“圣”的范围大大扩展,但相应的“圣”的高度则由此而降低。简文还更进一步将家内伦理中的父德规定为“圣”,谓“既生畜之,或从而教诲之,谓之圣。圣也者,父德也”(《六德》)。将父之德规定为“圣”,使“圣”的内涵有了萎缩之势。
综上所述,可以大致看出,郭店楚简时期儒家学派的思想当中,仁与圣二者较孔子所设定的意义,其高远性有所下降,内涵有所变化,而关于“礼”的概念则沿着孔子所提出的注重内心情感的轨迹继续发展。此外,郭店楚简所反映的儒学发展情况还表明,当时的儒家学派已经注意到了吸收其它学派思想以扩大儒学领域的问题。简文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孔子思想中多不详论的“命”、“时”、“性”、“天道”以及相关的“气”、“情”、“养生”、“养性”、“安命”等命题,时贤学者对此已多有讨论,故而这里不再多谈,我们只想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儒家对其学术主旨有所调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儒学的领域。
二
在孔子思想中,理想人格及修身途径问题是与义理观并重的内容,理想人格即是关于人格完善的问题,是高远的道德理想在人格中的具体体现,是信仰与实践、文章与操守的相融与统一。孔子对于理想人格的设定,可用“君子人格”一辞进行概括。
孔子对于“君子人格”的设定,其体系无比宏富,包括君子的日常行为规范、理想境界、理想主义精神等。前者诸如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就是对于君子修养行为的一种设定,不过,这类具体的行为设定是无限的,而且必定永远无限,因此睿智的孔夫子并不孜孜于在“君子人格”体系中将一切修身规范囊括殆尽,而是注目于高悬君子的理想目标,突出“君子人格”的最高境界,这个最高点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是君子最高的人生目标、理想的最终归宿,而一切具体的修身行为尽管无限,却只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但是,为了达到至高至远的人生境界,君子若只安于修身以完善自己的人格还不够,君子还必须具有一种理想精神,必须具备堪当大任的勇气和无比执拗的韧性。缺乏此种精神气象,高远的理想目标则只能无限遥远,最终成为虚空。君子所具有的这种为追求理想而百折不回的精神,正是孔子所关注的“君子人格”的内核所在。关于君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在他看来,君子专注于理想的追求,愈是窘困的环境愈激励起君子对于道德的执拗追求和对于客观环境超越的志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在“道”与日常生活之间,君子所忧虑的不是穷困而是理想追求不能完善。现实与理想之间可谓差距大矣,现实中的重重障壁,阻碍了君子理想目标的实现,而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恰恰具有内心的超越企向,因而表现出对理想追求的无畏精神以及对世事的通达。孔子认为,为了达到对于理想的追求应当不惜牺牲生命为代价,“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弟子曾子也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在安危紧要关头,君子宁可舍弃生命而不可使理想屈服于现实。其以道自任的大勇之气、虽死不悔的理想主义精神正是儒家思想中极具感召力的部分。
孔子关于君子人格的设定与其“仁”学有着一致性,从根本上说,仁是内心之德,体现着内在对于外在的超越志向,君子正是具有内在的超越志向,才表现出对于理想追求的无畏精神,换言之,内心具有仁德,必然表现为精神上的豪迈与创新不已。
郭店楚简中有关君子的论述数量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不少处特指在上位的君主。(注:简文于此的论述不少,如谓“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导之,其所在者内矣。君子之于教也,其道民也不浸,则其淳也弗深矣。”(《成之闻之》)又谓“故君子不贵庶物而贵与民有同也”(《成之闻之》),这里的君子均指在上位者。)关于道德君子的问题,简文也有不少论述,《五行》篇提出了“君子集大成”的说法,认为君子道德修养须尽善尽美,简文还探讨了何以成为君子的问题,谓:
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五行》)
简文认为君子在内心当中修养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于实践中而将其表现出来就堪称君子。关于君子的行为规则,简文又谓:
唯君子能好其匹,小人岂能好其匹?故君子之友也有向,其恶有方。(《缁衣》)
这里强调了君子心中能够做到道德自律,把握是非而使善恶泾渭分明。简文又谓:
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能口(差)池其羽,(注:“口池其羽”即《诗经·燕燕》之“差池其羽”,池前一字,简文从屈从走,与《诗经》对勘,当与差通假。差池为古连韵叠语,犹磋陀。《诗经》“差池其羽”,郑笺谓“张舒其尾翼”,故差池有开阖之意焉。《燕燕》一诗抒写别离之情,虽哀痛至深,但却能够“淑慎其身”,犹飞鸟之爱其羽而自珍自重,合乎儒家慎独之义,故简文引此为说。)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五行》)
简文这里所论与《礼记·大学》所云“君子慎其独也”如出一辙,体现着君子独处一隅时善于自律的精神。因而,简文中的“君子”,是道德各个层面的“集大成”者,显示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完美。此外,简文对于君子在追求理想时所显示的精神气质,也有论述,例如:
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五行》)
君子对于善的追求有始有终,而对于德的追求则永无止境。简文之意,显示出对于道德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简文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士有志于君子道谓之志士,善弗为亡近,德弗志不成”(《五行》),简文提出志士的概念,志者,“意也”(《广雅·释诂》),含有精神意向的因素,认为君子修习德行,必须具备坚定的精神理念。但是,对比而言,君子以道自任、堪当重任的精神气质在简文中并不多见,尤其是鲜有孔子关于君子不计成败利钝、不问安危荣辱而奋力直前的豪迈气慨。这可以说是简文关于君子人格论述的一个特点。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恐怕与当时人们普遍瞩目于“时”的观念有关。所谓“时”,《广雅·释言》谓“伺也”,以今语解之,便是时机、机遇、伺机。“时”的思想因素不能说在孔子思想中毫无闪现,因为他也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这样的话,流露出随遇而安的态度,不过纵观孔子一生,至为突出的还是他追求理想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与决心。简文多次探讨“时”,强调人们应当把握时机,反映了人们对于机遇的重视,也表现了当时儒家学派对于社会现实的洞察与透析。(注:郭店楚简多次提到“时”的重要,如谓“行之而时,德也”(《五行》),“圣以遇命,仁以逢时”(《唐虞之道》),“众强甚多不女(如)时”(《语丛》四)等。儒家强调“时”,即强调对于机遇的把握,这种思想变化值得注意。)然而应当看到,“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时,审时度势之心就会加重,而超越现实以追求理想的企向就会减弱,这在精神上就会表现出以道自任勇气的减退。此外,简文在这方面的特点,我们认为与其对于“仁”学的发挥不足也有关联。前文已经指出,仁与君子人格的设定息息相关,对于“仁”的立论深度直接影响了君子精神境界的高度。简文里面没有将“仁”从其它道德观念中凸现出来,未赋予“仁”以应有的思想高度,因而与之相关的君子大勇之气也就必然降低。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孔子在探讨“仁”的时候曾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这个论断中,刚、毅的规定使仁具有了坚强向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注:关于刚毅之义,《说文》谓:“刚,强断也。”段注:“有力而断之也”,即指强志不屈之义。毅,《说文》谓“有决也”,《左传》宣公二年谓“致果为毅”。总之,刚毅指品德的坚强与行为的果敢。),然而,郭店楚简却将仁引人了另外的道路,谓“匿,仁之方也;……柔,仁之方也”(注:匿本义为隐为藏,即《广雅·释诂》所释“藏也”“隐也”,孔子斥责“匿怨而友其人”(《论语·公冶长》)的做法;关于“柔”,意为弱,与刚义相对(见《广雅·释诂》)。孔子曾将“善柔”列为“损者三友”之一(见《论语·季氏》),朱熹谓“善柔”指“工于媚悦而不谅”(《论语集注》卷八)。简文将匿和柔都列为“仁之方”,显然与孔子思想相异。)(《五行》),简文认为含蓄、柔和就是仁,说明这一时期的儒家崇尚隐含的委婉的方式,从而与孔子、曾子所提倡的直言直行、义无反顾的精神有了不小的距离。
关于儒家学派一向所关注的如何抵达理想人格——亦即修身途径——的问题,简文之论也独具特色。诚如专家所论,郭店楚简在这方面实将儒家学派的“内转修习”的线索凸现出来了,简文重视修习心性,很可能源于这一时期儒家学派对于身与心、性与心关系的新认识。简文曰:“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诺,莫敢不诺;进,莫敢不进;后,莫敢不后;深,莫敢不深;浅,莫敢不浅”(《五行》),“凡人虽有性,心无奠志,……虽有性,心弗取不出”(《性自命出》)在这里简文探讨了心与身体各部器官及心与性的关系,认识到心是身体各部和性的中枢,起到更为根本的支配作用,由此而重视修习心性,强调“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五行》)应当就是逻辑的必然。关于简文的内在心性学说,前贤已论之甚详,这里不再赘言。总之,儒家学派自孔子始便重视修心,但孔子并未明确将其提出。简文关于心、性的论述表明,郭店楚简时期的儒家学派已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开启了孟子修心理论的门径。
儒家的理想人格,历来以“内圣外王”来概括,认为君子不仅成己也要成物;不仅立德于己,亦要立功于世。所谓“内圣”,概括地说就是通过心性修养,内在地抵达圣贤的境界。郭店楚简论述修身问题已经明确转向了内在修习心性的途径,只是其表述的君子人格缺乏孔子那种为理想而孜孜以求甚至不惜自我牺牲的理想主义精神,所以简文虽然也提倡内转修心,但修心之后成“圣”的高度却打了折扣。
三
郭店楚简所代表的儒学发展时代,诚如专家所论介乎“孔孟之间”。我们从上面的讨论中,约略可以看出孔孟之间儒发展变迁的情况。那么,郭店时代的儒学思想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处于何种地位,起到何种作用?现仅就本文所论的内容进行一些分析。
简文关于内省修心的阐述是思孟学派修身学说的基石,它凸现了孔子——孟子修心理论的思想线索。但就仁学理论及理想人格的阐述看,简文似乎并不代表儒家思想的主流。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究其底,它是人在道德面前的自觉性与主动性的体现,由此出发便会日益精进与创造;反之,则会一切流于昏昧忽失。同时,仁又是孔子思想中的至高境界,这种规定性愈强,与之相关的理想人格的品质便愈益伟岸。换言之,君子正是孔子所设定的“仁”德的具体体现。而这具有仁德的君子人格,经过历史的积淀,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基本观念和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为志士仁人人格理想的最终归宿。可以说君子人格的设定是孔子学说中极具魅力与活力的部分。之所以如此,不仅由于君子是兼具各种德行的善者,更是由于孔子赋予他理想主义的内核,从而使君子具有一种既便不容于世而仍然为追求理想百折不悔自我牺牲的无畏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昭示后人奋进不息的动力所在。
对于君子人格中所包含的不容于世的因素,孔子早有所悟,可是孔子并未因此降低君子精神境界的高度。所以当他被困于陈蔡之间而岌岌可危时,他仍然“讲诵弦歌不衰”,弟子们不得其解,他开导弟子道:“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向弟子询问自己的志向是否有误,子贡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他劝孔子将理想高度降低,以求容于世。孔子回答道:“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孔子强调君子肩任斯道的决心和守道不移的精神,远较见容于世为重要,故而他不肯降低自己的志向。弟子颜回推求孔子之意,发挥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不容然后见君子”正中肯綮,点明了儒家群体精神的伟大价值所在。这一精神更由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见称于世。“知”,表现了孔子的睿智及对于社会世事的洞察,所以孔子的躬行实践绝非不谙世事者的鲁莽与偏执,正由于如此,孔子那种堪当大任的豪迈气慨便愈益彰显。尽管当时和后人有谓孔子“迂”和“阔于事情”的评论,但倘若儒家学派消失了这种勇气和对于理想的无畏追求,那么儒学又用什么去感召世人?靠什么来防止曲学阿世、麻木不仁?又依什么来自别于其它学派?因此,我们认为君子精神境界的设定,于儒学中实占有特殊地位。郭店楚简的内容并没有将君子内涵中执仁立志的精神突出出来,因此,简文的君子之论不是对于儒学主流思想的发挥,而是一种流变。由此,我们也就感受到了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孟子正处于百家争鸣的兴盛阶段。从外部环境讲,各派思想均可能对孟子产生影响。从儒学内部传承讲,孔子之后儒家各派,如郭店楚简所代表的儒家流派也会对孟子有重大影响。因而,孟子思想中有许多概念,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并不多见,如“时”、“气”等,这些思想概念的出现有可能受道家影响(注:简文中出现了一些道家思想概念,道家的某些思想线索也时有所见,如谓“有是施小得有利,转而大有害者,有之;有是施小有害者,转而大有利者有之”(《尊德义》)即指明了大、小、利、害等的矛盾及双方的相互转换,这些都是道家所擅谈的内容。),但更有可能是儒家内部(如郭店楚简所代表的儒学流派)传承的结果,孟子的伟大之处即在于,他既将各种思潮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又突出了孔子仁学的大勇气象,孟子对于“气”这一概念的发挥即为典型。孔子很少谈气,然而郭店楚简中却有不少探讨。简文谓“节乎脂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正,安命而弗夭,养生而弗伤”(《唐虞之道》)。这里没有直接提到“养气“一辞,但却具备了养气的思想。孟子关于“气”的学说最著名的是其“养气”理论。他说:“夫志,气之帅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明确以“志”统“气”。将君子的宏远之志作为“气”的核心,关于这种浩然之气,孟子说:“其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有人询问“士何事”时,孟子回答以“尚志”,再问何谓“尚志”,孟子则回答说:“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孟子所说的“志”是君子以道自任而追求仁义的体现,而其“浩然之气”则代表了君子对于理想追求的大勇精神,其对于“气”的阐述,毫无神秘意味而多理想主义色彩。孟子也谈“时”的概念。他称孔子为“圣之时者”,谓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万章》下),以为孔子善于掌握时机,这显示出孟子对于“时”的重视。但是,孟子同时又规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强调顺从“时”变的过程中,君子固守理想的坚定性。孟子曾经总结出致胜的三个条件,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最终显示出对于人的精神的侧重。孟子还有对于“大勇”、“大丈夫之气”的论述,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种“大丈夫”的道德学说体现的是对于崇高和尊严的强烈感受,是不怕任何艰险而去完成自己使命的无畏精神,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君子才会自拔于流俗之外而成就其道德理想中的伟大人格。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郭店楚简所代表的儒学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简文关于“气”、“性”等的论述显示出异于孔子学说的思想发展倾向;其内转修身的理论也较孔子所论为精致;但是,由于对“仁”学把握得不够,对于君子精神高度的规定缺乏伟大之处,所以其思想发展中的缺失也是比较明显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学说的发展,从孔子以后到孟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孟子·滕文公》下)的阶段。到孟子之时,儒学思想的精华才正式形成博大体系而凝固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