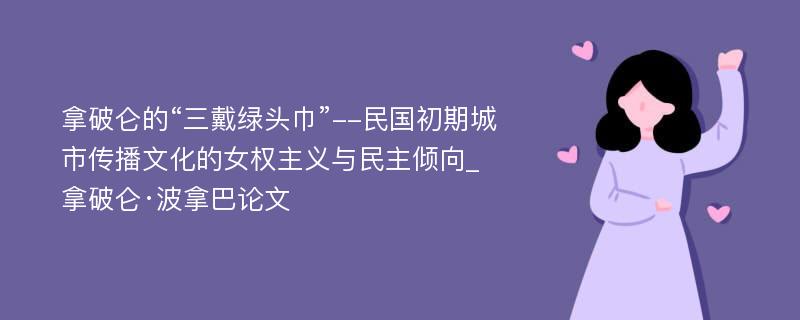
拿破仑“三戴绿头巾”——民国初期都市传播文化的女权与民主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拿破仑论文,女权论文,头巾论文,民国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3-0157-14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华盛顿和拿破仑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①,就这两人在中国的接受史而言,华盛顿则远不如拿破仑那么切入政治现实而充满主观想象,显得轰轰烈烈,光彩夺目。笔者曾在《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一文中论及②,自19世纪上半叶拿破仑生平事迹传入中土,伴随着法国革命的壮烈史诗和花都巴黎的浪漫传奇。尤其当皇朝末世、人心深受巨创之际,对于拿翁的英雄崇拜有增无已。然而1903年《绣像小说》连载洗红盦主的《泰西历史演义》,在描绘拿氏所向披靡、征战凯旋时运用了漫画化的戏谑手法,已有损英雄形象,特别写到滑铁卢战败,将拿翁比作楚霸王,尽渲染其愚蠢可笑之能事,体现了“反英雄”的通俗想象与欲望。
本文着重描述1910年代中期,在上海重又出现拿破仑传奇的传播热潮,而遍及小说、画报、影戏和戏剧。如包天笑主编的《小说时报》、徐枕亚的《小说丛报》、王钝根的《游戏杂志》与《礼拜六》及陈蝶仙的《中华小说界》与《女子世界》等,这些后来在30年代被左翼作家指斥为“鸳鸯蝴蝶派”的杂志,都加入了拿破仑文本的生产,不约而同地沿着大众文化“反英雄”的路向,对于拿氏盖世武功的“宏大叙事”兴味缺缺,而专注其私人生活,对他的婚姻家庭与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反映出多姿多彩的大众欲望与都市心态。从拿破仑东渐的翻译过程来看,这一阶段在文献的搜索方面,从“正史”之外的途径发掘逸史珍闻,波及大量文学资源,尽管真伪驳杂,雅俗兼备。在所发现介绍的传奇小说中,不乏佳作,为斑斓多彩的民初文坛锦上添花。
拿破仑是如何在其本土被通俗化的?他的文学传奇是如何进入中国的?翻译旅行中引起怎样的语言与风格的问题?对于这些饶有兴趣的问题,限于笔者能力与本文主题难以细究。这里拟从阅读史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尽管文本的选择与翻译有随机偶然性,但切入印刷文化的脉络时,受到政治土壤与市场气候的制约,也对大众接受心理与记忆构成新的时序。在民国初年“情”潮泛滥的思想背景里,拿破仑被通俗化意味着对“英雄”重新定义,首先将他还原为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也迎合了渐高渐涨的张扬女权的潮流,另一方面与袁世凯倒行逆施而引起的政治幻灭相关,借暴露或丑化拿翁隐私破除对于“伟人”的幻想,曲折表达出某种民主的意识与要求。这表明民国初期新兴的印刷传媒发挥从“革命”到“共和”的文化转型的功能,以都市日常情感的内容以及喜闻乐见的象征形式表达出万花筒般大众的欲望想象,同时民间印刷资本主义为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努力与当局政治势力保持距离而开拓其批评空间,尽管是有限的。展示这一民初大众传播颇富奇观的插曲,在全球文化价值迅速流通的今天,或许能带来某种观照与启示。
一、窥探“英雄”私生活
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刊出一幅拿破仑半身照相,从垂肩的流苏来看,身穿戎装,怀抱其爱子,即路易莎皇后所出。这也是梁启超所办的杂志首次刊登照片,借助日本的先进印刷技术,使国人见识“英雄”的尊容。拿破仑有儿子,不令人惊讶,而在当时却不寻常,因为很长一段时期里,流传的拿氏事迹一向局限在他的政治军事等公共事务方面,鲜有涉及其爱情、家庭等私生活。更有意味的是,次年也在他主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刊出另一幅照片,题为“拿破仑与普鲁士皇后会于的尔薛”,画的是拿破仑在1807年击败普鲁士与俄罗斯军队,在提尔西特(Tilsit)与两国元首缔结和约。原画为高斯(Nicolas Gosse,1787-1878)所画,今藏于凡尔赛宫,但《新小说》上刊登的却截取了原画的中间部分。拿破仑站在左边,也穿军服,身披绶带,从右肩斜盖至左腰,一手递给右边站着的普鲁士皇后,仿佛引她向左边走过去,中间是俄皇亚历山大。据史料说普鲁士皇后路易莎来到提尔西特,试图以她的姿色打动拿破仑,为丧权辱国的普鲁士赢得较好的和约条件,但拿氏不为所动。
刊登这两幅照相,给读者助兴,显得拿破仑有人情味,却为展示其私人空间开启了一道门缝。尤其《新小说》上那一幅,拿氏向普鲁士皇后投之以含情脉脉的目光,暗示其倜傥风流的一面。其时梁启超仍不倦宣传拿破仑,在《新民说》中推崇其“进取冒险”精神,说他原为“一小军队中一小将校”,却能“奋其功名心,征埃及,征义大利,席卷全欧,建大帝国”。③同时又鼓吹“小说界革命”,将拿破仑和华盛顿、释迦与孔子作为“新小说”应当表现的“英雄豪杰”。接着在1903年左右有数种拿破仑传问世,详略不一,为一种英雄崇拜的心态所笼罩。如罗大维的《拿破仑》译自日文,序言云:“呜呼!古今之英雄,孰不推拿破仑为第一?稍知学问者,无不震之于拿破仑之名。”④译者之顶礼膜拜溢于言表,书中始终颂扬拿氏的彪炳武功,几乎不涉及他的情感生活,讲到他与约瑟芬的结褵与婚变,都一笔带过。⑤却不料此后国人对拿氏的兴趣开始转移,这从林纾的翻译小说可见一斑。
凭林纾对政治与市场的灵敏嗅觉,早就注意到拿破仑文献,在推动拿氏传奇的公私转向方面也不遑多让。据他自白,甲午之后他打算翻译一部拿破仑传,以激励民族士气,但一念之差翻译了小仲马的《茶花女》。结果风靡一时,少男少女人手一册,但林纾觉得自己弃英雄而爱美人,于爱国不够虔诚,于是追悔不已。在“小说界革命”之后两三年里他不仅译了《拿破仑本纪》,还译了《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和《滑铁卢战血余腥记》,前者写拿氏在莱比锡惨败,后者有关他在滑铁卢的灭顶之灾。林纾觉得《拿破仑本纪》为“正史之体,必不能苛碎描写士卒冤穷之状,至可惜也”。因此他另辟蹊径,把目光转向野史别传或小说。看中《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因为“是中详叙拿破仑自墨斯科败后,募兵苦战利俾瑟,逮于滑铁卢。中间以老蹩约瑟为纲,参以其妻格西林之恋别,俄普奥瑞之合兵,法军之死战,兵间尺寸之事,无不周悉”。⑥在林纾看来如《拿破仑全传》、《拿破仑》之类也不外乎“正史之体”,而他别具只眼的取向更迎合了市场需求与一般读者的欲望。
1909年《图画日报》上“世界名人历史画”专栏连载拿破仑生平,从24号至52号共刊出29幅图画。值得注意的是,图画中出现两个女人,涉及拿破仑的婚姻和家族成员,给这部粗糙的通俗画传平添了些许浪漫的悲喜剧色彩。一图叙述拿氏军事上再传捷报,攻陷维也纳之后回到巴黎,“忽宣布与最爱之夫人约色印(即约瑟芬)离婚”。作者评论:“溯拿破仑此日之离婚之意,盖欲娶奥国之公主,以笃同盟之交,故于翌年娶皇女马里路易沙云。”⑦作者评论拿氏此举“盖即中国历代废后之污点也”,略示传统的春秋笔法。另一图是拿破仑之三妹波林,穿着曳地长裙,在海边与一位军人跳舞,旁边一群军人在围观。⑧该图讲的是拿破仑初次流放至厄尔巴岛,一年之后阴谋策划复辟。据说那日波林举行舞会,借以迷惑岛上的守军,在杯盘交错、舞兴犹浓之际,拿氏悄悄溜走。等到守兵发现,他已经进入巴黎凯旋门了。约瑟芬和路易丝在“小说界革命”十年里的拿破仑故事里,只是偶露身影,然而到1910年代,她们频频登台,成为拿氏罗曼史的要角。总之,《图画日报》使拿破仑通俗化,其事迹仍局限于历史文本的范围之内,且对于再现拿氏一生的公共性方面,从大众接受层面说,其正经形象大约也消费得差不多了。
小说界对于拿破仑的兴趣沉寂了数年,到民国初年又卷土重来,然而时过境迁,他的叙述和形象也物换星移,至此小说功能又一变,从国族共同体想象转化为都市文化与大众欲望的传播载体。此时大众急欲兑换革命对于自由的许诺,品尝幸福之果,在男女恋爱和婚姻问题上展开社会改革的愿景,都市成为思想交锋的前沿。一方面,西潮仍长驱直入,从自由恋爱观念、一夫一妻制到好莱坞软玉温香的影视产品,占领年轻一代与文化消费市场,男女平权和公开社交得到理论的支持,但另一方面政府腐败,法治幼稚,旧制度和旧习俗得到法律的保障,顽固的家长们掌握着财产和伦理的支配权,也掌握着他们子女的命运。因此追求自由常以悲剧告终,对幸福的欲望和渴念更伴随着眼泪。
一时间都市的文化形态呈现为情潮泛滥,由于改朝换代、国耻家恨而带来的心灵创伤、“悲剧”被认为具有高贵的文学价值,以及宣扬“物竞天择”的“天演论”带来对人的生物性的新认识等原因,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伤感情绪,徐枕亚《玉梨魂》之所以能畅销一时,也正在此。在1910年代中期小说杂志如雨后春笋,对这股情潮推波助澜。有关自由恋爱的衷情和伤感固然是其主潮,但杂志勃兴本身受赐于为民国所许诺的出版自由,且担负起调节都市日常欲望的复杂功能。翻开当日某报纸的广告栏,城市和人心的每个角落无不关情。《花月尺牍》提供情书样本,鼓励公开社交;《情海指南》不乏道德的开导训诫,而《荡妇秘史》则不无诲淫之嫌。又如《男女交合新论》鼓吹房事卫生、生产“强种”的国民;而“专治花柳病”的广告保证妙手回春。其中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工程要是将女子培养成健康的“国民之母”,随着工业化所造成的城乡人口和家庭结构的改变,女子走上社会成为瞩目的趋势,城市也随着她们的身影和欲望而跃动。
在这样的情海波涛中,拿破仑成为小说杂志的一个卖点。他表现为激情奔放,风流成性,或机智绝伦,仁爱为怀,其形象多元可塑,却体现了日常生活的瞬息万变、芸芸众生的价值观念。他成为都市欲望的棱镜,受到大众传播的操纵,更为复杂的是,在满足大众对伟人的窥视欲,包括对他的“三戴绿头巾”之类的嘲弄当中,多少还与袁世凯扯上瓜葛。
关于拿破仑的恋爱婚姻史,被关注的首先是约瑟芬。早在1902年史子彬的《欧洲第一雄主传》中,介绍了他们两人最初如何相识:
又有一嫠妇为贵家妇,名乔西非你氏,年二十八,仪容美丽。其夫为爵绅,被害于乱民。妇亦被乱民禁监,受尽诸苦。妇生子女各一,家产甚丰。拿波仑禁藏军器,令出惟行。妇夫有宝剑,亦被收去。妇之儿年十二,胆识兼优,谒见拿波仑,乞还其父之宝剑。拿波仑嘉其志与己同,命人取剑,亲手与之。儿喜极,以致流泪,叩谢而归。拿波仑以为有此佳儿,必有贤母。意欲访之,适乔西非你氏知拿波仑之爱其子,特乘马车以道谢之。妇人以其子之故,甚德之,似欲出涕。拿波仑不忍,亦于数日后造其居以慰问。时拿波仑年二十六岁,妇虽长二年,然其仪容之美不啻如少女,故拿波仑甚爱之。尔时法国无王,有五人治理国政。五人中有名排而司者,熟识此妇,力劝拿波仑娶为妻,亦劝妇人理应琵琶别抱,西律亦然。妇尚沉吟,排而司又劝之曰:“尔若再嫁此人,则我必荣其驻意大利军之主帅。”妇允之。一千九百九十六年三月初六,二人成婚。⑨
“乔西非你”即约瑟芬。这段叙述是可信的,如果把脍炙人口的路德维希的《拿破仑传》拿来参照,可发现有趣的相似,只是没提巴拉斯(即排而司)实际上是约瑟芬的情人。⑩《欧洲第一雄主传》以石印本出版,薄薄一册,据作者序言,写此书是鉴于“现今考试与昔迥殊,所出之题实学为多,策论泰西经史圣君良相得力振兴,在所不免”,因此要给“应试之士”输送“西史”知识。然而如此详细叙述拿破仑初交约瑟芬,似乎不那么实用。
1914年《香艳杂志》创刊号上有周槃的“历史小说”《约瑟芬》,叙述她与拿氏始末,较为简略而平板。说拿破仑尚未发迹时,对新寡的约瑟芬一见钟情,成婚后,“伉俪之笃,有甚于画眉者。拿破仑苟临阵有暇,必作书报约瑟芬,故青鸟鸾音,不绝于道”。当时的小说常常夹杂古文典故,如“画眉”、“青鸟”等。后来说到拿破仑“以国际上之权宜,与奥国公主玛丽鲁意萨订婚,而与约瑟芬离婚。怜新弃旧,置糟糠之情而不顾,拿破仑其不近人情者乎?”这篇小说把拿破仑写成一个薄情郎,另一方面称赞约瑟芬“诚多情之女子”,对拿破仑始终如一,即使他流放至厄尔巴岛时,她致书说:“妾始终爱君之素心,不因地时而稍易也。”(11)同年在《小说丛报》上刊出《拿破仑之艳史》,属另一种较近真实的拿破仑与约瑟芬(译文作“徐世宾”)的版本,远较详细,译笔也是文言,富有情感。在小说里,这两人是英雄美人的典范,所谓“百万军中,温柔乡里,堪称双绝”。拿氏既是军事天才,在情场上也热情澎湃。虽然英雄毕竟有负佳人,“拿氏儿女之情与夫立功之念,未尝一日去怀,然其爱情虽挚,究未敌勃勃之野心”。但小说刻意突出了一个情感真挚的拿破仑:“拿氏督军马上,殆无片刻之暇,而与徐世宾之书,殆无一日断绝。盖拿氏爱徐世宾之心,久而弥笃……可见英雄爱情之深。”
按照史家一般的说法,约瑟芬喜好奢华逸乐,嫁与拿破仑之后不久,就另觅新欢。拿氏也很快发现了她并不爱他,于是两人之间产生了裂隙。这部小说里的两人关系不像周槃所写的那么白璧无瑕,当写到拿氏出征埃及时,就开始怀疑她的不贞,但也没有明说她是否背叛拿破仑,而是说有人在他面前“谮言”挑拨,使他陷入痛苦。他责备约瑟芬,却马上反悔。类似这样的情节反反复复,拿氏想离婚,又同她和好如初。这个小说拿破仑热情温柔,儿女情长,最后同约瑟芬离婚,因为她不能生育,实在是万不得已,为了帝国的利益,使她成为“野心”的牺牲。小说仍表现了理想化的爱情,即使他们离婚后,仍心心相印,说拿破仑即使在进军莫斯科途中:
此当军书旁午之际,拿氏爱念旧妻之情,未尝片刻去怀,问候之书,络绎于道。枪林弹雨之中,而甜蜜之情书,较前转增数倍。拿氏为世界英雄,虽一思忽为狂风所撼,而其心愈益柔和。出其大智大勇,以寡击众,以弱敌强,纵战祸迫于眉睫,徐世宾苟有书来,即数语寥寥,亦加玩味,决不因军务之匆遽,而止其爱情之进行也。(12)
小说里的约瑟芬一往情深,而凸显了拿破仑的英武而多情的人君形象。在刻画她的美貌时,译者亦不吝笔墨,诉诸传统诗文的丽藻艳辞。这篇译作落入江山美人的窠臼,但美人倾国倾城,却甘愿为民族大义而贬入冷宫。民初期间对约瑟芬的描写大多抱同情态度,尤其是被迫离婚而对拿氏颇多始乱终弃的谴责。最极端的大约莫过于1913年《民权报》上一篇为约瑟芬忌日而作的短文,说拿破仑失势之后,皇后路易莎弃拿氏不顾,他遂深悔自己薄幸而写信给约瑟芬,其时她在病中,得信而悲痛不已,忧愤而死。临死大呼拿破仑之名,并祝愿法兰西永久安宁。有意思的是该文作者称赞约瑟芬是个多情而爱国的女子,而“拿破仑不能爱此女子,安能爱法兰西?夫英雄儿女,本为一事,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拿破仑负徐世宾,路伊赛负拿破仑,拿破仑帝业之所以失败,也正在此”。(13)当时《民权报》对于袁世凯的揭露和抨击不遗余力,这里是否有所影射不得而知,但要说的道理是,不忠于爱情,就谈不上爱国,更遑论富国强兵,也是民初重“情”思潮的表现。
二、拿破仑遭遇奇女子
1912年,以唐群英为首的妇女团体在参政与选举等方面要求“男女平权”,向国会递呈请愿书,女权运动一度高涨。是年在英美等地也发生妇女运动,《神州画报》把“中国女界之请愿国会”与“英国女界要求选举”相提并论(14),《妇女时报》上《泰晤士河畔妇女要求参政之怒潮》的文章(15),也遥相呼应。唐群英等人的国会请愿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拒绝,却标志着女权的觉醒。
1914年间都市杂志如雨后春笋,如《眉语》、《莺花杂志》、《香艳杂志》、《女子世界》等看似鸳鸯蝴蝶情话绵绵,在同类杂志中较具女性取向。《香艳杂志》上周槃的《美人与国家之关系》一文(16),说历史由“英雄儿女”所造就,其故事为大众喜闻乐见,这些属老生常谈,却特别举出拿破仑不可一世,偏偏有几位“弱女子”敢与之抗衡。一位是普鲁士皇后路易莎,即上文提到的1807年拿破仑战胜普鲁士之役中,她“驰骋于药云弹雨之中,身先士卒”,与普军一起作战。普军战败后,她又不卑不亢从中斡旋,使拿翁“以盖世之英雄不得不屈服于石榴裙下”,同意签和约于提尔西特。还有玛丽·路易丝,因她肯下嫁拿破仑,使奥地利免于并吞的厄运。其实货真价实敢于与拿破仑“抗衡”的却是另一位,即法国文学史上名声籍甚的斯蒂尔夫人(Madame de Staёl,1766-1817)。周槃描写她“往见拿破仑,转其如簧之舌,侃侃而谈,语虽强项,而逸韵曼声,气似兰香,舌如莲粲,殊令人心醉神往不置”。她与拿破仑政见不合,把他比作罗伯斯庇尔式的暴君,后来遭到流放,“然斯特尔反对之言,仍为国人所重,即以擅作威福、炙手可热之拿破仑亦为之侧目,不敢有所加害”。那时在有识之士看来,袁世凯已是“擅作威福、炙手可热”,周槃这篇文章是否有所影射另当别论,而对于反抗强权的“弱女子”加以赞扬,与当时女权运动亦步亦趋。对拿破仑的负面评价,如谴责他穷兵黩武之类,并不新鲜,然而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拿破仑变成一个可塑的指符、多种欲望的载体,正显出现代都市文化的无厘头特征。无独有偶,在1914年《礼拜六》上周瘦鹃的短篇小说《无可奈何花落去》(17),原作者即斯蒂尔。周氏作小传说她生平崇尚自由,当法国大革命演变为恐怖政治,她著述抨击,后来因为反对拿破仑而遭到放逐,在英国期间:
又著《退去之十年》一书,力诋拿破仑不遗余力。及拿被放于爱尔巴岛,乃买棹归巴黎,于政治上多所尽力。翌年,拿卷土重来,使使者告夫人曰:“今后予欲制定宪法,愿夫人助吾一臂。”夫人箕踞而答曰:“陛下于十年以前,岂非无我,又无宪法,而欲治天下耶?今奈何需我?”竟不应。
这样热情赞扬斯蒂尔夫人的自由和独立,比照之中拿破仑的形象就显得猥琐可笑。同样以《铁血皇后》为题,周氏以悲情激越的笔调描写普鲁士皇后路易莎在提尔西特和约前后,与军民同仇敌忾,奋身疆场。又写到为了拯救祖国,她不得已来到提尔西特,与拿破仑当面交涉。当拿翁走近握着她的手时:
皇后却立叱曰:“咄!大王近日召我至此,为两国大事耶?抑欲凌辱弱女子耶?大王幸勿轻视亡国之人,以为可随我所欲。须知我路易设固非易惹者,三尺白刃,碧血足以溅之袖,莫谓娘子军不足畏也。”四座闻言皆变色,拿破仑遂亦默然归座。(18)
皇后大义凛然,拿破仑则自讨没趣。这篇数千字短文,周氏说是根据美国某作家“八九万字”的原作简写而成,不论与史实合乎程度,既在《妇女时报》与《女子世界》上发表(19),也会考虑到杂志的读者对象,其有意提倡女子的爱国精神,拿破仑就成了冤大头。
以上那些女子限于拿破仑的家属或仇敌,实际上对他的私情窥视涉及他与形形色色的女子的情爱纠葛。如1915年底《小说新报》上《欧洲伟人之情史》说“拿帝生平情史,颇有足观”,由是历数其早年艳遇,形象颇为可笑,所谓“世间之求婚者多矣,未有如拿破仑之离奇者。其对情人,有时若畜牲,蛮不讲理;有时则又甚平和,出以柔婉旗旎。有数妇人曾与拿破仑相交者,恒称之为怪物,为情界之专制魔王”。(20)他是情场老手,惯于惹花拈草,然而在许多故事里,令人瞩目的是那些传奇式女子。她们或出现在战场附近的旅馆、或潜藏在深宫密室、穷乡僻壤,有的落入他的情网,有的成为他的雠敌,无不美艳动人,智勇决绝。她们大多不是法国人,因此当与她们背后的民族或政治力量纠缠在一起,给情节增添紧张感,使国际权力斗争的背景更为复杂。并非偶然的是,她们成为民国初年都市印刷文化的宠爱,与当时女权的张扬息息相关。在这样的境遇里,拿破仑作为一种现代男权的指符,通过这些译作带来了资产阶级对待妇女、婚姻和爱情的态度与伦理观念。
1914年的《中华小说界》刊出二幕剧本《拿破仑》,译者徐卓呆说在欧美颇多搬演拿氏的戏剧,此从某旧杂志译出。(21)写的是拿氏远征俄国失败,在莫斯科在遭遇大火,溃不成军,波兰女子滑斯凯(即曼丽·华勒斯加,Marie Walewska,1786-1817)携其儿子亚历山大前来看他。侍官裘洛克提醒拿破仑,这是他六年前的情妇,怀中即是他的亲骨肉。于是拿氏想起当年行军经过华沙时,被大群波兰村民包围,把他当做解放者来欢迎。其中一个少女美丽出众,尤其是一双明亮的眼睛,使拿氏迷恋,这就是瓦莱夫斯卡。拿破仑即展开对她的追求,其热烈之程度决不下于当年对约瑟芬的痴情。
在拿破仑的情妇中,数华勒斯加最为美丽、对拿氏亦最忠贞不贰,且由于她背后卷入波兰民族复国的政治势力,使他们之间的恋情呈现更为悲壮复杂的色彩,因此亦最为史家所乐道。这个剧本先以莫斯科大火为场景,即正当拿破仑在命途挫败之际,华勒斯加不顾一切前来看他,传奇性地突出了她的一片痴心,而剧本所表现的拿氏对她的健忘,已隐含他的寡情。这一点在第二幕更为明显。拿破仑放逐厄尔巴岛时,华勒斯加又带着亚历山大来,当侍官说:“夫人从巴黎来”,拿氏大喜过望,以为是他日夜盼望的路易莎皇后及其爱子。其实他还蒙在鼓里,路易莎不但不愿同他做患难夫妻,且在巴黎已另有情夫。华勒斯加要求留在岛上,拿氏不允,表示他不能辜负皇后。剧本借裘洛克之口,责备拿氏仍一意轻信皇后而亏待华勒斯加。
在润甫翻译的《拿破仑轶事》中,玛丽·格兰是另一类奇女子。这篇“侠义短篇”根据法国麦良巴威的原著,在1917年《小说丛报》上刊登。讲的是当年拿破仑的军校佛克休,在战争中成为残疾,双目失明,晚景凄凉,由其侄女玛丽·格兰服侍。一日皇帝与约瑟芬皇后驾幸他们住的小镇,见到佛克休,发现他容衰体羸,衣衫褴褛,却口口声声颂扬皇帝恩德,说他安度晚年,全靠皇帝恩赐养老金,而身上穿的中尉品阶的制服,乃因为他的侄女上书,使皇帝追念其旧功而特意赐赏的。拿破仑听了大怒,指责玛丽谎骗老人,她却侃侃而言:
谎言之罪,我甘承之。然陛下试思之,如佛克休之事陛下,若何忠勇,驱驰效命,至丧其足盲其目而不悔,陛下乃浑忘之。少赖其力,老弃其身,致彼困苦颠连而无可告诉,是何陛下之忍心也。我怜其老病,思有以慰藉之。诡称列词上诉,陛下笃念旧勋,赉以品服,赐以中尉之衔。彼行动不自由,两目又无睹,不知我言之虚谬也。于是老怀顿慰,时时念陛下之德勿忘。所谓养老金者,我日夜从事针黹,藉十指之劳以博之,谬托陛下之恩,以慰老人之心者也。我固虚妄,陛下亦寡恩,奈何不自知而反以罪我也?(22)
拿氏听了,深自责备,当即认错。这是个优秀的短篇,叙述简洁,结构巧妙,立意亦深远。前面写佛克休听到拿破仑将莅临,兴奋不已,与玛丽之间的对白和动作围绕着虚假的中尉制服,表现出老兵的急躁怀疑,以及她的忧虑恐惧,其间已设置悬念。而写到这一段玛丽的自陈和数落,真相大白,揭露中蕴含辛酸和悲愤,同情和崇高。这里情节忽起波澜,她的反问具震撼感,映照前面皇帝在小镇受到欢迎,童男童女挥舞花球,歌功颂德的情景,亦含出色的讽刺之意。当拿破仑厉声责问玛丽时,作者写道:“玛丽至此,其容肃然,前时暂栗之色,消归乌有,侃侃而言。”由是戏剧性地刻画了她的勇敢和自信。此刻小说更有惊人之笔,而带入高潮。玛丽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她真名娜亚,就是当初在巴黎行刺拿破仑不遂而逃亡的刺客,说完后她表示甘愿就捕。但小说的结局是:
拿破仑闻言,沉思良久,曰:“姑娘之所为,气谊殊足感人。第自今以往,姑娘尚欲枪击我乎?”娜亚曰:“我将视陛下之所为若何。”
拿破仑曰:“我知姑娘之用心矣。佛克休我旧部也,姑娘其为我善视之。”言已,竟赐佛克休以中尉衔,加以品服,并赐娜亚以细纱,遂行。越数年,拿破仑败,幽于荒岛。娜亚闻之,曰:“猛虎去矣,欧洲之民,其可以安枕而卧矣。”
这个结束意味深长,拿氏固然光明磊落,不失其伟人人格,但更令人骄傲的是娜亚,她挑战皇权,拥有平民的正义,当她发出最后的微笑,遂引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英雄?当初梁启超所始料不及的是,在这类拿破仑故事里,他心目中的英雄反而相形见绌,却成为被批评抗争的对象,且对他的大男中心不无讽刺的是这些新式的女英雄成为小说“群治”的重要机制。
1912年《小说时报》刊出剧本《拿破仑》,写拿破仑败于一位女间谍手下。该剧译自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的The Man of Destiny,被认为萧氏名作之一。译者陈景韩推荐说:“是剧现时当行出色之佳者,新剧家宜注意之。”(23)的确就剧中的拿氏形象而言,其细腻和生动的戏剧化程度,可谓冠绝一时,虽然这个文言译本未能充分传达其对白的神韵。这是个独幕剧,写拿氏在1796年出征意大利途中驻扎于某旅舍,与一个女间谍遭遇,互相展开了一场心理战。在他设法从这个女子那里夺回被窃的情报过程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的狡黠性格和内心的复杂冲突。当女间谍暗示他在被窃的文件中,有一封他的新婚之妻约瑟芬给法国执政官巴拉斯的情书时,他故作镇静,继而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决定不读这封信,对约瑟芬和巴拉斯之间的奸情佯装不知。
萧氏此剧明显带有取悦英国读者的目的,不仅暴露拿破仑的隐私,且挖掘其卑鄙的动机,如在剧本开场白中明白交代的:“他最近被晋升为大将军,部分靠他利用他的妻子去勾引执政官。”(24)这个执政官不是别人,就是在剧本里的巴拉斯。(然而在中译里,包含这句关键性提示的段落却没有译出来,(25)这显然不利于读者对剧本主旨的理解。)确实在拿破仑史传中,他和约瑟芬的不谐婚姻本来就足资谈助,尤其是他初征意大利期间,约瑟芬凭种种借口滞留巴黎,以致拿氏——由他连珠炮似的一封封战地情书见证——寝食不甘,要死要活,更为史家渲染。约瑟芬原为巴拉斯的情妇,但此时使她陷入热恋的是年轻中尉伊波利特·夏尔。(26)萧氏此剧集中表现拿氏利用约瑟芬而达到其个人野心,当然对这个伟人来说,极不光彩,这或许正表现了萧氏尖锐刻薄的风格。
在剧本里,戏份更多的是那个无名女间谍。为了不让拿氏从她身上夺回秘密文件,她欲擒故纵,忽而撒娇施美人计,忽而凛然不可犯,然而当她终于将文件交于拿破仑之后,又一步步暗示其中有约瑟芬给巴拉斯的情书,使他陷于尴尬的境地。她仿佛洞见拿氏的内心,在一旁冷眼观察,对他的狼狈相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盖世英雄却被操纵于纤指之间。但是另一方面,对拿破仑的戏剧化表现突出了他的丰富复杂的性格,从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英雄。他一眼就识破她的间谍身份,且不中她的美人计,最终使她乖乖交出文件,仍不失君子风范。当他表示敬重她的人格,但仍希望她交出文件时,女子说:“你重我,决非真心重我,实是重你要得的东西。”拿破仑说:
不是。我要得的东西,不久便得,何劳我重?我且问你,设或有人,以爱你之美,敬你之勇,转以爱我敬我,而我愧勿如。设或我竟别无他物,但为情故,令我手足被阻,致不能得我欲得之一纸。设或我之地位,已能得此夺自敌人之物,乃仍踌躇,至于空手而返。更有甚者,强作慷慨英雄的态度,掩饰胸中的懦怯,使人不敢以强暴手段相加。我若如此,如你妇人之心,得勿藐视我么?(27)
在剧本里,这一段说白极其有趣,充分表现了拿氏巧于辞令、刚柔兼得的性格。1915年在《大中华杂志》上的小说《拿破仑之情网》叙述拿破仑称帝之后,旧时皇党与外国势力阴谋暗杀拿氏,使用美人计打入宫廷,而巴黎警察机关棋高一着,使拿氏幸免于难。其中历史事件和人物叙来似乎凿凿有据,其实是大胆虚构想象,属于通俗畅销读物。精彩之处在于场面恢宏,情节曲折,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女主人公吕须儿,被荐入法皇宫廷,成为约瑟芬的侍讲员,拿氏一见倾心,为她另置金屋,密室欢晤。其实吕须儿一向是英国间谍,此番受皇党指使,身负重任,而拿氏果然堕入情网。这里写拿氏:
拿破仑固非溺于声色者,然亦非寡情之主。虽不若法兰西前王佛朗塞亚一世、亨利四世、路易十四世、路易十五世之恣情纵欲,然亦不能如路易十三世、路易十六世之耽静好道。虽不征艳选美,然亦多情好色之人也。约瑟芬外尚有两人,为拿破仑所眷。此威震全欧之雄主,所缠绵于胸中者,惟此三人耳。……帝年方盛,精力又强,战无不胜,功无不取,遂登帝位……功亦崇矣,业亦广矣,而约瑟芬年已半老,色衰爱弛,原欲征求一二美人,以娱英雄垂暮,故宫中之女伶、侍讲员及侍女,苟貌美而性情和柔易与,皆足以当皇帝片时之眷恋。盖军务倥偬,帝实无暇与性情高抗者相周旋也。且皇帝为郭思岛产,故性情飘忽,类意大利人。其用情也亦然,当其炽时,有若水沸,及其息歇,烟消云散矣。(28)
这一段说拿破仑乃“多情好色之人”,揭开了他的宫闱秘幕,比起他与约瑟芬之间英雄美人的理想化叙述模式,似接近一个更为真实的拿破仑,而他的性格表现也更为复杂。帝王大凡好色,不光在法国,在中国的帝王图谱里,更令人想起三宫六院,荒淫君主恣情纵欲,但拿氏的“义大利”类型带来某些新鲜感。他更像个急色之徒“无暇”谈情说爱,女人似成为他的泄欲之具。但尽管他“性情飘忽”,却也情有所专,虽然在拿氏传记里,情人不止两个。不论他是好色抑是真爱,在其帝国兴衰及英雄生涯里,女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中国美人们两样,既非“贤淑”典范,亦不止倾城覆国,跳出了“女人是祸水”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窠臼,而在传达拿氏的帝国版图与其对美女的欲望同时扩张这一点上,蕴含着对男子利比多的首肯(所谓“郭思岛产”语中含有地理与人种特性的讯息),这对民国初期兴起的基于生物性的“强种”话语有一致之处。
作为畅销小说,《拿破仑之情网》中有关性爱的细节描写较为露骨,这在历史文本中难以见到。当拿破仑与吕须儿初晤于藏娇之密室,拿氏挑逗道:
“……当汝出外闲游时,曾遇貌英秀而体妩妩之少年,对汝巧笑,当是时能无怦然有动于心乎?”帝语时渐以手加女郎胸,女郎亦不拒,惟答之曰:“臣永未遇此类事。”曰:“设有人以柔媚之声语汝曰:‘I love you’(吾爱汝)……吕须儿,汝将何以答之?”曰:“陛下乎,臣实不知所答。”帝是时觉女郎情动。夫拿破仑非长于媚术者,其对妇人亦不能絮絮作软语。彼之爱情,犹彼之战术也,贵神速而恶缓进。今见女郎情动,即急起乘之,语之曰:“朕苟语汝曰吾爱汝,汝将何以答吾?”女郎娇羞无以自持,曰:“陛下乎,陛下乎。”皇帝曰:“朕实爱汝。……朕一见汝,情丝即缠缚吾身,吕须儿……吕须儿……”遂搂女郎亲其吻。帝是时情不自禁,遂定情也。(29)
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有绿林好汉、皇党魁首、警察头子、贵族子弟等,无不栩栩生动,由法国革命种下爱恨之情,为新旧帝国的生存与复辟皆舍生忘死。尤其是小说情节头绪纷繁,密线穿插,巧于构思。在叙述吕须儿与拿破仑密约时,又写她在宫中重逢拿氏的近卫军尉士勃直尔,于是小说倒叙他们过去的一段恋情,而她将尉士引入密室,企图利用她暗杀拿破仑。中译本称为“侦探小说”,所谓“侦探”指的是贵族后裔罗鉴,其父在大革命中被皇党所害,为了报仇,他成为员警部的密探。小说的另一条主要线索就是写罗鉴不畏艰险,终于探知吕须儿的间谍身份及皇党阴谋。他与员警机关密切配合,掌握事态进展,精心布置,在关键时刻他出现在现场,使拿氏脱险。当勃直尔明白自己险些成为杀害皇帝的凶手,在愤恨之余,枪杀了吕须儿。此后他一直耿耿于怀,为了表现忠诚,在某战役中英勇捐躯,死时高呼:“皇帝万岁!”
有趣的是《大中华杂志》的主编是梁启超,在1915年初他在《告小说家》一文中严斥小说界的堕落,这篇《拿破仑之情网》正含有他所指斥的“侦探”、“艳情”的内容,这对梁氏似不无讽刺。另外在连载《拿破仑之情网》之前,曾刊出吴贯因《英雄与社会》一文,鼓吹中国社会需要英雄,并热情歌颂拿破仑:“问大革命之后,法国何以能使国势之勃兴,则皆大英雄拿破仑之赐也!”(30)这也使人想起梁启超十余年前的论调,其时吴贯因与康梁等立宪党主张“主权在国”,(31)但吊诡的是此时的中国拿破仑却落在袁世凯身上。
三、周瘦鹃的“拿来主义”
要特别举出的是周瘦鹃,一个地道的拿破仑迷。不光在这一时期编写与传播的深广度方面,无人能与之比肩,他更取一种“拿来主义”,把拿氏挪用到中国场景,体现了文化生产的操纵性,直接与大众欲望扣连起来。
周氏擅长翻译,对于拿破仑事迹尤具兴味,他自述:“予生平崇拜英雄,独数拿翁……余佩之既深,凡关于渠之轶事,搜罗亦富,得暇则译之。”(32)的确,从1912年到1915年数年间,他所发表的有关拿破仑的包括《科西嘉童子》、《六年中之拿破仑》、《铁血皇后》、《拿破仑之友》、《情场之拿破仑》、《拿破仑之子》、《香梦》、《何等英雄》、《多情之拿破仑与爱国之波兰女子》、《同归于尽》、《忠魂》等。即使在20年代,他仍乐此不疲,有关拿氏的著译大多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如果说,作为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化指符,“拿破仑”的中土之旅也颇挟持着某种文化“霸权”,那么如此热情绍介拿氏,显然给民初时期的自由情潮如虎添翼。而在他们中间,周瘦鹃更是个急先锋,从他写的《拿破仑之五百二十万吻》一文可见一斑。(33)当然,这样的热烈鼓吹现在看来夸张而可笑,所谓“五百二十万吻”,是作者将拿氏给约瑟芬情书中表达“吻”的次数加起来,遂称拿氏为“接吻之雄”。
在民国初年的都市杂志文化中,商品化的情的话语主导了文化生产过程,与共和政体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尤其在自由恋爱方面涉及如何对待西潮影响的问题,在不同的杂志与文人集团之间出现文化取向上的不同分野。在年青一代中男女公开社交、西式结婚等成为风尚时,守旧人士忧心忡忡,恐怕这不光危及现存伦理秩序,且传统文化根基也为之动摇。徐枕亚为首的《小说丛报》就采取这种文化姿态,尽管也谴责专制包办婚姻,但对于婚姻自主则持抑止态度。比方像男女“接吻”这一舶来品,在他们看来是一件严重的事,是不值得提倡鼓励的。与之相比,包天笑的《小说时报》以及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主办的畅销周刊《礼拜六》显然要主动、开放得多。在这意义上称他们是建设现代都市文化的先驱者也不为过。
另一方面,周瘦鹃把拿氏与浪漫主义传统相联系,这种理解较他的同仁们更深入一层。其实在欧洲拿破仑被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仅是他继承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也因他才情横溢,文采斐然之故。周曾作《情场之拿破仑》一文,副标题是“英国大诗人摆伦之情史”,即把拿破仑同拜伦相提并论。(34)另在1914年出版的《香艳丛话》中一则诗话说:
胎孕十九世纪者有二豪杰,曰卢骚,曰拿破仑。二杰固皆翩翩美男子也。西俗宴会,必士女杂坐,芳泽交错,钗光钿影,粉痕脂香,俱足荡人心魂。每值卢、拿在座,则群姝之盈盈秋波,争集其身矣。(35)
尽管不合历史,不无惊奇的是周氏那种把拿氏与那些欧洲浪漫派文士并列的倾向。他一再鼓吹拿氏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在1915年他就翻译了拿破仑的短篇小说《同归于尽》,在《礼拜六》上刊出。介绍拿氏于“横戈跃马以外,复能操觚为文”,说他早年即“痛心疾首,发愤著书”,并为他至今“文名乃寂然”而抱不平。(36)在1922年,周更在他的《紫兰花片》杂志上发表《小说家的拿破仑》,详细报道了最近发现的拿氏文稿。(37)
周氏的拿破仑文本生产几乎称霸于当时的文学杂志工业,成为一个探索民初都市大众传媒的运作与性质的有趣的文化现象。尽管内容上极其庞杂,但兼顾教育与娱乐,仍有一定的选择,被纳入传统“情教”的架构之中。一方面继续搜寻拿翁私人领域的方向,揭示了更多的宫廷秘事,暴露了更多的情人,表现了他的不羁的热情和超人的才智,但与当时其他杂志更热衷于拿氏的风流好色形象不同的是,周氏并未忽视其作为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正面“英雄”,即一个“仁君”的形象,但这一正面形象是经过他的多情层面的过滤,甚或透过他的风月之镜反映出来的。在周氏的表现中,拿破仑呈现为多重人格,满足瞬息变化的都市文化市场的需要和大众趣味的选择。他更体现为一种随意可塑的指符,大部分文本出自周氏的编译,干脆不指明资料的出处来源。
在反映拿破仑为“情场之雄”方面,《香梦》别具一格,属于“奇幻”(fantasy)文类,不明其翻译出处。(38)小说写英国姑娘莎绯霞去巴黎探望朋友,在一座豪宅里看见墙上所挂的拿破仑像,于是梦见与约瑟芬离婚不久的拿氏,向她求婚,正当两情融融之时,却闯入拿氏兄弟和约瑟芬的儿子,力劝他与奥国联姻,不应以一己私情而不顾民族利益。拿氏终于醒悟,向莎绯霞道歉,含恨离去。姑娘醒来,方知是南柯一梦,拿氏作古已经百年。这篇小说不外乎表现江山美人之间的冲突,但写到拿破仑向莎绯霞表示“梦想得一美满家庭,为吾个人私有之天堂”,颇合乎上海滩的小市民口味,也是周瘦鹃等都市作家所热衷的题目。30年代初周氏主编《新家庭》杂志,鼓吹“小家庭”哲学:“家庭,甜蜜的家庭。里面充满着无穷的爱……你可安然做这小天国中的皇帝,决没有人来推翻你。”(39)相比之下,拿破仑显得颇可怜,求小家庭还不能够,做皇帝到头来被人推翻。
前面提到过华勒斯加,拿氏最钟爱的波兰女子,已在徐卓呆译的剧作里有所表现。看来周瘦鹃找到了不少材料,在《多情拿破仑与爱国之波兰女子》一文里详细叙述了他们之间的恋情经过,交代了她的丈夫及波兰贵族们急于利用她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文中描写的华勒斯加美丽而高傲,一再拒绝拿氏,激起他忽而狂怒,忽而温柔,极富戏剧性。如在强迫她就范那一段,简直像个流氓暴君的拿破仑:
探怀出一时计,大声曰:“汝其视吾手中之时计,吾当碎之汝前,使成粉虀。汝如故固拒绝吾心,不以汝心予吾者,失望之余,吾必碎汝祖国波兰,一如碎此时计。”言时,即举其手,力掷时计于对面之墙上。时计然碎,尽成纤屑,纷纷落地上。女惶恐已极,遂晕绝。比苏,则拿破仑方执一白罗之巾,轻拭其梨颊上之泪痕,且作悔艾语,语语都至纯挚,而其拭泪时状,则直温媚类妇人也。(40)
然而另一处又美化拿氏:
拿破仑之爱女,直如崇拜大神。所以悦之敬礼之者甚至浪掷其强半之光阴,与女把臂,见女则喜,不见女则抑抑弗乐。
此文极力表扬华勒斯加的“爱国”,却也付出了代价,即不得不屈服于拿氏这般的淫威之下。另外周瘦鹃终于搞到了拿破仑的初恋情人的资料,在1920年《申报·自由谈》上作了介绍。她叫蒂西丽·克拉丽(Desiree Clary),这段恋史有所据,不久拿氏见到约瑟芬之后,就把她丢开了。(41)另外为周氏所一再乐道的是路易丝皇后,不过对她没有什么好感。本来这段姻缘就含政治性,在拿氏初次流放至厄尔巴岛之后,望断秋水,但路易丝不仅没去岛上,而且与一个叫奈伯克的奥军军官热恋,后来与他结了婚。拿破仑在晚景凄凉时,仍对她念念不忘,周瘦鹃写到拿氏在临终时,说要把他的心浸在酒精里,送给路易丝,表示对她的不移之情,这样夸张的笔法当然也反衬了路易丝的寡情。(42)
的确,在这样的情话语的框架里,拿破仑形象无不带着周氏的文学趣味和语言风格的印记。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在再现形式上他笔下的拿破仑是中西杂交的,因此也是更为复杂的。相对于五四新文学原则上拒绝本土“旧”文学传统而言,周氏包括他的同道们在形式上更因袭传统的文学模式,这不仅是他们有意保守本土文化的资源,也涉及一般大众文化记忆的问题。
总之,拿破仑传奇到了周瘦鹃那里,绽放出一树繁花,虽然拿翁在中土的想象之旅也差不多臻至盛夏之季。他在民初时期再度交运,华盖运也是桃花运,走运也是倒运。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充分显示了都市印刷与视像传媒的活力。从周氏的再现策略中,借用巴赫汀所说的“众声喧哗”,所呈现的是万花筒般多变的视点,尤其突出是那种女性化的视点。拿破仑成为都市欲望指尖上的傀儡,培养传统和现代交杂的温室,虽然在对自由的渴望中拌和着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五、“三戴绿头巾”与“黑幕”小说
1910年代拿破仑在上海演艺界频频登台亮相。1914年9月夏令配克影戏园开张营业,首映影片How Heroes Are Made为法国故事大片,以欧洲最先进电影技术描绘拿破仑煌煌战绩,场面恢宏。(43)周瘦鹃看了影片之后,深受震撼,据之写成《何等英雄》,发表在《游戏杂志》上。文中称该片为“影戏中唯一之杰作”,“情节诡奇妙到毫末。俄而喑恶叱咤驰骋、血飞肉舞之地。俄而温存缠绵、流连金迷纸醉之场。俄而恋儿女之情。俄而作英雄之气。其中则有贤妇有义夫,有侠客有壮士,有豪爽之君主,有英伟之少女,可歌可泣。观之令人兴起”。(44)其实此前不久新舞台即排演过新剧《拿破仑》,据2月21日《申报》上广告:
《拿破仑》一剧为本舞台杰作,早蒙观者称许。其中情节离奇,慷慨激昂,无容赘述。现加真车真马上台驰骋,诚未有之奇观,并以美术别开生面及异样电光布景,视前次所演,更觉有声有色。他如离婚之梦景、军容之荼火,公园、餐间、马厩、洋楼等,装饰精致,变幻莫测。
这段广告与周瘦鹃的描绘相映成趣,关于拿破仑的历史想象激发壮观的艺术再现,而当时的新剧正提倡戏剧改良,把真车真马搬上舞台,利用声光化电的技术造成视觉震撼,其实在追求写实风格方面是受了电影的影响。然而在1918年6月间拿破仑又成为舞台的宠儿,却大异其趣,由英雄变成了龟雄。先是笑舞台推出新编《拿破仑之戴绿头巾》(45),报纸广告说:“人多知拿破仑为盖世英雄,殊不知拿破仑之为双料大龟。以大英雄而为乌龟,则其剧也多佳趣、多曲折明矣。”(46)这“乌龟”有个出典,早先在1914年《中华小说界》杂志上登过一幅《拿破仑之龟》的图片。拿氏坐在岩石旁,足下爬着一个大乌龟,稍远处有一个守兵的背影。解说词说拿氏在圣海伦纳岛孤寂无依,与一灵龟形影相吊,喂之以食,此大龟活得长久,在拿氏作古百年后,仍不堪回首当年云。(47)这应当是一幅洋画,这个乌龟与“绿帽子”比喻没什么关系,但在中国的接受脉络中则有可能成为富于隐喻的一环。
看来这个情色题材的《拿破仑》能招徕卖座,接着当时“改良新剧”的头等剧场新舞台也开演《拿破仑之趣史》,由夏润月演拿破仑、欧阳予倩演路易莎、汪优游演奈伯格,卡司皆一时之选。《新闻报》上的广告用醒目字号标出“特请周君瘦鹃新编”,下文曰:
《拿破仑》为本舞台名剧之一,口碑载道,向为社会所欢迎。而拿皇娶奥国公主后,尚有一段趣史故事,为吾国人所未之知者。吴门周瘦鹃先生近编世界大黑幕《世界秘史》一种,中有“拿破仑趣史”一节,考据详确,情文兼茂。兹徇本舞台同人之请,允于未出版前先予本舞台排演新剧,以快先睹。(48)
剧情脚本是根据周瘦鹃编写《世界秘史》一书,所谓“拿破仑趣史”是根据书中《拿破仑帝后之秘史》一章,(49)讲的是拿破仑与约瑟芬离婚后,娶了奥国公主路易丝,尽管对她曲意讨好,路易丝别有所恋,与奥国名将奈伯格伯爵暗通款曲。其中描写奈伯格如何潜入后宫而有刺杀拿氏之嫌,穿插勒佛索尔公爵夫人当初救济拿破仑的旧事等情节,极富戏剧性。其时周瘦鹃的《世界秘史》尚未杀青,至次年方面世。在报纸上与拿破仑的戏剧演出同时,也在醒目刊登“《世界秘史》预约广告”,所谓“拿破仑三戴绿头巾”,(50)指的是路易丝风流不已,先后有三个情人。在拿破仑兵败而被流放之后,她与奈伯格结婚,奈伯格死后恋上庞培尔伯爵,后来又与某美少年音乐师私通。
这样的广告显得恶俗,不啻是对拿破仑的一次恶搞。从开始时“拿破仑之戴绿头巾”到“双料乌龟”,再到“三戴绿头巾”,被层层加码,愈加耸人听闻。即使不是出于周瘦鹃之手笔,起码他也是个同谋,但我们再一想这大众娱乐背后的政治性,不那么简单。这样的同谋中,有一种集体意志在起作用,有意思的是被嘲笑的主角是拿破仑,而不是路易丝。从英雄崇拜到如此不堪的丑化,这一拿破仑的中国传奇从大众传媒与文化消费的接受角度来看另有其涵义。
如本文开头提到,晚清以来拿破仑、华盛顿的中国接受中寄托了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想象,涉及对于西方现代历史经验及其政体模式的借鉴、对于政治领袖超凡资质的期盼,都与未来中国的愿景息息相关。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帝制,然而中国何去何从茫无头绪,由于南北军政力量的悬殊,孙中山交权与袁世凯。1911年11月袁世凯派人至武汉见黄兴,表示愿停战言和,黄兴致函与袁:“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51)函中那种对于某种强人政治的期盼,也代表了当时的舆论。我们知道晚清以来常把华盛顿与拿破仑并举,在政治选择上含有法国抑是美国模式的某种不确定性,如邹容《革命军》中把华置于拿之前,两者的前后排序隐含着某种价值取向,有趣的是黄兴把拿破仑置于华盛顿之前。这样的提法当然会引起警觉,特别对于拿破仑的幽灵表示不安,1913年6月袁世凯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1860-1921)在一张外交报上发表有关“民国现状”的文章说:“非如华盛顿拿破仑,则不能定共和政府之新组织。”具反袁色彩的《民权报》上刊出秋客一文,认为华盛顿、拿破仑“不能并为一谈”,而且把这两人来期望袁世凯“亦离奇极矣”。秋客推测有贺博士的意思,“殆欲袁氏居华盛顿之位置,而行拿破仑之政策者耶?”这里已在暗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可能,如果这样,作者预言其结果“恐不能为拿破仑而为路易,不得保首领以殁。”(52)然而很快华盛顿就不提了,袁世凯几乎等同于拿破仑,何海鸣《求幸福斋随笔》付印于1916年,书中说他想把一部有关拿破仑的日文著作翻译过来,“以《失败之拿翁》一篇冠全书,并赘以己意当短序。其意则略谓,以英雄如拿破仑而犹失败,则世之不及拿翁万一二妄思推翻共和,恢复帝制者可以猛省……”(53)这些说明当时的舆论,拿破仑仍然抓住中国人的政治想象,伴随着幻想、忧虑与恐惧。
袁氏于1916年6月在国民的诅咒声中死去,稍后1917年《小说时报》上出现《约瑟芬外传》,叙述拿破仑先后出征意大利和埃及,胜利凯旋后政变掌大权这一段,以约瑟芬为线索展开她与拿氏家族及巴黎上层关系的描写,比以前的同类作品较为细致。富于启示的是译者的开场白:
共和复活,百度维新,吾人际此时机,固宜阐明平民之义理,发扬法治之精神,以贡献我国人。顾吾译斯篇,既非述卢梭鼓吹民气之轶事,又非纪林肯拥护平权之往史,乃津津道及搅乱共和之魔王拿破仑王后之陈迹,毋乃太不识时乎。虽然是篇固述约瑟芬略史,而书中言当日法国革命之后,兵骄将悍,野心家以武力蹂躏国会,不啻为吾民国往事之写照。其论当时士夫,希荣慕势,国民之姑息偷安,驯至国事不可收拾,尤足为吾国今日社会之借镜。(54)
现实与历史的链接如此鲜活。所谓“吾民国之往事之写照”、“吾国今日社会之借镜”之语,再清楚不过把袁世凯比作“搅乱共和之魔王”。而拿破仑“三戴绿头巾”当然会与袁氏的后宫秘辛,如报纸上披露的“诸妃劝进”之类的丑闻联系在一起。(55)由此或可理解,1914年间把袁世凯比附拿破仑的舆论甚嚣尘上时,大众传媒出现把拿氏人性化的倾向,其中寄托着某些期盼或幻想,到1916年身败名裂,昔日“英雄”被剥落了皇帝的新衣,而对拿破仑的丑化也是顺理成章之举。在这样的语境里,“三戴绿头巾”的拿破仑在舞台上、报纸上成为公众嘲笑的龟雄,聪明的观众发出会心一笑,尽管对权威的蔑视也多少蕴含着专制政治条件下无奈的发泄。
六、大众传播的民主要求及历史反思
运用影射策略是一方面,不过另须注意的是都市传媒的自身开展逻辑,周瘦鹃的《世界秘史》也被广告称为“世界大黑幕”,与盛行于1910年代末的“黑幕”小说潮流扣联在一起,这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向被当做反进步的文学逆流。范伯群在《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中对这一文学重新加以检讨,认为1916-1918年间流行的“‘黑幕’书”与“黑幕小说”不能混为一谈,从“全球化语境”加以考察,参照美国20世纪之初新闻记者和作家所发起的“揭黑运动”,指出黑幕书具有揭露社会腐败与不公的功能。(56)揭示这一点极富启发,所谓“揭黑”实际上是要求政治透明度,而新闻传媒应当起到促使透明度的作用。一如当今的后工业社会中,政客明星受尽狗仔队的骚扰,却无法杜绝之,因为言论自由赋予他们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追踪特权阶层隐私的权利。
袁世凯蓄意实行专制,铲除异己,严厉打压新闻与出版与言论自由,袁氏死后“黑幕”书风起云涌,当然含政治性。如《中国黑幕之黑幕》一书,内容由“各省通信之员”、“海上侦察”等提供,所谓“实事求是”大约不免包含道听途说之类,但主旨在于揭露时弊,尤其声称“不屈于权势”,把矛头指向当局,甚至涉及具体的部门与人事。(57)又如《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旨在揭露:“中国上自军政大事,下至里巷琐屑,无不各有一层黑幕笼罩其间”,(58)“上而达官名将,下而走卒舆台,试聆其议论,当无一而非仁义道德者,顾察其行为,则适与之相反。”(59)同样把“军政大事”、“达官名将”作为批评对象,但这样的“揭黑”毕竟是有限度的,不得不运用“春秋”褒贬的传统手法,何况后袁时代北洋军政当局依然仇视和迫害自由文人。至于“拿破仑三戴绿头巾”从政治影射角度来看犹如向专制“恶魔”吐出的一口恶气,而周瘦鹃的《世界秘史》尽管也以“世界大黑幕”为招徕,尚有深一层的思想面向,它不仅把拿破仑,也把各国首脑——俄皇、德皇,包括华盛顿等人的情场趣闻、后宫秘事都收罗了进去,因此并非仅仅为难拿破仑而更具广泛的意涵,即对于英雄或历史伟人形象的扭曲或丑化,以娱乐性迎合大众的窥私欲望。大众固然崇拜社会明星,但也乐意看到狗熊般的英雄,对伟人隐私的偷窥欲包含着有权暴露伟人隐私的“民主”权利。
在周瘦鹃的大量书写中,拿破仑成为新的当代英雄。这体现了民初崇尚普世人“情”的思潮,对于晚清以来所鼓吹的那种一切服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英雄”来说,不啻是一种意识形态上从“革命”到“共和”的转折。其中含有大众启蒙的新议程,即建立人人生来平等的信念,既试图接续陷入危机的文化传统,也为资产阶级的发展铺平理论的基础。可资印证的,何海鸣说:“拿破仑曰:‘凡属英雄,每日必作小儿之举动二次以上。’伟哉言乎!是即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中国人好自大,年来伟人之称转含讥刺,是亦无真英雄故耳。”(60)所谓“赤子之心”即体现了人人平等的立场,而“伟人”一词专指以“革命”功臣自居的国民党人,此词也经常见诸《申报·自由谈》,其主编王钝根及其同人秉持一种“中立”立场,既反对袁世凯,对孙中山的继续“革命”也不表赞同。所谓“不屈于权势”也是“黑幕”书所取的批评姿态,不仅针对政府当局,也与所有“权势”保持距离。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历史地认识民初的都市大众传媒十分重要。
1918年秋民国教育部发表“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的函稿,(61)接着在《新青年》上出现钱玄同、周作人、杨亦曾等人的争论,对此这里不拟讨论。该“函稿”根据教育部属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报告:即“本会成立以来,对于不良小说,迭经呈准教育部,咨行内务部,通行查禁”。简单地说,这是官方对于文学出版的干涉,而钱玄同、周作人等竭力为“函稿”辩护,以纯洁民众道德为借口,实际上起到扼杀通俗文化的批评空间的作用,合乎北洋当局的利益。尤其不分青红皂白的是他们把“黑幕”与“鸳鸯蝴蝶派”连在一起同袁世凯“复古”混为一谈,后来文学史一网打尽民国通俗文学,其理据则追到钱、周那里。
然而这毕竟是在民初,在共和宪政的架构中印刷文化允许百家竞争,教育部的干预尚取“劝告”态度,《新青年》的主张不具法律效力,都市大众传媒也没有因此而放弃批评空间,这方面以“礼拜六派”王钝根、周瘦鹃等人较为主动。1919年底继《新青年》的“黑幕”争论之后,王钝根编纂的《百弊丛书》出版,(62)不以“黑幕”标榜,却明确声言旨在揭露“官场之黑暗”,以“国务院”、“外交部”、“内务部”、“陆军部”、“将军府”、“京师警察厅”等政府各部为子目,具体内容这里难以细析,如书中写到国务院“乃全国行政之总机关也,然除国务会议外,各部总长对院事从不过问。故秘书长、局长等只服从总理,能得总理信任者,视诸总长若弟兄行,甚且势凌其上,观徐树铮、孙洪伊往事可知矣”。(63)单看这段可知其余,可见王氏在其主编《申报·自由谈》与《自由杂志》之后,继续为大众传播开拓言论空间,发挥政治的批评功能。同样,周瘦鹃对拿破仑的书写预示了他后来对民初政坛的态度,尤其在1920年代前期,当他主编《申报·自由谈》时,对于中央政府、地方军阀、国会议员等嬉笑怒骂,或指名道姓的抨击,更挑战“言论自由”的尺度。(64)同时以他所主编的《半月》杂志全力把殷明珠——中国第一位电影女主角——打造成好莱坞式“明星”为例,继续努力推进女权,而这,如本文所述,大众传媒中女性公共空间的长足发展也是其“民主”倾向得以形成的重要动力。
注释:
①据胡兰畦回忆,她小时候在四川,辛亥革命之后妇女流行剪发,“梳着偏分式,当时这种发式叫拿破仑式。还有一种从头发中间分开,两边梳得一样平的,叫华盛顿式”。可见在中国拿破仑家喻户晓之一斑。见《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第14—1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邹容:《革命军》,见周永林编:《邹容文集》,第43页,重庆出版社,1983。
②陈建华:《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从〈泰西新史揽要〉到〈泰西历史演义〉》,载《汉学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年11月),第321—354页。另载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文学研究》,第9辑,第309-343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③任公:《新民说五·论进取冒险》,载《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
④⑤[日]土井林吉:《拿破仑》,第1、12、14页,罗大维译,上海,益新译社,1903。
⑥林纾:《〈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叙》,见[法]阿猛查登:《利俾瑟战血余腥录》,第1—2页,林纾、曾宇巩译编,上海,文明书局,1904。
⑦⑧《图画日报》,第1册,第519、5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⑨史子彬:《欧洲第一雄主传》,第6a—7b页,郇山学堂,1902。
⑩艾米尔·路德维希:《拿破仑传》,第40页,梅沱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11)周槃:《约瑟芬》,载《香艳杂志》,1914年第1期,第11—13页。
(12)[美]亚勃的著、东纳译:《拿破仑之艳史》,载《小说丛报》,第17期(1915年12月)。
(13)志群:《五月二十九日——徐世宾逝世》,载《民权报》,1913-05-29,第11版。
(14)荆诗索、柯岩初编:《帝国崩溃前的影像——晚清连环画中的晚清社会》,第332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15)瘦鹃:《泰晤士河畔妇女要求参政之怒潮》,载《妇女时报》,第7号(1912年7月),第9-12页。
(16)周槃译:《美人与国家之关系》,载《香艳杂志》,1911第1期,第1-3页。
(17)施退尔夫人著,瘦鹃译:《无可奈何花落去》,载《礼拜六》,第20期(1914年10月),第17-29页。
(18)瘦鹃:《铁血皇后》,第35—40页,载《妇女时报》,第8号(1914年10月)。
(19)周瘦鹃:《怀兰室丛话·铁血王后》,第3页,载《女子世界》,1914。
(20)树声:《欧洲伟人之情史》,第1—4页,载《小说新报》,第11期(1915年12月)。
(21)卓呆译:《拿破仑》,第1—9、11—18页,载《中华小说界》,第1—2期(1914年1—2月)。
(22)[法]麦良巴威:《拿破仑轶事》,第5—6页,润甫译,载《小说丛报》,第3期(1917年11月)。
(23)[英]嚣氏著,绿衣女士、冷译:《拿破仑》,第35页,载《小说时报》,第22期(1914年5月)。
(24)Bernard Shaw,"The Man of Destiny," in Plays Pleasant(New York:Penguin Books,1984),p.164.
(25)[英]嚣氏著,绿衣女士、冷译:《拿破仑》,第2页,载《小说时报》,第16期(1912年8月)。
(26)Carolly Erickson,Jesephine:A Life of the Empres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p.133—142.
(27)[英]嚣氏:载《小说时报》,第5—6页,绿衣女士、冷译,第22号。
(28)(29)[法]华度甫勃海传:《拿破仑之情网》,第10—11页,天笑、听鹂译,载《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9期(1915年9月)。
(30)吴贯因:《英雄与社会》,第4页,载《大中华杂志》,第1卷2期(1915年2月)。
(31)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第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2)瘦鹃译:《忠魂》,载《游戏杂志》,第27页,第7期(1914年7月)。
(33)周瘦鹃:《拿破仑五百二十万吻》,第124页,载《紫兰花片》,第6集(1922年11月)。
(34)瘦鹃:《情场之拿破仑》,第7-9页,载《女子世界》,第1期(1914年)。
(35)周瘦鹃:《香艳丛话》,卷2,第16页,上海,中华图书馆,1916再版。
(36)瘦鹃译:《同归于尽》,《礼拜六》,第20—25页,第52期(1915年5月)。
(37)周瘦鹃:《小说家之拿破仑》,第14—28页,载《紫兰花片》,第3集(1922年8月)。
(38)瘦鹃译:《香梦——美人梦中之拿破仑》,第14-28页,《礼拜六》,第75期(1915年11月)。
(39)周瘦鹃:《新家庭出版宣言》,载《新家庭》,第1卷,第1期(1932年1月)。
(40)瘦鹃译:《多情之拿破仑与爱国之波兰女子》,第9页,载《女子世界》,第5期(1914)。
(41)瘦鹃:《拿破仑之秘史:瑞典之第一王后为拿翁少时情人》,第14页,载《申报》,1920-01-22。另见周瘦鹃:《拿破仑少时情人》,载《紫兰花片》,第10集(1923年3月),第41—44页。关于克拉丽之画像,见Napoleon:An Intimate Account of the Years of Supremacy,1800-1814,p.157。1992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拿破仑情书集》,由梅沱等编译,据称作者们花了不少工夫搜集拿氏情书,并对他的情史作了探索。但在该书附录《拿破仑的罗曼史》中,克拉丽未被列入。作者称:“拿破仑晚年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他有过七个情人,不知究竟何所指。”的确,有六个情人被列入此“罗曼史”中,独缺克拉丽。
(42)周瘦鹃:《拿破仑之妻》,《紫罗兰外集》,上册,第10—12页,上海,大东书局,1924,第3版。又见瘦鹃:《名人风流史:玛丽·路易瑟(法帝拿破仑之后)》,载《申报》(1919年11月22,23,25日)。
(43)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8,1914),p.4.
(44)《游戏杂志》,第9期(1915),第27—28页。
(45)《拿破仑之戴绿头巾》,载《新闻报》,1918-06-09,第3张,第3版。
(46)《拿破仑》,载《新闻报》,1918-06-12,第3张,第3版。
(47)《拿破仑之龟》,载《中华小说界》,第7期(1914年7月)。
(48)《拿破仑之趣事》,载《新闻报》,1918-06-22,第3张,第4版。
(49)范伯群编:《周瘦鹃文集》,第3册,第110—127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
(50)《世界大黑幕〈世界秘史〉预约广告》,载《新闻报》,1918-06-11,第2张,第3版。
(5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1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52)秋客:《敬询有贺博士——华盛顿与拿破仑》,载《民权报》,1913-06-26,第6版。
(53)何海鸣:《求幸福斋随笔》,第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54)[法]伯桑著,建生、迪士译:《约瑟芬外传》,载《小说时报》,第29号(1917年2月),第1页。
(55)“诸妃劝进”语见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见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16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56)范伯群:《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见《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第167-1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7)见《中国黑幕之黑幕》广告,载《新闻报》,1918-06-26,第4张,第1版。
(58)刘豁公:《中国黑幕大观序》,见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77页。
(59)童爱楼:《中国黑幕大观序》,见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79页。
(60)何海鸣:《求幸福斋随笔》,第13页。
(61)《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第172页,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9号(1918年9月)。
(62)(63)王钝根编:《百弊丛书》,第5页,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1919。
(64)参陈建华:《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周瘦鹃与〈申报·自由谈〉,1921-1926》,见《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第141—17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