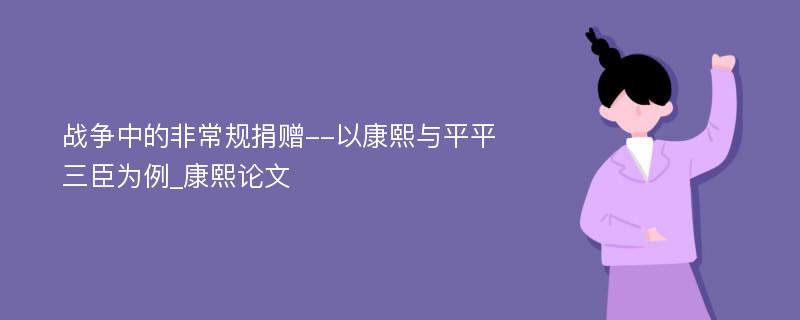
战事中的非常规捐纳——论康熙朝平三藩开启的捐纳事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事论文,事例论文,康熙论文,非常规论文,朝平三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史稿》曰:“捐例不外赈荒、河工、军需三者,曰暂行事例,期满或事竣即停,而现行事例则否。捐途文职小京官至郎中,未入流至道员;武职千把总至参将。而职官并得捐升、改捐、降捐,捐选补各项班次、分发指省、翎衔、封典、加级、纪录。此外,降革留任、离任、原衔、原资、原翎得捐复,坐补原缺。试俸、历俸、实授、保举、试用、离任引见、投供、验看、回避得捐免。平民得捐贡监、封典、职衔。大抵贡监、衔封、加级、纪录无关铨政者,属现行事例,余属暂行事例。”[1]简言之,清代捐纳向有“现行事例”和“暂行事例”之分,前者为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等,后者为赈荒、河工和军需而开设,有一定的期限。捐项主要包括:捐实官,诸如举贡可捐实授,现任官可捐升、捐改、捐加级等;捐复,革职离任纳银后可以坐补原职;捐免,试俸、历俸、保举、引见以及考职等项并可纳银免去。
学界将上述“暂行事例”的起始时间定于康熙朝用兵三藩期间,应该没有异议。然而,有关这期间的捐纳状况却始终是模糊的,不仅开捐的具体时间和省份由于资料的缺失显得混乱,而且各类捐项以及议叙授官的状况也有诸多需要整理之处。也就是说,《清史稿》所列举的捐例有哪些系由平三藩期间实施的,并没有给予认真的梳理与佐证。本文通过对档案和文献汇编的检索,找到一些尚未被人留意的捐纳事例,它直接与战争有关,却又不见于日后确立的常规捐例,而此后愈益繁杂的捐纳事例对吏政形成的危害,大都可在平三藩期间的捐例中找到源头。
一
在清代的文献中,由官方记载的捐纳事例,就捐纳内容而言,主要有捐银、捐米谷及捐马等捐项,但在历史档案中却可发现,在平三藩的战役中,捐造战船也是当时湖广主战场最重要的捐项。
自康熙十三年(1674)初,清军与吴三桂的主力部队在荆州与岳州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后,湖广便成为清军平叛的主战场,由于荆岳一带江河湖泊纵横交错,因而水战多于陆战,战船便成为交战双方不可或缺的重要军事装备。早在十三年六月,康熙便向前线总理粮饷的左都御史多诺等下达了打造战船的谕令,命将“所需船只当于荆州预造百艘,其作何造办及所需工费详议以闻”。[2](P659)年末,鉴于吴军在衡州等地大规模造船,再次命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与岳州主帅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等修造战船,于沿江要地严加防守。[3](P703)而有关前线急战船之需、督促地方打造的记载,更是多次出现在十五和十六年的《实录》中。
康熙十五年(1676),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奉命由江西取长沙,由于缺少战船,面对吴军水师集长沙城下而束手无策,遂于七月疏“请发江西得胜船十只,及安庆、九江沙船五六十只赴长沙”,“并乞敕巡抚韩世琦伐木造船”。康熙一面令尚善自岳州发沙船百艘转送长沙,一面“如安亲王所请,着江西总督董卫国、巡抚佟国桢等采办物料,雇募工匠,运赴长沙军前修造战舰。如不敷用,江南总督阿席熙、安徽巡抚靳辅等速行采办雇募,转送江西,一并运致。仍预行安亲王遣兵迎取,付韩世琦督造”。[4](P841-887)至十六年(1677)正月,“安徽巡抚造送沙船四十艘于本月十五日到岳。……上命京口将军王之鼎发沙唬船六十艘,随带礟械水手人役、量配官兵护送至岳州,并靳辅所送船足百艘之数,以备安亲王岳乐、将军穆占取用。”[5](P882)
造船需要政府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拿出不少的银两作为经费开支。这些造船的银两来自何处呢?在《清实录》等官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在《平定三逆方略》中似可窥得一点信息,即运送粮米使用的盐船系捐纳所集。
十六年九月,“命增造战舰。先是,上谕议政王等:逆贼吴三桂凭江湖之险抗拒大兵,为日已久,若不速行剿灭,湖南民困无有已时。闻逆贼多备鸟船战舰,死拒我师。我师亦宜倍制鸟船、沙船,更令捐助盐船多载粮米,由岳江入洞庭尽占江湖,断贼粮道,夹攻岳州”。虽然经议政王大臣讨论后,只决定造鸟船六十艘、沙船二百艘,“盐船停其捐助”[6],但是采用“捐助”的措施以缓解船只紧张的信息已经透露出来了。
此外,唯一一处在《清实录》中出现的“输助”字样,出自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的奏疏。十七年(1678)九月,喇布疏言:“茶陵、攸县、水陆俱通衡州诸处,宜造战船及小沙船百艘备用。议政王大臣等议如所请,令劝勉绅衿百姓输助,速行营造。”但是康熙并未同意,他明确指示:“造船事关紧要,令刑部侍郎禅塔海于江南动支正项钱粮,备药礟及需用器物,前赴茶陵诸处督理修造。”[7](P1035)也就是说,以康熙为代表的清朝政府是主张以国家的正项钱粮作为造船的主要经费的。
但是,清代档案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却是这些奉命打造的战船,其经费来源大部分是“捐输”,而承担造船职任的是那些被寄以封疆之责的地方督抚。从保留下来的档案看,江宁巡抚慕天颜和湖广巡抚张朝珍的担当最多。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十五年,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曾疏言:“得鸟船四十艘即可破贼。”于是,康熙即交与江宁巡抚慕天颜督造,所谓“因令江南造船如数送往”。[8](P965)有关此次造船的记载,在《清实录》中是这样的。十六年六月,慕天颜疏曰:“所造鸟船甚多,必须时日,臣躬自督工,期以六阅月告竣。得旨:岳州需船甚急,若六阅月始竣,则秋冬已过,有误破贼之期。慕天颜其昼夜并力,务于八月内竣工,遣往岳州。”[9](P910)这里只字没有提到造船的经费来源,更未透露捐造的具体情形,而几件档案中慕天颜的奏疏却对此做了交代。
第一件,十六年(1677)六月,慕天颜奏称:康熙有谕旨曰:“岳州大将军贝勒尚善等题称,若得鸟船四十只可以破贼。既称破贼鸟船得用,应令速造鸟船,其造船事宜着交与巡抚慕天颜,设法令各官捐助,作速造鸟船四十只,以资大兵之用,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议政王大臣秉承康熙的旨意,议由慕天颜“设法鼓励文武官员及乡绅捐助成造,其造船时,该抚遴选贤能官员作速制造,若所造之船精坚,告成迅速,将监造及捐助各官俱听该部酌量从优议叙。”由于“鸟船比沙唬船甚大,所需钱粮甚多,若各官所捐钱粮不敷,该抚将四十只船共需钱粮若干,现捐之钱若干,不敷银若干,再行会议。”[10](P925)这里明确指出,清政府指令地方督抚、文武官员及乡绅捐纳银两以备造船,捐助后不足部分,再作计议。
第二件,慕天颜向户部奏称:“鸟船一项,京口、崇明等处向未成造”,而旧式船只,“每只工料银二千一百余两”,鸟船约比旧式船只长大,“虽所费颇繁,工程亦必数月,然酌计宜先。臣一面遍诸练匠工,确估务期节省,标明另疏齐奏外,但应否成造若干只,仰候敕部议覆。”显然,慕天颜对在短期内打造四十只鸟船是没有信心的,但户部的答复却是不容更改的。“查近经议政王等会议钦遵上谕制造鸟船四十只,交与巡抚慕天颜设法鼓励文武官员及乡绅捐助成造,再鸟船比沙唬船甚大,所需钱粮甚多,若各官是所捐钱粮不敷,该抚将四十只船共需钱粮若干,见捐之银若干不敷银若干具题到日再议。咨行在案,此疏应无容另议。”[11](P1753)由此可知,即使按照旧式造船所需工料银两,四十只船尚需工料银八万四千两,而鸟船当更多,但清廷不吝银两造船的决心也是十分坚定的。
第三件,十六年十二月,慕天颜所造鸟船已完二十只[12](P977),由于鸟船需用大桅,大桅要用杉杂等木打造,江南采购维艰,故尚有二十只未能造完。于是,慕天颜题明以“捐措银四千两委员解楚,就近办料修造”[13](P1041),即拿出捐纳银两赴湖南修造二十只船的大桅。
除了慕天颜督造战船之外,档案中记载最多的还有湖广巡抚张朝珍奉命打造战船的情形。
十六年七月,贝勒尚善以“岳州军前需用快船,成属至紧急务”为名,直接谕令张朝珍打造“快船”,并明确指示其“设法劝输”。“大兵所需快船最为紧要,该抚设法劝输所属官员,捐输十六把桨、快船二十只,并水手一并拨解,仍将捐输快船官员移咨(报)部,分别议叙。”随后,张朝珍立即檄行按察使高翼辰催促各官设法捐备,然武汉、黄安等五府的官员却回奏说,民间既无桨也无快船,更无打造快船的木材可买。[14](P954)至次年正月,布政使徐惺奏称:“经本司勉自用价办料”,“复又捐备银两、采办物料,雇觅工匠照式改造,今已造完十只,一应桅蓬锚缆什物等项俱已备齐,并未动钱粮”。[15](P1010)随后,张朝珍等将打造好的快船交送到岳州的讨逆将军鄂内军前。[16](P1024)
就这次打造快船的经费来源,布政使徐惺说“并未动钱粮”,张朝珍也直接说明:“先奉贝勒谕令各官捐助”,并声称:“若动钱粮恐难报销,若派各属又累官民,且更稽延时日,有误军务。本司勉行自捐价银二千二百一十七两九钱八分两,发汉同知买料鸠工造完……解赴军前应用。复奉贝勒谕因不合式发回,令照提标式样改造十五桨,本司不得已又自捐,照式样另造二十只,其一应桅蓬锚缆什物等项俱已完备,并未动用细毫钱粮,亦未用官民一夫一木。”[17](P1039)这说明张朝珍等造船的所有经费都出自“捐纳”,且自身承担了捐纳的主要款项。
以上资料虽然使我们难以获悉打造战船所需的确切银两,但却说明,康熙十六年,是清军大规模修造战船作水上战备的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在湖广、江南地区的捐纳所得应该主要用于造船。即便到了翌年,清军在军事上已稳操胜券,但由于岳州、长沙等重镇仍然未下,捐纳用于造船也并未结束。
三月,清军前后调集岳州的船艘已多于吴军数倍,除了“原有鸟船,又奉旨添造鸟船一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在康熙看来,“合此船破敌,何难之有?”[18](P976、972)于是,采纳了投诚吴军水师将军林兴珠的水陆围困岳州的战略计划。[19](P991)六月,清军的鸟船、沙船进湖,一半泊君山,余船泊香炉峡、扁山、布袋口诸处。但是,吴军船小且快,仍不时出击柳林嘴等地,往来获取粮食。而清军所有快船为数无几,不敷应用。以故,贝勒尚善谕令巡抚张朝珍,“率领各官奖励捐快船一百只,星夜打造。至七月二十日内,令其解到岳州。其捐船之处,并限期内速行造完情由,题请一并议叙。”[20](P1204)这应该是清军最后一次为岳州用兵打造战船,依旧是“捐造”。
从当时的情形看,不仅造船需要捐助,修船同样需要捐助。十六年十一月,湖广前线将五十七只损坏的沙唬船发回京口,兵部令江南总督阿席熙与安徽巡抚徐国相作速设法修理。随后,阿席熙等人在回奏中称:由于经费筹措困难,“臣一面劝谕捐输,一面行安徽布政使确估与修”,只是“行文劝谕捐输,报捐寥寥”。兵部不得已批复曰:“若劝捐钱粮不敷,动支正项钱粮修理可也。”[21](P2017)由此可知,在筹措造船与修船经费的过程中,清政府通常是先采用劝捐的方式汇集经费,如果报捐不足,方动支来自正项钱粮的官帑。
以上系战船的大修,而在荆岳对峙的五年间,战船的小修更是经常的事情,系由专管船艘的官员负责,他们修船的经费也是来自捐纳。据讨逆将军都统鄂内等启称,一次需要“大修鸟船一十二只、沙船三十五只外,其余各船因月深日久,逐船俱应小修”。至于修船的经费,鄂内说:“游击张世捷等自行捐修是实,其破坏之船每多各捐己资修理,今困苦已极。”[22](P1452)
由此而言,捐造、捐修战船主要为解决湖广主战场的军备问题,且已形成规制。十八年(1679)九月,湖广提督徐治都在其“密陈川江险要情形并议战守机宜”一疏中提到了“捐造船工之例”,谓:湖北打造战船,“船内棉帘遮阳等项,为水战必需。以战船一百只共需一千二百扇,为费甚大,请照捐造船工之例,捐造完之日听抚臣核实录叙。”[23](P2019)
以上说明,平三藩期间,清军在军费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筹措军备大都寄托于捐纳所得银两,而捐造战船当是湖广主战场的重要捐项,这是其一。其二,就报捐者而言,则突破了我们所知悉的“文职自道员至佐贰、武职自副将至守备”①的捐例规定,高级官员也加入了捐纳者之列。其三,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它与我们熟悉的纳钱买官的制度性捐纳没有直接的关系,捐造船只者均为职任担当、奉命行事。因此,由于捐造战船没有被写入代表官方意志的会典和则例,本文在此将其称作非常规捐纳。
二
马匹一向被视为冷兵器时代的重要军备,在平三藩的战争中,康熙多次强调“马匹铠仗,行军要需”、“大兵剿贼,惟马是赖”。就战争中清军的配备而言,满洲八旗将领通常给马二至三匹,如十四年,康熙谕令“驻西安诸将帅酌量每人给马二三匹,其铠仗着动正项钱粮修办”[24](P714),而“绿旗兵每人止有一马”[25](P1127),但马匹的不足与不断增加的需求是一常态。
早在十三年(1674)六月,战争初期就出现了“岳州兵马,草豆匮乏”[26](P659)的现象。是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反叛,就是一起因马匹在满洲与绿营官兵之间配给不均直接导致的激变,而马匹毙于战争中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如十四年(1675),镇西将军席卜臣自汉中进抵西安,经过一路与叛军交战,以致“见在官兵俱无马匹器械”。[27](P776)十六年(1677)四月,镇南将军莽依图率军入粤,军中官兵“无马者众”。[28](P900)与此同时,安亲王兵因久入湖南,亦“马多致毙”。[29](P908)
战争中既然需要如此之多的马匹,而平三藩又是清朝开暂行捐例、捐实官的开始,那么马匹的捐纳应当是捐项之中的。但是,这在清朝的官书中同样未见诸明确记载。也就是说,平三藩期间是否开捐马事例,一直以来不得而知。不过,档案提供的资料依然给了我们肯定的回答。
与捐造战船不同,捐马无需经过制造环节,捐的是实物。查找《清实录》,有关“捐马事例”的记载始于康熙三年(1664)二月。所谓“兵部议叙捐马人员,凡文武各官有捐马百匹者,准纪录二次;捐马五十匹者,准纪录一次。得旨依议,捐助紧急军需者,着即准行。寻常捐助者,仍送总督、提督分别具奏”。[30](P182)这里所说的捐马人员只提到了文武各官,捐马者获取的利益也只是通常议叙当中奖励层面的纪录,不涉及官职的升迁,也没有提到捐纳官员的级别限制。这与我们通常认识当中的捐例不同,但可以肯定,捐马当是捐例中的常项,且已先于平三藩前存在。
平三藩战事初期,清军的马匹依惯例主要由蒙古各部捐助。十五年八月,康熙在给前线将领的谕旨中说:“仍令理藩院传示外藩蒙古诸王以下酌量捐助马匹,以济军需。”[31]次年八月又谕议政王等曰:“外藩蒙古王等捐马甚多”。于是,以江西邻近湖广、广东,令拨五千匹发往南昌,由总督董卫国遴委贤能官员督视秣养,又命简选兵部喂养马及营驿马二千匹发往湖广武昌,饲秣备用。[32]
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马匹供给的不足仍然是十分严峻的问题。于是,清廷在号令蒙古各部捐马的同时,更大规模的捐马活动也兴起于满汉官员中,时间当在康熙十六年,相关资料来自档案中。
据记载,十六年二月,湖广巡抚张朝珍接到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的谕令,以岳州口外蒙古兵丁马匹殆尽,有至步行者,令其“檄行所属地方文武官员有情愿捐马者,将各官职名并所捐马匹,俱于四月初旬内送到军前”。于是,张朝珍当即檄行按察使高翼辰移会文武各官,星速捐解。然“楚北文武各官节年办理军供,日事防剿,疲苦不堪,兼之俸薪久裁,无力捐输”。[33](P930)显然,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开捐事项。
与此同时,因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围取长沙,“大兵需马甚殷,非寻常比”,兵部等衙门于十五年十二月会议,决定以捐纳的形式解决安亲王军中的马匹补给问题,开捐地区限于江西袁州,但最初的捐纳马匹还有来自安徽的。据“原任安徽巡抚靳辅疏称:臣及按察使薛柱斗等共捐马一百二十三匹”。[34](P1733)这里显示的不仅是捐纳马匹的数量甚微,而且亦非兵部所议的江西袁州地区,而是邻省安徽。它至少说明当时的捐例与执行情况有着距离。
十六年二月,贝勒尚善奉命遣兵由岳州送马三千匹赴长沙岳乐军前,由于护送官兵仅一千人,三月初,清军解马抵七星台时遇叛军伏兵,三千匹马俱被劫夺。康熙十分震怒,欲以贻误军需罪重罚尚善,岳乐亦因迎马迟缓受到斥责。[35](P897)然而,处分仍然解决不了军中缺马的现实,问题更加棘手。其时,清军一时无法攻下长沙,而长沙“军前马匹倒毙者日多,则需马匹更为急切”。是月,康熙谕兵部:以福建、江西、陕西俱已底定,而诸将又分路进取湖南,宜协助马匹以资大兵,令“王、贝勒以下文武各官可酌量捐马并拨内厩马一千,送赴长沙军前”。这次由太仆寺卿温岱负责护送,温岱直抵长沙,交明始回。[36]
这条只见于《方略》的“捐马”谕令,是清政府加大力度和扩大规模实施捐马事例的开端,并由兵部下令在江西袁州与湖南长沙实施捐马,定期由九月解送至长沙。[37](P1782)对此,有档案中保留的偏沅巡抚韩世琦与兵部的几份奏疏可以佐证。
一份是十六年六月兵部的题奏,这份文书的中心是讨论韩世琦的“请变通捐马事例以济大兵急需事”一疏。其中有捐马数量、捐马人姓名及捐马者的议叙状况。
韩世琦称:“大小官员捐送长沙军前共马一千三百一十八匹,军前马匹需用甚殷,定限五月终以满,限至九月将捐助马匹数目、官员职名造册具题前来。查议政王大臣等会议所题,若在长沙、袁州捐助马匹者,于康熙十六年五月以内准其捐纳,六月初一日以后应停其捐纳等语。今虽捐送长沙马一千三百一十八匹,送到马匹为数无多。”兵部的意见是:“见今长沙大兵需马甚紧,应照该抚所题,于本年九月终止捐纳,俟命下之日通谕遵行。定例内,文武官员在长沙大兵军前捐马一匹者,纪录一次,二三匹者纪录二次,四五匹者纪录三次,捐马六匹以上至十匹者加一级,如有多捐者,照此递加议叙。能有捐至一百匹者,不论俸满即升、候选官员,于出仕之日照此例纪录、加级。在江西袁州府,捐马三四匹以上者纪录一次,捐马七八匹以上者纪录二次,捐马十二匹以上者纪录三次,捐马二十匹以上者准加一级,捐马四十匹以上者准加二级,如数目多者,递此纪录、加级等语。提督赵国祚等十员武职在长沙捐助马数与例相符,应在臣部(兵部)纪录、加级。在长沙捐助马匹偏沅巡抚韩世琦等九员,在袁州捐助马匹总漕帅颜保等十三员俱系文职,应交与吏部议叙。”[38](P932)
由以上的捐例不难发现,捐马注重实效与实用性。在规定了议叙的等级与捐马数量的同时,也就捐马难易程度对议叙做了区分。由于在长沙捐马需要直达军前,故捐例规定相对宽松,而袁州稍逊之。同样是加一级,捐至长沙者只需捐马六匹以上至十匹者,而捐至袁州者则须捐马二十匹。而且,这些捐例仍只行于现任文武官员之内,捐纳者的利益也只是纪录和加级而已。但是,如果与康熙三年捐马五十匹方准纪录一次的捐马事例相比,平三藩期间的议叙对捐马者而言当有不小的诱惑。
第二份是十六年八月兵部就偏沅巡抚韩世琦的奏疏所上的题奏文书,其重点在于它列举出捐马各官的姓名及各自捐马的数量。“偏沅巡抚韩世琦疏称:各官陆续捐助马匹,有经送至长沙军前者,有解至袁州转送长沙军前者,以上共二百一十九匹,均于六月初一以前原定期限内,解送到之日,当即启明大将军和硕安亲王。”同时,“将捐马各官职名马数造册题奏前来。(兵部)查册内九江总兵官马云程在袁州捐马二十匹,偏沅抚标右营中军守备赵宝在长沙捐马六匹,臣部应照例各加一级。其候补给事中硕木科、礼部员外郎周朝佐、江宁府知府孙芳、宁国府知府泰弘等十一员在长沙、袁州捐马,俱系文职,应请敕下吏部照例议叙。至出兵之翰林院侍读学士勒贝等七员,现在进剿,相应俟回京之日再议,其捐助地方马匹数目及捐马各官职名开列于后。”[39](P1769)
第三份是十六年十月兵部车驾司的“题请变通捐马事”的题本。其中有曰:“该臣等议得,偏沅巡抚韩世琦疏称,长沙大兵远近各官长沙捐助马六百四十五匹,袁州捐助马七十七匹,当即咨明大将军和硕安亲王分给各旗讫;再江西抚臣佟国祯驳回,马缺,又补解马三匹,布政使姚启圣驳回,马缺,又补解马二匹,应否?作何查叙?合听部夺等因。查将军王之鼎等武职捐助马数与例相符,王之鼎等三员各加一级,副都统胡启元应加二级,苏州织造官加一级…查本年五月内,偏远巡抚韩世琦疏称,江西巡抚佟国祯捐马三十七匹,布政使姚启圣捐马三十八匹等……前捐马匹数内,议叙布政使姚启圣捐助马匹不及数目,应毋庸议。其捐马文武各官职名马数,捐马之处,开列于后者。”[40](P2016)对于所捐马匹尚不足额,韩世琦回奏称:南方天气炎热,“捐输寥寥”,题请展限,由九月题请展限至十二月。[41](1782)
在湖南长沙战场捐马的同时,由西北战场调往湖南的清军也在捐马。十六年三月,抚远大将军公图海麾下副都统穆舒混等统兵前往湖广,因兵丁马匹羸弱,不得已将各旗驻扎官兵的肥马参换给骑,仍不敷,“共捐马一百三十七匹”。捐马官员职名、捐马数目如下:“查本年正月内,臣部会同吏部议覆,内外文武人员若捐马三四匹以上、二十匹以下,纪录一次等语。今陕西总督哈占等自十匹以下捐助,陕西总督哈占、四川总督周有德、云南总督鄂善、陕西巡抚杭爱、西安布政司巴锡、按察司库尔康、咸宁知县唐文学,应交与吏部议叙,总兵官陈奇谟捐马三匹,应照例于臣部纪录一次,其抚远大将军公图海等自十匹以下捐助理应议叙,但现在进剿,等事平之日再议,其副都统穆成格等三十一员、粮储道教化新等六员、都司祈彻白等十一员,所捐马匹俱不及议叙之数,均毋庸议。”[42](P1722)
有关平三藩期间的捐马,有几点需要注意:其一,在以上档案资料中,已经出现了“捐马事例”、“各省捐马之例”的相关记载,即捐马已形成相应的规制。其二,捐马的地区已经波及数省,除了江西袁州、湖南长沙外,档案中见到的还有安徽、广东、陕西、四川,云南等省,所谓的“各省捐马之例”就很说明问题。其三,各省的捐马事例不一。除了上述江西袁州与湖南长沙的不同外,二十年(1681)四月,在兵部题奏的一件文书中有云南巡抚伊阙的捐马题本,也说明了各省的差异性。伊阙疏请设置驿马以应对紧急军机,比照“各省捐马之例再减分数,捐马一匹准纪录一次,捐马四匹准加一级”。经兵部车驾司等议定:“捐马一匹者纪录一次,捐马二匹者纪录二次,捐马三匹者纪录三次,捐马四匹者纪录四次,捐马五匹以上者准加一级,捐马十匹以上者准加二级,如有多捐者亦照此加级。若候选官员与进士举贡监生捐有马匹,亦照此例于出仕之日纪录加级。至所捐马匹各自备草料喂养,送至该抚,将接收马匹数目造册报部,照例议叙,俟马匹足额即行停止。”[43](P1976)这份由兵部尚书、侍郎及车驾司郎中、员外郎集体签名的文书得到了康熙的批准。
与捐造战船一样,档案中记载的捐马者中不乏督抚等高级官员。它再一次验证了由于战争的需要,平三藩期间的捐例没有对捐纳者的身份做出严格的界定,仍属于战事中的非常规捐纳。但是,与捐造战船不同的是,捐马已经与官员的仕途有了直接的关联,规定了对捐马者的议叙标准,成为日后对该员升迁调补的依据。
三
相对于当时通行的“现行事例”,“暂行事例”也属于清政府为平定三藩而开启的非常规捐纳,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被称作“暂行事例”,它作为一种应急情况下筹措资金的蓝本被保留了下来。
“暂行事例”直接规定了捐银得官的比价数额,其“作用”与危害性也最大,向为研究者所关注。然而,档案中没有留下平三藩期间捐纳事例的完整内容,有关研究主要采用许大龄先生根据《云自在龛笔记》所作的梳理,分为两项,即军需捐纳与赈济捐纳。[44](P26-27)本文整理如下:
军需捐例规定:(1)捐虚衔捐出身。笔帖式等捐银二百两给八品顶戴,包依佐领子弟照例捐银准为监生。(2)捐革职起复。因公诖误及江南抗粮案内革职官员,内外四品以下者及进士、举人、生员俱准捐复,照原品录用。(3)捐中书与知县。进士捐一千两以中行评博及内阁中书用;举贡分别捐银一千两、两千两以知县用。(4)捐免候选。汉人候选各官,自通判、知县、州同、州判、县丞、经历、主簿等分别捐银五百至二百不等俱准先用,候选州同州判经历捐一千两者以知县用,捐一千五百两者以知县先用。
赈济捐例:(1)外官告病起复捐纳。文职自道员至佐贰、武职自副将至守备,分别捐银四千至五百两不等。(2)贡监捐纳知县。贡监生充教职未考职捐一千两,官监生捐一千二百两,监生准责已考职者捐一千五百两,例监未考职者捐一千七百两,俱以知县用。(3)进士捐五百两以内阁中书用。(4)廪生捐三百两准作岁贡。
同时,许大龄先生还根据《六部则例全书》整理出康熙十九年(1680)的“贵州捐例”。此次捐例规定:“除原革职、贪酷、侵仓粮、大计军政处分、失陷城池官员,并一应因公诖误革职之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文武布政、总兵以上官员不议外,在外参政道员、副将以下官员并进士富民,情愿捐助粮草,分别鼓励。”凡捐纳之富民,给八、九品顶戴荣身,并给匾旌奖,廪生、增生、青衣生、俊秀可纳监,廪、附生并得捐为岁贡生。现任官员捐加级纪录,革职离任捐官复原职,而捐纳知县者又可捐先用、即用。
而且《六部则例全书》对捐纳数额也有明确记载:“查定例准贡生监生考职者纳银一千五百两,未经考职者纳银一千七百两,俱准以知县用。今议,考职者纳米四百八十石,或草三万三千六百束,未考职者纳米五百四十四石,或草三万八千八十束,俱准以知县用……并定例,加纳知县者,再加银一千五百两,准其盖行先选。今酌议加纳知县者纳米四百八十石,或草三万三千六百束,准其先选。如有纳米六百四十石,或草四万四千八百束,于先选之中,与长沙等处捐纳者分缺即用。”[45]
在上述捐例中,除了捐出身、捐虚衔等属于“现行捐例”外,捐实官、革职捐复、捐免、捐先用、捐即用等,基本构成有清一代“暂行事例”的核心内容。
但由于上述某些内容属于孤证,总会给人以不甚确定的感觉,这里,本文拟利用《清经世文编》中左都御史、御史等言官们的奏疏,对上述捐例进行印证和讨论。
第一,捐实官(主要是捐正印官知县)与捐先用、捐即用。康熙十六年,左都御史宋德宜有三年开捐,“捐纳最多者,莫如知县,至五百余人”的说法,“请敕部限期停止,慎重名器”。[46]可见,在时人的认知中,以捐纳知县对铨选的冲击最大而非议之,且与之并行的还有捐先用、捐即用。对此,接二连三有官员提出异议。
如御史蒋伊上《甄捐纳以恤人才疏》曰:“查康熙九年起至十八年,应选者不下两千人。每遇铨除,捐纳者居十之六,应选者居十之四……捐纳知县,原出于一时权宜之策,乃有先用,又有即用,更有小京职之一途。”[47](P429)可见,在乎三藩期间,仅捐纳知县便在应选官员中占去了百分之六十的绝对多数,而且有捐先用、捐即用、捐小京官等捐例。而蒋伊所言及捐纳知县在选宫中的比例,康熙后期,历官左都御史、户部尚书的田从典也有类似的议论,他在《疏通选法疏》中说:“今以选法论之,十七人为一班,推升捐纳共得其七,进士举贡共得其十,不为不多矣。然举贡以两途而得五人,不特少于进士,亦并少于推升捐纳。”[48](P427)
众多捐纳人员涌入官僚队伍,且可捐先用、捐即用,直接造成官僚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而其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对官僚体制、特别是对铨政的冲击,影响到正常的仕进。所谓“捐先用”、“捐即用”,即捐纳者在官员制度化的选班中,可以通过纳银打破正常的任官秩序,居选班之先,甚或当即选授为官。而变考试做官为花钱买官,是对被视为传统选拔人才“长策”的科举制度的重创。因此,蒋伊在条奏中呼吁:“将捐纳未选者,在内责成吏部,行拣选之法……其捐纳已选者,在外责成督抚,行保举之法。”康熙三十年(1691年)初,清军征剿噶尔丹,因军需浩繁开捐,四川道监察御史陆陇其上《速停保举永闭先用疏》,直接抨击曰:“前此有捐纳先用一例,正途为之壅滞,至今尚未疏通。”“臣窃见近日督抚于捐纳之员,有迟之数年既不保举又不参劾者,不知此等官员果清廉乎?”故认为,“不但目前先用之例万不可开,而从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49](P425)请敕部查一切捐纳之员,将到任三年而无保举之捐纳官员罢任,以澄清吏治。
第二,捐纳生员与贡生。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左都御史徐元文上《酌议捐纳官员疏》,曰:“伏察康熙十八年定例,凡捐纳授官及捐纳复职州县,到任三年后,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题参,照例议处,其官箴有玷者不时题参。是凡捐纳之人,无论称职不称职,皆当以三年为限分别具题也。”“所亟宜停止者也,岁贡一项。所谓正途,自捐纳事例渐推渐广,而生员、俊秀并得输纳,嗣又开捐纳生员之例,虽复目未识丁,而今日纳生员,他日即纳岁贡,名则清流,实多铜臭,公然冒滥,自诩正途。臣以为正途非可捐纳而得,其由捐纳岁贡得官者,仍须保举。”并请于滇南收复之日停止捐纳。[50](P430)
对于徐元文上述条奏,《康熙起居注》概括为三层意思:“捐纳官员三年满后,应定去留,其捐纳升转请行停止;捐纳贡生,有保举者方入正途;云南荡平之后,捐纳事例应行停止。”[51](P715)然其重点在于徐元文所痛斥的捐纳生员与贡生。特别是生员,乃读书人取得功名、晋身为“士”的身份标识,是科举考试途中的第一步,生员不但可以考取举人、进士,也可走举贡一途。所以,生员可以捐纳,则无疑使正途出身的进士和举贡中也掺入了捐纳的成分,它的潜在危害在于对传统选举制的破坏。为此,康熙十五年,暂行捐例实行不过一年多,江南道御史田六善即针对捐纳生员一项力陈其有伤国体:“纳监者从来本有之例,纳生员自古未有之条,从前黄宫之士皆市读书之人,忽而二百两侧其中,则人皆不以之齿矣。有力之家必惜体统,如此进步何足为荣。臣谓虽悬捐纳之例,必无捐纳之人,无益军需,徒伤国体耳。”[52]
第三,捐纳未经考职即授正印官。康熙二十四(1685)年正月,新任左都御史陈廷敬上《请严考试亲民之官以收吏治实效疏》:“自捐纳以来,有未经考试之人辄授正印亲民之官者。”“臣查俊秀一项,初捐既是白身,有司曾未一试,而吏部辄与选补……臣又查吏部有考试招民知县之例。……臣愚谓知府知州知县,凡俊秀捐纳有已经考职后捐纳者,依例选补。有未经考职遂行捐纳者,于补选之时仍行考试。”[53](P427)说明开捐之后,由于相关机构的急功近利,竟将未经任何考试之人直接授予官职,甚至授予守土一方的正印官知县、知州等官。对此,雍正初年,御史顾琮曾尖锐地指出:“今不问才也、能也、文理优通也,朝为白丁,上一千七百两,而暮则堂堂县令矣,再上一千两而先用,再上一千两而即用矣。通计不过三千七百两,即授一小县而烟火万家,司其政令光荣极矣。”[54](P432)它说明捐纳选官过程中缺少了必要的考察机制,但论银两,不计才能。所以,陈廷敬提出:“亲民之官,其职至重,至于文移簿书期会讼狱之事,皆身自经理,不得假手胥吏,使夤缘为奸其事又甚难也。”因而,“须略晓文义之人委以民社之寄”。他根据兵部有考试武举、吏部也有考试招民知县的先例,提出对捐纳正印官者进行考试。
第四,“捐复”。“捐复”一项弊端尤多,它为许多革职官员甚或劣迹昭著之人提供了起复的机会。根据许大龄先生提供的资料,当始行于康熙十九年的贵州捐例。他认为:“贵州事例之开,系因袭广东、长沙,当时开例之广,规模之宏,实为道咸以后张本。”清制,凡革职官员均在八法处分之例,非“不谨”、“疲软”者,即属贪酷,不乏侵盗钱粮之人,均在不称职之列。所以,捐复是所谓“金多者可与称职者同科矣”!但官员在倡捐之时,往往为求捐纳数额,而不计捐纳后果,其中也不乏贿买之人。顾琮上《请分繁简重名器疏》指出:捐纳“降级还职犹可言也。而革职者,朝而白身,暮以五千两而黄堂矣。彼既费有重资,能保其不取偿百姓乎?”[55](P432)
康熙二十年(1681)十二月,有原任佥都御使史赵之符,在大同捐米一千石,报捐复原官。为达目的,他与“山东巡抚赵祥星结为兄弟,在京奔竞”。[56](P720)虽然尚无资料对这些捐复官员的品行作出评价,但从康熙四十四(1705)年的山东捐例可以看出其问题的严重性和潜在的危害。有披露曰:“革职知州谢廷玑有应追库帑五万两、米一万石未完,捐银一千二百两,即议以原官补用;郎中靳治豫、员外郎席永勋俱以行止不端革职,靳治豫捐养用银一万三千两,议复原官,以应升之缺即用。席永勋止捐养用银六千二百两,亦议复原官,以应升之缺即用。”[57]我们不妨借用顾琮之言:“彼既费有重资,能保其不取偿百姓乎?!”
总之,由以上档案和奏疏,可以认为,在平三藩期间所开的“暂行事例”中,有捐造战船、捐马等捐项,它在客观上保证了清军在平定三藩战争中取得胜利。虽然它只行于战事中,但开启的捐纳风气却留下了深深的隐患。而作为官典被记载在则例中的“暂行事例”,因与铨政直接相关,对官僚体制的冲击最大,它所规定的议叙选官,即由虚衔而实官,由知县而知府,由先用而即用,并为后来所沿袭。其影响之深,时人王士祯以其七年任职户部侍郎的经历评论说:“顷自滇闽两广用兵,始开捐纳之例。始犹经户部斟酌,不致过烂。其后陕西赈荒出塞运粮等事,则渐泛滥矣。始商人巴某等初捐即补知府,言官论之,因革去。其后于振甲为总镶都统,则不由户部及九卿集议,径移吏部铨补,于是佥事方面显官,亦在捐纳之例,初任即得补授,不惟知府矣!”[58](P235)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吏治的败坏始于铨政,其源头在于捐纳,而捐纳中的“暂行事例”则创于平三藩。
发人深省的是,在康熙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同时,其代价除了八年战争的生灵涂炭外,官僚政治体制也由此遭到侵蚀。对捐纳之弊,无论是官僚大臣还是康熙本人,都知之甚悉,每声言“捐纳非善事”,但终因“无旁策以补库绌,仍将依仗捐纳”,并将捐纳进行到底,伴随了有清一代。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饮鸩止渴”吧!
注释:
①武职可捐至副将,是许大龄先生根据《云自在龛笔记》所得,见许大龄:《明清史论集》,26~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而《清史稿·选举志·捐纳》则曰:“文职小京官至郎中,未入流至道员;武职千把总至参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