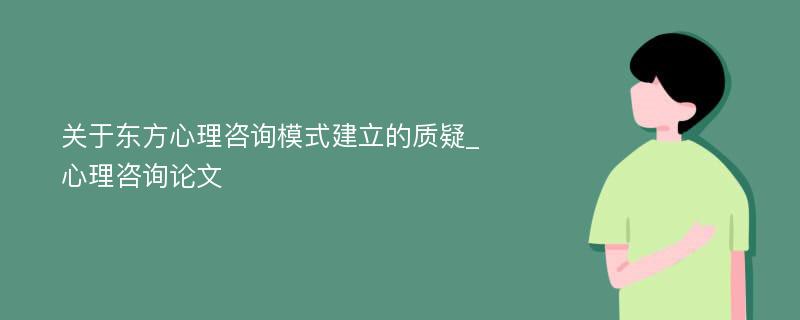
对建立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咨询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3)02-0071-04
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的对立现象,也普遍存在于心理咨询和治疗界。由此引出另辟东方心理咨询模式以别于西方心理咨询模式是否适宜的争论。文化普遍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基本特性相同,东方人和西方人共享同一人类文明,因而,主张无所谓特意的东、西方咨询和治疗模式之别。而文化的相对主义观点则指出,任何绝对文化主义的理论在不同文化圈内的实施都是困难重重的,因此,极力主张东方人应有自己的咨询和治疗模式。那么,如何看待咨询治疗和文化的联系呢?本文在分析了文化的相对主义关于此问题的观点后提出作者的一家之言。简言之,笔者更倾向于文化的普遍主义观点,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圈不一定要刻意追求独有的咨询模式。当然,这不等于否定在不同的文化中咨询会存在种种差别。
一、支持东方心理咨询和治疗模式的观点
早在1969年,李东植(韩国)就提出东方的道德思想是东方社会克服现代文明缺陷的唯一道路,认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东方心理咨询者和治疗者应从西方的理论方法中摆脱出来,代之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的理论方法[1]。这一事件说明了东方国家的咨询事业的发展,还是反应了文化本位思想的抬升。在1994年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精神治疗学会上,心理学家终究就这一理论探讨了其可行性。
综观这一方面的研究,可见支持东方心理咨询治疗模式的论据如下:
1、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
东方的主流哲学思想应公推儒家思想,它重视集体的或国家的利益,讲究“精忠”,强调服从,行为适当,道德训练和接受社会义务,人际关系方面强调权威性,注重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而西方的哲学主流应是倡导个人自由、自我实现的人本主义思想,它重视个人的价值和自由,重视个性,个体具有明显的个人性格,如自我实现、竞争、享受、自由和平等。这导致东、西方人对心理健康的定义、正常人的合理行为标准、以及人际关系的标准的认识都大相径庭[2][3]。儒教认为人性本善,要想寻求内心的安适或心理健康,就要回归为善的本性。儒家思想认为人类的成熟状态应该是人类随心所欲地行动却不会违背法律道德。而且认为陷入本能的欲望,失去道德理性就是精神病理状态,进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是通过“克己复礼”。但西方人普遍认为欲望和本能的压抑过度会产生精神病理状态,趋向健康的生活道路就是通过“疏导”,通过创设一定的环境,提供一定的帮助,使人能够满足所需,能够自我实现,趋向健康。
2、东、西方人的意识结构存在差异
韩国的李符永认为韩国治疗来访者的意识结构的范围要比西方来访者的意识结构范围宽泛[1]。他认为,在西方看来是属于无意识的领域对于东方人来说则已属于意识范围,东方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立关系不是那么尖锐,而且,延伸至无意识深层次领域的东方人的意识往往没有得到表现就被沉默了,因而认为东方人的沉默不是无知而是既知。东方人有高超的暗示技巧,因而西方人就难以理解东方人不直接用言语和行动直接表示出来的暗示。华裔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许琅光曾于1985年从自我结构与界线的角度进行了分析[4]。对东、西方人来说,同样是“自己”,却有不同的“自己”的结构和界线。以个人为取向的西方社会,自我的界线相对地较为分明,注重内在精神需要,与周围外界的家人、亲友或朋友较疏远。西方文化培养的是“个性化”的自我结构,自我有独立性、可分化性,这使得个体容易将自己当作客体来看待,一旦出现心理异常,就容易出现与生存有关的情感体验。然而,在以他人为取向、强调人际关系的东方社会(包括华人社会)里,其成员在心理结构上,“自我”(self)的界线相对地较为模糊,与外在人际关系较密切,比较忽视内在精神需要。东方人的自我结构是“非个性化”的,社会化的过程培养了个体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对多数人来说,“自我”不是一个客体。当处于心理异常状态时,“自我”不会进入到存在意识与情感需要的层次,也就不会有丧失自我意识之感受。
3、东、西方心理疾病表现以及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存在着差异
在东方社会里,心理疾病来访者否认自己有任何的心理或情绪障碍,相反地,他们常诉说自己身体不适,但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器质性病变。当然,东西方都有此种情况,但东方人更常常诉说身体症状而非心理症状[4]。例如,虽然西方已取消了“神经衰弱”这一病名,认为应归为心理病症抑郁,但神经衰弱常被看成是东方人特有的症状,表现为疲惫、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衰退、头痛失眠等身体症状。在台湾地区还出现诉说“肾亏”代替心理疾患的心理症候群[4]。
在对待心理咨询的态度上,东西方也表现出了差异。一方面,在东方人的传统观念里,认为精神病变与伦理道德不相容,并常常贴上“神经病”的标签。这种歧视造成人们靠自我修养达到某种精神体验来加以排解,而不愿向他人或心理咨询员袒露自己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有来访者自愿寻求心理咨询员的帮助,也认为心理咨询员应该象教师或医生一样具有权威性,给予来访者具体的指导或直接的治疗,而不是西方心理咨询过程中咨询员建立在同感、尊重、真诚等中立的非指导原则的咨询关系基础上,挖掘心理来访者的自我潜力助其成长[5]。因此,东方文化里的来访者更关注眼前问题的解决,对长远的成长与发展不太顾及。
二、建立东方心理咨询和治疗模式引发的思考
以上有关支持建立东方心理咨询和治疗模式的论述,涉及到了本土心理咨询界中客观存在的现象和问题,由此引起对西方的咨询模式普遍实用性的怀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所述理由并不足以支持另立东方心理咨询和治疗模式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文化与心理结构以及咨询治疗的关系非常复杂,目前也不是很清楚。况且西方的咨询理论也并没有大一统,这本身就反映了西方各咨询理论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实施过程中带来的各种问题不宜简单的归纳为理论超出了所适用的文化范围。
1、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的人类的共同心理规律是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基础
尽管西方文化把精神或心情看作是心理的实体,而东方文化并不十分明确地区分心情和事物,灵魂和身体,但是这并不影响无论处于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的研究使命,即研究人的意识的变化以及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无论是在何种文化背景中,比起心理的差异性说,人类自身存在的共同心理规律是主要的,一定程度上这种规律性构成了心理咨询的基础。心理咨询理论的价值也就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多大范围内解释或解决了人类自身面临的共同问题。人类都特别关注如何认识自身在内的主客体世界,都关注如何生活得更加美好。西方心理咨询虽然是植根于西方文化,反映的是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但其所揭示的西方人心理与行为活动的规律必然有能适合中国人之处。因此借鉴西方心理咨询的成果是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步骤,在过去的20年中,对待西方心理咨询的态度可以说经历了重新验证、修正创新到逐步摆脱束缚等阶段。虽然存在的较多理论没有一致的对复杂心理现象的解释,但也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接受了许多西方心理学理论中所渗透的心理现象的诠释。心理咨询理论无论是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学派还是人本主义,其中隐含的对心理现象的解释都能在东方文化中发现它的原型。
文化的概念非常宽泛,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而且一般都不反对主流文化、亚文化、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的提法。目前,我们的世界是空前开放的,各种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融合,绝对文化观因其片面性将越来越不合时宜。文化的这种融合性体现了心理的交互作用规律。我们知道,佛教、道教和儒教实际上并行影响着东方人的世界,它们本来甚有差异,但没有影响它们的共存。在长期受西风感染的香港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6]。这种融合性说明两种文化能并存,同一人群也不是不能接受两种理念,更不用说接受具体的治疗技术。以非东方主流的老庄思想为本源,倡导“顺其自然”和“为所当为”的森田疗法在东方国家有较好的疗效[7],那么怎么能说明以人为中心的疗法与东方人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阻隔呢?而且西方人也承认森田疗法在西方社会环境中也有一定的疗效[8]。这些事实说明了问题的症结并非完全在于文化不同。林孟平教授将儒家教育思想同罗杰斯的学说作了全面的比较后认为两者有很多的契合之处[5],这种契合是该理论在中国有市场的根基。总之,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咨询人们并不清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肯定是存在的,但这种差异是否必然导致东西方咨询和治疗就必须有不同的模式呢?至少目前答案不太清楚。
2、现有的为数众多的心理咨询模式存在着整合的可能性
目前,已有上百种心理咨询理论,心理咨询从传统的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2],整合主义和折衷主义逐渐成为治疗技术的主导发展方向[9]。基于为数众多的心理咨询中没有哪一种疗法在疗效上明显高于其它的疗法,而且,单一的治疗技术常常有其局限性,于是人们认为在各种治疗方法中存在着共同的因素,这种共同的因素可以将不同的心理咨询进行整合,虽然这些共同因素与疗效间的因果关系还未确定,一些共同因素所具有的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在实践中,许多心理咨询者也是更多地以整合的方式进行心理咨询而不是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治疗理论约束。如系统疗法就是基于这种思路[10]。西方的积极心理咨询是将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技术相整合,注重与其它心理咨询流派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将原先认为不可融合的行为疗法、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中有效的方法纳入自己的治疗体系中,在不同的治疗阶段进行不同的运用。在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用太极理论,综合现代所有的心理咨询流派,形成一个综合的理论。因此,心理咨询理论不能孤芳自赏,追求所谓的“特殊化”模式(我们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而是应该将眼光投向整个心理咨询领域,在宏观上把握心理咨询的发展。
当代心理咨询呈现一种整合的取向的背景下,细心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心理咨询也积极从东方文化中汲取营养。东方文化中“标本兼治”、“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对讲究科学与逻辑性的西方心理咨询予以启发,从而注重“全人”的发展以提高心理咨询的整体效果[11]。荣格的分析心理思维就体现了与东方思维的契合,其哲学基础为道家思想。心理咨询也在运用东方的治疗技术,如气功疗法、瑜珈疗法、故事疗法、相声疗法、音乐疗法、诗歌疗法以及娱乐疗法等等[11]。同时,针对东方人特点的钟友彬先生的领悟疗法也是从临床医生的角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阐述了精神分析理论;香港学者岳晓东主张将罗杰斯非指导性心理辅导方法结合到孔子教育思想中,开发出启发式辅导模式[12]。
3、心理咨询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可分离性
由于任何理论方法都不能适合于所有来访者和所有的问题,并且相同问题用不同疗法可取得较相近的效果。虽然某一具体有效的技术(比如说放松训练或系统脱敏技术)是源于某一理论的,但由理论到技术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主观的先入之见进入,一些理论更是对技术的后验解释。据我国《续名医类案郁症》载[13]:韩世良治疗一个“思母成疾女病人”时,暗中叫女巫告诉来访者,她母亲在阴间抱怨自己因女儿之命相克而死,在阴间准备报克命之仇。来访者大怒:“我因母病,母反(欲)害我,我何思之!”她痛恨亡母之后,“病果愈”。这是中国传统情绪疗法的一个典型案例。此具体疗法是有效的,而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古代的情志相克疗法是用五行说来解释治疗的原理的。五行说认为五情归于五脏,五情相生相克,利用相生相克的原理就可以治病。上述的是怒胜思疗法。然而技术的有效不能推出理论的完全正确。理论在未成熟之前往往有很多的后验解释成分。实质上,同样的技术手段,不同的理论可以有不同的并能自圆其说的解释。由此可见,在理论不太成熟阶段,理论和技术常常具有可分离性。西方心理咨询理论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出现困难就认为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原因,还不如承认理论本身需要改进,进而去努力探寻放之四海皆准的咨询和治疗的理论和方法。这样不知要省去多少无谓的争辩。
三、总结
目前,心理咨询的本土化建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依托东方传统文化,更不是返回传统文化而刻意自成一种东方模式。我们应当考虑到以整合主义和折衷主义为主导的心理咨询发展方向。无论治疗者还是咨询师都在一个文化圈中,不可能无依托地接受西方咨询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在不断地克服具体应用中出现的困难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从而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将西方的理论结合于东方的文化,能帮助认清西方理论中的一些不正确的隐含假设,这本身就是对咨询事业作贡献。另辟东方心理咨询模式实际上是学科的离心趋势,离心趋势势必会影响学科的科学地位和发展,而且其可行性也值得质疑。应共同努力,建立一种理论框架,整合所有的咨询领域的现有成果。所以,不应赞同建立单独的东方心理咨询模式的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