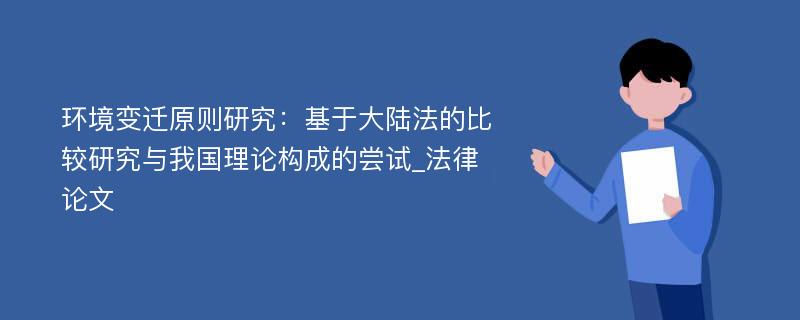
情事变更原则研究——以大陆法为主的比较考察及对我国理论构成的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事论文,原则论文,理论论文,大陆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世界上任何发达的法律体系,无不是建构在有效成立的合同须予遵守这一原理之上的,这一原理便是“契约严守”(pacta sunt servanda);我国合同法实际上也规定了这一原则(参见合同法第8条),这样便发生了如下问题,即任何合同在缔结之际,无论其当事人是否意识到,均是以当时存在的法秩序、经济秩序、货币的特定购买力、通常的交易条件等特定的一般关系(或环境)为前提的,如果这些一般关系不可预见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合同的当事人是否仍然受原来合同内容的拘束?如果不受拘束,则其要件和效果是什么?这些均是需要由通常所说的“情事变更原则”来回答的问题。
所谓情事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事情的发生(或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事变更),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或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时,则应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的法理。究其实质,情事变更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运用,目的在于消除合同因情事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注: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实践证明,情事变更原则赋予法院以直接干预合同关系的“公平裁判权”,使法律能够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更好地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经济流转的正常秩序。因此,情事变更原则已经成为当代债法最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注: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梁慧星执笔),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
情事变更原则虽然发展于人类历史的灾变时期,特别是20世纪的早期,却不独于灾变时期有其适用,这已是学说上不争的定论。在我国,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尤其是我国正处在改革时期,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对于经济活动产生剧烈影响之情形时有发生;不独国内诸多情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尤其是中国即将加入WTO,国际经济、政治的风云变幻,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经济活动的开展。如此,因情事变更而造成合同履行障碍,自属无法回避之事,我国的法律应当借鉴外国经验,备有应对之策,以避免“法律不足”之现象重演。不无遗憾的是,新《合同法》明确回避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就在此后不久,海峡对岸的台湾修正了其民法债编,明确吸收了情事变更原则。这正说明我们对于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入。(注:我国大陆关于情事变更原则的论文已经不少,但存有陈陈相因的不足,已经受到学者的批评,参见张淳:“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进一步研究”,《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本文作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对情事变更问题进行考察和探讨,就教于方家。
二、对情事变更原则的比较考察
(一)“情事不变条款”理论的沿革
1.“情事不变条款”理论
按照通说,情事变更原则并非起源于罗马法,其最初的萌芽见于12、13世纪的“注释学派”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其中有一项法律原则,假定每一合同均包含一个默示条款,即缔约时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应继续存在,一旦这种情况不再存在,准予变更或解除合同,称为“情事不变条款”(clausula rebus sic stantibus,亦称“情事变更条款”或“事物不变更约款”)。至17世纪,自然法思想居于支配地位,情事不变条款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诸如格老秀斯(Grotius)和普芬道夫(Pufendorf)的著述中均有演示(尤其是在国际法方面)。凡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法律行为,无论其属于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公法或者教会法,均有情事不变条款的适用。及至18世纪中叶,该理论同时在自然法和普通法上被更为详细地定式化,在《普鲁士一般州法典(ALR)》以及《奥地利一般民法典(ABGB)》中均有规定。到18世纪后期,情事不变条款的适用过分广泛,以致被滥用,损及法律秩序的安定,在学说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然拿破仑战争以及大陆封锁的时代、革命战争的动乱以及德意志第一帝国的解体,则对于该理论又重新赋予了效力。19世纪初,德国历史法学派兴起,对于自然法以及受自然法影响的法典化思想予以低调的评价,一时间“情事不变条款”理论在德国的法学理论上偃旗息鼓;在萨维尼(Savigny)的巨著《现代罗马法体系》(System des roemischen Rechts)中,以及在19世纪的大多数潘德克顿教科书中,甚至根本未提及这一理论。(注:参见〔德〕Karl Larenz:《行为基础与合同的履行》(〔日〕神田博司、吉田丰译),中央大学出版部1969年版,第19-20页;彭凤至:《情事变更原则之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前言。)
2.“前提假设论”及其争论
针对上述空白,在1850年温德赛特(Bernhard Windscheid)(注:温德赛特可以说是19世纪潘德克顿法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同时也是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主要起草人。他致力于“罗马法德国化”,亦即综合罗马法的传统和德国法的传统,在现行法的基础上制订一套没有矛盾的法的信条。温德赛特作为准备制定民法典的首届委员会的委员,并通过他那基本的《潘德克顿教科书》(3卷,1862-1870年,1906年第9版)对德国民法结构的形成和法官的审判都有很大的影响。德国民法典的时常受批评的“教条主义”就是温德赛特的“概念法学”的一个结果。参见〔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0页。)发表了一篇专题研究论文,(注:Die Lehre des roemischen Rechts von der Voraussetzung.)提出了与情事不变条款相似的“前提假设论”(德Lehre von der Voraussetzung,英the theory of presupposition),其主要思想后来收入其《潘德克顿教科书》第2卷中。(注:Pandekten,II,8th edn.By Kipp,1900.)其理论认为,行为人通常假定其所欲追求的法律效果惟在一定的环境下始得发生,然而,这种关于事物的特定状态之持续存在的假定(assumption)并未被作成合同条款。如果相对人业已意识到这种“预想”(presupposition)已根本性地影响了行为人的意思,则一旦这种基本的假设(预想)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就不应当令行为人受其诺言的拘束。这便近似于说合同本身的缔结是附条件的,条件即被假定的事物的状态在合同的有效期间保持不变,这便是为何温德赛特将这种假定描述为“不完全条件”(德unentwickelte Bedingung,英inchoate condition)。这一理论因而被称为“前提假设论”。(注:Cf.B.S.Markesinis,W.Lorenz & G.Dannemann,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Vol.I,(1997),Clarendon Press·Oxford,p.517.)温德赛特所谓的“前提”,是位于动机和条件中间的自己意思的限制。这种前提如属自始欠缺或消失之场合,则发生当事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前提在后来丧失之问题,这一点上该理论便与情事变更原则具有关联了。(注:〔日〕五十岚清:《情事变更原则与行为基础论》,载〔日〕加藤一郎、米仓明编:《民法的争点Ⅱ》,有斐阁1985年版,第95页。)
对于温德赛特的理论,关注交易安全的学者们予以了反击。他们认为,一方当事人单方面的动机,即使为对方所认识,也不能够像条件那样来对待,除非它们已经被订入了合同。否则,就会允许一方当事人将其合同风险转嫁给另一方,必会损及法律的安定以及商事交易。不过,他们认为法院可以采用其他的手段来处理这类案件,因为法院可以在其认为其介入是公正而衡平的场合,推定对解除权的保留。反对派的观点占了上风,特别是由于温德赛特没有再被任命为民法典第二草案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他189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注:AcP 78,161,197(1892).)温德赛特作为对其论敌勒内尔(Lenel)1888年提出的反对意见(注:AcP 74,213 et seq.(1888).针对温德赛特的反驳,勒内尔后来又专门撰文再作反驳。Lenel,Nochmals die Lehre von der Voraussetzung,in AcP,79,49-107(1899).)的回答,反驳认为对这一问题不能够置之不理,认为“默示的预想(tacit presupposition)理论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承认,你把它从门里扔出去,它还会从窗户里再进来。”他在主张解决这一问题方面是正确的,然而他的理论却并不怎么正确。(注:Cf.B.S.Markesinis,W.Lorenz & G.Dannemann,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Vol.I,(1997),pp.517-518.奥特曼显然扬弃了温德赛特的见解,指出:自罗马法以来整个法律的发展证实,无论实定法如何排斥情事不变条款,它总是去而复来,无法消灭。Oertmann,Die Geschaeftgrundlage,Leipzig-Erlangen,1921,S.45,48,135,139,140,143.转引自前引[4],彭凤至书,第154页。)他的“前提假设论”最终是承认动机错误的,有害于交易安全,在这点上受到了通说的批判,并从德国民法典中消声匿迹了。(注:前引[9],〔日〕五十岚清文,第95页。)
3.19-20世纪之交时期的状况
后起的分析学派(Pandektenwissenschaft),强调实证法主义(Rechtspositivismus),主张形式正义,重视契约严守及法律秩序的安定,因而情事不变条款学说愈益丧失其重要性。(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2页;前引[1],梁慧星书,第180页。)尽管情事不变条款在一些法典中被规定为正式法律条文,但在《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及《德国民法典》中均未规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承认情事不变条款法理(clausula法理)会使合同的解消变得容易,与伴随资本主义的发达而确立的“契约严守”原则是相对立的。整个19世纪,“契约严守”原则居于统治地位,这些法典未规定情事不变条款法理,自属当然。(注:前引[9],〔日〕五十岚清文,第9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发了经济社会的大动乱,大量的现实问题使得已被各国忘却了的clausula法理重新被人想起。(注:应当注意到,情事不变条款亦有其缺点,正如彭凤至女士指出的,首先,情事不变条款一如“条件”,即正由于当事人对于环境的持续不变,认为确定不疑,因此未将之作为条件,也因此不能解释当事人“默示”合同中应包含一项“情事持续不变”的条款。换言之,当事人愈是确信环境不变,因而未作任何防范措施,同一旦情事发生变更时,愈不能认为当事人于为法律行为时,有加效力保留条款的意思。因此,严格而言,愈需要以情事不变条款解决的问题,理论上愈不能以之作为解决依据。其次,情事不变条款只涵盖了一群自法律政策的角度观察,性质类似的问题的一部分,可称之为一项未思考完全的概念。因此,整个情事不变条款学说,仅能视为一种以不完全、不充分的方法,解决一群较其想象更为广泛且普遍的问题的一项尝试。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37页。)比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解决情事变更问题,学者和实务方面主张改变立法精神,采解释方式弥补“法律漏洞”,而立法者则坚持民法典的立法精神,不承认有“法律漏洞”,而是采取特别立法方式解决各种特殊问题。
(二)德国的“法律行为基础”理论的发展
1.“经济不能”理论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与经济的混乱,导致了大量的合同根基的动摇,判例上尽管肯认了对债权人的合同内容的改订或者将合同解除的权利,但是这时的理论所采的法的构成尚为“经济不能”的理论(Lehre von der wirtschaftlichen Unmoeglichkeit)。德国民法典对于债务人债务免责所作的一般规定是法律不能与事实不能(第275条),而经济不能的理论,是将经济不能与法律不能及事实不能作同样的处理。所谓经济不能,指超出义务的困难(überobligationsmaessige Schwierigkeit),亦即,给付的实现本身虽属可能,然给付的实现,在诚实信用原则上,只有当债务人在其原来负担的义务之外再作出牺牲(Opfer)或者付出始属可能,这样使得给付的实现具有巨大的困难。不过,按经济不能处理问题只是一时之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主张“不能”如果获得了法院的认可,其结果是合同自动地解除,而事实上,大量的纠纷很快即表明,这一结果在很多时候,不符合任何一方合同当事人的意愿。(注:Cf.B.S.Markesinis,W.Lorenz & G.Dannemann,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Vol.I,(1997),p.523.)于是,判例上在1922年(RGY,103,328)采用了奥特曼所主张的行为基础丧失理论,自此以后,这一理论成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时的主导性的视点。(注:参见〔日〕椿寿夫、右近健男:《德国债权法总论》,日本评论社1988年版,第31-32页。)
2.奥特曼的行为基础丧失理论
1921年,德国哥庭根大学的奥特曼(Paul Oertmann)教授参考“情事不变条款”理论及“前提假设论”,提出了“行为基础说”(Geschaeftsgrundlage),随即为法院判例所采纳,成为裁判上的固定见解。(注:奥特曼的著作《行为基础:一个新的法律概念》的出版,恰值一战后德国法院急需为其以实用主义之方式解决新问题提供理论基础的时候,可谓是生逢其时,在这点上,奥特曼的确比其岳父温德赛特幸运得多了。)依奥特曼的解说,所谓“行为基础”,是指“(交易)行为缔结之际表现出来的、且当时相对人明知这种前提观念的重要性而未作反对表示的一方当事人的前提观念(Vorstellung,预想),或者多方当事人共通的前提观念,是行为意思(Geschaeftswille)得以构筑其上的、对于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发生所具有的前提观念。”(注:P.Oertmann,Die Geschaeftsgrundlage,Leipyig 1921,S.37.转引自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11页。另外参见前引[18],〔日〕椿寿夫、右近健男书,第32页。“奥特曼公式”的英文译文为:"'Contractual basis' is an assumption made by one party that has become obvious to the other by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tract and has received its acquiescence,provided that the assumption refers to the existence,or coming into existence,of circumstances forming the basis of the contractual intention.Alternatively,'contractual basis' is the common assumption on the part of the respective parties of such circumstances."translation by EJ Cohn,"Frustration of Contract in German Law",(1946) 28 J Comp Leg & Int L 15,20.)此项概念的提出,意在尝试弥补德国民法由于接受齐特尔曼(Zittelmann)对于“错误”这项法律制度之研究与分类,使得所有关于人与事物的“期待”(Erwartung),除了“本质错误”(Eigenschaftsirtum)以外,均纳入法律上不予考虑的“动机”范畴之内而产生的法律漏洞。(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31页。)因行为基础有瑕疵(自始欠缺或嗣后丧失)而受不利益的当事人,具有消灭合同关系的权利。
根据奥特曼对行为基础所下的定义(称奥特曼公式),奥特曼认为法律行为基础应当具备以下特点:(1)法律行为基础为法律行为的客观的基础,而非任何当事人为意思决定及为表示时的主观的基础,因此与动机截然不同。(2)法律行为基础并非法律行为的构成部分,尤其不须明示提升为限制法律行为效力的条件。(3)法律行为基础并非一般所称的法律行为目的(causa,原因)。(4)法律行为基础概念本身的确定标准应当是主观的,是依当事人的“预想”而定的。(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32-33页。)
行为基础理论与情事不变条款的关系极为密切,可谓是就同一种法律政策而发展出来的两种不同对策方式。但二者仍有一些区别在于:(1)情事不变条款是默示的合同条款,因而是合同的构成部分;法律行为基础并非合同的构成部分。(2)情事不变条款乃“拟制”当事人的意思,而法律行为基础则不须借助于这种“拟制”;(3)法律行为基础所涵盖的范围比情事不变条款更广泛。(注:参见前引[1],梁慧星书,第183页;前引[4],彭凤至书,第36页。)
奥特曼的行为基础理论虽然是在修正温德赛特的“前提假设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在奥特曼的行为基础理论中,对于事物的未来进程的预想,单纯地由后来遭受不利益的一方单方面拥有尚未为足,该方当事人须对此预想在合同的缔结过程中表露出来,而且要为对方所默许。因而,奥特曼已经从其岳父温德赛特强调的当事人的希冀和期待,转向了变更的情事对于(交易)行为的外在的效果。(注:Cf.B.S.Markesinis,W.Lorenz & G.Dannemann,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Vol.I,(1997),pp.518-519.)
3.判例的展开与学说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判例虽然仍以奥特曼的公式作为判断行为基础的依据,不过更加推进了一步,认为因情事的变化而导致债务人“期待不可能”(unzumutbar)场合,即存在行为基础的丧失,以期待不可能作为判断标准而予以强调。不过,对于判例的这种动向,学说上是持批判的态度的。比如拉伦茨(Larenz)认为,判例此一动向放弃了对行为基础之要件的具体化和类型化,最终对于要件和效果,公平的考虑(Billigkeitserwaegung)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因素,导致行为基础丧失场合允许的订正的合同解释(korrigierende Vertragsauslegung § 157),与法官根据公平裁量改订合同场合的合同救助(Vertragshilfe)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注:参见前引[18],〔日〕椿寿夫、右近健男书,第32页。)这样,学说上便力求基于一定的方针,对行为基础丧失的典型事例加以类型化,具有代表性的见解为拉伦茨的行为基础丧失理论。
4.拉伦茨的行为基础丧失理论
行为基础说提出后,引起了学者间数十年的争论,其焦点在于:究竟什么是行为基础?二战后,拉伦茨提出“修正行为基础说”,(注:拉伦茨认为,奥特曼所提出的法律行为基础学说,理论虽然成立,但用以解决其所提出的问题态样,一方面显得太宽,因为如果严格以奥特曼公式加以衡量,则许多使用目的不能实现的问题均将成立法律行为基础丧失案例,如此,以交易安全所要求的合理危险负担而言,实有失公平;另一方面,则又显得太窄,因为它只问当事人的预想,而不问实现当事人共同的合同目的、客观必要的环境因素为何,因此,一旦发生最常见的案例当事人未作任何预想而情事变更时,法律行为基础学说反而无用武之地。因此,拉伦茨综合温德赛特、奥特曼、考夫曼、克吕克曼等人所提出的主、客观学说,主张区分主观及客观行为基础,以求法律行为基础学说在适用上趋于具体化。参见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24页;前引[4],彭凤至书,第43页。)将“行为基础”区分为主观的行为基础(Subjectiver Geschaeftsgrundlage)和客观的行为基础(objectiver Geschaeftsgrundlage)。
“主观的行为基础”,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表明了的并且对于双方当事人动机的形成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前提观念。“客观的行为基础”,指作为合同的客观基础,是为了实现合同的客观目的而在逻辑上必须存在的全部情事。因而,“客观的行为基础”指的是当事人在达成合同时并未存在于其头脑中的情事。(注:参见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29页。)其结果是,行为基础丧失理论被适用于所有的情事变更,而不论当事人在达成合同时是否在头脑中意识到了这些情事。(注:Cf.Wemer F Ebke and Bettina M Steinhauer,The Doctrine of Good Faith in German Contract Law,in Good Faith and Fault in Contract Law,ed.by Jack Beatson and Daniel Friedmann,(1995),171,184.)
在拉伦茨看来,主观的行为基础是动机发生过程(Motivationsprozess)的构成部分,因而,对主观行为基础在法律上的把握,是与动机错误的理论以及“意思欠缺”的理论相关联的。与此相对,客观的行为基础是与合同目的以及合同双方当事人全体的意图是否实现相关联的,从而,对于客观行为基础的处理是与主观不能、后发的客观不能以及目的达到的理论相关联的。(注:从比较法来看,这种区别在英国法上是特别明了的,在英国法上,拉伦茨所谓的主观的行为基础的诸事例是被作为共同错误(common mistake)的事例处理的;另一方面,客观的行为基础消灭的诸事例,与后发的履行不能的事例一同,被以“合同基础”(basis of contract)的消灭的观点加以把握。另外,在奥、瑞两国的理论或者法律上亦有与拉伦茨的此一分类方法的相似之处。参见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30页。)主观的行为基础丧失方面所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共同的“动机错误”。(注:此所谓共同的动机错误,其典型的案型为:(1)双方当事人对于共同认定的计算基础、和解基础发生错误;(2)双方当事人对于据以签约的事件,或对于决定将来给付的情事或关系的持续不变,发生错误的期待等。)客观的行为基础丧失,主要发生在两种场合,一是所谓“等价关系的破坏”(Aequivalenzstoerung,或作“对价关系障碍”)场合,另一则是“目的不达”(Zweckvereitelung)场合。(注:参见前引[18],〔日〕椿寿夫、右近健男书,第33页。)
拉伦茨的修正法律行为基础说一经提出,便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而成为德国目前的通说。但在主观基础与客观基础之划分标准上,受到严厉的批评。(注:不同意拉伦茨的修正法律行为基础说者,如学者莱曼(Lehmann)认为,严格划分主观与客观法律行为基础实际上并不可行,故将二者合并观察,出“联合公式”,认为“所谓法律行为基础丧失,乃指契约当事人于签约,如曾考虑到某种情事之不确定性,则该契约之相对人,依诚实信用原则并兼顾契约之目的,必曾以该情事之存在为契约效力发生之前提,或公平而言应该以之为契约效力发生之前提者。”又如学者费肯歇(Fikentscher)认为,情事变更原则问题即为合同危险问题,因此基本上一旦问题发生,即应当先考虑各种债之中,有关危险负担的任意规定,经由直接或类推适用此类规定,应当可处理大部分情事变更原则问题,无法解决的,始可考虑较一般化的观点,称为“信赖基础”,是为信赖基础说。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45-47页;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25页。)
8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越发认识到,情事变更原则问题乃是合同的实质公平问题,随着合同法的伦理化及形式主义合同概念的扬弃,使情事变更原则愈益增加其重要意义。主张彻底改变民法典立法精神,直接以“实质的合同概念”作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的理论依据。在方法上突破概念法学的限制,有效运用“判例拘束”方式,创设在法律行为基础概念之下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经此派学者修正,法律行为基础成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的概括性上位概念,在此概念之下,以“对等性原则”及“无期待可能性原则”为事实上的决定标准,并根据无期待可能性的程度,决定法律效果为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47页以下。)
法律行为基础学说提出后,经过法院判例反复引用,形成一项具有一定功能与内涵的新兴法律制度,称为“法律行为基础制度”。一战以后的实践证明,该制度是用来处理经济及社会情况剧变问题的有效制度,是用来排除因情事变更所发生的不公平后果的普遍准则,并成为打破契约严守原则的途径之一。(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52页。)此项制度虽形成于灾变时期,然其运用却不限于灾变时期,尤其对于社会环境瞬息万变的现今时代,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制度。
(三)法国的“不预见理论”(théorie de l'imprévision)
如果合同缔结之时未曾预料到的新的事态发生,则对合同是应当严格强调其强制力而要求当事人严格履行抑或应当允许当事人以此为由主张合同的变更呢?对此问题在法国有不同的看法。原来法国法院坚持契约严守;而反对的见解则认为应肯定合同变更的可能性,此类理论便被称为“不预见理论”。
目前在法国法上,行政法院对于“行政合同”(contrat administratif)一般肯定了不预见理论的适用,这被认为是行政合同的一个特色。而与此相反,对于民事合同,司法法院基于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严格地维持合同的强制力原理,原则上并不肯认情事变更之主张。这一立场,自法国破毁院1876年3月6日判决(canal de Craponne事件)以来,迄未变更。(注:参见〔日〕山口俊夫:《法国债权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65页。有关法国破毁院“卡波纳运河事件”案的中文介绍,可参见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在法国学说上,肯定“不预见理论”的学者认为,合同乃应予诚实履行的事物,肯定情事变更之主张,合乎正义衡平的要求。针对此类见解,反对的学者认为,允许因事件的发生而变更合同者惟限于构成不可抗力之场合,债务人的负担纵然过大亦须履行合同,此乃合同制度的本质使然。如果根据衡平或者正义之类的一般概念而认有合同拘束力的例外,则必然害及交易的安全。两派观点在早些年争论比较激烈,现在这种争论已趋于平静,有力说基本上一致支持判例的立场。另一方面,此派学说认为,在发生的新的事态超出了当事人合同经济的范畴,而涉及社会的一般利益之场合,对于合同关系作系统的变更,这并不是法官的任务,而是立法者的任务。(注:参见前引[35],〔日〕山口俊夫书,第65-66页。)
实际上,在因事态的发生而需要系统地变更合同关系之场合,法国的立法者到目前为止已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加以介入,这也是使学说上有关“不预见理论”之争论趋于平静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世界大战后,法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变更租金或者租赁期间的法律、变更转让营业财产的价格的法律、增加终身定期金的法律等。而且,也通过一些立法措施,肯定法官通过考虑债务人的情事、经济状况、合同条款的性质等变更合同的权限。这些措施常常改正了民法典的规定本身,合同的强制力对法院的效果也得到了缓和。(注:参见前引[35],〔日〕山口俊夫书,第66页。)
(四)我国的情况
1.大陆学说
在我国学说上,情事变更原则是被普遍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陆的学说上,最早系统论述此一问题的是梁慧星先生,他在1988年发表的《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问题》一文,(注:梁慧星:“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问题”,载于《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情事变更原则的历史沿革、我国解决情事变更问题的实践、大陆法上关于情事变更问题的学说与实践、英美普通法上的合同落空问题等,为我国大陆此一领域的奠基性论文。此后发表的论文,笔者所见到的约有20-30篇。(注:杨振山:“试论我国民法确立‘情事变更原则’的必要性”,《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肖学文:“论情势变更原则”,《经济与法》1991年第5期;史浩明:“我国合同法应确立情势变更原则”,《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耀振华:“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法学研究》1992年第4期;彭诚信:“‘情事变更原则’的探讨”,《法学》1993年第3期;夏先鹏、刘凌云、刘晓安:“情势变更原则及其表现形式”,《法学评论》1993年第3期;彭真明:“民法上的情势变更原则论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于伟:“情事变更原则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中的适用”,《政法论坛》1993年第5期;黄小民:“论情事变更原则在经济审判中的适用”,《经济法制》1994年第2期;张庆东:“情事变更与商业风险的法律界定”,《法学》1994年第8期;马俊驹:“我国债法中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法学评论》1994年第6期;郑跟党:“试论情事变更原则及其适用”,《中外法学》1995年第5期;王建林:“论情事变更原则在经济合同案件中的适用”,《法制与经济》1995年第6期;蓝承烈、樊惠筠:“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比较研究”,《求是学刊》1996年第5期;张坦:“论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限制”,《河北法学》1996年第5期;邓自力:“情事变更原则在预售商品房纠纷中的适用”,《法学》1996年第11期;王江雨:“论情事变更原则”,《现代法学》1997年第1期;王宝发:“论我国合同法应当确立情事变更原则”,《法学家》1997年第2期;张淳:“外国法上情势变更原则内容差异及我国立法选择浅议”,《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秋季号;朱国光:“合同一方当事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程序探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郭洪俊:“艰难情形与不可抗力的区别及其不同法律效果探讨”,《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张淳:“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进一步研究”,《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淳:“论情势变更情形下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变更权”,《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钟小文:“论情势变更原则”,《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马永双:“合同法中的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研究”,《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等等。)
2.大陆案例及裁判见解
(1)“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违约纠纷案”(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6辑,第110页以下。)
案中原被告于1987年签订技术转让协作合同与煤气表散件供应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要求被告按月平均向原告供给煤气表散件若干套。后因物价大幅度上涨,履行出现障碍,被告多次与原告协商请求变更合同中的价格条款未果,遂于1988年9月起停止向原告供应煤气表散件,至此发生纠纷。
一审判决被告败诉,被告提起上诉。受理上诉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2)27号作了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2)27号的主要内容为:“本案由两个独立的合同组成。……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事变更,即生产煤气表的主要原材料铝锭的价格,由签定合同时国家定价为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000元,铝外壳的价格也相应由每套23.085元上调到41元,如要求重庆检测仪表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显失公平。对于双方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你院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公平合理地解决。”
湖北高院认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如果要求一审被告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将显失公平。对此,应依据民法通则规定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和《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予以处理。一审法院判决令被承担违约责任显系不当。遂于1992年4月3日裁定: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原审法院在重审中主持调解,当事人双方于1992年10月26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技术转让合同及煤气表散件供应合同终止执行;二、煤气公司应退还仪表厂实物和材料款,其他损失自负;三、仪表厂一次性补偿煤气公司21万元。
学者由此认为本案是我国司法实践正式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判决的第一个判例,在理论上、立法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注:参见前引[39],耀振华论文。)严格说来,这只是一个案例,尚称不上判例。另外,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是我国法院在法律欠缺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处理案件的惯用方法,自法院方面而言固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无可讳言,这一结案方式使得本来可以通过业经最高人民法院授意后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发展法律的机会浪费了。好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已基本表明其立场,开始同意将情事变更原则适用于实际案件的裁判。
(2)“长春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购销房屋因情势变更而引起的价款纠纷案”(注: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4辑,第127页以下。)
案中原告与被告在1992年6月签订房屋购销合同一份,价款随工程进展分期支付。1992年11月该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在施工期间,由于市场建材价格大幅度上涨,为此当地有关部门曾发布地方性文件规定,从1992年1月1日起,建筑工程结算以原合同所定直接费用的50-70%计取上涨价差。于是,被告报经市房屋开发管理办公室审核,将由原定房价每平方米1900元,调整至每平方米2480元,并据此通知原告结清余款及追加房屋调价款99万元。原告不同意上调房价,遂向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购房协议为有效协议。被告不按协议规定向原告交付房屋,而强令原告按照被告单方提高的购房款结算,实属违约行为,应负违约责任,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根据民法通则第85条、经济合同法第35条规定于1993年2月22日判决:一、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按购房协议规定的要求,向原告交付房屋;二、原告验收后支付购房余款119万元;三、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原告违约金109200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建材大幅度涨价,从而使房屋成本提高,这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无法防止的外因。根据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由于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上诉人是在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初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如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情况下,而提出对原协议价格的变更请求的,应当允许。被上诉人应按上调后的价格付房价款。但如将计划利润全包括在内,则对被上诉人来说,也不公平,因此,应扣除计划利润部分。根据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1、2项之规定,于1993年4月9日判决如下:一、维持一审判决之第一、二项,撤销第三项;二、被上诉人给房地产公司房屋调价款671453.11元。
(3)“徐俊利诉墩台村经济联合社果树承包合同纠纷案”(注:参见《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3年卷。)
案中原告于1985年1月1日通过社员大会公开招标、投标的形式与被告签订了果树承包合同。后因部分群众反映承包费偏低,被告将原告承包费由原来的年交160元调至700元,因原告不同意未能达成协议。被告又以招投标方式,将原告等5户承包的果园另行发包给第三人,由此发生纠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擅自解除合同又另行发包给第三人,属于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指出,根据民法通则第59条第1款第2项(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第1款第2项、第7条第3款等规定,(注:该《意见》第4条(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问题)规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允许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一)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二)订立承包合同依据的计划变更或者取消的;(三)因国家税收、价格等政策的调整,致使收益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四)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的;(五)因发包方或承包方不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义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六)承包人丧失承包能力的;(七)承包人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经发包人劝阻无效的。”(第1款)“因变更或解除合同使对方遭受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但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除外。”(第2款)第7条:(承包指标过高或过低问题)规定:“审理因承包指标过高或过低而发生的纠纷案件,应对承包指标的高低作具体分析,主要审查指标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承包指标一般可根据承包前三至五年平均产量(或产值)并考虑合理增产比例予以确定。”(第1款)“对于发包人因缺乏经验,导致指标明显过低而发生的承包合同纠纷,应当通过调解,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合理的承包指标。如果承包指标基本合理,承包人通过积极努力和科学管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发包人为此要求提高指标的,则不予支持,而应维持原合同的承包指标。”(第3款)“对于承包指标的调整,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法院依法判决。”(第4款)。)被告在开始发包时由于缺乏经验,造成承包指标偏低,由于承包以来果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收益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对原承包费做适当的调整也是应该的。遂判决:一、果树承包合同有效,承包期由50年改为20年。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果树承包合同无效;二、自1992年至2005年,原告每年向被告交纳承包金1511.45元;……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案中承包合同是以招标、投标方式签订的,应当继续履行;但由于发包时经验不足及果品连年涨价,造成承包金偏低和收益情况差别较大,故依法适当调整承包金也是应该的。二审判决:一、维持一审一、四、五项判决;二、撤销一审二、三项判决;三、上诉人自1992年开始,每年按750公斤二等国光苹果的同年本地收购价格计算当年承包费;……
应当说,该案实际上也是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情事变更而引起的。一审法院以民法通则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显属不当,承包合同既然是按公开招标、投标方式签订的,即无从认定其为显失公平,也不能因此而动摇合同的效力;合同是有效的,而显失公平结果的原因在于后来因苹果价格上涨而发生的情事变更,故属后发的显失公平。由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意见》中并未直接使用“情事变更原则”之类的用语,该案判决中也没有言及该原则。当然,对于《意见》的有关规定是否属于情事变更原则之规定,学者见仁见智。本文以为,《意见》是在1986年4月14日作出并适用的,当时我国大陆学说理论对情事变更原则尚没有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司法解释中没有直接使用情事变更原则之用语,便不难理解。虽然如此,实际上《意见》第4条第1款第2、3、4、6项所列事由均可构成情事变更,第7条第4款又授权法院可以裁判调整承包指标(变更合同),因而可以认为,这些规定虽无情事变更之名,却有其实。在这一案例中,法院实际上也通过判决调整(变更)了合同的内容。
(4)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注:1993年5月6日法发[1993]8号。)
该《纪要》指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至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的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
这一纪要虽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实证法律的效力,却可以视为法院审判实践中形成的“裁判上固定见解”而为各级法院遵从,有着实际上的效力。
3.大陆立法
我国现有立法中并没有关于情事变更原则的完整的一般性法律规定。原《经济合同法》(1981)第27条第1款第4项规定“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的规定,大多学者认为均是关于情事变更的规定,(注:参见前引[38],梁慧星论文。同此见解者如前引[39]耀振华、彭诚信等人论文。)少数学者则持否定意见。(注:参见前引[3],张淳论文;另外,前引[39]王宝发论文中亦表露出否认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为情事变更之规定的看法。)在制定合同法的过程中,草案中曾经设明文规定,然争论激烈,最终并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
(1)合同法草案中的规定
在合同法的多个草案中,均规定过情事变更原则。(注:包括1996年6月7日“试拟稿”(第三稿)第55条、1998年8月18日草案第77条、1998年12月21日“三次审议稿”第76条、1999年1月22日“四次审议稿”第76条。)其中比较成熟的是最后的一个草案的规定,即“四次审议稿”第76条,规定:“由于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商业风险不适用前款规定。”
(2)立法过程中的争论
反对的意见认为,如何划分正常的商业风险和情事变更较为困难,在经济贸易中能够适用情事变更制度的情形是极少的,掌握不好,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有的法官也可能滥用这项权力,甚至助长地方保护主义。
赞成的意见认为,情事变更不同于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情事变更是致使履行合同显失公平,规定情事变更制度有利于贯彻公平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已作出过有关情事变更的判决和规定。
(3)最终的审议结论
最后,情势变更制度,被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就有不同意见。这次大会审议,不少代表提出,根据现有的经验,对情势变更难以作出科学的界定,而且和商业风险也难以划清,执行时更难以操作,实际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现在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条件尚不成熟。法律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建议对此不作规定。”(注:1999年3月13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之修改意见三。)
4.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债编修正
在大陆制定《合同法》的同时,海峡对岸的我国台湾地区也在修正其施行了60多年的民法债编,并于1999年4月21日正式公布。修正案吸收台湾多年判例及学说的发展成果,一改台湾地区民法原来仅某些法条就个别法律关系例外设有承认情事变更原则局面,(注:依台湾学说见解,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52条、第265条、第418篥、第424条、第442条、第472条第1项、第489条、第549条第2项、第561条、第594条、第598条第2项、第674条、第750条、第1202条等,体现了情事变更原则,但对于情事变更原则并没有一项一般性条款,就环境变迁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如何,加以规范,此应视为一项“违反计划”的行为而为法律漏洞。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178页。)于第227条之2规定了情事变更原则,即“Ⅰ契约成立后,情事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当事人得声请法院增、减其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之效果。Ⅱ前项规定,于非因契约所发生之债,准用之。”明文宣示旧法未予明定的法律原则。(注:有关台湾民法债编的修正,可参见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的论文《台湾民法债编部分修正条文要论》,载于《第二届“罗马法 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文,1999年10月),第365页以下。)
三、我国法引入“情事变更原则”的障碍及其排除
从合同法草案的讨论过程反映出来,情事变更原则引入我国法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的障碍,一是操作方面的障碍。
(一)理论方面
情事变更原则最终从草案中删除,原因固然复杂,但起草过程中对于该原则在理论存在的诸多模糊认识,无疑是一个致命原因。比如立法机关的负责官员即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情事变更制度,国际上尚无较为成熟的经验,在和平建设时期,真正适用情事变更制度是极个别的事例。(注:参见王胜明:“从合同法的草案到审议通过”,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28-229页。)这种认识颇具普遍性,人们一提到情事变更原则,往往想到的是战争、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危机,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对策。殊不知诸如战争及社会动荡,仅为情事变更之荦荦大者,正如德国学者所见,情事变更原则问题,不是因为战乱而发生的问题,而是法律行为理论本身,未考虑环境因素,所造成的结果;除上述荦荦大端之情事外,随着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影响的增强,科技以及交易形态的发展日新月异,合同的履行难免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经济计划、甚至技术更新、交易方式改变的影响。因此,德国法学界对于情事变更原则问题的讨论,不仅未因世界大战及经济恐慌结束而匿迹,反而日趋蓬勃。(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335页。)这些观念上存在的误解,非通过加深理论研究而不能根本消除。本文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只拟对此作一些探索尝试。
情事变更原则如要在我国法上确立其地位,总的说来,理论上需要处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可称为外部问题,即情事变更制度与周边法律制度的关系,特别是履行障碍法诸制度在功能上的分工、协调与配合问题,这点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其二则可称为是内部问题,即情事变更原则所要处理的件案的类型化问题、适用该制度的构成要件问题以及法律效果问题。此处先讨论情事变更原则的外部问题。
1.严格责任对情事变更的影响
在我国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并未讨论严格责任与情事变更的关系问题,甚至对此没有问题意识,当然严格责任也就算不上是情事变更原则立法化的障碍了。不过,严格责任与情事变更的关系,作为一个展开理论讨论的基础,是不应当予以忽视的。
在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大陆法系的理论中,情事变更原则问题是在其债法从整体上采过错责任原则的框架中展开的,这样,债务不履行责任是否构成,要受到过错有无之要件的限制。我国《合同法》在整体上采纳了英美合同法的严格责任原则,这样,大陆法理论上所谓的“通常事变”即要由债务人负责,扩大了违约责任得以发生的入口。(注:参见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以下。)而发生违约责任的场合并没有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余地。这样,情事变更原则的作用领域便由此而受到了挤压,对此不能不予以注意。另一方面,在我国学者通说上,情事变更的构成要件之一要求“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以此为前提,“情事变更原则”如欲确立自己的作用领域,就免不了要与违约责任在“通常事变”范围内“争地盘”了。
2.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
在我国合同法上,一般的法定免责事由仅为不可抗力(《合同法》第117条),除此之外,依严格责任原则,通常均要承担违约责任。这样,责任与免责构成了一个周延的框架,似乎并没有情事变更原则发挥作用的领域。形成这一幻像的原因恰在于《合同法》没有肯定情事变更原则,使得我国合同法上的严格责任比英美法上的严格责任更为严厉,因为英美合同法在普遍奉行严格责任的同时,也还承认“合同落空”制度,于若干特别场合对当事人以为补救,限制违约责任的发生。笔者以为,我们应当确立如下观念:在违约责任与免责之外,尚有因合同变更或解除而不构成违约责任的领域,这一领域在时间维度上是在违约责任与免责之间的,(注:由于情事变更属于“责任不构成”范畴,居于违约责任的“上游”,因而在我国合同法上可能发生的情事变更与违约责任的地盘之争中,情事变更有先行“截留”的优势,只有在当事人不主张情事变更时,始可能轮到责任是否构成之考察。)情事变更原则正是在该领域中发挥作用的。那么,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的关系如何呢?
反对合同法规定情事变更原则的见解认为,所谓情事变更被不可抗力包含,既已规定不可抗力,就没有再规定情事变更的必要。(注:参见前引[1],梁慧星书,第192页。梁慧星先生是极力反对这一观点的。)
其实,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制度,两者的区别在于:(1)两者虽均构成履行障碍,但程度不同,不可抗力已构成履行不能,而情事变更未达到履行不能的程度,仍属于可能履行,只是其履行极为困难并导致显失公平。(2)不可抗力属于确定概念,民法通则第153条规定了不可抗力的定义,而情事变更属于不确定概念,法律上无法规定其定义。(3)不可抗力属于法定免责事由,当事人只要举证证明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即可获得免责,法庭或仲裁庭对于是否免责无裁量余地;情事变更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其本质是使当事人享有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而同时授予法庭或仲裁庭公平裁量权。(4)不可抗力的效力系当然发生,情事变更的效力非当然发生,是否构成情事变更、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及是否免责,须取决于法庭或仲裁庭的裁量。(注:参见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2页。)
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既属不同,那么两者能否同时发生进而出现规范竞合现象呢?当然,如果按照不可抗力规范的对象是后发的履行不能,情事变更规范的对象是履行极为困难并导致显失公平,则答案是否定的。有观点认为,不论是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抑或是其他事件,只要其具有不可预见性、不可克服性或不可控制性,则都可能发生情事变更的效果。在合同实务中可能存在某种既可视为情事变更又可视为不可抗力的情形。若是发生了此种情形,则应当由受到这些事件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决定采用何种救济措施。如果其主张不可抗力,其目的在于使其不履行获得免责;如果其寻求情事变更,则应当首先以重新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或谈判为目的,以便允许合同经修改某些条款后继续存在。(注:参见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上)(王闯执笔),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第274页。)此一见解如欲成立,首先须解决一前提障碍:情事变更是否仅限于履行困难?换言之,履行不能可否构成情事变更?其实,这一问题最终是一个如何理解履行不能的问题,特别是有些履行困难能否视为履行不能的问题。传统见解认为,种类之债惟于所有相同种类的物均告灭失,始构成履行不能;后来的发展表明,这种严格的形式主义的理解过于不近人情,于是在德国的司法裁判上,这种理解均被修正,履行不能或给付不能在解释上均被扩张,基本上认为,只要相同种类之物在当时的市场上难以买到,就可以认定为履行不能。(注:比如德国帝国法院在“棉花子面粉案”(RGZ 57,116[1904])中曾指出:即使是民法第279条,亦不得如此扩张解释,认为仅于所有同种类之标的物完全灭失时,债务人始得免责。对于第279条的正确解释,乃不仅于所有同种类的标的物全部灭失,而是取得同种类的标的物变得十分困难,以致依人情之常无法期待任何人做到时,即为种类之债的履行不能。并认为,如果市面上尚能取得该种种类物品时,则出卖人仍须履行。出卖人须彻底询问,但不须问遍国内外市场;须出较高的代价,甚至自第三人转买;但已交付第三人的货品,即非所谓市面上的货品。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103-104页。然台湾司法实务固守传统见解,彭凤至女士对此亦有批评。)我们也应当接受这种见解,这不仅关系到不可抗力的适用范围问题,同样也关系到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能否同时发生的问题,笔者在此问题上持肯定见解,并认为上引见解的结论值得赞同,惟其理由尚有进一步发掘的必要。笔者以为,由于在我国《合同法》上,不可抗力虽属于法定免责事由,却并不导致合同关系当然消灭,仅在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场合(《合同法》第94条第1项)发生法定解除权,此时双方当事人均享有解除权;而此所谓“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实与德国民法学说所谓“目的不达”同其内涵,在我国应当作为情事变更的一种情形。这时,如果双方当事人均不愿消灭合同关系,则可以通过变更合同的方式,调整双方的合同关系,在不能达成新的变更协议场合,则可通过法院作出公平的裁判,改订合同。
3.情事变更与商业风险
《合同法》之所以没有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情事变更与正常的商业风险难于区分。我们认为这二者仍然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1)商业风险通常是应当预见到的,而情事的变更通常并不能够预见。(2)二者在过失的有无方面不同,商业风险由于具有可预见性,故此可以说当事人对此存有过失;而情事变更由于不具有可预见性,因而不存在过失问题。(3)从外形来说,通常商业风险没有达到异常的程度,而情事变更往往是情事的变化特别异常。(注:参见前引[58],崔建远主编书,第257页。)(4)从结果来说,商业风险是能够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的,通常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也已将此种商业风险合理地计算在内并形成相应的合同价格,由一方当事人自行承担并不会发生不公平的后果;情事变更所要处理的问题,则是由于当事人缔约时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仍然坚持契约严守,在结果上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另一方当事人可能不恰当地获取超常利益,有悖于诚信原则。
当然,对于情事变更抑或商业风险的判断,尚需结合具体个案综合地考察。以“武汉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案”为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幅度不大,则仍然属于当事人在订约时预见的范围,是当事人在订约时应承担的合理的商业风险。而且由于价格变化不大,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影响并不严重,也不必要运用情事变更。否则,将会导致情事变更原则的滥用,使交易当事人免除了其应负的商业风险,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也受到了破坏,这对于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维护是极不为利的。(注: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4),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08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判例一般并不轻易承认情事变更,如买卖合同中,价格上涨了六倍,但日本最高裁判所仍然不承认是情事变更,因为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这些都是合理的,是当事人应当预见的或必然承担的风险。(注:参见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与课题”,《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由此应当注意的是,不能够单纯地从价格的涨落判断是商业风险还是情事变更,有的场合涨价很多可能仍属商业风险,而有的场合,价格在别人看来不太剧烈的波动,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却可能已经构成致命的打击,则不妨认定为情事变更。
(二)操作方面
反对合同法规定情事变更原则的见解认为,情事变更原则属于一般条款,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故担心在实践中导致滥用,影响法律的安定性。(注:参见前引[1],梁慧星书,第192页。梁慧星先生对此种见解是持反对态度的。)
既然情事变更原则的实质在于授予法庭或仲裁庭自由裁量权,因而不容否认会存在实践中滥用此裁量权的危险。对此,正如梁慧星先生指出的,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在法律上不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就能够避免这种滥用?实际上中国审判实践中已经有承认情事变更的判例,统一合同法不规定这一原则并不能阻止法院根据情事变更理论裁判案件。与其如此,莫不如对情事变更原则作出明文规定,使法庭或仲裁庭在适用这一原则时有所遵循,减少裁判的任意性,减少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前引[57],梁慧星书,第192页。)
另一方面,反对规定情事变更原则者担心法官滥用该原则并因此影响法律的安定性,这种情况不独在我国起草《合同法》的过程中出现,在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在台湾地区民法债编修订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德国及台湾的经验教训均表明这种担心实际上是多余的,是不必要的。(注:滥用一般条款的危险在逻辑分析上固然有其道理,但如果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司法活动作一社会学的考察,则不难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而且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程序的健全,这种危险会日益缩小。时至今日,如果对一位德国学者言及滥用一般条款的危险,我想这大概会使之产生杞人忧天之感。)既然情事变更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回避,就应当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在实践中犯错误并不可怕(我们还有上诉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作为进一步的防范),如果因为怕犯错误而逃避实践,则纯属一种悲衰!考察一下法律发展史,任何一般条款无不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修正错误而变得富有可操作性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形成所谓“裁判上固定见解”,法律的生命也因此而获得充实。
四、情事变更问题在我国的对策
由于我国成文立法中并没有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因而,在实践当中如何适用这一法理处理实际问题,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在实践中如果发生个别需要按情势变更来处理时怎么办?合同法有可参照国际惯例来处理的规定,国际商事通则中对此是有原则规定的。因此,不在合同法中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制度,并不会妨碍个别真正需要时处理的法律依据。”(注:顾昂然:“合同的履行”,载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社会是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只能预见到正常的商业风险,预见不到异常的变动,如金融危机等。那么,现实中遇到这类案件该怎么办呢?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按照1992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批复,即《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来办理,这是针对一个情势变更案件的解答。审判实践中,可以把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判例来应用。第二个方案是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即合同法第6条的规定。可得到巨大利益的一方当事人硬要获得巨大利益,不惜使另一方当事人遭受巨大损失,这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可直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注:《正确理解和适用合同法的各项规定梁慧星在合同法施行前夕答记者问》(记者张娜),载《人民法院报》1999年9月30日第三版。)
两种观点比较而言,第一种观点本身有所误解,即其所谓“合同法有可参照国际惯例来处理的规定”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合同法条文中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反映出来这一思想,因而国际商事通则中的原则规定自然难以使用。故该见解不足采。第二种观点是比较可行的。既然《合同法》明确回避对情事变更原则的规定,遇到此类问题,也只能以所谓“法官造法”的方式予以处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的复函以及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纪要》,虽然有些内容已经过时(涉及经济合同法的部分),然其精神与《合同法》并不抵触,作为“裁判上固定见解”仍然应当沿用。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原则的上位原则,当然是处理此类问题的终极法宝。此外,“违约金过高或过低之调整”(《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债务分期清偿”(《民法通则》第108条)等法律规定,在法院处理情事变更问题时,当然亦可资利用。(注:同此见解者,可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178页。)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以司法解释进行补救;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将来的民法典作出规定。
五、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要件
该原则的适用条件为:(1)须有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2)须该情事变更之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人;(3)须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
(一)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
1.情事变更的类型化考察
“情事”即作为合同基础或环境的一切客观事实,“情事变更”即合同基础或环境在客观上的异常变动。然而,“情事”及其“变更”毕竟是不确定概念,需要加以类型化,始能够从容把握。通过前文对情事变更原则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来,对情事变更的司法裁判以及学说讨论在德国最为活跃,其经验和对策也最具参考借鉴的价值,故以作为德国通说的行为基础理论所作的类型分析为出发点,探讨我国情事变更的类型化问题。
当然,必须注意到,由于德国学说所谓法律行为基础的“基础”,虽必须为一客观的事实,但是其决定方式是主观的,即依当事人之间共同的“预想”加以判断,而非以法律秩序或客观第三人的观点加以衡量。因此,法律行为基础学说中,相当于情事变更原则中“情事”二字的范围,即可能十分广泛,除天灾、地变、政治金融混乱等,可称为“情事”外,如购入学术书籍,其为最新版的事实等,也并非不能为“情事”。(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253页。)对此,似乎不应全盘接受,而应斟酌扬弃。另一方面,又不能仅将“情事”限定于币值或物价。
(1)“主观行为基础”与情事
在德国,主观行为基础主要是指合同当事人共同的动机错误。德国民法就此除了在和解契约有特别规定外,并没有规定一般条款,以致当双方动机错误发生时,尤其是所谓“计算基础错误”,往往只能以单方动机错误处理,与法律上不予考虑的错误结果相同。德国帝国法院后来感到,双方当事人对于交易过程中的某一行为或事实,同时发生错误,结果一方获利,一方受害,法律上竟然没有什么救济途径,实有不公,堪称一项法律漏洞,因而自1906年开始,认为此种情形可作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适用德国民法第119条第1项加以撤销。(注:德国关于双方动机错误的重要的判例有:RGZ 105,406(1922);RGZ 94,65(1918);RGZ 90,268(1917);RGZ 101,107(1920).具体内容可参见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40-52页;前引[4],彭凤至书,第111-115页。)在奥特曼的学说提出后,其中“自始欠缺法律行为基础”概念,是针对合同履行的困难非因缔约后情事积极的改变而发生,而是因为缔约时,双方认定存在的情事不存在、认定将来发生的情事消极地未发生、认定真实的情事为虚伪等问题态样而创设,以它处理双方动机错误案型更为贴切,于是被实务采为裁判依据。(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132页。)
在我国,“错误”作为意思表示的瑕疵,仅当其构成“重大误解”时,始可作为撤销的对象。不过,一方面,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上,重大误解的构成所包括的内容是比较宽泛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学理解释上,此所谓“重大误解”,并不仅指其中一方当事人的错误,而且可以包括双方当事人的错误。这样,在我国法上,当事人的共同的动机错误已经由合同效力制度加以规制了,因而不必再借助“情事变更原则”进行处理,故可以排除在“情事变更原则”法理的考虑范围之外。另外,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等,似乎也可以发挥某些规范功能。
(2)“客观行为基础”与情事
其一,等价关系的破坏。双务合同中,以给付与对待给付互为等价为常态,如果这种等价关系遭受破坏,其典型的事例是因通货膨胀或者国家价格政策调整造成的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不均衡,这当然是我国情事变更原则法理适用的最主要的对象,前述我国实际发生的三起案例,均属于因物价上涨而造成双务合同等价关系遭到破坏案型。这时,通常可以通过变更合同、使合同对价关系达到新的平衡来解决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在有些场合可以解除合同。
其二,目的不达。所谓“目的不达”,我国合同法上亦称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时既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然没有继续保存合同关系的必要,因而在我国《合同法》上是发生法定解除权的典型情形(第94条)。比如,《合同法》第337条规定:“因作为技术开发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致使技术开发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2.对“情事变更”的时间要求
一般认为,情事变更的发生应当在合同成立并生效之后至履行终止之前。
情事变更应当是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2条(a)项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11条第2款第1项)。如果情事变更在订立合同之前或在订立当时即已发生,且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已经知道该变化的发生,仍然订立合同,则表明当事人自甘冒险,合同法没有予以特别保护的必要。
如果情事变更在缔约之前或之时已经发生,但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在缔约之后才知道该情事而主张情事变更的,则应当成立合同成立后的情事变更。因为该场合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在缔约之前或之时并不知道该情事之变更,所以存在主观的不可预见性。当然,该当事人应当对其“善意”负担举证责任。(注:参见前引[58],崔建远主编书,第268页。)
迟延履行或者受领迟延期间发生情事变更,能否适用情事变更原则?一种见解认为,依民法公平诚信原则,答案是肯定的,但并不因此而免除违约行为人的责任。只是一方面通过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来消除因情事变更造成的合同继续履行的重大公平显失。另一方面通过让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来弥补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注:参见前引[39],彭诚信论文。)另一种见解认为,迟延期间风险由违约方承担,其无权主张情事变更,这属于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例外。(注:参见前引[39],张坦论文。)笔者以为,这时不妨参考不可抗力的处理方法,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在迟延场合受到限制(参见《合同法》第117条第1款后段),但学说上普遍认为,如果违约方能证明纵无迟延,仍会发生不可抗力并致履行不能,即能证明所谓“假想因果关系”,仍然可以免责。对情事变更也可作同样的处理。
如果情事变更发生在合同履行终止以后,则因为合同关系已经消灭,通常并无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余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法律行为基础制度却没有这一限制。(注:在德国,法律行为基础制度,是自法律行为成立及效力理论上,解决所谓情事变更问题,因此法律行为虽已消灭,但该法律行为的基础“曾”欠缺或丧失者,当事人不妨嗣后主张基于法律行为基础制度的权利。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266-267页。)我国理论上应否承认个别例外,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3.“情事变更”的不可预见性
情事变更的可能性于达成合同之时应属于不可预见到的(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2条(b)项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11条第2款第2项)。对于此一要求,应当明确:预见的主体为因情事变更而遭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预见的内容为情事变更发生的可能性,预见的时间为合同缔结之时,预见的标准应当确立为主观标准(即以遭受不利益一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为准)。
4.“情事变更”之风险非受不利影响之当事人所应当承担
“情事变更”之风险非受不利影响之当事人所应当承担(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2条(d)项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11条第2款第3项)。如果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承担了情事变更的风险,则不能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承担”一词表明不需要明确所承担的风险,但却可以从合同的性质确定。一方当事人参与投机交易(比如炒股票或者期货),被认为应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即便该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没有完全意识到交易的风险。
(二)情事的变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
情事变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主要是指情事的变更不为当事人尤其是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所能控制(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2条(c)项)。比如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动荡等。如果情事的变更可以由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控制,则其发生直接表明该当事人具有过错,自应遭受其损失,没有特殊保护的必要。
(三)维持原有合同效力显失公平或有悖于诚实信用
这是情事变更与正常商业风险有显著不同的地方。情事变更的构成是对于“契约严守”原则的否定,惟应于例外场合予以承认,自然应当要求相应后果的严重程度,即维持原有合同效力(契约严守)在效果上显失公平或者有悖于诚实信用,比如仅仅因为价格的超常涨落,使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即遭受“经济废墟”或“生存毁灭”(德国判例创造的概念)的结果,而另一方当事人由此而获取巨额利益,显然不公,显然悖于诚实信用。
六、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效果
(一)比较法考察
1.奥特曼法律行为基础理论中的法律效果
奥特曼认为,法律行为基础不论自始欠缺或嗣后丧失,各该法律行为如因而无效,则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样的,撤销、不生效力、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如用作此种问题的法律效果,自法律政策上考虑,也有其缺点。因此比较合理的解决方式,应该是赋予因法律行为基础的瑕疵而受不利益的当事人,一种消灭法律关系的可能。提供此种“消灭法律关系的可能”最通常的方式,在双方法律行为,应为享有解除权,在单方法律行为,则为撤回,不过此仅适用于法律行为基础自始完全不具备,或者嗣后完全丧失的情形始可。而且,此时解除权的溯及效力应有限制,既非完全溯及,亦非完全不溯及,而是溯及自法律行为基础欠缺或丧失时起,双方当事人互负回复原状的义务。至于对继续的债务关系,则解除权应当转换为终止权。这在法律行为基础嗣后丧失的情形固然没有问题,然在法律行为基础自始欠缺时,何以不发生解除权而使法律关系溯及消灭?是因为法律行为已部分履行完毕,其效力既已实现,则已没有使之复归消灭的必要。(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40页。)如果是仅对法律行为中的某一部分债务关系而言,其行为基础欠缺或丧失,则此时仅应区分具体的情形,发生有限制的法律效果。
2.日本的情况
在日本,情事变更原则法理的效果为合同解除及合同改订。对于这两种效果,在日本下级审的层面上均有很多的例子;然而,从最高级审判机构的判决来看,对于解除,在大审院时代虽有肯定的事例,及至最高裁判所则尚未出现肯定的事例。对于合同的改订,无论是在大审院还是最高裁判所均未见到肯认的事例。这样,在日本最高裁判所尚没有实际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法理的例子,对此,在日本学者的解释上认为,并不能够由此解释认为否定了情事变更原则之法理,只能反映出日本最高裁判所对于情事变更原则之法理的适用极为慎重。(注:参见〔日〕内田贵:《民法Ⅱ·债权各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版,第75页。)
对于两种效果的关系,在日本学理上一般认为,如果因情事的变更使得合同的履行完全丧失了意义,则必须予以解除。如果履行尚属有意义,则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当事人始应当努力地通过再交涉改订合同的内容,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情事;在这一意义上,应当说当事人负有“再交涉义务”。法院亦应当在其力所能及的限度内力求通过合同的改订来维持合同关系;只有在如此行为困难之场合,始承认合同的解除。(注:同上书,第75-76页。)
其法律效果为赋予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以请求变更或消灭合同的可能性,属于实体权利,但以诉讼(仲裁)方式行使为必要。
综合比较,日本实务上的处理方式更适合我们借鉴;而奥特曼理论中直接赋予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消灭合同关系的实体权利(形成权),比如解除权或撤回权,并没有言及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这种方式容易发生纠纷,是应予修正的;不过他对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问题的分析是很正确的,对我们颇有启发性。以下将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效果区分为实体法上的效果与程序法上的效果,分别探讨。
(二)实体法上的效果
1.再交涉义务
(1)“再交涉义务”的由来及表现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3条第1款规定:“若出现艰难情况,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有权要求重新谈判。但是,提出此要求应毫不延迟,而且应说明提出要求的理由。”
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11条第2款前段亦规定:“如果由于情事的变更使合同履行变得格外困难,当事人应当进行磋商以改订合同或者解除合同”。
我国合同法草案也曾规定,(注:参见1998年8月18日草案第77条、1998年12月21日“三次审议稿”第76条、1999年1月22日“四次审议稿”第76条。)情事变更的效果包括:受不利益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草案的这一规定,被认为“堪称是相当前卫的立法”。(注:前引[58],崔建远主编书,第278页。)
(2)我国法上应否引入“再交涉义务”
“再交涉义务”已被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所肯定,我国合同法草案也曾尝试借鉴,但最终随同整个条文而被删除了。虽然如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的情事变更原则之法理上,是应当肯定“再交涉义务”的存在的。同时,也应当明确,“再交涉义务”不是在赋予权利,而是在设定义务;不是体现了私法自治,而是限制了私法自治。这样,对于“再交涉义务”在法律上的要求就不应当定得太高,详言之,我们不应要求当事人一定要达成新的合同或者达到某一特定的结果,即不能够将它理解为一种“结果义务”,而只能够理解为“行为义务”,只要当事人符合诚信地再交涉了,即符合要求。
(3)再交涉义务的法律效果
第一,再交涉义务是否产生中止履行抗辩权?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3条第2款规定:“重新谈判的要求本身并不能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有权停止履约。”其原因在于艰难的例外特性和可能滥用救济手段的风险。停止履行可能仅仅在很特例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注:例如:A与B为建筑一工厂订立合同,工厂将建在X国。在订立合同后该国施行新的安全法规。新法规要求使用另外的设备装置,由此导致合同双方均衡的根本改变,极大地增加了A的履行负担。这种情况下,A有权要求重新谈判,并可以停止履行,因为它需要时间去执行新安全法规;而且,只要对相应的价格修改没有达成协议,它也可以停止对该设备装置的交付。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第6·2·3条的注释4。)
而在德国学理及实践中,当事人主张基于法律行为基础制度的权利要以抗辩的方式,惟对于究竟应以永久抗辩或一时抗辩之方式主张此权利,学说上并无定论,端视当事人主张权利的目的如何而定,并被认为是法律行为基础制度权利行使上的一个特色。(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59页。)
在我国理论构成上,应当作什么样的选择呢?一般说来,发生情事变更之后,受不利益的当事人在主动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之后,对方往往是受利益者,或者是期待获得利益者,多不愿同意对方的提议。这时,如果仍然坚持原合同效力,则受不利益一方中止履行就会被认定为违约,这从前文介绍的我国实际发生的案例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前两个案例的一审判决即是如此;二审对此予以了纠正,受不利益方中止履行,并没有被追究违约责任。前文我国判决(或调解)的结果应当说是合理的,而对于其中所寓含的法理,则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为什么按照合同应当履行而中止履行后不承担违约责任?其道理只有通过承认此时受不利益方享有中止履行的抗辩权,才能得到解释。所以,笔者以为在理论上还是应当承认情事变更场合受不利影响当事人的中止履行抗辩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虽然对此予以否认,但仍不得不允许存在例外。
第二,违反再交涉义务的法律后果
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11条第3款后段规定:“在任何一种情形,法院可以对因一方当事人悖于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之拒绝磋商或者终止磋商而遭受的损失判予损害赔偿。”显然肯定了因违反再交涉义务而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我国法上应否借鉴此一做法,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个人以为,如果对于违反再交涉义务不规定一定的法律后果,将使得这一义务沦为道德规范的宣示,而不成其为一项法律义务。因而,欧洲合同法原则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同时,我们对于此项法律义务的要求仅限于符合诚信地行为,并不要求必须达到一定的结果,因而,也可以限制不良影响(即对义务人的要求过高)的发生。
2.合同的解除
在合同目的因为情事变更而不能实现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事变更成为不可期待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事变更而丧失意义场合,一般就可以解除合同。对于继续性合同或者长期合同,其解除通常并不能溯及合同成立之时,仅应自情事变更时起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对于一时合同则可溯及合同成立之时。
3.合同的变更或改订
在合同目的并非不能实现场合,处理的办法通常是合同的变更或改订。应当说,这一效果是再交涉义务所要求的,合同当事人应当依诚信原则进行协商。协商不成时,则可以请求法院通过判决的方式变更合同。严格说来,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没有权利依其单方意思变更合同内容,有的学者提出“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之概念,甚至认为这种权利是合同法上唯一的关于合同的法定变更权,并据此提出需要对传统的合同法理论进行修正。(注:参见前引[3],张淳论文。)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情事变更原则的主要法律效果,是赋予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以变更或消灭合同的可能性,梁慧星先生认为它属于实体权利,但以诉讼(仲裁)方法行使为必要,故有别于解除权,相似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撤销权。(注: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这一认识是正确的,解除权属于典型的形成权,依权利人单方的意思即可使法律关系变动;而请求法院变更合同的权利,本身尚不是形成权,最终是否变更合同,还要经过法院审理后再根据诚信原则及公平原则加以决定,在这点上的确与撤销权相似。如果认为当事人可以享有法定的单方的变更合同的权利,作为一种形成权,其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必然导致合同秩序的破坏,影响正常的经济流转,实在不足取。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所规定的违约金调整“请求权”,也正印证了这一结论。
(三)程序法上的效果
1.当事人主义抑或职权主义?
对于情事变更,是由当事人主张还是可以由法院依职权直接认定?是在以诉讼方式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时在程序上首先须予回答的问题。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97条曾规定过情事变更原则,其内容为:“法律行为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情事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法院应依职权公平裁量为增、减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效果之判断。”“前项规定,于非因法律行为发生之法律关系准用之。”显然采职权主义之做法。而台湾地区民法债编修正后的第227条之2规定了情事变更原则,即“Ⅰ契约成立后,情事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当事人得声请法院增、减其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之效果。Ⅱ前项规定,于非因契约所发生之债,准用之。”似可认为,已改变职权主义而采取当事人主义。
我国民法诉讼法已有“超职权主义”之诟病并遭到学者批评,近年来诉讼剧增,法院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故有全国范围的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实际上即在不断扭转固有的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做法。《合同法》在立法精神上也体现了对于职权主义的回避,比如合同的撤销要基于当事人的请求(第54条)、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要基于债权人的请求(第74条第1款)、违约金的调整要基于当事人的请求(第114条第2款)等,从合同法草案的规定中也反映出来,起草者对于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奉行当事人主义,先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变更,不成时再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因而,在日后处理情事变更问题时,亦应当采取当事人主义。
2.形成判决抑或确认判决?
对于合同关系的调整,双方当事人无法通过协议完成时,便只有通过法院(或仲裁)介入,由法院基于当事人的请求,以裁判变更基于原来的合同关系发生的权利义务,因而可以视为是对于原来法律关系的一项形成性干预,其判决应属于形成判决。
在德国有见解主张此时的判决属确认判决,其实这种看法不无牵强之嫌。“因为法律行为基础制度适用时,并不能导出确定的法律效果,换言之,此非单纯经由法官之认定所能解决之问题,而必须在裁判权斟酌范围内,进行价值判断,始能完成之工作。”(注:前引[4],彭凤至书,第60页。)
本文在对大陆法系情事变更原则作比较考察的基础上,尝试我国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构成,力求将此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文中难免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抛砖引玉,也期待学界先达及同仁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