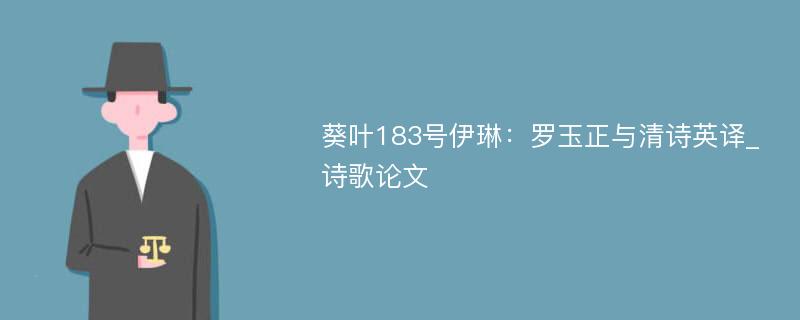
葵晔#183;待麟:罗郁正与清诗英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译论文,葵晔论文,罗郁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4)05-0133-08 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与传播,经历了一个从《诗经》译介起步,到唐诗译介进入一个高潮期,再逐步向各朝代诗歌译介纵深发展的过程。早期为此奠定基础并推动这个历史进程持续迈进的主要力量,是一批出自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员或商贸人员群体的汉学家,其中鲜见华裔的身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一批早期汉学家旅华的时间段里,清诗对于他们而言是“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不在“古典”的范畴之内。因此,虽然清诗被他们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20世纪中叶以前出版的各类有关中国的英文书籍里,零散可见一些清代的“诗歌”英译,不过这些“诗歌”都是笔记小说、民歌戏曲、传奇故事里的内容,离中国传统严肃文学的“诗歌”定义距离太远。而且译介的目的也大多不在于介绍清诗,而是在介绍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或民俗民情之时顺带提及。 谈到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色与成就,一般认为清诗既无法与唐、宋抗衡,也不配与同时代的小说、戏剧相提并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就曾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断言,清代诗歌“真可谓衰落已极”。这种评价在被王国维明确概括并广为流传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框架之中,被反复强调,形成清代文坛上只有小说堪为关注,清代文学研究唯小说独尊的局面。这些观点严重阻碍了世人对清诗的研读,在本土学界尚且如此,外邦学者对清诗的轻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毫无疑问,清诗在中诗英译领域的整体缺席,必然影响英美学界对中国诗歌演进历程这一有机整体的基本认识,影响对中国古典文学总体的文化传承和历史连续性的宏观总结,也必然影响对近现代诗歌发展源流的客观判断。这一点不仅引起了后来新一代英美汉学家们的注意,更促使华人学者提起译笔去填补这一空白。 罗郁正便是为清诗英译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一位华人学者。20世纪中期以后,华人移民群体的受教育程度、综合人文素质较过去总体提升,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也相应改变。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一批华人学者译家。他们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和研究带来了不同的观照角度和立场,大大增强了译介和研究的力度,促使古典诗歌开始了从母体语境向西方文化语境的主动进入。因此,中国古典诗歌及其内在文化元素对美国文学艺术界产生了比过去更广泛、也更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较为知名的华人学者,首推创立比较诗学理论体系,享誉中西学术界的刘若愚先生。在潜心研究中国传统诗论的基础上,刘若愚结合西方文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观念和评论标准。“用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术语介绍和阐释中国传统诗学,既让西方读者感觉通俗易懂,又以其饱含西方学术素养的系统批评方法为习惯于中国传统文论术语和思维方法的东方读者拓展了视野。”[1]49中美建交之后,美国的知识界和社会大众对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关注进入一个高潮时期,柳无忌、叶维廉、罗郁正、吴应熊、余宝琳等华人学者先后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各显身手,带着跨文化传播的高度自觉与使命感,通过著书立说和讲授相关的大学课程,大力推介中国古典文学。 在这批华人学者里,罗郁正教授对清诗英译与传播的贡献可圈可点。在西方学界对清诗的认识由贬斥到正视,对清诗的译介由零散走向系统的进程中,罗郁正所主持编译的两个重要中诗英译文本,《葵晔集》和《待麟集》,前者辟出专章译介清代诗人及他们的作品,后者更是清诗英译的第一部专著。 一、罗郁正生平及主要学术成果 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1922—2005).192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家境殷实,从小接受私塾的启蒙教育。先后在上海圣约翰附中、圣约翰大学文理学院英文系求学。1947年,大学毕业后的罗郁正偕妻子邓瑚烈(Lena Dunn Lo)远渡重洋,赴美求学。先在哈佛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1952年,经由原上海圣约翰中学的英文教师Rosa May Butler的推介,罗郁正进入阿拉巴马州的斯蒂尔曼学院(Stillman College)英文系讲授英国文学,期间加入了美国籍。随后他曾先后在密西根州西密西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执教,讲授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课程。1967年,罗郁正受聘为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Indiana University)教授,数年后担任该系主任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罗郁正的第一本中国古典诗歌译介专著,《辛弃疾》(Hsin Ch'i-chi),作为知名的《泰恩世界名家丛书》(Twayne's world authors series)中国作家系列专辑之一,于1971年出版。在这本译著里,罗郁正详细介绍了辛弃疾的生平,也介绍了“词”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诗歌形式的发展源流、格式和特点。书中翻译并赏析辛弃疾词作40首,继而根据这些词作的内容,将辛弃疾创作的主要特色归为“带有英雄色彩的爱国主义风格”。 1975年,罗郁正与他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同事,另一位华人学者柳无忌(1907—2002)共同主编的英译中国历代诗词曲的大型选集《葵晔集:汉诗三千年》(Sunflower Splendor: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一书出版。此书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由英、美两地50多位学者合力,译出中国历代共145位诗人近700余篇作品,其中罗郁正本人翻译的将近150首。 除两位编者外,此书译家群中荟集了美国汉学界大批宿将新秀。有刘若愚、傅汉思(Hans H.Frankel)、薛爱华(Edward Schafer)、马瑞志(Richard Mather)等当时已声名显赫的大家,还有柯睿(Paul W.Kroll)、宇文所安(Steven Owen)、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等后来成就斐然的学者。附录中还包括了所录作品及作者的详细背景介绍、中国朝代与历史时期表,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是最早、最完整的中国历代诗歌中西合璧译本。此书最后一章“悠久传统:承继与挑战(In the Long Tradition:Accommodation and Challenge)”,选译明、清、民国及以后共25位诗词名家的作品,其中清代占了一大半,包括钱谦益、谭元春、陈子龙、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纳兰性德等14位。 《葵晔集》出版后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到半年即印行1.7万千册。《纽约时报》每周日版的《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于当年12月21日在首页全文刊出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亚洲研究系比较文学教授David Lattimore撰写的书评,称该书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好的中国诗歌西方语言翻译文本”。《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等报章杂志也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此后美国多家大专院校的相关科系采用《葵晔集》作为中国文学课的教科书,并沿袭至今。此书后来被再版及重印的次数与数量,堪为同类书籍之最。 1986年,罗郁正与William Schultz教授合作,召集39位北美学者从清代诗词作品中遴选、编译成中国清代诗歌选集《待麟集》(Waiting for the Unicorn:Poems and Lyrics of China's Last Dynasty,1644—1911)。此书同样有中、英文两个版本,导言引李白《古风》和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以明期待太平盛世之“待麟”题旨。内容划分为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三大部分,沿用英文“Poetry”的宽泛定义,诗、词兼收,包括钱谦益、吴伟业、陈维崧、纳兰性德、袁枚、蒋士铨、龚自珍、王闿运、黄遵宪、康有为、王国维等72位清代名家的作品,中文本计398首,英文本译出328首,绝大部分都是首次被译成英文。《待麟集》对清诗的肯定,以及书中所展现的清代诗家阵容、作品数量与诗风演进历程,使之成为清诗断代英译的开山文本。 除了上述译著之外,罗郁正还曾担任《英译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的编辑顾问,为这部囊括从上古至现代全世界非英语国家名作家的大型工具书撰写陶潜、白居易、李商隐、李清照及辛弃疾等人的作品英译简介,并曾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撰写温庭筠等人的词条,为《20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撰写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及其作品的介绍,也曾经将周恩来、北岛、顾城等人的诗歌作品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 在他执教的印第安纳大学,罗郁正从1975年起担任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翻译》(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丛书与《中国文学、社会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丛书的主编,1979年起为《中国文学:随笔、报道、评论》(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杂志编辑组成员、顾问委员会成员。 1989年退休之后,罗郁正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学两年,也曾多次应邀到中国大陆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与短期讲学。2005年7月,这位平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与传播的华人教授去世于新泽西家中。 二、清诗英译的概况 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主要集中在英译唐诗。那些古老诗句的英文文本为英语世界带来新鲜的阅读经验与巨大的文化冲击,唐诗英文译介的文本到今天还层出不穷。宋词或元曲能得到译家、学者和作家们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其形式上与唐诗的显性差异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对清诗所知甚少且评价消极的现象普遍存在,清代文学作品的英文译介以小说占压倒性优势,诗词不仅被冷落,几乎可以说是被蔑视。认为清诗词乏善可陈的偏颇评价,在当时与中国文学或诗词相关的书籍或文章中并不少见。 英国汉学大家哈伯特·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编译中国诗词选集《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1898)一书,从《诗经》开始按朝代选译中国古典诗歌近200首,唐代以后仅录入袁枚一人一首而已。在其鸿篇巨著《中国文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当中的“清代文学”一章里,翟理斯认为“当朝的,尤其是19世纪的诗歌,只能说是些人为的工巧句子,充斥着那些毫无情趣的观察者的粗俗。1857年出版的辑录了近200名代表作家的诗集,也没什么可读性,更无任何思想性可言”[2]416。为他所称许的清代诗家只有袁枚、赵翼等寥寥数人。 1904年,有一本题为《广东情歌》(Cantonese Love Songs)的汉诗英译文本面世。因其中文原著刊行于清代,往往被误认为是清代诗词专门英译本。实际上此书译自清代文人招子庸编选辑录民间唱本《粤讴》,由第17任香港总督Sir Cecil Clementi(1875—1947)翻译成英文。此书虽也归于“English-translated Chinese Poetry”(英译汉诗)的类别之中,究其内容却是坊间的唱词俚句,不在中国正统严肃文学的“诗词”范畴之内,不能算作清诗英译的专门文本。在这一时期,英译清代诗词只是散落在一些中国历代诗歌英译的合集里。众多清代诗词名家之中,最早被译家们关注的是袁枚及其作品。 1916年,英国前拉斐尔派诗人劳恩斯勒·克莱默-班(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1872—1945)的第二本汉诗英译集《灯之飨宴》(A Feast of Lanterns,1916)作为《东方智慧丛书》(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之一出版。此书正文选译历代诗人作品近60首,以袁枚作品数量最多,一共9首,被编在全书压轴的位置,并取其中第一首的诗题“灯之飨宴”为书名。此外,克莱默-班还曾经在专门选登小历史故事的月刊《金色书本杂志》(The Golden Book Magazine)上发表过题为“神秘土地”的文章[3],是袁枚《子不语》书中故事的译文。 克莱默-班不是经院派的汉学家,受翟理斯引导进入中国古典诗歌的世界。他的英译汉诗虽是对他人译本的再加工,不见得更接近原作,却更切合西方读者的审美情趣,以语言优美、诗意灵动见长。他的数本中国古典诗歌重译作品,《长恨歌及其他》《灯之飨宴》和《玉琵琶》流传至今仍在不断被再版重印,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界的范畴。 1921年,由著名美国作家、报人约瑟夫·法兰西(Joseph Lewis French,1858—1936)主编的《莲菊集:中日诗选》[4]一书中,可见到的清诗有袁枚作品10首,9首直接转录自克莱默-班的《灯之飨宴》和《玉琵琶》,还有一首是美国翻译家爱德华·马瑟斯(Edward Powys Mathers,1892-1939)对克莱默-班文本的转译。1917年,美国作曲家查尔斯·汤姆林森·格里费斯(Charles Tomlinson Griffes,1884—1920),从《灯之飨宴》一书中选取袁枚的同题诗,谱成声乐与钢琴曲,收录于他的《古中国与日本诗五首》中出版。[5]此后,英国作曲家格兰维尔·班托克(Sir Granville Bantock,1868—1946)从《玉琵琶》和《灯之飨宴》两书中选取克莱默-班译诗32首,谱成六组声乐套曲,题为“来自中国诗人的歌”,先后于1918年到1923年间陆续在伦敦出版。[6]其中为袁枚作品《灯之飨宴》的英文版谱成的曲子最受欢迎,近年还有声乐家在美国华盛顿D.C.的国际音乐节上演唱。 克莱默—班是一个诗人,他的译笔只为了向英美读者传达他自己所体味到的中国诗歌之美,并不拘泥于原文的字句。就袁枚这首《灯之飨宴》而言,笔者几乎查遍现存袁枚诗稿,却找不出对应的原文。但无论后来评家如何贬斥克莱默-班译本既无信也不达,他都当之无愧是向英美世界译介清诗的先驱者之一。此后相继出版的各种历代汉诗英译选本里,即便能见到清诗词作品,也只有一两首,雪泥鸿爪而已,篇幅及影响都远远不能与《灯之飨宴》相提并论。 1918年,、美国翻译家詹姆士·威特沃(James Whitall,1888—?)在纽约出版的《中国歌辞:白玉诗书》[7]一书里可以见到纳兰性德的作品。1947年,著名美国传记作家、诗人罗伯特·佩恩(Pierre Stephen Robert Payne,1911-1983)编著的《白驹集:中国诗选集》[8]出版,选诗的时间跨度很大,从《诗经》一直到近代,每朝代一章,一共只有60余首,“清代诗歌”下只收录了纳兰性德一人的3首词作。而且,此书的翻译是佩恩召集当时的中国学者们完成的,并非出自英美汉学家或作者之手,在英美的流传十分有限。 直到1933年,加州大学的知名汉学家,以译出《西厢记》知名的亨利·哈特教授(Henry H.Hart 1886—?)出版《百姓诗:中国诗歌简介》①,相形之下更受学界关注。此书以朝代选诗,“清代诗歌”一章译出清诗词作品45首。最后一章“更多诗歌”随机收入各朝代诗词,又可见清代作品4首。全书总计译出49首,《百姓诗》因此成为最早辟单章集成介绍清诗词的英译文本。 不过,哈特教授在此书前言题为“中国诗歌史”的第一部分当中,述及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的传承、流变、代表作家及创作特色,对清诗仍是不以为然:“在满洲统治的250年间,诗词创作的数量巨大。乾隆皇帝一个人就写了九百余题,三万三千余首,格式工整而毫无生气,不值得翻译。19世纪最知名的中国诗人是袁枚(1715—1797),他的才学与智慧显然是辉煌唐代的回响。但大多数清代诗词作品都不过是生硬、工整的句子,缺乏形式上内容上的美感。只有女性诗人们是例外,像明代一样,很多女性写出了优美的诗句。”[9]19-20 到1938年,哈特又出版了《牡丹园:中诗英译集》[10]。此书所选译的诗歌也按朝代排列,清代部分选徐灿、王士禛、孙云凤、吴藻、袁枚、席佩兰、樊增祥等人作品30余首,以女性的作品居多。与《百姓诗》选诗的着眼点不同,如哈特在译序中的自述,这些诗歌都是他自己在中国诗歌的烟海当中,所特别偏爱的那些。因此,书中所呈现的既不一定是公认的各朝代名家,也不一定是各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哈特这两本译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清代女性诗词作者的大力推崇和充分肯定。除此之外,他对袁枚的称许,以及对清诗词总体的不以为然,都与翟理斯遥相呼应。 1962年,有华裔血统的罗旭稣(Sir Robert Hormus Kotewall,1880—1949)与Norman Smith合作,译出《企鹅丛书·中国诗词》[11]。全书仅有80多页,除李白、王维、白居易、袁枚、胡适等少数几位而外,其他众诗家每人名下只译一首作品。这本小书当时能引起人们注意的重要原因,便是此书选诗以《诗经》始到冰心止,时间跨度相当大,而且唐、宋、明、清各朝所选入的诗歌在数量上差别不大。清代诗家有18位,与唐代数量相等,旗鼓相当,突破了长期以来英译中国诗歌选本中唯唐诗独尊的框架。 而作为“满洲时代最后一位杰出诗人”[10]142,袁枚这个名字是如此突出,以至于在断代清诗英译文本出现之前,袁枚专门译介文本便先问世了。1956年,汉诗英译大家,英国汉学家、诗人亚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的《袁枚:十八世纪中国诗人》一书在英美同时出版[12],成为英语世界最早的清代诗人专门译介文本,确立了在英美汉学界的视野里,袁枚之于清诗几可等同于李白之于唐诗,具有典型的代表地位与表征的意义。 诗歌翻译的前提,首先是解读诗歌。而文学的语篇特征,往往与作者的生平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像哈特这样治学严谨的学者,在选诗译诗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诗人生平的考订。可他的两本译著中所涉及的清代诗人词人,数量不能算多,能列出生卒年月的不及其中十之二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看不到全貌,不了解总体情况,并非哈特一人而已。这种近于“无米之炊”的文化贫血状态,是导致自翟理斯以降的英美学者们集体贬抑清诗词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观中国本土学界,20世纪中期以来,以钱仲联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为清诗的整理、校注和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致使清诗的成就及其历史贡献逐渐得到认识和肯定。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清诗英译也走过20世纪前半叶的破冰期。以罗郁正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们以其高度的学术敏感追踪国内清诗词研究的进展步伐,使清诗英译从规模、数量和译介质量上来说,都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开始迈向一个更整齐可观的阶段。 前文提到罗郁正编译的《葵晔集》于1975年付梓,书中所包括的那些清代诗词名家后来也出现在《待麟集》里,但两书选译的他们的作品并不重复。 1976年,《中诗英译金库:古典诗歌121首》中英文对照本由联经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3],在英美发行。此书中有纳兰词4首,袁枚、赵翼、李调元诗各1首。译者John A.Turner(1909—1971)曾是旅居中国30余年的耶稣会神父,一生翻译中国诗歌300余首,主张韵体译诗,刻意追求中诗的英式古典再现。因此,他的译文用词生僻,语意晦涩,影响了普通读者对此书的接受程度。 1985年,倪豪士编著的《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参考》[14]出版。尽管没有诗词作品的翻译,但书中详细介绍了37位清代诗词名家的生平、生活和创作情况,为后来的清代诗词作品和诗人译介提供了参考。 同年,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刘渭平(1915—2003)著有《清代诗学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etics in the Ch,ing Dynasty),是关于清代诗论研究的英文著述。②刘渭平曾于苏州大学讲学期间,得以聆听钱仲联等先辈方家宏论,该著述原是刘渭平用英文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文版本曾连载于我国台湾地区期刊《中国文化》(1985—1987),“主要介绍清代四大诗说——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而于诸说渊源、清初和清季诗论,亦有所考察”[15]。惜英文本至今尚未公开出版,未得寓目。 1986年4月,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的弟子,美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齐皎瀚(Jonathan Chaves)编译《哥伦比亚中国后期诗歌精选:元、明、清三朝(1279—1911)》[16],在纽约刊行。译诗所本原文虽也包括词、曲,但大多还是中国古典文学正统概念的“诗歌”。译序简略介绍三代诗歌的发展,强调“诗”这一中国古典文学的瀚海中最精致、最典雅的形式,自唐宋以降并未衰落。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和学界的研究指向都停留在“诗”惟唐、“词”属宋、“曲”归元、明清标举“小说”的状态,不过是被所谓“黄金时代症候”(Golden-age Syndrome)误导的结果。全书正文分元、明、清三辑,译介三朝诗家43位,每一位名下平均有10余首作品。清代辑中仅遴选钱谦益、吴伟业、吴嘉纪、恽寿平、道济、金农、郑板桥、袁枚、刘鹗等13人,和元、明两朝的诗词作品阵容相比明显单薄,自袁枚之后的诗家词人也只提到刘鹗一家而已。从作者人数及所处时代的覆盖面来看,此书的清诗部分只能算有清一代诗歌总量的沧海一粟。 但这毕竟是清诗踏上经院式汉诗英译研究前台的开始。此书既出,《待麟集》作为第一个清诗断代英译文本几乎同时亮相,在现实中或许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但从清诗英译的历程来看,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三、《待麟集》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待麟集》的长篇导言。罗郁正与舒尔茨从“分期的问题”开始,对清诗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经济背景”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继而从“诗歌与政治”、“政府资助、论争与流派的诗歌时代”③、“层出不穷的诗歌理论”、“唐宋诗特质的缩略”④、“清末的文学评论家”、“清诗中现实主义的兴盛”、“词的复兴”等几个方面阐说清诗的特征。文中指出:清朝建立之初社会、民族矛盾尖锐,待政局巩固之后诗坛出现全面承继唐宋诗歌传统的“复古”状态,是当时政治与文化氛围所造成必然结果,并非清代诗人词家“毫无创造力”。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的诗艺源远流长,在后世诗人中,清代诗人摆脱传统束缚的愿望最为强烈”,他们“没有像唐、宋、元的诗人那样创造新的形式,可是他们试图调和传统和时代变迁使之更加丰富”。 该书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原的大历史背景,激发出充溢于诗人胸中笔下的“爱国激情”,是清诗词相对于前代诗歌而言最突出的特色,“这在该时代的一首一尾,人们由悲愤转向绝望之时尤为突出”;二是在模仿前人与创新突破的反复摩擦、不断冲突之中产生了大量批评理论;三是明确的历史感与写实主义的倾向;四是随着词体的重新被推崇而提倡比兴,注重婉约隐曲的表达。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对清诗的概括总结也是中肯的。清诗坛流派纷呈,风格竞出,承载着那个特定朝代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心态,大有名家佳作存在,其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链条当中,不能割裂,不可忽略,也不能替代。导言中反复强调的这一主旨,于是,凡谈及清代文学一概注重戏曲和小说,对诗歌普遍缺乏感性认识的美国学界,被《待麟集》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文学》(CLEAR)发表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麦大伟(David R.McCraw)的评论文章,称此书的编译者们“灵巧地速写清诗词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政治热望及其衍生后果、诗歌风格及其演变”,“进一步阐明了一些似曾相识的观点,比如清诗坛拟古主义与诗歌批评的繁盛”,他们对清诗的评价令人耳目一新,“驳斥了那些认为清诗词不足为道的陈腔滥调”[17]。 加州知名汉学家范佛(Eugen Feifel,1902-1999)在《华裔学志》撰文,认为与涉及英译清诗词的其他文本比较,《待麟集》“从作家阵容和作品数量上都很突出”,展示了清代的诗人词家和学者们是“如何探讨革新开拓的有限可能性,并在风格与内容上运用于他们的创作实践,直到最后这个朝代终了,所有可能性被耗尽而新诗(文)应时而生”。另一方面,中国断代诗歌的英译文本因《待麟集》而终于达到历朝完备,体现出“自唐代以后的各朝诗歌都各有其璀璨之处,使得对中国诗歌的体认从时段上迈进了一步。”[18]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奚密(Michelle Yeh)发表在《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的评论文章,也充分肯定了《待麟集》作为第一个清诗断代英译专辑的范本意义:“作为汗牛充栋的有清一代诗歌的精粹呈现,此书充实了汉诗英译的文库,填补了一项缺失太久的空白。”[19] 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亚洲语言文学系副教授Sharon Shih-Jiuan Hou刊发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的文章更进一步指出,《待麟集》的中、英文两个版本都是对清诗研究的积极贡献。文章预言,此书从清代诗坛总体介绍到代表诗人生平简述再到作品翻译,其架构厚重的学术含量必使之成为此后西方清诗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就英文版主体内容而言,译诗与相关注解也已“在忠信、可读与文体精美等方面尽可能地周密”[20]。 如前文所述,齐皎瀚的《哥伦比亚中国后期诗歌精选》与《待麟集》出版的时间在前后之间,其中涉及清诗的部分与《待麟集》交相辉映,因此学者们自然少不得要将两书并列比较。一般认为齐皎瀚文本以译笔生动取胜,《待麟集》则以选诗跨度见长。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学系的宣立敦教授(Richard E.Strassberg)认为,两书都“包括了大量资料,并尝试综合观照各个典型诗派的诗人们”,使清诗珠玉重光,共同为西方世界延展了探求中国诗歌精神及其文化渊源的路径。尽管选题类似,针对的时间段也相同,但两书“在内容拣选和翻译方法上各有侧重”,因而具有各自的鲜明特色。齐皎瀚出于个人对中国传统书法与绘画艺术的偏好,选取的不少诗歌最初是配在画上的,实际上偏重于山水田园的内容,其形式为读者们“增添了新鲜感”,却也限制了对清诗整体风貌的全面展示。相对地,罗郁正与舒尔茨着眼于清诗自身流变脉络选诗,立场和角度更为客观,为有志于研习清诗的后来者提供了“实用的参照”。[21] 现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伊维德(Wilt L.Idema)也具体指出了齐皎瀚因过于注重书法绘画,造成从诗人拣选到诗歌内容拣选的偏颇。哥伦比亚选集的清诗部分实际上没有完成对清代诗坛的整体展现,而《待麟集》则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清诗坛的总体格局。两书并驾齐驱,“如果目标是让西方大众更了解这末代皇朝的诗歌,他们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了”。即便如此,这位汉学家对清诗词的偏见依然令人遗憾的根深蒂固。他认为两书中所译介的诗也好,词也好,“都鲜见跳脱传统框架的独创性或特色”,实难与唐诗宋词的成就相伯仲。伊维德最后倔强地声明,两书的内容不仅未能消除,反而是加深了他对清诗词的不以为然。[22] 同样是将两书并列的评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文章不仅篇幅更长,涉及的内容其实也已超出了单纯评点两书的范畴。他先用了不少笔墨列举出当时中国本土清诗研究的实绩,诸如1984年《文学遗产》刊发的“清诗讨论专辑”,钱仲联先生主持下《清诗纪事》以及一批别集的整理出版,各家选本和《清诗选》的问世,等等,补充了《待麟集》导言里提及的相关情况。 宇文所安对清诗的了解以及对清诗研究进展的关注,显然比他同时代的其他英美学者深广得多。他提到,任何一种“清诗选集”成书之难,首先难在清诗的数量实在太大,诗人太多;其次难在对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定论”,各大流派及其代表诗人与作品的排次就很模糊。因此,要达成呈现清诗“全貌”的目标并满足大众的阅读期待,并非易事。立足于诗人及其作品拣选的角度,他认为哥伦比亚选集的主体内容以明诗为重,齐皎瀚在三朝600余年的诗海里自由巡弋,他所选取的诗家及其作品带着明显个人喜好的印记。他并不在意是否完整、忠实地展示“清诗的格局”,他只需要译文能够传达他自己领会到的中国诗艺之丰美就足够了。罗郁正与舒尔茨基于保守的立场,基本上围绕公认的清代名家选诗,虽译文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读错译,也并不妨碍《待麟集》对清诗研究的典型价值。[23] 以上各家评说,足证《待麟集》以时间历程划分清诗发展阶段,以代表作家及其作品为主要范例的编译框架,经纬交织并相得益彰,为英美学界勾勒出了清诗词集大成的风格特征与精神特质。 在充分肯定《待麟集》对清诗英译与传播的历史意义的同时,诸位学者也指出了很多此书存在的缺憾与不足,尤其是针对译文。麦大伟、范佛、Sharon Hou和宇文所安的评论文章里都用了大量篇幅,逐字逐句探讨翻译的缺失。 和齐皎瀚的译笔相比,《待麟集》中清诗的英文呈现总的来说的确略显生硬,力求详尽的注释实际上阻碍了阅读审美的连续贯通,欠缺流畅的诗意与灵动的诗情,限制了此书后来在普通读者群中的流传。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待麟集》的翻译经数十位美国学者之手,难免瑕瑜互见,要统一诠释原诗的角度与译文创作的风格谈何容易。译文的不尽如人意处,并不影响此书对后来清诗词研究的参考价值,更不应该影响后人对此书历史价值的判断。 纵使今天我们用现代文解读、赏析古典诗歌,都还往往难免错漏,更何况这些英美学者们在解读之后,还要用一种完全异质异构的语言去重新表述。因此,任何一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英译文本,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待麟集》也不例外。以清诗艺术形式之百法纷凑,思想内容之宏衍丰盈,现存作品数量之盈千累万,《待麟集》所包括的内容也只是管中窥豹、冰山一角而已。然而综合选诗的时间跨度、辑入的作家及其作品等几个方面来看,《待麟集》不仅集中呈现出清代诗词承继过去历朝传统并向纵深发展的成就,揭示了清代诗词处在中国诗歌古今裂变特殊历史时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脉络,更填补了清诗词断代英译的一大空白,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各朝断代文本至此得以完备。对英美学者重新评价并提高对清诗的学术判断,更清晰地认识中国诗歌史各个重要环节的转承流变,更客观地总结中国诗学的历史源流及其内在的逻辑性,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学术首创性,其开山之功是毋庸置疑的。 如今,各种中国古典诗歌选译文本中已不难见到译介清诗词的专章,袁枚、钱谦益等名家专门译介也陆续问世,但尚未见到《待麟集》以外的清诗词断代英译文本。随着本土清诗研究的纵深发展,随着中美文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清诗英译与研究终将展开一个新局面是可以预期的。这或许正是可以告慰罗郁正这位先辈学人之处。 ①此书于1933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初版时,中文书名为《百姓》,英文书名为:The Hundred Names: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后中文更名为《百姓诗》,英文也更名为:Poems of the Hundred Names: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etry Together with 208 Original Translations,于1935年由史丹佛大学出版社再版。后数次再版与重印都基于1935年史丹佛版本。 ②此著述为作者的博士论文,英文本未能公开出版,现藏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图书馆、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图书馆等处。 ③此书的导言原是英文,中文版由潘捷译出,此处译为:“诗歌获赞助时期中演成的争议和流派”,笔者对照英文原文“Poetry in an age of Patronage,Controversy and partisanship”重译。 ④此处潘捷译为:“唐宋诗性质的对比”。笔者对照英文原文“Qualities of T'ang and Sung Verse Contrasted”重译。标签:诗歌论文; 袁枚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诗经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