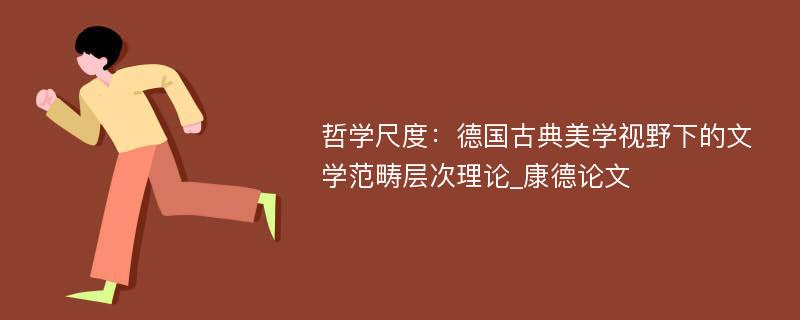
哲学标尺:德国古典美学视阈中的文类等级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尺论文,德国论文,美学论文,古典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5)03-0092-08 德国古典文类理论由康德开风气之先,据其哲学理论体系从宏观上批判一切客观、外在性的文类规则,开启了德国古典文类理论哲学化转型之路。继康德之后,研究者对文类问题的关注要直接得多。文类等级问题即是其一。德国古典文类理论中,对此问题的论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具体情形,即:两文类之间的等级问题,“三分法”产生的等级问题以及单个文类的等级问题。 一、两文类之间的等级问题 此问题可以席勒关于悲剧和喜剧孰高孰低的论说为代表。他以康德美学思想为指导,给出了合乎逻辑而又别具特色的等级观。席勒如此说道: 有好几次人们争论:悲剧和喜剧,二者之中哪个等级更高些。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二者之中哪个处理着更重要的客体,那么毫无疑问是悲剧占有优势;但是,如果人们想要知道二者之中哪个需要更重要的主体,那么几乎就不能不赞成喜剧了。①在席勒看来,喜剧之所以高于悲剧,主要有以下几层原因。 首先,从审美判断层面来看,审美的合目的性作为判断的唯一依据,使得喜剧高于悲剧。席勒继承了康德关于美、美的艺术、审美判断的学说,认为美是不需要说明或不借助于概念说明自身的形式;形式的美或表现的美是艺术所特有的;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外观;有审美心境的人,只要他愿意,他就会普遍有效地判断,普遍有效地行动;假如审美趣味的判断是完全纯粹的,那么就必定完全弃绝了那种认为美的对象有某种(理论的或实践的)价值和有某种质料构成以及为某种目的存在的观念等等。总之,康德美学体系中由审美判断的先天原则“审美的合目的性”导致的对形式审美独立性的极度重视,在席勒美学思想中得到了延续。席勒认为,在一部真正的美的艺术作品中,内容不应该起任何作用,而形式应该起全部作用,只有从形式中才有希望得到真正的审美自由。故而,席勒反对束缚于质料而让外观为目的服务的做法,吁求“对纯粹外观作无利害关系的自由评价”的人性革命,以期实现外观在理想的艺术中具有独特的个性。而且在其对于三个王国的区分之中,外观、形式、形象、自由游戏诸概念在审美王国里本质相通,他认为审美王国就是游戏和外观的快乐的王国,置身其中,人与人就只能作为形象来相互显现,人与人就只能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面面相对。那么,就悲剧与喜剧而言,悲剧无疑受题材内容(质料)的因素影响很大,因为它要始终处于一种特殊的目的(激情)的支配之下。而根据席勒关于美的无功利、无目的的规定,悲剧作为一门激情的美的艺术,其称谓本身即为矛盾体。其次,就审美判断的自律性来说,如果任何东西都不是由于质料而存在,而是由于形式而存在,那么表现就会是自由的。因此,内容(质料)的因素作为他律,严重侵犯了艺术作品形式的审美自律,此时产生的艺术作品只能是矫揉造作的。席勒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一旦艺术品“以质料的自然(本性)为基础的特征,那么美就受到了损害;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他律”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悲剧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艺术。最后,席勒从审美判断与认识判断的界限出发,认为如果基于内容(质料)来寻求艺术效果,那么,接受主体只是以知性或感性出发,直接寻求道德教化或感官快适,而这并非真正纯粹的审美判断,故而会破坏作品目的与合目的的形式、感性与知性的有机统一。席勒说: 如果一部作品仅仅通过它的内容来产生效果,那么并不一定就证明在这部作品中的无形式性;这倒往往证明在判断者心中缺乏形式。……他可能习惯于不是仅仅用知性来接受,就是仅仅用感性来接受,所以,即使在最成功的整体那里他也只会偏执于部分,即使在最美的形式那里他也只会偏执于质料。……而艺术大师却运用无限的艺术要使这种个别的东西消失在整体的和谐之中。他对艺术的兴趣绝对地不在道德方面,就是在自然方面,只是恰恰不在应该在的方面,即不在审美方面。③在以内容(质料)这一客体为重的悲剧接受过程中,上述不良倾向委实在所难免。悲剧也因此有把自身排除出艺术审美范畴之虞。或正为此故,席勒提出他的“悲剧的理想”说,即:“在一部悲剧之中,如果被激起的同情是比较少运用题材的作用,而更多的是最好地运用悲剧形式的作用,那么,这部悲剧就是最完美无缺的了。这部悲剧可以算作悲剧的理想。”④ 从艺术生产层面来看,艺术家主体的自由统一性,使得喜剧高于悲剧。为了论说的便利,可以从席勒关于素朴与感伤的理论及其与康德美学思想的关联谈起。席勒认为诗的天才借以表现自己仅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或模仿现实,或表现理想,前者造就素朴的诗人,后者造就感伤的诗人。个中原因在于文学与完满人性表现的特殊关系,席勒指出: 诗的概念只不过是给人性提供尽可能完满的表现,如果我们现在把诗的概念应用到上述那两种状态中,那么就会发现,在自然的素朴状态中,由于人以自己的一切能力作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发生作用,因而他的全部天性都完全表现在现实中,所以诗人就必定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相反,在文明的状态中,由于人的全部天性的和谐协作仅仅是一个观念,所以诗人就必定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表现理想。这是诗的天才借以表现自己的仅有的两种可能的方式。⑤这一观点的别样表达就是:诗的艺术只有两个领域,它必须要么在感性世界里,要么在观念世界里。不管是在感性世界里的素朴诗,还是在观念世界里的感伤诗,不论是模仿现实,还是表现理想,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完美人性。不同之处在于:素朴诗人直接在现实自然中加以表现,而感伤诗人在扬弃或克服现实自然中间接地加以表现。按席勒意见,如果说对素朴的满意是对显现观念的自然的兴趣,那么,不妨说对感伤的满意是对显现观念的被扬弃或克服后的理想自然的兴趣。此间感性与普遍理性(观念)之间的和谐统一论,认人联想起康德美学思想中审美的合目的性、美的艺术、天才诸范畴。因为康德正是先天地从形式的合目的性出发凭借审美判断来连接、统一知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此类的二元对立;又以自然通过天才为艺术创作自我立法,来呼应形式的合目的性,最后得出结论:美的艺术只能是天才的产品。两相比照,席勒和康德的期求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理论运思如出一辙,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席勒会说“每个真正的天才必定是素朴的,否则他就不是真正的天才”。⑥ 对于作为不可分割统一体的素朴诗人而言,其与现实表现对象的关系是和谐、一致;而期待表现理想的感伤诗人,其与现实表现对象的关系是对立与冲突。所以,感伤诗人或表示对现实的厌恶,或抒发对理想的渴慕。前者产生讽刺诗,后者产生哀歌。席勒认为,悲剧和喜剧分属讽刺诗里激情的讽刺和戏谑的讽刺。出于文学完美地表现人性的神圣使命,席勒提醒诗人务必注意实际的自然与真正的自然、真正的人的自然本性与实际的人的自然本性两组对立范畴的不同涵义,千万不可将其混淆,否则将是文学之灾、读者之大不幸。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种种谬论就是因为混淆上述范畴得以存身诗学,贻害匪浅。而只有真正的自然、真正的人的自然本性才是天才诗人需要恪守的永恒准则,而这也正是诗的尊严、审美的尊严的有力保障。简而言之,所谓真正的自然,与实际的自然、庸俗的自然相对,是丰富多彩、富有诗意、充满生气的具有感性真实的自然;所谓真正的人的自然本性是身心健康和谐、人格独立自由、道德高尚纯洁等完美人性要求的显现。席勒认为,就作为激情艺术的悲剧来说,激情的每次勃发,即使极其庸俗,也仍然是实际的自然;它甚至可以是真正的自然,但是它不是真正的人的自然本性。如果悲剧中的每个行动主体都是真正的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现,那么悲剧的激情是无以产生的,因为悲剧激情往往来自身心、人与现实此类的对立冲突,而非和谐。他还批评悲剧舞台演出的激情表达并未模仿真正的自然,而仅仅是对实际的自然进行了无聊而鄙陋的表现。复就喜剧来说,由于喜剧传统上一般都是模仿社会底层人物,席勒认为低劣的自然不是不可以模仿,但是此时,作为喜剧诗人“他自己的美的自然本性必须影响对象,而不容许模仿者与庸俗的材料沆瀣一气。只要他本人——至少在创作的时刻——是真正的人的自然本性,那么他给我们描绘的是什么东西,就无关紧要了”;而丑相在丑相中映现是与完美表现人性的真正的诗的精神相违的。席勒在他处论说悲剧与喜剧关系的一段话亦可与之相参照:“前者早已借助他的严肃的题材而避免了轻浮;但是后者只能处理道德上无关紧要的题材,如果在这里不使内容的处理高尚化,如果诗人的主体不能代替他的客体,那就必然会陷入轻浮,就会丧失任何诗的尊严。”这里就提示我们,客体激情本身作为悲剧的内容(质料)并非完美人性的表现,悲剧是以激情爆发为媒,从而将业已破坏分裂的完美人性重新予以表达;而喜剧借助于体现完美人性的艺术主体直接表现完美人性,与内容(质料)无关。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要求喜剧诗人以其美的自然本性影响对象,发挥其真正的人的自然本性的艺术主体作用,殊不知,无论是美的自然本性,抑或真正的人的自然本性,都属于素朴的范畴,这就在喜剧诗人身上实现了素朴与感伤的某种融合,而这恰恰是席勒无比期待中的优美人性的理想的模式显现:“不论素朴的性格还是感伤的性格,单独来看,都不能完全详尽地阐明美的人性这个理想,这个理想只有在两者的紧密结合中才能出现。”席勒同时指出,优美人性的理想即诗的性格,亦即处于审美状态的自由人。因而,不论是就喜剧诗人的素朴状态中的真正的人的自然本性而言,还是就喜剧诗人实现了素朴与感伤的融合来说,喜剧诗人皆与优美的性格内在相连。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更好地理解和领悟席勒所谓“喜剧的目的是和人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目的一致的,这就是使人从激情中解放出来,对自己的周围和自己的存在永远进行明晰和冷静的观察,到处都比发现命运更多地发现偶然事件,比起对邪恶发怒或者为邪恶哭泣更多地嘲笑荒谬”。而一旦这一目的达到的话,那一切悲剧就都成为多余的和不可能的东西。因为从对立和冲突的激情复返素朴式的优美和谐,悲剧丧失了产生和存在的土壤。既然喜剧诗人与优美的性格对应,那么悲剧诗人则与崇高的性格相连,而崇高的性格只是断断续续地自由,而且只是通过努力才获得自由。总而言之,在席勒看来,喜剧的美妙任务是在我们心中产生和维护这种心灵自由,悲剧的使命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在这种心灵自由被激烈的情感粗暴地破坏了的时候帮助把它恢复起来。⑦ 综上所述,席勒在审美判断层面否定了悲剧内容(质料)的他律性,在艺术生产层面详细阐述和论证了艺术生产主体作为自由统一体的优越性,从而两相结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大有别于传统关于悲剧与喜剧等级认识的理论画卷。而此画卷之所以能够完满构成,离不开康德美学思想的强大支撑。回顾西方文类理论史,狄德罗也曾通过强调喜剧诗人的主体性来抬高喜剧等级:“喜剧诗人是最地道的诗人。他有权创造。”⑧但狄德罗的主体性只是针对审美主体的创作方式,而非席勒所指涉的审美主体自身的特别规定性。如果前一种主体性是归属本体的外延,那么后一种主体性即是本体自身。其次,就素朴诗人与感伤诗人的概念而论,对应古今时段划分的武断性与悲剧、喜剧等文类历史性存在形态的客观性之间,理论与事实之间,实难吻合,只是唯心主义一厢情愿的美好传说。正如谢林评论所说,素朴与感伤“整个对立本身是某种主观者”。例如“有关索福克勒斯,任何人都不会说:他是感伤的;而且正因为如此,任何人也不会说:他是素朴的。一言以表述之,索福克勒斯只不过是绝对的,并无任何进一步的规定。席勒所袭用的古希腊范例,主要来源于叙事诗”;而且叙事诗也只是“有时呈现为素朴的”;而“戏剧既不能呈现为素朴的,亦不能呈现为感伤的;莎士比亚,譬如说,可被视为素朴的,——正是这一点,使他在这方面再度成为近代的人”。⑨再次,虽然席勒首次将悲剧与崇高的性格相关联,但是仍未超越优美的性格。优美范畴的压倒性胜利,也间接地再次反映出德国新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最后,席勒对于喜剧诗人作为素朴的自由主体的角色强调,以至于视内容(质料)为可有可无,还是承续了康德以审美判断的自律、主观必然性反对迎合庸众这一做法的精神传统。因为席勒也同样坚持认为:“观众的满足,仅仅就是对于平庸之辈的激励之举,但是,对于天才来说却是辱骂和威胁之举。”⑩ 二、“三分法”产生的文类等级问题 此可以谢林为代表。众所周知,康德美学提出用判断力连接起处于对立关系的知性和理性,以审美的合目的性或主观合目的性这一先天概念为原则,审美判断借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使感性表象与知性概念达到对立的统一。这在康德看来,正是属于审美判断力的辩证论,即:“一个判断力如果应当是辩证的,就必须首先是推想的;就是说,它的判断必须提出对普遍性的要求,并且是先天的普遍性的要求:因为辩证论就在于这些判断的相互对立。”(11)更为重要的是,在回答人们关于他对纯粹哲学的划分为何总是三分的困惑时,康德认为事物的先天划分必然是三分的,而三分法正是对辩证论的印证。他说: 有人曾对我的纯粹哲学的划分几乎总是得出三分的结果感到困惑。但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个划分要先天地进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这时它总是两分的(quodlibet ens est aut A aut non A,任何一个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综合的;而如果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数学中那样从与概念相应的先天直观中)引出来,那么这一划分就必须按照一般综合统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这就是:(1)条件,(2)一个有条件者,(3)从有条件者和它的条件的结合中产生的那个概念。(12)康德的辩证论思想,清晰地勾勒出“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论公式,尽管其本人没有将此演绎入艺术的划分之中,但是在谢林那里,古希腊诗学中提出的“三分法”因为辩证论而首次得到了别具一格的解读与诠释。 谢林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艺术和哲学虽都是自由绝对体,但是在“唯一的绝对者”面前,它们又各自作为现实者和理念者“同一”于其中。所以,“绝对者以普遍者与特殊者之绝对不可区分映现于普遍者中=哲学(理念);绝对者以普遍者与特殊者的绝对不可区分映现于特殊者中=艺术”(13)。那么,当艺术被划分为特殊艺术形态时,“作为现实者与理念者之完满的复合”(14)这种同一关系就会被打破,艺术世界从而首先被区分为对立之两端:作为现实范畴的造型艺术与作为理念范畴的语言艺术。其中原因在于:“造型艺术所赖以表现其理念者,乃是某种具体者本身;语言艺术所赖以表现其理念者,乃是某种普遍者本身,即语言。”(15)前者所谓“某种具体者本身”即声、光和人体。就语言艺术内部而言,以辩证论实现对三分法的逻辑演绎,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 首先是从反映手段来看,谢林认为,叙事诗采用的是模式化方式,即“普遍者在其中成为特殊者的表征”;抒情诗采用的是比喻方式,即“特殊者在其中成为普遍者的表征”;戏剧采用的是前两种对立方式之综合,即象征方式:“在其中,普遍者并不成为特殊者的表征,特殊者亦不成为普遍者的表征,而两者绝对同一。”故而因为戏剧采用的是唯一的“绝对的方式”而高于其它两者。(16) 其次是源于哲学体系的内部划分,谢林认为哲学包括以知为特征的自然哲学、以行为特征的理性主义以及将对立的知行置于不可分地位的艺术哲学,此观点明显受到康德对于纯粹哲学体系的划分思想的影响。以此为参照,谢林认为抒情诗对应于知,最富主观性;叙事诗与行相对应,最富客观性;戏剧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是两者的综合。正因为这种综合,戏剧又高于其它两种文类。 最后是源于席勒有关素朴与感伤的理论,谢林认为诗歌肇始于“作为同一、作为一种质朴状态之叙事诗”,继而在抒情诗阶段,同一分裂为知与行、主观与客观、必然与自由之间的斗争;终于在戏剧阶段里,在这“尤为完善的创作中”再度达到“高级的同一”:“戏剧将两种相互对立的形态之属性纳于自身,成为真正的自在存在以及任何艺术的实质之最高表现。”(17)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谢林继承了自康德伊始的连接和统一对立因素的思路,对传统三分法进行了具体演绎和分析,既是辩证的,又是唯心的;但其实三分法自诞生时,似乎就打上了辩证的烙印,不管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史诗(叙事诗)都是作为戏剧、抒情诗的综合者而面向世人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综合者不同,即从曾经的叙事诗转变为现在的戏剧。其原因在于文类的历史演变。一度以史诗为代表的叙事诗,日渐从动作模仿的表演性和诗人直接叙述,蜕变为仅是叙述;而戏剧除了动作模仿之外,随着近代戏剧中人物性格因素的增强,叙述成分地位抬升。故而在此消彼长之间,戏剧取得了适宜作为综合者角色的主动权。二是两个“综合”本质存在差别。受同一哲学的影响,在谢林对三分法的辩证演绎中,戏剧作为最后的综合,不是数量、程度、平面上的综合,而是质上的、立体的逻辑递升。从上述诸如“绝对的方式”还是“真正的自在存在”、“最高表现”等词汇对于戏剧综合性质的概括中,都不难感知到这一点。而在古希腊文类理论里,三分法中的综合则至多是表现方式上数量的汇总。正是受此辩证演绎三分法的影响,在康德于一切美的艺术中,把文学(诗艺)置于“至高无上的等级”(18)之后,戏剧(尤其是悲剧)在文学之中的地位借以迅速提高,谢林把戏剧视为“使艺术世界的这一领域臻于完满”者,誉为“一切艺术之最完美的结合”(19)者。此后作为德国古典美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也类似称誉戏剧为“最完美的整体”、“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20)直到别林斯基那句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评价“戏剧诗歌是诗歌发展的最高阶段,艺术的皇冠,而悲剧则是戏剧诗歌的最高阶段和皇冠”(21),把戏剧、悲剧推至人类艺术的巅峰。谢林在悲剧被抬高到戏剧之皇冠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还在于,他首次从哲学高度解释了悲剧在戏剧中的“始初的”、“第一种形式”的地位,从而把悲剧视为戏剧的代名词,喜剧则是悲剧之转化。他说: 显而易见,我们索性将戏剧直截了当地解释为悲剧;因此,看来,我们似乎摈斥另一种形式——喜剧形式。前者不可或缺。须知,一般说来,戏剧只能产生于那种真正的和实际的斗争,即自由与必然的斗争,可区分体与不可区分体的斗争。……而须知,这一斗争之直接的和绝对的表现在于:必然形成客观的范畴,而自由则形成主观范畴;这也就是悲剧的规律。总之,悲剧是第一种形式,而喜剧则是第二种形式,因为它无非是产生于悲剧之反其道而行之。 必然呈现为客体,自由则呈现为主体。自由与必然在悲剧中的关系便是如此,因为悲剧为戏剧始初的、似乎肯定的表现。这样一来,借助于这一关系的转化,一种形态应运而生;在这种形态中,恰恰相反,必然或同一则呈现主体,自由或差别则呈现客体;这便是喜剧的规律……(22) 谢林从辩证论出发对于传统三分法的逻辑演绎,在西方文论史上影响巨大。从弗·施莱格尔、黑格尔到别林斯基,从浪漫主义到形式主义,无不见到此说之踪迹。尤其是此说本身开针对三分法进行不同模式演绎之先河。例如雨果就指出:“诗有抒情短歌、史诗和戏剧三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和一个相应的社会时期有联系。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而近代则是戏剧性的。”(23)俄国形式主义大家雅各布森则用语法上的人称来对应三分法:抒情诗对应于第一人称,戏剧对应于第二人称,而叙事诗对应于第三人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三、关于单个文类的等级问题 此可以悲喜混杂剧的地位为例。在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时期,悲喜混杂剧曾经作为被大力推崇的混合型文类来反对古典文类理论中对于悲剧的一味肯定。瓜里尼、拉辛等都是悲喜混杂剧的坚定支持者,狄德罗、博马舍等人亦通过提出介于悲剧与喜剧之间的严肃喜剧、严肃戏剧、家庭悲剧等新类型对此予以积极响应。然而在德国古典文类理论中,悲喜混杂剧在黑格尔看来却是无足轻重者,他说:“处在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是戏剧体诗的第三个主要剧种。这个剧种没有多大的根本的重要性,悲喜混杂剧也可以列入这一种。”(24)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将此类混种归入“还不够完善”(25)者之列。为何黑格尔会下此结论呢?这还与上文所论的三分法的辩证演绎密不可分。受谢林影响,黑格尔仍旧把戏剧视作“史诗的客观原则和抒情诗的主体性原则这二者的统一”,“把史诗和抒情诗结合成一体”,(26)因此,在黑格尔的文类理论体系中,戏剧同样高于其它两者,恰如他认为戏剧是“最完美的整体”、是“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一般。而得出此结论的前提之一是戏剧对于主客体矛盾的解决,不是包含悲喜混杂剧在内的正剧的基础。黑格尔认为,正剧的基础不同于悲剧,即正剧的自然基础是“幸运或圆满的结果”。“剧中人物本来并不要牺牲自己就可以抛弃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或是彼此言归于好,用不着造成悲剧的结局。”(27)而同样视悲剧为戏剧“第一种形式”的黑格尔认为,戏剧(悲剧)的最高任务是通过矛盾双方各自克服片面性但谁也不是胜利者来实现标志“永恒正义”胜利的“和解”,而“真实只在于矛盾的解决,所谓解决并非说矛盾和它的对立面就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们在和解里存在”,“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去表现上文所说的那种和解了的矛盾”。(28)可见,戏剧(悲剧)艺术的真正和最高使命不是表现作为悲喜混杂剧基础的圆满结局和幸运收场,而是“冲突和解决的悲剧性”(29)。因而,悲喜混杂剧自然就处于不太重要的地位。 在文类理论中,文类等级(genre hierarchy)向来被视为文类间“最活跃的关系”之一。(30)此前也曾出现过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洲文艺复兴与新古典主义时期“古今之争”等有关文类等级的不同论说,但是它们从未像德国古典美学这样全方位贯彻自身哲学观作为文类等级的衡量标尺,也从未涉及如此之广泛的等级范围。由此可见,德国古典美学不仅在西方美学史进程中占据不可代替的位置,而且对于西方文类理论发展同样具有与众不同的历史意义。文类等级问题的探讨,不仅深化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已有研究,同时开拓了西方文类等级理论的新疆域,值得学界予以高度关注。当然,由于德国古典美学一味高举哲学观的标尺,导致的不良结果也是显见的,即文类等级论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哲学观的附庸,文类等级观探讨的先验、唯心色彩遮蔽了文类理论自身发展的独立传统。这一问题也不容回避。 注释: ①[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②[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③[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69~70页。 ④[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19页。 ⑤[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⑥[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⑦此段参见[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48~223页。 ⑧[法]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艾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55页。 ⑨[德]弗里德里希·谢林:《艺术哲学》,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139~140页。 ⑩[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 (1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12)[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页,页下自注。 (13)[德]弗里德里希·谢林:《艺术哲学》上,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23、65页。 (14)[德]弗里德里希·谢林:《艺术哲学》上,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5页。 (15)[德]弗里德里希·谢林:《艺术哲学》下,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16)[德]弗里德里希·谢林:《艺术哲学》上,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65~66页。 (17)[德]弗里德里希·谢林:《艺术哲学》上,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364页。这里三者关系是“素朴—感伤—再素朴”的辩证演绎过程,而非简单的总分关系,例如有学者这样说道:“根据总体框架,诗也有三个级次,即三种特殊的形式。谢林认为,各种诗的次序可按两种原则排列,一种是按自然和历史的原则,把史诗放在首位,因为史诗是诗的原始统一体,抒情诗和戏剧诗都是从史诗(叙事诗)中分化出来的,按其起源来说,史诗或叙事诗也最早。”(参见曹俊峰等:《西方美学通史·德国古典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31页) (18)[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19)[德]弗里德里希·谢林:《艺术哲学》下,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385、417页。 (20)[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0页。 (21)[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374页。 (22)[德]弗里德里希·谢林:《艺术哲学》下,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370~371、389页。 (23)[法]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40页。 (24)[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94页。 (25)[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1页。 (26)[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1、243页。 (27)[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29~330页。 (28)[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67~69页。 (29)[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30页。 (30)Fowler,Alistair,"Genre and the Literary Can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11.1,1979,p.100.标签:康德论文; 席勒论文; 三分法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审美教育书简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艺术哲学论文; 文化论文; 人性论文; 喜剧片论文; 戏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