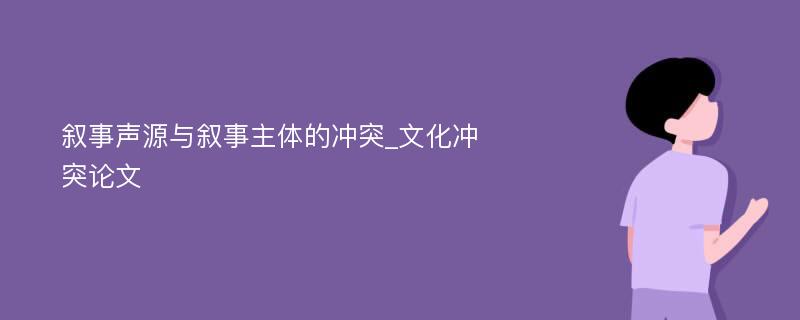
叙述声音的源头与叙述主体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头论文,主体论文,冲突论文,声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叙述声音源头的叙述者之构成 任何叙述存在的前提是有一个叙述者,同时,任何叙述者存在的前提是有一个叙述,叙述和叙述者是互为存在条件的。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只有有了言语的主体,才可能有言语,同时,只有有了言语,言语的主体才可能存在。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一部分不能进行语言表达的人永远都成不了表达者,因为没话语被他说出来。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言语,也就不存在任何言语主体,尽管这几十亿人照样存在。这与洛特曼对文本与语境、作者的关系的看法是同样的逻辑:“洛特曼认为语境并不先在于文本,是文本的前提条件;相反,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文本创造了语境,包括所有在传播行为中的参与者”,“并不是作者创造了文本,而是文本创造了作者”。①由于这个原因,生活中的作者和叙述者的区别也就特别好理解,作者不等于叙述者。因为任何作者一旦开始叙述,他已经分裂出一个叙述功能。同理,一旦存在一个叙述,这个叙述的叙述者就不再可能等于作者。换句话说,叙述者只存在于叙述之中,而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只可能根据叙述去建构叙述者,而不可能在任何世界找到叙述者。叙述者不存在于实在世界,不存在于可能世界,也不存在于虚构世界。它不是一个形象,也不是一个人格,而是一个功能。如果把叙述功能进行人格化想象,我们就得到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唯一功能就是叙述,他是叙述的声音源头。由于“人的所有感觉、思维都是在符号中进行的,思维就是符号的衔接游戏”②,所以从符号文本就可以反推出一个思维形态,思维也只能通过符号反推。要建构叙述者,唯一的依托就是叙述声音。叙述者,只是一个比喻,一个声音源头的比喻。 因为叙述者只以声音源头的形式存在,所以我们就只可能根据叙述声音去判断叙述者的形态。叙述声音也可以叫做“话语”,其形态直接决定叙述者的形态。在一个叙述文本中,由于叙述声音可能来自多个不同的叙述主体,所以叙述者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框架③,叙述声音可以来自框架中的任何部分,特别是在多媒介叙述文本中最为明显。例如一部纪录片,声音可以来自采访者、被采访者、旁白、字幕,甚至来自观众的二次叙述,等等。就是说,任何叙述,都不可能由一个主体独立完成,它必定是在主体间交互完成的。即使是内心独白,也要设想一个能够听见自己独白的自我作为接收主体,进行叙述的自我叙述出来的话语,必须让作为接收主体的自我能够理解,他就不得不考虑作为接收主体的自我的感受和理解能力。一旦内心独自的发送主体和接收主体能力不一致,自己说的话自己听不懂,人即陷入精神分裂。正常情况是,有多强的理解能力就有多强的叙述能力;同理,有多强的叙述能力也就有多强的理解能力。叙述者受限于叙述的文化框架。只有一种叙述宣称是例外,那就是“神谕”。即使是“神谕”,也要选择一种语言,不得不进入语言的文化框架之中。 黑格尔认为:“在古典型艺术里“神谕”毕竟还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其中人的个性还没有达到内在性(精神性)的最高峰,而只有在这种最高峰上主体才能完全凭自己的行动作出决定。”④就是说,对叙述者形态的想象和建构,至少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认识过程。柏拉图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真理存在于“理式”之中,“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⑤柏拉图反对诗人进入他的理想国,是因为诗人作为“人”的主体没有得到柏拉图承认,所以诗就与他说的那个作为“理式”的真理隔了三层。换句话说,柏拉图既不承认“诗人”具有独立精神,更不承认“诗”本身具有独立精神,诗就是对现实的摹仿,而现实又是对真理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虽然师承柏拉图,但是却为诗人做了辩护,承认诗人的主体性地位。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诗人是“情节的编制者”。⑥亚里士多德所论的情节核心,是“事件的排列顺序”和事件的“因果关系”,而这二者,都掌握在诗人手中。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最大变化,就是叙述的权力被掌握在了诗人的手中,诗人有资格安排情节而成为叙述者。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历史、史诗、悲剧、喜剧都是摹仿,但是摹仿的对象变了,是“可能”或“必然”的事,“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因而它既是对“行动”的摹仿,也是对真理的摹仿。现代叙述学的又一个重要变化,是以叙述文本为中心,“强调作者客观化和非个人化”,“要求消除小说里作家出面的一些明显的标志”。⑦布斯在做出上述判断的同时也认为,“作家的判断总是存在的”,“纵使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的伪装,他绝不可能使自己消失”。⑧在读者中心论崛起之后,仍然不可能去除作品而空谈读者。英伽登强调的是“必须区分文学作品与作品的具体化”⑨,伊瑟尔强调的是“本文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⑩,姚斯认为“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11),他们都没有否定作者和文本的地位。简言之,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都只是研究重心的偏向,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余二者。 作者、文本、读者中心论的分别崛起,恰恰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一个叙述而言,每一个组件都是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组件都是叙述框架不可或缺的部分。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叙述者的时候,就会发现,各大理论所论的中心,都是作为框架的叙述者的一个部分。叙述声音可能来自框架中的任何部分。当然,由于叙述者本身的框架化性质,不论这个声音的源头在哪里,它必然通过框架叙述者这一个总渠道发出,故而叙述中的任何声音都可以认为是由叙述者发出的。但是,这样说并没有多大意义,完全不利于我们辨别修辞或结构意义上的声音差别,因此我们又必须悬置框架叙述者,转而讨论有差异的声音源头。即是说,虽然叙述者可以有多种伪装方式,但是当我们讨论修辞或结构差异的时候,我们宁可去谈它的伪装,而不愿谈那个本质。 叙述语与转述语的相对性和判别困难 经典叙述学一般区分两种不同的叙述声音,一种是叙述语,一种是转述语。在此领域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中国学者是赵毅衡,他在《文学符号学》《苦恼的叙述者》《当说者被说的时候》等多部著作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叙述语被理解为对叙述者话语的直接引用,转述语被理解为叙述者对人物话语的引用。由于叙述者和人物在常规理解中很容易被理解为处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所以这个区分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王彬认为“小说是叙述语和转述语的组合”,“叙述语被叙述者控制”,“转述语被人物控制”(12),徐岱认为叙述语就是“由叙述者发出的言语行为”,转述语就是“由人物发出但由叙述者引入文本的言语行为”(13)。但是这样区分也容易陷入两难困境。在多层次引语中,我们极难判断一个主体到底是人物还是叙述者。例如,小仲马的《茶花女》原文是第一人称叙述,常规理解是将“我”理解为叙述者,所以小说中的非引文部分就应视为叙述语。但是林纾在翻译该小说的时候,在小说的开头加了一个“小仲马曰”(14),由于这个引导语的作用,我们就应该把原来被视为叙述语的部分全部看作转述语。又如福克纳的小说《坟墓的闯入者》,小说中人物语言全用单引号,暗示整个小说文本是对另一个人物的话语的引用,这样一来,整部小说都是转述语,那叙述语又在哪里?难道一个单引号就能改变叙述声音的性质?这两个例子说明的问题是,叙述语和转述语是相对的,转述语就是上级叙述主体声称或暗示并非由他直接叙述的话语。这样,我们既可以把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我”的声音、吕纬甫的声音、老发奶奶的声音都视为叙述语,也可以把“我”的声音视为超叙述层叙述者对“我”的声音的转述,把吕纬甫的声音视为“我”对吕纬甫声音的转述,把老发奶奶的声音视为吕纬甫对老发奶奶声音的转述。叙述语是实质,转述语是修辞技巧,凸现的是“主体冲突”(15)。任何叙述语,对上一级叙述者而言就是转述语。任何转述语,对下一级人物而言就是叙述语。 使用转述语并不具有改变该叙述的意义的作用,但是却可以改变该叙述的表达效果和风格。转述语分为四类:直接引语式、间接引语式、间接自由式、直接自由式。凡是有引导句的都是“引语式”,无引导句的就是“自由式”;“直接记录”人物语言(说话人物在转述语中自称为“我”)的就是直接式,叙述者用自己的口气把人物语言说出来(说话的人物就称为“他”)的就是间接式。(16)这个区分非常清晰,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却会遇到麻烦。赵毅衡列举了两种情况,第一是“如果转述语中讲话者没有自称”时应当如何区分直接式与间接式,第二是“自由式与引语式的区分——引导句,在具体叙述中也会出现各种变体,引导句可以变得很模糊”。(17)在遇到上述情况的时候,接收者的感觉和判断就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在现代小说中,由于转述语常常故意模糊话语主体,让这四种转述语的界限非常模糊。例如,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中的两段: a.你在全国跑了不少地方吧?可是你不到新疆,就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 b.我是怎么到新疆来的?那说来话长了。其实呢,我也应该算是回乡知识青年。 由于《肖尔布拉克》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汽车司机在说话,司机自称为“我”,所以可以算是“直接式”,整个文本应该算是直接引语。然而,这个直接引语既没有引导语,也没有引号,只能算“自由式”,但它又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和语气的引导,所以又像是“引语式”的。如果整个文本都是转述语,那么上面a、b两句中的问句又该怎么归类呢?我们发现,只有把司机看作叙述者,把他说的话都视为叙述语,才能将这两个句子与其余部分区别开来。我们先假定司机的话都是叙述语,那么b句中的问句是间接自由式的,这很明显,然而这个话语的声音源头又是“你”,“你”既是人物又是受述者。若将其看作受述者,又怎么能够将其理解为转述语?现在再来看a句中的问句的声音归属。它既像司机问搭车人“你”的话(因为根据下文b,“你”问司机时司机都被称为“我”),也像搭车人“你”问司机的话(因为根据内容,只有司机才会在全国跑不少地方)。根据上下文反复揣摩,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司机问“你”的话,这个判断是根据语流、语气、风格以及后面那个“可是”做出来的。既然如此,它就应该是叙述语,但是因为是个问句,暗含了一个“我问”的引导语,所以它又好像是一个转述语。如果将其看作转述语,它应该归入哪一类,又很费周折。由于没有引导语,它应该算自由式,但是问句格式又相当于给它加了一个引导语,又像引语式。 这个例子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叙述语和转述语是相对的。只有把上一级话语看作叙述语的时候,下一级的话语才能被看作转述语。当我们确定一个话语为转述语的时候,上一级话语自然就成了叙述语。所以,所谓的转述语中的“引导语”,实质上就是一个把它所在层级的声音定位为叙述语的标志。第二,区分叙述语和转述语,并不是依据该话语的表面形式(有无引导语,有无人称变化),而是根据该话语的声音源头到底处于叙述框架中的哪个部分来确定。又如《肖尔布拉克》的下一段叙述: 你(a)别看让人搭车是件小事。他招呼,你(b)停下,他上来,就这一眨眼的工夫,他的心里就会想:咱们(c)国家还是好人多哇!你(d)呢,一看他那副笑脸,心里也会暖呼呼的,开车也有劲了,人也不困了。我(e)倒不是个爱聊天的人,只要旁边有个人,我(f)就觉得不孤单了。 确定了有叙述语的大框架之后,这段文字中就有一些是转述语。a“你”应视为对受述者的称呼,因此第一句应视为叙述语。b、d两个“你”,是叙述者对自己的称呼,但是仍然应该视为叙述语,因为声音源头还是叙述者的。如果声音是叙述者的,为什么他自称为“你”呢?赵毅衡认为这种情况下的“你”是“‘我’的另一种说法”(18)。但是毕竟在语言中,“你”不可能指说话人自己,所以此处又像间接自由式转述语。也可看作声音源头从司机处跳到了叙述框架的背景深处,所以又像是司机引用框架的声音,像直接自由式转述语。而c“咱们”一句,从形式上看,前面有引导语,应视为“他”的自称,应该算直接引语。然而,又因为这句话应该视为“司机”对“他”心理活动的推测,所以这句话并不是“他”想的,而是司机想的,声音源头应该在司机处,看作“引语”就很牵强,所以又应该是叙述语。e、f两个“我”又回到了司机的那里,所以还是叙述语,但又像“假性直接引语”。在这个例子中,叙述者所处立足点在不断变化:有时立足在司机处,有时立足在框架深处,有时立足在司机所述的乘客“他”处。由于叙述者所处位置可以不断变化,我们就很难在一个叙述中确切分清哪个是叙述语,哪个是转述语。 由于存在各种复杂的情况,对叙述语与转述语的判断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形式上的判断和实质上的判断又有各种交叉,加上叙述语与转述语具有相对性,我们就更难确定一个叙述中的话语到底是叙述语还是转述语了。特别是在多层级叙述和意识流式的独自叙述中,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声音就更难分清。又由于叙述者形态的复杂性,叙述声音可能来自框架中的任何部分,它甚至可以来自人物,所以将叙述者与人物对立起来进行的叙述语与转述语区分在处理比较复杂的叙述声音的时候就会陷入困境。在如下几种情况中,我们很难判断该话语是叙述语还是转述语: 1.叙述中的设问句或反问句。梁军著《金瓶梅札记》第六回: 那么,读者一定会问,这位王六儿是何许人也?她凭什么能让西门庆这位久经沙场的前辈神魂颠倒、欲死欲活的呢? 《玉梨魂》第一章: 梨花满地不开门,花之魂死矣。唤之者谁耶?扶之者谁耶?怜之者又谁耶? 第一个叙述的形式是直接引语,但是声音来源却不是人物,所以又不能算转述语。由于有“读者一定会问”的引导语,所以又不能说它是叙述语。此类叙述假定引用读者的话语,也可理解为引用隐含读者或受述者的话语,然而它本质上是叙述者的话语。第二个叙述的问句声音源头并不清楚,似乎是几者的综合。反问句预设了一个答案,有时相当于预设发问者已有答案,有时相当于假定读者已有答案,所以也相当于引用了读者的话语,目的是增强说服性。有学者统计并发现在古代白话小说中反问句被“高频使用”,其作用是“教化功能的需要”(19)。《论语·学而》连用三个反问句,达到的正是这种效果。根据直观感觉,民初文言小说中反问句比古代白话小说还要多,大概是因为此期小说的说教氛围更浓。乔治·桑的散文《冬天之美》结束时说:“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20)也可以视为已经为读者预设了一个答案。 2.叙述中的格言警句。格言警句既可以理解为叙述者说的,也可以理解为叙述者引用的话语,但该话语不是来自人物。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曰”,可以看作警句的变体。《西游记》第一回:“历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看起来很像转述语,但是声音源头并非人物,所以又不符合转述语的定义。 3.叙述中的常识。常识之所以是常识,就是因为假定作者、叙述者、人物、受述者、读者都知道且明白的话语。所以,它就既可视为叙述者的话语,也可视为对其他组件话语的引用。用“话说”引领的叙述可以算此类型中的一个亚型。《三国演义》第一回:“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颠倒了动宾结构“说话”,“话”成了言语的主体,“说”成了动作,言说者就可以是叙述框架中的任何一个。 4.以“本文”、“本书”自指的叙述。《西游记》第一回:“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叙述者以“这部书”自称。《红楼梦》第一回介绍书的复杂来历之后写道:“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然后开始讲故事,叙述者就成了文本。既然叙述者并无一个确定的人格主体,我们又何以能够确定哪些话语是叙述者的话语,哪些话语是人物的话语?难道人物话语就不是叙述者话语之一? 5.各类主体冲突过强的转述语。第一人称叙述中的直接自由式转述语,如果风格特征不鲜明,极易与叙述语混淆。对这一类,“转述语需要有很强的主体特征”(21)。对间接式而言,申丹认为“因为‘自由间接引语’在人称和时态上与叙述语相同,因此有时与叙述语难以区分……即便可以区分,我们也能同时听到人物的声音和叙述者的声音”(22)。她说的“自由间接引语”可能是“间接自由式”转述语,这种转述语也只能靠风格标注,若风格不明显,极难判断。由于中文没有时态接续性,两类“自由式”转述语都靠风格区分。而“引语式”转述语如果叙述主体特征过强,也会变成“假性引语”。申丹在讨论赵毅衡的转述语划分之后认为,“在没有人称或人称不起区分作用的情况下,由于无法断定转述语的时态,很容易出现直接与间接的两可型。”(23)转述语确实是叙述主体冲突的主战场,而斗争过于激烈的话又造成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转述语。 介于此,本文认为叙述中的主体冲突还要远远复杂于转述语中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主体冲突,叙述框架中的各组件之间都可能产生冲突。为了说明主体间的冲突,第一个工作应该是分清声音源头是框架中的哪一个部分。上文提到的五类情况说明,叙述者的声音源头可能来自隐含读者(第1类)、文化框架(第2类)、叙述框架(第3类)、文本(第4类)、隐含作者(第5类),叙述声音还可以来自人物,特别是第一人称叙述,我们可以认为所有声音都来自人物“我”,那它是叙述语还是转述语?叙述声音还可能来自作者和读者。每一种声音之中,都可能包含转述语,也可能被转述,这样就使整个叙述成为一个转述语大集合。 叙述中的主体冲突都是叙述框架内部的冲突 叙述者确实是变化多端的,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可以附身于叙述中的任何一个组件,可以自由地引用任何组件的声音。我们既可以把叙述中的任何话语都视为这个千变叙述者的话语,又可以把任何话语都视为这个千变叙述者对各组件话语的直接引用,或者说各组件本就是叙述者的一部分。为了整一性,我们常用第一个视角,为了区分性,我们可以采用第二个视角。 在话剧、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中,叙述声音总是来自人物,人物分裂出一个叙述功能,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也属此类。在这类体裁中,所有话语都应视为“直接引语”型转述语,那叙述语又在哪里?如果把舞台呈现看作叙述语,那么广播剧的叙述语又在哪里?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任何叙述中,人物本身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叙述功能,任何转述语,其中已经内含了一个叙述语功能。任何人物的话语都反向叙述了发出该话语的人物,所以人物本就是叙述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的文体中,叙述者的声音源头可以被明显地安排在人物那里。只要我在生活、在行动,我就在叙述我自己。 在图片、雕塑等影像叙述中,从文本中找不到任何叙述声音源头,情节依靠读者“二次叙述化”重构。这时,叙述者的声音源头就在读者那里。读者也是叙述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特殊的叙述文本必须依靠读者才能完成叙述过程,这种情况在现代文字叙述中也越来越多,例如于坚的长诗《○档案》,叙述语基本上要靠读者重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者的记忆可以被‘唤起’,记忆容量可以扩充”(24),读者可以感觉到来自自己的记忆中的声音。 叙述声音也可以来自文本本身,而不需要来自文本外的任何组件,这个类型的典型代表是元小说中的故事。元小说详细叙述一个故事的写作过程,可以在文本中展示另一个文本的构思过程,所以声音就来自文本本身。鬼子的短篇小说《卖女孩的小火柴》中,写了吴三得构思写作《卖女孩的小火柴》的“构思备忘”,描述这个题目下故事的多个构思可能,读者不能通过二次叙述还原一个情节,作者也没有写出一个故事,但是鬼子的小说之中又包含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可能情节。如果非要说该故事有一个声音源头的话,那么这个源头只能存在于文本之中。这就说明,文本本身也是叙述框架的一部分,声音源头可以只在文本。又如占卜,如果占卜者是无神论者,那么声音源头就只能存在于占卜文本之中。 当我们面对一个异国文化展的时候,很容易感觉到文化参与叙述,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体系在向我们讲述存在于该文化之中的各种物品和人物。当我们阅读一本外文原著小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当一个不同于我们所在的文化体系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文化本身的叙述功能就得到了突出,我们会感觉到一个抽象的文化的声音在向我们传达意义,讲述这个文化及其中人物、物品的特点。胡壮麟认为,“意义是从‘符号资源’中根据所要体现的功能进行选择和被表达的”,“在创作多模态小品时,作者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模态,或两种,或三种,或更多”(25),“符号资源”就是文化体系,作者虽然有选择权,但是“选择”并不以“声音”的形式体现,声音存在于文化之中。 就是说,在一个叙述中,我们除了听到作者的声音之外,还能够同时听到其他组件的声音。有时某一个组件的声音比较突出,淹没了其他部分的声音,有时各个声音势均力敌从而让我们不知声音来自哪里。所谓转述语,就是人物声音源头得到突出而其余声音源头被弱化或退在幕后的叙述话语。直接引语式转述语是人物声音源最突出的,间接自由式转述语是最弱化的,直接自由式和间接引语式介于二者之间。由此观之,所谓的叙述中的主体冲突,就不是仅存在于叙述者和人物之间,而是存在于构成叙述者的各组件之间。存在于转述语中的主体冲突,只是叙述主体冲突的一小部分。 叙述中的作者(或隐含作者)可能与读者(或隐含读者)冲突,例如德国诗人奈莉·萨克斯的诗歌《你们这些旁观者》:“你们这些旁观者,你们虽然没有亲手杀人,可是你们却不能将你们欲念的尘埃抖掉。”(26)作者显然不完全同意读者或隐含读者的人格和行为。而在反讽式叙述中,读者的判断总是与叙述文本相悖,所以反讽就是制造文本、读者冲突的修辞。作者与文本冲突的情况常见于低调陈述、夸张、委婉语等修辞格中。低调陈述把严重的事件作轻描淡写的叙述,读者可以感觉到叙述者的作者部分对此事件十分重视,但是文本部分却极其不重视。夸张与此相反,作者本来不重视,文本却相当重视。委婉语则是作者的意向性意义与文本意义已经隐含不一致,但是该不一致并不是仅仅由读者判断出来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作者已经与文本产生冲突,叙述者的两个组件已经暴露。黑色幽默在文本层面有一个幽默的叙述者,而在作者层面却有一个悲剧的叙述者,二者的声音强度基本一致,从而产生“双声叙述”的效果。 人物与作者的冲突也是很常见的主体冲突。描写一个反面人物的心理活动,作者并不同意他的想法,但是人物的想法又看似合情合理。《孔乙己》的后半部分,作为人物的“我”在孔乙己腿被打折之后仍然冷漠地叙述,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并不赞同“我”的这种态度,而作者对孔乙己的态度已由嘲讽转变为同情。人物与读者的冲突常发生在具有反讽性的人物身上。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常自称“流氓”、“痞子”,但是读者却老是在他们身上找到闪光点。伊沙的诗歌《饿死诗人》最后几句:“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我”是叙述框架中的人物部分,他对自己及所属的诗人群体进行了彻底否定,但是读者却不会真如他那样否定他,反而会自动为他辩护。 作者与文化的冲突常见于“戏仿”、“恶搞”之中。作者使用一个体裁叙述,但他并不赞同这个体裁;使用一种说话方式,并赞同这种说话方式等等。鲁迅《野草》中的《我的失恋》副标题是“拟古的新打油诗”,作者不同意的,正是“拟古”的诗或“新打油诗”这种文体,也不同意在这种文体之中的文化心态。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称讽刺的是“当时盛行的失恋诗”(27),韩石山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首诗是讽刺徐志摩的”(28)。而读者在听到作者声音的同时也听到了体裁和文化的声音,而这二者是互相矛盾的。又如台湾网络上曾经有一个很轰动的恶搞小说《铁拳无敌孙中山》(29),历史和文化的声音还在,然而却被作者进行了“恶搞”。刘志强的《笑时代》,就像个当代流行文化大杂烩,文化声音很突出,作者的声音也很突出。文化与读者的冲突常存在于具有文化革命性的作品中。作品中存在一个全新的文化思想,而假定读者不会同意这个思想,因此常给具有该思想的人设置一个“疯子”或“天才”的身份。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有一个在礼教中看出吃人本质的思想,然而假定读者并不能看出这一点,所以通过“狂人”发言。高铭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也有这样一个假定,若假定读者都同意“疯子”们的奇思妙想,那其中的思想和文化就成了常识,也就不需要给有该思想的人一个“天才”和“疯子”的身份。 在上一节列举的五种类型中,设问句和反问中同时显现了作者与读者的声音;格言警句同时显现了作者与文化的声音;常识叙述中同时显现了各种声音;以“本文”自称的叙述中同时显现了文本和作者的声音;主体冲突过强的转述语同时显现了(隐含)作者和人物的声音。除此之外,各组件还可能自我冲突,形成悖论。事实上,上述各类都是某种叙述修辞。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所有冲突类型进行全列举。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处于叙述框架内的各部分均可以发出声音,而任意两个声音之间都有可能发生冲突从而造成叙述者内部观念的不一致并达到特殊的表达效果。制造叙述者的内部冲突,正是叙述修辞的重要着手点。这在电影修辞中十分明显,例如黑色电影,“严格意义上的黑色片或当代黑色片里最令人激动的东西恰恰都是‘杂交’的,而且以一种隐约的焦虑不安渗透于布景、风景、人物、甚至最为熟悉的故事之中”(30)。“杂交”的目的往往就是制造冲突,这正是电影修辞的重要手段。在文字类叙述中,制造各种不同叙述组件的声音冲突正是现代小说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可以视为对叙述者冲突的早期探索,他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是“多声部性”、“全面对话”性的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31)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小说结构的各个要素:“小说结构的所有要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均有其深刻的独特之处……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32)虽然巴赫金讨论的重点是作者声音和人物声音之间的冲突,但仍然给叙述者的主体构成分析以强烈的启示意义。申丹发现,“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进程,一是情节发展,另一个则是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流”(33)。这个所谓的“叙事暗流”,同样可以理解为被淹没在显在声音中的声音暗流,其声音源头仍然来自框架中的某一个部分。叙述声音源头的分析必须首先依赖对叙述者构成的本质分析,赵毅衡发现所有的叙述者都表现为“框架-人格”二象(34),将对叙述者的本质形态的认识继续向前推进。由于叙述者由多个部分构成,所以具有框架特征,由于组成框架的各部分可能是人物、作者、读者,当这些人格化部分发出声音时,他又可能具有人格化特征。 对叙述者认识的深化推动了叙述学的发展,许多悬而未决的叙述修辞问题在构成叙述者的成分清晰化之后也将逐渐清晰化。所谓叙述修辞,很大部分都是在叙述的声音源头上有意制造矛盾冲突而形成的特殊表达效果,其总体倾向是造成叙述解释意义的不确定性。由于叙述者不再被视为一个单一的人格,许多曾经模棱两可的说法和暧昧不明的修辞定义都可以纳入这个框架进行更为清晰的描述。 注释: ①[俄]米哈依·洛特曼:《主体世界与符号域》,《符号与传媒》(春季号)2013年第6期。 ②王俊花:《〈声无哀乐论〉与皮尔斯现象学》,《符号与传媒》(春季号)2015年第10期。 ③谭光辉:《作为框架的叙述者和受述者》,《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④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6页。 ⑤[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82页。 ⑦⑧[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0页。 ⑨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⑩[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金元浦、周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11)[德]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2)王彬:《小说文本的解放——简论叙述语与转述语合流》,载鲁迅文学院培训中心编《文学之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13)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9页。 (14)[法]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王寿昌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15)(21)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18、222页。 (16)(17)(18)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55、155页。 (19)卢惠惠:《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20)乔治·桑:《冬天之美》,载冯至《世界散文精华》(欧洲卷,上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20页。 (22)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页。 (23)申丹:《再谈中西小说叙述中转述语的不同特点》,载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24)彭佳:《另一种文本中心:论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符号与传媒》2011年第3期。 (25)胡壮麟:《谈多模态小品中的主体模态》,《符号与传媒》2011年第2期。 (26)[德]奈莉·萨克斯:《你们这些旁观者》,孙凤城译,载孙凤城《欧美女子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27)卫俊秀:《卫俊秀学术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28)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全新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29)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30)[法]让-卢普·布盖:《好莱坞:欧洲电影人之梦》,严敏、朱震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31)(32)[苏]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30页。 (33)申丹:《“隐性进程”与界面研究:挑战和机遇》,《外国语文》2013年第5期。 (34)赵毅衡:《叙述者的广义形态:框架——人格二象》,《文艺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