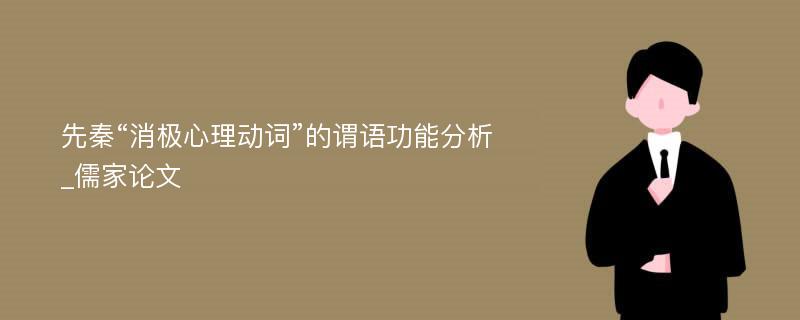
先秦“负面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析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动词论文,负面论文,功能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表示情绪、态度、思虑、计议等带有隐性意味的行为活动的动词群体中,有些词表示的是哀悯、忧虑、憎恨、害怕等方面的心理活动,如:哀、怜、恤、恶(wù)、憎、畏、 惧等词所反映的都是造成人们心理负担的一种负面心理活动。根据它们的共同的语义特点,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负面心理动词”。本文以《尚书》、《诗经》、《论语》、《左传》、《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面文献资料为对象,以词项为单位,就较为习见的20多个负面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及其特点进行了考察。
一 负面心理动词与宾语
先秦负面心理动词能带单宾语,不能带双宾语,但就其能带什么样的宾语而言,内部成员是不匀质的。据此,可以将其分为若干小系,即:
1.“怜”系:包括怜、哀、悲、矜、恤、吊、闵;
2.“怨”系:包括怨、怒、妒、忌、尤;
3.“厌”系:包括厌、恶、憎、疾;
4.“忧”系:包括忧、患、恤、病、疾;
5.“惧”系:包括惧、惮、畏、恐。
以上五个小系共计25个词,1769例(穷尽式)。下面就各系带宾语的情况分别作些讨论。
1.“怜”系 本系都可带受事宾语。如:
(1)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 (《庄子·秋水》)
(2)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诗·周颂·闵予小子》)
(3)哀我填寡,宜岸宜狱。(《诗·小雅·小宛》)
(4)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 曰:“恤病,讨贰。”(《左传·宣12》)
(5)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诗·小雅·巷伯》)
(6)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 其后而日远矣。(《庄子·徐无鬼》)
“怜”系诸词在谓语位置上共出现130次,无宾69例,有宾61例。 所带宾语的结构形式主要是体词性的(含名词、名词词组和代词,后同)。另外,“矜”宾有1例为谓词性的(含动、形、动词词组、 形容词词组,后同):夏,归粟于蔡,以周亟,矜无资(《左传·定5》); “悲”宾有1例为复句形式: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 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韩非子·和氏》),均系个例。
2.“怨”系 “愠”不带任何宾语,其余都可带受事宾语。如:
(1)不惩其心,覆怨其正。(《诗·小雅·节南山》)
(2)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 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荀子·臣道》)
(3)主苟忌胜,群臣莫谏必逢灾。(《荀子·成相》)
(4)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 (《左传·襄21》)
(5)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
“怨”系诸词在谓语位置上共出现374次,无宾258例,有宾116 例。所带宾语,体词性的108例,主谓词组(含“主之谓”词组,后同)6例,谓词性的2例。
3.“厌”系 本系都可带受事宾语,如:
(1)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
(2)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墨子·亲士》)
(3)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 (《荀子·荣辱》)
(4)子产憎其为人也,且以为不顺,弗许,亦弗止。 (《左传·昭19》)
(5)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厌”系诸词在谓语位置上共出现311次,无宾20例,有宾291例。所带宾语,体词性的189例,谓词性的76例,主谓词组26例。 “疾”宾范围最广,涵盖了体词性的、谓词性的和主谓词组等。
4.“忧”系 本系都可带受事宾语。如:
(1)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忧财用之不足哉? (《墨子·节葬下》)
(2)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 广莫之野……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
(3)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 (《左传·襄16》)
(4)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
(5)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 如此则可谓贤人矣。(《荀子·哀公》)
(6)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左传·昭4》)
“忧”系诸词在谓语位置上共出现311次,无宾95例,有宾216例。所带宾语,体词性的150例,谓词性的37例,主谓词组23例, “介·宾”词组4例,复句形式2例。与“厌”系相比,最突出的是宾语中有“介·宾”词组和复句形式。
5.“惧”系 本系可带受事宾语。如:
(1)敝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惧谗慝之间谋之,以启贪人, 荐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忧。(《左传·昭18》)
(2)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韩非子·南面》)
(3)无虐茕独而畏高明。(《尚书·洪范》)
(4)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尚书·盘庚中》)
(5)今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梁惠王下》)
“惧”系诸词在谓语位置上共出现643次,无宾207例,有宾436 例。所带宾语包括体词性的、谓词性的、主谓词组、“介·宾”词组和复句形式等。与“厌”系、“忧”系相比,谓词性宾语、主谓词组宾语和复句形式宾语的数量均明显增多。
现将各系谓宾情况综合列表如下表:表1
系
词出现数及其所带宾语的结构形式
词出现数宾语
别 总数 无宾 有宾 体词 谓词 主谓词组 介·宾 复句
130696159 1
0 0 1
374
258
116
108 2
6 0 0
31120
291
18976 260 0
31195
216
15037 234 2
643
207
436
174157 834 18
表中体词指含名词、名词词组、者字词组、代词;谓词指含动词、形容词、动词词组、形容词词组;主谓词组指含“主之谓”词组。宾语的结构形式,从左到右表现为由简单到复杂的线形序列,“负面心理动词”与它们组合为谓宾关系的或然性,其涵盖面大小的顺序是:“怜”系<“怨”系<“厌”系<“忧”系<“惧”系(<小于号),一系比一系加大,左右两端之间的反差尤为突出。这种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原因,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的轻重不同,可能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内容的宾语在组合上存在选择性特点,“负动”受事宾语的内容包括人、物、事三个方面,体词性宾语表示的主要是人和物(“之”有时表示事物),其余几种结构形式的宾语表示的都是事。请看例子:
(1)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尚书·多士》)
(2)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尚书·汤誓》)
(3)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孟子·尽心上》)
(4)知命者不怨天。(《荀子·荣辱》)
(5)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货资有馀者, 是之谓盗竽矣。(《韩非子·解老》)
(6)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左传·襄28》)
(7)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庄子·庚桑楚》)
(8)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墨子·兼爱上》)
(9)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
(10)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诗·郑风·将仲子》)
(11)谚有之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左传·僖7》)
(12)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荀子·非十二子》)
(13)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论语·季氏》)
(14)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左传·襄21》)
例(1)(2)(3)为体词性宾词,表示的是人;例(4)(5)(6)为体词性宾语,表示的是物;例(7)(8)为谓词性宾语,例(9 )(10)为主谓词组作宾语,例(11)(12)为“介·宾”词组作宾语,例(13)(14)为复句形式作宾语,它们所表示的内容都是事。现以“怜”系和“惧”系为例,将其宾语内容列表如下:表2
系词宾宾语所示
语
别目数 人 物 事
怜 5 0
5
0
矜 7 7
0
0
恤11 9
2
0
怜吊 3 3
0
0
哀27 25
0
2
悲 6 3
0
3
系闵 2 2
0
0
总计
61 49
7
5
惧
114 14
3 97
惧惮34 1
2 31
畏
157 52 28 77
恐
131 3
2 126
系
总计 436 70 35 331
从表中可以看到,“怜”系宾语具有单一性特点,主要局限于人;“惧”系宾语,既有表示人和物的,更有大量表示事的,其述谓功能远高于“怜”系。回头再看表1所展示的数据,关于各系“负动”对5种结构形式的宾语在组合中存在差异的内在制约因素之谜,便可得到合理解释了。
二 负面心理动词与状语
“负面心理动词”作谓语可以带状语,出现的例句总数是426。 下面是各词所带状语组成情况的综合统计(材料来源同宾语统计表所列文献):
怜:可[,1]
矜:不[,1]、宁不[,1]、敢不[,1]
恤:不[,3]、其[,1]、未[,1]
吊:不[,1]、亦不足[,1]
哀:不[,13]、其[,1]、甚[,2]、可[,2]、可不[,1]
悲:不[,1]、又[,2]、莫[,1]、固最[,1]、不亦[,3]
闵:0
怨:不[,20]、亦[,1]、又[,4]、其[,2]、相[,1]、无[,2]、勿[,1]、能[,1]、敢[,1]、奚[,1]、必将[,1]、相与[,1]
怒:不[,8]、又[,1]、一[,4]、皆[,1]、必[,2]、大[,10]、惮[,1]、重[,1]、不可[,1]、怫然[,1]、悖然[,1]、未可以[,1]
愠:不[,1]
忌:0
妒:敢[,1]、相[,1]
尤:不[,2]
厌:不[,22]、既[,2]
恶:不[,9]、可[,2]、且[,1]、亦[,3]、相[,1]、又[,8]、皆[,1]、甚[,2]、无[,1]、始[,2]、真[,1]、敢[,1]、能[,1]
憎:且[,1]、甚[,1]、相[,2]、复[,2]、佯[,2]、不佯[,1]、不可复[,1]、不可以佯[,1]
疾:0
忧:不[,11]、可[,2]、必[,2]、亦[,3]、无[,1]、勿[,3]、其[,1]、姑[,1]、甚[,1]、久[,1]、足[,1]、何[,2]、不足[,1]、将欲[,1]、犹足以[,1]、为天下[,1]
患:不[,7]、无[,1]、亦[,1]、又[,3]、皆[,1]、最[,2]、何[,7]、奚[,2]、亦不[,1]、犹足以[,1]
恤:不[,12]、必[,1]、重[,1]、无[,1]、同[,3]、遑[,1]、能[,1]、不能[,1]、未能[,1]
疾:不[,8]、其[,1]
病:不[,5]、未[,1]、方[,1]、甚[,2]、何[,2]、其犹[,1]
惧:不[,15]、可[,1]、必[,2]、犹[,7]、将[,1]、又[,1]、无[,1]、始[,1]、其[,2]、益[,1]、相[,1]、亦[,1]、唯[,1]、大[,2 ]、敢不[,1]
惮:不[,9]、犹[,2]、其[,1]、敢[,3]、不敢[,1]
畏:不[,20]、可[,4]、必[,1]、无[,1]、固[,1]、犹[,1]、其[,2]、皆[,1]、甚[,1]、足[,3]、相[,2]、何[,2]、必可[,1]、亦可[,1]、不可[,2]、不能[,1]、敢不[,1]、胡不[,3]、惨惨[,1]
恐:不[,6]、且[,2]、必[,1]、又[,2]、将[,3]、犹[,2]、尚[,1]、甚[,1]、咸[,1]、常[,1]、皆[,1]、唯[,17]、大[,4]
从表中可以看出:1)能带表示状态、程度、方式、范围、时间、 愿望、肯定、否定的状语,没有表示处所、工具、方向、目的、原因等方面的状语,也没有任何句首状语(如“是岁也,晋又饥”、“难故也,是以缓”的“是岁”、“难故也”);2 )状语中既有多种副词和助动词,也有非同类词的连用形式,如不敢、不能、敢不、亦不、胡不、必将、将欲、其犹、不可以、犹足以、未可以、不可复、不可以佯等,反映出所带状语的丰富多样;3 )“介·宾”词组作状语为先秦汉语所习见,且有极强的表现力。而“负面心理动词”的状语成员中却只见到“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荀子·富国》)1例, 与带状语例句总数之比为426∶1,与零无异。因此,可以认为,先秦时代的“介·宾”词组与“负面心理动词”在状动关系上不是一种合宜状态。
三、负面心理动词与补语
先看例子:
(1)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下》)
(2)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 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荀子·非十二子》)
(3)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 (《左传·昭13》)
(4)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诗·小雅·雨无正》)
(5)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
(6)及文子卒,卫侯始恶于公叔戍,以其富也。 (《左传·定13》)
以上例中带“·”的 6个句子,表层结构同形,似乎都是动补关系,实际上后3例不是动补关系而是动宾关系,例(4)的意思是“为什么不互相畏惧?是因为不(知)畏惧天命”,例(5 )的意思是“你们何必担心丢失(官职)呢?”例(6)的意思是“等到文子死了, 卫侯开始讨厌公叔戍,因为他富有。”这种同形异构的深层语法关系,很容易与动补相混,必须结合文意,细加审视。其他如: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左传·庄21》)谚有之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左传·僖7 》)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左传·僖28》)君无秽德,方国将至,何患于慧?(《左传·昭26》)二三子间干忧虞,则生疾疢,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左传·哀5》)。句中“于”的有无, 并不影响句子的动宾关系,有时用上它,可能是出于对宾语的强调和句子节律上的要求。为划一起见,本文将其视为“介·宾”词组作宾语,因为非“负面心理动词”谓语句也有同样的情况,如: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曰:“又何如?”臣对曰:“好以暇。”(《左传·成16》)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左传·襄13》)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左传·哀11》)
根据结构形式与语义关系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察析,在“负面心理动词”作谓语的1769个例句中,只有9个带补语的句子,仅占总例句的0.5%。它们是:
(1)丙怒甚,不肯来。(《韩非子·内储说上》)
(2)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论语·公冶长》)
(3)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诗·邶风·柏舟》)
(4)赵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左传·宣12》)
(5)郑人惧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 (《左传·成2》)
(6)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左传·庄19》)
(7)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韩非子·八奸》)
(8)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 (《韩非子·忠孝》)
(9)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左传·襄14》)
句中状语的作用,分别表示程度、条件、凭藉、比况等。
“主状动(宾)补”同现,是上古汉语陈述句中最为完备的结构形式,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尚书·牧誓》)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同上)。襄仲使告于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左传·文14》)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左传·襄12》)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违于淖。(《左传·成16》)这种结构能够同时展现与动作行为相关的对象、事物、条件、凭藉、方式和时空,表现了动词谓语句最为丰满的功能形态。“负面心理动词”虽主要出现于陈述句,却普遍缺乏补语这一组合部件,且在其状语组成成员中,“介·宾”词组呈个例状况,说明彼此间处于一种枘凿状态。因此,先秦“负面心理动词”所能体现的述谓功能形态应该说不是最为丰满的。
四 负面心理动词与语气和句式
“负动”在语气和句式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一)一无例外地大量出现于陈述句。“忧”、“惧”等少数几个词有时也可出现于疑问句,如: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左传·隐1》)齐侯曰:“鲁人恐乎?”(《左传·僖26》)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诗·小雅·雨无正》)何许子之不惮烦?(《孟子·滕文公上》),但涉及的词和句子数量都极少。
(二)同祈使句无缘。能生成感叹句的只有“哀”、“悲”、“畏”三个词,如: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诗·大雅·召旻》)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庄子·列御寇》)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12》)据此不难看出,“负面心理动词”对句子语气环境的适应力带有明显的封闭性。
(三)可以组成“(主)+宾+是/之+负动”的特殊句式。
“负动”陈述句,除了有“(主)+负动+宾”的一般句式之外,还有一种特殊句式:(主)+宾+是/之+负动。如:
(1)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 (《左传·僖15》)
(2)不然,其何劳之敢惮?(《左传·襄28》)
(3)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左传·文7》)
(4)小国失持,而惩诸侯,使莫不憾者,距违君命, 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左传·昭31》)
(5)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左传·昭1》)
(6)寡君其罪之恐,敢与知鲁国之难?(《左传·昭31》)
(7)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 用(丧)阙师。(《墨子·非命中》)
通过助词“之”或“是”的作用将宾语提前,目的在于加重语气,突出宾语。增加助词变更动宾词序,是先秦汉语句法特征之一,《左传》尤为常见。这种特殊句式涉及的动词,范围很广,自然不限于“负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所调查的9部文献中, 却只见到一个带有“正面心理动词”的例子:“非子之求,而蒲之爱”(《左传·宣12》)原因何在?个人的初步看法是:句中的“非子之求”和“而蒲之爱”都是倒装句,彼此两两相对,虚实交映,整齐和谐,极具表现力。如果是“非子之求,而爱蒲也”,意思尽管没有变,句子却显得松散无力,气韵全无,这正是古汉语组词造句的大忌。很可能,“正面心理动词”在先秦时期压根儿就不适宜于这种特殊句式,只是由于特定语用环境的修辞制约作用才使之发生了临时性变化。换句话说,“蒲之爱”的出现,是前一分句“子之求”直接影响的结果。
从前面的分析和各项结论中,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负面心理动词”作谓语反映出的种种功能形态,说明语义上的不同聚合类别,不论在组合关系上或语气、句式方面,总是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同一语义类聚的语词之间最深刻的一致性,既反映在它们所指称的概念的类别上,更表现在它们进入句子后的表达功能上。因为任何一个词或语义类聚,只有在动态的句子中(而不是在静态的词汇库中)才能全面凸现其固有的功能形态。充分重视词的语义与语法的内在关系,着力揭示各大类聚合中不同小类的语法功能及其对句子结构的制约,应该是深入探讨汉语固有特点的一条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