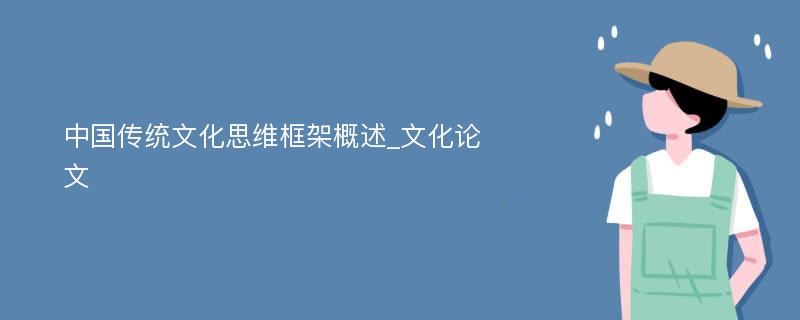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框架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框架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33(2003)03-0036-09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无论在哪个向度、哪个层面上,都呈现出鲜明 的个性色彩。我们认为,最终决定这种个性的,是民族特定的思维空间、思维旨趣以及 思维方式所构成的思维框架。这个框架整合了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性。历史上不同思想 团体、流派,尽管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可能势同水火,但在思想的根基处却是一致的,正 是这个共同的框架构成了他们争论和对话的基础。同时,这个框架也构成了民族文化的 内在局限性:它运作于天人之际,镶嵌于心灵深处,成为思想着的个体无以逃避的宿命 。
关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已多有研究。如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其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中,讨论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预设”[1](P17 8);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对此有所涉及[2];今人 葛兆光先生于此尤为用心[3](第1卷)。总地看来,以往专家们的论述一般是就事论事, 点到为止。至于详细地勾勒出这个框架的要素与结构,在此基础上把传统文化中纲纽性 的观念与价值范畴连结起来,使之形成一个脉络分明的系统,以凸现出中华文明的内在 统一性,这是本文所要进行的尝试。下面通过对大一统宇宙自然图式的展开,揭示中国 传统文化思维框架的要素、结构与机制,以求有助于世人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次整体性理 解。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本来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是对王者一统万物 的地位与权力的强调。但它实际上凸显了先在于民族心灵中的宇宙自然图式。《春秋》 破空而来第一句即“元年春,王正月”。公羊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 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为先言王尔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 一统也”。何休释“元”曰:“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 始也”;释春曰:“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4](P6 -7)。可见,“元”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第46章)的“一”, 是功能态的道;《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所言王者“布政于邦国都鄙”的春之始 正月,则是人类事件进入自然之永恒的端口。在这里,通过一个时间序列(正月、春、 元)的回溯,将人类与他的自然根源(元)连结到了一起。于是,历史归于永恒,时间本 身陷入了自然物象的轮回里。因而,“大一统”描述的是一个以天道与人王为中心的、 尽善尽美、无所不包、天人合一的宇宙、政治图式,它包含了时间、空间、人伦三个纬 度,形成一个向心式的球形系统。
这个系统图式由以下要件构成:天圆地方的向心式场态空间结构;神圣的价值和权力 中心——道本源;阴阳化生机制;作为过程的、循环论的时间观;有机的、系统论的普 遍联系;天、人同构,道、德一体的价值设定等等。在这个框架内,中华民族建立起了 宇宙的秩序、文明的基础和人生的意义。
一、天圆地方的向心式场态空间结构
人类通过对结构的理解为人生赋予意义。中国人对宇宙结构的理解体现在其独特的空 间观里。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角度,空间观是构成一个民族之“世界 模型”的基本要素,它反映着宇宙人生的内在关系方式,在横向度上塑造着文明的最高 庄严性。
传统的空间观可以分解为两个要素:天圆地方的结构形式与呈现为气场效应的功能与 机制。
(一)天圆地方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古鲜卑族民歌中这句歌词就是这种观念的生动描述。但是 ,这个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是如此巨大,如此持久,却是在其它文 化中罕见的。
“天圆地方”内容包括:天是半球型的,有一个中心,即北天极;大地是一个正方形 的平面,中国处于大地的中心,中国之外有四夷,四夷之外有四海。中国的中心在夏故 都阳城,是大地的绝对中心;天和地在远方相连接。
因而汉语中有四海、四表、四方、五方(加上中央)、四隅、八方、八极、六合等词、 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
《尚书·尧典》里即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1987年发掘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韵 文化遗址中的第45号墓,墓穴头部作圆弧形,底部作方形[5]。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当时 已有“天圆地方”观念。作为一个封闭的区域,圆与方都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的唯一 性使它成了能量的聚集点,信息的发散处,因而它本身即是一种价值确认。这个神圣的 中心,呈现了秩序的最高庄严性:支配一切的“道”由这里生发,专制帝王那俯瞰万象 的黄金宝座也在这里建立。如《尚书·尧典》载尧帝命羲仲宅东方旸谷,羲叔宅南方 明都,和仲宅西方昧谷,和叔宅北方幽都,以观测天象,校订历法,已经暗含了“居中 央而驭四方”的意思;甲骨卜辞有商王祭四方风的记载,说明“大邑商”是自居于世界 之中的。
关于寻求天地之“中”的最早历史记载可上溯到周朝。《周礼·地官·大司徒》谈到 大司徒的执掌,有一项就是“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作为权力合法 性的象征,地中的确立象创世一样是人间秩序的重建,历史新纪元的开始。
“圆”与“中”一样,成为一种预设性价值。传统文化表现了对“圆”的热衷与偏好 :在描述事物动力机制的阴阳结构中,阴阳两种因素构成一个相互缠绕的太极图;两种 主要的认识模式——周易模式和五行模式——都是在圆与圆的相交、相切、相统摄中确 认和规定事物性质的。如在周易模式中,六十四卦构成一个圆、十二消息卦构成一个圆 、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各构成一个圆、本卦和变卦构成一个圆、每一对对卦和反卦构成 一个圆、每卦自身也构成一个圆;在五行模式中,五行相生构成一个圆、相克构成一个 圆、相邻四位(如水、木、火、土,或木、火、土、金等)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圆、相邻 三位(如水、木、火,或木、火、土等)也构成一个自足自在的圆。其中对立因素之间的 矛盾斗争采取的不是直线式的机械反弹,而是走曲线,即“克其所生者”,如“水”克 “火”,“火”对“水”的反制是克生“水”之“金”。中国人喜欢走曲线,太极拳中 没有一个动作是直来直去的。所谓“首鼠两端”即“左右逢源”;“扣其两端取其中” 的中庸之道亦即行圆之术。
“天圆地方”作为对立统一的一种阴阳形式,被抽象为一种深具中国特色的原理和策 略:圆动而神,方智而静;一为神明变化,一为方正严肃,两者相形相补,相生相成。 不论君主治国理民,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应力求“方”与“圆”的辩证统一。
(二)气场效应
“天圆地方”、“上下四方”构成的不是一个纯物理空间,而是一个价值空间,这是 一个天人合一的有机系统,是生命意志表达自己的旋转舞台:它有一个神圣中心,从中 心向外辐射,距离越远价值越低;它具有德性的意志和力量:东方为春,主生;南方为 夏,主养;西方为秋,主杀;北方为冬,主藏。在此基础上,再“以类行杂”[8](《
王制》),与五行、五气、五德、五声等结合起来,人类生存的整个空间便成了一个天 人同体、万类同构、有节有序、有情有义的神圣世界。空间不仅内涵了时间,而且渗透 了人伦价值。所以,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空间,不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心目中那种充满了 各自独立事物的“大盒子”,而是一个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气场,其中不存在一个超然 独立自我持存的局部的可能性,因为环境渗入了每个存在的本质之中。环境表现为时空 交织中生命能量的聚散运行。任何局部都是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接受环境的特征并把 自己的特征投射于环境。
在中医理论中,草药的采集不仅与地点有关,而且与时辰也有关。地点不同,时辰不 同,作用于人的疗效就不同;人体的穴位也是这样,不同的时辰有不同的敏感点。根于 阴阳五行观念的太乙、六壬,奇门遁甲及八字等数术,把时间因素与空间因素交结在一 起,构成各种瞬息万变的场效应。风水术是场效应的更典型的例子:每个局部构成一个 相对独立的能量场,而任何一个要素的加入都会改变整个能量场的结构和活力。总之, 这种泛场效应、时空共振观念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观念之一,渗透了人类生活的各个层 面,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方式。
二、神圣的生命与价值中心——道本源
春秋以后,“中”被向上提升抽象为宇宙的本体——众所周知,老子的“道”实际上 是“中”的直接抽象化:“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6](第6 章)。王弼释谷神曰:“谷神,谷中央无谷也。无形、无影,无逆、无违;处卑不动, 守静不衰”[7](P141)。其实,“谷”就是由人之“中”——子宫——拟象类推出来的 天地之子宫,谷神即玄牝即宇宙自然的化生之力,亦即“道”。这是对万物本源的解释 ,是中华智慧的最高体现,是整个民族共同遵循的最基本思维“预设”。如果说,印度 文化提供了一种精神力量,使人类能够从正面突破存在的局限性;希腊哲人提供了一系 列智慧工具,使人类得以从表面进入事物的本质;中华文明则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内, 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体悟宇宙人生的坐标原点。这个原点就是“道”。
道是宇宙的动力因,由于道的创化之力,大宇宙才生生不息,美景常新。事物的意义 体现在其唯一性的过程之中。因而,“天地之大德曰生”[9](《系辞下》),长养生息 是宇宙自然最大的德性。——在宋儒那里,天地之仁即其生生之心。因而,“生”成为 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价值范畴。中华民族表现出了强烈的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执著。道 是世界的根源,是万物的凭借。因而,道即是世界的统一性:它聚则为天地之根,散则 为万物之精,形成一个统摄一切的中央机制,从中心向外层层推衍,在推衍的过程中, 万物显现出来,并天然地形成合理的秩序。因而,道是宇宙价值的最终也是最高依据。
道在人间的统一性落实于圣人。《说文解字》释圣:“圣者,通也”。圣人无所不通 ,他掌握着天地之道的秘密,并以自身对道的践行照耀着世界。故《易·文言》云:“ 圣人作而万物睹”;《礼记·中庸》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圣人继天理物,参 赞化育:“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10](《道基》)。因而,“圣人便是天, 天便是圣人”[11](卷68)。又因为王即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替天行道,抚养 小民,天子便成了当然的圣人,成了道的化身。因而,最终坐实于大一统之核心,作为 万物之决定者的,是人间的王。道是他的无极大法,圣人不过是他放大了的道德影像。
三、阴阳化生机制
这是对宇宙事物的结构、功能及运动机制的理解。各个思想流派都认为万物是由阴阳 二气所构成、所化育的。阴阳的结构功能生成了世界的秩序,并随时突破这种秩序,推 动着事物的发展。同道一样,阴阳二气及其表现为对立统一的作用机制也是中国人思维 中不证自明的前提。
阴与阳的对立统一,首先是一种动力机制。任何事物都内含着阴阳两种因素,构成事 物的两极,两者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互缠绕,相互包融,处在动态的转化过程之中 ,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因而,善恶吉凶、泰否强弱,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是事物运 动不同状态、不同侧面的反映。
也是一种结构、功能原理。阴与阳对立统一有轻重主次之分:阳为主,阴为次;统一 为主,对立为次。阳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阴则自觉的顺从和归依于阳。在阴阳二气合 和化育的过程之中,动静以分,卑高以陈,万物各归其位。因而其中天然地含有一种秩 序观念:尊卑之别。——阴阳秩序具象地体现着其分类功能;在功能实现的过程中,天 然地生成了秩序。因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特别重“礼”:“夫礼,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也是一种认识原理。它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准二元论:无论在什么场所,中国人都 追求对称、对偶,追求“合”:天地、君臣、夫妇、父子、以及君尊臣卑、民重君轻等 ,都是这样的“对子”。中国人就是在事物的相互“对待”中认识事物的。
也是一种价值取向。由于阴阳的相互转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又是一个由量到质的渐 进过程,中国人养成了一种消极等待的处事态度:等待“瓜熟蒂落”,等待“物极必反 ”。
四、作为过程的、循环论的时间观
时间观反映着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韵律、节奏与方向,在纵向度上提供着社会的终极价 值。“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条件和限制因素必然反映在其语言和行为里”[12](P31)。 因此,要理解我们民族的时间观,应当从分析我们民族的语言以及生活、生产方式入手 ,去发现其中包含的时间感知、表达及度量方式。
(一)时间感知方式
我们民族对时间的感知主要是通过自然万物内在的生命节律实现的。无论是春草抽绿 、秋叶泛黄,还是鹰变禽化、蝉振蛰伏,种种细致微妙的变化震颤着人的感官,显示着 时间的流逝。
“时”首先是时节,时令的意思,是大自然的一种韵律和节奏。时间划分的基本单位 年、季、月、节、候、日、辰主要依据的是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自然物象的变化。春夏 秋冬四季的划分一开始依据的是花开花落等感觉经验;时节、时候等标时名词直接就包 含了物候形象;时律则表志着某一时间段内自然之旋律的“调值”的高低;“时令”则 直接把时间宣布为大自然意志的表达者。中国传统的节日如春节、清明、仲秋等,都是 与物候有关的。在振荡起伏的时间潮流里,一切都如雪泥鸿爪,转瞬之间就被抹去痕迹 。人们根本不能支配时间。因而汉语放弃了对时态的执着,而只是在需要时用“曾”、 “过”、“当”、“在”等符号临时性地把事件之流点开。
(二)时间表达及度量方式
传统中国人对时间的感知是纯经验型的。这种时间与现代人那种不可逆的、可等值等 量划分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以中性的坐标形式出现的。它实际上是支配万物的大 宇宙创生之力的演进过程,随着阴阳二气的推荡而往复循环,即所谓“一阳开泰,万象 更新”。因而,时间不是一去不复返的矢量,而是事物生死演化的周期,呈现为首尾相 接的圆环:大宇宙处在沧桑劫变的轮回里;任何事物都有盛有衰,有终有始,盛衰相依 ,终始相接。因而,诸如元、纪、世、代、甲子等都标志着一个圆周的结束与开始。四 季循环,往来相接,是这种时间观的最直观表达:四季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是宇宙生 命力的起伏涨落,是人类生活内容和场景的交替展开;万物如寒暑交替,浸淫在由生而 死,由死而生的循环里。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在合而分、分而合的演变过程中,最终皈 依于起始处:儒家的黄金时代和道家的纯朴之世。
(三)这种时间观的文化内涵
时间为人类事件赋予方向和意义。它以其最终支配性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庄严步调:在 古代中国社会,不论是农祭兵刑等军国大事,还是婚表嫁娶等世俗情节;不论是王者的 起居巡狩,还是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必须征询时间的意志。——寻找一个适宜的时间点 。
在对事件过程的把握中,国人最重视两个关键点:“始”和“终”。“始”包含着生 命的潜能,而“终”则是过程的必然结果。故做事必须力求“善始善终”。事之始必“ 微”,故君子求“知几”,重“防微”。另外,还注重对每一个动态的时间点——时机 的把握,因为时机意味着某种趋势,某种可能性。因而,“时”成为一个重要的价值概 念:不论做什么事,得其时则吉,非其时则凶。“天时”与“地利”、“人和”一起成 为争战取胜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这种时间观构造了中国人独特的历史观——一种 自然主义的有机历史观。这将在第七部分论及。
五、有机的、系统的普遍联系
因为任何事物都来于一个共同的根源,都呼应着共同的中央机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 只能是有机的、系统的。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方式,可以作如下概括:它们是圆形 相交相切而不是直线相推相荡的,是随机性的相感相召而不是决定性的此因彼果。故在 这里称之为“因缘观”。这是对万物之间普遍联系的理解,反映了一种文化对必然性、 偶然性等神秘力量的独特感受,以及在支配自己的命运的努力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精神的 诗意与崇高。
(一)任何个体都被规定在某种共同体的复杂关系里
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里,不存在原子式的实体,而只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任何事 物都有自己的生、相、克、制者,也同时作为生、相、克、制者在其它事物的运动里发 挥着作用;每一个个体都作为局部系统中的一个分子参与到更大系统的运作中。五行模 式即是这种关系方式的高度概括。作为阴阳模式的展开,五行模式同时从事物的内在动 力及外部联系两个方面解释了事物运动、演变及相互关联的途径、程序及方式。由此生 发出了中华传统一个十分珍贵的思想:一种宇宙全息观。如天干地支作为一种符号代码 ,被认为包含了某个特殊时空的整体信息。
(二)任何事物都处在一定的场所、位置(位)以及一定的过程之中(时),按照各自特有 的轨道发生、发展、演化着
《周易大传·系辞上》开宗明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践位矣。动 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事物在不同的“位”、不同的“时”会呈现出不同的功能状态,因而对“位” 和“时”的把握就成了认识和改造事物的关键。中国人由此发展起了一种居安思危的忧 患意识和一套异常精致的处世智慧:不论治国理民、用兵布阵,还是人际间的权术操作 ,无不刻求得其时而处其位,以便进退有据,往来从容。
(三)任何事物都是一个阴阳结构,这个结构是不平衡的,或者侧重于阴,或者侧重于 阳,这使该事物内涵了一种与他物相互感应、相互激发的“冲动”
如果两物是异质的,则表现为“和”,《国语·郑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产。”若是同质的,则表现为相应相感,《周易大 传·乾》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因而,古 人发明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认识事物的万用妙诀,即《荀子·王制》所谓“以类行 杂,以一知万”,通过比附类推去认识事物。这种方法一开始有其合理性,后来不计边 界地一味类推(特别是在各种方技术数中),结果把精神领域搞了个乌烟瘴气。
(四)物群之间以两圆相交相切的方式发生联系,不同的交切点会有不同的情况
这一点特别典型地体现在中医理论精髓“辨症施治”上:在脏腑和经络学说等整体观 念指导下,结合时令、地域、环境、性别、年龄等因素,综合分析致病原理和发病原因 ,提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治疗方案。这里实际上就是许多“圆”的相交相切:东 木南火西金北水中土构成地域圆环;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与十二时辰构成一大一小 两个时间圆环;五脏六腑构成一个营卫功能圆环,八脉十二经构成一个精气运行圆环… …大圆套小圆,不同的圆相交相切,其“切点”或“交集”就是治疗方案所在。
各种术数依据的所谓“太极感应思维”更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象奇门遁甲、太乙、六 壬等方术,就是通过天盘、地盘、人盘三个圆的相交相切综合判断吉凶的;象梅花数、 铁板数、金钱卦等预测术,实际上也是把预测者、预测对象、预测时间、地点等,看作 一个个环形场,在场与场的切割中捕捉信息。
这种认识事物的角度与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系统论思维,毛病是过于表面化,程 式化了。它使古人发现了伟大的真理(如中医、气功等),也把自己搞得迷迷糊糊溺而不 返。
六、天、人同构,道、德一体的价值设定
抽象源于价值的获得。作为对中央观念的抽象,“道”集中地体现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对权威的崇拜、向自然法则的无条件委顺;也体现着人类自我实现的人生理想:对自 我角色和地位的认定,以及面对永恒时的伟大抱负。这一点体现在中国人的主体观里。
这个概念包含了主体观与对象观两层意思,两者很难区分开。对象观是主体观的另一 个侧面。主体观的基础和前提是自我观,是自我观的强化和升华。自我观以自我为着眼 点,旨在把自己与他物区别开来;主体观则强调了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自我的地位;因而 主体观这个概念在这里指的是作为族类及个体的存在的人对自己的属性、地位、价值以 及与自然对象的关系方式、作用方式的体验、理解和认识。是人类的自我定位、自我评 价,直接反映着一种文化的格调与色彩。
(一)主体观
在原始社会中期以前,人们把世界分为两大块:族类与非族类。前者包括氏族成员、 保护神、氏族图腾物等,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非族类。其后随着族类范围的扩大,形成 了种族自我意识;再后通过理性的启蒙,在与自然的紧张与对立中,人类意识到自己的 独特价值并开始自立为主体,自我主体意识成为改造自然、创造文化的活性因素。作为 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中华主体观具有两大特征:类主体性与道德主体性。
1.类主体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体性从来就不意味着“具有坚强的主体性格的自由自在的个性 ”(黑格尔语),而只体现为一种类主体性,即人作为一个族类面对作为对象的自然界时 的自我确认、自我张扬。人们总是通过与“他者”的对立来认识自己,因为对立是认识 的前提。然而在道的世界里,人类没有真正的“他者”,他深陷在大自然的结构和律动 里,同其它事物保持着一种割不断的有机联系:每一个个体都是无限网络中的一个结点 ,决定其价值的,仅仅是它在时间与空间里的位置。他没有权力可以伸张,因为他被统 摄在道的呼吸里,被规定在与“他者”的关系里。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向整体性的 自觉依附。这在道家那里,表现为乘缘随化,反朴归真;在儒家那里,则是彻底自弃, 自觉奉献于群体的目标。
主体性的觉醒始于西周。周代殷后,统治者鉴于“天命靡常”的事实,得出了上天“ 唯德是辅”的结论,从而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从原始宗教的蒙昧中冲破一 条缺口,为人类自觉的理性认识活动和历史主动性开辟了道路。此后经春秋、战国至秦 汉,这种类主体意识始定型为民族性的文化观念。其内涵包括:其一,人为万物之灵。 其二,人能够参赞化育。
类主体性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主体性。因为只有极少数人——上面提到的王、圣、君 子,才能有资格代表人类整体,芸芸众生实际上只是被宰制的纯粹客体。
2.道德主体性
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最主要地体现在道德上。正是通过道德上的建树,人类个体实现自 我的价值,人类整体获得生命的尊严。对道德主体性的追求,使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形 成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塑造了民族文化的高尚尊严,强化了民族凝聚力。 然而,物极必反,对道德主体性的过份强调,则最终导致了主体性的丧失,使整个民族 丧失了认识和批判的武器,使知识拥有者成为专制王权的同谋和帮凶。因为“任何道德 法则都具有否定自由的被给予性”[13]。其结果必然是:社会性的人格卑化,伪道学的 泛滥,批判理性的丧失,纯粹知识的缺如。
(二)对象观
这里指的是对处于天人关系之中的、作为人类之他者镜像的自然的理解和认识。正是 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人类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的局限性,也发展了自己的能动性。
然而在古代中国,自然界从来没有成为纯粹的认识客体。相反地,人类总是自觉地归 依于自然,认同于自然,把自然法则作为人类生活的最终依据。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所来自之处。人与大自然同质同 构。《尚书·洪范》第一次以明确的语言构筑了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曰王省惟岁, 卿土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周易大传·乾》则以庄严的笔调,构建了一统天人的神圣框架:“大哉乾元,万物资 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春秋时期的老子则第一次用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 ,表达了世界的根源,万物的本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怠,可以为天地母”[6](第25章)。
各派思想家,在认识事物时进行抽象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基本预设却是一致的,这 就是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天地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系统,任何部分脱离了整体就会失去 生命力。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就是在人与自然这两个有机系统相互进行 信息与能量交换的动态平衡中把握生命周期及身体状况的。无论是草木虫鱼,还是人类 鬼神,都是气所化育。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能“致虚极,守静笃”;庄子才能委形去质 与万物同游;儒家的圣人们才能理阴燮阳,参赞天地。这导致了认识论上一种浅薄的乐 观主义:通过取象比类,就可认识万物;通过因天顺道,就能功成事遂。
总之,古人保持并强化了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尽管有几个“圣人”叫嚷着要“为天地 立心”,但同样作为自然的产物,圣人又安能逃于天地之间!这种自然观投射于社会生 活,则是对“秩序”与和谐的强调:大自然所以能正常运行,是因为万物各保其序,一 旦物失其序,就会灾异横生;“秩序”体现在运动中就是“和谐”,因为每一个部分都 必须以适合自己的方式顺从和呼应整体的节奏——这是“重名份”、“讲折中”的礼乐 文化的心理基础之一。这种自然观使中国人避免了西方人常见的世界疏异感,失意时可 以投入自然的怀抱抚平创伤。然而,主体性的缺乏导致了批判能力的丧失,终于使整个 民族在似是而非的取象比类——风水、相面、八字之类——里耗尽了心智。
七、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基本观念
在这个大一统的框架之内,关于人的本质、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 等,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并形成了具有共同性的价值取向,这里分别称 为人性论、社会观、历史观、方法论、知行观。这些观念作为理论思考的基石,在民族 主流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建构作用。
(一)人性论
关于人性,向来多有分歧。历史上有持性善论者,有持性恶论者,有持性自然论者。 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性者,生也”或“性出于天”。所谓性善性恶,不 过是在本然之性上加上一个道德主义的标签而已。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基本上是 一种自然主义人性论。
这种人性论为圣人的道德教化留出了余地,也为法治管理提供了依据,但没有为个性 的成长开辟空间。因为“人”被过深过多地包含在自然里。
(二)社会观
社会是以血缘与文化相认同的人的群体。它首先是血缘认同。个体只有作为家族的成 员才成为社会的成员,其个体存在的意义完全归系于家族的延续和发展上。因而“孝悌 ”成为维系社会的最坚韧纽带。国是家的扩大,国王即天下人的家长。对家长“孝”就 应当对国王“忠”。忠孝观念因而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第一法宝。其次是文化 认同。在谈到人与禽兽、华夏与夷狄的区别时,古代哲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文化,譬如《 荀子·王制》中说“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因而,政治必须从教化 始。圣人的作用就是“化民”。民在未化之前,仅是一种形同禽兽的自然存在。
(三)历史观
传统历史观可以称为自然主义的有机历史观: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展开过程,有循 环但没有对必然性的设定。这种历史观具有以下特点:
1.全景式把握 自然与社会在一种相互纠缠的状态中共生共存,历史体现为宇宙自然 的大框架下人类生活场景的不断转换。在二十五部官修正史中,除人类社会的编年内容 外,还专门设有对天文、地理、灾异等自然现象的描述与记载。
2.后馈式价值取向 尽管个别思想家在特别历史时期出于现实的需要强调变化,重视 “今天”,整个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基本上是后馈式的,是“厚古薄今”的。大概再也没 有哪个民族象中华民族这样拥有如此强烈的祖先崇拜情结了。这是因为中华先民所处的 生存环境相对恶劣,谋生艰难,不得不靠家族集体的力量维系生存。家长与族长自然成 为众人希望所托,情感所系;而那些对家族邦国的发展有所建树的祖先自然受到后人长 久的感戴。对历史的深切关注,无疑不断强化着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凝聚力,使中华文明 历经五千年而不绝。然而,总是把目光投向过去,则使这个民族失去了发现新的可能性 的机遇和能力。
3.主体性的消解 除了历史发轫处少数几个为万世垂范的道德英雄外,再也找不到历 史的主体:连皇帝也只是“应天顺人”,为一种神秘意志所支配;其它王侯将相不过是 按照别人强加的台词进行表演的傀儡而已;芸芸众生只是跑龙套的或干脆就是背景。在 家族范围内,个体存在的意义就是保证家族基因的承继和传延。
(四)方法论
中华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感性依赖和生存依赖特征:认识世界的范围局限于人的感性 接触,并且含有明确的致用倾向。因而,传统思维方式与方法以世界的整体性为运思依 据,以直觉与思辨的相互渗透为运思机理,用公式可以表示为:正心、观物——取象、 体道——类分、类推。
1.正心、观物 “正心”是进入宇宙功能场之前的自我调谐,“观物”即去感受某种 现象的存在状态。大自然为人类的生活确立了标准和依据,因而“观物”是认识宇宙和 自我的第一步;又因为人心与天心的契合是进入世界的唯一途径,“正心诚意”就成了 “格物致知”的保证和前提。
2.取象、体道 即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地反复观察与感受,从有限的事物中直觉出某 种统一性,概括、提炼为意象。这是一个通过体悟进行抽象的过程。它不象西方思想那 样,通过分解与排除抽象出本质或“纯粹形式”,而是把对象作为处在联系中的、 活动 着的整体,在直观类比与辩证综合中直接猜测或领悟事物的本质。因而,“取象” 取的 不是实体,而是某种属性、某种关系,以“比附”为主要手段;“体道”是人对自 然的 验证和认同,以“体悟”为主要手段。《周易》太极模式是这种认识方式的集中体 现。
3.类分、类推 由于世界的同质同构性,由于事物的本质体现于与他物的关系之中, 这就存在着利用某种功能属性对事物进行分类整理的可能;同样原因,没有必要也没有 可能对某个具体事物进行深入的结构与性质分析,而只要依类外推,就能旁通博贯,穷 尽天下奥秘。阴阳五行就是这样一种依类推论的模板。
(四)知行观
对被束缚于整体性关系之中的中国人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自足的有待认识的对 象,而是践行其人生理想(立功、立言、立德之类)的环境条件;发现真理的过程是向世 界深处的不断沉入,而不是理性之光对物质奥秘的层层照亮:因而知即是行,知行合一 。知的目的在于行,行的自知自觉即为知。
这种知行合一的人生姿态导致了两种价值偏向:一是侧重于道德行为与道德意识。在 人生追求中,把人格修养和道德建树放在首要地位;在现实事务中,则注重行为的动机 、过程而非行为的后果。二是侧重于“行”而非侧重于“知”,经世致用之学成为学术 主流。这使知识成为权力的奴婢,也使“诛心”,“诛意”之类思想禁锢成为一种文化 传统,整个民族在封建社会后期陷入了道德主义的泥潭。
结论:时间观、空间观、主体观以及因缘观等基本观念构成了时空共振、天人合一的 大一统宇宙图式。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框架。这个框架不仅限定了人们思考和想 象的方式、范围,而且预设了人们行为的准则和依据,即以王、道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包括中央权威(王)、等级秩序(礼)、合谐(乐)、中庸(道)等核心价值,审美的生活态 度,实用主义的生存原则,以及怀方行圆、以静制动、知微待时、安份守位等人生策略 ;在这个框架之内,在认识与实践领域,则形成了中华特色的社会观、历史观、人性论 、方法论、知行观等纲纽性观念,作为思想家们构筑其理论体系的基石。
收稿日期:2003-0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