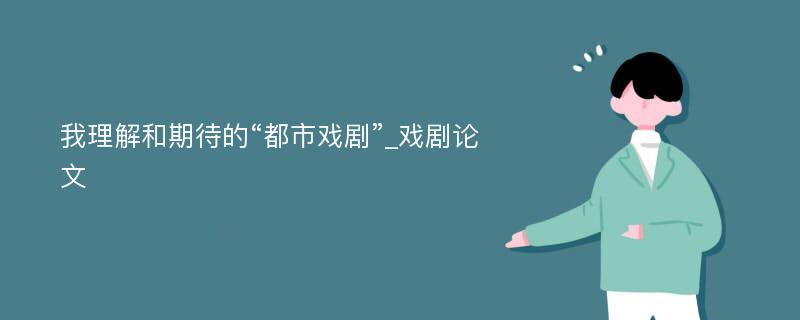
我所理解与期待的“都市戏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所论文,戏剧论文,期待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怀臻先生的大作《重建中的中国戏剧》提出了“地方戏剧都市化”这个重要命题, 体现出他致力于推动中国戏剧健康发展的建设性态度。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年 毛泽东时代以乡村和农民为最重要的权力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已经被彻底颠覆,现 在怀臻提出“都市戏剧”这个称呼(或者说口号)时,已经不再有什么忌讳和冲击力,也 不用像当年那样战战兢兢。怀臻20世纪90年代初就以“都市新淮剧”命名他的成名作《 金龙与蜉蝣》,近几年又再度以“都市戏剧”冠于多部新作之上。什么叫“都市戏剧” ,以及这些剧作是否可以称之为“都市戏剧”,都还值得讨论,但中国戏剧的发展,确 实已经到了必须正视都市戏剧的关键时刻。因此,我在这里不打算具体评价怀臻的创作 ,只是想就他提出的“都市戏剧”问题,写下我自己的思考。
怀臻的文章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传统戏剧现代化”和“地方戏剧都市化”,在他 看来,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或者是同一种观念的两种表达方式,至少可以说,它们 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但是在我看来,“现代戏剧”和“都市戏剧”之间的关系,还 需要加以细细辨析。“现代戏剧”这个词经常被滥用,舍去将“现代”纯粹当作一个时 间范畴的中性的用法,即使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架构里,什么是“现代戏剧”,什么 是“传统戏剧的现代化”,都值得认真思考。在最直观与朴素的层面上,假如我们在认 真地谈论传统戏剧的现代化,最好不要将它简单地等同于一些现代技术手段,比如干冰 、电声乐器、电子射灯和转台的运用之类,也不要把在舞台上跳几段露大腿露肚脐的艳 舞,表现寡妇的思春和青少年性冲动当作“现代”——西谚有云,“在商业和道德领域 里,禁令和走私总是形影不离的”,即使是最“传统”的剧目里也不缺乏情爱与性的大 胆描写,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如果纯粹从题材角度看,这些内容与现不现代实在了无干 系——那个可以与“传统”相对举的“现代”,恐怕用“现代性”加以阐释更为合适。 至于什么是“现代性”,从事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前贤们已经给出过很多定义,角度和 说法不一,无法在这里细述。不过,至少在用“现代”指称社会发展的场合,它确实是 与城市的形成、工业化以及世界性的商业流通相关的,确实意味着城市与农村的二元格 局向着全社会的城市化方向发展,也即乡村向着城市趋同的基本走向;最近经常被提及 的现象是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它是在世界视野里消解了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分离——它 使后发达国家这些世界意义上的“农村”渐渐地与发达国家趋同——因此,“现代”确 实与“都市”存在某种相关性。
如果说在一般的社会领域,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现代化与都市化有着高度相关性的话 ,那么,在艺术领域,进而在更为广阔的人文领域,这两者却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阿 多诺和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学者有个非常著名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审美现代性” 与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启蒙现代性”不仅不是同质的,恰恰相反, 它们事实上是互相对抗的。具体说,在开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批判时 ,他们找到的重要武器之一,恰恰就是审美,是审美现代性。所以我们看到,现代艺术 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力度要远远大于古代艺术对古代社会的批判。回到我们的戏剧语境, 或明或暗地诱导大众使之成为顺从专制者的愚民的作品,固然缺乏起码的现代性,而卖 力地歌颂“先富起来的人”,努力证明经商致富的合法性的思想立场,同样与现代性无 缘。
因此,假如我们是在谈论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那么,都市化的重要 性是毋庸置疑的;艺术领域的审美现代性却在本质上包含了对它的反思与批判。事实上 ,如果说商业以及工业的发达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的话,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与都市 化相关联的进程,恐怕足可以远溯到唐宋年间,城市的出现以及扩张且越来越繁华,正 是这种走向重要的标志性现象。但是当我们讨论艺术问题,讨论戏剧问题时,答案就很 不一样。确实,城市的出现与商业流通的扩张、市场日渐繁荣对于戏剧的诞生乃至于发 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最好把这样的作用,局限于戏剧的商业运营领域, 最好将它局限于戏剧的商业化或者说商业戏剧领域。就以20世纪商业戏剧势头最盛的三 、四十年代为例,大城市里有影响的名演员如梅兰芳、杨小楼等人,经济收入当然远远 超出乡村露演中的戏剧艺人,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只有最大化地实现了自己的艺术的经 济价值的这些城市演员才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的优秀戏剧表演艺术家,只有他们才代表了 中国戏剧艺术的现代化——这就像我们不会轻易地把当今最走红、出场费最高的歌星视 为当代最伟大的、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歌唱艺术家一样。这是说,城市对于戏剧的重要 性,首先在于它对这个行业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它实现其经济价值的重要性,至 于艺术,则要复杂得多——当然,这是说即使在现代性的维度上,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地 、绝对化地以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判断戏剧的高下。
作为一个行业的戏剧和作为一门艺术的戏剧,两者固然相关,却又有差异。明乎此意 ,我们才可以讨论都市戏剧,才可以来讨论都市对于中国戏剧当代发展的重要性。
如同我在佛山召开的“当代戏剧之命运”研讨会上特别提及的那样,当代戏剧发展不 平衡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衡,而城市戏剧的低迷状态,对于戏剧 整体上的负面影响力,不仅完全抵消了农村部分地区戏剧的繁荣景象带来的推动作用, 对于中国戏剧未来生存的可能性与发展空间,也构成了最为严峻的挑战。因为都市集中 了大量的有钱、有闲且文化水平较高的消费者,他们的文化娱乐消费欲望最高,这样的 文化环境对于戏剧的需求,无论量还是质,都远远超过农村,也更能够包容不同风格不 同品位的戏剧在竞争中蓬勃发展,因之它对于戏剧的生存与发展的推动力,也就远远超 乎农村。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既拥有促进戏剧繁荣发展的更强劲的文化动力,同时也 为戏剧家在竞争中不断提高艺术水平提供了必需的平台和空间。同样重要的是,城市地 区在人才资源配置上比起农村有明显的优势,它最有可能聚集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它对 于优秀的艺术人才的吸引力是无与伦比的,也有培养和催生更具影响力的戏剧大师的土 壤,这使得城市在整体上能够拥有相对于农村的艺术优势。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演变 ,城市生活方式与城市人的审美趣味相对于农村的示范作用和辐射力越来越大,城市在 引领全社会戏剧发展方面的中心地位,也愈加凸显。但这样的结论,不能误解为只有在 城市里,戏剧才可能体现出它的“现代性”诉求,才可能出现“现代戏剧”,更不能说 坚守地方风格与民间趣味就必然与“现代性”相悖。
重视都市戏剧或者说重视戏剧在都市里的生存状况,并不是说农村的戏剧演出不重要 或农村演出市场不重要,而是说,在多数场合,作为一种比较纯粹的文化娱乐消费对象 的戏剧,不像作为祭祀仪式之组成部分的戏剧那样植根且依赖于农村,城市的文化消费 环境对它的成长与发展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必然远远超过农村。因此,诞生于城市的中 国戏剧只能以农村为它最后的保护地,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虽然 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与农民在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与文化消费领域所 占的绝对份额仍然极大,但如果要考虑戏剧的发展与未来,不能不看到,城市地区的戏 剧生态比农村戏剧生态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因此,我非常同意怀臻“民间是戏剧存在的 基础,城市决定着戏剧发展的命运”的论断,但我想加以说明,或者说我与他的异见在 于我并不认为城市的重要性在于它代表了“先进文化”或者聚集了更多的“先进文化人 ”,而更多地将城市的重要性,置于商业的角度加以讨论,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越来 越成为文化的产业基地、越来越成为文化产品的“原产地”的特征上加以讨论与研究。
讨论“都市戏剧”,尤其是提及“都市戏剧”以及戏剧的商业前景,很容易让人们联 想到近年里那些高额投入的“大制作”。其实,近年里戏剧界经常出现的豪华制作的大 投入现象,如果从都市戏剧的角度加以分析,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合理性。有学者站在“ 贫困戏剧”的立场上批评戏剧界的大投入,波兰戏剧导演格洛托夫斯基提倡的“贫困戏 剧”只是一种戏剧实验的设想,他主要是在寻找戏剧中最为本质的元素,而不是着眼于 提倡不花钱或少花钱办大事。坦率地说,目前戏剧界剧目创作的大投入现象,其弊端显 而易见。尤其是许多剧团的大投入,出发点本来就不是为戏剧,而是或主要是为了借机 拉动政府财政开支趋向,使之更多地向戏剧方面倾斜,在一个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几乎 不受任何监督的特殊环境里,这是戏剧界挤入现存财政分肥机制的一条特殊通道。许多 高额投入的剧目,完全成为各地宣传文化领域和部门领导的“形象工程”,它和城市建 设领域的“形象工程”同样充斥腐败的气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由于对精神产品 的评价更具有不确定性,文化领域“形象工程”中的失误也就更难受到追究。这样的大 制作,其实质是宣传文化部门的掌握权力者无节制地调用公共资源以服务于自己的职务 保全或升迁,而一部分戏剧界人士由于可以在这个分肥模式中得到些许实惠,自觉不自 觉地参与其中,甚至怂恿和鼓动它的存在与发展,也对大投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戏 剧界并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对隐含在这一现象背后的体制因素的批评存在 政治上的高风险,理论与批评界只能将他们对于这些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现象的强烈不 满,转移到对这些剧目外在浮华呈现的批评上。这样的批评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仅仅着 眼于新剧目创作的投入资金之大,仅仅注目于舞台呈现上的豪华奢侈,予以不加分析的 批评,却不能说是客观的态度,也有悖于都市戏剧的规律。
在一个正常的、相对比较健康的戏剧市场里,戏剧制作人在新剧目创作中投入较多的 资金,有意识地运用多种多样的技术手段,极力营造以声光电色为手段的诉诸官能刺激 的戏剧空间,以此吸引大量的观众,这是商业戏剧中常见的现象,我们可以质疑这样做 的艺术价值,可以小心谨慎地将一部戏在商业上的成功与艺术上的成功区别开来,但是 如果局限于商业的角度,大投入也可以说成是市场规律的一般要求,是由工业化时代文 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恰恰由于都市在现代社会中成为财富与文化精英的聚 集地,才有可能催生出大投入的戏剧,并且经由这种大投入制作出来的戏剧作品,获得 超乎寻常的经济回报。其实这正是西方音乐剧普遍选择的赢利模式——从艺术的角度看 ,音乐剧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认真讨论的特点,它们的“成功”无非是商业上的成功。诚 然,大投入并不必然地获得高收益,小投入有时也有可能获得巨额经济回报,好莱坞就 是这样,类似的现象在戏剧市场中同样屡见不鲜。这两种现象并存,一方面说明的是一 种普遍的、基本的通例,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另一个规律——所有规律都有例外。一般而 言,在艺术创作领域,大投入的戏剧创作,首先有可能吸引一流的编导和演员的加盟, 以此保证它在人力资源配置上的相对优势,继而能够促使编、导、演等各部门在创作过 程中精雕细刻,以保证作品在所有方面包括细节上的精致与完美,最后,它还能够通过 多种途径,尤其是通过大众传媒吸引尽可能多公众的注意,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在激 烈的演出市场的竞争中,具备这些优势的作品,获得市场成功的概率当然要大得多。由 此我们可以并且应该认识到,在都市环境里,尤其是在那些业已形成一个高收入阶层的 都市,戏剧创作的大投入、大制作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高票价的演出固然远远超出了普 通百姓的消费能力,但是假如它确实能够得到那些有较强文化消费能力的观众的青睐, 也未必不能赢利,甚至完全可能比起低票价的剧目获得更丰厚的利润。
在现代戏剧历史上,以上海这样的开放城市为例,各大剧院在新剧目创作方面的投入 也经常很可观,往往借各种机关布景吸引观众,极尽奢华之能事,商人之所以能借此牟 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投入的剧目有可能通过相对较高的票房收益,获得更好的经济回 报。现在我们所讨论的都市戏剧,理想状态之一,恰恰是对这段历史的回归——而目前 还很少有剧团和剧目能够实现这样的经济目标。目前国内戏剧演出市场上那些所谓的“ 大投入”,一部戏的所有直接投资只不过几十万到一两百万人民币,且这些投资多数是 用于舞台美术及改造灯光音响设备、添置固定资产,用以吸引一流演艺人才的比例并不 大;以这样的投资力度,如果真能着眼于商业演出,按照现在大城市里的基本票价水平 ,不计直接演出成本,如果票房理想,不过演上十来场就足以收回投资且略有盈余,从 商业的角度考量,这样的投资回报率不能算低,对剧团经营运作的要求也不能算高。在 北京、上海、广州这类人口超过千万且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高收入群体的国际性大都市, 这类新剧目创作的投资风险决不能说大;事实上,以最近几年在保利剧院和长安大戏院 上演的商业戏剧的投资收益情况看,一个新剧目能够上演二十场,就足以达到收支平衡 甚至有所赢利。进而,就算是一般的省会城市,以专业化的水平衡量,投资商业戏剧的 经济风险和困难程度,恐怕远远比不上其它商业领域;在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竞争 的环境里,按一般的世界惯例衡量,投资新剧目创作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只不过现在 多数剧团的大投入大制作,在创作动机方面基本不涉及到它的市场前景,至少是在创作 过程中,有关市场收益的考虑总是要不断让位于诸多既非艺术、也非商业的因素,不仅 要经受许许多多的干扰,剧团的主管部门也很少有真正专业化的眼光和能力以主导剧目 的市场化运作,这才导致它成为深受众人诟病的文化“形象工程”。所以,回归到商业 的层面,现在国内戏剧界的大投入不是太多太滥,而是太稀缺,当然,太多太滥的是只 期望获得权力回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回报)的大投入,真正期望于获得经济回报, 因此要以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式运作的大投入,就显得极为稀缺。
但是都市戏剧的话题还不能到此为止。我们认识到在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越是 穷人乍富就越是渴望通过非理性的奢侈以确证自己从穷人到富人的身份置换,而豪华昂 贵的戏剧演出恰好能够满足他们这样的需求;因此大中城市实在是可以有而且应该有相 当多大投入的、制作精良或貌似制作精良的戏剧作品,都市戏剧实际上拥有极大的市场 空间,非常需要这类戏剧作品去占领。同时还要看到,在多数城市,包括沿海城市,普 通市民的经济收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高收入群体人数众多只是由于城市和国家的人口 基数较大;如果按照国际惯例,一般的戏剧演出票价的中间价位应该是人均日收入的一 到两倍,那么,上述那些因为大投入所以必然导致高票价的戏剧,即使是在北京、上海 、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也只能是戏剧市场金字塔最顶端的塔尖。如果我们将这些奢华 的创作视为面对戏剧高端市场开发的产品,那么,我们还需要更多供更大多数普通消费 者欣赏的作品,符合戏剧低端市场需求的作品。因为需要欣赏戏剧的不仅仅是阔人;民 众对戏剧的爱好不能只赖每年欣赏一两场演出培养,而需要像每个时代真正的戏迷那样 经常泡戏院;爱好戏剧的意思不是把戏剧当作偶尔为之的盛宴那样每逢重大节庆才大肆 饕餮挥霍一餐,而是将它当作日常的零食小点,只要愿意就能够享用。而要能满足一般 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需求,假如只有少数大投入的戏剧“精品”,无论是从数量上看, 还是从观众的经济承受能力上看,都只能是不符合实际的幻想。
正由于此,中国目前城市地区的戏剧衰退状况,才真正令人担忧。
城市地区的戏剧衰退,并非始于今日,但近十多年来却呈现出恶化的趋势。虽然从表 面上看,各地政府近年对戏剧演出设施的投入有所增加,并且一直在努力改善戏剧演出 场所的落后状况,但事实上除了一些中心城市建造了一批号称达到“国际水准”的大型 剧院以外,居民基本的文化设施建设却处于严重滞后的状况。以前曾经有过的一些剧院 ,或者被改造成商业经营场所,或者因经营不善而被废弃,因而导致演出场所急剧减少 ;根据去年上海文广影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03年5月,上海全市有专业剧场1 7家(市区14家),其他具备演出条件、兼营演出的影剧院173家(市区32家)。根据上海市 文广影视局每月编印的《上海市文艺演出一览表》,2002年市区剧场(包括影剧院),全 年每月有演出的仅18家。与历史数据相比,1950年时上海市区的专业剧场多达109家, 以后逐渐减少,到了1995年剩下22家,2003年更萎缩到只有17家。(引自李永乐:《上 海剧场经济效益欠佳》,《联合早报》2003年10月20日)而在此期间,上海市的人口则 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上海,也普遍出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
演出场所急剧减少与戏剧演出市场的萎缩两者是互为因果的,由于演出市场萎缩,现 有的演出场所不能充分实现其收益,更难以吸引资本流向演出场所建设;现有演出场所 既少,仅剩的几个设施较完善的演出场所,也就可以漫天要价,人为地提高了剧团演出 成本,同时也遏止了经常性的戏剧演出,反过来也成为演出市场萎缩的原因之一。无论 如何,它们都已经是目前许多城市现实存在于戏剧领域的痼疾。同样根据上引的材料, 上海市2003年全年的剧场收入一共是1个亿,其中上海大剧院就占了8000万。对于上海 大剧院而言这固然是骄人的业绩,然而对于上海整个城市的戏剧市场而言,数字中蕴含 的悲凉自不待言。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戏剧的繁荣与否不仅要看少数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体现其 艺术水准、引领艺术风潮的高端市场上的戏剧杰作达到的高度,还需要更多的、能够成 为普通百姓日常文化娱乐的一般剧作,让更多的民众有更多机会直接欣赏戏剧演出。不 是说一般民众无权享用高水平的戏剧精品,而是说当精品与一流的演出不足以满足民众 的欣赏需求或者是其成本超出一般观众承受能力时,应该选择的对策不是让人们闲着荒 着,而是让他们能有机会欣赏到与其消费能力相当的戏剧演出。回到前面所说的剧院的 话题,我们的城市固然需要建造标志性的、能够“与国际接轨”的设备精良的大戏院, 但同时也需要、甚至更需要遍布城市各个社区的、因其造价适中,所以不至于使演出票 价超出一般观众经济支付能力的普通剧场。进而,我们固然需要以国家和市场两方面的 力量共同培养一大批优秀的、代表了中国戏剧艺术水平的戏剧家和国家级的标志性剧团 ,同时还需要更多虽然未必称得上一流或国家级,却能够通过常年在剧场演出谋生,因 而能够用自己的艺术劳动为民众提供切合其经济承受能力的戏剧产品的普通演员,以及 由他们组成的一般的营业性剧团。
因此,在我看来,都市戏剧的关键,正在于社区戏剧的发展。这也符合国家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我们可以在看到富人为欣赏一场演出随随便便就花掉千儿八百时 平心静气地笑笑,权当那是赞助文化事业的善举;但我们有权要求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 生活的城市里获得更多欣赏戏剧的机会,当然必须是票价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 众的文化消费能力相称的戏剧演出。如果这种演出也有资格称为怀臻所说的“都市戏剧 ”,我就忍不住要殷切期待它的出现,运足中气准备着为“都市戏剧”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