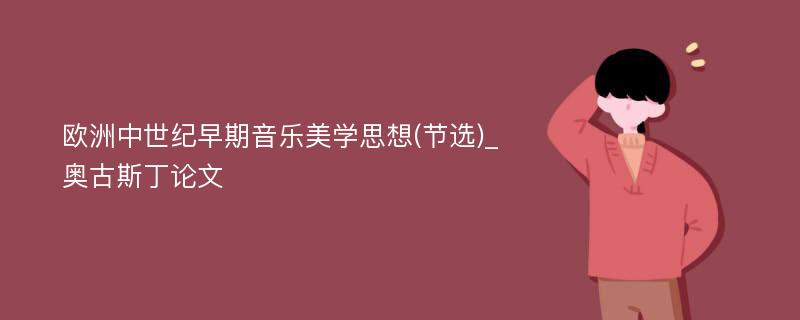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音乐美学思想(节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中世纪论文,美学论文,思想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世纪的美学与音乐美学而言,主要的思想基础有两个:历史的是古代希腊、罗马美学,如毕达格拉斯的数论、柏拉图的理念论与艺术价值观等;现实的是基督教神学与哲学,并在宗教教堂这一音乐实践场所中得到充实。
本文所探讨的音乐美学思想仅限于中世纪早期(约5~11世纪), 属于封建社会形成期。将此阶段音乐美学思想作为本文的讨论对象,是因为这一时期从哲学到美学,到音乐美学都是奠定基础和确立规范的时期,最能体现中世纪音乐美学的这两个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奥古斯丁、波爱修和卡西奥多。其思想基本上代表了中世纪早期音乐美学的发展状况,并能够表明当时的特殊现象,即宗教对美学的影响与作用。
奥古斯丁的音乐美学思想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是中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被罗马教廷奉为圣·奥古斯丁。他对基督教的贡献是巨大的,如他的原罪观成为中世纪对异端裁判的理论依据;他的预定论成为以后加尔文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奥古斯丁本人来说,他的神学思想是他自己各种思想的总纲;就整个中世纪来说,他的神学思想是以后整整一千多年宗教意识形态继续形成的基础,日后几乎原封未动地再现于经院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及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著作中。
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部分。从神学直接引出的就是他的宗教功利主义和禁欲主义。这两者,不同程度地贯穿在他的哲学和伦理学中,也贯穿在他的美学和音乐美学中。
在奥古斯丁年轻时,曾经写过一部六卷本的《论音乐》,主要讲述音乐节奏的原理,其中的第六章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音乐于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与前几章相比较有更大的史料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奥古斯丁受到的古希腊音乐思想的影响;然而当时他对音乐的观点,并不能代表他对音乐的最终看法,在他皈依基督教以后,这部书就基本上被他遗忘了。因此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既丰富又芜杂。丰富,是因为他兼收并蓄了希腊古典美学许多派别的思想,融汇到他那以神学为核心的体系中;芜杂,是因为其中各色成份都有,且又散存于他的各种论述中。本文主要从神学角度出发来分析奥古斯丁对音乐的理解,这样能够代表中世纪思想的主要倾向和特点。
研究中世纪早期的音乐美学必须将它与一般美学相联系。就奥古斯丁流传下来的思想资料看,纯音乐美学的甚少,属于一般美学的相对要多一些,而其中潜含着音乐美学的成份;联系并参照奥古斯丁一般美学思想将会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
对奥古斯丁美学的探讨分为客体对象与主体审美两个方面:
1.客体对象方面,主要涉及美本原与美本质两个问题。
1)美本原。这是决定奥古斯丁美学观的根本性质的问题。 在美的本原论上,奥古斯丁的美学与哲学同出一辙,都持“神创论”的观点,即认为美的本原是来自于神明的创造,而不是现实世界所本有的。如他说:“美善的天主创造了美善的事物,天主包容、充塞着受造物。”
这种美本原论的源头来自柏拉图,而不是奥古斯丁本人的杜撰。柏拉图认为美本原在于冥冥彼岸世界的“美本身”,即在于“理式”的美:“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有了它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1 〕柏拉图关于美本原的理式说到了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那里就与基督教的神结合起来:“神才是美的来源,凡是和美同类的事物也都是从神那里来的。”〔2〕
因此,从柏拉图经普罗提诺再到奥古斯丁将美本原置于“天国”中是顺理成章的。至于美本原是怎样从上界来到这个现实世界的,柏拉图认为是从理式“分享”来的;普罗提诺认为是从比理式还在先的“太一”那里一层层“流溢”出来的;奥古斯丁则干脆认为是“神创”的。这种客观唯心论的本原说很有延续力,它不但贯穿了中世纪,到18世纪黑格尔关于美的理念论也都与之一脉相承。
在奥古斯丁与前人的言论中,几乎都不直接论及音乐美学本原问题。他们回答了一般的美本原,也就包含着音乐的美本原。音乐美的本原也在“上帝”那里。
神创论的美本原说必然导致美的永恒观念,因为作为神的天主永恒不变,永恒即绝对。所以奥古斯丁说:“美好并不来自有限度的存在,而来自绝对的存在。”而这一“绝对的存在”即“所有和谐与协调的起始者,上帝”。〔3 〕柏拉图则将永恒的绝对美给予了更明确的描述:“这种美(理式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不生不灭的,不增不减的。”〔4〕柏拉图解释过这种矛盾,他将世界分为三个:理式世界、 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这绝对美只存在于第一个理式世界那里,而理式美被分享到现实与艺术世界时,它就变绝对美为相对美,永恒性消失。奥古斯丁这样说:“这些美好事物的美好秩序达到终点后,就会消失,在他们身上有早晨、有黄昏。”
当脱离神界回到现实世界时,奥古斯丁终于不能不看到事物的辨证和发展,兴起和衰落,完全回避现实(艺术)中美的相对性是不可能的。只有回到现实世界,奥古斯丁才清醒地看到了美的相对性。总的看来,奥古斯丁等人虽然注意到美的相对与绝对的两个方面,却仍然与我们所持的观点很不同:对我们来说是“相对之中有绝对”,而奥古斯丁等人是“相对之上有绝对”。
2)美本质。奥古斯丁曾说过“事物本身和谐的美”〔5〕以及“和谐都给人以快感”〔6〕之类的话。 应该看到他对和谐包容的丰富内涵还是有全面的理解的。首先他认为和谐是个整体性的概念,而不是部分性的概念,他是这样说的:“各部分……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个和谐的整体里。”
那么各部分又怎样才能结合成为一个和谐美的整体呢?这就需要一些规范形式美的法则(或条件),如整一、数比、对称、均衡、协调、节奏、色彩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整一与数比法则。关于“整一”法则,即有序化,奥古斯丁说到:“整一是一切美的形式”,“没有一种有秩序的事物是不美的。”关于数比法则,即各部分要有合适的数比关系,奥古斯丁又是这样说的:“美取决于形状;形状取决于比例;比例又取决于数。”〔7〕其它的次要法则奥古斯丁也有讲述。 如他说“世界美存在于对立事物的对比中”〔8〕等等。奥古斯丁对形式美的主要、 次要法则都很注意,因为这些法则与和谐美都有联系,并和神学不相抵触。
从历史的渊源看,奥古斯丁美的和谐论是来自公元前6 世纪的以数为世界本原的毕达格拉斯学派。而和谐观念的建立,正是毕达格拉斯对音乐研究得出的结果。毕达格拉斯是最早发现音乐和谐比例关系及黄金分割率的人,这促成了他们的和谐论的形成,并将其推广,走向宇宙的和谐论。奥古斯丁由此而推论“没有达到原理程度的节奏是缺乏美感的”,〔9〕音乐再一次失去了感性特征,变为理性的观念。同时, 奥古斯丁关于整体性的观念,则是从亚里斯多德那里接受过来的。
2.主体审美方面
奥古斯丁在这里充满了矛盾,具体表现在审美的情理问题上。他主张理性应处于主导地位去引导感情,感情也要服从理性的引导。《忏悔录》有这样一段记述他审美感受的文字:“你的圣堂中一片和平温厚的歌咏之声,使我潸潸泪下。这种音韵透进我的耳根,真理便随着而滋润我的心田,鼓动诚挚的情绪,虽然泪盈两颊,而此心觉得畅然。”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审美是既含情又含理(智)的,而且还是由理致情的;这里审美的理智处于主导地位,又是以智胜情的,可见他对自己的这种审美反应是肯定的。然而当审美的理智不处于主导地位而以感情胜于理智时,奥古斯丁是不能予以肯定的。关于这一点,在《忏悔录》里也表示得很明确。那是在有一次他被歌声“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和谐荡漾”的时候,说出了他这种极端的审美观点的,他用非常忏悔的口吻表述道:“快感本不应该使神魂颠倒,但往往欺弄我;人身的感觉本该伴着理智,驯服地随从理智,仅因理智的领导而被接纳,这时居然反要以客为主地超过理智而自为领导。在这方面我不知不觉地犯了错误。……如遇音乐的感动我心过于歌曲的内容时,我承认我在犯罪,应受惩罚。这时我是宁愿不听歌曲的。”
奥古斯丁的忏悔逐步升级,先说是“犯了错误”,后又说“在犯罪”,以至“宁愿不听歌曲”,这表示了他对宗教神圣理性卫护的决心。因为这些歌曲都是以天主的“语言为灵魂”的,他不容许这神圣理性(理智)被审美快感所亵渎。
另外,奥古斯丁为了崇尚神圣的理性、抑制人的情感,主张让音乐变得语言化,他说:“歌曲的声调要极少变化,不象唱歌,更近于朗诵。”还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他又提出同样的看法:“听了清彻和谐的歌曲,激动我的不是曲调而是歌词。”为了宗教理性,他要音乐向后退,退向语言;要曲调不激动人。然而音乐还要照样地激起情感,审美的规律仍然起着作用,奥古斯丁自己也认识到了。比如,他曾不自觉地说了这种符合审美实际的话:“这些神圣的歌词通过乐曲唱出,比不了用歌曲更能在我心中激起虔诚的火焰。……对于配合着你(主)的语言的歌曲,以优美娴熟的声音唱咏而出,我承认我还是很爱听的……”
奥古斯丁在客观对象方面肯定美的存在,尽管他认为美的本原在上界的天主那里,是永恒的绝对;而到下界人的世俗生活中,美却变得不永恒而相对了,但这毕竟是对美的承认。可是当他回转身来面对主体审美问题时,却改变了态度,几乎为理性而否定了审美。
前面我们曾分析到:在信仰与理性比较上,奥古斯丁是重信仰而轻理性的。所以他不能不以信仰压制理性,不给理性以审视为判断信仰的权利,这在他的著作中表现得很明白。如果说在奥古斯丁那里还有理性的话,那便是宗教给界定的理性。然而到审美中,奥古斯丁又变得重理性而轻感情,轻美感。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奥古斯丁心中三者的关系:信仰至上,理性居中,美感在下。奥古斯丁曾说到审美“快感的危险”,将其排在最下,危险就会减小,就不至于使人的快感去冲击信仰;并且一旦陷入审美快感中时,主还能拯救你出来。奥古斯丁这样说:“声音之娱本来紧包围着我,控制着我,你(主)解救了我。”
爱美是人的天性,但奥古斯丁认为这种世俗的感官的爱是一种情欲的表现,而情欲是会使人迷失本性的魔鬼。人不应该这么爱,而应该爱那上界的美好。他说道:“不是爱各种歌曲的优美的旋律……我爱天主,是爱另一种光明、音乐……我内心的光明、音乐……他的音乐不随时间而消逝……”
这是一种宗教理智的爱,抽象存在的爱。这种爱也不是审美的爱,而是非审美的爱。这又一次显出他理性主义的特点。
在《忏悔录》中也有脱离开理性纠缠的审美心理分析。这就是该书卷中关于审美期望、注意、记忆的论述。并且讲得很出色。他说:“我要唱一支我所娴熟的歌曲,在开始前,我的期望集中于整个歌曲;开始唱后,凡我从期望抛进去的,记忆都加以接受,因此我的活动向两面展开:对已经唱出的来讲是属于记忆,对未唱的来讲属于期望;当前则有我的注意力,通过注意把将来引入过去。这活动越在进行,则期望越是缩短,记忆越是延长,直至活动完毕,期望结束,全部转入记忆之中。整个歌曲是如此,每一阙,每一音也都如此。”
不过这并不证明奥古斯丁不是一个审美的理性主义者。因为在讲到听歌曲的时候,他曾说过:“我记忆所收藏的,不是意义的影像,而是意义本身。”他还是忘不掉理性的意义。
奥古斯丁的音乐美学思想不止上面分析的这些,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涵盖了音乐美学的许多方面,如他曾说道:“我们内心的各式情感,在抑扬起伏的歌声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音调。”显然是声情相应说的观点,是今天心理、物理的“异质同构”说的萌芽,这里不多论述。
波爱修〔10〕、卡西奥多〔11〕的音乐美学思想
奥古斯丁所建立的宗教、哲学、音乐美学思想,为其后近一千年思想领域里的活动奠定了基础。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被称为“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者”的托马斯·阿奎那(约13世纪)时代。在奥古斯丁之后,思想领域虽然存在着带有根本性的(宗教)哲学争论,但也同时出现了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倾向;音乐美学也是如此:在挖掘和整理古代音乐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对音乐的特殊性进行探讨。波爱修、卡西奥多等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罗马帝国后期的劫难使学术研究降到了最低点。在中世纪早期的音乐领域,学者们渐渐明显地看到了这种空白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无法建立与基督教相适应的音乐理论体系。而在了解了古希腊丰富的音乐理论之后,他们发现这些理论若加以改造可以和基督教的教义相结合,于是对古代知识的介绍,就成为必要的工作。他们的研究对象包括:毕达格拉斯学派、斯多噶学派以及柏拉图等人的理论。尤其是毕达格拉斯学派的“数”论,不但被波爱修、卡西奥多等人加以全面阐述,而且更进一步得到引申,成为他们音乐理论体系的基础。
与奥古斯丁相比,波爱修虽被当时的人们称作“真正的音乐家”,其音乐理论在整个中世纪享有崇高地位,但他本人却更象一个善于思辨的哲学家;他对哲学思考的热爱甚于宗教信仰,其著名的在狱中写出的《哲学的慰籍》,通篇没有引用《圣经》一句话,却同样反映了他的宗教观点和道德哲学思想;而卡西奥多从今天的意义上看,则近似一个音乐学者:他对古代的音乐理论进行了整理和总结,使音乐理论更加系统化。
(一)波爱修的音乐美学思想
波爱修在挽救濒于失传的古代知识方面是很出色的,他继承和整理的古代理论有:毕达格拉斯学派的“美存在于形式中数的比例的观点”,并认为比例越单一,美越宏伟;斯多噶学派的美在和谐的观点,但这一和谐存在于事物的表面,因而地位较低等等。这些观点充分显示了古代音乐美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波爱修真正成体系的理论是他关于“音心相应”的学说及“宇宙音乐”的概念。
1.有关“音心相应”〔12〕的解释:在其论文《音乐的体制》的序言中,波爱修证明了音乐与人心存在的内部联系。文章开头他提到“所有感官的知觉力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在某种生物中存在,以至于设想一种动物没有感觉知觉是不可能的”。这明确了感官存在的实在性以及它的自然属性,然而只有这些是不够的,他说:“但要知道一个方形或三角形的特性,他必须去询问数学家。”就是说在人感受事物的过程中,要有“数”的因素加入,或说加入一些理性的判断能力才行。想对事物进行正确的感知,就不能只靠感觉,还要有在感觉经验基础之上的分析与加工,这其中就有“数”的因素。
由此,波爱修又吸取了毕达格拉斯学派“身心的整个结构是与音乐的和谐紧密联系的”观点,得出了对音乐与人心相联系的内部原因:“我们身心的状态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其比例与我们后面的讨论表明的把和声各变调连接在一起的比例相同。”这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精巧结论,他用数这个中介物解决了音乐与人心之间联系的问题,完成了主客观的统一。
据以上感觉中存在数及毕达格拉斯学派的观点,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其中的思路:
在数(比例)等于和谐的前提下,因为身心的结合状态(表现为数)、感觉中的数以及音乐中的数,三者有相同比例;所以音乐和谐,身心和谐;又通过感觉,音心和谐。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就不难解释波爱修所说的以下一些观点:各职业、年龄的人都“自然地使情感与音乐保持和谐;而且不同的头脑喜好不同的调式”。如粗陋的人喜欢“色雷斯人的粗陋调式”,有教养的喜欢“较严肃的调式”。以及由此而谈到的音乐的价值判断。
波爱修的这一理论影响至今。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家阿恩海姆提出的关于审美心理的“异质同构”说与此相似。只不过前者的主客体中介是数,而后者是所谓的“力”的结构。
2.“宇宙音乐”图示:
对音乐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在我们看来是明显而自然的事情。然而,在中世纪音乐美学中音乐的分类问题却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这个时代音乐科学的内部结构和音乐科学的基本概念和问题”。〔13〕音乐分类问题是了解中世纪早期美学的一个良好契机。
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提出了“天体音乐”与“人间音乐”的划分,前者指宇宙中的星球以和谐的距离相间隔,以预定的速度沿着一定轨道运行,其旋律形成和谐的音乐;后者则是指音乐家模仿天体音乐的旋律创造出的人间音乐。毕达哥拉斯学派以研究“数”为基础,以音乐为依据所创造出来的“天体音乐”与“人间音乐”的划分已把一部分音乐的内涵确定为抽象形式,这为后来波爱修对音乐的进一步划分奠定了基础。
在完全接受了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观点以后,波爱修将音乐划分为三个部分:宇宙音乐、人类的音乐和器乐音乐。宇宙音乐,用波爱修的话说,可以在“基本元素的结合以及被观察到的天际中不同季节的变化等方面得到研究”。在这些事物的运行即交替变化中,必然见出限度与规律,也就是存在了“和谐的音乐”;人类的音乐:人身体中灵与肉的有机结合,也同样表现了和谐音乐所具有某些特征;而器乐音乐,才是指现实的音乐,它本身和谐,又反映宇宙的和谐。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今天意义上的音乐在波爱修理论中的地位。
波爱修关于宇宙音乐和人类音乐的划分,其实是对以往所谓的“大宇宙”、“小宇宙”的划分,二者已经涵盖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包括客观的和主观的;他称之为音乐,就是看到了整个宇宙间无处不在的所谓“和谐”的规律,正是有了这些规律,世界才在运行发展。
波爱修对于音乐的划分,使上帝脚下的尘世(物质世界)完全归于音乐的统辖之内,它们依照上帝所制订的和谐规律运行,反映了音乐所具有的特性;而他的“音心相应”学说又把主观意识纳入到音乐范畴以内,并与客观相连,于是在他眼中音乐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代名词。
(二)卡西奥多的音乐美学思想
卡西奥多的主要工作是对古代音乐知识的整理与保存。他被认为同波爱修一样,“是把古希腊的音乐知识通过其著作传至中世纪的主要作家之一”。
1.与奥古斯丁不同,卡西奥多更注重对音乐本身的研究,他研究的范围更接近我们现在的音乐理论;这还使他比奥古斯丁更为肯定音乐的价值,“他承认音乐的美学作用,并引证圣经传统和造物主的话来肯定它”〔14〕。
卡西奥多同样继承了古希腊音乐理论中关于音乐是数的观点,认为音乐是与算术、几何、天文一样对数进行研究的学科,“处理与声音相关的数”,或者换句话说“是研究检验相互间处于和谐状态中的事物,亦即各种音响间的异同的艺术”。〔15〕从这一点来说,音乐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不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制约的;并且按卡西奥多的话说,它甚而“以其法则制约和控制我们”:音乐由此获得了超越人控制之外的独立性。
在这一基础之上,卡西奥多对音乐进行了较客观的整理与研究,他限定了“交声”〔16〕的概念,把音乐分为三部分:和声(分辨高低音的音乐科学)、节奏(探求词与声音结合得好或坏的音乐科学)、韵律(通过广泛的依据了解各种韵律尺度的音乐科学),研究了音乐的调式,还对乐器进行了划分。
卡西奥多承认音乐的美学作用,又强调了音乐的独立性,那他是如何把这两者纳入到基督教体系中的呢?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从现实角度来看,卡西奥多看到音乐是能够自然而然地感动人心,这是无法回避的,所以他说音乐本身是“能给人以快感的”,而这与古希腊毕达格拉斯“数”的观念相统一,即音乐是由数构成的,身心也是由数构成的,因此它们都是和谐的,二者之间也就形成了和谐,于是产生美感。
从宗教角度看,卡西奥多认为只有人的向善,即对基督戒律的服从,才能使人感受到独立于人之外的音乐的美感。所以人必须遵守上帝的规则,变得“公平”,这样才有音乐,才与和谐产生联系。而“音乐实际上是适当调整的知识”,一旦人与音乐产生联系,音乐的法则就会“通过我们生命的所有活动得到传播”。〔17〕
因此可以看出,卡西奥多把古代的和谐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认为善良(公平)也是和谐,这样就把和谐论引入了伦理学的范围,从而使以数为基础的古代美学与基督教神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2.卡西奥多最重要的美学贡献在于他的关于音乐价值的理论。在肯定音乐的美学价值之后,他进一步探讨其社会功用。
前面说到奥古斯丁对音乐的态度是矛盾的,时常徘徊于肯定与否定之间,而卡西奥多则比较直率地肯定了音乐的社会功用,这与他直接接触音乐基本理论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音乐理论,毕达格拉斯的数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一提起音乐,就自然地与古代的“和谐”论(以数为基础)相联系,甚至相对于基督教而独立存在,使得学者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找出二者的沟通点。卡西奥多也不例外,他的音乐价值理论也是直接站在波爱修的音乐和谐论基础之上的。
由音乐和谐,身心和谐而得出音心和谐,卡西奥多于是没有顾及基督教关于“禁欲”的约束,直率地肯定了音乐(所有的音乐)给人的感官愉悦。认为音乐用“旋律愉悦我们的耳朵”,“给人以快乐”;显然作者肯定了音乐形式美的价值,并以健康的心态欣然接受了优美音乐对听觉的抚慰。而且还不止这些,卡西奥多更关心的是音乐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即它的伦理教化作用。
他说:“音乐能升华心灵,使人思维合理,谈吐优雅,行至得当”,另外音乐“还有精神宣泄的作用,唤醒沉睡的灵魂,赋之以高尚的情操。”这里的音乐完全不同于简单的感官愉悦,不只是一种娱乐形式,而具有更高的道德伦理价值,并完全胜任于使人举止优雅,情操高尚的任务。人的向善就是和谐,至善是最高的和谐,通过心音相应的原理,音乐把自身的和谐传给了人,使人内心协和,到达善的境地。显然,这一说法与柏拉图的因为文艺不真实和伤风败俗而遭贬斥的观点大相径庭,同样也与基督教对文艺的否定态度不同。
正是在波爱修和卡西奥多等人的努力下,使音乐渐渐地摆脱了与其它艺术相同的遭贬斥的地位,并以科学的名义站到了各类知识的前列:卡西奥多等人解释说音乐是“处理数的科学”,所以它就不同于其它只是“技艺”〔18〕的艺术,这样在卡西奥多著名的关于“七艺”的分类中,只有音乐是唯一的今天意义上的纯艺术,其它都是科学门类,如算术、几何等。
在卡西奥多和波爱修那里看来,音乐的作用不止是这样抽象的,还有具体的医疗效果。如他们记载大卫用“健康的旋律”使扫罗重获自由的心境,使国王恢复健康;毕达格拉斯用一“扬扬格”的旋律使暴怒的年轻人恢复了自我控制;“特潘德和麦斯那的阿罗林在歌声的帮助下把莱斯堡人和艾奥尼亚人从肆虐的疾病中解救出来”等等。从中可以看出音乐治疗在西方的渊源,而且正是通过这些事例更加直接的、有力地说明了音乐的功用。
总之,波爱修和卡西奥多二人的音乐理论如果说属于基督教,还不如说属于古代更合适。然而这并不说明他们与基督教无缘,相反,他们总是把古代知识和宗教教义相结合,而如果出现矛盾的情形,他们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即宗教至上,理论服从信仰,只不过这种矛盾情况没有发生。波爱修和卡西奥多是把古代音乐理论保存整理至中世纪的重要人物,没有他们,音乐在中世纪就不会有那么高的地位,也不会有完整的古代音乐理论保留下来,成为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基础。
部分结论
通过对奥古斯丁等三个人物的介绍,我们初步了解了欧洲中世纪早期音乐美学的发展情况,它们既系统又繁杂,既出自古代又自成体系,形成独特的风格。而这种独特性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一种思维定势:想要把世间的一切纳入到一个理论,即宗教神学之中。从音乐美学思想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
前面提到过,中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而最根本的就是人与神之间的矛盾,它集中表现在人的内心世界,就象圣经中说的人“以内心服从神的律”,而“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新约·罗马人书》)。音乐,作为人类情感最直接的表达手段,必然深深陷于这种矛盾之中,它或者因能给人以精神的娱乐而受到欢迎,或者因违反“禁欲”戒条而遭到贬斥。奥古斯丁面对这种两难境地,并没有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虽然他一再表白自己对音乐的感受上的喜爱,有时这种喜爱也是纯洁的,但在宗教的利益下,他最终对音乐进行了否定。波爱修和卡西奥多却不是这样,他们找到了一条途径,使音乐中的神与俗的矛盾得到融合。这一途径就是把音乐以理论形式融入基督教神学。
在继承古代数论的基础上,他们把宇宙看成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有了理论上的依据,变为可理解的。音乐(它在当时就是和谐与数的代名词)于是作为抽象秩序的具体表现而与世界的规律发生联系,成为了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他们的观点,上帝用数创造了世界,而音乐可以说就是数的代表,所以亦或可以这样说:上帝用音乐创造了世界。
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波爱修的“音心对应”理论和宇宙音乐图示以及卡西奥多的音乐价值观就是这样从不同的角度对上帝脚下的世界进行了解释的,并且殊途同归,以古希腊毕达格拉斯学派的数的观点,结合于基督教神学及哲学之中。使基督教的知识体系在音乐美学的角度包括了对客观的认识(宇宙音乐)、主客观的统一(音心对应)和社会学(音乐价值论)等多方面阐述。音乐美学成为宗教学说的有机组成成分。
这样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出音乐在当时的地位:它是人与上帝沟通的方式之一。不论理论还是实践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音乐的解释得到答案。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对音乐的内涵就有了过于复杂的界定,从总体上看,宗教内容排除了音乐中的情感因素,占据了主要位置,这极大压抑了音乐的实践活动,当时音乐理论比音乐实践活动更加宏伟,就是这个原因。
以上对中世纪早期奥古斯丁、波爱修、卡西奥多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索,仅是对中世纪十分庞杂的思想体系所作提炼和整理的尝试,希望能对当时的音乐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注释: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第57页。
〔2〕《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57页。
〔3〕引自“St.Augustine's De Musica ”, 由W.F.Jackson Knight翻译,整理。
〔4〕同前柏拉图注。
〔5〕何乾三《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6〕塔塔科维兹《中世纪美学》,第75页。
〔7〕同注〔6〕。
〔8〕同注〔6〕,第76页。
〔9〕《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57页。
〔10〕Boethius,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约480—524 年),罗马哲学家,政治家,被称为“古罗马最后一个哲学家和中世纪第一个哲学家”。出身于罗马贵族,曾在雅典和亚力山大里亚等地受教育,510年任执政官,522年在拉韦纳的提奥多里克宫中任首席行政官,同年被诬陷叛国而入狱,写下了著名的《哲学的慰籍》,524年被处死。 其著作很多,译注了亚里斯多德的许多著作,如《范畴篇》,以及一些神学著作,如《论三位一体》等,而《论音乐的体制》根据希腊资料写成,是中世纪的教科书典范。
〔11〕Flavius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约480—575年,曾在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宫中任职,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制定了“七艺”,建立过修道院。
〔12〕为方便,这是借用的说法。
〔13〕符·波·舍斯塔科夫著《从美育论到主情论》第一卷(下),张泽民译。
〔14〕同〔13〕。
〔15〕《中世纪美学》第109页。
〔16〕源自古希腊音乐理论,即具有和谐音程的音。
〔17〕引自“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 Donald Jay Grout整理。
〔18〕波爱修曾沿袭古代的“自由艺术”与“奴隶艺术”的分类而提出“艺术(art)”和“手工技能(artificium)”的区别。
标签:奥古斯丁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中世纪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艺术论文; 哲学家论文; 格拉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