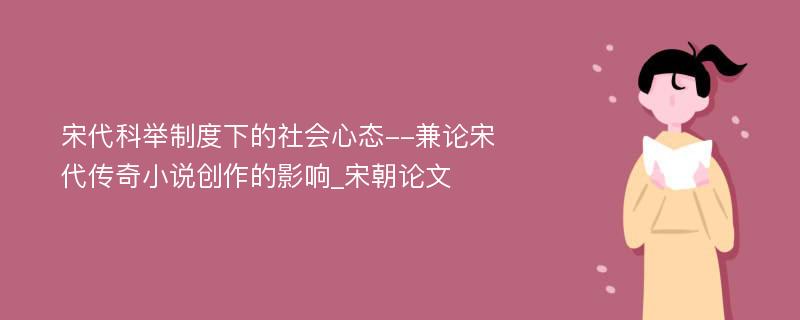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定论文,宋人论文,科举论文,宋代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2-0099-08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如何?这无疑是个值得关注、也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社会心态”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且不同时期的社会心态不尽相同,情况极为复杂,而科举带给每个士子的际遇和感受又千差万别,甚至悬若天壤,欲进行考察,只能从形形色色的“心态”中寻找共同点。于是我们发现,在极重“科名”的宋代,由“科名至上”衍生出的“科名前定论”,是宋代科举制度下社会心态的凝结点。一个无论是“金榜题名”者、还是“名落孙山”者,甚至是与科举毫无干系的人都要接受或不得不接受这个理念,即便是时过境迁,也还会津津乐道。故本文从“科名前定论”切入,研讨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而由于反映社会心态的材料多来源于笔记和志怪小说,因而略及“前定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
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是由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决定的。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曰: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霾於卑近而不获超卓於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於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1](卷11)
刘壎是由宋入元的士人,他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有宋科举制度的深刻反省。习时文,取科名,然后入官治民,虽然一生“皇皇焉”,“不识高明之境”,但却心甘情愿。不仅获得了心理平衡,而且得到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余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2](4之43)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决定士人的命运,原因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仕进之途。也就是说,“科名”成为官场的唯一“准入证”,“含金量”极高。在唐代,先是明经科,后是进士科,虽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但有此科名者不过是做“美官”,成“清流”,而入仕门径却不少,不像宋代这样“出是科”者就“必弃之”。
科举决定士人命运的严酷事实,给社会心态带来强烈的冲击。
首先,如上引刘壎所说,“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同样的话,早在北宋就有人说过,如孙觉在熙宁元年(1068)六月所作《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更》中就曾写道:“今有道德之士,不由科举,则无以进仕于朝廷。是使天下之才,皆汨没于雕虫篆刻之技,弃置于章句括帖之学也。”由宋入元的赵孟頫也说过:“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3](卷6《第一山人文集序》)这种“科名”至上的后果,是使科举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些宣称“绝意科举”或所谓“隐士”,也是在经历了多次下第痛苦之后,才不得已而放弃的,并非天生高尚或有“隐德”。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不失为选拔人才的有效方式;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宋代科举制度也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相对公正,可它的唯一性指向所造成的社会弊端,也为有识者所共嗟,如刘壎所感叹的:“可哀也!”
二是举国沉溺于时文。欧阳修曰:“是时(按:指仁宗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4](卷73《记旧本韩文后》)宋元之际,舒岳祥回顾两宋时文盛而诗歌衰时,说:“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第一,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从之列,举子盖鄙之也。”[5](卷12《跋王矩孙诗》)前引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曾说“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他又在《隐居通议》卷21写道:“宋初承唐习,文多偶俪,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然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数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士大夫方游场屋,即工时文;既擢科第,舍时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称文士。大者培植声望,为他年翰苑词掖之储;小则可以结知当路,受荐举,虽宰执亦或以是取人,盖当时以为一重事焉。”既然“科名”重于一切,而要猎取科名,又必须靠“时文”,那么士子全力投入到时文的学习和写作,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是士子除“科名”之外,对其他则是“集体冷漠”,甚至“爱文而不爱国”。身历亡国之痛的刘壎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感慨良深地写道:“《南唐书》载:金陵被围,亡在旦夕,后主犹命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及第。史臣反覆哀痛,谓其不识事势,每读使人殆无以为怀。而比岁襄围六年,如火益热,即使刮绝浮虚,一意救国,犹恐不蔇,士大夫沈痼积习,君亡之不恤,而时文乃不可一日废也。痛念癸酉(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之春,樊城暴骨,杀气蔽天,樊陷而襄亦失矣。壮士大马如云,轻舟利楫如神,敌已刻日渡江吞东南,我方放解试,明年春,又放省试。朝士惟谈某经义好,某赋佳,举吾国之精神工力,一萃於文,而家国则置度外。是夏又放类试,至秋参注甫毕,而阳罗血战,浮尸蔽江。未几上流失守,国随以亡,乃与南唐无异,悲夫!爱文而不爱国,恤士类之不得试,而不恤庙社之为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为背时之文,在当日为亡国之具。夫安忍言之!”[1](卷11)科举制度对士人乃至全社会人格的扭曲,真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洪迈《容斋四笔》卷8《得意失意诗》记曰:“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金榜题名,举子下第,成了人们公认的大喜大悲的两个极端。当人们还在咀嚼或喜或悲的滋味时,三年一个周期的贡举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悲喜剧重又拉开帷幕。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整个被扭曲了的人格,就是科举制度下宋人社会心态形成的背景,也是“科名前定论”产生的土壤。
二、“科名前定论”
那么到底这些悲喜剧是谁导演的?是知举官?科举制度看起来是那么严密和完善,并不是哪位考官说了算,何况上有“御试”,是皇帝?皇帝只不过是“御试”的挂名“主考”,阅卷、定等都是由御试班子集体决定的,何况谁敢将矛头上指?在这里,任何理性的解答似乎很难消除人们的迷惘。于是,人们只有另求答案。柳子文在元祐间任考官时,曾作《未试即事杂诗》二首,第一首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徒劳争墨榜,须信有朱衣。万事前期定,升沉不尔违。”[5](《同文馆唱和诗》卷3)他所说的“朱衣吏”,代表的是“神”。(注:按:清杨潮观《吟风阁杂剧》收有《开金榜朱衣点头》,“朱衣”自我介绍:“吾乃文昌帝君殿下朱衣使者是也。”《菩萨蛮》道:“巍巍金榜云霄立,不凭文章凭天鯫。……”传说欧阳修知贡举,常觉座后有一朱衣人点头,然后其文入格(此事据说见赵令畴《侯鲭录》,然今本《侯鲭录》无)。)王安国曾在《举士》一文中,指出“有道德者往往耻于求举”,但同时又说:“贫者又多困于不售。夫不售者,古以为有司之罪,而今之操升黜者反咨嗟叹息,以为彼有所制,而吾亦无如之何。”什么叫“有所制”?据他说,那就是“有司不得行其志而归之于”。原来,是“神”与“命”在冥冥中主宰着士子的前程,是悲喜剧的幕后总导演。
“神”与“命”决定一切,宋人归纳为“科名前定”。上引柳子文诗,有自注道:“朱衣吏事,见《登科前定录》。”《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登科定分录》七卷,张君房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科名分定录》七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作《科名前定录》一卷。《麈史》卷中亦作《科名定分录》七卷。《郡斋读书志》卷9著录元符中无名氏《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引其序云:“己卯岁(元符二年,1099),得张君房所志唐朝科场故事,今续添五代及本朝科名分定事,迄于李长宁云。”(注:参李剑国《宋代志怪叙录》,1997年南开大学出版社版,第70页。)由此可知,《科名前定录》(或作《科名定分录》)七卷,虽记唐人事,却是宋人著作,后又有人补入“本朝科名定分事”,重纂为《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按:张君房,安陆(今属湖北)人,真宗景德二年(1005)进士,官至著作佐郎,曾编《道藏》、《云笈七签》等书。他是位笃信道教的官僚。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科名前定”,虽社会上早有此说,(注:柳宗元在《送蔡秀才下第归觐序》中说,他始贡于京师时,曾向蓍者求卦,后来果然应验,因感叹道:“噫!彼莫莫者,其有宰于人乎?何其应前定若是之章明也。”(《柳宗元集》卷23)则唐代已有“前定”说。)但把它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著书公开宣扬,始作俑者则是张君房。
无论是《登科前定录》或《唐宋科名分定录》,都已久佚,我们无从获见收在两书中的包括前述“朱衣吏”在内的全部故事,但两书之外的同类作品,却仍在不断地创作,至今还大量保存在宋人文献(主要是小说、笔记)之中。
考察这些“科名前定”故事,大约可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科名主于“神”。如《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4引荆伯珍《神告传》,荆伯珍自述他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省试时,赋中误书“焚”为“喷”,归而始觉,中夕不寐,于是向“二相公庙”(子由、子夏庙)乞祷,”是夕梦二神人,朱衣,坐大坛上,谓伯珍曰:‘莺鸣六合,数应二朱,亦须头戴金冠,脚蹈玉象。’怀中出一枝花,曰:‘桂也。’伯珍跪受之,遂觉。”后来他又遇二皂衣吏,自称是送今年举人的“冥中走吏”,告诉他本来落韵不合过,“二相公苦救之,前夜已命宋舍人与改了,今却注名过也”。所说“宋舍人”,指当年的权知贡举宋白。荆伯珍于是去见宋白,宋告诉他:“所试赋甚佳,一‘喷’字固知笔误,前夜已与贾舍人(指贾黄中,当年为权同知贡举)同改为‘焚’字了,勿忧!勿忧!”这年,荆伯珍顺利地通过了省试。宋代科举条制规定,凡诗赋落韵,便入“不考式”,是必定要落榜的,但“神”却可以“扭转乾坤”。而且上引二“朱衣神”所说的“莺鸣六合”云云数语,也都一一应验:“御前试《六合为家赋》,《莺啭上林诗》,名字在第二等末,徙尾第二人魏元枢之下、彭垂象之上。”又如《夷坚支乙志》卷2《邵武试院》,记淳熙十三年(1186)秋八月邵武解试,誊录院失火,文卷被焚。明日,治群胥,皆奔迸隐处,忽一黑物从空而下,状貌如鬼,携当三钱二十余,视案时有喜色,便置一钱于案头而去。吏自念:岂非得钱者预荐?因默记之,待揭榜,果与所料同。作者议论道:“名场得失,当下笔作文之时,固有神物司之于冥冥之中,无待于考技工拙也。”这是典型的“科名前定论”,那个所谓从空而下的“黑物”,便是“神”的使者,有如所谓“皂衣吏”。这类故事现存特别多,再如:
天圣四年(1026),海州书表隽宗远梦有神告之,来年状元是王尧臣。宗远寤,题于司房北壁。是年秋赋,开封府解榜到,见王之姓名,因指谓同列曰:“此是明年状元。”洎省榜到,见王又预奏名,隽再题于壁。未几殿试,王尧臣果魁多士。至和中,毕景儒仲询之父知海州,亲访其事,备载之于《幕府燕谈录》。”[7](卷8《隽宗(远)神告》)(注:《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8《隽宗(远)神告》。该书记“科名前定”的,还有同卷引《灵应记》的《刘悦第三》、《文缜状元》等。)
王安石以《三经》取士,遂罢词赋,廷对始用策。先是,叶祖洽梦神人许之为状头,惟指庭下竹一束,谓之曰:“用此则为状元。”叶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叶果为首,竹一束乃策(原注:又梦中神为设狗肉片为“状”字),定数如此。[8](《制科词赋三经宏博》)
不仅科名前定,连科举考试的题目也是“前定”:
艾侍郎颖,少年赴举,逆旅中遇一村儒,状极茸闒,顾谓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贱子家于郓,无师友,加之汶上少典藉,今学疏寡,聊观场屋尔,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书一卷以授君,宜少俟于此,诘旦奉纳。”翌日,果持至,乃《左传》第十卷也。谓艾曰:“此卷书不独取富贵,后四十年亦有人因此书登甲科,然龄禄俱不及君,记之。”艾颇为异,时亦讽诵,果会李愚知举,试《铸鼎象物赋》,事在卷中,一挥而就。愚爱之,擢甲科。后四十年,当祥符五年(1012),御前放进士,亦试此题,徐奭为状元。后艾果以户部侍郎致仕,七十八岁薨于汶;徐年四十四,为翰林学士卒。[9](卷2)
更奇特的是,试卷中可以对考官起震撼性效果的妙语警句,竟也可由“神”授。如《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8引《灵应记》:
大观元年(1107),孙鈜岁贡辟雍,乞梦于英显神君。是夕梦赴试,有一人赉策题而立。因就读之,见第一题问某事,余皆如之,其人曰:“‘锡燕津亭,郡国举宾兴之礼;计偕给食,多士忘奔赴之劳。’用之可以取高第。”既觉,记之于书。及就试,则所问策题皆协于梦,如其言用之,果中优选。岂特人之富贵前定,而文章亦自有阴相之者。
第二类是科名主于“阴司”。《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8引《张君房自占》三则,第一则《淳化看蛇》,谓淳化三年(992)省试后,梦入一大第,一妇人请其赋诗,“写讫,呈览次,忽大蛇自条床下出,或闻人大唱曰:‘看蛇!’遂惊觉。占之多不解。后逾纪至景德乙巳(二年,1005)年,君房始忝科第,岂蛇之兆乎”。第二则《景德随棺》,谓“君房应二举,败于垂成”。到第三次应举,“尘忝御试之夜”,乃梦随一棺椁,因而问之,曰“一人李沆,一人李至”。“因嗟讶而觉,自亦知其吉兆矣(引者按:洪迈《夷坚甲志》卷13《卢熊梦母》:‘人言梦棺得官。’故此称‘吉兆’)。来日果叨名第。”第三则题《戴昭领钱》:
君房三举及第年,梦涉昏雾,沿蔡河东行。旋憩一茶肆中,有公吏若承符状,人曰:“秀才将来名第,某必把手拽上也。”君房又谢之。然其人似有所求,复有言若邀其多少之限。君房曰:“若向及第,奉银钱十万贯。”其人大感,意似过所望也。既别数步,又曰:“秀才将来化钱必与谁?”君房曰:“亦不知与谁氏耳。”其人曰:“某姓戴,名昭,本江南人。奉钱日但呼戴昭,即自领也。”景德二年果登第。成名后三日,乃偿。其梦人之名第,阴司自有主者,孰非前定乎!
“冥司”的“公吏”居然索贿,真是人间社会活脱脱的“克隆”。又如:
韩宗绪,龙图贽之子,以父任补将作监主簿,皇祐秋镇厅预荐,偶于相国寺资圣阁前,见其家旧使老仆,呼谓曰:‘若非某乙乎?死久矣,何得在此?”曰:“某今从送春榜使者。”又问:“榜可见乎?”曰:“有司收掌甚密,不可得而见也。”又谓曰:“汝能密询有我姓名乎?苟无,亦可料理否?”仆许诺试为尽力。又问:“复于何处为约?”仆云:“复期于此,他处难庇某之迹。此地杂沓,人鬼可得参处。”他日如期而往,仆果在焉。遂开掌,见己之名在片纸上。揭其下,乃田宝邻也,仆曰:“此人明年当登第,官甚卑。郎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况身已有官,故得而易之。若白身,则不可。”因忽不见。明年韩登第,曾以兹事说于亲旧间。[10](卷5《韩宗绪》)
因主之于阴司,故科名须积阴德方可得,如:
罗维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1169)省试罢,梦其父告曰:“尔在举场,不可与福唐杜申争,缘尔家较杜申亏了二十八年阴德也。”两人皆以治《诗》有声。暨榜出,杜为经魁,罗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第,杜居第二甲,罗第四甲,相去甚远。[11](夷坚支甲志卷7《罗维藩》)
袁仲诚,绍兴十五年(1145)赴省试罢,还丹阳,夜梦人叩户,袁叱之曰:“汝何人,安得夜半敲吾门?”答曰:“来报省榜耳!”犹未信,自隙中窥之,乃一黄衣人持文书而立,欣然启门,取其书展读,见己姓名在第二,自余间三四名,或五六名,辄缺其一。复诘之曰:“汝所报若此,非全榜也。”曰:“不然,君知士人中第,非细事否,要须有阴德,然后得之。大抵祖先所积为上,已有德次之,此所缺姓名,盖往东岳会阴德司未圆故尔。”既觉,历历记其语,甚异之。后奏名,果居亚列。[11](《夷坚志补》卷3《袁仲诚》)
在今天看来,“科名前定论”固是谬论,所有的“故事”也绝无科学依据。事实上,宋人早就提出过批评,范仲淹在庆历三年(1043)九月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之三“精贡举”中,就曾写道:“既乡举之处不考履行,又御试之日更拘声病,以此士之进退,多言命运而不言行业。明君在上,固当使人以行业而进,而乃言命运者,是善恶不辨而归诸天也,岂国家之美事哉!”[12](卷上)但是,“前定论”的产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欣赏,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前定论”诞生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张君房撰《登科定分录》的确年虽不可考,但可肯定是在他真宗景德二年(1005)登第之后,此前他蹭蹬场屋,断无作《定分录》的雅兴。我们知道,自景德间至大中祥符初,降“天书”、封泰山,赵宋朝野沉醉在一片“仙风”拂煦之中,故他此时出笼的“科名前定”(也就是“神”定)论,乃时代的产物。其次,科举制度的变革,即糊名、誊录制的普遍实施,是孕育“科名前定论”的温床。太宗时殿试已开始实行糊名制,咸平间又推广到省试,而景德二年御试则开始用誊录制,后来也成为定法。如果说中唐以后的“通榜”使人对谁登科早已心中有数而不感惊奇和意外的话,那么糊名、誊录制的施行则设定了许多神秘莫测的未知数,而中第得“科名”者又未必学业优胜,其中有太多必然、偶然或显性、隐性的因素制约,不仅使人无法把握,也让人难以捉摸,上引范仲淹所说的士之不以行业进甚至“善恶不辨”的事,可谓比比皆是,如欧阳修所说:“使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但能诵诗赋、节抄《六帖》、《初学记》之类者,便可剽窃偶俪,以应试格,而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选。”[4](卷104《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对这类形形色色无法解开的“谜”,“前定论”正好给出了最简捷而又不容究诘的答案。再次,“前定论”对登科得志,然后据要津、获显爵的朝廷新贵们极为有利,他们可借此大肆炒作,自命不凡,以巩固既得地位,捞取更多利益,似乎科名、官爵本是其命中物,故这类人是“前定论”的坚定信奉者和积极宣传者,可以说,许许多多“前定”故事,就是由他们(张君房只是肇其端而已)一手制造,而“前定”故事的炮制,实际上就是自我造神运动。最后,落第者从“前定论”中得到了精神安慰,找到了求得心态平衡的支点,似乎科名原非自家所有,不必妄求。总之,“神”既是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扭曲,又是由人所“创造”,正如列宁所说:“普通的人的观念一旦离开人和人脑,就成了神的观念。”[13](P232)
我们可以从正史、野史或当时大臣奏章中了解宋代科举制度,以及三百年来甚至后人对其是是非非的各种议论和辩难;但似乎可以说,“科名前定论”弥合了一切是非,虽表面上它不过是“民间理论”,(注:统治者至少在表面上仍是鼓励“苦读”的,如旧题宋真宗《劝学诗》有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见《诸儒注解古文真宝》前集卷上。)且非“国家之美事”,却给统治集团帮了大忙:它不仅为科举制度、也为统治者自身涂上了神圣的色彩,而且成了上上下下化解矛盾的润滑剂,治疗心灵创伤的麻醉药,甚至是掩盖社会阴暗面的遮羞布,故虽显然谬妄,却能长盛不衰。
三、“科名前定”下的士子心态
“科名前定”的宿命论,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既然“科名前定”,举子在科举制度下显得那么被动和无能为力,便不能不转而求助于冥冥中的主宰,除此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首先是乞神。如上文已引的荆伯珍《神告传》,因乞神而能成功地将试赋时误书的“喷”改正为“焚”字,即一典型事例。又如:
余尚书靖,韶州曲江人,天圣元年(1023)第进士,又中拔萃。始自曲江将求荐于天府,与一同郡进士刘某偕行。刘已四预计偕,行至洲头驿,有祠颇灵。余谓刘曰:“与足下万里图身计,盍乞灵焉。”遂率刘以楮镪、香酒祷祠下,乞梦中示以休咎。是夕,余梦神告召而谓曰:“公禄甚厚,贮于数廪,官至尚书,死于秦亭;刘某穷薄,止有禄六斗耳。”公谢而退,遂寤,其后出入清华,声望赫然,……刘某者,以累举不第,就南迁,遂摄一尉,才逾旬而卒。[10](卷2《余尚书》)
其次是求巫。由于人神阻隔,士子欲与神“对话”,预知科名,就不得不依靠“中介”——巫。所谓“巫”,有僧人、道士、日者、相人,以及诸般自称深谙术数者流。如:
蜀人严储者,与苏易简之父善。储之始举进士,而苏之子易简生。三日为饮局,有日者同席。储以年月询之,日者曰:“君当俟苏公之子为状元乃成名。”坐客皆笑。后归朝,累亦不捷。太平兴国五年(980),果子易简榜下登第。[14]
吕文穆蒙正少时,尝与张文定齐贤、王章惠随、钱宣靖若水、刘龙图烨同学赋于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乡先生。一日,同渡水谒道士王抱一求相,……文穆对席,张、王次之,钱又次之,刘居下座。坐定,道士抚掌太息。众问所以,道士曰:“吾尝东至于海,西至流沙,南穷岭峤,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谓贵人,以验吾术,了不可得,岂意今日贵人尽在座中!”众惊喜。徐曰:“吕君得解及第,无人可奉压,不过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将入相三十年,富贵寿考终始。张君后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贵寿考终始。钱君可作执政,然无百日之久。刘君有执政之名,而无执政之实。”语遍及诸弟子,而遗其师。郭君忿然,以为谬妄,曰:“坐中有许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动,徐曰:“初不受馈,必欲闻之,请得徐告:后十二年,吕君出判河南府,是时君可取解。次年,虽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卿益怒,众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诏下,文穆果魁多士,而延卿不预。明年,文穆廷试第一。是所谓“得解及第,无人可压”矣。后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钥之命,悉如所言。延卿连蹇场屋,至是预乡荐。[15](卷中)
这些巫的“神通”非常之大,不仅能知人科名,而且连考题也可预知。如:
进士董祐之,咸平元年(998)将赴举,颇怯于公战。常歇马于信陵君庙下,忽遇秣陵进士许骥自南来,亦将求荐于府,叙话久之,许曰:“适于院见一翁,云开禄命书甚灵,盍往谒之?”二子同诣,各说其生之年甲,翁曰:“据命,二君未见食禄之期。”许戏之曰:“今年状元谁也?”翁曰:“此却知之。”遂于禄命簿后揭出一页,上画一人极肥大,被金紫,下注曰:“咸平元年状元,三十。”董、许莫能辨。又问曰:“府试题可知否?”曰:“岂惟府试,虽省试、监试皆可知。”又于簿后揭一页,上画赫日一轮,此省试赋题也。又一页亦画日一轮,曰:“国子监试题也。”二子莫测。已而收其簿入于院,后莫穷其迹。后府试《离为日赋》,监试《迎长日赋》,省试《仰之如日赋》,状元乃孙仅,最丰博,年果三十。其年二子果不利于春官。此可以见科举题目且皆前定,况得失乎?(原注:出钱希白《小说》。)[7](卷12《董祐赋题》)
再次是乞“先师”。读书人以孔子为“先师”,在决定命运的科举考试中自不能忘,于是让这位死去一千数百年的古“圣人”再做好事:
宋王沂公(曾)父,虽不学问,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纸,必掇拾涤以香水。尝发愿曰:“愿我子孙以文学显。”一夕梦先圣抚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欤。恨汝已老,无可成就,当遣曾参来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状元及第,官至中书侍郎、门下平章事,封沂公。[16](卷8附《郴学大成》)
除上述外,在宋人眼里,能预兆科举吉凶的还很多,形成了民间的各种传说、信仰和风俗。如《能改斋漫录》卷11《临川王右军墨池》曰:“临川郡学,在州治之东,城隅之上。其门庭之间有池,深而不广,而旱暵不竭.世传以为王右军墨池。每当贡士之岁,或见墨汁点滴如泼,出于水面,则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又《祥瑞谶应》:“黄冕仲未第时,尝有魁天下之意。元丰四年(1081),南剑州谯门一柱忽为迅雷所击,口占绝句云:‘风雷昨夜破枯株,借问天公有意无?莫是卧龙踪迹困,放开头角入亨衢。’次年,冕仲遂膺首荐,又次年,对策为天下第一。饶之浮梁县有谶语云:‘青山圆,出状元。’邑人程瑀尚书在上庠,累为优等,而尚未登第。尝寄诗与乡人云:‘试问青山圆也未?不应久负壮图心。’明年,公试上舍,为第一人。”又《梦粱录》卷4《解闱》:“亲朋馈送赴解士人点心,则曰‘黄甲头魁鸡’,以德物称之,是为佳谶。”
应当指出,上述事例,无论是乞神求巫,还是相信所谓佳谶吉兆,皆非偶然的个别行为,而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在宋代,卜祸福、占吉凶的民间巫术,势力非常强大。鲁迅先生说:“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实在巫鬼。”[17](《中国小说史略》)王安石曾作《卜说》,对当时的卜筮之盛进行了考察,据他估计,“逆斥人祸福”的卜者,举天下而籍之,“盖数万不啻,而汴(京师开封)不与焉;举汴而籍之,盖亦以万计”。何以此业如此兴旺?究其原因,是“以彼为能决”,能解决人们急于要解决的“惑”与“忧”。[18](卷70《卜说》)对科场举子而言,最让他们“惑”与“忧”的,莫过于自己的命运和前程,故求神问卜,遂成常事,而“科名前定论”也就在这种气候下,拥有了最广大的市场,成为最为流行的社会心态。
当然,宋人也有不崇拜科名而相信自己能力的,如徐度《却扫编》卷下所记:“王文安公尧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青)始隶军籍。王公唱名自内出,传呼甚宠,观者如堵。狄公与侪类数人立于道傍,或叹曰:‘彼为状元,而吾等始为卒,穷达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顾才能如何尔。’闻者笑之。后狄公为枢密使,王公为副,适同时焉。”不过像狄青那样不靠科名,而以武功致高位的,毕竟是极个别人,既不足以改变科名在通往官场道路上的重要性,更难以影响整个社会心态。
若“前定”的命运是下第,士子们便不免失态甚至变态。刘壎《本州教授曾月崖墓表》记述一位在宋季下第的举子,入元许多年后,仍然追悔不已,死不瞑目。他为之表墓的墓主、所谓“本州教授”叫曾友龙,淳祐初试礼部不中,准备再试,而宋亡科废,犹琅琅吟哦,舌本流津,曰:“吾志也。”间遇曾擢第成名者,辄倾倒礼敬,曰:“吾羡也。”大德甲辰岁(八年,1304)六十九,“一日,怅然曰:‘吾试礼部时,吾与某人俱,吾赋与某人正同,然某人得之,吾竟失此一领绿衫(按:宋代赐新进士并诸科登第者绿袍),吾遗恨也,’吾闻之流涕,盖距科废已三十年,距属纩几日耳,愤闷未平犹若此。吾故曰:可哀也。”刘壎感慨道:
自唐赓进士科,宋因之成俗,凡齿章缝,亲觚翰,率以词章科目为儒者之极功,而它不皇务。得之者也,于人家国正亦未知其何如;而偶失之,即愁苦怨抑,如不欲生,如学佛而臻疾证,如修仙而不遂冲举,甚至垂绝犹耿耿凄断,为终古之恨,若吾故人曾君者,诚可哀也。[1](卷8)
前面说过,宋代科举严重扭曲了士子的人格,而曾友龙可谓是又一典型,是“宋版”本范进式悲剧人物。确如刘壎所反复感叹的:“诚可哀也!”
四、“科名前定论”与宋人志怪小说
翻开宋人笔记(包括常说的“史料笔记”),特别是小说集,上述“前定论”故事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洪迈的《夷坚志》中,可谓连篇累牍。在我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中,很早就有所谓“灵验”、“报应”之说,而在佛、道二教中,“灵验”故事成为“辅教”材料,向为善男信女喜闻乐道,深信不疑。自从有了科举,“灵验论”很自然地延伸到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领域,成为“科名前定论”,也很自然地要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志怪小说创作取材立意的丰富矿藏。
就“前定论”志怪小说的类型看,以“梦”与“神”通者为最多,如《夷坚甲志》卷4《詹烨兄第》、卷5《龚舆梦》、《汤省元》、卷7《青童送笔》等等皆是。再举《夷坚支甲志》卷7《姚迪功》为例:
建昌新城姚叟,政和三舍法行时为军学生,尝谒梦于神,以卜穷达。梦己著公服设香于所居门外谢恩,觉而不晓其旨。或云:老生当受恩科而不及赴者,列门赐敕牒,以为诸州助教。于是怃然自念曰:“岂吾旦夕预贡选,而蹉跎不第,至于特奏名乎?”已而累举不登籍,遂束书归休,绝意荣路。己卯(绍兴二十九年,1159),皇太后庆八十,霈恩锡类,姚以孙思贤,获乡荐,得迪功郎,实祗命于家门,距昔者之梦,恰五十年方验。
由本篇可概论这类故事的一般结构:先设举子梦中通“神”,“神”或给以约略可晓的谶语,或让你处于某种迷离恍偬的环境之中(如此篇),等等。总之“神”不能说破,而谶语或环境须是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然后经过人各不同的一番曲折,而结果似乎都可从“神”的指示中找到依据,也就是——“应验”,让人顿然惊骇“神”的先知先觉,证明“前定论”的正确性。这几乎成了套数。
“前定论”志怪小说除写人、神交通外,也有社会性较强、含义深刻的。如方勺《泊宅编》卷下(三卷本)《朱晓容》,就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朱晓容“尝为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间,号容大师。后因事返初,惟工相贵人,他人虽强之使言,终非所喜,而中者亦寡”。他曾为大理寺丞致仕朱临的二子行中、久中看相,一见朱行中,“惊起贺曰:‘后举状元也。’”作者写道:
是秋至京师,二朱舍开宝塔寺,(朱晓)容寓智海禅刹。相次行中预荐,明年省闱优等,惟殿试病作,不能执笔。是时,王氏之学士人未多得,行中独记其诗义最详,因信笔写以答所问,极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经御览,神宗良爱之。行中不知也,日与同舍蔡冲允(蹈)、丁葆光(经)围棋。……未唱名前数日,有士人通谒,……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而语曰:“某乃梁御药门客,御药特令奉报足下,卷子上已置在魁等,他日幸相记。”行中唯唯而入,再执棋子,手辄颤,缘宠辱交战,不能自持。冲允觉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冲允曰:“曾询梁氏所居否?”曰:“不曾。”或曰在州西,急赁马偕往,欲审其事。至梁门,日已曛,度不能返,遂复归。而行中念容,独往智海宿。容闻其来,迎门握手曰:“非晚唱名,何为来见老僧?必是得甚消息来。”行中曰:“久不相见,略来问讯尔。”师曰:“胡不实告我?冯当世未唱名时,气象亦如此。”行中知不可欺,因遭渠氏之事。师甚喜,为开尊设具。……
据《泊宅编》卷上,朱行中后来典数郡,方勺是其门客,故所记当有一定的真实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学”在当时科举中的重要地位,只要能记王氏新经义,哪怕是“信笔”写答,自我感觉“极不如意”,仍能置高第,从中不难体会作者的讽刺意味,此其一。其二,“梁御药”的预传消息,吩咐“他日幸相记”,科场内外相勾结的把戏,昭然若揭。
又如《说郛》(涵芬楼校本)卷30《隽永录》引王铚《来岁状元赋》,写大中祥符中西蜀二子赴省试的穷困之状道:“既得举,贫甚,干索旁郡,乃能办行。已迫岁,始发乡里,惧引保后时,穷日夜以行。至剑门张恶子庙,号英显王,其灵响震三川,过者必祷焉。二子过庙已昏晚,大风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祷于神,各占其得失,且祈梦为信。草草就庙庑下席地而寝。”贫寒举子的艰辛,千载之下仍让人鼻酸。小说接着写道:二子既祷,入夜,见一神曰:“帝命吾侪作来岁状元赋,当议题。”一神曰:“以《铸鼎象物》为题。”“既而诸神皆赋一韵,且各删润,雕改商确,又久之,遂毕,朗然诵之,曰:‘当召作状元者魂魄授之。’”二子尽记其赋,无一字忘,以为科名可得。至御试,果是《铸鼎象物赋》,二子却“懵然一字不能上口”,皆被黜。于是“二子叹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罢笔入山,不复事笔砚”。透过“神”的光环,作者为我们揭开了宋代科场的“假手”黑幕,有力者得助,而贫寒举子“命”中注定的便是落第,科名对他们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镜中花”。
另一类“前定论”志怪小说的内容是“劝善”,如上引《夷坚支甲志》卷7《罗维藩》,就是叫人多积“阴德”。这里再举《夷坚支乙志》卷8《张元干梦》:
张楠,字元干,福州名士也。入太学为学录,既优列解籍,而省试不利,乃止土地祠致祷曰……。是夕,梦神来谒,语曰:“君当登科,缘比者受无名之钱四百三十几贯几百几十文,为此遭黜。楠觉而默念:身为寒士,安有是哉?时诸生从受业者闻师赴省,各随力致助,然度其数亦不能多,意其必以此故。试取记事小册逐一算计,正与神言合,贯百分文奇零不少差。然后大悟,遍以告人,使知非己之财,不可妄得如此。续以上舍赐第。
以“科名前定论”为主题的宋人志怪小说,一般篇幅不大,叙事简洁传神,其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尚待作进一步的专门研究,总的说来,它折射了宋代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真实地反映了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应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宋代科举不仅大大刺激了小说的创作(如以士子赴举为题材的作品占了很大比重),而且促进了志怪小说创作的转型:小说家由唐以前热衷于搜奇猎异,描写山精水怪,转而追踪社会热点问题。这是值得注意和肯定的。
收稿日期:2003-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