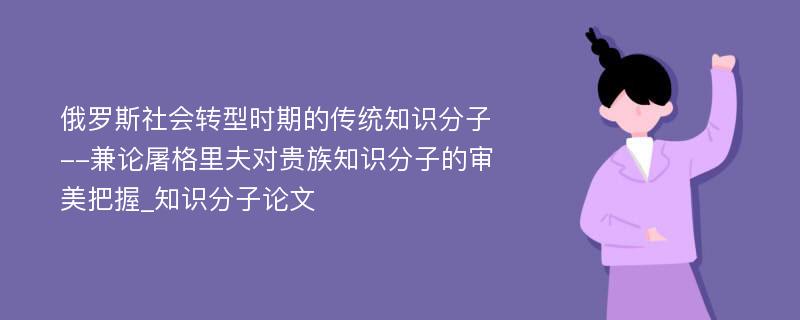
俄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传统知识分子——论屠格涅夫对贵族知识分子的审美把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屠格涅夫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俄国论文,贵族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地看,屠格涅夫时代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的俄国传统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贵族知识分子,因为俄国到了19世纪还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可能系统完整地接受教育成为知识分子,至于30年代以后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那是“没有经历、过去”〔1〕的新生阶层。 贵族在俄国的优越地位由来已久,从《罗斯法典》开始就不断有法律赋予这一阶级以特权, 〔2〕又有那么多凝结民族文化传统的意识形态一直在维护这一阶级。然而历史一进入19世纪,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影响和冲击下,俄国及贵族的出路问题就日益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代表俄国社会精英阶层的贵族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或者不断出现问题,或者遭到失败,而且这种危机有增无减。对这一社会普遍现象,几乎每个俄国作家思想家都予以强烈关注。不过,屠格涅夫在这方面及相关方面的创作却引起了俄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激烈争论,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抑或革命民主派、正统意识形态派,无不时而攻击他、时而吹捧他;十月革命前后对俄国社会出路大争论中时常有人提及他及其传统知识分子等问题,〔3〕苏联解体后他依旧是俄罗斯现今社会争论的人物。〔4〕我认为屠格涅夫的这种文学效应或社会效应与他独特的审美视角密切关联,即站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立场上思考俄国社会转型和传统知识分子问题,既超越斯拉夫派的主张和官方意识形态,又不与激进的革命民主派或西欧派的意见吻合,批判性地对待俄国传统文化对民族进步、贵族知识分子改造与出路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当时的或后来的人,一旦涉及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知识分子等问题,就无不想到屠格涅夫。赫拉普钦科早在1920年就发现,传统的解读屠格涅夫的方式,即力图从他的创作中了解和认识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俄国生活方式、社会问题、风俗习惯等,是值得怀疑的。〔5〕今天俄国和中国都处在一个急剧转型时期,我们把屠格涅夫的传统知识分子题材创作放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矛盾中来重新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一)
按照目前权威的现代化理论,就狭义而言,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包括利用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6〕, 所以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的俄国历史都可称得上是现代化进程。但是,俄国现代化是外源性的,即外来因素的冲击和压力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生产力要素和文化要素要从外部移植或引进,市场发育不成熟,政治权力发挥着巨大的控制作用,改革领导者求改心切、采用激进手段,社会转型急剧,伴随有剧烈的社会动荡等。〔7〕也就是说, 俄国这种激进的外源性现代化必然要给传统文化以强烈冲击,要求知识分子迅速适应社会这种急剧转型。但是,俄国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俄国现代化过程自身的矛盾相交织,使得传统文化在贵族知识分子身上没法得到改造,因而贵族知识分子本身也就要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双重牺牲品。
众所周知,俄国传统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不断交融、矛盾的复杂体系,它一直在寻求自己的支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方式。基辅罗斯原本属于东斯拉夫,在它发展初期就带有东方的封闭性,因其西面有立陶宛、波兰等历史上的强国存在着,隔断了它与意大利、法、英等西方先进文化的联系。公元988年, “弗拉基米尔大公由拜占庭接受基督教……从而使它与基督教的欧洲接近了“(利哈乔夫语)〔8〕, 然而拜占庭的东正教原本就带东方特征,即教义、礼仪、宗教精神既有很浓的保守性,又世俗化、功利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等等(也许正因为它的东方性才为俄国所接受)。这样,名之曰接近了西方,实际上民族精神东方化加剧。特别是,后来欧洲文化中心渐渐西移,西欧出现了代表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人文主义思潮、市场经济,相反,拜占庭文化则慢慢地变成了一种落后的东西,而罗斯——俄国却不调整自己的文化接受方向,反而继续固守着它,以后还希冀光大这种东方文化,还原东正教的光辉史;与此同时,蒙古人事件又强化了罗斯—俄国东正教的东方性和俄罗斯民族的东方化色彩,虽然最后是蒙古人失败了,但俄国这个“欧洲人所以战胜了‘亚洲人’,只是因为它自身变成了亚洲人”(普列汉诺夫语)〔9〕。就在俄国为确立、巩固封建农奴专制政体、 进一步东方化而尽力建构相应的传统文化体系时,西方却在世界近代文明的路上越走越远,步入了现代化,因而俄国与西方的差距也就呈加速度扩大,此后俄国在西方文化面前就更加没信心,尤其是贵族知识阶层,斯拉夫派的诞生与这种心理不无关系(屠格涅夫语)〔10〕。彼得大帝鉴于与西方交战必败的现实,被迫推行以西欧为模式的俄国激进现代化,然而改革的目的却是要进一步巩固旧政体与旧文化,只不过是采用了西方的某些现代化手段而已。此后历代沙皇改革都以此为榜样,在西化与东方化、现代化与传统化之间寻求出路,延续并巩固封建农奴专制政体。这种状况到屠格涅夫时代还在持续着。与此相适应,俄国贵族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场合下接受的话语结构都是1832年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所归纳的“维护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因而社会状况比西欧的落后国家德国还要糟糕,〔11〕他们作为社会精英阶层普遍不知道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思想,没有科学和市场经济意识、应用科学的知识和能力,社会却反而助长他们的优越感,生活方式照旧没有物质方面的压力,用不着为谋公职而奔波,即便从军、为公务员也有最好的位置留给他们,甚至自己的庄园也用不着亲自去管理……现代化原本是要摧毁这种话语结构、改造贵族知识分子的,然而俄国的现代化却是用这些东西来规范其进程的。所以,19世纪中叶前后的传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大潮自然也就不知所措了,既不能抛弃传统文化却又被它束缚着,想适应生活变化却没有相应的价值观与能力。
在俄国杰出作家中,屠格涅夫是接受本国和外国系统教育最多的人,“这种文化背景就使得他有明显的西化趋向,因而能理解30年代莫斯科大学思想运动发展的走向”〔12〕,能特别意识到19世纪中叶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知识分子问题(下文讲的俄国现代化进程,一般指1861年改革前后历史,不另加修饰语)。在他看来,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一样,而“哈姆莱特在整个世界上都找不着灵魂的依靠,是个怀疑主义者;一直只替自己忙碌,但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处境……自我欣赏地骂自己、观察自己、注视自己内心深处、蔑视自己,透切地知道自身的不足……手握一把双刃锋利的自我分析利剑……他不能给别人指示方向,自己也没有目标……对来自女性的真诚之爱,他或者是厚颜无耻,或者报以漂亮的空话……在恋爱中关心的仍然是自己……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只是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病弱无力”,平民知识分子则像堂诘诃德,后者才是英雄,〔13〕作家还自认为塑造英沙罗夫形象(《前夜》)就是要张扬堂诘诃德精神〔14〕,以从反面批判传统知识分子的哈姆莱特气质。屠格涅夫对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虽很奇特,但确实抓住了这些人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即意志弱化问题,“对意志问题发生兴趣,在思考中注意到声名狼藉、潦倒不堪的人……观察这些人的垮台,寻找他们在绝望的冒险主义中存在共同的悲剧根源”(H.詹姆斯语)〔15〕。作家的创作就是用文学方式来体验这些问题。他早期塑造的贵族知识分了形象“我”(《安德烈·科洛索夫》,1844)和成名作《猎人笔记》中刻画的卡拉塔叶夫(同名篇, 1842)、“我”(《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1849)等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就把注意的中心放在这类人的意志问题上,描绘出他们在日常生活诸方面作为失败者的特征:或者是没有勇气去爱一位村姑;或者即便有勇气去追求一个农奴身份的姑娘却没有能力维持这份爱情,处理好恋爱中常出现的基本问题;或者没有调整自己与社会关系的能力,也没有毅力从事任何一项事业。他进而揭示了这些特征存在的内在根源,即自视有教养的贵族要讲究高雅或体面、过份注重自我评价和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等等,因而他们的失败虽各有其具体原因,但都与传统文化导致他们的生命力萎缩有关,表现为心理上的犹豫不决和意志力的丧失。初试之作固然有很多不成功之处,但别林斯基还是从中看出了作家“巨大的才华”,认为它是“俄罗斯人性格卓越的风貌特写”;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作家对贵族知识分子心理作了绝好的描写。〔16〕屠格涅夫以后的贵族知识分子题材创作基本上是对意志主题和现代化过程中贵族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思考的深化,力求揭示出他们在这种矛盾中所具有的精神、心理和思想状态,挖掘这些状态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把后者的价值形态和对精英阶层的作用方式真实地呈现出来,以启发他们与民众认识到民族的进步,调整自我与社会之关系。
(二)
俄国传统文化虽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但它是由许多具体内涵构成的,而这些内涵是可以用一个个哲学范畴、观念来表述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在这个转型时期所出现的意志弱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整体上是与整个传统文化体系有关,但在具体情况下则与某种或若干种内涵有关。屠格涅夫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转型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审美把握,最大的特征之一是:用中篇小说或戏剧这种文学样式,营造了一个个结构精致的婚恋故事,把他们放在能自然而然地显示自身性格某一方面特征的语境中——这个语境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必然要进入的——来观察他们外在行为的心理、精神、思想等根源,分别探究他们话语体系中传统文化的种种具体内涵在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意义,对俄国传统文化作具体范畴的共时层面的考察、理解。
无论是正规教育的话语结构,还是生活方式的要求和当时大部社会成员所认可的话语系统,都崇尚贵族的身份、教养、姿态……结果导致贵族知识分子不去培养自己认识社会、把握生活的能力,以至于感受不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非道德化、金钱化以及贵族身份的贬值这种趋势。传统文化这一特征的这种消磨贵族知识分子精英价值的现象却没有随现代化进程而有所减少、消失,相反,它持续地存在着。对此,作家一直在做追踪体验,在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成果之一是:在塑造别杜什科夫(《别杜什科夫》,1848)、叶尔古诺夫(《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1868)和古西科夫(《旅长》,1868)等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中,表达了崇尚贵族身份、教养和姿态等传统文化内涵对他们自身命运影响的体验。这三个人都具贵族知识分子那套教养、温情、道德感,也都希望拥有纯真的爱情,但又都以为凭借自身贵族军官的身份和知识分子那些品格就可以得到这份理想之爱,结果别杜什科夫把平庸的女人瓦西里莎的卖弄风情当做美女对他这位贵族军官的爱慕;叶尔古诺夫将犹太姑娘爱美莉雅姐妹的勾引视为对自己贵族身份、军官风度之爱恋,差一点断送了生命;古西科夫身为高级贵族军官(旅长),却把自己本来应该是辉煌的一生浪费在对阿格丽宾娜的狂热恋爱中,沦落为食客、“杀人犯”。
对贵族名份、教养、风范等的崇尚,导致贵族知识分子意志力、生活感知力的钝化,出现了上述大批好人吃亏、上当、害了自己或误了一辈子等社会问题,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它又会不仅给他们本人带来悲剧,还要给那些被他们视为爱恋对象的无辜女性造成各种不幸。这是作家对传统文化这一特征进一步体验所得到的感受,而这种感受主要体现在对这几个贵族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上,即戈尔斯基(《绳在细处断》,1848)、华斯托夫(《不幸的女人》,1869)、阿历克谢·彼得罗维奇(《通信集》,1856)和萨宁(《春潮》,1872)等,这些人都是比较出色的贵族青年,因而都分别得到了美丽、纯洁少女的真诚之爱,可是传统文化的这部分内涵没有赋予他们坚强的毅力和社会公民的责任感,他们结果都纷纷失去了那美好的爱情并各有不幸,还使得他们各自爱恋的女人深受心灵创作,或者带着贵族知识分子的失望而随便嫁人,或者由于生活失望而死亡或痛苦不堪。
屠格涅夫对近代贵族知识分子问题的体验,其可贵之处还表现在:从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中,思考他们命运转折与传统文化这部分特征的关系。在他看来,他们作为社会楷模的阶层也是希望实现理想的,只是因为现实处境和生活方式使他们没法隔断整个话语体系中崇尚贵族身份、教养、风范这些价值结构的关系,跟不上现代化进程,因而意志力越发被消磨掉,结果连过去看来还是高尚的爱情品格现在也被扭曲了,既不能在爱情中变得崇高起来,又不能真正实现爱情,但是又只有在与贵族中的优秀女性恋爱时他们的生活才有所充实。这样,他们的不幸是必然的,而被他们当作恋人或爱人的女性自然也就不会有好结局,尽管这不是他们所愿,甚至是要避免的。韦亚佐夫林(《两个朋友》,1854)这个很有教养的贵族青年,因为经济窘困而移居乡村,但他受不了贵族庄园生活的寂寞、无聊,又没有毅力和技能改变自己的处境,于是就在走访周围贵族少女过程中打发时光,在与乡间贵族少女维罗奇卡的爱情生活中寻求满足。可是,婚后生活很快就显得不和谐起来,而他没想到要降低贵族教养的水平来适应生活,没有去做提高妻子教养水平的工作,连充实小家庭生活的意识或能力都没有。他能做的只是逃避,独自离家出走。途中,他时常觉得妻子是个不错的太太,但一想到庄园生活又害怕回去,反而在忧郁中不由自主地随同船只漂到海外。作家原来构思时是让主人公决定迅速回国,并因此而激动,不慎落水而死。〔17〕为了突出贵族知识分子问题的严重性,作家改写了这个结尾:韦亚佐夫林一方面想回国,另一方面却不能自我控制地与法国风流女人日尤丽逢场作戏,而且还出于贵族的体面原则,不自觉地和“情敌”决斗并因此丧生。永远撇下忠贞于他的妻子。巴维尔·亚历山大·伯(《浮士德》,1856)这个贵族知识分子是因为感到不适应正在转型的都市生活而退居庄园的,又因忍受不了仅有《浮士德》一书陪伴的寂寞生活,便重新爱幕旧恋人维娜,并以《浮士德》的艺术魅力唤醒维娜那沉睡已久的爱情。可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贵族少妇维娜早已心力衰竭,她渴求爱情,却认为这种爱恋是一种罪恶,而他却没有让她摆脱这些束缚的能力,同时他又没有毅力停止追求这种爱情,因为她对于他的意义相当于生活的根本希望所在。原本催人向上的《浮士德》,在他们身上却产生了相反的效应,“他和维娜坐在一起,或幻想着她——这就是他的事”(车尔尼雪斯基语)〔18〕。最后维娜为自己的这种爱情心理行为而倍受由传统文化转化而来的精神压力的折磨,痛苦至死。他为此忏悔不已,决心永远滞留乡间以赎罪来打发余生,并认为“生活就是苦役,生活的奥秘在于不断弃绝乐趣。人应该关心的不是希望而是义务,要用义务观念来束缚自己”。 类似的形象还有维列季耶夫(《偏静的角落》,1854)等。
作家对贵族知识分子意志弱化与传统文化这一特征关系的体验是极其细致、深刻的,对促使人们反思贵族的教养、身份与风范等传统文化现象的当代意义,现代知识分子应如何对待它或应该有什么新的文化内涵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如此,作家还关注到血统、门第、财产等传统文化特征与贵族知识分子意志弱化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审美把握同样是在婚恋故事中进行的。H先生(《阿霞》,1858)年轻时是一位很有涵养的贵族知识青年,他热烈地爱上了纯朴又优雅的少女阿霞,但她不是纯粹贵族血统的。因此,对是否求婚他非常犹豫,苦于找不到理由来调和真诚的爱情与不合门第的婚姻这种矛盾关系。后来得知她曾把他们幽会的事转告给她的兄长,于是在决定是否订婚的最后幽会中他就借口这件事,说她是不守信用的人,并骂她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然后撇下热切纯真的阿霞而逃之夭夭。作家很能理解他们爱情悲剧的实质,便细致描述在传统文化观与爱情的冲突过程中他身上所表现出的哈姆莱特式心理,一反温文尔雅的贵族知识分子常态而做出的野蛮举动,有意识地突出传统的话语结构对现实爱情或其他美好事物的破坏力量这一深刻体验,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能理解,认为H“如果像前部分那样, 那么他就不能采取卑鄙粗鲁的行动;如果他能这样行动,那么他一开始就应该给我们展示他是这种恶劣的人”〔19〕,涅克拉索夫也没能理解作家这一审美倾向而有类似微词。〔20〕雅可夫·巴生可夫(同名作,1854)沦落到被人收养才能生存、上学的困境, 居然还要找文件证明自己是世袭贵族的后代。作为一个读了不少书的贵族青年,却对有高贵血统的索菲娅爱慕不已,虽然她并不是美丽可爱的姑娘。又囿于同一种观念,作为门第衰落了的贵族,虽然是大家公认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但从来没敢向她表白爱意,当然也没有毅力割舍这个实际上不存在的爱情。其实,同样出于这种文化传统,索菲娅也从来没注意过与她门第不配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两位着实不错的普通少女瓦尔瓦拉和玛莎却看中了他是一位有教养的贵族知识分子,但因为她们不是名门望族的后代,所以他一直没想到要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给予爱的回报。一生追求诗意爱情的雅可夫·巴生可夫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爱情,甚至丧失了辨别爱情的能力,难怪作家称之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21〕,以示传统文化这一特征促使他脱离社会现实的严重程度。对于这部作品反思传统文化之现代意义的主旨,当时连纯艺术论者德鲁日宁(1824—1864)和杜得希金(1820—1866)也感觉到了。〔22〕
作家在贵族知识分子问题上对传统文化作共时层面的体验,虽然不很完备,但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他深刻地体验出了贵族知识分子精神退化的严重程度、精英意义失落的可怕状况以及这种退化和失落的传统文化根源,把19世纪中叶莫名其妙的常见生活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问题来感受,使之变得具体、可分析理解,从而让人领悟到贵族知识分子的目前位置、传统文化有关层面的现代意义和社会变革自身问题的所在。
(三)
俄国传统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作用的,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贵族知识分子作为当时社会的重要成员,除了男女恋情之外还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屠格涅夫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知识分子问题的审美把握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主要采用长篇小说样式并辅以部分中短篇小说,建构一个个不限于婚恋题材的故事,把他们放在有意无意显示其性格各个方面的不同语境中(而这些语境也是他们无法避免的)来观察他们各种选择的内在依据,综合感悟他们话语体系中的整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作历时层面的体验。具体说来又有多种特色。
首先是让贵族知识分子本人亲自走进生活的不同领域,着重通过语言与行为表征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性格及其与整个传统文化的关系。按作家的说法,罗亭(同名作,1856)是19世纪40年代热爱生活的贵族青年,是个有“天才特征”的人。〔24〕他有宣传、捍卫真理的热情和独特的思维—语言能力,因而在拉松斯卡娅庄园与蔑视真理的毕加索夫的辩论,使大家为之倾倒,唤起了主人的女儿娜达丽娅热爱真理的情怀,还赢得了她的坚贞之爱。可是,他却没有一种坚决的力量来接受这可贵的爱情。“在这里两种文化发生了冲突,结果使她的期望出现了转折。他想固守传统文明,相反,她则准备破坏它。”〔25〕他作为门第衰落了的贵族优秀知识分子,觉得在婚恋问题上应该门第匹配,服从家长权威,首先是对长者负责而不是第一步就考虑感情,因此主人一旦反对他与她恋爱时,他便什么反抗举动也没有,连反抗意识也没产生过。罗亭尽管后来牺牲于1848年法国大革命,可是贵族的那套教养却使他不谙俄国社会发展变化趋势,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好具体事务,即使知道该怎么去做了,传统文化铸造的他也没有毅力、技能去真正完成那种工作,更何况正如他的真理宣传在某种程度上相当空洞、肤浅一样,他的许多计划也是不切实际的。对此,“作家虽然非常同情自己的主人公,却不敢把他过于理想化,反而时常迫使自己从怀疑的角度看待他”(涅克拉索夫语)〔26〕。而“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1859)与‘见识广博’却无根的罗亭是一样的”,因为“他父亲给他安排了一种使人迷糊的西式教育,以迫使他把俄罗斯精神与假定的英国男士保守气质结合起来”〔27〕,而且这种教育又是在封闭保守的贵族庄园中进行的。这样,他的精神、人格、思想等都不能健康发展,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化,以至于第一次正面看一个女人就要和她结婚,而她(名叫瓦尔瓦拉)却是赶潮的非正统女性,正好看中了他的高贵门第和大笔财产,很快就答应他的求婚,以期尽快得到各种享受,无所谓爱情、伦理、贞操之说。对她的这些“现代性”他一无所知,等婚姻悲剧酿成后才悔恨。但对此不是好好总结自己,而是不知所措,继尔痛恨促使社会转型的西方文化,转化成坚定的斯拉夫主义者。而斯拉夫主义是反现代化的,不信任新式教育,仇视近代文明,认为工业、理性主义原则决定了整个西方历史的悲惨前途,西方文化的原则为理智化,比起俄国文化的“虔诚思索”、“整合的理性”和道德完美主义等要低劣得多,俄罗斯精神就是被挑选出来用以拯救全人类的。〔28〕因此,拉夫列茨基更加保守、封闭,继而越发意志弱化,没有正视现实的思想和实现个人理想的信心。在守旧的贵族庄园环境里可以战胜西欧主义人士、赢得精神上也很保守的纯洁少女丽莎之爱,可是却没有力量解除与瓦尔瓦拉那种荒唐的婚约,没有信心和毅力把丽莎从传统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宁肯牺牲自己个人的爱情幸福、放弃对丽莎真诚之爱的责任并不顾她削发为修女的悲剧,也要以贵族知识分子的姿态去对传统文化观念负责。不仅如此,他还不肯改变贵族的生活方式、那套价值观念,要去当个好主人,结果不被新一代人认同,他甚至连自己也感到是被现代生活抛弃了的旧式人物。拉夫列茨基在婚恋上的无力自主、在生活上的无所作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悲剧“应当引起每一个读者对支配着我们整个生活的一整套观念及意义深刻思考”(杜勃罗留波夫语)〔29〕。由此可见,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用自己一生的悲剧事实昭示出:俄国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社会正准备大幅度转型之前就已经使贵族知识分子无法再崇高起来,消磨了他们促进社会进步的精英作用,甚至使他们不能适应正在到来的社会变革。
其次,超出贵族知识分子阶层,从正在变动的社会关系中体验处于社会转型急流中贵族知识分子精神变化及其文化意味。这方面的审美把握,作家分别从两个视角进行。一是通过叶琳娜(《前夜》,1859)这位正在觉醒的知识女性眼光来比较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知识分子,从而给后者下客观判断。在她看来,贵族青年舒宾和伯尔森涅夫都是才学不错、品行优良的知识分子,但无论是艺术追求还是学术理想都是他们作为贵族精英的产物,而且与他们作为贵族子弟的爱好、兴趣联系在一起,各自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社会转型的要求是根本不相符的,即使如此也会因贵族的那套教养和现实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而不能取得多大成就。至于他们对叶琳娜的单相思,那是作为有教养的贵族青年的一种通常选择,即在优秀的贵族知识女性中寻求感情寄托,因为他们谁都不真正理解她,不懂得如何使爱情变得有意义、崇高,面对“情敌”英莎罗夫谁都束手无策,对这种根本不存在的情爱互相还提防着,不能自己。如此平庸的事业和恋爱又伴随着强烈的哈姆莱特心理。因此,叶琳娜宁可冲破任何阻力也不去爱这种人,她跟着保加利亚的平民知识青年英莎罗夫远走高飞。二是通过基尔沙诺夫家的两兄弟尼古拉和巴威尔(《父与子》,1861)与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巴扎诺夫的面对面冲突,让他们给自己下结论。俄国外源性现代化的产儿巴扎罗夫,他没有接受过任何贵族的教养,成为知识分子过程中他信奉的是科学主义、实用价值观、理性原则,因而他嘲讽贵族温情主义,主张彻底破坏正统规则。对于这种来势汹涌的新文化冲击,俄国传统文化是无可匹敌的。因此,尼古拉对敌手要彻底否定俄国传统文化和贵族知识分子价值,则主动退让并开始怀疑起自己这类人的现代命运。而巴威尔却力图用贵族的那套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惯例当作民族精神,以维护民族精神的理由来对抗巴扎罗夫,很显然是要一败涂地的,因为即使民族精神,后者也主张用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来改造之。非常有意义的还在于:连生存依据都被论敌消解了,巴威尔还出于贵族的体面原则和巴扎罗夫决斗,而决斗的借口却是后者向长得像巴威尔旧日恋人的费涅奇卡(其实她是与尼古拉公开同居的女农奴)做出友善的举动。巴扎罗夫并未碍于贵族特权阶层而不敢决斗。决斗失败后;巴威尔便置国内贵族知识分子命运危机于不顾,去国外打发余生了。作家公开申言,他这部作品的倾向就是要反对把贵族作为先进阶级看待。舒宾、伯尔森涅夫与基尔萨诺夫兄弟等形象显示出,现代化一旦塑造出新人,在社会自觉变革的关键阶段,传统知识分子如果继续完全囿于历史积淀的价值观、生活原则,那么他们的结局将是悲剧性的。
最后,着重对贵族知识分子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本身的描述,间接体验出社会持续变革之后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当代意义。利托维诺夫(《烟》,1862—1867)作为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居然对60年代俄侨政治活动、上层显贵腐败堕落等社会热点提不起一点兴趣,而像一个小青年那样为某个事实上不存在的问题苦恼,即:是选择贵族少女的传统爱情,还是认同“现代”贵夫人的“开放”恋情。传统知识分子的旧伦理观并不能帮他抵挡肉欲、享乐的诱惑,他也根本认识不到贵夫人的“现代”标准不再是传统的忠贞、温情、信用等,而是随时随地转移感情。“我”(《彼尔耶斯之行》,1857)早在社会大变革到来之前就痛感大自然并不是一种崇高的美,在它面前人是不能审美的,而是感到人生渺小、软弱无力。社会大变革后,“我”(《幻景》,1855—1863)还发现农奴专制的皮鞭声照旧在伏尔加河两岸的大地上响着,而西方现代化带来的是卑俗不堪之景。这样,“我”就没必要和魔鬼爱丽斯博斗了,让它吸“我”的血好了,反正“人比苍蝇还不如”,活着也没前途,社会转型对“我”这种旧式知识分子没好处。要知道,“我”(《够了》, 1865)本来是对人生充满信心的, 因亲眼目睹到现实生活中还严重存在着两千年前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就讽刺过的各种卑污现象、几百年前莎士比亚就批判过的暴君式人物或哈姆莱特式人物,于是“我”觉得世界和人是没有希望的,还不如像其他贵族知识青年(《狗》,1866)那样以讲或听无聊故事打发时光,以论证荒谬命题发泄精力,活得轻松些。到了七八十年代,阿尔托夫(《死亡之后》,1883)这个贵族青年更加不关心现实社会、人生、事业和婚恋等基本问题,而是极度沉浸在个人幻想心境中,把早已死去了的女戏子克拉拉“小姐”当做活人来恋爱,彻底摒弃现世人生。诸如此类的现象表明,社会转型将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传统文化如果一直得不到现代文明的改造,那么它将会使传统知识分子生命力和精神越发地萎缩、作为社会公民的特征更加减少,继而加剧悲观、厌世等消极情绪。
作家通过对传统知识分子问题作历时的体验来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虽然涉及的时间跨度仅仅是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二三十年,但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他以艺术形象系列演变的方式,勾勒出了传统知识分子精神退化的过程,展现了他们的精英作用和意识沦丧的历程以及作为先进阶层退出历史舞台而逃避到幻想世界的趋势;同时,他还倡导用传统文化来保护俄国,使之强大而不西化。然而现代化有着自己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贵族阶级本身及其所热衷的那套价值观必然要贬值,同时伴随着非道德化现象的出现等问题。这样,他们在社会转型时期要遭受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的冲击,又要被传统文化束缚着不能适应或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这种历时体验与上文论及的共时体验相结合,就使得19世纪中叶前后的现代化对传统知识分子生存—精神状态发生作用的方式和结果很完整地呈现了出来,既描绘出个体知识分子心灵痛苦、意志弱化的实际状况,又描绘出整体知识分子命运变化、精神退化的历史性过程和发展趋势。而俄国19世纪中叶前后所推行的激进现代化对于后进现代化国家、俄国后来以及今天的改革都很有典型意义,贵族知识分子命运—精神的那种变化蕴含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因此,屠格涅夫对贵族知识分子的审美把握对我们现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如何改造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知识分子等问题是很有启示价值的。
注释:
〔1〕[苏]沃罗夫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239页。
〔2〕参见[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社会各阶层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
〔3〕参见[俄]彼得罗夫为《屠格涅夫12卷文集》写的《序言》, 见《屠格涅夫文集》第1卷,莫斯科,1953年。
〔4〕参见俄《文学评论》杂志1993年第11、12 期合刊中纪念屠格涅夫逝世110周年国际会议学术报告。
〔5〕[苏]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26页。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 页。
〔7〕同〔6〕,第123—124、137页,同时可参见Black,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1975.
〔8〕A.C.利哈乔夫《罗斯受洗和罗斯国家》, 载苏联《新世界》杂志1988年第6期。
〔9〕[俄]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 1988年,第101页。
〔10〕〔13〕〔14〕〔16〕〔17〕〔18〕〔20〕〔21〕〔22〕〔23〕〔26〕《屠格涅夫文集》,莫斯科,1956年,第12卷第217页、 第11卷第170页—174页、第3卷第376页、第5卷第431页和第1 卷第473 —474页、第5卷第455页、第6卷第367页、第6卷第368页、第6卷361页、第6卷第362页、第2卷第311页、第2卷313页。
〔11〕[苏]鲍戈斯洛夫斯基《屠格涅夫传》,莫斯科,1961年,第47—50页。
〔12〕〔27〕Charles Mos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on Litera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209—210,p.282.
〔15〕《英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5年,第321—322页。
〔19〕《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2),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7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18页。
〔25〕Barbara Heldt,Terrible Perfection,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20.
〔28〕[美]艾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68页。
〔29〕《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第2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