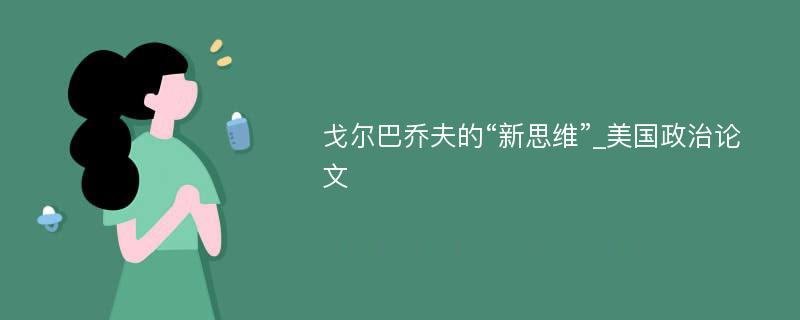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新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5年前,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当权派发动了三条战线的变革,试图改变苏联的制度 。在经济战线,他实施了一系列重组,试图改变低效率状况和僵化的行政结构,但没有 根本触及国有经济。像所有折衷方案一样,改革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导致了经济崩溃 。在政治战线,他引入了开放政策,目的是消除已经成为经济改革严重障碍的国家和党 的影响。政治改革较为成功,但同时也释放了反对派的力量,最终导致戈氏的下台。
第三条战线的改革最终证明是拯救苏联的措施中影响最深远、最持久的改革。作为国 内经济和政治改革紧迫需要的辅助支持手段而提出的“新思维”,在结束冷战、统一德 国中起了重大作用,为戈氏赢得了历史地位和国际声誉。
苏联解体已历时10年,现在来评估“新思维”与“新思维”者在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国 际事务中的作用正当其时。他们的改革观念进展如何?后苏联10年的经验使他们对全球 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安全这类观念如何作重新评估?
“新思维”者本身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没有几个人留在权力中心,大多数人在苏联科学 院各部门以及各政策机构担任高级研究员。然而他们所取得的巨大历史作用,只有美国 智囊团和大学研究人员才能充分感受到。如今,“新思维”者已不复往日的显赫,他们 仅仅是俄罗斯混乱的政治世界中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激烈竞争中的一种声音 而已。
“新思维”的起源、实质与作用
“新思维”出现于80年代,但其根源深深扎在苏联过去的历史中。1956年赫鲁晓夫对 斯大林罪行的公布,说明共产党年轻一代试图改变社会主义观念。古巴导弹危机后,赫 鲁晓夫推行共同利益观念来避免全球的核战争。1964年他下台后,新领导抛弃了这一观 念。戈氏在回忆录中写道,对苏联国内和国际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盘踞在共产党各级年 轻领导人的脑海中,1968年苏联对捷克的镇压强化了这一思考。70年代,年轻的苏联学 者开始与美国和欧洲的科学家取得联系,他们都主张军备控制和缓解对抗的观念。
这批年轻领导层的存在,以及他们接受军备控制和安全合作的观念,是“新思维”产 生的必要条件。观念固然重要,但只有观念是不够的。观念必须受到政治领导的有力支 持。苏维埃制度本身的性质使“新思维”及其鼓吹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思维”有三个核心观念推翻了支撑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理论。其一,“新思 维”否定了这个观念,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本质上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 ,一方的存在对另一方的安全和繁荣构成基本威胁。1987年,普里马科夫在《真理报》 发表了“对外政策新理念”的文章,对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提出质疑。“新思维”者认为 ,人类的共同利益比阶级利益更为基本和紧迫,尤其是避免核战争所产生的共同利益。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的联合国演讲中,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在东欧强行推行社会主义的理 论,主张“选择自由”。
其二,“新思维”对军事力量的均衡是安全的必要条件这一观念发起挑战。“美国加 拿大研究所”的学者们提出了“合理足够”和“自卫性防御”等观念,认为苏联不需要 部署大量武器和维持400万军队来保护自己。安德烈·科科申(Andrei Kokosh.n,后来 成为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撰文主张在欧洲实行非进攻性防御,苏联单方面削减核武器 和常规军。维塔利·茹尔金(Vitaly Zhurkin)、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ksei Arbat ov)等人的努力使“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成为国防问题研究中心,而“世界经济和国际 关系研究所”则从理论上对列宁主义对外政策提出质疑。
最后,“新思维”拥护者否定了军事力量的目的是打败苏联的敌人这样一种假设。他 们害怕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认为军队的目的必须是防止冲突和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 。这个观点使“新思维”者与西方学者在主张安全合作和共同防止战争的国际讨论会上 有了共同语言。
尽管“新思维”者要依靠政治支持才能使其观念影响苏联的政策,但这些观念本身对 苏联政策的巨大作用却不容置疑。戈氏在1987年取消了与其军事理念不相称的核武器, 并从1988年开始,单方面削减了50万驻欧军队。接着苏联承认在阿富汗的失败,撤回了 全部军队。戈氏任苏联总统期间,没有干预改革派政府在匈牙利和波兰的上台。1990年 ,苏联与西方不仅协商解决了德国统一问题,而且签署了欧洲常规军协议和新的欧洲宪 章,宣布结束欧洲大陆的分裂。虽然一年后苏联解体了,但冷战在1990年基本结束,这 主要是因为戈氏执行了“新思维”政策,这与他的不成功的经济政治改革政策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新思维”遭遇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
“新思维”在结束冷战上获得了胜利,看来它也会形成俄罗斯冷战后的对外政策。叶 利钦总统和外长科济列夫(Kozyrev)都是“新思维”的赞同者。科济列夫明确认为与西 方存在强大的共同利益,他主张与西方进行合作。叶利钦政府重视与西方的合作,以便 获得财政支持,争取成为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成员。许多人认为,“新思维”关于共同 安全与人类价值观的理念将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础。
然而有一些因素干扰了这一进程。首先,不同的观点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对科济列夫的 主张提出了挑战。这表明俄罗斯政治中的多元民主化取得积极进展,但也意味着合作理 念将与其他利益集团和残留的苏联各机构进行竞争。共产党重新复苏,在没有财力参与 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经济和社会部门中找到了当然的支持者。民族主义派别找到了自己的 领袖: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Zhirinovsky)。
第二,“新思维”主要是一种观念形态,并不是一套实际政策纲领。它的主要人物是 知识分子,并非外交政策专家。这种状况在戈氏向列宁主义世界观发起挑战时非常有用 ,但在俄罗斯外交政策遇到划分军队资产和参加世贸组织条款的谈判时就不够用了。俄 罗斯需要的是能保护并平衡新社会中涌现的各种利益集团的专家,而不是理论家。
第三,国际系统并没有通过非军事合作方式来响应“新思维”关于共同利益和安全的 理念。俄罗斯诞生第一年,周边国家军事冲突不断。俄罗斯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面临着 地缘政治的挑战,这些国家经济衰弱,政治狭隘。当人们认识到俄罗斯政治体系严重分 裂,许多人并不愿意看到苏联衰退时,俄罗斯应付挑战的能力只能是黔驴技穷。
对科济列夫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批评者就是戈氏集团的主要成员普里马科夫。他反对科 济列夫的西方中心论,认为俄罗斯的利益在欧亚两大洲。他认为俄罗斯不能完全接受西 方的价值观念,因为俄罗斯扎根在欧亚两大洲,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和历史条件。俄罗 斯的欧亚特质造成它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国内和周边关系紧张 的根源。简言之,俄罗斯的利益与价值观与欧美社会具有本质的区别。根据欧亚论观点 ,俄罗斯的主要利益在于多极国际关系,这种关系能限制美国的权力,因为俄罗斯的利 益与美国的利益并不一致。
“新思维”虽然推翻了列宁主义,但并没有解决现实问题,即以权力与国家利益为基 础的国际关系问题。利益冲突与权力争夺是国与国关系的特征。普里马科夫提出俄罗斯 国家利益观念、批评科济列夫为获得西方承认而牺牲国家利益的理论,这在“新思维” 者中并非绝无仅有。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巴托夫,外交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卡拉 加诺夫(Karaganov),都认为俄罗斯必须明确自己的国家利益,叶利钦政府必须使政策 以国内选民为根基,才能获得可靠有效的对外关系。与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相比, “新思维”者并不认为俄罗斯国家利益必然与西方产生冲突。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俄罗 斯不明确界定自己的利益,就无法与西方进行安全合作。这是他们的政策重点。
“新思维”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俄罗斯抛弃苏联意识形态后,与美国的关系没有预 想的那么顺利。军备控制已不再具有紧迫性,协商重点已经从最高级会谈转移到如何防 止俄罗斯的核武器落到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手中了。
预期中的西方援助并没有兑现,俄罗斯经济继续恶化。更糟的是,许多俄罗斯人都认 为,西方的帮助不但不够,而且他们的对俄政策进一步破坏了俄罗斯经济,将人民抛向 了深渊。早在1993年12月事态就已感到了激烈的反应,那时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 俄罗斯大选中获得实质性多数。倾向“新思维”的资深记者阿列克谢·普希科夫(Aleks ei Pushkov)感叹道:“密月已经结束。”
科济列夫对“新思维”观念的发展遭到了失败。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其他“新思维” 者与欧亚主义者进行了合作,他们都主张要明确表述俄罗斯利益,要与美国权力取得平 衡。合作依然需要,但调子放低了,把合作看作是手段,是就事论事的解决方案。叶利 钦接受了北约的扩张,签署了“北约俄罗斯建设法案”,试图参与北约的发展。普里马 科夫成为俄罗斯外长,开始致力于发展与前苏联各国、中国和伊朗的关系。
“新思维”面对同西方的关系问题
90年代中期,“新思维”的共同利益观念受到怀疑,但相互依赖与非军事安全理念依 然在俄罗斯对外政策部门中具有影响。普里马科夫寻求多极地缘政治,目的在于取得与 美国和主要大国相同的合理地位。叶利钦没有完成西方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设定的标准 ,但为了继续获得西方的金融支持,俄罗斯开放了金融市场和货币。
199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卢布贬值,暴露了相互依赖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俄罗斯 参与西方经济似乎就是为了遭受摧残。“新思维”经济学家奥列格·博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早在80年代末就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质疑,呼吁通过参与西方经 济来促进发展。2000年,他撰文谴责“华盛顿共识”。要求限制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和7 国集团的影响,对俄罗斯为加入世贸组织而自我改变提出警告,从而代替了反对改革的 观点,成为稳健的中间派观念。
科索沃事件粉碎了“新思维”合作安全观的最后堡垒。一直在寻求合作和西方化的“ 新思维”者现在面临着日益明显的俄罗斯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和欧亚主义。他们认为科 索沃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他们现在认识到北约在冷战后的发展是非良性的,对俄罗 斯形成了军事威胁。阿尔巴托夫说道:“突然之间,第三次世界大战……非常现实地迫 在眉睫了,……冷战的本能又复活了。”
现在是杜马成员的科科申认为科索沃冲突是“北约对南斯拉夫的侵略”。现在担任“ 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的务实的“新思维”欧洲主义者卡拉加诺夫说道,北约的行动“试 图把世界倒退到上一个世纪去,倒退到60、70年代去,那时对抗和军事实力最有发言权 。”
西方媒体和官员把俄罗斯的激烈反应看作是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古老的斯拉夫关 系的体现。科索沃事件对俄罗斯的真正影响,是使“新思维”者最终放弃了安全合作理 念。阿尔巴托夫在指责俄罗斯本身工作失败的同时说道,“美国没有正确理解最重要的 问题;美国本应就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协商,例如地区安全、恐怖主义、防止极端 民族主义的安全措施、加强联合国力量的机制、如何在欧洲和亚洲创建和平与安全地区 组织等问题。”
使美国失望的一个结果就是使俄罗斯把希望重新放在了欧洲,不仅像卡拉加诺夫这样 的欧洲主义者,而且像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之类美国主义者和科科申也 持这种观点。其他人则寻求制定一种自由主义的多极政策,例如,“世界经济和国际关 系研究所”前副所长布拉戈沃林(Blagovolin)就曾主张俄罗斯与欧洲和日本合作,作为 发展地缘政治的实现手段。科科申和阿尔巴托夫则积极从事军备控制,尤其致力于谋求 导弹防御系统的妥协方案。
科索沃事件引起的另一个激烈反应,就是“新思维”者拒绝接受西方对车臣问题的观 点。科科申认为“处理与车臣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问题属于俄罗斯的主权”,这 表明普京总统的政策唤起了很大的共识。我曾与“新思维”主要人物共同参加了几次会 议,发现在科索沃和车臣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学者的分歧简直有天壤之别。就像我们 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似的。
“9·11”事件后,“新思维”是否获得了新生?
好几年来,俄罗斯官员一直把恐怖主义看作是对俄罗斯形成主要威胁的因素之一。这 种威胁的表现之一就是车臣,车臣与本·拉登的基地有联系,其联络网涉及好几个与俄 罗斯作对的集团。另外还表现在中亚地区,在阿富汗国界内外活动的本·拉丹恐怖分子 与其他恐怖组织威胁着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造成局势的不稳定 ,引起俄罗斯极大关注。“9·11”事件前,俄罗斯与美国已经着手开始合作,合作内 容包括打击为许多恐怖网络的跨国活动提供资金的毒品交易,以便阻止恐怖网络自由行 动。尽管这种合作很有前途,但90年代两国间形成的差距,加上导弹防御体系、北约的 行为和车臣事件所引发的紧张关系,致使合作蒙上了阴影。
从表面上看,“9·11”事件改变了两国间麻烦不断的关系。美国媒体报道了普京如何 使俄罗斯加入了反恐联盟的消息,但在俄罗斯看来,是美国终于承认了反对国际恐怖主 义是目前的头等大事这个现实。普京否定了俄罗斯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他们反对与美国 进行合作,担心美国渗入俄罗斯和欧亚地区会取代俄罗斯的影响。普京明确拒绝了这种 担心背后的竞争性的地缘政治零和思维,他赞成加入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反恐联盟。
普京的选择与两年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发展是相一致的。普京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欧洲 非常活跃,并取得了成功,获得了贸易、能源开发和参加欧洲联盟等协议。普京的政策 扎根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需要上,其重点建立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控制这一基础上。他谋 求欧亚地缘政治与国际经济整合之间的平衡关系,解决了俄罗斯在两方面的国家利益问 题,一个方面是欧亚稳定及其影响,另一个是发展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经济门类,例 如能源,金属和常规武器。为此目的,俄罗斯与中国、伊朗、印度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 建立了关系。
从俄罗斯政府对“9·11”事件的反应来看,很明显,俄罗斯的政策混合了“新思维” 、全球主义、欧亚现实主义和欧洲—大西洋经济国际主义等各种观点。合作与分歧都存 在很大的余地,因为美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具有共同性,但不是等同的。分歧将继续存在 ,例如关于车臣问题、俄罗斯在欧亚的影响问题、俄罗斯与伊朗和中国的关系问题等。 俄罗斯也担心,美国在中亚和中东毫无节制的反恐战争会加剧不稳定局面。戈尔巴乔夫 赞成美国在阿富汗对恐怖分子进行打击,但反对美国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切尔纳耶夫认 为“9·11”事件“彻底结束了残余的冷战因素”,有希望使美国开始重视俄罗斯的力 量和统一。但他也警告说,不要觉得“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来规定世界秩序,有权对 别国施舍稳定和幸福”,比如对科索沃和阿富汗。
虽然这种变化产生了一种比“新思维”更复杂的关系,但它有利于美国的政策。俄罗 斯在反恐方面合作的根源在于关于国家利益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受到俄罗斯社会中重 要部门和机构的支持。这个观念虽然取决于俄罗斯领导人,但它比“新思维”在90年代 初所表述的观念更有生命力,因为它符合俄罗斯国际和国内的现实。例如,如果俄罗斯 设法联合北约与恐怖主义作战,那么它的政策就扎根于全国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会受到 俄罗斯企业和政治机构中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这个政策并不像“新思维”有时候那 样为合作而合作,而是一种深深理解了自身利益的合作。
“9·11”事件后,俄罗斯与美国合作的新基础并不是由于“新思维”者及其观念发生 了什么影响,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新思维”梦寐以求的基本安全合作很 可能会实现,但这是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自身利益与实用主义选择,并不是“新思维” 发展的结果。这种似是而非无疑是历史的一种讽刺。
[美]塞莱斯特·A·华兰德(Celeste A.Wallander)
选自美国《华盛顿季刊》2002年冬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