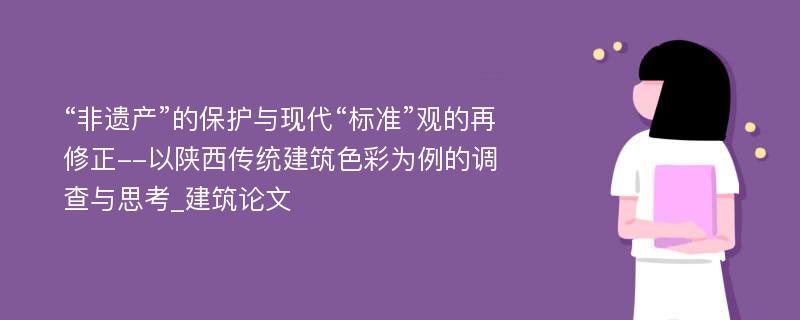
“非遗”保护与现代“规范”观之再校正——以陕西传统建筑彩作为例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西论文,为例论文,观之论文,传统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U-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1)05-0103-07
“彩作”一般指在木质或其他材料的建筑构件上运用彩色涂科进行装饰和防腐处理,这种工艺技术与知识体系是中国古典建筑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表征。
中国传统建筑彩作在以往历史上的生存状态,可以引用一句话来概说:“彩画在历史上是不存在保护问题的,一代新彩画出现了,老彩画自然被取代,这就构成了彩画自然演变的过程。”[1]针对以往的“自然演变”状态,1934年,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提出:
彩画 修理古物之原则,在美术上,以保存原有外观为第一要义。故未修理各部之彩画,均宜仍旧,不事更新。其新补梁,柱,椽,檩,雀替,门窗,天花板等,所绘彩画花纹色彩,俱应仿古,使其与旧有者一致。[2]
1935年,梁思成进一步阐述意见说:
我们今日所处的地位,与二千年以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以往的重修,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破敝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却不同了,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于是这问题也就复杂多了。”[3]
作为一代大师,他这个意见是高屋建瓴的。但作为新学术代表人的梁思成和他中国营造学社的诸位同人,在20世纪前期起步学习整理建筑彩作的国故时,筚路蓝缕、多费周折,很自然地是“以《清工程做法则例》为课本,以(北平尚有曾在清宫营造过的老师)匠师们为老师,以北京清故宫为标本,清代建筑之营造方法及其则例的研究才开始有了把握。以实测的宋辽遗物与《宋营造法式》相比较,宋代之做法名称亦逐渐明瞭了。”所以,梁思成先生一直称这两本书是整个“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4]
就当时中国情势而论,梁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所做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价值和重要示范意义的。但在“非遗”保护的新视角下我们察觉到一个值得重新反思的迹象:20世纪50年代中期,主要立足于整理“清代官式”而辑成的一套大型建筑彩作图谱,由国家主管部门出版发行后,就被作为整个中国古典建筑彩作的施工范本而加以推行,在不少地方,给这套“正规化”范式之外的各地方传统彩作样式造成持续半个世纪的压迫、打击,使它们几乎陷于没顶之灾。人类的社会生产中,“式”是必然地也是自然地以多支派、多样化的面貌存在;现实生活中不同境遇下产生的各种“式”都具有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与应有边界;不同的“式”对于全人类乃至每一民族文化生态的完整协调都具有互相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弄通了一种“课本”、掌握了一种语言的“文法和辞汇”,还应当以此作参照借鉴,进而虚心平等地研究别种语言的“文法和辞汇”。而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建筑和建筑彩作,其艺术语言都有它更深层次的文化目标和文化布局属性,某一种“式”,哪怕是何等高超的“式”,一旦超越了自己文化目标和文化布局的适可边界变为绝对化的“正规”标准,就会遏制下层文化活力,造成大面积“土壤板结”,引发文化的“生态灾难”。
“规范化”是以超大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所极力标榜的理念,它常意味着商品衡量与制造的标准惟一化,以满足机械化、自动化和超大批量的生产与流通。这种经济活动的准则会向人的情感、习俗和文化艺术的领域侵蚀蔓延吗?当前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濒危的现状,从根本上说跟此种经济活动趋势及社会理念取向有关。近5年来因介入陕西传统建筑彩作样式保护课题,从调查实践中获得的一些体验,真切地唤醒了我的这一认识。
问题的最初触发点在“陕北匠艺丹青”的调查途中。“陕北匠艺丹青”是自2004年起由我领队实地考察和主持申报,先后进入了陕西省人民政府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国务院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地方性传统手工技艺。该项考察展开的第二年夏天,我们就“撞”上了其中传统“榆林式”建筑彩作的一则保护难题……在榆阳城老街一座古代跨街楼的重建工程中,以任今民为首的当地画匠抵制省建筑设计院“清代官式”的彩画设计,脱图施工,画上了榆林本地的传统花式。从现行建筑工程管理制度而言,这些画匠是“胆大妄为”、“以下犯上”的,但从更高更宽的文化层面看,他们的“反叛”却无疑是合理和正当的。就从这一“文化冲突”现象扎进去,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高晓黎系统地对以榆林市为重心的陕北地区传统建筑彩作遗迹展开艰苦深入的调查,写成毕业论文《传统建筑彩作中的榆林式》并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该文阐述并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榆林式”建筑彩作具有古老的历史传承源流,特别在近三四百年里,尤其活跃在陕北土地上;它在相对封闭的边塞文化环境中比较独立自主地传承和发育成一种当地生活与艺术的纽带,在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载体上,卓有成效地进行建筑的内外装饰,演变出自身富于创造性的技艺面貌。
“榆林式”建筑彩作保持了较多明代的传统特色,构件组合灵活多样,色彩搭配绚丽多变,布局构图丰富饱满,图案设计既包含以青绿色调为主的旋子(“狗爪子”)花,又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性图案。同时,它在彩画中很注意综合调动雕塑、髹饰、绘画、装置等手法,生活气息清新,艺术气质往往显得生动鲜活;在吸收消化外地(主要是中原)彩画格式和经验的同时,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其表征形式切合着自身背后的地理、历史、经济技术条件及文化生态环境,在我国传统建筑彩作范畴内发展形成为一支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彩作样式。[5]
更简要点讲,传统“榆林式”建筑彩作的特色就在于它鲜明的草根性和自由活泼的创造力。其遗迹广泛存在于当地世俗生活建筑和宗教庙宇两大类建筑物上,诉说着它们不可替代的功用。譬如乡间的龙王庙,因为是掌管风雨决定庄稼收成的神灵,人们在龙王庙殿的外檐上常会创造一个人寿年丰、鸟语花香,神仙为之奏乐的美境;娘娘主管人间生儿育女事,在娘娘庙殿的檐子花里,“凤穿牡丹”、“鹭鸶鹐莲”、“鹊儿踏梅”、“麒麟送子”等喜气欢快的传统纹式往往雕绘得十分经心;这些庙檐的斗拱眼位置,往往塑造有一组组鲜美的果品,表达乡民一片心意。当你把它们同庙里壁画下端百十年间留下的“祈雨”墨书题记或墙上村民还愿送来的彩旗镜匾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认识这类建筑彩作的文化内涵;这种处理范式在官式彩作里当然是难以想象的。
历代的自然损毁与20世纪中叶的社会性大破坏对“榆林式”建筑彩作这项文化遗产造成了巨大损害,而新时期以来它所遭到的损害并不稍轻。这些新的损害经察有以下几类:
1.由地方文物部门管理的 如榆林市米脂县盘龙山上初建于明代的真武祖师庙(今人更喜命之“李自成行宫”,实则并未被李自成使用过),是陕北现存一组较完整的古建筑,是专设的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省文物界专家曾称赞:“这儿的殿宇楼阁,不但规模宏敞,而且建筑坚实。所有房屋,完全是用松柏木材和花琉璃砖瓦修成的,所有的梁栋门窗以至重檐层薨,或是玲珑剔透的雕刻,或是五彩缤纷的绘画,游龙、翔凤、飞禽、走兽、古木、怪石、奇花、异草、应有尽有,样样都使你感到神情栩栩,姿态婆娑,人们看后,都会叹服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真是心灵手巧,妙夺天工!”[6]自2005年起,当地历经两年耗资200万元将这里原有的彩画全部改造过了,2008年6月,我们看到这里的建筑彩画已焕然一新变成清代官式,无论从布局构图还是设色雕饰上已经不再有刘斌先生当年描述的那种生动感人的艺术气息了。文管所的申辩似乎蛮有道理:“李自成是坐过皇上的人,他的行宫当然得有官府的样子嘛!”但是,一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古窟寺……,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怎么能不把地方风格的彩画当成是一种文化遗产,是文物不可分割不能改变的原状一部分?二则对被满清剿杀的农民英雄李自成,怎么能用他死后近百年才定出、又200来年后才传入陕北的“清代官式”来“正规化”其门庭装饰?这种所谓的“文物保护”事实上成了无知掌权者个人心意的发挥,如此造成了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对传统文化遗迹的破坏,也是对国家文物保护原则的漠视。
2.由民间庙会管理的 在地旷人稀的陕北,不少庙宇是由乡民集体营造、由群众推选会首组成庙会,相当大程度上是民主治理的。但它们越来越受到主流社会意识的影响。这些庙宇中不乏历代民间丹青高手的杰作。考察中屡屡听到“四清”、“文革”那时乡民顶着“封建迷信”和“反革命”的帽子,自发地用封屋、堵路、涂泥刷粉或转移埋藏等方法保全庙里宗教艺术文物的感人故事。也是在这里,新时期以来农民经济宽裕了,于是翻新神庙风气大盛,不少老庙被翻造得“焕然一新”(如元代砌石墙壁被裹上水泥镶上瓷片,许多老戏楼被拆去,好些精彩的旧壁画聘当代新画匠拙笔重妆重描,或者干脆铲掉墙皮改画),至于古老建筑上彩画的被“刷新”,更是首当其冲的事。
20世纪90年代起,延安市宝塔区姚店的青化寺在山上陆续修建新庙院,2010年3月来到山上看到,其中1995年之前建成的山门、娘娘庙,建筑彩作尚保留着形式变化丰富、乡土情趣浓郁的陕北地方风味,而2000年以后竣工的钟鼓楼和几所殿宇,檐下却整列整列地重复着清代官式“龙和玺”彩画纹带,奢华的大面积金色取代了往昔倚重色彩变换组成的绚丽效果。更出人意外的是,庙里会长并不赞同我们说的地方传统文化,坚决认为“这才是正规佛教庙宇,我们就是照正规化的样式来的!”①
3.来自施工画匠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结束后,乡村宗教生活刚回归正常化时,应运复出的那些老画匠比较熟悉早先陕北地方的老样式,同时也较多记忆着老式施工相伴的宗教仪程;那个时段由这些人领工整修的庙宇彩作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榆林式”传统特色,这些彩作因此对下一代新手曾发挥过传统样式的“示范”作用。随后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信息交流加快、思想观念改变,许多地方都产生出这样的景观:同一座庙院里,当年由老画匠修缮甚或是新造的庙殿上,建筑彩作在古朴淳厚中闪现着华美细巧,内容丰富十分耐看;而近十年来由第三代青年画匠包揽施工的一些庙殿上,便明显出现几个倾向:其一是对“清代官式”(主要是其中的龙、凤和玺式)图案的生搬滥用,其二是纹式简单化、重复化,其三就是色彩上的大量用金。这些倾向其实内部是具有一致性的,那就是顺应主流社会的“正规化”心理和向施工速度要效益的经济驱动力。
2008年7月,在榆阳临近佳县的龙岩寺,庙院南端高大的乐楼彩画刚完工,青绿调子倒是非常明艳,但图案显然搬自书本上的“清代官式”,脱离了传统“榆林式”图案对具体建筑功能的针对性,缺失了欢快热闹的生动性。年轻画匠就在一旁,自我感觉良好。问他们图样从哪儿来的,先搪塞说是自己凭想象画的,一番交谈后,他们便不好意思地掏出了从图书上复印下来用作参照的画页。对我们评价其艺术价值远逊于老画匠留下的民间样式、以及劝他们多留意学习本土传统的建议,他们并不理解。
横山县波罗镇的接引寺,是号称有千余年历史的古刹[8];2010年7月25日在此地看到,新增修的高大山门及一些殿宇包括娘娘庙,前后檐均采用了清代官式金龙和玺彩画,一些较古旧的庙殿建筑也大部分以清代官式改画过了,图式内容显得单调空洞。下山磴道上,我拦住似是匠人的过客探问:这里原有的建筑彩画样式上哪儿去了?佛爷庙为啥要改成北京紫禁城里的彩画?有一千几百年历史的老庙为啥要用那只有二百来年历史[9]的彩画样式?答曰:“那都是有正规样子的,照书上来的。”4天后在神木县花石崖乡阳崖村弥勒寺改建工地上,再次询问正在作梁架彩画的一家匠人:知道榆林彩画有老样式不?当初学手时候照什么作、现在靠什么样子画?老汉支支吾吾不肯细讲,年轻的儿子却爽快地隔着架板向下伸出双手,张开封皮让我看——赫然一本《中国建筑彩画图集》②。
书啊书!成事在书坏事也在书。时代变了,年轻画匠们不再满足于跟着前辈师傅下长期“默会”的功夫而求助“正规”书籍,想“照葫芦画瓢”好“热蒸现卖”。就一般情况言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惜我们处在的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知识地位不对称、话语权力不对称的社会环境中,这种通过主流渠道的求助就引出了很多大麻烦,引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要靠和“正规”的“书”作斗争的悲剧。
2010年正月里,一次偶然的聚会上与一位相违近30年的老友——苏东亚不期而遇,1945年生于周至县,少时与本县民间画匠亲近,青年时入县文化馆工作,“文革”结束调到楼观台文管所,从那时开始专做古建彩绘工程。先后领工做了兴平杨贵妃墓献殿、三原县城隍庙、汉中市博物馆、武侯祠、澄县乐楼等文物保护单位的彩画工程;1982年调到咸阳市文化局筹建市古建艺术公司,半年后辞职,承包宁夏贺兰山游览区古建彩画及彩塑工程;以后又长期居住在新疆,边搞美术创作边承揽建筑彩作工程。这次会面中问起他所了解的关中地区传统建筑彩画的遗存情况,他讲述了自己在楼观台起步做古建彩画时的经历:好不容易找到当时陕西省文管会负责古建的刘最长先生,并在那里看到了1957年精印出版的一套关于中国古建彩画的图片资料,求得允许后赶快组织人力连续加班两天两夜将这套资料临摹了下来,这就是他们以后长期工作的标准样式,这样才取得了官方认可的施工“资质”。遵照这种官方指定的图谱施工,接受官方管理部门的审检验收,你画匠们顺从不顺从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3月份开学后我带着学生专程去找他再做访谈,也简要介绍了近几年我们对陕北“榆林式”彩作所做的调查工作。他再次说到近几十年里领工修复关中地区许多古典建筑上的彩画,都是照着国家文物总局20世纪50年代颁布的建筑彩画规范,将当时尚能看到踪迹的古老花样一一涂盖刷新……沉吟间他突然冒出一句喟叹:“唉,我觉得自己简直是在犯罪!”这位老友是个实诚人,一旦有了新的觉悟便会不加掩饰地表露,他的话令我怦然心动也教我肃然起敬。他说:那就是“一言堂”!还说自己近些年在新疆的“陕西清真寺”③施工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已拍下了一些旧枋梁上尚隐约可辨识的老花子照片,有生之年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也要出一本书,做自己人生的弥补!
画师苏东亚讲述的这种事态,我是有所预知的。早在2003年,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学生王娜就对长安县古建工程队(公司)做过采访,结果问明白了,他们50年代中期承担修缮古城西安的钟、鼓楼时,即是按照文管部门提供的印刷图片来做的清代官式彩画。这就是说,近十年来在陕北凸现出来的地方彩画文化遗产的生存危机,在比较“先进”的关中地区已经浸蔓半个世纪了!4年前抢救性保护“榆林式”彩画的考察课题,就是以关中老彩画已无法抢救、陕北地方彩画不能再坐以待毙的紧迫心情确定下来的。应当感谢“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潮的推动,传统建筑彩画中的“榆林式”如今有幸能传存下来了,而陕西关中地带传统地方彩画遗产到底还有没有抢救下来的可能呢?关中地区受“进步”与“革命”的扫荡甚烈,据我所知,大多数史上有名、规模宏大的古建筑如长安王曲一十三省总城隍庙、眉县湫池宋建太白庙、周至楼观台附近元代的宗圣宫等,早就被拆毁了;抢救这里的传统地方彩画,希望太渺茫,也许只能作一场梦想吧。2010年8月,在秦岭五台山脚下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内,我看到了该院自渭北一带移来的一批明、清建筑,包括私家宅邸、戏台、乡镇城门和一座庙宇,因为近些年里高速公路修建到了僻远山村,它们都是挡了路而必须拆掉,由王勇超先生主持的民营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斥资收购迁建过来的。真有点“因祸得福”的意思啊,在这里我终于亲眼看到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传统“关中式”彩作遗迹,包括门头、窗户和檐下的斗拱、枋、檩、雀替,以及廊下与室内的木构梁架等彩作。虽然出于吸引旅游客源的动机,现已复建完工的这批建筑不少地方的彩画不科学地经过了重描新妆,对历史原貌有不少干扰乃至破坏,但仔细察看下来,就总体布局、纹样刻划、大致色调而言,仍可明确显示渭北一带传统建筑彩画,在构图、花式及处理手法上不雷同于北京的清代官式,有别于黄河东边的晋中模样,相异于更东南方面的徽式、苏式,也不全像陕北榆林式,而具有关中彩画的独特风貌。一座中庭院门前檐下,最突出最华美的主题纹饰不在绦环板而在兼作“满堂花门”的下枋上,那些硕大饱满的牡丹花朵之间穿插着刻绘夏收劳动场景的几组彩妆木雕,生活气息浓郁、处理手法样生动从容。那是素来以农为本的关中才能有的;所谓本土独特的历史内涵、情感习惯和既成的匠艺表现体系,从这里扑面而出。站在这里,我再次领会到这块厚土上传统文化积淀的深沉性;转而想象“西府”④一带同类遗存残留的可能性,心中的宿念忽然又被挑动了起来——关中传统地方彩画样式体系,莫非还有死里逃生的一线机会?
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其核心词汇即是“多样性”。《公约》坚持的思想原则对于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国际间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合作具有积极意义。“多样化”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往往呈现出“细分化”的特征,同样是建筑彩作,不同自然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功能用途,总之是不同生态条件下的不同文化布局,使得建筑彩作的内容和形式风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分化,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技术体系,也自然地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法式规范。
现代学术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探索、前后接力的过程。20世纪中国的学术进程中确实存在缺环,有值得反思改进之处。张昕博士在她的学位论文中已经很谨慎地批评到:“事实上,早在修葺曲阜孔庙之时,梁思成就已提出‘新修殿宇之彩画恶劣者宜重画’的观点。蒋广全和马炳坚更重申了油饰彩画工程‘确立设计制度’对传统建筑的保护与继承,以及对施工单位的管理等方面的必要性。但官式彩画毕竟适用范围有限,若随意施之于地方建筑,反而会缩小风土彩画的生存空间,乃至使地方风格丧夫殆尽。”[7]身为建筑学“圈子”里“后生”辈的张昕能讲出这样的意见,其勇气真是难能可贵的!
胸怀“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高志的梁思成先生,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何以提出“新修殿宇之彩画恶劣者宜重画”(还有“石柱上之油漆彩画宜洗去”)的“原则”?这件事可能确实是“问题颇复杂”[8]的。后来在1964年发表于《文物》第7期的《闲话文物建筑的重新与维护》一文中,梁先生也曾坦承:“我们完全知道,我们还是有不少缺点的。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还缺乏成熟的经验。”他还具体地说到:
古来无数建筑物的重修碑记都以“焕然一新”这样的形容词来描绘重修的效果,这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至于木结构上的油饰彩画,除了保护木材,需要更新外,还因剥脱部分,若只片片补画,将更显寒伧。若补画部分模仿原有部分的古香古色,不出数载,则新补部分便成漆黑一团。大自然对于油漆颜色的化学、物理作用是难以在巨大的建筑物上摹拟仿制的。因此,重修的结果就必然是焕然一新了。“七七”事变以前,我曾跟随杨廷宝老先生在北京试做过少量的修缮工作,当时就琢磨过这个问题,最后还是采取了“焕然一新”的老办法。这已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但直至今天,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9]
这样一种矛盾心态,刨过物质技术上的时代局限外,背后的最大心理障碍还是国人对历史文物古迹“古为今用”的惯性势力。最可惜的是这种技术知识不足的时代条件下宁要“焕然一新”不要“寒伧”的选择,往往将一些本该挖掘保存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匆匆忙忙之间不可追回地消除,以某种强势的“文法”给“格式化”了。至于在油饰彩画工程中“确立设计制度”一事,我以为问题就更复杂了,其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有设计和设计制度,问题关键在于那些掌控了主导权的设计家、设计主管机关和设计管理制度……他们所奉行的“传统建筑的保护与继承”中有没有“多样性”的文化理念?占取强势地位后的他们还有没有前辈大师“我们还是有不少缺点的”、“还缺乏成熟的经验”的坦诚胸怀谦虚学风?这种“对施工单位的管理等方面”集中强化的“制度”,是运用现代社会赋予的公权力,凭借抱残守缺而自命不凡的“课本”知识,来排斥、压制不同的文化流派、剥夺民间匠工的设计参与权、推行“一言堂”搞设计擅权,还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尊重地方经验?
过多的意识形态纠葛和褊狭的“制度”框架共同迟滞了我们学科发展的步子,也促成了褊狭扭曲的“规范”观被“制度”化的现实。与50年代中期以来出自专制帝廷的“清代官式”“规范”在“文物保护”旗帜下横扫各地的情势相伴,我们建筑学术界曾过久徘徊踟蹰在“清代官式”圈子里,即使不说是辗转抄袭,也是因循守制少有开拓,对祖国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各种地方彩作资源的考察探索用功太少。最近十来年这种学术土壤“板结”的形势已经松动,但从已经出版的对一些地方性彩作样例有限的辑录看,旅游式的掠影或“唯美”性多而学术考察功夫常常缺位,所介绍的样例中缺少翔实辨识,甚至混杂着晚近清代官式的新作彩画;因此可以说已往积重难返的学术形势尚没有根本扭转,“规范”观的再校正尚没有真正引起重视。
关于“清代官式”彩绘,当代中国学界在认可其高度成就的同时,是有人清醒认识到其先天性缺点的:
“和玺彩画”和“旋子彩画”等,都是规格化了的彩画装饰构图,这样,在装饰任何梁枋时就便于保持一定的技术水准,也便于施工;并使徒工易于掌握技术。但是,由于这种(彩画装饰)规格地制定了构图上的分划和组合,便不免限制了彩画艺人的创造能力。虽然细节花纹可以作若干变化,但是这种过分标准化的构图规格是有它的缺点的。[10]
据我的观察认识,同许多地方彩作式样相比,清代官式彩作先天性的缺点主要在于构图上几何式的线条划分过于生硬机械,还有装饰内容上的过于森严呆板而缺少人间温情和诙谐味;最典型的象征就是深蓝底子上姿势一律的金龙或金凤,形象与色彩配合上总给人以不舒服的压抑感。
酿成“官式”中心主义的“规范”观,主流学界文化人类学视野的长期缺位是其中最要紧的原故。皇宫文化是否即为“最高”文化我们暂且搁下不论,但皇宫文化绝非就是中国全民的,更非放之天下而皆准的万应灵药。自然生态中因地制宜、群众参与、多样化、多用途的中华建筑彩作,通过国家管道以狭隘视野被自上而下限定的“规范”统一化,把皇宫禁苑里的特定样式如同“普通话”那样推广到全社会,这个领域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工业化改造过程中传统农业、林业、自然环境、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物种多样性等遭受生态性损害的翻版。价值和功能的单一化促成生产内容的同质化亦即批量复制化,进而带来生产人员的工具化低能化亦即个体生命活力的衰颓,乃是这种“现代”变化趋势的共性。对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而言,传统建筑彩作也许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文化生态构成而言它反映的或许就不止是一种局部问题。
任何一种“式”,只要它处在社会的活态里,便自有灵动性、自能发扬创造精神、自有持续发展可能。例如沈阳故宫中女真族刚刚崛起时所兴建的殿堂,就曾“创造出很多地方风格的彩画艺术作品。……在一座大殿的外檐彩绘中,同时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彩画”,成为“东路多民族建筑艺术的成功之作”[11]。
2010年8月26日,我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据说是该市最老庙宇的吕祖庙。这里已转化为佛教的妙禅寺,比原初规模也扩大了上百倍;庙里的建筑彩画显然存在三种不同的风格:承担为清代咸丰年间古建筑吕祖殿彩画四檐的是陕西佳县的画匠班子,带来的自然是近些年很流行的“榆林式”花子;西边近年新起的大量殿宇由山西代县的匠工队伍彩作,他们秉持着五台山一带深受清代官式影响的庙活路数,这也很合理;出乎意料的是一部分由包头市本地画匠老陈师傅于上世纪80年代里所做的那些屋檐彩画……它们显然与清代官式有关联,但留给人深刻印象的是:第一,总色调以白色为引领,多处用白色宽线条穿插提醒,用金较少;第二,纹式风格变得细楚清秀:圆檩和抱檩替或檩与上枋连接的大面积宝蓝底上,图案往往以横向舒卷取势如云气草羽飘拂,色彩绚丽恍如织锦绣缎;格架替也用有地方乡土传统的云朵形;第三,斗拱眼常涂土红色地布置侧面纵势的云龙纹,成为设色最浓重的部分;第四,“旋子花”在枋上不取官式“藻头”“一整两破”的基本构图格式,大多用“两整四破”和“两整六破”,浅亮的花卉因大面积铺展而上升为主纹,而将原官式常用于枋心的深蓝底金龙主纹面积压缩、并排挤到边角外缘处。跟当地人拉起话才知晓:老陈师傅已在2003年以90多岁的高龄去世,继承着他画风的儿子如今也有70岁了,吕祖庙这些遗作应是老陈师傅70岁左右的作品;老陈师傅年轻时候在北京故宫里当过很多年头的彩画匠人,回到包头后以壁画山水享有盛名(可惜他的山水壁画作品因为庙宇失火都烧坏了)。这是一则重要实例,以蒙古人民崇尚的白色冲淡了原清代宫式彩画色调的沉重感,化解官式凤纹而来的舒卷的云羽纹富于草原气息,“旋子花”面积的加大使蓝地金龙枋心图式固有的紧张感大大缩减……它说明即使是从北京故宫清代官式彩画老窝里出来的,一旦回归于乡野自然,一旦脱离了所谓“正规化”的樊笼,那种“过分标准化的构图规格”也会顺乎民情发乎天性地变革,在适应风土中显出一种别致而自然的生态衍化!
由此不难想到:“标准化”是现代社会大规模、批量性经济生产的要求,但经济生产的发展毕竟不等同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上规模、上效益”也绝不能用作文化创造力的标尺。任何一种设计,说到底都不止是生产规模与效益的预案,从本质上说更是文化创意、民族智慧的摇篮。就手工艺门类而言,个别性没计、个别性生产,设计寓于生产全过程即边设计边试制、边生产边调整设计,不拘守某种僵固标准观,可能正是它的一大美德。单一化僵固化标准在手工艺门类的强制推行,不仅无视并搅乱了地方性民间手工艺的生态学及“地层学”关系,而且会伤害民众创造力的生长点;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乃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尊重文化的多元、开放,承认各种文化自我发展的意愿与行动,这是人类学与“非遗”保护一致的目标。对现代社会高度清一色的“正规”化,需要从这样一种长远的文化角度进行反思和再校正,对其妨害人类全面健康发展的危险性给予揭示和预警。
作为艺术人类学圈子里的人,我们要感谢并且珍重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新课题。对于诸如地方建筑彩画这类尚隐藏在“多样性”引号内的遗产,我们能做的事,首先是“勘探”,发现和抓往矿苗,大量打钻采集“岩芯”;接着是像考古学那样为实样标本一一化验定性,考识文化归属、已知度,辨认特征性标志,分期和建立演变序列;在此基础上做艺术史的风格与图像学分析,考察该遗产的位置、成熟程度、成就点及影响力,从文化学层面复原其技术文化的地域体系,辨析其传承演变的生态关系,并尽可能地考察它在大文化系统中显示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意义。在此全过程中伴随着对传承人与传承活动做民俗学详细询问忠实纪录以及人类学深入现场跟踪观察的功夫。所有这些内容贯通起来,才是艺术人类学者完整的工作。由于面临着太多的习见,恐怕只有我们把这些功夫下够、把问题一个一个地考识和理清,艺术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才能对当代“规范”观的再校正产生说服力、影响力,从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真正发挥出推动力。
注释:
①据我们在考察中所闻,整个陕北地区近代较大些的“佛寺”,其实原本都是民间混源教的庙院。姚店青化寺即属此类而并非所谓“正规”佛教的庙宇。“正规化”的理念已经如此浸染渗透到民间传统信仰领域,这也同样是桩发人深思的怪事。
②《中国建筑彩画图集》,何俊寿主编、王仲杰副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在该书修订版中王仲杰先生有一篇短文对“地方彩画”这一问题给予关注,还附刊了少量地方彩画图样,范围涉及晚清苏州、山西及辽宁、黑龙江;但是该书绝大的篇幅、成系统介绍的主体,还是在清代官式彩画上。
③即由清代后期陕西迁疆的回民兴建,由陕西籍工匠依陕西老样施工并彩画的清真寺。
④陕西人习称的“西府”是指西安、咸阳以西,以凤翔为中心的关中西部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