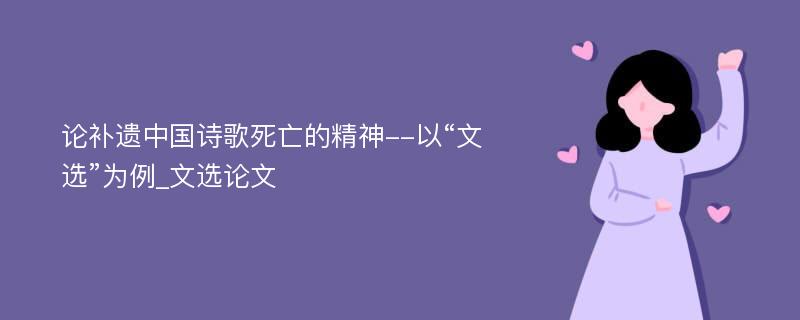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诗歌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3-0034-06
《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诗文总集,由于其选录的诗文大多能做到情义与辞采并重,几乎囊括梁代以前的诗文精华,以至于唐宋以后的学者,无不诵习,影响极大。《文选》篇目的编排是:先赋体,后诗体,接着是骚体,最后是各种散文文体。在所选各类诗体中,补亡为各类之首,而束皙的《补亡诗》六首被作为补亡诗的代表入选。(注: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约生于晋武帝泰始初,约卒于光熙中,年四十岁。曾作《玄居释》、《劝农》、《饼》诸赋。又著有《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蒙记》以及被选入《文选》的《补亡诗》等。又补亡诗除束氏之作外,当时潘岳、夏侯湛等亦有。)何为补亡诗?据《文选》李善注引束氏《补亡诗序》云:“皙与司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1](P337)又据《文选》李周翰注引王隐《晋书》称,束皙“尝览周成王诗有其义亡其辞,惜其不备,故作辞以补之”,[1](P337)则知“有义无辞”即“有其义亡其辞”的缩简。束作凡六首,依次为《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南陔》等六篇篇名本来是笙乐之名。郑玄笺《诗》时却将“亡”字释为“亡佚”,认定《南陔》六篇原来有词句,但词句后来丢佚了。(注:郑氏认为《南陔》六题,乃“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朱熹《诗集传》重新按《仪礼》中出现的顺序排列,以为《南陔》六篇本来就只有乐曲而无词句,而不是有词句后来亡佚,认定《南陔》六篇为乐谱之名,《诗序》所述篇名之义,当为乐曲所表达之义。这样,据郑玄、朱熹等对“亡”字理解的不同可知,“补亡”一词当有两义:一为补原有之失,一为原无后补。束氏的《补亡诗》也就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了。不管哪一种,《补亡诗》仿旧制“补无”的性质是一样的。由于束氏之作为补亡这一类诗的代表,则可以断定:所谓的补亡诗即出于补写原有之失或补写原来根本没有之作而产生的一类诗。下面从《文选》中所收束皙的《补亡诗》入手来综论鲜有论及的中国诗歌补亡传统,以见《文选》补亡诗的意义及其影响。
一、从束作的文化背景看补亡诗的成因
有关束皙写作《补亡诗》的文化背景,胡大雷先生在其专著《〈文选〉诗研究》中主要从西晋重儒教的风气作了探讨,以为“补亡”是种种重儒教的形式之一。[2](P10)这诚然不错,但似乎有点简单化,兹详论之,以见补亡诗成因。首先,束皙的《补亡诗》是西晋复古思潮的一个反映。一般说来,动乱时代过后的王朝在政治文化制度上总是趋向复古,以恢复古制为尚。西晋正是如此。司马氏结束三国鼎立,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恢复前代制度也就成了必需。礼乐制度也就是其中一项。如晋泰始五年,张华上表曰:
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3](卷十九)
可见,当时有取古辞入乐、增损其文,以求合古的复古倾向。今观西晋朝廷所为郊庙歌辞、公宴、颂赞等诗篇,亦多类《诗经》《雅》、《颂》篇什。又由束氏《补亡诗·序》可知,束氏乃因乡饮之礼所咏之诗“有义无辞”而补缀,而《补亡》六首又恰恰是《仪礼·乡饮酒礼》及《仪礼·燕礼》中所奏笙乐之题目。自然,束氏之举亦属恢复古礼而作的尝试。
西晋复古思潮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尚古、拟古的现象。束氏《补亡诗》既是西晋时“四言为正”文体尚古的体现,又是拟古风气所被的特例。诗体发展至魏晋,五七言诗尤其是五言诗逐渐取代了四言诗而成为当时文人经常采用的诗歌体式,五言诗成为当时诗体主流,四言诗也因“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4](P2)然而这并不是说四言诗因此而消亡。相反,四言诗逐渐成为“雅正”的象征,廊庙化了,成为“廊庙文学”主要的抒写形式。面对五言诗的兴盛,当时文人趋新的同时,不忘“旧制”的复古、拟古的作品不少。总览西晋的四言诗,就可发现多数为拟古之作,其题材也多为应制类的郊祀、公宴、献祭、劝戒等。如晋初荀勗、傅玄、张华曾受诏撰写正旦朝会所用的歌辞,多依四言;傅咸多作四言诗,以《七经诗》著名;陆机“诗本奉古,亦步亦趋”。[5](卷八)其于《文赋》中亦云:“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故明人王世贞说道:“陆病不在多而在模拟。”[6](卷三)其弟陆云仿拟《诗经》有《赠顾骠骑》、《赠南曼季》等等,更将拟古的内容由庙堂乐章、应诏应制转向了一般赠答、抒情、写景,形式上也模仿《诗经》小序,凡此足见拟古风气之盛。
而束皙的《补亡诗》与纯粹的拟古诗虽在写作目的上不相同,但在写作形式上与拟古诗无别。尤其是与束氏同时代的潘岳、夏侯湛也写有补亡诗。《世说新语·文学》载: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7](卷上)
由刘孝标注可知,所谓《周诗》实际上也就是《南陔》六篇,夏侯湛也是因“有其义而亡其辞”而“续其亡”。潘安仁所作《家风诗》,胡大雷先生以为“算不上‘补亡诗’了”。[2](P21)实际上,东晋葛洪已指出,潘岳所作亦为补亡诗了。其《抱朴子·钧世篇》云:“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8](卷三十)则束氏之作也属拟古之一种,只不过多了“补填”目的罢了。
再则,束氏《补亡诗》还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这种贵古心理自汉魏至西晋乃至后世,支配着文人在写作上因贵古而托古、补佚的嗜好。陆机《文赋》所云“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可视为这种托古、补佚现象的总括。葛洪在《抱朴子·钧世篇》也指出,“世俗率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8](卷三十)葛洪所批判的这种贵古贱今风气正是束皙《补亡诗》产生的又一原因。由前面分析可知,尽管《南陔》六篇实非《诗经》所有,乃笙乐之名,无所谓“失”,但一经郑玄笺释,遂有亡失之意。束氏承继郑氏之说,补《诗经》所亡失的笙诗,遂成《补亡诗》。这样《补亡诗》就具有了“采遗韵”、“收阙文”的补古性质。
须指出的是,束氏这种“有义无辞”式的补亡,并非如胡大雷先生所言为“开创”,也并非如胡先生所认为,唯有补《诗经》的才称得上“补亡诗”。[2](P443)六朝诗歌中即有很多类似束氏之作者。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所录《琴曲歌辞》大多是原本“有序无辞”,或“有弦无辞”,而后人补填或者伪托补写的。如《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等诗,《太平御览》引原为“大周正乐,有序无辞”;《陬操》,《孔子家语》称,孔子临河不济还息于邹,作《盘操》,《史记》之前“盖有弦无辞”,《孔丛子》乃托为此歌;再如《雉朝飞》言牧犊子作琴操之曲,《别鹤操》言商陵牧子事,《箕山操》言许由事,《归耕操》言曾子之事等,均有乐曲而无辞,为后人依托本事而填补。与束皙同时代的石崇曾补写《明君词》,还作有《思归引》古曲,其序亦云“有弦无歌,乃作乐辞”。将此序与束氏补亡序相较,则知《补亡诗》与《思归引》在“补填”乐曲歌辞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且《思归引》亦“有序无辞”,[9](P321)只是在诗体形式上一为四言,一为多骚体句式。
因此,若仅从句式上来判断是否补亡诗,显然不太得当。不惟《琴操》曲辞多有依托补古的现象,其他像托名卓文君的《白头吟》、托名班婕妤的《怨歌》、《文选》中所录伪《苏李赠答诗》以及王嘉伪撰尧帝时代的《皇娥》、《白帝》二歌等,与其说是“伪作”、“伪托”、“伪撰”,不如换个角度说是后人“补亡”之作。所谓的“伪”是后人或今人的看法,在当时他们何尝不是像束皙那样抱着补古、托古的心态呢?
束氏之作,乃至潘岳、夏侯湛之作,当时之所以不称其“伪”,是因为束氏补的是经典之遗,且有补诗之序言明,而像《白头吟》、《怨歌》、《苏李诗》等则或许因未言明补古,或许有序后来丢失,或许所补之人名声不大,遂使“补古”之义隐没,而使后人误以为真,非辨不知其伪。明乎此,可知束氏等补亡诗的产生并非偶然,实在是当时贵古而托古遂拟古、补古的风气使之然。
二、补亡诗写作心理与其他类型诗歌的异同
在写作心理上,束氏的《补亡诗》与一般拟古诗同中有异。无论是拟古,还是这种特殊的拟古——“补亡”,都体现了他们对模写对象的尊崇钦佩之情。正是这种尊崇,激起了他们的创作欲望,既要与古人作品的思想“共鸣”,又要合乎古人作品的体制、规范、风格。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欲与古人比高争长的心理。他们企图以文才取胜,达到古今难辨的目的。而补亡虽属拟古,但由于是“有序无辞”、“有义无辞”或“有声无辞”,没有原作,缺乏明显的模拟对象,这就比一般的拟古难度大,更需要原创性的才力,“遥想”当时情形,“存思”在当时,力求所作符合题义所反映的境界,并且由于是填补歌辞,还须注意音乐与歌辞的协合。这是一种“虚拟写作”。首先将自己置身于当时环境,使自己成为古人,以古人的口吻来表达题义,从而达到“虚拟中的真实”。这一点很类似“代言体”作品。只不过“代言体”作品是揣摩时人或女人的心理。如魏晋时的《寡妇赋》一类赋作、齐梁宫体以及诗词中“男子而作闺音”的作品等,而“补亡”一类作品揣摩古人声吻,有点像八股文那样代古人立言的意味。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论及八股文时说:
此类代言之体,最为罗马修辞教学所注重,名曰Prosopopoeia,学僮皆须习为之……亦以拟蓦古人身分、得其口吻,为最难事。[10](P33)
以此理来看,比起一般拟古诗来说,补亡诗的虚构成分更大一些,难度大一些,也就更能激发作者的创作欲望。
正由于虚构成分大,补亡诗的文学意味也就比一般拟古诗浓一些。如陆机《文赋》在主张模拟的同时虽也主张独创,但这只是针对诗歌单个的意象与遣辞造句而言。而补亡诗原本无辞,就须从整篇作品的语言、意境等方面进行总的构思,明显带有个人的创造。胡大雷先生曾将束氏的《补亡诗》与《诗经·小雅》的作品相比较,以为《补亡诗》的抒情口吻多以人物群体出之,而《诗经》则多以人物个体出之;《补亡诗》均直奔主题之理,其诗中比兴与描摹叙写多指向概括化的事物或道理;主题指向上,《补亡诗》全为劝与颂,而《小雅》还有戒有怨。[2](P453)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即缘于西晋以雅乐为正、以颂美为主的创作风尚。束氏在“虚拟”时,难免使“古人”带上晋人的腔调。而这正说明了补亡诗的创作成分很大。那些“托辞古人”的补古之作招致怀疑原因也正在于此。
前文我们把伪诗作为一种特殊“补亡诗”,但在写作态度和虚拟情态上二者也有不同。伪诗虽说有“补亡”的性质,但或如章学诚所说“事类古人,不忍明言而托言”。[11](《言公》)或多出于借重古人以提高自己,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或为迎合世俗之人贵古贱今的嗜好,进而欺世盗名,扩大个人影响。这样,作伪诗者在写作时,就尽可能接近古人其他作品风貌,以达到“乱真”目的,这种“偷补”毕竟不如标明“补亡诗”的写作情形。作伪式的“偷补”,其所据的“义”或本事虽有,但其序义乃作伪者自己加工制作的,写作时必处处规仿古人他作,力求形似,这就限制了创新。而纯粹的补亡诗作者不是带着“虚伪之心”,而是带着尊崇希慕之心言明托古,在模拟时,加入了不少个人的主观因素和时代精神。束氏《补亡诗》的写作,即是后一种心态的反映。
补亡诗的虚拟情态也与诗人常为的即事即景类诗篇不同。钟嵘《诗品·序》中“若乃春风春鸟”至“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一段,虽是针对诗之“群、怨”说的,却也正好把即事即景类诗篇的特征描述了出来。即事即景类一般写当下的情、景、事、物及其所引起的感受,具有写实的一面。只是在艺术加工方面,适当采用虚拟或想象,是“真实中的虚拟”。由于写的是诗人们自身所经历之情、景、事、物,易“感荡心灵”,触发诗兴,因而诗人们常写此类有利于抒发真情实感的诗篇。而补亡诗则是“虚拟中的真实”,当初人不一定写,时过境迁由后来人AI写作、补填,从情景事物、谋篇布局乃至描辞言语都是凭借“遥想”、“存思”这样的想象完成的,难免有做作、虚假、模式之嫌。虚拟情态的不同,导致即事即景类诗篇的文学色彩更浓,而补亡诗虽有一定的文学意味,却难与古人同类作品相颉颃。如束皙的补亡诗就没有全面地模拟出《小雅》的神韵。这诚然是因四言诗体所限,更多的原因则由于补亡诗缺乏真实感受这一基础,不是“真实的虚拟”,而是“虚拟中的真实”。
正由于补亡诗与一般拟古依托之作以及即事即景类诗作存在着诸多不同,萧统《文选》把《补亡》单列为《选》诗一类,自然是合乎道理的。
三、《补亡诗》置《选》诗之首的缘由及意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萧统不但将《补亡》单列一类,还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萧统这样编辑的目的缘由是什么呢?
首先,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使得萧统如此。刘跃进先生曾指出,这种思潮的形成,是皇太子萧统具体贯彻其父萧衍文化政策的必然结果。[12](P447)而束氏《补亡诗》是仿拟《诗经》、补有义无辞的乡饮之礼所咏之诗,正合乎这种复古思潮。从内容来讲,束氏之作合乎萧统《与何胤书》所云“研寻物理”的要求。如萧统《答晋安王书》称:“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况观六籍、杂玩文史,见孝义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师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诚至,无俟傍求。”[13](卷二○)拿束氏《补亡诗》《南陔》六篇的序“义”相比较,不难发现,与萧统的表白何其相似。对重儒家政治教化的皇太子萧统来说,束氏《补亡诗》适得其宜,合乎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的主张。更何况,束氏之作乃补儒家经典《诗经》之亡佚。置之于《选》诗之首,理所应当。
萧统列束氏《补亡诗》于众诗之首,还缘于其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在萧统那里,赋体是“诗之六义”之一,乃“古诗之体”。这种观点自汉魏以来,乃至后世普遍认同。按照此理,“诗之六义”的顺序是风、赋、比、兴、雅、颂。“比、兴”为诗歌手法不谈,“风”作为“古诗之体”当列在“赋”之前,“赋”体之后当列《雅》、《颂》。萧统《文选》“赋”体为其首,似乎与此相悖。然若联系《文选·序》下文,可知,萧统乃因《风》、《雅》、《颂》乃儒家经典《诗经》的内容,“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1](P2)才不敢选编入《文选》。这样“赋体”之前就少了“风”这一体,而其后,则少了《雅》、《颂》二体,如此赋体便跃居“古诗之体”首位,成为《文选》众体之首。循此思路,《补亡诗》虽为西晋时的作品,然却是束氏补《诗经·小雅》“有其义无其辞”的“笙诗”,与《小雅》旧制相符,且多劝颂之义,堪称“《雅》、《颂》之遗篇”,萧统按“诗之六义”的顺序将其列于赋体之后、《选》诗众体之首,于理无碍。
其次,束氏《补亡诗》当符合了萧统《文选》的选录标准。其《文选·序》云“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即有之,文亦宜然”。[1](P2)束氏之作正是“踵”《诗序》而“增华”。一般人们把《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萧统的选录标准。以此标准来看《补亡诗》,束氏在《补亡诗·序》中所云“遥想”、“存思”不正是“事出于沉思”?束氏鉴于《南陔》六篇“有义无辞”而补缀其阙,不正是“义归乎翰藻”?与其他流美华丽的五言诗相比,束氏之作虽然“略输文采”,但基本上还是符合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提出的“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的文学主张的。
第三,我们还可以从萧统选录四言诗的态度来察看其列《补亡诗》为《选》诗众体之首的原因。莫砺锋师曾通过比较《文心雕龙》与《文选》指出,《文心雕龙》选评、选录作品的基本倾向是详古略今,重古轻今。[14](P244)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萧统对四言诗不重视。在萧统那里,重视是一回事,编选是一回事。重视四言诗乃因其为儒家经典《诗经》所采用的形式,是礼仪文章、庙堂文章的表达工具,四言乃礼仪、廊庙之体的专用格式。而萧统更多地注重那些文质彬彬之作,这样就造成编选的“重今轻古”与政教需要上的“重古轻今”的矛盾。由《文选·序》可知萧统把以四言为主的《诗经》奉为经典,才不敢妄加“芟夷”、“剪截”选入。
而《文选》所收四言诗除《补亡诗》六首外,尚有劝励类、献诗类、公宴类、哀伤类、赠答类、郊庙类、乐府类、杂诗类等共计38首,14位作者,仅占《文选》诗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其中汉1人(韦孟2首);魏3人(曹植3首、王粲3首、嵇康7首);西晋9人(束皙6首、张华1首、陆机3首、陆云1首、应玚1首、潘岳2首、潘尼1首、刘琨1首、卢湛1首);刘宋1人(颜延年4首)。通过统计可以看出,萧统也视西晋为四言诗创作的又一高峰,这与西晋文学状态相侔。这说明萧统选束氏之作为补亡类的代表是有根据的。又从这些四言诗的内容来看,多应制、应诏、应酬类之作,像曹操抒发情志的四言诗,则一首未选。由此可推知萧统正是以礼仪廊庙之体来看待四言诗的,也表明萧统感受到了四言诗的衰微与消解,在编选时对它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总之,在文学思想方面,萧统是提倡儒教复古的,在文学艺术方面,他是贵今重流的。萧统《文选》入选《补亡诗》这一类的四言诗,是其文学观念上崇雅与尚文矛盾冲突的反映。他将补亡诗列于《选》诗众体之首,无非是出于折衷的目的,以表明儒家政教观念在文学上的重要作用,着眼点并不是其文学特征。然如此一来,却将补亡这一诗体样式纳入了正统轨道,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
四、《补亡诗》的典范意义
自《文选》将《补亡诗》列于《选》诗众体之首以后,后世继承发扬补亡精神这一传统者不乏其人。无论从狭义的“补亡”,还是从广义的“补亡”都有作品出现。从其狭义的角度,补亡诗乃补前代“有其义而无其辞”的礼乐篇章。即凡是像束皙那样补古乐、古辞之缺的诗作,均可称为补亡诗,不当以其是否仿《诗经》来判断。(注:胡大雷先生《〈文选〉诗研究》即把补亡诗仅限于仿《诗经》、用四言。而元结、皮日休等人之作亦有用骚体者。)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在叙述自汉至唐古曲、音辞存亡情况后说:
大抵先世乐府,有其名者尚多,其义存者十之三,其始辞存者十不得一,略其音将无传,势使然也。[15](卷一)
可见“有声无辞”或“有义无辞”的现象不惟束氏所补的《南陔》六篇。这样就给束氏以后的作者提供了补填的条件。如唐人元结有《补乐歌》十首补伏羲氏至商十代的乐歌,其《序》云:
自伏羲氏至殷室凡十代,乐歌有其名无其辞,考之传记而义或存焉。呜呼,乐声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亡古音,呜呼,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遂亡古辞。今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岁时荐享,则必作乐,而无《云门》、《咸池》、《韶夏》之声,故探其名义以补之。诚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宫羽,而或存之,犹乙乙冥冥有纯古之声,岂几乎司乐君子道和焉。乐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义以序之,命曰《补乐歌》。[16](卷二四○)
此诗序虽长,与束皙的《补亡诗·序》相较,作诗缘由却相同,均因乐辞亡阙而据义补之。虽命名不同,但“补亡”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不像《南陔》六篇那样已有诗序之义,元氏则就“各引其义以序之”,再补乐辞。 又如皮日休有《补九夏歌》九篇,其序称为补《周礼·九夏·系文》。且其序数语,亦如束皙《补亡诗·序》之义。所谓“《九夏》者,皆诗篇名”,实际上也是《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中出现的“笙乐”名称,均为无辞之乐,也一如元结各诗“引其义以序之”后补之。像此类作品显然是纯粹的补亡。既是他们希心远古为恢复古乐古辞而作的努力,也是中国古代礼乐教化在诗歌中的反映。至北宋初的古文家石介干脆以“补亡先生”自号,更可见这种尚古复礼的补亡精神。
相对于狭义的“补亡”,广义的“补亡”是根据束氏《补亡诗》“有义无辞”的原理,不管是否补乐辞的亡阙,凡是据事义而补写前人当作却阙而未作的,即可视为补亡,其诗体也不一定拘泥四言或古体。前面我们称伪诗为特殊的“补亡”,即是从广义而言。除“伪作”这种特殊的补亡外,《文选》以后的诗坛上,“据事义而补”的补亡之作数量不少。即如萧统本人就有《咏山涛王戎》二首,由其序云“颜生《五君咏》不取山涛、王戎,余聊咏之焉”知,其诗乃补颜延之《五君咏》“竹林七贤”之未备。又如中唐韩愈据题义而续补《琴操》十首。李贺有《还自会稽歌》,序云:
庾肩吾于梁时,尝作宫体谣引,以应和皇子。及国世沦败,肩吾先潜难会稽,后始还家,仆意其必有遗文,今无得焉。故作《还自会稽歌》,以补其悲。[16](卷三九○)
很明显,这当是一首补亡诗。其《金铜仙人辞汉歌》、《秦宫诗》等也具有补亡的性质。(注:李贺之所以写有不少广义补亡诗,当与其曾任过奉礼郎之类的官职有关。)李商隐有《代魏宫私赠》,其序云:“黄初三年,已隔存没,追代其意,何必同时?亦广《子夜》鬼歌之流。”[16](卷五三九)这里的“追代其意,何必同时”,正是广义“补亡”诗的原理所在。李商隐诗集中此类“追代其意”的补亡之作尚有《杜工部蜀中离席》、《追代卢家人嘲堂内》、《代应》等。再如南宋朱熹曾追答初唐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由于声吻毕肖,后人不明此乃补亡之作,遂误收入《全唐诗》中,直至当代才被证伪。诸如此类补亡之作,虽与束氏补亡诗不大相同,但在“补写彼时当作末作”或“追代其意,何必同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是中国诗由写实走向虚拟的一个突出表现。由此来看,《文选》选《补亡诗》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反映当时重礼崇古雅的风尚,而且隐约注意到了中国诗歌史中这种据事虚拟的补亡现象,将中国诗歌中的另一类型——据事虚拟诗标举了出来。
如果再将这种补亡精神推而广之,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会真诗》、韩愈的《石鼓诗》等与传奇相配的诗作均可视为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如北宋词人晏几道的词集原名《乐府补亡》,由其自序云“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谓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遗,第于今无传耳。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等语可知,[17](P2)晏几道正是本着补亡精神来写词的。尽管晏词备写儿女之情,却与束氏《补亡诗》在体制、风貌上相去甚远。与此相仿,南宋末年的词集《乐府补题》借咏龙涎香、白莲、蟹、蝉等词来补写元兵发掘宋帝后寝陵一事,其据事补亡的性质自不待言。
要之,这种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创作的兴盛,某种程度上也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像后来话本小说、戏剧中所出现的诗作、唱词均可视为代言“补亡”而来。其他像诗词本事、演义、续书等文学现象也均可视为“补亡”精神的承继。可以说,类似文选《补亡诗》的这种补亡精神,正是中国文学由实用、写实等传统向审美、虚构等方向转变的动因之一。
收稿日期:2003-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