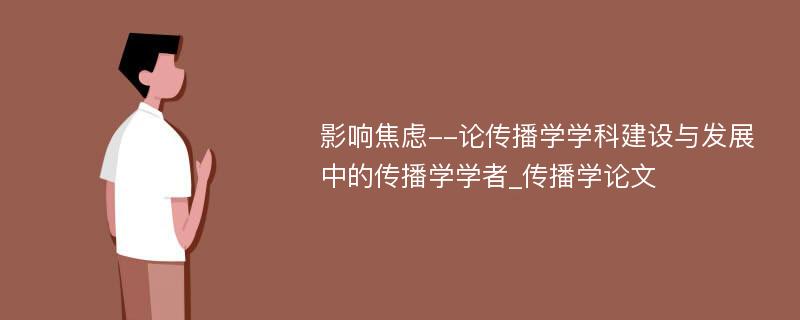
影响的焦虑:再论传播学科创建与发展中的传播学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人论文,焦虑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奇哉!他们身处父亲的庇荫而不认识他。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序 传播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其起源和创建史仍然是云遮雾罩,不甚明了。近年来,作为传播学科建制者的关键人物,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贡献备受质疑。施拉姆曾被国内学界视为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被誉为“传播学之父”、“传播学鼻祖”。但是,近年来这些头衔在中西方学界不断受到质疑。当下的很多研究都在弱化施拉姆在传播学科创建和发展中的作用,如胡翼青(2011)就认为施拉姆“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和辉煌后止步不前,最后都陷入了困局”,甚至全面否定施拉姆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品格(伍静,2011:72),将传播学科后续发展过程中的路径单一和视野封闭归咎于他,施拉姆逐渐被推下神坛,其所钦定的四大奠基人也备受争议。笔者无意为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翻案,也不想重新将其扶上传播学科的神坛供学界参拜,而是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传播学科的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传播学人在其中的角色,再现历史参与者的良苦用心。知识社会学注重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历史情境、文化传统、社会群体、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无疑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传播学人在传播学科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冲击与回应、犹豫与决绝、守成与突破、回归与标新。本文借用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来解释传播学人的心路历程,认为传播学科创建和发展中,传播学人面临前者影响的焦虑,驱使他们努力摆脱影响,自立门户,并不断捍卫传播学科的尊严,而后辈学者对施拉姆的批评也是基于施拉姆所确定的单一研究路线的焦虑。如果说既往的传播学史的探索可以说是从“内史”的角度,即追寻传播学科内在的发展理路和自身的演进逻辑的话,那么本文尝试从“外史”的层面辨明学科发展与外在社会因素的互动,以及传播学人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并从影响的焦虑角度得出结论,传播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已不再是偶然性的学术史事件,而是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学科生成模式,这可以为学科的“发生学”提供一些另类视野,这也是心理史学的题中之义。 一、何为“影响的焦虑” 美国文艺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其名著《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中提出“影响的焦虑”理论,被称为最大胆最有创见的一套文学理论之一,成为解构主义批评和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经典。该书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结合尼采的超人理论,试图通过阐述诗人之间以及传统与个体艺术家的各种关系来提出一种新的诗歌理论(布鲁姆,1973/1989:3)。 布鲁姆的中心主题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受到了他们必须维持的与前驱诗人的模式关系的影响。他认为“诗人之中的诗人”(the poet in a poet)是那种通过阅读其他诗人的诗而被启发去写作,倾向于生产出现存诗歌的衍生物,因此是脆弱无力的。因为一个诗人为了保证他在后世的流传,必须创造出一个原创性的诗歌版本。在诗歌传统中,有些是“诗人中的强者”,他们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矢志超越前代巨掣的诗坛主将们。天赋较逊的会把前人理想化,而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则会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但是后辈诗人会由于受人恩惠而产生负债的焦虑。前驱诗人的影响变成某种使后人无法摆脱的焦虑。后来诗人处于一种甚为尴尬的境地,总是处于传统影响之阴影里。那么,如何摆脱这个阴影,使自己的诗作显得“并未受到前人的影响”,从而足以跻身于强者诗人之列呢,由此形成了“影响的焦虑”,即对于传统影响的心理焦虑,或由于传统影响而引起的焦虑感。于是强者诗人,就用各种方式去“误读”和“修正”前人,就是贬低我们的前人,从而树立我们自己的风格与之抗衡。布鲁姆认为渴望跻身强者诗人之列的当代诗人“新人”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诗人之间的关系类似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之父子相争关系。诗人面对着诗的传统——他之前的所有强者诗人——这一咄咄逼人的父亲形象,两者的关系是绝对的对立,传统企图压倒和毁灭新人,阻止其树立起“强者诗人”的地位,而新人则试图用各种有意和无意的对前人诗作的“误读”达到贬低和否定传统价值的目的,从而树立自己的诗人形象。后来诗人必须敢于跟诗坛巨擘或者说强者诗人作殊死的抗争,对他们进行“修正”,重新审视、否定,甚至推翻传统价值,才有可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正是这种焦虑驱使诗人去走出前人影响的阴影,创造自己的风格,最终推动了诗歌的发展。布鲁姆本人的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影响的焦虑”,其理论的特点是富有挑战性,敢于否定前人的观点。为了与前人的文艺批评一争高下,达到一鸣惊人的目的,布鲁姆有意识地使用许多深奥莫测的“玄语言”,企图以晦涩的文风独树一帜而取胜,对诗的传统和诗论持否定态度,树立起自己诗论传统中的强者形象。 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的主体都是人(诗人),不管是前辈“强者”诗人,还是后辈的“弱者”诗人在诗歌发展历史上都至关重要。前辈强者诗人是在影响的焦虑下推翻他的前辈强者而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供后人顶礼膜拜,而后辈诗人同样在影响的焦虑下自觉在形式和内容上推陈致新,修正前辈强者,创建自己的新风格,努力走出前辈强者的阴影,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同样这种权威也会被后来者修正和推翻,这种循环反复、前赴后继、兴衰更替、互相竞争造就了诗歌的繁荣更替。诗人的影响的焦虑铸就了诗歌史上繁花似锦的景观,传播学科亦是如此。 二、学科前史:社会学的焦虑和芝加哥传播研究的没落 在传播学科创建之前,由于影响的焦虑,社会学抛弃了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抛弃了传播研究,传播研究命悬一线。1892年美国社会学家斯莫尔(Albion Small)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培养了一批社会学研究生,出版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1894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George Vincent)、托马斯(William Thomas)、帕克(Robert Park)、伯吉斯(Ernest Burgess)等人,成为同期美国和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形成了芝加哥学派。芝加哥也成为当时社会学家心中的圣地,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成为当时社会学中当仁不让的“强者”。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作为研究人类结构和活动的社会学也面临着学科范式的转型。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浪潮逐渐回落,城市变得相对井然有序,社会问题暂时得到缓解,芝加哥学派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显得不合时宜。同时,新的社会学力量在美国其他大学崛起,逐渐改变了芝加哥学派一支独大的局面。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科学中的领导地位不断受到了挑战,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即哈佛大学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哥伦比亚大学默顿(Robert Merton)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异军突起,并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当时的“强者”社会学家,即芝加哥学派的库利、米德、帕克等人的地位最终被后继的强者帕森斯和默顿所取代,芝加哥学派走向衰落。 在社会学范式转变和芝加哥社会学派衰落的种种原因中,影响的焦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早期曾与芝加哥学派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在当时社会学界,芝加哥学派几位代表人物影响实在太大,后继者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路径来开辟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虽然拉氏对传播研究领域的贡献恐怕要超过同时代的大多数从事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学者,但在社会学的历史长河里,他不可能在社会学圈子里取得理论上的主导地位(哈特,1992/2008:120)。一个学科的完善化和精致化也面临着衰落的危险。当芝加哥社会学派处于社会学巅峰时,当时的社会学者已经不能在探讨具体社会问题上超过芝加哥学派的几位强者社会学家,美国东海岸的社会学家们无疑感受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而产生的焦虑,他们在研究具体社会问题和质化分析方法上无法与芝加哥学派的“强者”抗衡,于是另辟蹊跷,为了树立自己的强者形象,便从社会整体结构和组织系统的角度采纳量化研究方法树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新范式,用“平衡”取代了“冲突”。 芝加哥学派衰落后,整个社会学主流走向结构功能主义和定量研究方法。当范式实现转变时,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不得不面对着范式转变的影响,衰落的结果必然是分道扬镳、人走茶凉,芝加哥学派难以为继。在影响的焦虑下,传播研究就被视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分支领域被社会学抛弃了,社会学人的目光聚集到了新的“强者”——结构功能主义身上而无暇顾及本来就是芝加哥学派的副业的传播研究。虽然最新的研究也在不断证明,最初的传播研究源于芝加哥大学的传播委员会。1但是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在面临着焦虑时,最终选择在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大树下寻找庇护,而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开拓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另外,学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传播研究的衰落,芝加哥大学的传播委员会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管理也比较混乱,尤其是传播委员会成为了社会学系的竞争者,社会学系主任反对传播委员会的传播研究实践(Wahl-Jorgensen,2004)。传播委员会陆续失去了核心的教授,这些人在影响的焦虑下陆续在其他地方开辟新的天地。芝加哥学派顾此失彼,而传播研究成了牺牲品。正如当时历史见证者卡茨(Elihu Katz)所说的,社会学最终抛弃了传播研究(Katz,2009),社会学失去了传播研究,尤其是大众传播研究兴趣,传播研究危在旦夕。 虽然芝加哥大学传播委员会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益增长的传播研究建制化的信号。但是,没有一个历史时刻或者英雄式的个人站出来使这个研究领域和学科成为现实。芝加哥大学传播研究委员会只是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失败的教训:缺乏制度支持,这也为后来的强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验。芝加哥学派早期传播研究的消失证明没有像施拉姆这样一个坚定的后继“强者”和一个热心的学科建制者,这个学科不能成为现实。传播研究领域的产生没有一个固定的历史时刻,但是学科的诞生却是可以描定的,传播学科的出现必需有“强者”站起来,那就是后辈强者施拉姆的及时出现。就在传播学作为一个还未诞生的胎儿即将流产时,是施拉姆的努力让传播学科来到这个世界上。 三、学科创建史:施拉姆的焦虑和传播学科的创建 由于芝加哥学派融入了主流社会学,而将传播研究抛弃,强者施拉姆的及时出现拯救了传播研究。芝加哥传播研究项目的没落和消失,既给施拉姆带来了影响的焦虑,也让施拉姆看到了机会。当精英大学抛弃传播研究的时候,施拉姆以美国中西部大学为阵地,延续了传播研究的香火。在强大的社会学领域内,当时有志于传播研究的后来学者感到没有出头之日,很难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作出新的突破,于是产生了影响的焦虑。当时施拉姆面对的正是秉持社会学主流范式的庞大学术群体,出于后辈新人对强者的影响的焦虑,他希望减弱传播学与芝加哥学派的联系,而试图开天辟地,开创一个新的领域,这对传播学的独立无疑是明智之举。影响的焦虑成为施拉姆创办学科的内在驱动力。在传播研究思想史上,天赋较逊的施拉姆无法在理论创造上超过芝加哥学派库里等巨擘,于是转而寻求新的成为强者的路径:制度建设。施拉姆正是受到前驱传播研究者的影响,而产生了难以排遣的焦虑,并激励他独辟蹊径,创建传播学科和领域。这与施拉姆本人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以及养成的精神气质有关。 从施拉姆成长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布鲁姆所说的“强者”,他性格坚强,虽幼年口吃,但并没有妨碍他的生活,也没有限制他的职业选择。高中时期就为当地报纸撰写专栏。在大学时,他先后学习数学、物理、历史和政治科学,以优秀成绩毕业。在哈佛大学他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善于利用在波士顿所遇到的各种机会,为报纸撰稿,表演长笛,打篮球赚钱。后来受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前往艾奥瓦大学继续学业,深受白壁德(Irving Babbitt)的学生诺曼·佛瑞斯特(Norman Forester)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施拉姆适应局势而左右逢源的性格在当时就有所体现。当佛瑞斯特不受教职工欢迎时,施拉姆开始疏远他和新人文主义运动,并最终背叛了佛瑞斯特(Glander,1990:274)。施拉姆文笔出色,是知名的小说文学家,在二战中任战争信息办公室的教育主任,曾多次为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执笔,战后任艾奥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并开始热衷于创办学术机构,创办了著名的写作小组和舆论研究中心,积累了创办大学机构的成功经验。 施拉姆的性格和能力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甘为人后的人。他被称为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Pooley,2007),也是一位爱国的意识形态斗士。他不喜欢臣服于权威,不管将自己身处什么位置,他都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不喜欢哲学争论,而热衷于建设研究机构(Cartier,1988)。这种性格也决定了他不想重走芝加哥大学传播研究项目失败的老路。超强的行政能力和制度化的热情使他创建传播学科成为可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传播和媒介研究并没有被学术界所认可,四大先驱也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传播学者(Eid & Paré,2008)。施拉姆试图打破社会学强大影响的阴影,通过误读、贬低前人传播研究传统而自立门户,树立起自己第一个传播学专业教授的形象。他将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卢因四人称为传播学科的奠基人,这个鲁莽的决定成为后人攻击的焦点,但在当时看来,他正是通过这种无意间的误读,吸纳了当时学界有影响力的强者学人和研究路径,为传播学科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奠定了基石,为传播学科赢得了一定的尊重。当他看到传播研究在社会学系中已经无法立足后,他以过人的眼光,让大众传播在渴求合法性的新闻学院中寻找庇护,传播与新闻的联姻最终证明是成功的,并最终决定了后来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主要模式。 从客观上来说,两个因素造成了施拉姆的焦虑:一是社会学学科危机和范式转变导致了芝加哥学派的衰落,使施拉姆转向了定量和效果研究。当时人文主义面临政治经济的高压,也迫使施拉姆最终离开了人文主义,背叛了他的导师。社会学抛弃了芝加哥学派,文学界又抛弃人文主义,施拉姆对种种影响感同身受,也让他饱含焦虑。二是芝加哥学派抛弃了传播研究。这使施拉姆认识到对传播学科创建的紧迫性。短命的芝加哥大学传播研究项目由于缺乏制度支持而死亡,使他认识到学科领域的持续健康发展依赖制度的支持。在意见领袖和两极传播等理念在大众传播研究文献中流行之前,他就认识到接触受众的最好地方就是他们接受教育的机构(Glander,1990:261)。在影响的焦虑下,他不想让传播学成为社会学的衍生物,生长在社会学的阴影中,而试图自立门户,成为传播研究中的强者,创建一直被人忽视的传播学科。 1947年,施拉姆受邀出任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社长和校长助理,使他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施拉姆努力获取和利用各种资源(如美国军方、政府、大学、民间基金会)2创建了第一个传播学的大学项目——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招收了第一批传播学研究生,标志着传播和媒介研究作为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的正式诞生,传播学科实现了建制化。施拉姆成为第一个传播学者和传播学教授,成为这个新领域的第一代学者的老师。他也理所当然地被贴上了创建者、创造者和界定者的标签。其学生,也是著名的传播学者查菲(Steve Chaffee)和罗杰斯(Everett Rogers)说他“不仅是在美国,也是全世界传播研究的创始人(founder)”(Chaffee & Rogers,1997)。正是施拉姆建立了第一个以大学为基地的传播教育和研究机构,从此传播研究便有了自己的大本营,而不再像四处流浪的弃儿,传播研究从此开始走上正规化。 在影响的焦虑下,施拉姆与芝加哥学派有着不同的大众传播研究概念,他试图走出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阴影,而体现了自己的特色,树立起自己的强者形象。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植根于实用主义哲学,集中研究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当下状况,主张深入研究传播过程如何影响心智和自我的方式等相关议题。施拉姆试图打破芝加哥学派强者社会学家的影响,而对传播研究领域进行自己的界定(陈世华,2010)。在1947年底提交的一个传播研究所的成立计划中,施拉姆对传播学的看法与芝加哥学派大相径庭(Schramm,1947)。在传播模式上,他也选取了拉斯韦尔的5W模式。施拉姆将大众传播研究视为一个大学学科,而芝加哥学者认为传播是源于说服问题的一系列研究,二者界限明显,知识的性质和定义都迥然有异,这也正是体现出施拉姆试图推翻前辈强者而取而代之的焦虑。 1973年《影响的焦虑》一书付梓时,布鲁姆43岁,正是书生意气风发,不惧推陈立新之人生阶段。而1947年,施拉姆也是在40岁的时候几乎单手将大传播研究领域制度化,使传播学科在大学中成为现实。施拉姆也借此树立了其传播研究传统中的强者地位,并长期屹立不倒,但也不断受到质疑和攻击。从那开始,他在这个领域度过了一生,并决定了随后三四十年里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引发了后继新人出于影响的焦虑而做出的种种批判。 四、学科捍卫史:学科建设中的焦虑 坚守往往比创建更为艰难。施拉姆创建了传播学科之后,他的焦虑并没有消失,反而与日俱增。学科创建之后,他的焦虑就是如何维护“强者”的地位而不被后继新人所误读和推翻。在焦虑的驱动下,他为新生的传播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正如坦卡德(James Tankard)所说:施拉姆可能比其他任何人在界定和建立传播研究领域上做的更多(Tankard,1988)。施拉姆意识到新生的传播学科被人质疑,于是不断从外在的制度化建设和内在的理论积淀上增强传播学科的合法性。在建立了传播学研究机构后,虽然施拉姆身兼数职,但他主要将精力放在传播学科的建设上。施拉姆像福音传道士那样努力为传播研究抓住各种商业和学术机会。他坚持不懈地建设这个新生的跨学科研究部门,邀请了多位其他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如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阿多诺(Theodor Adorno)来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短期任教,还雇佣了FCC经济学家斯麦兹(Dallas Smythe),将新闻学教授西伯特(Frederick Siebert)和“广告教育之父”桑德奇(Charles Sandage)、心理学家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转入到传播研究所。他利用人脉关系获得美国政府、军方、民间基金会的资助举办了各类传播学术会议(Schramm,1947),并与当时的著名学者频繁通信以获取学界支持,他编撰了多部传播学教科书和参考文献汇编,还创办了几个后续传播教育和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引和培养了第一代的传播学者,其中包括如罗杰斯、查菲、坦卡德等重要学者。 在理论积累上,施拉姆的贡献虽然备受质疑,但也不能忽视,他持续编撰出版多本传播学理论和方法教科书,每本书都有他的导论界定传播研究领域的内部框架和外部边界。他不仅自己贡献了许多理论观点,如双向传播模式、积极受众、子弹论、知识沟、使用与满足理论的雏形等,还不断综合、解释和总结其他传播研究成果(Rogers,1986:108),主动发现其他人的贡献。在任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社长时,他出版了信息论的奠基之作:申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由于其显著的文学背景,施拉姆对大众传播研究不寻常的贡献在于他大量使用隐喻,如十字路口、时光窃贼等,这让他写作颇具活力,现在仍然在传播研究中被广泛引用,这也直接启发后来很多传播学者采用浅显清晰的写作方式。 年轻的传播学科不断受到质疑和攻击,影响的焦虑时刻伴随着施拉姆,他时刻积极主动捍卫传播学科的尊严。1959年,社会学家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发了一个“讣告”,宣告了传播领域的死亡。他认为传播研究正在凋零,传播研究的主要路径都在逐渐衰弱,创新不断耗尽,思想领袖已经消失,没有新人出现来取代它们(Berelson,1959)。贝雷尔森的说法沉重地打击了施拉姆,因为他在中西部新闻学院里建立传播学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而且获得了成功。施拉姆将各种社会资本投资到这个刚刚建制的领域。备受伤害的施拉姆,则努力试图证明这个领域的生命力。他第一个回复了贝雷尔森,在第一时间保卫了传播研究领域,形成了后来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说的“贝雷尔森-施拉姆”争论。贝雷尔森眼中的死尸,在施拉姆的眼中充满生机。他在回应中首次提出了“四大奠基人”的说法,为传播学科寻找知识源泉。施拉姆用他英雄式和光辉的传播实践作为一系列解释证据论证传播研究的活力(Schramm,1959),将传播看作是一个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事后看来,施拉姆是明智的,在种种争议声中,传播研究在他的有力指导下而生存下来,他的掌舵稳住了传播学科的进程。在影响的焦虑下,施拉姆还试图从社会实践的角度为传播学科合法化,他将传播提高到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和国家发展的高度,吸引人们对传播学科的关注。他不断出版理论著作和教科书,建设国际传播学和发展传播学,他在萨尔瓦多、哥伦比亚、中国、韩国、萨摩亚等地近距离地考察传播现状,探究大众媒介的指导潜力和其在教育中的作用(Singhal,1987)。在施拉姆的努力下,传播研究领域超越美国国界,走向亚洲、非洲和拉美,扩大了传播学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 影响的焦虑也体现在其他后辈传播学者身上。当施拉姆确定了传播学科的主流范式时,其他学者在他的影响下,也产生了关乎传播学科发展的焦虑,试图走出他的阴影,开创传播学多元发展的路径。施拉姆一直将自己视为传播研究领域的发言人,他作为传播学传统中的“强者”无疑是成为后来新人的最佳攻击对象。彼得斯就批评施拉姆开创的研究传统,将传播思想枯竭的原因归结于施拉姆的建制化,认为传播研究缺乏内聚力就是建制成功的代价。彼得斯将施拉姆描述为不是一个理论精深的学者,而是一个忙碌的爱国领袖,其所构想的领域是早期传播研究的残余与其他无依无靠的领域,如新闻学、戏剧学、语言传播的联姻,缺乏理论高雅或者科学缜密,而是社会问题研究,这些议题同时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被研究,而在概念意义上与传播没有什么关系(Peters,1986)。彼得斯对施拉姆的质疑就是一种出于施拉姆所界定的传播学科单一发展路线的焦虑。后辈学者试图打破前辈“强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媒介效果的影响,而从思想内部拓宽传播研究的发展路径。从某种角度来说,彼得斯也是试图作为一个传播学史的新人打破施拉姆这个强者的影响,而从传播思想史的角度来树立起自己在传播研究领域的新的权威。 施拉姆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就是:传播领域是一个学术十字路口,很多人经过,但是几乎没有人停留。但是在几代人的努力下,这个十字路口已经发展为一个大城市。在其他人为了其他兴趣而离开,施拉姆还仍然在坚守。他一直停留在这个十字路口,其一生的工作都在奠定这个城市的基石(McAnany,1988)。彼得斯说施拉姆在推销一种传播学科的国家主义(Peters,1986),施拉姆无疑是传播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正是影响的焦虑驱使施拉姆成为了那个时代传播学科的代言人,铸就了施拉姆光辉的生涯。正在影响的焦虑驱使下,几代传播学者努力开疆辟土,打破施拉姆这位“强者”的影响,为传播研究寻求多元的发展路径和方向,树立起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强者”。 五、学科后史:影响的焦虑与四大奠基人的争议 一个没有思想来源的学科注定会备受人攻击,四大奠基人是施拉姆为传播学科寻找权威性而确定的传播研究起源。如果施拉姆可以被称为传播学科之父的话,他就需要一个为他洗礼的教父(McAnany,1988),开始他选择了拉扎菲尔德,3后来就演化为四大奠基人,而四大奠基人的说法也成为施拉姆备受争议的焦点。 影响的焦虑可以解释后辈学人对四大奠基人的争议。施拉姆正是在影响的焦虑下,力排众议,拨冗去繁,果断地决定四大奠基人。将其放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来考察,施拉姆也有他的苦衷,他正是试图通过这四大奠基人寻找传播研究的合法性,争取其他传统学科的尊重。在“施拉姆-贝雷尔森”争论中,施拉姆采纳了贝雷尔森四种路径的说法建构了传播学科的起源神话,第一次从谱系学的角度赋予了拉斯韦尔等人四大先驱的美誉,作为传播研究前学科时代的先驱。不可否认,在选择传播学奠基人的人选过程中,施拉姆有其自身主观偏见和亲疏远近,4其理由也不够充分。但是我们要看到传播学科遭遇危机时,他试图通过追溯传播研究源头来为传播学赢得尊重的努力和良苦用心。施拉姆在面对贝雷尔森对传播研究领域的不屑和挑战时,匆忙应战,仓促之中做出了四大奠基人的论断。在当时的紧迫情况下,施拉姆没有时间深思熟虑。本来不注重思辨讨论的施拉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考虑到传播学科诞生的方方面面,他总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找出几个代表性学者。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熏陶的施拉姆不是中国文化中的面面兼顾的好好先生,他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学科创建中需要的正是这种勇气。而且,当时芝加哥学派已经没落,而结构功能主义兴起和定量研究方法盛行,芝加哥学派已成昨日黄花,除了四大奠基人之外,很难有合适的人选被施拉姆用来当作传播学源头。而拉斯韦尔等四人确实是在传播研究理论和方法上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施拉姆确定这四个人为美国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也是有理有据。芝加哥学派已经成为过去时,施拉姆只有割断与其联系,在新的语境中寻找新的庇护。另一方面,现代学科的发展,经验性和确定性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而施拉姆选择这四人而不是芝加哥学派无疑更为明智。如果回溯芝加哥学派的人物来作为渊源,在当时的经验主义大潮中,传播研究无疑更容易受到攻击,而这对新生的传播学科来说无疑更为不利。 后辈学者关于四大奠基人的争论就是试图打破施拉姆的影响而另寻源头的努力。施拉姆“四大奠基人”的说法成为传播学科三十年里泰然自若的起源神话,确定了传播研究发展路线,后人则担忧这种传播起源的说法禁锢了其他发展路径而无法突破,从而产生了新的影响的焦虑。凯瑞(James Carey)就试图重新将传播研究的源头追溯至芝加哥学派,努力打破该领域长久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行为科学路径,叙述一种以库利、杜威和芝加哥社会学派为中心的替代性的传播思想史。彼得斯批评“四大奠基人”的研究内容没有任何值得贴上传播的标签,明显缺席的正是杜威、库利、帕克这样的思想家。从影响的焦虑来说,凯瑞和彼得斯也是试图打破经验研究路径的统治地位,而试图在传播研究领域复兴思辨研究方法,树立起一种替代性的研究路径。这些都体现了后辈学者试图打破施拉姆的影响,重新寻找传播研究多元的知识渊源,为传播研究寻找新的发展可能性的努力。 近年来国内学者试图颠覆施拉姆的四大奠基人也体现了一种影响的焦虑。施拉姆对效果研究的重视而忽视政治经济体制,无疑并不适合中国的语境。很多学者意识到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必需打破施拉姆所确定的发展路线。黄旦就认为施拉姆按照自己的口味,找到他所欣赏和满意的人选,这是毫无意义的(黄旦,2004)。既然我们不是美国,那我们没有必要心甘情愿顺着施拉姆指点的路子走下去,体现了一种试图在中国语境下,打破施拉姆所界定的传播研究路线,获得一个更新更宽的传播视野的努力。胡翼青试图颠覆施拉姆观点,认为芝加哥学派的先驱人物,都可以被看作是传播研究的奠基者(胡翼青,2007:5),体现了对施拉姆四大奠基人说法限制传播思想源头的焦虑,试图还原真实多元的传播思想源头,使传播研究重归正确的发展方向,探索多种可能的研究方向。其实施拉姆并没有忽视芝加哥学派,只是没有将其中的学者列为奠基人。在他多本教科书中,都选用了芝加哥学派多位学者的著作。在晚年的总结传播研究起源时,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包括拉斯韦尔以降的传播效果和功能研究;米德、撒皮尔、香农的意义哲学;莫特和豪赛(Arnold Hauser)的传播史研究;霍夫兰、卢因、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传播社会心理学(Schramm,1980)。施拉姆也从来没有贬低芝加哥学派的路径,只是由于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的分歧使他没有把芝加哥学派学者作为奠基人,这是要严格区分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施拉姆被冤枉了。 我们不能以今天眼光来要求施拉姆而忽视当时的学术政治。我们如果去翻看麦卡锡主义影响下的五六十年代学界,我们不能不为施拉姆的这一路线庆幸。如果走的是芝加哥学派的路径或者欧洲批判学派的路径。那么施拉姆辛辛苦苦创办的传播项目可能会是另一个芝加哥短命的传播研究项目的翻版。在定量研究大潮中,如果施拉姆逆当时学界的潮流,选择曾经抛弃传播研究并且具有一定批判色彩的芝加哥学派作为传播研究先驱,传播学科的结果不一定比现在更好。当然这也不符合施拉姆的性格,施拉姆本质上是一个主流学者和意识形态斗士。有主观性的科学研究是危险的,但是没有热情的研究者注定导致研究领域的寂寞。不管施拉姆是热忱的冷战勇士,还是一位机会主义者,他的四大先驱的归类代表了一种社会研究的自觉。同理,后辈学者的质疑是一种焦虑的体现,我们今天要推翻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也是出于打破传统,开天辟地的一个新的焦虑,如果不考虑到这种的焦虑,而盲目地由果推因,将传播学科当前的困境归咎于施拉姆的一时之举无疑是缘木求鱼。构建学科本身是一种确立学科内外秩序的学术政治活动,胡翼青评价他是所有传播学奠基者中的第一个政治家(胡翼青,2012:194)也不失公允。 今天,我辈学人批评施拉姆忽视了芝加哥学派,并试图颠覆施拉姆的起源神话,可以说是影响的焦虑下,对前人施拉姆的误读和修正,从而达到树立起自己强者形象的努力。归结传播学科起源的种种争论,都是基于影响的焦虑下,试图重新厘定传播研究历史和发展路径的尝试。八九十年代就出现了各种关于传播领域是否终结、传播领域的骚动等争论,都是出于这种影响的焦虑。传播研究的源头本来就是多元的,无需争论而应该不断发现。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求施拉姆选择四大奠基人的科学性,正如吴飞所说:一个科学的发展是需要借助于范式的革命的,施拉姆应该没有这样的野心也没有能力去控制传播学范式的革命(吴飞,2008)。 虽然施拉姆提出了四大奠基人,但是正是他第一个决定在传播学这个绿洲上度过一生。他启发了其他很多人在这个绿洲上停留,可能没有施拉姆传播科学永远不会达到现在的状态。施拉姆虽然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奠基人之内,他可能比任何其他个人都界定了大众传播研究的领域(Glander,1990:121)。他可能本身是一个比四大奠基人更好的候选者,是真正的传播研究的奠基人。 正是影响的焦虑,芝加哥学派抛弃传播研究,正是影响的焦虑,施拉姆创建传播学科,并捍卫终生,正是基于焦虑,后辈学者质疑施拉姆的起源神话,并试图重构传播学的思想渊源。正是对施拉姆确定的传播研究路线的质疑,催生出各种新的研究路径。焦虑体现在历代传播学者身上。科学不能一劳永逸,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的影响,使下一代产生难以排遣的焦虑,并不断打破前人的影响,通过修正和误读,树立自身在学科内的地位,推动了传播学科的发展。考察学科的诞生史和发展史需要审视学科本身的历史地理学文献,要追溯该领域的制度化演变和其他学科的嫁接,也要考察学科诞生的社会心理学史。焦虑伴随传播学科的发生和发展,焦虑使传播学能够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体现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在不同时期进行思想重构,让学科路径更加多元丰富。布鲁姆说诗歌是一种焦虑,传播学科也是焦虑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驱使强者走出前人影响的阴影,创造自己的风格,不断推动了传播学科的发展。其他学科未尝不是如此。从影响的焦虑来说,学科的发生与发展不再是一个偶然性的学术史事件,而是一个又一个影响的焦虑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结果,这是在人类焦虑心理在学术领域的体现,是知识生产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学科和流派的诞生与发展都概莫能外。焦虑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的每个角落,焦虑是知识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催化剂。我们不必对焦虑敬而远之,或者大加挞伐,我们应该避免学科成熟精致之后的洋洋自得,而应该欢迎和鼓励学人时刻胸怀这种独辟蹊径、立言立行的无处不在的焦虑感,正是这种焦虑驱使下的创新铸就了思想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强者和巨人,让思想史和人类社会的繁星璀璨。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和避免“焦虑”的异化,焦虑是基于创新意识的科学心态,不是为了新而新,创新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目的还在于寻找人类知识的真善美。焦虑不是“文人相轻”式的互相诋毁和贬低,而是基于求真理念下就事论事、推陈出新的学术智慧。我们需要的是焦虑催生的冷静、公正、理性的学术争论,而不是互相攻讦的谩骂,我们要让思想史上的前人与后人、强者与强者、强者与弱者在影响的焦虑下自由竞争,让学术殿堂形成真正的“真理自由市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在影响的焦虑下,有人放弃(如芝加哥学派),有人坚守(如施拉姆),有人墨守成规,有人独辟蹊径,有人人云亦云,有人立言立行,其中的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在传播学诞生和早期发展时期,没有一个人像施拉姆那样执着于这个学科,没有人在界定传播学科的路线上有施拉姆那样的影响力,没有人像施拉姆那样如此有意识地和持续地承担起思想和制度责任。施拉姆无疑是传播学人中的一个强者,他体会到的影响的焦虑代表了传播学人普遍的心理,我们如果要了解传播学科领域的历史深度、当下状态和未来走向,我们需要继续研究这些胸怀焦虑的传播学人,施拉姆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典范。 用《影响的焦虑》的序曲标题来结束全文:奇哉!他们身处父亲的庇荫而不认识他。 ①近年来的研究将传播研究追溯到芝加哥大学1941年成立的传播和舆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哈钦斯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Press,1943-1946)和传播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Communication,1947-1960)。 ②参见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的档案,内有施拉姆的大量信件和会议记录。 ③施拉姆在194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一书的扉页写道:献给拉扎斯菲尔德。 ④施拉姆与拉斯韦尔等传播学四大先驱都熟识,而且在二战期间,施拉姆与他们合作和共事过。 ⑤美国《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1983年和1993年分别以“领域的骚动”(Ferment in the Field)和“领域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ield)为题进行过两次学术论战。标签:传播学论文; 施拉姆论文; 社会学论文; 芝加哥学派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历史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