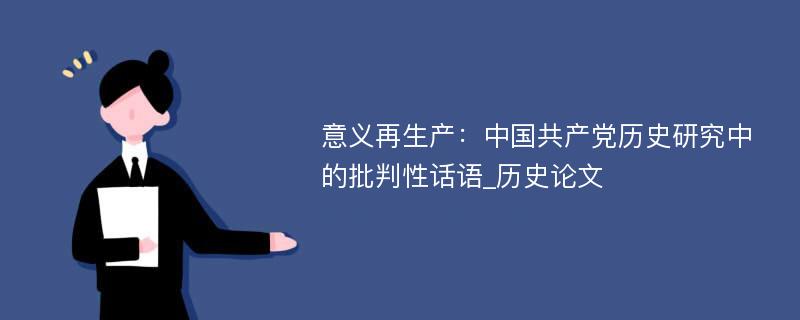
意义再生产:中共历史研究的批评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话语论文,批评论文,意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可否认,如下事实,很少受到中共历史研究业内人士的关切:党史研究缺少批评的参与,似乎没有这种批评的存在,研究活动同样可以自得其乐。党史批评——一个为讨论问题提供方便而取的称呼,其实质内涵,包含了对所有中共历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一种学术性评论。批评即评论。批评已超越党史研究成果——进入公共学术领域的文本——所设定的栅栏,它是一种业已固定化文本的再阐释,结果是一种意义再生产。换个表达方式,党史批评是对党史研究话语的再生产,其本身亦可构成另一种话语,并演化为各具样式的话语类型,这就要看批评方式是如何的构成。但无论如何构成,党史批评话语类型锁定的目标,都一致性地在于揭示党史研究文本话语的意义——通过对这种文本话语的分解、阐释、判定、鉴别、评判等功能来实现。
一、话语阐释:党史批评的核心
只有启动阐释,党史批评才有可能进入话语构成,形成批评话语。不过,批评话语之于文本话语并无先天的优越性,反倒可以说,文本话语理所当然地支撑了批评话语的可能性。在价值层面上,这两种各自言说的话语类型,是意义平等的,并无优劣之分,只不过因为各自的言说边界相异,在学术共同体内形成一前一后的逻辑队列。显然,文本话语——党史研究最终以文字符号按一定的历史叙事形式,构成具有内在自足性的学术文化代码,这种代码是构成党史批评可能性的基石,而阐释正是重新编排代码的过程。这里,任何用单纯句子表达的党史本事的批评性阐释,都尚未形成话语,因为按照现代话语学,“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① 显然,话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文化维度的指谓,如在福柯知识系谱学中即是如此。这里无须纠缠“话语”一词的原始起源。研究福柯的一些专家认为,尽管福柯“话语”概念充满矛盾性,但“对福柯而言,话语是由那些彼此关联的陈述构成的。它们共享一个空间,共同建立语境;它们也可能会共同消失并为别的陈述取代。”② 但是,福柯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话语的所谓关联性陈述,按照弗兰克的引申,福柯“声称话语并不是个别地编码的,而是通过一种权力意志的介入。”③ 话语只有在权力场景中才能够被界定,而权力就是某种关系,即知识生产与权力机制共存于一个共生体内的关系。我们一旦阐释话语,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权力——尽管在其中可能存在极复杂或细微的多元因素,但正因为这种多元因素的左右,话语阐释引导人们的关注从说什么转移到怎么说。这样,阐释就有可能产生能被理解的新话语,一种新的文本又再次诞生。
阐释——正如我们在谈论的党史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文本话语的批评原则。阐释是所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学理成立的基础。按照现代诠释学的提示,阐释的基本功能在于将一种意义关系从一个世界(被分析的文本)转换到了另一个世界(被理解后的新文本),这是一个从陌生化含义过渡到被重新理解的话语转换过程。党史批评——尽管目前从知识体系上说,它还不成为一门学科,但与其他学科化知识类型一样,就阐释本身而言,它是处在党史文本与批评者之间的关系中。在这里,党史文本是已编纂成型的学术文本,它既可以是专业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也可以是一部独立成型的学术专著,当然也可以是一篇专门的学术演讲报告,它们的共性都是由语言文字符号构成的,而文字符号实际上是某种含义的代码。党史批评需要阐释,正是因为需要破译这些代码。
解码过程实际就是将一种陈述话语转换成另一种陈述话语,而这个转换的前提便是文本理解。理解与阐释不同,但它们之间又是同构的。对党史文本的理解,是党史开展阐释批评的前提。这两者——理解与阐释,是同时产生在整个批评过程中的。当对党史文本的批评一开始,理解活动也就开始,阐释借助于理解得以展开。由于党史文本的生成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其一是原始材料的分析、取舍、使用等,直至用文字符号表达成文本,这一连串的“制作”本身就存在局限性;其二是作者与所叙述的事实存在时间距离,他不是现场的直接观察者,因而本身也限制了对事实叙述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而最终形成的文本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意味着文本具有陌生性,破解陌生性内涵的文本意义,首先必须经历理解过程,有如伽达默尔所称的“理解必须被视为意义时间的一部分,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④
在理解活动展开的情况下,对解读党史文本意义的期望,将会转换为引领阐释活动。随后的党史批评正是建立在相应的阐释活动基础上的,而阐释的深度与广度又决定了批评的深度与广度。阐释(当然经过阅读)是在高于理解层次上对文本的分析与判断,继而呈现新的评判姿态,这种“姿态”可以是是非之分,也可以是价值褒贬。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阐释的过程,而通常情况下,对于批评而言,后者来的更为关键。党史文本一旦产生,假如对它展开学术价值或实践价值的评判,这就标示以阐释为主体的批评话语开始运作,也同样意味着党史文本从话语生产进入意义生产。也就是说,党史文本经阐释而被重新厘定的价值已锁入一定的代码,获得新的解释和分析,最终形成展现在公共学术领域中新的文本话语——它的价值取向,可能是肯定性的,也可能是否定性的,当然也可能介于中间状态,被中性确认。
毕竟,阐释是批评者的阐释,阐释的维度只能是批评者的维度。没有任何理由画地为牢,要求党史批评只能在这里展现,而不能在那里出场,更不能置批评风格、批评方式、批评视界等等限于单一策略。一旦批评者被刓方为圆,批评也就没有选择阐释代码的余地,深度阐释将变得举步维艰,无论来自历史的现代主义批评,抑或历史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在这里只能滑出党史批评界域之外,而党史批评本身将无法迎接奔突而至的学术挑战,更无法在批评学术共同体内确立自身的原则。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党史批评似乎无法出生。
党史批评不可能是纯粹价值无涉,当然也不应当毫无成规地在学术空间漫游。党史批评应当在党史的学术逻辑设定的场域发言,在相应的知识谱系、理论标准和现实问题的复杂互动中袒露自己的批评身份。不过,对于党史批评来说,由于批评者主观因素的限制,由于与党史本事的时空距离感而导致的判断不完整性,阐释性的批评极易误入被空泛所遮蔽的圈套,这就是过度阐释。正如党史文本常常存在过度演义一样,党史批评也因批评者知识结构的老化、意识形态的情感诱惑,或者浮浅的好恶观念、想像性的解释情调,导致批评空间的随意放大,以一己之见拔高党史文本的学术价值。这种过度阐释,非但无助于增加批评的分量,反而使批评失去应有的学术尊严。
二、党史叙事与批评的内在张力
党史批评是党史文本阅读与理解的后续动作,批评是对文本的分析、判断与评价,它的基础首先是建立在文本所提供的知识与思想信息之上的。没有这一点,批评就将不可能,因为没有对象、没有目标,也就没有批评的前提。反之,党史文本必须而且应当接受批评,这是检验党史文本在学术思想上居于何种价值档次的必要举措,而党史批评在这当中也能显示它最起码的思想与历史分析功能。
当然,作为批评群体中的一种类型,党史批评可以展现各色各样的面具,但它绝不是一种故友重逢时的寒暄式的交流,它必须直逼党史文本的内宫后殿,而所谓的内宫后殿,就是党史文本的本质属性。党史文本的本质属性,就是它作为历史文本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就像任何历史文本一样,党史文本首先是一种历史叙事文本。现代叙事学提示,叙事“通常被看作是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它通过对某件事情或某些事情依时间顺序的描述构造一个可以理解的场景即有意义的语言结构。”⑤ 时间维度是叙事文本的内在特征,尽管虚构文本如小说也具有叙事的时间性,并且如利科所揭示的,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具有“结构统一性。”⑥ 但是,即便如此,始终被认为将历史等同于文学的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也不得不承认“造成‘历史’故事和‘虚构’故事不同的,首先在于其内容,而非其形式。历史故事的内容是真实的事件,实际发生的事件,而不是虚构的事件,不是叙述者发明的事件。这意味着,历史时间向一个将来的叙述者呈现自身的形式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建构的。”⑦ 党史叙事同样必须建立在时间的演讲上,这点常常被党史研究者所忽略,而作为严格学术规范的党史文本,只有在时间概念渗入叙事形式之中后,文本的历史意义才能产生,党史的真实性才能得到有效验证。
显然,党史批评关注的,首先并不是作为文本的党史研究的立论与结论是否宏大——尽管这些面相往往被认为是必要的,而应当是判断这个文本是否具备历史叙事的本质特征以及支撑叙事的各种要素,如时间序列的存在及其合理化便是其中最关键的要素。一旦批评的指针朝向文本的叙事特征,那么文本内在历史情节的合理性结构和事实的清晰度,就成了批评首当捕猎分析的目标。党史文本中的事件(包括人物活动)历史性,需要通过叙事才能表现出来,而历史性则必须有时间结构的安排来组成。就历史的无限可能性来说,时间之流,当在可能的前提之下,按无数历史存在的实事代码来连结,这就对党史批评——只要批评一旦开始——提出两个分析的对象。其一,对某个特定的党史文本,站在批评的立场上考察,首当揭示的是,这个文本中叙事实践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说,文本撰述是否能成功地将叙事的真实性表现出来。换个说法,文本对历史行为(事件或人物)的陈述是否已叙事化。叙事化并非盲目接拼,或者随意编造。文本的叙事必须经过对各类曾经存在的事实进行裁剪,但这种裁剪能否构成历史完整性(相对意义上),则是这个文本话语是否内含意义陈述的标志,也是叙事化是否成立的前提。其二,党史文本内在历史情节的事实清晰化,对于党史批评是另一个挑战。在通常情况下,所谓的事实清晰化,往往被认为是史料使用的合理化。这固然不错,但对于一个历史文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时间结构的存在。只有时间结构的合理化,才能使事实清晰化。时间具有顺势与逆势之分,对于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它属于自然时间,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文本通过语言陈述,表示某种话语意义,这已经是文本时间了。因此,要使事实清晰化,首先必须使文本时间清晰化。当然,在这里,时间的清晰化并非一定是某月某日,但却必须是某种时间概念的符号表达,也就是说它存在短时段或长时段的起始、过程和结尾相一致的历史情节。党史批评的任务是既要考察时间概念在某个特定文本中的存在与否,还要考察这种时间——文本时间——具有逆向回忆特征的时间是否符合历史进程。
或许有人会提出,时见各类学术期刊上,常有以论说形式出现的党史研究成果,因非叙事文本,是否应排除在批评之外呢?毫无疑问,叙事文本与论说文本在陈述历史方面是不同的,怀特曾明确提出这两种文本话语的不同:“历史学家的论说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一种阐释,而叙述则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一种再现。”⑧ 虽然两种文本各有相对优点,但是,作为论说的文本,“对时间的阐释,可以是有启发性的、精彩的和明晰的等等,但是它的正当性仍有可能得不到真实的证明,仍有可能在话语的虚实方面,同有关的故事不相符合。”⑨ 因此,叙事文本是基本的,而论说文本则是次要的。可以这样说,党史文本一旦进入历史范畴,它首先是叙事的,而不是论说的,正如怀特转引克罗齐的一句著名格言那样:“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⑩ 到目前为止,由于党史批评的滞后发展,致使对这两种文本的批评没有很好地展开,更谈不上从史学学理上对之作出必要的区分。党史批评是作为历史批评的一种方式而存在,那么批评的重点就应当放在叙事文本方面,而且党史批评之所以必要,其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在历史观念上区分这两种文本。
三、党史批评的意义话语再生产
批评到底是一种价值判断,既然是判断,就必要有所取舍。在任何价值批评方式中,不同的价值判断——只要这种判断在学理上是成立的,都不可能回避批评话语的产生。批评话语一旦产生,就意味着批评对象——某种特定的文本,已经被重新解构,意味着文本内在的文化代码被重新安排,这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已不是文本固有的言说系统,毋宁说是一种新的意义的诞生。显然,批评的结果将不得不(假如不如此的话,它将毫无价值)再生产出超越固有文本的意义话语,这大概是任何一种批评存在的依据。
历史批评是大花园,党史批评隶属其中,它有居住这个大花园的身份证。不论是否夺人眼目,党史批评不应随意越过花园的栏栅,因为栏栅内有它的游戏规则,历史的观念是它最基本的学术边界。毫无疑问,党史批评不应当也不可能与历史批评中的其他形式雷同,它有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不妨一枝红杏出墙来,形成符合学科规范的话语系统。在整个历史批评话语生产流程中,党史批评话语尽管可以是其中的一个门类,但却应当在话语内部隐藏符合身份的批评冲动。
党史批评无论情愿与否,一旦进入批评场域,便成为党史文本与党史知识再生产的中介,它已不仅仅是文本知识合法性督察功能的体现,更具重要的是,它是新文本意义再生产的知识制造者。新文本不是党史文本的简单翻版或延伸,也就是说,具有积极意义的批评,在党史文本被重新阐释后,必将形成一个新的具有内在价值重估的文本。新文本最大功能,在于意义阐释,而不是叙事重复。显然,这是一种文本转换,从党史文本到批评文本的转换,它既呈现形式上的思维转向和语言转向,同时也呈现内容的从叙事到阐释的转向。
当然,批评的存在,对于党史文本而言,意味着种种不同的解码方式享有各自的阐释空间,在这空间之中,党史批评与党史文本之间产生了对话。对话不是单向度自话自说,而是党史文本为党史批评提供最起码的分析判断元素,而批评则探讨了文本的意思,也就是巴特所称的批评产生意思(11),这里的“意思”不应仅作狭义解释,而应当作文本话语交流的一种持续,是“对话”中的意义再生产。在此之中,党史批评拥有意义再生产权——这种话语权的存在,可能导致各种党史“文本”产生不必要的不安,甚至反感,但又不得已面对它——一种无奈的现实。党史批评可以挑战党史文本的所有知识前提,修改原有的知识谱系,质疑立论的理论预设,这是批评特质所做的天然允诺。对于党史文本的事实析义、道德判断、意识形态评价,甚至语言符号传达历史信息的方式等,党史批评都可以表示自己的意义立场,公开亮出分析策略。无论“表示”什么,党史批评都是在党史知识场域中,从一种话语到另一种话语的置换,亦即格雷马斯所谓的“置换代码”(12)。置换后的话语代码是对前话语代码的重新编排,这种编排,可能是对原代码(即党史文本)隐性意义的重新发现,也可能是对其显性所指的重新阐释,两组合围,使党史文本可能有的(绝非一定有)内在价值,以新的意义文本呈现出来,从而继续开始新文本与新理解的循环旅程。
应当提醒的是,党史批评导致意义再生产,它的被认可与否,直接关系到这种再生产是否能规避被人视为一种无效生产。也就是说,这种意义再生产是否具备意义价值,将决定党史批评的合法性。当代学术早已不承认独断论的权威,任何批评企图为学术走向定下音调,以便充当“立法者”的角色,也已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即便不将党史批评装入孤独嗫嚅的批评模式内,党史批评的合法性,或者说它的意义再生产的有效性,也必须取得学术共同体的基本认可,而这种认可的入场券,则是看批评是否是党史学科讨论的合格参与者。鲍曼认为,在某种学术共同体内,“每一个参与者都被其他所有参与者要求用‘共同的语词’说话,他们是一个‘共同世界’的成员,共享这一‘意义共同体’”(13)。假如党史批评不是以“立法者”的角色,而是以“阐释者”的身份,在党史学术共同体内出场,并以对话与交流的方式展示批评的魅力,那么党史批评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批评话语,或许并非痴人说梦。
(作者附识:本文曾被某刊采用,但标题被换过,有“文不对题”之嫌;正文亦被删改近半,结构有令人支离之感,故在《党史研究与教学》重发,特此声明。)
注释:
① [法]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② [澳]丁·丹纳赫等:《理解福柯》,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
③ 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⑤ 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⑥ [法]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⑦⑧⑨⑩ [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董立河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37、37、37页。
(11) [法]罗兰·巴特:《批评与真理》,《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2) [法]A.J.格雷马斯:《论意义》上册,吴泓渺、冯俊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3) [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