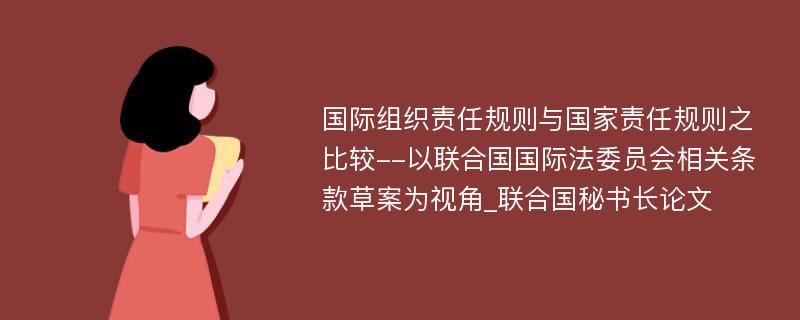
国际组织责任规则与国家责任规则之比较——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有关条款草案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则论文,联合国论文,责任论文,国际法论文,国际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组织责任是国际组织法的一个基本问题。然而,在现行国际法上并没有关于一般的国际组织责任的明确规定,只在某些技术性领域(如外层空间法、海洋法及国际环境法等),有国际条约对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做出专门的规定。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经过多年努力,继2001年二读通过了《关于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国家责任条款》)后,于2005年8月审议并通过了《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条款草案》),它目前仅涉及第一部分“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包括四章内容,共16条案文。该草案虽然还未成为现行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件,尚属学者学说的范畴,但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欲结合以上两个条款草案,集中探讨如下问题:同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它们的国际责任规则有哪些异同之处?针对国际组织责任方面的某些法律空白,能否类比适用国家责任的相关规则予以处理?在展开这些问题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行界定与国际组织相关的责任问题。
一、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界定
国际组织在与各个国家、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各国的自然人或法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各种法律关系,并产生与国际组织有关的各种责任问题。
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国际组织本身的法律责任。当某一国际组织侵害到一个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时,若该侵害是因国际组织违反了条约规定或国际习惯法下的国际义务而造成,那么该组织就得承担责任。例如,联合国维和行动对有关国家及其国民造成的损害责任。其二,其他法律主体对国际组织的责任。譬如,如果国际组织的权利受到其他国际法主体的侵害,那么该组织有权要求赔偿(此时将产生国际组织作为受害者的索赔权)。国际法院在1949年的“在为联合国服务而受损害的赔偿案”(以下简称“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认为,当联合国的职员在执行公务时遭受损害,联合国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就联合国、被害人或继承人受到的损害提出赔偿要求。① 其三,国际组织成员国对第三方的责任。所谓第三方,主要指的是直接与国际组织发生交往而形成的法律关系的相对一方,但它不是国际组织成员国。成员国对第三方的责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这种责任的性质属于赔偿责任(liability)。诚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在某一国际组织的行为侵害到第三国或其他国际组织时,如果前一国际组织本身不具有法律人格,它就不能成为独立于其成员国的权利或义务的承受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归因于国际组织的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债务或不法行为的责任将由该组织的成员国承担。然而,如果该组织确实具有法律人格,情况则不同。独立的人格隐含着对发生的活动承担责任。② 换言之,若某一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该组织的成员国对第三方则一般不承担责任。但成员国的责任可以在下面三种情况下产生:通过国际组织的章程做出明文规定,或者如果事实上该组织处于有关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或在法律和事实上以该国的代理人资格行事,或者在特定情况下由该国单方面做出了保证或担保。③ 在上述国际组织责任的三个方面中,第一和第二个方面属于一般性的问题,而第三个方面,即国际组织成员国对第三方的责任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它在若干例外的情况下才存在。根据《条款草案》第1条,该草案涉及的规则适用于国际组织责任的上述第一和第二个方面,即既适用于一国际组织本身负有的国际责任,也适用于一国对某一国际组织负有的国际责任。
在论述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时,首先应区分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的责任与在国内法上的责任。依据各种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或暗含权原则,国际组织在各成员国甚至非成员国国内享有法律人格。由此,国际组织能够独立承担国内法上的责任。这样,在国内法院,自然人或法人可以依据同国际组织签订的合同或者基于国际组织所为的侵权行为,提出某一国际组织的责任或赔偿责任问题。鉴于与国际组织相关责任情况的错综复杂,《条款草案》第1条规定,该草案仅处理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即只从国际法角度出发,处理国际组织依据国际法负有的责任,而不涉及国际组织依据国内法而负有的责任或赔偿责任问题。
与国家责任分为违法责任和国际损害责任两种相对应,从责任的起源来划分,国际组织的责任可分为以下两种:可归因于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国际组织责任,以及由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造成的损害性后果而产生的侵权行为责任。前一种违法责任,起因于国际组织自身的国际不法行为,它与国家的违法责任情况相同,损害不是引起这种国际组织责任的必要条件;后一种侵权行为责任则要求有损害性后果的发生方可引起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这种责任,与相对应的国家责任一样,只有当国际组织进行了一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时出现了违反国际法所规定的一项义务的情况,才可能引起国际责任。例如,当某一国际组织在从事一项不加禁止的活动,但却未能遵守有关的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此时该组织便可能承担国际责任。根据《条款草案》第1条的规定,该草案仅适用于国际组织对国际不法行为所承担的责任,这种违法责任是最常发生的国际组织责任。
国际组织的责任本应包括非政府组织的责任在内,因为这种从事跨越国界活动的民间组织或根据国内法成立的国际组织,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然而,鉴于非政府组织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情况复杂,难以规范,故《条款草案》把这类组织的责任排除在外。《条款草案》第2条规定,该草案中的“国际组织”是指根据条约或受国际法制约的其他文件建立的拥有自己的“国际法律人格”的组织,亦即政府间国际组织。
在《条款草案》中,“责任”是指国际组织或其成员在履行国际组织职能中所从事的国际不法行为在国际法上所引起的后果。也就是说,《条款草案》所处理的国际组织责任并没有涵盖现实生活中国际组织的所有责任,综括前述,该草案不涉及如下几种国际组织的责任:国际组织的民事责任(即国际组织对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国际组织在国内法上的责任、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此外,为了与《国家责任条款》有关国际组织责任的第57条相衔接,《条款草案》既处理国际组织的责任,也将作为国际组织成员的国家对国际组织行为承担责任的情况纳入其中。
二、国际组织责任规则与国家责任规则的相似之处
国家国际责任的原则适用于任何国际法主体,包括国际组织。这诚如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具有普遍性,这些条款所反映的原则明显适用于任何国际法主体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④ 联合国秘书长曾在1996年的一份关于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的报告中指出:“普遍公认可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国家责任原则,即如果违反国际义务而导致损失,而且这种损失是由国家(或国际组织)造成的,那么该国(或该组织)应承担赔偿责任。”⑤ 因此,国际法委员会在讨论国际组织责任问题时,对与涉及国家责任问题相类似的问题,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即借鉴了《国家责任条款》的模式和表述。这样,国际组织责任规则与国家责任规则之间就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它们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责任的构成方面,《条款草案》第3条所规定的一般原则,是按照《国家责任条款》第1条和第2条所规定的适用于国家的一般原则的模式拟订的,故此两种责任的构成要素相同。
《条款草案》第3条第1款规定了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一般原则:“一国际组织的每一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国际组织应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国际责任的原则,在1999年国际法院“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的咨询意见中也得到了重申。法院指出:“享有法律诉讼豁免问题不同于对由于联合国或其代理人以公务身份采取行动造成的任何损害予以赔偿的问题。对此损害可要求联合国承担责任。”⑥ 国际组织的责任是由该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那么,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是怎样构成的呢?对此,《条款草案》第3条第2款的规定是:“在下列情况下,一国际组织有国际不法行为:(1)依国际法,由作为或不作为构成的一行为属于该国际组织的行为;而且(2)该行为构成对该国际组织国际义务的违反。”这表明,与一般的国家责任一样,因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发生的责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存在违背国际组织国际义务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且该作为或不作为依国际法可归因于该组织。实际上,《条款草案》第3条中两款规定的顺序和措词均与《国家责任条款》第1条和第2条中的一样,只是将“国家”改成了“国际组织”。
事实上,《条款草案》的这种处理规则是对当代有关国际组织责任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在国际法委员会讨论国际组织责任专题之前,学者们就已指出:国家责任的构成要素(违反国际义务和不法行为归因于国家)同样适用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确定。⑦ 国际司法判例和国际组织实践也支持这一规则。例如,在1980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地区办事处案中,国际法院指出,正如一个国家会因其对国际组织的侵害而负责任一样,国际组织在侵害到一个国家时,如果该侵害是因该组织违反条约规定或国际习惯法原则而造成的,那么该组织同样要对损害该国的行为承担责任。⑧ 国际法院早在1949年的赔偿案中就已经指出:国际责任的基础是违反国际义务。⑨ 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的实践证明,即使国际组织实施了有害的行为,但如果此行为不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反,那么该组织不承担责任。针对联合国维和部队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和规则的军事行动所导致的损害,联合国总是拒绝承担责任。⑩
(二)在行为的归属问题上,《条款草案》第二章有关可归属于国际组织行为的条款,以《国家责任条款》第二章相关部分为参照,处理了哪些行为应归属于国际组织的问题。归属责任规则是要解决在哪些情况下,哪些国际不法行为应当被作为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行为而由它们承担国际责任。而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组织,其行为都是通过个人的行为而实现的。由于这一缘故,比照《国家责任条款》第4条至第7条和第11条,《条款草案》依次在其第4条至第7条中规定了可归因于国际组织的行为的四种情况,它们分别是:
第一,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所谓“代理人”包括该国际组织行事时所借助的官员和其他人或实体。而在确定该组织的机关和代理人的职能时,应适用该组织的规则(关于“国际组织的规则”的含义,见后面第三部分的有关阐述)。以联合国为例,联合国的行为不仅包括其主要机关和附属机关的行为,还包括联合国的代理人的作为或不作为。在此“代理人”不仅指联合国官员,也指根据联合国的机关赋予的职能而为联合国行事的其他人员。对此,国际法院在赔偿案中也予以了确认:“本法院非常宽泛地理解‘代理人’一词,也就是说,此人是本组织的一个机关委托履行或协助履行它的一项职能的任何人,而不管是否向他支付薪酬,也不论是否长期雇佣他。简言之,就是本组织通过其发挥作用的任何人。”(11)
第二,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交由另一国际组织支配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如果后一国际组织对该行为行使有效控制,那么该行为应视为后一国际组织的行为。在现阶段,国际组织责任问题较多发生在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以及维和部队的成员的活动所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在于有关不法行为是否可归因于联合国。如果不法行为者或维和人员是处于其本国的管辖之下而非联合国的管辖之下,那么联合国不承担此项不法行为的责任。1950年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和1990年在科威特的军事行动中,有关的部队并不在联合国的控制之下,因而排除了联合国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中的有关责任。(12) 不过,原则上,联合国认为它对维和部队的国内特遣队的部属拥有唯一的控制,基于此,联合国的法律顾问曾指出:“作为联合国的一个附属机关,一支维和部队的行为,原则上可归属联合国。如果实施此种行为违反了国际义务,则会引起联合国的国际责任及其赔偿责任。”(13) 例如,20世纪60年代早期,联合国在刚果的维和行动中,因维和部队的违法战斗行动对比利时、希腊、意大利、卢森堡和瑞士等国的国民造成了伤害,这些国家向联合国提出索赔要求。为此,1965年联合国分别与这几个国家缔结了赔偿协定,做出了一揽子赔偿。
在确定一国际法主体交由另一国际组织支配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的归属问题上,许多学者主张采用有效控制原则。再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为例,出于军事行动的效率考虑,联合国坚持要求对维和部队进行唯一的指挥和控制。然而,有关行为的归属应当以实际的指挥和控制为依据。联合国秘书长在1996年联大第51届会议上所作报告中的下面这番话说明了这一点:“联合国对联合国部队与作战有关的活动负有国际责任的前提是,假设有关行动完全在联合国的指挥和控制之下……在联合行动中,军队行为的国际责任在于根据确定军队提供国和联合国之间合作方式的安排所赋予的行动指挥和控制权。在联合国与军队提供国之间没有正式安排的情形下,则根据双方在行动中所行使的有效控制的程度逐一个案地确定责任。”(14)
第三,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中,只有当有关的指示对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具有约束力时,该行为才可归属该组织。此外,出于保护第三方的需要,即使有关越权行为被视为无效或不符合该国际组织的规则,也可能引起该组织的责任。这一越权或违背指示行为的责任规则已获得国际司法实践的确认。国际法院在1962年关于联合国某些费用案的咨询意见中,接受了将国际组织机关的越权行为归于该组织的可能性,法院表示:“如果确定所涉行为属联合国职能范围内,但据称是由若干机关以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述职能分工的方式启动或实施的,这就涉及联合国的内部组织架构。若该行为对内部组织架构而言是违规行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产生的费用不是联合国的费用。国内法和国际法都预期可能发生法人或政治团体因一代理人的越权行为而对第三方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法律顾问在2003年2月7日给国际法委员会的信中也认为:“如果一官员未遵守规则或玩忽职守,那么,即使他逾越了授予他的权限,也可将所涉行为归于该国际组织,但该官员并非以官方身份行事的行为不可归于该国际组织。”(16)
第四,国际组织承认并接受其为自身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不属于某一国际组织的行为的归属,取决于该组织对该行为的态度。这种行为若获得某一国际组织的“承认”和“接受”,则表明该组织认可或同意该行为是其自身的行为,并为此承担责任。支持这一责任规则的案例,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第二审判分庭的一项判决。在“检察官诉Dragan Nikolic”一案中,分庭要判定的问题是,逮捕被告的行为是否可归因于稳定部队。也就是说,在假定的事实基础上,是否可以认为,稳定部队已经将个人所采取的行为“承认并接受为其自身的行为”。分庭的结论是,稳定部队的行为不等于将这些违法行为“接受或承认为其自身的行为”。(17)
(三)在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问题上,《条款草案》第三章(第8-11条)四个条文对国际组织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界定,与《国家责任条款》第三章(第12条至第15条)(18) 规定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将“国家”改为“国际组织”)。《国家责任条款》第三章的规定是适用于任何国际法主体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一般性原则,将这些原则适用于国际组织而产生的相对应规则,譬如,若某一国际组织的行为不符合一项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该组织就违背了该项国际义务;国际组织违背国际义务必须是在该义务有效的时期内发生,才产生该组织的责任,等等。
(四)在一个国际组织对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问题上,《条款草案》第四章第12条至第16条,与《国家责任条款》第四章第16条至第19条相对应。除了国际组织对其自己的国际不法行为负有国际责任这一国际组织责任中最常见的情况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特定情况也可能引起国际组织的责任,这就是《条款草案》第四章规定的内容。据此,国际组织可因为以下理由被追究责任:(1)援助或协助另一国际组织或国家从事不法行为;(2)指挥和控制另一国际组织或国家从事不法行为;(3)胁迫另一国际组织或国家从事一种在没有胁迫情况下仍会是国际不法行为的行为;(4)一国际组织可对作为其成员的另一国际组织犯下的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条款草案》对构成这些情况的条件和处理方式的规定与国家责任方面的相同。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国家责任规则借用来的一般性原则和规则,是如何适用于本质不同的国际组织的责任和涉及国际组织行为的国家的责任情况。《美国国际法杂志》的编委马迪逊认为,《条款草案》的特别报告员将那些与国际组织职能有关的国家责任条款适用于国际组织责任规则的拟订当中。(19) 在《条款草案》和《国家责任条款》中,不仅作为责任承担者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均是国际法的主体,而且这两个草案处理的国际责任的性质也是一样的,即因国际不法行为而产生的责任。基于这样的共同点,对那些与涉及国家责任问题相类似的问题,《条款草案》似乎没有理由不采取与国家责任规则基本一致或相似的模式、内容、处理方式和措词表述。
三、国际组织责任规则与国家责任规则的相异及特殊之处
国际组织种类繁多,情况相当复杂,而且,国际组织的固有特性和职权范围均有别于国家,这些因素使得国际组织责任规则与国家责任规则不可能完全相同。两者的差异体现为,一方面,调整国家责任的原则和规则大多需要做必要的修改后方可适用于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国际组织与国家的责任范围并不相同,两个条款草案中部分条款的规定存有明显的差异。
《条款草案》虽然借鉴了《国家责任条款》的模式和表述,但它并非照搬《国家责任条款》的内容,而是对相应的条款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譬如,题为“将行为归于一国际组织的一般规则”的《条款草案》第4条,相当于《国家责任条款》第4条,其第1款在将国家机关的行为归属一国时,强调“不论该机关行使立法、行政、司法职能,还是行使任何其他职能,不论它在国家组织中具有何种地位,也不论它作为该国中央政府机关或一领土单位机关而具有何种特性”。在带有双引号的规定中,最后一句的描述并不适用于国际组织,所以没有被移植到《条款草案》第4条中;其他有关国家履行的全部职能的说明文字,鉴于各个国际组织的情况差别很大,故而《条款草案》第4条第1款只是概括地规定“不管该机关或代理人相对于该国际组织而言具有何种地位。”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在确定将何种职能委托给某一机关或代理人时,通常是按照《条款草案》第4条第3款提及的“国际组织的规则”办理的。该款的规定为国际组织责任规则所特有。所谓“国际组织的规则”,根据《条款草案》第4条第4款的规定,它包括:一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件(或称“组成文书”、“组织章程”)、该组织依据组织约章所通过的各种决定、决议和其他文件,以及该组织业已确立的惯例等。“国际组织的规则”有时被称为国际组织的内部法,该内部法主要由调整国际组织内部各种关系的法律规则组成,其涵盖诸如雇佣关系、附属机构的建立和职能、行政服务的管理等事项。(20)
此外,较之于《国家责任条款》第4条,《条款草案》第4条增加了一款(第2款)规定,赋予“代理人”一词以宽泛的含义,以涵盖《国家责任条款》第5条和第8条所指称的“人或实体”和“一个人或一群人”等名词,进而使《条款草案》第二章的篇幅比同为界定行为归属性的《国家责任条款》第二章显得更简洁。这种改变实为事出有因。《国家责任条款》第5条的标题为“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人或实体的行为”,其中“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提法对国际组织不合适,且此陈述不能准确地表示某一实体与某一国际组织之间的可能关系。而《条款草案》第4条第2款规定:“‘代理人’一词包括该国际组织行事时所借助的官员和其他人或实体”。该条款的定义使“代理人”一词足可涵盖《国家责任条款》第5条所设想情况中涉及的“人或实体”。类似地,对于《国家责任条款》第8条所指的“一个人或一群人”,放到国际组织的语境中,对涉及实际上按照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指示或在其指挥或控制下行事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可视为《条款草案》中的代理人。
《条款草案》中的多数条文虽然沿用了《国家责任条款》的一般写法,但鉴于国际组织和国家的特性不同,它们的责任范围是有差别的。以有关行为的归属问题为例,《条款草案》与《国家责任条款》的规定之间存有一些根本的区别。《条款草案》有关这一问题的规定仅四条案文(第4-7条),而《国家责任条款》适用于此问题的有八条案文(第4-11条),其原因在于后者处理的一些问题只与国家有关,这些问题只在例外情况下才可能适用于国际组织。例如,《国家责任条款》中有关官方当局不存在或缺席时实施的行为(第9条)和叛乱运动或其他运动的行为(第10条),它们也涉及行为的归属问题。但这些条款涉及的情况不可能在国际组织方面发生,因为这些条款已预先假定:行为所归属的实体行使着对领土的控制。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国际组织不仅缺乏属人管辖权,而且其属地管辖权也是有限的。除了联合国担任过对某一领土和其居民的管理当局(1999年联合国在科索沃和东帝汶建立临时管理当局被视为国际组织管理领土的事例)之外,国际组织根据它与东道国之间的协议只对被承认为国际组织“总部场所”的很有限的区域具有属地管辖权。因此,国际组织的责任不能依据传统的领土主权原则来确定。(21) 由于涉及属地管辖的情况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微乎其微,因而没有必要在《条款草案》中也做出与《国家责任条款》第9条和第10条相对应的规定。不过,万一在国际组织方面发生了上述问题而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此时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对国际组织适用《国家责任条款》第9条或第10条的规则。(22)
《条款草案》中有的条款是国际组织所独有的。譬如,在一国或国际组织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问题上,《条款草案》比《国家责任条款》多一个条文,用以处理一国际组织对作为其成员的另一国际组织犯下的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国家责任条款》中没有被提及,它涉及国际组织成员对国际组织所作决定的遵守。由于国际组织是有别于该组织的成员(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这使得该组织有可能试图影响其成员,以便通过这些成员来实现该组织不能以合法方式直接达到的逃避其国际义务的结果。为了防止国际组织逃避责任,《条款草案》第15条规定了一国际组织因向成员国和作为其成员的另一国际组织做出决定、建议和授权而被追究责任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形的责任规则并不意味着授权或建议的国际组织要为被授权或建议的成员国或作为成员的国际组织可能实施的一切违背义务行为负责。下述联合国秘书长于1996年11月11日给卢旺达总理的一封信可作为说明:“就‘绿松石军事行动’来说,虽然该行动是安理会授权采取的,但该行动本身却是在国内指挥和控制之下进行的,它并不是联合国的行动。因此,联合国不对可归因于该‘绿松石行动’的作为或不作为承担国际责任。”(23)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第15条规定的情形不要求国际组织一定要有逃避义务的具体意图,所以当一国际组织要求其成员采取某一行为,而这将意味着规避该组织的国际义务时,该组织不能通过表明它没有逃避义务的意图来推卸其责任。而且,无论有关行为对于接受决定、授权或建议的成员国或作为成员的国际组织来说是否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做出决定、授权或建议的国际组织均负有国际责任。
在《条款草案》之外,同国家责任相比较,国际组织责任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当国际组织的权利受到其他国际法主体侵害时,该组织向有关国际法主体提出索赔要求的权利,是建立在履行国际组织职能需要的基础之上的。这正如国际法院在赔偿案中所指出的:本组织向有关国家提出索赔要求的权利,是基于受害者是代表联合国行事,他在行使着联合国的职能。所以,“联合国对其工作人员具有职能保护的权利。”(24) 与此不同的是,国家代表受害人主张索赔权是基于国籍的联系。第二,国际组织履行赔偿责任的能力是有一定局限的。维也纳大学霍亨维尔登教授曾指出:“国际组织作为债务人,其信誉远比不上国家。与国家相比,国际组织能用来满足求偿要求的财产是有限的,它没有可作为报复对象的公民,也不能在国际法院作为当事方而被诉。”(25) 第三,涉及国际组织责任的国际条约规定并不多见。迄今为止,主要在一些特殊领域的国际组织责任问题上,存在着专门性的国际条约的明文规定,如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第6条和第13条,1972年《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第22条第3款以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63条等。第四,有关国际组织责任的现有实践不多,尤其是有关下面情况的实践很有限:一国际组织将其机关交由另一国际组织支配,国际组织违背国际义务,一国际组织对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
以上国际组织责任的几个特点表明,国际组织责任的现实意义不如国家责任突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与国家的国际法律人格不可同日而语。国际组织国际违法责任的基础,是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而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是成员国通过组织章程明示或暗示地赋予的。实际上,是国家赋予了国际组织权能,授予国际组织一定范围的职权,从而最终决定了国际组织责任的范围。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派生性和有限性,与国家国际法律人格的固有、与生俱来的完全性截然不同,诚如国际法院所指出的:“国家具有国际法所确认的全部国际权利和义务,但像联合国这样的一个实体的权利和义务,则必须取决于其组成文件所具体说明和暗示的以及在实践中所演变而成的宗旨和职能。”(26)“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与国家不同,国际组织不具有一般的权限。国际组织受特定性原则的支配,也就是说,创建这些组织的国家赋予它们权力,该权力的限度取决于共同利益,而创建国委托这些组织来增进这种利益。”(27)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是派生的和有限的,这意味着不同的国际组织,其国际法律人格的范围可能不一样,而人格范围的不同将带来国际组织责任的不同。学者们指出,国际组织的责任取决于国际组织与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法律地位,因而它将因国际组织的不同而不同。(28) 国际组织国际责任能力的这种差异性或多样性,与国家责任能力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综上所述,调整国家责任的规则可以有限适用于国际组织,多数国家责任规则经过必要的修改后同样可适用于国际组织。然而,由于国际组织的特性和其职权范围有限的原因,《条款草案》中有些条款是国际组织所独有的。通过对《条款草案》和《国家责任条款》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对有关国际组织责任某些问题上的法律空白或者《条款草案》未涉及的情形,一般可以类比适用《国家责任条款》中与国际组织职能有关的规则来处理。
注释:
①Advisory Opinion on the Reparations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ereinafter called Reparations case) ,ICJ Reports,1949,p.184.
②M.N.Shaw,International Law,5th ed.,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影印版,第1201-1202页。
③参见M.N.Shaw,International Law,5th ed.,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影印版,第1204页。关于国际组织成员国对第三方的财产责任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阅戈雷:《国际组织对第三方的责任》,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8》,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④2005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报告,A/60/10,第199段。
⑤UN Document A/51/389,p.4,para.6.
⑥Advisory Opinion of the ICJ on Difference Relating to Immunity from Legal Process of a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ICJ Reports,1999,pp.88-89,para.66.
⑦P.Sands and P.Klein,Bowett' s Law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Sweet & Maxwell,2001,p.520; M.N.Shaw,International Law,5th ed.,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影印版,第1200页。
⑧WHO Regional Office case,ICJ Reports,1980,p.73.
⑨Reparations case,ICJ Reports,1949,p.180.
⑩P.Sands and P.Klein,Bowett' s Law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Sweet & Maxwell,2001,p.520.
(11)Reparations case,ICJ Reports,1949,p.177.
(12)C.F.Amerasinghe,Princip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44.
(13)200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报告,A/59/10,第88页。
(14)UN Document A/51/389,p.6,paras.17-18.
(15)Certain Expen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ICJ Reports,1962,p.168.
(16)200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报告,A/59/10,第93页。
(17)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 Challenging the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by the Tribunal,9 October 2002,Case No.IT-94-2-PT,para.64.
(18)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请参阅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9)参见M.J.Matheson,Current Development:The Fifty-six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9,2005,p.218.
(20)C.F.Amerasinghe,Princip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24 et seq.
(21)E.Suzuki and S.Nanwani,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of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7,2005,pp.193-194.
(22)参见200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报告,A/59/10,第82页。
(23)见联合国文件,A/60/10,第88页。“绿松石军事行动”(Operation Turquoise)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S/RES/929(1994)号决议建立的。
(24)Reparations case,ICJ Reports,1949,pp.180,184.
(25)I.Seidl-Hohenveldern,Corporations in an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Grotius Publication Ltd.,1987,pp.87-88.
(26)Reparations case,ICJ Reports,1949,p.180.
(27)Legality of the Use by a State of Nuclear Weapons in Armed Conflict,ICJ Reports,1996,p.78,para.25.
(28)K.Gin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Responsibility" ,in Bernhardt,Rudolf,ed.,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Vol.2,1995,p.1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