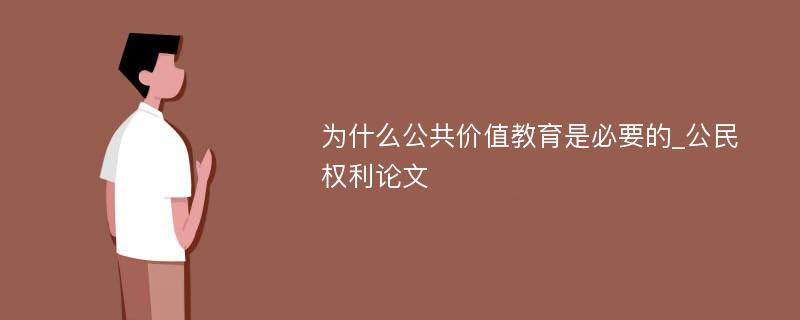
公共价值教育何以必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社会的建构依赖于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依赖于公民的价值认同。“公民道德”的概念其实蕴含着按照公共价值而自主行动的伦理标准。因此,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公共生活能够超越个人的价值偏好和利益取向,提供道德生活的形式吗?① 公共价值是否可以在普遍的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得到理性辩护?公民怎样形成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存在公共价值观教育的可能性吗?
一、公共生活的道德实践
一个共同体存在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是这个共同体每一个人共同分享的利益,它既是共同体的繁盛和美好的条件,也是个人生活福祉实现的条件。公民作为共同体的平等成员,一方面通过分享公共福祉而实现自我福祉,另一方面在个人的生活中具有扩大公共福祉的道德义务。如果没有公共福祉和公共善的支持,个人的自我价值以及个人福祉都难以实现;如果个人不能承担扩大公共善和公共福祉的道德义务,或者在实现个人利益的过程中蚕食公共利益,破坏公共善,那么公共福祉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承担促进社会的公共福祉的道德义务是共同的。公民个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必须考虑对于促进公共善的价值承当。
对公共价值的承担是每个公民不可推却的义务。从人处在共同生活环境的特点来看,个人的生活必然包含着公共影响力,也就是说,公民个人的生活行动,会产生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公民个人的行动必须自觉地关心公共福祉。也就是说,对于公共善和公共利益的自觉和积极地促进和关心,是公民的道德承担和价值承担的内容②;而且,承担促进公共福祉的责任是出于公民营造美好的共同生活的需要。③
公民个人的生活由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组成。私人生活促进个人福祉,而公共生活促进公共福祉。私人生活虽然总体上是属己的,但是有些内容与行为具有公共影响。从公民的人生而言,每个人通过有秩序的生活实践,不仅成就自己,而且成就与他人一起的共同的生活,也就是说,公民个人的生活具有公共生活的实践内容和意义。如果排除个人生活中公共生活的内容,那无疑把个人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私己者,在实现个人利益中没有公共影响。当然,虽然两种生活具有不同的表现领域,但是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两种生活都是人生有为的实践。④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本身是对个人美好生活和公共美好生活的期许的一种实践。
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公共生活实践是具有公共理性的行动,这表现在他的所有生活历程中。如果把公民的公共生活表现划分为四个领域,即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公众领域⑤,那么,公民个体的生活行动和生命价值不仅仅限于个人的私人行动领域,也表现在政治的领域、公众行动的领域、市场的领域。也就是说,公民个体具有政治领域的行动,也具有公众领域的行动,同样也具有市场行为,当然他们也具有私人领域里的行动。因此,公民的道德实践的领域也可以分为以上四个领域,也就是说,公民的道德价值的表现与实践领域必然要包括国家领域、公众领域、市场领域和个人领域。⑥
如果把公民的生活实践领域分为以上四个领域,那么公民的公共生活是四个领域中共有的特征,公民在四个领域中的行动都可能具有公共的道德影响。公民的公共生活是公民发出的以促进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为目的的生活行动及形式,而不是仅仅指以“政治事务”为特征的社会结社的行为形式。公民生活中的每一个特殊领域里都具有公共性的维护公共利益的行动。公民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中适当行动,维护公共利益,为公共福祉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公共生活的道德实践。
如此说来,公共生活是公民表现在四个领域的行动,其表征就是促进公共善。如在国家领域中,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是政治生活的行动,其特征就是公民为政治的善付出的参与行动;在市场领域中,公民对于公平交易规则的遵守、合法地缴税、履行社会责任等就是他公共生活的内容;在公众领域(公民的自愿结社)中,公民的志愿行动以及参与民间组织,关注公共问题,就是促进公共利益的行动,他理性地参与针对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公共讨论也是公共生活的行动形式。就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公民对于子女的教育的公共立场以及自己节制或环保的生活方式等,都具有促进公共福祉的意义,具有公共性。因此公共生活领域不单纯是一种社会领域,也不单纯是完全脱离个人生活的政治生活,它把部分市场领域的生活以及个人生活的一些品质的行动也看作是公共生活的形式,因此,公共生活的范围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和公民组织。
从四个领域来理解公民的公共生活,实际上整合了公民的生活实践,将公民的多种生活领域和多种行动领域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公民的生活截然分离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不是把私人领域看作与公共善的促进无关的领域,也不是把公民的公共生活仅仅限于政治领域。如果把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行动看作是没有公共影响力的,就会导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截然断裂,个体在私人领域的为所欲为可能会造成对公共利益的危害。⑦
公共生活作为不同生活领域的重叠部分,使得公共道德领域具有了一种整合的范围,使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范围内,都能够以公民的价值立场发出行动,使得公民自己的行动有一种更全面、更综合的价值立场;也使得公民把公共福祉作为价值行动的一个重要维度,从而使得消费领域、私人领域的行动不仅促进个人的福祉,也促进公共福祉;不仅符合个人利益,也符合公共利益。
公民生活的四个领域依赖于公民的面向公共生活的实践行动。国家领域的正义、公共领域的自治、市场领域的有序和公平、私人领域的节制和得当,都与公民的公共美德相关,都是通过公民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对公共福祉的共同促进而形成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原子式的私己个体的选择和自我确认。所以,公民的公共生活的道德实践是文明社会的共同生活的伦理保障。这意味着公民不仅具有自我选择的道德理想,而且也具有对于公共生活的价值承担,具有对于公共生活的道德基础的认同,或者说,公民具有公共(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所有公民在理性上普遍认同和实践的,表达了一个社会在公共生活中的什么是值得追求和实现的,什么是值得敬重的事物,这是公共生活的重要支点,是对共同生活的公共价值的认同。没有这样的公共价值及其认同,共同生活的和谐就不可能实现。
因此,公民的生活实践具有公共生活的纬度。公共生活是公民在生活领域追求公共福祉、维护公共利益而表现的行动⑧,不仅仅是指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生活,即不仅仅是发生在政治领域里的行动。这样的公共生活激发出人们的公共精神,将他们聚合到共同体中——进入到与其他公民的联系和团结之中,在不背离个人福祉的基础上,积极实践扩大公共福祉的公共生活。⑨ 公民的公共生活直接面向公共善的促进,这是公民实践的本质。公民对这种公共生活的实践是他之所以成为公民的关键。公民这一概念是指称,公民拥有的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使他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自觉服务于公共利益,从而自觉地捍卫共同体的自由和繁荣、并最终确保公民自己的个人自由和繁荣。
二、公共生活的普遍价值
从公民个人的公共生活的范围及其客观性来看,为公共生活奠基并实现其可能性的公共价值是存在的。公共价值是由文明社会的公共福祉所定义,既促进公民的个人的公共生活的道德实践,又促进公共福祉实现的普遍标准和原则,是支撑公民公共生活的基础。⑩
公民的私人生活的价值与公共生活的价值是不同的。从个人的生活的领域来说,个人生活所依赖的价值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促进个人的自我生活的价值,另一个是促进个人的公共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把促进个人的自我生活的价值叫做个人价值,那么,促进个人的公共生活的价值就是公共价值。尽管公共价值是引导公民个人的公共生活的价值,但它不是个人自我决定的,而是一种普遍共享的。因为公共价值是表现在共同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而公共生活是公民们发生公共交往的生活,尽管公共价值的承担主体是公民个人,但是它是所有公民共同追求的价值,因此是普遍的、具有指示性的公共价值。(11)
就价值的普遍性而言,源自人性普遍需要的价值是第一性的基础价值(primary values),第二性价值(secondary values)是那些来自不同传统、不同习俗和不同社会背景相关的价值。第一性价值或基础价值是普遍的,是源自普遍人性的,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共同的;而第二性价值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个人判断。每一个人的美好生活的实现既基于第一性的基础价值的实现,也基于第二性价值的实现。但是第一性价值的实现是每一个人生活福祉的根本需要。(12)
就公共生活而言,公共价值是与公共生活促进公共福祉的基本需要相关的。从普遍人性、历史延续、社会凝聚三个角度看,这些基本的需要是源自人的共同生活本性的需要。比如正义、公平、自治、政治平等、希望,和平、生活中免除恐惧、公民友爱、公共安全、参与、认可、尊重,等等。因此是“基本价值”,也就是第一性价值。
公共价值是涉及公民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实践的共享的、在理性上共同认可的价值。这些价值基于人类每一个人普遍的共同生活的需要,因此具有普遍性。公共价值是人们通过理性而共同认可或接受的。它能够获得所有理性的人的赞同,因为它保证公共福祉的提升的需要和要求,保证人们惬意的共同生活的可能。在一定意义上说,公民个体在特殊的个体性的生活中追求的第一性价值和第二性价值必须以公共价值为基础和依托。公共价值虽然指导的是公民的公共生活,但是因为公共生活与公共福祉和个人福祉不可分离,真正的公共价值与个人价值是和谐的。
公共价值尽管在实践上涉及到个人的判断和评价,但价值内容不是个人自定的。公民个人对公共价值的排序可能是不同的,但是,公共价值的实质内容都是他公共生活的基础。与个人的私人领域里的价值不同,公共价值的体系里不同价值必须是兼容的,也就是不同的价值内容之间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否则,追求一种公共价值的实现而损害另外一种公共价值的实现,那公共生活就根本不可能,因此,公共价值之间是兼容的。尽管有的人把正义作为自己公共生活的首要价值,但是不妨碍他关心他人的福祉;同样,尽管有的人把关心他人放在首要位置,也不妨碍他对政治参与的价值的追求。
公共价值的普遍性来自于公共生活的需要,公共生活的实现依赖公共价值的奠基和引导。因此,公民的公共生活的实现必须选择和认同公共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公共价值的认同和实践是公民的道德实践的内容,即在公共生活中追求公共价值,是公民的道德追求与实践的重要部分,对于形成公民的公共道德风范以及社会的道德风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民的公共生活的道德来自于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公共生活以追求公共价值(比如政治的正义价值)为基础,因此,公共生活的良好实践包含着对公共价值的归属和承诺。(13) 尽管公民的公共生活的程度和范围不同,但是公共生活的价值是普遍的,它不是个人的一种简单偏好,因为个人的偏好无法具有公共性。从公共生活的特性而言,公共价值是普遍的,对公共价值的认同是公民的价值承担的普遍义务。
尽管我们在选择美好生活的方面具有自由权利,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需要一个共享的公共空间,需要共有的公共善和公共利益。我们还需要公共制度,因为公共生活空间和公共制度维护不同的生活方式合法和非法的界限,维护公民相互交往的条件,如平等的身份,还维护文化的条件以及社会的整体的道德风气,还要保障公民的个人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动力。因此,公共生活空间和公共制度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原则的基础上,这就需要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对公共制度、公共规则以及他们包含的价值的理解和共识,需要公民追求公共价值实践的道德行动,需要公民对文明社会的共同生活表示出道德价值的承诺。因此,公共价值的认同是公民的公共道德实践的基础。
在伦理性的公共生活中,公民的德性表现出公共性。德性不是私人生活的独有,德性本身意味着个体性和公共性的和谐,一个人在生活中获得的德性品质诸如正义、智慧、节制、勇敢、希望、诚实等,不仅表现在个人生活中,而且也表现在他的公共行为中。仅仅沉湎于私人生活的个体,对他者的冷漠和公共生活的疏远,无法形成德性品质。具有德性的人就是具有公共德性品质(civic virtues)的人。(14) 生活就是与他人一起生活。生活的德性就是与他人共处的德性,这不仅造福于个人,也造福于公共的文明社会。这不仅是人性不断完善的基础,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伦理传统的基础。所以那种排斥公共生活的所谓的洁身自好,虽然在个人的道德追求中是可能的,但是却容忍了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恶,在德行上依然是欠缺的,因为并没有承担公共生活的伦理义务。(15)
公共性是道德的根本标准,人们相互交往和促进公共善的公共生活和社会空间是一个道德领域。文明社会首先是一个由道德情操所凝聚起来的价值领域,它不仅提供了一种道德网络(moral grid),也提出了公共价值认同的要求。如果说公共生活是公民个人服务于其他公民和公共善的实践,那么,公共生活就是公民的道德实践领域,也是公民个人追求道德价值的领域,也是公民的美德得以表现的领域。
三、公共价值观的教育
在现代性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价值教育的重心发生位移。价值认知的方式变得重要,而价值的内容不再重要,价值教育仅仅是让学生了解工具性价值的作用,而不是了解实质性价值的内容,仅仅学习价值选择的程序,而不是体认价值的内容与秩序。价值教育的重心放置在个体对私人生活领域中的价值及其选择方式上,价值指向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而非公共生活领域,价值成为个人偏好与个人倾向性。价值教育忽视了普遍性的公共价值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培养。公共价值的教育被排除在外。
现代的价值教育过于专注于个人依据自己的偏好进行价值判断程序的学习,把价值选择限于个人的生活价值的自我确定,至于个人如何通过价值教育学会治理自己的生活和参与共同生活的治理,如何获得造福于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德性和智慧,如何获得公共价值的认同和承担,仅仅从个人福祉的角度出发的价值教育可能是没有作为的。现代价值教育成为了一种工具型装置,那就是在尽量减少个人价值冲突情况下扩大偏好的满足。这种价值教育也许强化了个人对自己幸福自我负责的意识,但却忽略了对公共福祉负责的公民的公共义务。
否认或拒绝公共价值,就会消解个人的价值承担的公共维度和道德维度,使得个体的生活导向以自我偏好的满足为中心,个人无法具有思考共同问题的价值视野,这导致个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稀释化,并使得个人对于公共生活失去道德敏感性。因此,如果没有公共价值的认同,没有对公共生活的价值承担的教育,公民的道德品格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从公共生活的客观性来看,关键是形成为公共福祉而行动的公民品德和公民价值观,这是我们的公共价值观教育的根本使命。价值教育塑造公民的公共价值观对促进文明社会的道德建设和公民生活的福祉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通过公共价值观的教育,公民才能理性地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才能在公共生活中付出符合价值的行动。这是公共共同生活的文明、和谐和稳定所需要的。正如前文所论,如果文明社会没有一定程度的价值共享,没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归属,没有一定形式的公民的公共道德实践,公共秩序就难以维持,文明社会的共同生活就变得举步维艰,社会的道德传统无法为继,道德风尚将会不断失落。中国社会目前的道德危机与道德教育与缺乏公共价值的维度具有一定的关系。只有当社会中的公民共同享有公共价值时,才能实现公共生活的秩序良好,才能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否则,任何制度和共同生活的基础都迟早会堕落下去。
公民不仅仅享有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公民必须具有责任意识和价值承当意识,必须具有公共理性和公共品质,这是维系社会健康与和谐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的公共价值认同是他们的公共生活道德化的基础,也是把个人的生活追求与公共福祉相互连接的基础。价值教育不仅要形成促进个人福祉的价值观,也要形成公民的促进公共福祉的公共价值观。
公共价值塑造着公民的公共生活,促进公共福祉和个人福祉。(16) 教育必须包含对于公共生活的实质性价值的学习,如果排除了公共的、普遍性的价值的学习,个人就不可能为共同生活承担伦理责任;如果价值教育仅仅是工具性的、程序性的,那么,价值教育事实上就排除了价值的道德性,教育仅仅是一种选择能力的训练,而不是养成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丑与美的判断力。这样的价值教育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仅仅进行对价值选择能力的训练,受教育者就无法理解价值的内容及其判断标准,无法确定价值指向的领域的合目的性和合道德性。所以,仅仅程序性的价值教育根本就不是价值教育,因为它没有对公民的价值选择起到实质性的引导,或者说它放弃了对公民的价值引导的责任。(17) 应该说,在公民的价值学习和道德发展中,实质性的价值引导是至关紧要的。没有实质性的价值目的,公共生活就是空洞的,公共生活的共在、公民的相互的道德砥砺也难以落到实处,公共生活的教育维度也无从实现。只有公共社会的领域承担着价值教育的实质作用,也即是成为教育性的,公共的道德价值才可能共有。
公民的价值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和促进人的基本能力和人格的健全发展,在此基础上,培养实现公共生活道德实践的公民美德与“公民风范”(civility)。(18) 这是公民彼此相互合作与关爱,同时具有个人自由的品质。(19) 这种品质表现了公民通过公共生活促进公共善以及公民之间相互友爱不以暴力和霸权相对待的伦理行动。这是实质性的公民道德品行的表现,也是在公民群体意义上的公民风范,是文明社会的伦理精神和道德风尚。
公民价值的教育同样也重视公民的自由权利,重视公民的理性精神的培养。培养公共价值观和公共精神其实也是发展公民的公共理性和社会理性(social rationality),这是建立在公民的自由基础之上的进行公共生活实践的判断力。所以,公共价值的认同并不是灌输的,并不是要培养社会成员的依附性。公共价值教育依赖并尊重公民的自由的同时,对共同生活的基础价值达成、判断、理解和认同,并不是通过欺骗公民(学生)而骗取共识。公共价值教育是通过创造公共生活的具体形式,让学生公开地运用自己的公共理性,反思公共生活中的价值问题,培育公共道德。
公共价值教育必须保护受教育者的自由权利,让他们在自由中学习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培育他们的公共理性和公民精神。为了实现这样的价值教育,我们一方面必须取缔那些束缚儿童理性发展或有碍儿童身心健康的不良的教育组织和形式,必须取缔可能会使学生的社会理性发育不良或者使公民的社会理性处于瘫痪的教育形式;另一方面,公共价值教育应当形成公民基于公共价值的道德承担,培育他们公共生活的道德风范,也就是培养公民的公共心灵。
收稿日期 2010-03-16
注释
① 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被认为生活实践中值得追求的根本原则、标准或品质,反映了生活实践的目的和可能性。价值为实践奠定基础,什么样的价值决定着什么样的行动。
② 这不仅仅是社会公德的内容,还是公民的公共道德的内容。一般意义上,公德仅仅是对公共场合的规则或道德要求的遵守,而公共道德要广泛得多,既包括公德,也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义务、对公共福祉的关心以及公共利益的促进行动,等等。
③ 公民的公共生活的行动形式和范围是不一样的,因此,公民介入共同生活的领域的侧重点可能也是不同的。但是,公民的公共生活的目的的指向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公共福祉的丰富和促进。
④ 实际上,公民德性这一术语是指称,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最需要拥有的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使我们自觉服务于公共利益,从而自觉地捍卫我们共同体的自由和繁荣,并最终确保我们自己的个人自由和繁荣。
⑤ Yanosky将文明社会分为四个领域: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公众领域。参见托马斯·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⑥ 因为,从单纯的人的社会性来看,无法区分不同的道德实践领域。单纯的个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区分难以说明人的道德实践领域的复杂性。
⑦ 我们不排除个人的私人领域的存在,也不否认私人领域的价值选择问题,但是就社会价值而言,价值的正确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力量,在社会中是普遍的。参见L.Nucci:《道德领域里的教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⑧ 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公共领域(offentlichkeit,英文是public sphere)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对二者进行调节的领域,公众可以通过对共同关切之问题进行论辩和沟通,形成影响公共事务治理的公共舆论。在阿伦特的思想里,公共领域虽然不同于国家和政治体系,但是公共领域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的。我认为,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其实包含了政治的公共权力的作用,公共领域大于政治体系,政治生活具有公共性是因为政治表现在公共领域中。我认为公民的公共生活是多样化、多层次的。因此,我从公民生活的双重性出发,提出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突出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形态差异性。公共生活领域与公共领域在许多方面是重合的,但是前者注重个人生活的特性,而后者可能具有制度性的韵味。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性的公共领域是在近代的市民社会产生中出现的,而我们不能说古代人没有公共生活。
⑨ Aristotle.Nichomachean Ethics.Book IX,Ch.6.
⑩ 制度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制度的价值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作为总体的制度实践的政治主体。价值评价的对象不是公民的行动,而是作为制度的实现者——政治的行动。
(11) 参见J·N·芬德莱:《价值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页、第15页。
(12) 关于第一性价值和第二性价值的区分,参考了John Kekes的理论。他是价值多元主义者,他认为,公民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不同价值之间甚至可能是冲突的(incompatible)和不可比较的(incommensurable),同时,没有统摄性的价值,没有可分高低的价值次序。J.Kekes.The Morality of Pluralism.Princedon University Press,1993,38; J.Kekes.“Pluralism,moral imagin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in in Education in Morality.”Ed.J.Mark Halstead and Terence H.McLaughlin,London:Routledge,1999.
(13) 当然在公共生活中存在着“搭便车”的非正义现象,这种现象对公共生活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仅是非正义地享有了公共利益,更严重的是将促使不正义行为的发生。
(14) 帕特丽夏·怀特在《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Civic Virtues and Public Schooling)专门探讨了公共生活中公民的公共德性,她虽然没有明确区分个人德性和公共德性,但是在书中她显然主要论述民主社会的公共德性及培养。在一次与我的谈话中,她认为二者有明确的区别。而我认为,在个人生活境域和公共生活境域不能明确地区分德性,因为生活是一种共在。参见帕特丽夏·怀特:《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
(15) 公共性的存在具有对人性的构成性价值,个人在实现公共性中追求卓越的德性品质,如正义、勇敢、智慧、节制等德性,体现了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对自我的一种治理理想,这使得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走向善,也使得个人的德性和公共精神获得了提升。
(16) 威廉·A·盖尔斯敦:《自由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价值多元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John Kekes也有相同观点。
(17) MacIntyre note:To teach an indeterminate morality is to teach no morality at all.参见A.MaIntyre.“How to seem virtues without actually being so,Education in Morality.”Ed.J.Mark Halstead and Terence H.McLaughlin,London:Routledge,1999.
(18) 公民的概念来自civitas,是指共同体成员合作共事的实践。
(19) 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亦可参见Michd Oakeshott.On Human Conduct.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