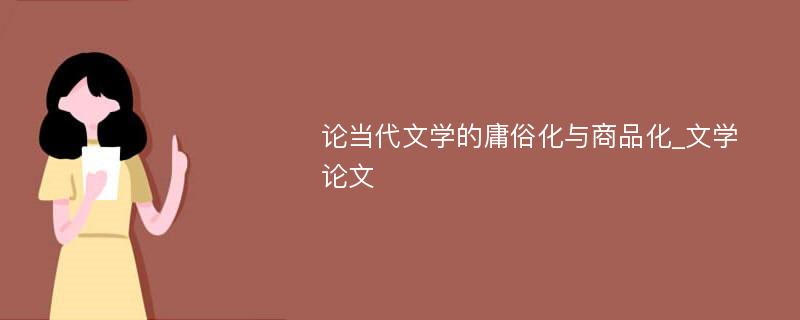
论当今文学的俗化与商品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当今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的俗化与商品化,是当今文坛上最令人注目的新景观。
所谓俗化,乃指文学由纯、雅转向通俗,以内容的贴近性和多样性及以体现对民族俗文学传统的审美继承与创新为文学特质,去求得更广泛的让市民大众接受的读者效应。任何时期的市民大众的接受心理都与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原先的刻板乏味的凝固状态,因此消费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而在文化消费上追求精神愉悦,于是文学的通俗化、生活化、娱乐化、消遣化的种种特征,就适应了这方面的需要。所谓商品化,即指精神产品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文学作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必须纳入市场商品经济的轨道,它要通过货币这一媒介同消费者进行交换,以使作家获得对自己劳动支出的补偿。毋庸讳言,文学俗化的直接诱因就是商品化,种种迹象表明文学本身越来越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与社会接轨。由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带来了新的审美意识的崛起,在精神文明领域呈现出多层次的态势,人们对具有情节性、传奇性、可读性的俗文学作品颇感兴趣,产生了超越严肃文学的阅读渴望。基于这种情况,此类作品就成了推向书肆的畅销商品,异乎寻常地“走俏”,而滞销图书市场的恰恰是与俗文学相对峙的纯、雅文学,似乎象“贵族文学”与平民大众拉开了心理距离,可以说通俗文学在不断升温中以刚健清新的生气,战胜了“阳春白雪”。面对通俗文学席卷文学界的局面,纯、雅文学创作的作家队伍中,有不少人加盟通俗文学创作阵营,他们不再徘徊于以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的制约的范围圈内,株守着原有的园地作正统文学的耕耘,而是借着创作环境气氛的宽松,转向新的叙事空间,用叙述平民百姓的故事,写出令读者能“观世情、启心智、怡性情”的作品。这些作家深知有了读者就有了市场,自觉或不自觉地往“商品化”靠拢。他们在雅俗共赏的结合点的寻找上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以获取文化市场竞争的实力。据此观之,文学的俗化不仅仅是文学商品化的一种表现形态,而且是促进雅文学与俗文学取得沟通和融合的得力手段,既符合开放性的要求,又见出拓展性的效果。
近几年来,通俗文学构成了对整个文坛全面性的影响,它以疾风的气势及逼人的姿态, 从严肃文学手中夺去了半壁江山和众多的读者。 1985年被称为“通俗文学年”,从港台那里滚来了“热”浪,由“金庸热”、“琼瑶热”到“梁凤仪热”等等,热得金庸、梁羽生、古龙以及琼瑶、三毛……这些人的作品供不应求,发行量一增再增,盗版更不计其数,销售的红火是严肃文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进入九十年代后,通俗文学非但热浪不减,而且沸沸扬扬。大陆作家在港台通俗文学的启示下,也针对庞大的读者群的文化心态,纷纷抛出了与平民大众接近的文学作品。经济转型期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建立,加之有新闻媒体与书商的介入,致使通俗文学在九十年代蓬勃兴起。应运而生的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民间文学等及历史文化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匪盗小说、神话小说、侦破小说……,在图书市场上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在林林总总的通俗文学报刊上,这一艺术门类的作品固然屡见不鲜,即使是一些纯文学刊物也相继改旗易帜,走向文学的俗化。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文化消费者会成为作品的裁判,因此文化的生产和存在方式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需要。为适应文化消费者的需要,作家们由创作严肃文学转向创作通俗文学,并把精神产品以商品的形式推上了文化市场。尤其是长篇小说,拆去了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壁垒,真正地以俗化的面目热销市场,就眼见所及,丛书、套书不下几十种,书店、书摊摆得琳琅满目,大有独领风骚的势头。例如,1993年上半年最热门的畅销书《警告中国人》系列丛书,其作者周洪,原来是《当代》编辑部的几位编辑的集体笔名,主笔周昌义过去是从事纯文学创作的。四川两位严肃文学作家谭力、雁宁摹仿港台和海外通俗文学以“雪米莉”的笔名,写出了融言情与侦破于一炉的系列作品,题材内容是地道的“通俗”。以“文化先驱”自命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通俗文学的冲击下跨向“俗化”的大门,从内容到形式向着写实、民俗文学复归。“先锋小说”创始人之一莫言说:“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所谓的‘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吸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把书读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唯一的一条出路。”〔1〕先锋作家们写作的题材, 有着由超验的、想象性、幻想性的世界而转为现实的、形而下的经验世界的趋向,同时也强调了传达方式的故事性。格非的《敌人》、北村的《施礼的河》、余华的《鲜血海花》、苏童的《妻妾成群》(电影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与《红粉》等,就把通俗小说中那些恩怨相报,生生不已的历史母题移植到作品之中。1994年初出现的“新体验小说”,是用“亲历”和“纪实”的叙述方式,显示纯文学的俗化,陈建功、赵大年等人的多篇作品就是通俗文学大环境下所催生的产物。王朔、贾平凹、范小青、张宇、刘心武的“新市井小说”,是表现市民生活、富有故事性的写实小说,其指归在于重铸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在嘲讽、戏谑中表达新的“俗人”,即改革中生活发生变化了的新一代市民与上流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市民意识,这是在纯文学困境和俗文学的成功启迪下所产生出来的较高级的俗文学。其实,纯文学作家写出的作品很多已具有了俗文学的特点。冯骥才的《神鞭》,丛维熙的《野浮萍》,柳溪的《大盗燕子李三传奇》,毛志成的《在清晰的枪声背后》,朱晓平的《魔寺》,彭荆风的《窄巷一剑》,等等,都因为用了通俗的语体,表现了大众所喜爱的生活内容,在读者中间广泛的流传。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厚厚三大卷,120万字, 海峡两岸的读者不只是读得下去,而且读得兴味盎然,姑不论在短短的时间内分别由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四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于文化圈内颇为罕见,单就湖南文艺出版社连印10次书店还经常脱销而言,足以说明文学的俗化是能够出“精品”的,也足以说明精神产品作为商品首先得是高质量的,否则何以会如此销路大畅!《曾国藩》是严肃文学中的通俗文学,它厚重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文化深度是严肃的,但从大众化的广度去深入挖掘作为中国封建末世理学名臣的曾国藩的文化心理,不去单纯地将他作政治上的定位和道德上的批判,而是置于传统文化系统中来进行考察,描绘出这位历史人物的悲剧,并将历史生活化、人情化、心理化、立体化却又是通俗的。叶永烈的“黑色系列”文学传记《王洪文传》、《张春桥传》、《江青传》、《姚文元传》、《陈伯达传》,对一个个传主的记述,在把握他们不同于一般类型的具体特性时,不作简单地丑化,而去赋予形象的血肉。这种文学传记带有世俗化的倾向,在注重史料的准确性的前提下,注重作品的可读性与生动性,满足了平民大众进入尘封着的神秘场境而了解内情的强烈欲望,但作者没有将其写成稗官野史之类,有着传记文本的不同凡响的真实魅力,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争相传阅,销售行情看好。以某些土匪或类似土匪的人物行为为描写的“匪盗小说”,在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掀起了热潮。1986年莫言的《红高梁家族》问世以后,写土匪、强盗一类的作品不断涌现。到了1990年,贾平凹推出了他被称为“匪盗系列小说”的《烟》、《美穴地》、《白朗》和《五魁》,后又有名篇《晚雨》。杨争光的中篇小说《黑风景》,与他发表于1991年的《赌徒》、《棺材铺》,也构成了“匪盗系列”。1992年和1993年以来的“匪盗小说”日见增多,有尤凤伟的《金龟》、《石门夜话》、《石门呓语》,有刘国民的《关东匪与民》,冯苓植的《落草》,孙方友的《绑票》,陈启文的《流逝人生》,池莉的《预谋杀人》,刘恒的《冬之门》……,形成了一股“新历史小说热”。“新历史小说”在力图“走向文化与人性探求的深处”上取得了成就,功不可没。这类小说或显现野性十足的土匪有的弃善从恶,变极好的人而为极坏的人,有的改恶从善,向着悲壮的超度与自我救赎飞升,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匪徒的不同历程,概括涵纳着作家源自社会与道德的思考。“匪盗小说”,具有典型的通俗小说特征,被大量发表、出版,畅销一时。另外,数量相当可观的作品,明显地有着通俗文学的传统的天然题材,或在民情风俗中勾画蒙积着的历史尘垢,在这不值得赞扬乃至必须改变它的一面的另一面,又去发掘民主精神的美好;或展示人情世态,曲尽人情世趣,象武侠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可看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或表现痴男怨女们衷情不渝,在那些普通人身上的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故事,联系着社会的、历史的,也有个人的、性格的种种纠葛,以人物历尽沧桑的真挚感情去打动人心,平民大众对这样的言情小说往往是耽味沉迷的。上述各类的作品成为图书市场的热销读物,说明有稳定的读者群体。
文学的俗化意味着通俗文学获取了与社会对话的渠道,大有芳草萋萋的景象。那些惨淡经营在高雅斋里的作家们,因其不顾及平民大众的阅读胃口,并对通俗文学嗤之以鼻,从而去制作玄奥莫测,难以读解的纯“个人化”的作品,往往使大批读者一见生冷的面孔和高傲的姿态就敬而远之,这与炙手可热的俗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些高雅文学的结构模式、叙述方式、语言运用,可以从西方文学中找到母本,横一个什么“主义”,竖一个什么“流派”,无奈作家对这些却是素昧平生,得之于耳食者也不很多,付诸创作实践只得去依样画葫芦,搞得神秘艰涩,对于只具有初步文化知识的平民大众来说自然是不愿看也看不懂的。那些没有时间的跳跃交错,没有空间的切割拼贴,还有变形、隐喻、荒诞、魔幻等等技法,他们是无法欣赏的,唯有文化素养较高的精英层知识文化人士才能知悉其来龙去脉,心领神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域外文化必须引进,但切忌生硬照搬了来故弄玄虚,把读者吓跑。谁都得承认这样的事实:当前文学能够于文化市场上与电视音像、娱乐功夫片等竞争的当首推通俗文学,其主要的原因是作品中与现实契合的生与死、善与恶、爱和恨这些永恒的主题,都用生活化的形式表现,让平民大众心理上很乐于亲近和接受。俗文学作品所具备的这一为广大读者所认同的心理基础,决定了它商业化操作的得以领热潮之先。例如,王朔的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他的小说是十足的俗文学,在文化市场上走红。在文学最不景气的1992年,王朔以前的集子《空中小姐》、《王朔谐趣小说选》、《过把瘾就死》以及新推出的150 万字的《王朔小说专集》,成了全国各地大小书摊上销售量最大的一本书。购买王朔文集独家版权的华艺出版社在将四卷本《王朔文集》推上市场的同时,不惜印制了150万王朔画像张贴在京城的几乎每一个图书购销点。 陕西几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等,被人们称之为“陕军东征”的现象,这些作品和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也同样在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的驱动下,形成了购买热。由此可见,文学的俗化成了文学增值的一种商业手段,作家们的创作心理亦刺激出了功利需求。
通俗文学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雅与俗兼有的作品,为多层次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并且以其显著的经济效益,除保证了自身的生存,还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然而,它的地位仍然不高,对它的评价在褒贬上众说纷纭,究其原因,盖出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社会偏见;二是来自于负面效应。
通俗文学理应纳入当代文学的视野,而不应存有社会偏见。作品的生命力的有无,就看读者的裁决,没有生命力是没有读者的同义语。不着重读者,不抓住读者,那作家的文学文本起什么作用?从接受美学观点来讲,作品如不被读者阅读接受,那只不过是束之高阁的印刷品而已。君不见,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经过接受主体的欣赏性阅读,使其潜在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得到了实现,构成了现实的美学对象。王蒙在长篇小说《暗杀——3322》中告示读者:“这不过是一个跟随布老虎的雅俗共赏的潮流编撰的故事。作者把这个故事卖给了春风文艺出版社,你又为了解闷而花钱买了它——谢谢您”(指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散文等不同系列的“布老虎丛书”)。这里可探知王蒙是认同文学的俗化的。在“布老虎丛书”中作家洪峰的《苦果》,铁凝的《无雨之城》等等,是雅俗合流的作品,也就是说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创作往通俗文学靠了。有很多作品很难作雅文学与俗文学的界定,如《花城》上方方发表的《何处是我家园》,可以视作雅文学,也未尝不可以当作一个通俗故事来读。陈福郎的长篇小说《怪味嘻皮士》,以袁世凯称帝事件为历史背景,塑造了性格上有强烈的传奇色彩的人物——辛宏祖,情节中的内容是“俗”的,而语言运用上追求的是“雅”,其寓庄于谐的艺术风格及幽默风趣的人物故事,可以定性为俗文学,而从打破传统形式上的时间线性结构,向多样出新的叙述样式发展,又可见出雅文学的成份。文学的俗化未见得就是文化素质的低劣,也未见得就是思想观念的浅薄,属于“雅”的范畴的作家,他们抱着“适俗”的愿望,关注着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大众文化,以自己的“雅”去提高“俗”。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雅俗交融,可兼顾到文学的两个层面,又可处理了文学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拆除“通俗”与“高雅”的界限,文化程度高的人看了不觉浅得如“下里巴人”,文化程度较次的人看了没有深得象“曲高和寡”的感觉。再说,考虑到大多数读者的需求,又考虑到文学作品的不失去市场,可在逐步提高通俗文学的文化品位时不断提高普通读者的文化品位,这是不应忽视的创作导向。郑振铎曾给通俗文学下过定义:“‘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也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2〕而今看来, 俗文学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情况有了改变,俗文学中也不仅仅是民间文学,还包括有“作家文学”,即纯作家、严肃作家写出来的俗化文学,其中优秀的作品应当说能够看到它们的精神内涵和精神价值,亦能够看到“人文精神”(是有平民意识的“人文精神”),它们引人向善,富于真情,为普通人民所喜闻乐见。如果对通俗文学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则未免是一种“精神贵族”的偏见与歧视。贱视通俗文学的人,一般都认为它代表了低浅层次上的社会文化,而高雅文学的失落是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结果。这种看法失之于片面,且不论读者是多层次的,文学也必然是多层次的,为什么非得要让大一统的思想来控制,给纯雅文学占有唯一正宗、独尊的位置呢?即以通俗文学的生存状态而论,作品也是要在提高其文化品位上实现自身的超越的,不能断言通俗文学就是文化品位低的文学,因为通俗文学不是不要开拓创新和强化精品意识的,事实上已经创造出了“名优特”的产品,尽管臻于此不算很多,但却表明了它的发展。那么,是不是因为大众文化素质低,才出现了通俗文学热?这不贴切,正确的看法是:它与普通人民大众的生活接近,感情相通,还有一副平易近人的面孔。再有,今天人们不象过去受政治禁令束缚,可以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读物,去看以前看不到的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的阅读对象不限于一般文化状态中的读者,也有文化水平高出他们的大学生、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甚至有资深望重的学者,如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牌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选修课,听者甚多。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员严家炎先生在《通俗文学评论》开辟的《金学经纬》栏目内撰写了《论金庸武侠小说的生活化趋向》,这是对通俗文学的评论,也是通俗式的文学评论,有助于人们对通俗文学作家与作品的理解。学者对通俗文学的推崇,并在通俗文学发展的史论性研究上付诸于行动,如,向以严谨而著称的著名“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在《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中,称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将其作品誉为“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由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范伯群先生主编,由一批获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共同参与编写,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煌煌可观,共计12册。这一项开拓性的学术工程,对于了解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基本面貌,借鉴学习前人经验,使通俗文学沿着更明确、更高尚的目标迈进,具有相当重大而积极的现实意义。理论界有很多学者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发生了兴趣,因此通俗文学在文化大家庭中的地位、价值就被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认为它是低浅层次的偏见就连处于高层次的人也不会苟同了。至于商品经济大潮使文学进入市场,既是冲击,亦是挑战和选择。不可否认,商业机制、市场经济对文学的走向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原来居于天国独特的社会地位的高雅文学受到了冷落,倒不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文革”期间虽无商品经济发达带来的冲击,而文学却是凋零衰败的。如今,经济体制的转换,社会状况发生的变化,为通俗文学维系着社会中大多数文学读者的爱好与交流提供了消费环境。这些大多数文学读者的审美情趣及欣赏习惯,随着文学观念的改变,倾向于通俗文学。作为读者,选择读物由封闭走向了开放,阅读的目光盯上了通俗文学。在文学渐渐消解了原有价值体系和功能格局的危机中,通俗文学增强了竞争能力。作家们出于文学市场供求关系及流通过程中价值观念的趋动的启发,向通俗文学吸取合理的成分,重建文学审美体系,在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互渗互补上寻求了文学的出路,融合着市场观念。这样,就争取到了流失的读者。有的作家似乎无视读者大众在相对稳定中的活跃性与变化性的阅读心理,依然攀援着纯之又纯的创作之峰,使用的是不为大众容易接受的体裁,不想在“俗”与“纯”之间架起一座通行的桥梁,加之作品离生活很远,为此又怎么能得到读者的选择呢?文学的俗化并不意味着对精致的纯雅文学的冲击,冲击的是故作高深,实际上并不精致,不能投合社会心理的东西。冲击的本身是呼唤改革,改革就要了解“民众的心”。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中说过:“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当然,在了解、研究“民众的心”时,不要忘了“设法利导,改进”,这才能使通俗文学真正文学化、美学化、人民化、民族化。
通俗文学的适俗不等于是媚俗,通俗也有异于庸俗,媚俗悦众,低级庸俗,确实败坏了通俗文学的声誉。这种现象的存在,受到了有些作家的猛烈的抨击。如张承志就有这样的严词厉语:“现在的知识分子太脏了,甚至以清洁为可耻,以肮脏为光荣,庸俗为时髦。”〔3〕张炜则怒不可遏地指出文学“它的制品——垃圾——包装得再好也仍然只是垃圾。”〔4〕通俗文学的这些负面效应虽然并不代表通俗文学的全部,它不是通俗文学的主流,但是其指责和批评却是有根据的。不少作者、编者和出版者,在感受市场经济的信息之际,功利心理、商业意识使他们全然把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艺术话语转换为金钱话语,不惜打着通俗文学的旗号,贩卖抢劫、凶杀、色情、卖淫等精神垃圾,心无旁鹜地想出主意来赚钱,不顾艺术质量,粗制滥造,种种低俗、恶俗、庸俗之作肆虐泛滥。如,比《废都》更废,比《骚土》还骚的作品招摇过市,撩拨读者感官的《畸恋》、《裸野》、《野鸳鸯》、《女人的诱惑》、《七个光棍货》等等的“马路文学”、“地摊文学”到处都可见到,不要看内容,仅看书名你就觉得取得俗不可耐了。漫步大街小巷的众多书摊,触目而来的是配有图画的图书广告招贴,画面充满着色情暴力,说明文字乌七八糟,这哪儿还有操守可言,理应清除出文学殿堂!通俗文学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决不能拿肉麻当有趣,将腐朽为圭臬,让读者去吞下“鸦片”,某些作家涉足于兹,在商品市场光怪陆家的诱惑下,他们的生存支点完全转向商业的功利性,财迷心窍,为了经济效益,故意去迎合低俗猎艳的读者,出现了创作主体精神境界的滑坡,所写内容,令人匪夷所思。文学作品是商品,但毕竟还有崇高的精神宗旨,应警惕在拜金主义面前心灵的脆弱。我们重视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讲究经济效益,更要重视精神产品的特殊属性,它有陶治人的情操、完善人的道德、净化人的灵魂的巨大作用,不能单纯用市场需要来衡量其价值,因此要处理好商品经济和精神目的的关系,要摆正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要理解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就现阶段来看,对通俗文学要引上自身机制良好循环的大道。将文学的俗化变成了纯粹商业行为,这是“失控”的错误,并非是通俗文学的罪过,因此努力提高通俗文学创作者的素质,提高通俗文学作品的质量,以深邃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文学修养去影响通俗文学的大量读者,同时加强对通俗文学的研究与批评,这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注释:
〔1〕《谁是复仇者?—铸剑解释》, 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3期。
〔2〕《中国俗文学史》第1页,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
〔3〕引自《法制与新闻》1994年第1期
〔4〕《文汇报·文艺百家》1993年3月20日:《抵抗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