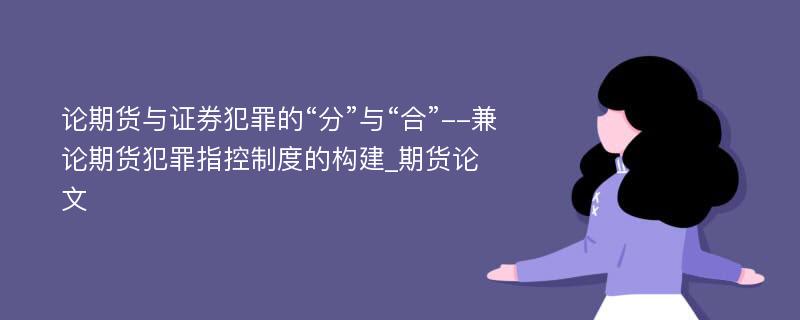
论期货、证券犯罪罪名的“分”与“合”——兼论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罪名论文,期货论文,体系论文,证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刑法》中的“直接性期货犯罪”,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方式,即在相应条文的“证券”二字后面加上“期货”二字。期货犯罪罪名的这种依附性状况,引发了学界对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的讨论。本文试图以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罪名的“分”“合”之争为切入点,探讨如何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一、“分”“合”之争:与证券犯罪罪名的关系
我国金融刑法将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做法,有着其立法背景和相对的合理性。首先,我国期货市场起步较晚且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比如商品期货市场,1990年的时候,还是一片空白。到了1994年,全国号称期货交易所的市场就有约40家。这些交易所为了招揽业务,盲目地开发新的期货上市品种,最终导致各交易所之间的恶性竞争,交易品种重复建设,难以实现交易规模,致使期货价格发现等基本功能得不到体现。为此,国务院发布国发[1994]69号及国发[1998]27号等文件,将期货交易所撤并、整合。《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也于1999年6月份出台,商品期货交易市场这才逐渐规范起来。金融期货市场更是命运多舛,直到现在还处在开市的酝酿和试验阶段。期货市场的不发达、不规范,导致我国尚未建立起独立的期货犯罪立法体系。《期货交易法》几经易稿却始终没有出台,《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此前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虽然在期货交易制度构建和风险控制等方面有不少亮点,但其毕竟是行政法规,无权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权限。因此,作为金融刑法保护对象的期货市场以及作为罪名载体的期货立法的不发达、不完善,是期货犯罪罪名具有依附性的现实依据。
其次,我国现阶段期货犯罪的特点也是金融刑法将期货犯罪规定在证券犯罪中的重要因素。和证券犯罪一样,早期的期货犯罪主要体现为发生在期货市场上的贪污、贿赂以及一般诈骗等“相关性犯罪”,“直接性犯罪”数量较少。如据司法机关和证监会的统计,现阶段人民法院期货案件收案数量明显少于股票、债券类案件。并且,由于证券和期货在企业中分别肩负着风险投资和套期保值的使命,二者联系密切,所以,期货犯罪往往伴生于证券犯罪发生。如号称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大案”的“中科创业”事件,就是具有期货犯罪依附性特征的典型例证。基于此,出于立法经济性的考虑,我国立法机关没有采纳国务院1999年5月提交的《关于惩治期货犯罪的决定(草案)》,而是采用了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将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
随着我国期货立法和期货市场的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金融刑法将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做法提出较为激烈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当将二者罪名区分开来。批评者主要是围绕期货交易与证券交易的本质区别来讨论这个问题的。首先,两者的对象不同。期货交易的对象是期货合约,而证券交易的对象是证券。证券和期货是两种不同的金融工具,证券的本质是资产的所有权凭证,而期货既不是货物,也不是所有权凭证,只是货的合约。证券交易是现货交易,而期货交易属于远期合约交易。其次,两者在所有权的转移上不同。在期货市场上,绝大多数期货交易不必转移期货合约标的所有权,交易者是通过对冲来免除履约义务,而在证券市场上,所有的证券交易度必须转移证券所有权。再次,两者在交易方式上不同。期货交易中的保证金制度使这种交易成为信用交易,交易者可以“以小博大”,进行大量的买空卖空。在此基础上,学者认为,这两种犯罪在犯罪构成和刑罚配置上也应有较大区别。
二、“独”“分”之别:构建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的基点
应当说,学者的上述批评和建议都是比较中肯、合理的。但是,笔者认为,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罪名是“合”还是“分”,只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这个立法技术问题尽管也很重要,但其毕竟是问题之“标”。据司法机关统计,我国期货犯罪发生率相对于证券犯罪而言比较低,可见,我国现阶段的立法对期货犯罪的规制和防范还是卓有成效的,这同时也说明了两种犯罪罪名的具体处理方式并非问题之“本”。因此,学者一味建议将两种罪名区分开来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顺应期货市场发展的需要和实现对期货犯罪的有效治理,我国期货犯罪罪名的依附性有待改造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具体的立法技术上的“分”或者“合”,而在于应当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是“分”还是“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绝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应当分别规定;但也不排除出于立法经济性和金融犯罪综合预防等刑事政策的需要而将二者合并规定的情况。
首先,从国外立法例来看,期货犯罪立法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从一开始就将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作为价值取向的。以美国为例,自第一部期货立法1922年《谷物期货法》对在场外交易上散布能够影响谷物价格的虚假信息予以刑事(轻罪)处罚开始,美国在其后的期货立法中,逐步扩大期货犯罪刑事处罚的范围。直到2000年《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止,其期货立法已经建立起了包括重罪和轻罪的完善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再如日本,以《刑法典》为核心,以《金融期货交易法》及1990年修改后的《商品交易所法》为两翼,日本立法构筑起了包括欺诈、操纵期货市场等七种主要形式的期货犯罪和一系列其他形式的期货犯罪在内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另外,新加坡、英国、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期货犯罪立法莫不如此。可见,大多数期货立法发达的国家一开始就致力于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类似我国的“分”“合”之争,在国外金融刑法领域鲜见存在。我国学者在以外国立法为参照系对我国期货犯罪罪名依附性进行批评的时候,大多只是看到外国立法中期货犯罪罪名与证券犯罪名分立的表象,而没有看到分立是建立在构建独立、完善的罪名体系基础之上的。这些批评似乎给人一种只要一分就万事大吉的感觉。
其次,外国立法也并非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将期货犯罪和证券犯罪截然分开。由于这两种犯罪有着诸多天然的联系,所以发达国家的期货立法,也会考虑将两种罪名适当地予以合并规定。譬如,2001年颁布的《证券期货法》是新加坡调整期货市场和期货犯罪的基础性法律之一。其在第十二章“市场行为”部分,对一些法律禁止的期货犯罪行为和证券犯罪行为作了合并规定的立法处理。其在第3节“内幕交易”部分中明确规定,本节适用范围、“信息”范围、“证券”范围等内容,既包括证券,也包括期货。类似规定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另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期货和证券是分别立法的,但是在许多具体犯罪行为上,美国法采用了共通性的规则。譬如美国法中的sceinter,虽名为欺诈,但其和其他领域的欺诈并不相同,而是专指发生在证券业和期货业交易中的欺诈。Sceinter的构成和传统欺诈大相径庭,但是在证券犯罪和期货犯罪中,其基本构造却是一致的。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即使在已经建构起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的国家,有些期货、证券犯罪也是合并规定的。
由此可见,在探讨构建合理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罪名的“分”与“独”的关系:独立不等于一定要分开,独立不排除某些情况下二者合并规定;分开也不等于独立,独立性强调期货犯罪罪名体系要自成一个独立、完善的系统。完善期货犯罪立法,构建合理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的根本在于“独”而不在于“分”。并且,正确处理期货犯罪和证券犯罪罪名的关系,也不是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惟一需要考虑的内容。除了这问题之外,我们还要综合考虑期货犯罪罪名体系在金融刑法中的位置、期货犯罪立法模式以及期货犯罪与其他犯罪罪名的关系等问题。
三、几点构想
(一)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有赖于我国整个金融刑法罪名体系的完善。
我国整个金融刑法的罪名体系完善性的欠缺,是期货犯罪罪名具有依附性的结构性原因。金融刑法的罪名体系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上,金融犯罪罪名应当包括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三个部分。纵向上,金融刑法应当在上述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基本框架下,按照所属领域的不同,将金融犯罪罪名为分别归属到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四大板块。其中,证券一块应当包括狭义上的证券、期货、基金三个板块。目前,我国金融业中的期货和基金管理还没有完全脱离证券业,比如,我国没有类似于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那样独立于证券监管机构的期货监管机构。这种情况很难适应期货市场发展的需要,也导致立法上,期货犯罪罪名难以自成体系,只能依附于证券犯罪,因此亟待改观。第一,从金融学的角度看,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期货交易与证券交易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尽管以“混业经营、混业管理”为特征的金融综合业务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个金融领域的基本特征可以忽略不计。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金融业混业的典型代表,但是其期货市场的独立性从来不受质疑。第二,从金融犯罪综合预防看,期货犯罪和证券犯罪在基本构造和责任形式上都各有不同特点。因此,以金融领域为向度来考察罪名设置,有利于清楚地了解每一金融领域内犯罪的基本形态,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制定犯罪预防对策,从而有利于金融犯罪的综合预防。由此可见,在上述两个维度内完善的我国金融犯罪的罪名体系,是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的大前提。
(二)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有赖于犯罪圈的合理设定。
我国目前期货犯罪罪名具有依附性,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期货犯罪犯罪圈设定的不严密和不合理。其一,从罪名数量上看,我国《刑法》仅仅通过修正案的方式规定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编造并传播期货交易虚假信息以及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等几种期货犯罪,这个犯罪圈的设定过于狭窄。犯罪圈过于狭窄意味着刑法对期货交易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及各个形态的犯罪行为规制难以周延。罪名数量过少,是期货犯罪罪名没有形成独立体系的重要原因。其二,从罪名分布上看,我国期货犯罪罪名存在片断性的问题。立法的片断性是我国整个金融刑法共通的问题。这种片断性不仅体现在金融违法行为入罪方面有严重缺失,而且还体现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罪名设置方面,“只注重对金融市场准入阶段金融管理中所出现的违法行为入罪,而忽视对在金融市场交易阶段和退出阶段出现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进行入罪”。立法的片断性,导致期货犯罪罪名不能够形成完整体系,也就谈不上独立了。基于立法中期货犯罪犯罪圈设定的上述缺陷,学者提出,在入罪方面,金融刑法应当增设期货交易欺诈客户、非法进行期货交易、挪用期货保证金、私下对冲以及期货任职违法等罪名。在矫正罪名片断性方面,我国金融刑法立法应当在摈弃“金融管理中心主义”、“金融机构本位主义”理念和确立“金融交易中心主义”、“金融客户本位主义”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三)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还有赖于立法模式的完善。
期货犯罪立法模式是解决一国采用何种形式的法律规范来规定期货犯罪的问题。发达国家的期货犯罪立法多采用特别刑法(包括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或者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尤其是附属刑法模式较为盛行,而我国则采用的是单一刑法典的模式。采用附属刑法模式,期货犯罪多被规定在相应的非刑事法律中,而绝大多数国家的期货立法和证券立法是分开的,除新加坡在其《证券期货法》中将证券交易和金融期货及能源期货交易一体规定外,很少国家在一部法律中同时规定证券和期货。采用这种模式,必然导致法律对期货犯罪和证券犯罪分别规定的结果,也必然导致这些国家在其期货法律中构建起一套独立、完备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相反,在刑法典里规定期货犯罪,由于证券、期货犯罪在行为形态和基本构造上的诸多雷同之处,出于立法经济性和刑法分则体系协调性的需要,将二者合并规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另则,立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一国市场发展和立法水平的体现,采用刑法典模式的国家,其期货立法一般处于欠发达阶段。这样,在合并规定的过程中出现期货犯罪对证券犯罪罪名的依附性也是情理之中的了。由此可见,欲完善期货犯罪立法,立法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笔者认为,包括期货犯罪立法在内,我国金融刑法应当改造现行模式,采用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以实现构建期货、证券、信托、保险等几大金融领域各自独立的罪名体系。
四、结语
综合而言,当前我国金融刑法理论中关于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罪名“分”与“合”的争论,对于完善期货犯罪立法而言,尽管是有益的,却是不得要领、乃至是舍本逐末的。笔者认为,这两类犯罪罪名的“分”与“合”,仅仅是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立法现状的折射,是我国期货市场和期货立法发展程度的折射,也是金融刑法对期货犯罪进行规制的基本理念的折射。我们不能够只将视野停留在对这个表象问题进行争论的层面上,还应当从金融刑法立法理念、期货犯罪立法体系和立法模式等更深层面入手,致力于构建一套独立、完善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