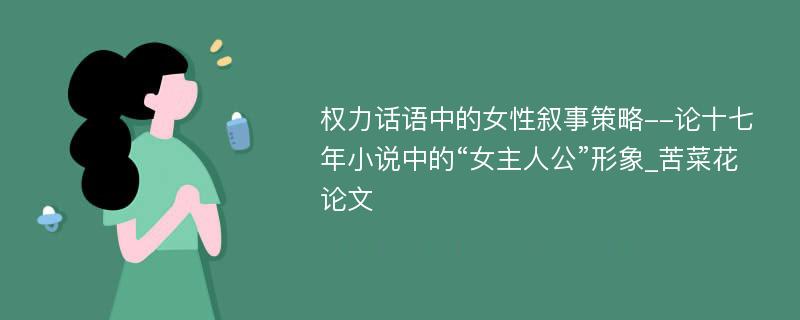
权力话语的女性叙事策略——关于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权力论文,形象论文,策略论文,女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9)02-0123-05
一
“十七年”是一个追求英雄的年代。在“十七年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转折之一就是革命英雄形象画廊的形成。人们注意到,文学叙事开始摒弃一般的人生存在方式和意义,减弱描写日常生活的兴趣,转向把战争年代的生死问题典型化,把英雄的经验普遍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塑造这些英雄的中、长篇小说似乎超越了文学的功能和文体,而变成一个时代具有特殊意义的“教科书”。对付出了一场巨大牺牲的人们而言,在和平时期重嚼痛苦的探索历程,缅怀长逝者的英灵,以期在民族的精神生活里重建价值的丰碑,这在任何国家,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有合理的思想内核[1]59。“十七年文学”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那种既“自觉地注意反映现实认识效果”,又不乏“神话主义”浪漫色彩的文学的另一例子[2]317-319。这一时期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女性作为一种性别的生活存在已经堙没在一片统一的色调、社会环境和行为要求之中,“普遍强调的革命化特征导致了女性意识的遮蔽或相当程度上的消解”[3]11。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现实语境所决定的,主流话语也即权力话语在女性身上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方面是大肆宣扬男女两性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在经济上同工同酬;另一方面是对女性性别特征、情感生活的极度贬抑。女性政治地位的极大提高,使女性人物从历史叙事走向革命话语的讲述中心,而对女性性别的贬抑使女性意识无法在文本中得到合理的表现。这样在文学文本中,“女性意识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从而销声匿迹,在此女性解放的神话困惑为阶级解放的现实所遮蔽”[4]44。
在“十七年”小说中出现了被柳青形容为“党的儿子”的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涌现出具有英雄特质的“党的女儿”即“女”英雄。这类女性人物如何走向英雄的道路,的确与男性不太一样。首先,她们往往是伴随着男英雄出场,如徐改霞伴随梁生宝(《创业史》),春兰、严萍伴随运涛、江涛兄弟(《红旗谱》),区桃、胡杏和胡柳伴随周炳(《三家巷》、《苦斗》),娟子伴随姜永泉(《苦菜花》)等;有一批女性英雄则是被男干部“翻”出来或在运动中“跃”出来的,如孟祥英、金桂、双眉、萧淑英、李双双、吴淑兰和张腊月等。她们在以男性为中心开展的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运动中,逐渐具备了与英雄一样的崇高理想,坚忍不屈的精神和不怕吃苦、热爱劳动的品格。其次,她们可以说是“妇女解放”概念的产物,是晚清政治小说中的“巾帼英雄”,五四时期以后现代小说中的“新女性”人物系列的延伸,尽管“十七年”的“新女性”在思想、行为和情感的起点已不同于她们之前的莎菲、喜儿等女性形象,但仍烙有追求解放、从“旧”到“新”的转变痕迹。不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女性”更多表现为具有叛逆精神、个性追求与自我意识觉醒的内容,而解放区与“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新人,则拥有与男子一样的政治、经济地位[5]81-82。
中国几千年以来就是一个男权世界,女性只是陪衬,权力话语说到底也就是男性话语,女性处于权力的边缘地带和失语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推动下、在当时的现实语境作用下,“十七年”小说创作中关于女性解放和对女性价值认同也是以权力意识形态为标杆,矫枉过正地极度虚构并阐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以彰显新政权的新特质。
二
女性英雄人物是在“十七年”小说中,如何完成其人物形象构型的呢?本文从权力语话的叙事策略角度予以探究。
1.叙事策略之一:雄化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因此,集“解放妇女”与“党的女儿”于一身的女英雄,革命道路是她们必须走到底的路,也是英雄神话得以在她们身上展开的基础。
女英雄形象第一个而又是最明显的特征是“像男人”,因此塑造这类形象的基本叙事策略是“雄化”。“雄化”是突出女性人物“雄”的一面,即让她们在外貌、言行举止和工作表现上贴近男性和模仿男性,并进一步引导她们加入男性的世界、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以至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接受,最终成为英雄人物。
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对女英雄的“雄化”,主要是突显其力气和刚强。《苦菜花》中的娟子“像乱石中的野草”,是在苦难的年月中倔强茁壮地成长起来的女英雄,叙述者不仅强调她用“那激动的带男音的声音”向姜永泉表示参加抗日的决心,而且具有雄强的气力和机智,一次她受到敌人宫少尼袭击,她能如女侠一般跟他肉搏,最后将他制服。又如《苦斗》中的胡柳也曾“横冲直撞,闪避腾挪,英勇非凡,像学过武艺的男子一样”,拿起竹竿去打那些从保安队派来的男人。《青春之歌》中被残酷的刑罚折磨得已经站不起来的革命者林红,仍然一如既往地教育后继者,不要以为死就是生命的终点,要坚持努力地奋斗,总有一天,红旗将随着太阳照遍全球。《红岩》中的江姐,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刑场,表现出革命者的沉着坚毅、凛然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新的政治意识的强力号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催生了女性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男作家和女作家的笔下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意义上的强壮体力的顶礼膜拜。铁姑娘、娘子军本身就是妇女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代名词,王汶石的《黑凤》所叙述的是一个有关那位“干劲冲天”的姑娘黑凤在大跃进时期如何闯入男性劳动世界的故事。黑凤是一位“决心要做个生活在战斗中的女战士”,叙述者以强调她的竞赛意识作为雄化的手段。男人能干的,女人亦能干,黑凤参加进山背矿石劳动,背的与男人一样的多,累了也不让其他男性帮忙,黑凤显示的是与男人一样的体力和强者的姿态。终于赢得了一个由矿石、“猛虎连”、“钢铁英雄”、窝棚等构成的男性世界的接受,并得以进一步成为以非凡的干劲、无比的热情和不怕吃苦的战士精神参与的英雄人物的一员。张腊月(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以男性的价值标准代替自己的价值标准,以男性自我实现的程度作为自己的归宿。她豪爽泼辣,男子气十足,她对伙伴吴淑兰说:“吴姐,咱们俩交个朋友吧,旧前呀,男儿志在四方,五湖四海交朋友;如今,咱们女人也志在四方啦,咱们也是朋友遍天下。”李双双(李准《李双双》)是一个什么农活都学过,能和男人一比高低的女英雄。她跳下水里抬石头,她挑着普通男人都挑不动的麦子在田野上飞奔,她挣的工分比男人还多。如此强悍的女性形象得到社会(也包括女性)普遍地接受和喜爱。“十七年”小说文本中所显示的女性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由此产生了对拥有超强体力的女英雄、铁姑娘的推崇,则表明了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已经从伦理道德和政策法规两个层面获得普遍的认可[6]。
总的来说,“十七年”女性英雄形象闪耀的是阳刚之美,无论是在战场上,或生产战线上,都以像男人、模仿男人和追超男人为目标,这是典型的男性审美意识,而“雄化”便成为男作家追求的修辞方式,这是“十七年”尤其是大跃进期间的总体解放观念和所谓“无性别”文化心理的反射,“新女性”似乎等于“非女性”或“男性化”。
2.叙事策略之二:道德化
“十七年”小说中,男作家在雄化女英雄的同时,又动用了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把女英雄形象的“女”的一面突出,即“道德化”手段。正如赵园“有点迷惘地发现”,这些新女性“更多地被人们从道德的而非美学的方面评价”,她们“最足作为形象的特异性的表征的,是人物在两性关系方面,在性道德这一敏感问题上的独特姿态,和正是在这一方面显示出的尖锐的性格的矛盾”[7]264。女英雄作为“女”的性格特征,在中国传统中一直对其有一个严格的道德规范。“十七年”女英雄形象的叙事模式,仍然恪守着中国传统道德的若干成分:贞节、驯服、纯洁等,即使在雄化了的生产“闯将”、“女战士”中间,她们虽拥有大胆、泼辣等被认为是“非女人”的品质和受称颂的阳刚之美,但也不能避免男性加诸她们身上的道德规范,而纯粹以突出女性的道德美作为“女”英雄的性别特征的修辞。黑凤这位在男性的劳动世界中已经失去了性别意识的英雄人物回到家里的时候,却马上恢复她那传统的女儿身份和娇滴姿态:一手灵巧的针线活,为男人打扮自己,渴望家庭的温暖,甚至胆小得害怕牛犊。《创业史》中的改霞,“改霞的思想像她的红润的脸蛋一般健康,她的心地像她的天蓝布衫一般纯洁”。她绝对不会与她钟爱的对象以外的男人“勾搭”,“有谁多看她几眼,她就埋下头去,躲避赞美的目光”。她和梁生宝之间虽然有矛盾和误会,但是“一个农村的贫苦青年,丝毫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想法,这一点,也紧紧地抓住了改霞的心”。改霞纯情羞怯,是一个相当道德化的女英雄。孙犁的《铁木前传》中的九儿也是如此,九儿非常纯洁:“那一对大眼睛射出的纯洁亲热的光芒。”九儿也非常忠贞,对童年时代与六儿萌发的那份纯真的感情,并没有随着岁月的增长和离别而淡忘。
进一步地论及,我们如果把孙犁抗战题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集中起来考察,便会感觉到他在小说中也明确表达出一种显然基于男权中心意识的贞操观念和女性纯洁之美的审美取向。“我留下洁白的身子,你争取英雄的称号。”在小说《采蒲台》里,这与其说是唱自小红和两个青年妇女之口,倒不如说是代作家自己表达的理念。对于女性而言,保持身子之“洁”,即不被日寇奸污,与在战场英勇杀敌同样重要,亦即,当时与英雄之美等量齐观。在对待保持身子的“洁净”与保全生命上,正如《荷花淀》中水生对水生嫂嘱咐那样:“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作者也意味深长地认为,“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因为被捉了“活的”就意味着贞操丧失,在水生的价值判断里,为了保住身子的洁净要不惜殒命。因此有论者认为“对女性贞操的过分强调反映了封建传统女性意识在孙犁观念中的投影,它也限制和束缚了女性的自由发展及其解放”[8]。
“十七年”小说在对女英雄道德化的叙事中,对女英雄性道德强调和对女性美的虚幻化也是叙事策略中的着力点。《三家巷》中的区桃貌美如桃花仙子,她的出现如同一位下落凡间的仙女:“她的细长的眼睛是那样天真、那样纯洁地望着这整个世界,哪怕有什么肮脏的东西,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她一定也不曾看见。”这种带有比喻性质的叙述,不动声息地在区桃身上打上道德的烙印。区桃在游行队伍中中枪倒地那一刻也采用虚幻化的修辞方式:“她觉得很奇怪,她自己到哪里去了呢?只有夏天的太阳,她还依稀认得:那太阳老是那么明亮。”死亡化作美的永恒的神话——“太阳老是那么明亮”。周炳则藉着对区桃的追忆,奋身投入革命洪流中去。区桃被塑造为一位精神化的女英雄,为后来出场的女英雄树立起一种完美的女性道德规范[4]93。诸如《三家巷》中的胡杏,以及《红旗谱》中春兰、严萍等都是权力话语中具有纯洁与忠贞的典型女英雄人物。
3.叙事策略之三:非家庭化
家庭,曾是女性头顶上仅仅望得见的一片狭小天空。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被圈养在家这个牢笼里,被压迫、被奴役,“用被假塑或假冒的形象出现,以被强制的语言说话”[9],成为男性的附庸和家庭的奴隶。家庭对女性的意义非凡,正因如此,五四妇女解放的矛头直指旧式的家庭关系。“十七年”小说中对女英雄的家庭观念做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改写。由于“十七年”是一个弥漫着集体意识的时期,本来与女性命运息息相关的婚姻家庭功能和位置逐渐变得弱化和边缘化。家庭被叙述为阻碍女性走上英雄道路的因素之一。因此,“非家庭化”成为女英雄形象塑造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方式主要是把传统以血缘关系为根据的家庭观念消解了,并以“革命大家庭”或“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观念和新关系取代之,或者是把血缘家庭升华为革命大家庭。
《苦菜花》中的娟子和姜永泉为了“革命事业”而结合,生育和照顾下一代人的事情根本没法提到她的生活日程,娟子以超人的韧力,在战地生下孩子,但当她发现母亲的责任耽误她的革命事业时,她好像完全丧失母爱,要把孩子送给别人,甚至诅咒小菊生:“都是你这小东西,害得人守在家里,你不早死了好!”后来,娟子的母亲用她干枯的乳房挤出奶汁来代替女儿喂孩子。娟子得以走出家庭,安心走上革命道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为了摆脱旧家庭,两次从家庭叛逃。第一次是为挣脱包办婚姻,厌弃公安局长和县长视其为玩物的姨太太生活,愤然离家出走。第二次是在看清救命恩人余永泽内心的自私卑劣后与之分道扬镳。后来在卢嘉川、林红、江华的指引下,投身到革命的大家庭。《红岩》中江姐,她虽然有家庭,却等于没有家庭生活。比如,她年幼的儿子在作品中从没有出现,与丈夫的关系也只是草草几笔带过。《红旗谱》中的春兰从运涛那里知道更多革命道理后,便敢于穿着绣上“革命”两个字的蓝布褂走进药王庙会,以她的方式公开“表示”对革命的向往。春兰虽然在锁井镇的革命斗争中只属于边缘和辅助性的女英雄人物,但向往革命也应走出家庭。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不仅在大跃进期间的劳动竞赛中风风火火,“男性”十足,而且在家里也扮演男性角色,对丈夫的态度是命令式,而丈夫却唯命是从。社会与家庭界线模糊不清,家庭的秩序完全汇入极度高潮,甚至接近疯狂的社会建设竞赛中去。与张腊月竞争的对手,吴淑兰“举止文静”,也在走出家庭,显示其阳刚之气,是一位正在走向女英雄道路途中的人物。李双双从入迷地学习识字到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从发出摆脱家庭羁绊走向社会的宣言到真正迈出第一步,从要求与男性平等到显示出自己更高的聪明才智,并非处处一帆风顺,相反时时遇到阻碍,陷入矛盾冲突中。家庭中自己的丈夫时时拖后腿,给自己制造麻烦。社会上也有人处处与她为难。嫌她管得太多[10]。《归家》中的菊英,从农科学校毕业后,怀着为农业技术改革服务的远大抱负,回到阔别五年的家乡时,发现她与原来的血缘家庭已经格格不入。菊英从三叔家搬回她那已改装为农业实验室的房子,象征着她与旧家庭的彻底决裂,全面投入亲情化的集体,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又红又专的好女儿。
不过,“非家庭化”叙事没有打破家庭制度本身,即基本的权力关系和结构,家庭只是换了一套外衣出现。没有动摇传统的女性特质,而只是模仿男性。女英雄作为如何面对家庭角色与革命事业之间的冲突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出自血缘家庭或传统家庭角色的矛盾,只不过被“革命理想”简化或遮盖罢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构筑的也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
三
“十七年的文学文本是受压抑的,它的显性乃至隐性层面都明显地烙上那个时代共有的印记。作家不可能真正排斥外部政治权力对它的控制和渗透,它的文学文本写作也不可能不具有现实的指向性。”[11]由于女英雄处于双重的矛盾位置,若要在“集体”、“男”与“个人”、“女”的夹缝之间求得生存,她们必须付出双倍的代价,也就是说:一方面,她们若要闯入社会重视的“集体”和“男”的世界,就得模仿男性行为,追随男性上战场、发动和领导群众、承担粗重的体力劳动、掌握技术或起码成为劳动生产大军的一员,那么,她们也就得摆脱家庭和女性的角色;另一方面,作为“个人”,“女”的世界的一分子,若要得到社会、男人的认可,她们则必须保持传统的女性特质,不可有越轨行为,那么,她们只得退守女人的世界(家庭)的樊篱。要把握这些女英雄的“进”与“退”的度,作家就得使用不同的叙事策略,“雄化”、“非家庭化”等叙事取得的是“进”的效果,而“道德化”取得的则是“退”的效果[5]108-109。
当然,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权力话语叙事之下的女英雄形象,面临着一种“困境”,“女”与“英雄”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互通的性别鸿沟。女英雄首先要恪守传统女性的道德标志,保持“好女儿”的身份。男性话语对女性“道德化”叙事有一种天然潜意识的执著,但与此同时,“雄化”和“非家庭化”的叙事又在破坏女英雄形象“女”的一面的树立,以致所塑造出来的女性特征显得不伦不类。总的来说,“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男权叙述主体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十七年”文学对女英雄、铁姑娘的崇拜在本阶段妇女解放运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折射出人们在创建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中的某些失误。女性这个五四文化革命后艰难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在“十七年”却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利与可能。女性意识即女性对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我意识呈现出极度萎缩的状态。正如戴锦华在其访谈录《犹在镜中》中所说:“妇女在赢得了空前权利的同时,却丧失了讨论自己问题的文化可能,甚至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称呼。”
收稿日期:2009-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