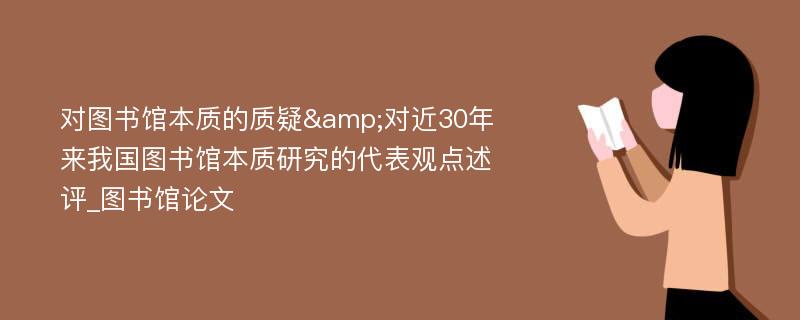
追问图书馆的本质——近30年来国内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代表性观点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图书馆论文,述评论文,代表性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馆学诞生至今,尽管学界和业界从未停止过对图书馆本质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是,除了对图书馆作为“特殊社会机构”或“特殊社会制度”的共识之外,在新时期尚缺乏公认的新的本质认识。鉴于透过事物现象把握其本质是科学的基本任务,深入研究图书馆的本质仍可谓任重而道远。经查询中国学术期刊网并初步统计可知,在过去27年里,国内期刊上至少发表了100余篇专门论述图书馆本质或定义的论文,所出版的图书馆学专著或教材几乎也都论及。本文拟在对图书馆学研究范式进一步概括与分类基础上对近30年国内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代表性观点作总体评析。
1 近30年来图书馆学研究范式转换及其分类
近30年来,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总结性或综述性文献或多或少涉及了图书馆学研究范式问题,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文献则较为系统论述了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及其转换问题。蒋永福和王明霞[1]强调了范式形成对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意义;简介了美国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分类,如米克沙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存在两大范式,即机构范式和信息运动范式,而信息运动范式又分为系统导向范式、贝尔金的知识非常态状态范式和德尔文的意义建构论范式;知识非常态状态范式和意义建构论范式又合称为认知观范式;重点评析了机构范式、系统范式和认知观范式的优点和不足;指出认知观范式的个体主义局限性,促使人们去寻找基于集体主义或社会维度的新范式,而领域分析范式和阐释学范式的出现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但其应用前景如何目前尚难定论,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新的范式。熊伟[2]则认为,从广义本体的角度看,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可以分为“主体”范式、“客体”范式、“中介”范式和“本体”范式;图书馆学近二百年的历史主要是“客体—中介”综合范式形成与转换的历史;图书馆学目前面临全面的范式转换,而转换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图书馆学可能形成的新范式是“本体—客体—中介—主体”综合范式。张欣毅[3]基于科学本体论进化的立场,阐述了图书馆学研究范式转移的机制,分别述评了机构范式、广义文献范式、客观知识范式、文献信息范式、信息资源范式、认知范式和文本范式,并主张以文本范式、信息资源范式和认知范式为三大思想来源来构建业界基本本体论,也即“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新范式或者说是“超文本范式”。储流杰[4]认为,图书馆学主流范式事实上已经发生并正在持续发生重大转换:从对研究客体的研究角度和视点看,经历了整理总和范式(即所谓的“书皮图书馆学”)、图书馆管理范式(即所谓的“尺寸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范式(即所谓的“机构图书馆学”)、知识信息交流范式(即所谓“本质图书馆学”)的转换过程;从对研究客体的研究层次看,经历了微观实体范式(即以图书、文献、图书馆构成要素等物质实体为起点构建理论体系)、宏观系统范式(即将图书馆纳入社会文献信息交流大系统中进行宏观考察,建构理论体系)、(微观和宏观兼具的)技术应用范式(即试图以微观的信息处理和传递技术、宏观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和应用技术为基础建构的虚拟的数字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转换过程;从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深度上看,经历了具体表象的认识范式、整体抽象的认识范式、本质规律的认识范式、深入整合的认识范式的转换;从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来看,经历了文献范式(包括图书、文献等)、信息范式、知识范式的转换过程;他特别强调,建立在客观知识基础上的知识组织理论最有可能成为图书馆学的主流范式。刘君[5]概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发展与变革的历程,指出传统图书馆学以文献为中心展开,进入80年代后,信息资源论思想在我国深入人心,系统科学方法被广泛应用;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组织研究则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杨晓农[6]认为,近20年来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发生了三次嬗变;以文献为逻辑起点图书馆学;以信息资源为逻辑起点的图书馆学;以知识为逻辑起点的图书馆学,并认为这种嬗变更是图书馆学对自身学科逻辑起点(文献)的更高层次的回归。
不难发现,上述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具体概括和分类均不尽相同。为了方便图书馆学科学共同体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评价,很有必要对现有的范式概括和分类做进一步的概括并形成较容易被方方面面所接受的核心范式分类方案。这里,笔者拟提出用途不同但可以兼容的三套参考方案。第一套为专指度较高的分类方案:迄今为止的图书馆学研究主要范式有“机构范式”、“文献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情报范式”、“文本范式”、“认知范式”、“制度范式”、“技术范式”和“人文范式”。第二套为网罗度较高的分类方案:迄今为止的图书馆学研究基本范式有:客体对象范式(包含“文献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情报范式”和“文本范式”)、主体对象范式(包含“认知范式”和“人文范式”)、中介对象范式(包含“制度范式”和“技术范式”)和综合对象范式(包含“机构范式”)。第三套为网罗度更高的分类方案:迄今为止的图书馆学研究学科特征范式有:理论科学范式(包含“文献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情报范式”、“文本范式”、“认知范式”、“制度范式”和“人文范式”)、技术科学范式(包含“技术范式”)、工程科学范式(包含“机构范式”)。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图书馆学研究的机构范式问题。笔者认为,迄今为止,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机构范式都是图书馆学最重要、最常见同时受到批评最多的一个研究范式。这一情形出现有诸多复杂原因,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图书馆学是为数不多的以机构命名的学科之一,既已如此,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二是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作为社会机构的图书馆都是全社会共同使用文献(或信息,或知识,或情报,或文本)体系的中心实体,因而无论是从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不能不深入研究它;三是从范式特性角度看,它不仅一个学科传统范式,也是一个经典范式,既属于综合对象范式,也属于工程科学范式,因而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与研究优势。《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7]曾给图书馆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图书馆是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该定义蕴涵了学界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一个普遍共识,即图书馆是一个有着特定功能与使命的社会机构。学界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的拓展绝大部分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但是,对于机构研究范式,学界也有深刻而中肯的批评,如徐引篪、霍国庆[8]指出,图书馆学以机构命名是不科学的,主要表现在对研究对象概括的不准确性、不稳定性和局限性,今后尚需努力揭示这一学科的本质内涵,并尽力为它寻找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
2 近30年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代表性观点
2.1 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性观点
1983年,周文俊[9]认为文献是情报交流工具,图书馆是情报交流机构。1985年,吴慰慈、邵巍[10]认为图书馆便是帮助人们利用文献进行间接交流的中介物。1986年,周文俊[11]认为图书馆本质上是文献交流体系;《理论图书馆学教程》[12]认为图书馆实质上是文献信息存储与交流中心。1988年,宓浩、刘迅、黄纯元[13]认为,图书馆是通过对文献的收集、处理存储、传递来保证和促进社会知识交流的社会机构;黄宗忠[14]认为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的存贮和传递中心,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藏用性,即对图书文献的收藏与利用,或称知识信息的积聚与传递。1989年,陈源蒸[15]认为图书馆是社会文献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性观点
1991年,《图书馆学基础(修订本)》[16]认为图书馆是对文献信息进行搜集、整序、存储、开发、传播和利用的科学、教育、文化机构,其本质属性是文献信息交流的中介。1992年,卢泰宏、孟广均[17]认为图书馆本质上是一种信息资源管理体系。1994年,那春光[18]认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其作为文献信息交流机构对文献的存储性。1996年,倪波等人[19]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本质是社会符号系统的组织和转换。1997年,郑金山[20]认为,图书馆本质上是一个符号信息的收集、整序、存储和再生产、再创造、再发现及其利用的体系。1998年,叶鹰[21]认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丁国顺[22]认为图书馆是一种公共信息的特殊流通形态;梁灿兴[23]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本质是保证文献群中的知识单元对于服务对象的可获得性;黄纯元[24]认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应是社会知识交流;徐松源[25]认为图书馆的本质是对知识的再创造。1999年,徐引篪、霍国庆[25]认为图书馆的实质是一种动态信息资源体系;张锦[26]认为图书馆在本质上是对社会信息过程的控制体系。
2.3 21世纪初期的代表性观点
2000年,郭玉娥[27]认为图书馆的本质是支持文献信息在社会与个体之间运动的公共中介;蒋永福[28-30]认为图书馆是对客观知识进行专门组织和控制的社会组织,而图书馆组织知识的实质是为客观知识主观化提供社会保障。2001年,周久凤[31]认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是知识存取。2002年,吴慰慈、董焱[32]认为图书馆社会记忆(通常表现为书面记录信息)的外存和选择传递机制,其本质属性是中介性,图书馆工作的实质就是转换文献信息,实现文献的使用价值和部分价值。2003年,吴建中[33]认为图书馆是终身教育和文化娱乐中心,也是信息传播与交流中心;张欣毅[34]认为图书馆的本质是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胡述兆[35]认为图书馆是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文庭孝、邱均平、侯经川[36]认为图书馆是一个动态增长的信息管理与交流系统,是一个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的公共性的教育、科学、文化、服务机构;龚蛟腾[37-38]认为图书馆实际上是人类公共知识中心,并强调知识馆的概念比图书馆的概念更加准确,可把知识馆定义为:把广泛搜集到的信息整序成知识,并进行知识管理和提供知识服务的科学、文化、教育系统;谢宝媛[39]认为图书馆是促进人类智慧交汇的地方;王子舟[40]认为,图书馆的实质是客观知识或者说是知识集合;于良芝[41]认为图书馆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构或服务,即对文献进行系统收集、加工、保管、传递,对文献中的知识或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交流,以便用户能够从文献实体、书目信息及知识三个层面上获得它的资源;杨岭雪[42]认为图书馆活动的实质是构建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之间的对应关系。2004年,汪全莉、胡誉耀[43]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本质是知识“营”播,即一切围绕知识传播环境的营造、知识传播目标的实现而开展的全部工作活动过程,包括知识收集、组织、存贮、保护、服务及开发等环节。柯平[44]认为,图书馆实质上是一种知识资源体系。2006年,黄俊贵[45]认为图书馆的本质就是知识与服务,或者说就是知识服务;周慧[46]认为,图书馆的根本属性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知识的社会性。
3 总体评析
3.1 成绩与启示
首先,上述观点是近30年来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其发展演变轨迹在很高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图书馆学从经验到科学、从一元到多元、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抽象的理论变革轨迹;其次,每个年代都有多种范式并存,但是,都有鲜明的主导范式:20世纪80年代的主导范式是文献范式,90年代的主导范式是信息范式,21世纪初的主导范式是知识范式。这些主导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日益精深。经进一步审视,笔者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最有理论价值的观点分别是:周文俊的“情报交流”与“文献交流”观点、《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的“文献信息交流”观点和宓浩、刘迅、黄纯元的“社会知识交流”观点,它们共同构成图书馆存在及运动作为“广义信息交流体系”这一阶段性研究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最有理论价值的观点分别是:卢泰宏、孟广均的“信息资源管理”观点,郑金山的“符号信息运动体系”的观点,叶鹰的“信息集中时空”的观点,丁国顺的“公共信息特殊流通形态”的观点,徐松源的“知识再创造”的观点,徐引篪、霍国庆的“动态信息资源体系”的观点,张锦的“社会信息控制体系”的观点,它们共同构成图书馆存在及运动作为“公共信息资源体系”这一阶段性研究主题;在2l世纪初,最有理论价值的观点分别是蒋永福的“客观知识组织”观点,周久凤的“知识存取”观点,张欣毅的“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观点,龚蛟腾的“人类公共知识中心”和“信息整序成知识”观点,王子舟的“知识集合”观点,杨岭雪的“主客观知识对应构建”观点,汪全莉、胡誉耀“知识营播”观点,柯平的“知识资源”观点,黄俊贵的“知识服务”观点,周慧的“知识社会性”观点,它们共同构成了图书馆存在及运动作为“公共知识资源体系”这一阶段性研究主题。再次,上述多数观点都是基于2个以上研究范式经过认真论证得出的,其中机构范式在各个年代都比较活跃且频繁出现在很多观点的概括之中,这充分说明机构范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适性;最后,上述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深化或拓展我们对图书馆存在及其运动的博大、复杂和深刻的认识,从而消弭某些理论误区或认识偏见。换言之,它们各自的充分展开,将为我们认识图书馆的共同本质和深层本质开辟道路。
3.2 问题与不足
首先,上述观点都不够全面和深入,主要揭示的只是图书馆存在与运动现象局部或浅层的特殊本质和初级本质,因为,仅从范式的角度看,这些观点都是基于某个核心范式或几个核心范式经过论证而得出的,如果这些观点承认基于并列的其他某个核心范式或几个核心范式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也就等于承认自己有局限性,这在不同年代之间、同一年代甚至同一年中都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例如:在2003年,诸说并存且不能互相证明非己之说不能成立;其次,上述观点均未妥善处理好认识的广延与专深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部分观点还突出存在专而不深且广而空泛并存的问题。许多文献对这种现象已经做了点评,这里不再赘述。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观点对图书馆存在与运动的博大、复杂和深刻估计不足。众所周知,文献、信息、知识、情报、文本等都是图书馆工作经常面对的客观对象,无论怎样,试图依据某一方面来揭示图书馆的共同本质乃至深层本质是不可能的。再次,上述观点所依据的范式明显不够平衡,多数观点对图书馆本质的生成性认识不足。在已指出的十个核心范式中,“情报范式”、“文本范式”、“认知范式”、“制度范式”、“技术范式”和“人文范式”尚未得到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应用,而在3个学科特征范式中,基于技术科学范式的观点也非常少。同时,从上述观点中,我们也尚未发现对学界对知识范式之后新的主导范式的特别关注。实际上,在人类认知链条中,知识只是一个重要中间环节,知识环节之后至少还有“智能”环节和“智慧”环节。目前学界的“知识域”研究已经为我们开启了走向智能范式和智慧范式之门;最后,上述不少观点中,对图书馆本质的概括显得意义含混,难以经受推敲。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概念并联问题,如“文献信息”、“知识信息”和“符号信息”等,这些并联概念之间有很大的语义重叠。笔者认为,这一情形出现可能与图书馆学研究范式转换与过渡有关,并提示我们今后应妥善处理好不同研究范式的关系,要尽可能保持概念的清晰。
3.3 讨论与小结
回顾历史是为了开辟美好未来,而我们只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立足现实世界,才能开辟美好未来。我们到底应怎样揭示图书馆的共同本质和深层本质呢?这里,拟谈几点初步设想:第一,应探求上述历史性代表性的统一性问题。可操作性的思路使用前述第二套范式分类方案,即将已有核心范式进一步概括为客体、主体、中介和综合对象范式,然后以此为平台分别解决各自内部的统一问题,例如:我们可以从人的认知过程或信息结构的等级划分角度[32],首先认识到信息与知识的统一性,即知识经过人类的智力活动由信息转化而来,是信息的一个特殊子集;然后认识到情报可能由信息转化而来也可能由知识转化而来;接着可发现文本是从内容角度对信息、知识和情报的概括,而文献是结合物质载体对信息、知识、情报的综合概括,这样一来,基于“广义信息”概念,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文本和文献的统一问题;第二,应合理拓展新的研究范式,然后解决相应的传统范式与新兴范式之间的统一性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发现介于事实范式与信息范式之间的符号范式和数据范式等,还可以发现知识范式之后的智能范式和智慧范式等,然后基于“社会记忆”或“信息谱系”概念实现已经发现的图书馆的全部客体对象的统一问题;第三,应构建能统一客体、主体、中介和综合对象范式的新的广义范式,例如“广义本体范式”,以解决涉及图书馆的所有对象范式的统一问题;第四,应努力克服对图书馆本质概括的泛化问题,给出必要的约束。最重要的两个约束可能分别是广义信息服务方向的公益性和广义信息服务内容的精华性。第五,应明确图书馆的终极关怀,要站的高、看的远、想的深且落的实。目前看来,“通过图书馆独特的社会功能以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进而实现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似乎可以作为图书馆的终极关怀;最后,应深入研究并全面把握图书馆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形态演变规律,从而高度概括出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并且这种概括应有强大的解释能力和包容能力。根据上述六点设想,基于图书馆广义本体范式[47],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这里,笔者试图对图书馆本质的新认识暂时性地概括如下:“人类全部社会记忆精华的全息共享体系”。关于这个新认识的具体内容,笔者将另撰文《魂系全息共享:图书馆本质构成体系的再探讨》专门予以论述。
收稿日期:2008-04-26
标签:图书馆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图书馆学研究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情报搜集论文; 情报学论文; 科学论文; 范式论文; 文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