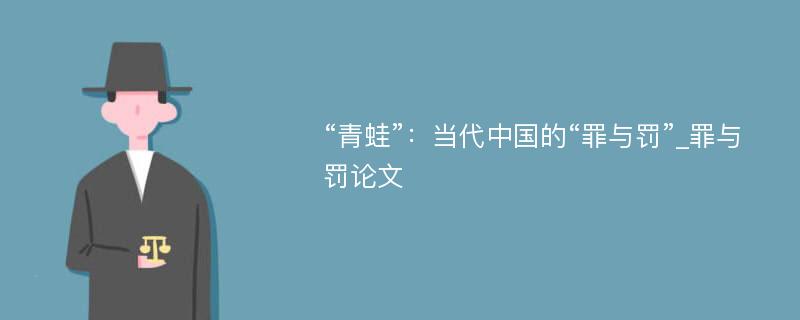
《蛙》:当代中国的“罪与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罪与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叙事意指:政治之维与生命之维
莫言以其惯用而擅长的叙述方式,展开小说《蛙》的长篇故事,“我姑姑”的叙述视角,与二十多年前《红高粱》“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样态,构成跨世纪叙事呼应。“姑姑的一生,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了”——莫言“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其“讲故事的人”角色原型可追溯至民间故事里的叙述人,内容表现则聚汇丰厚的历史蕴涵。
《蛙》开篇,叙述人蝌蚪的讲述兼跨辽阔时域,叙事收纳高密度历史内容,笔涉乡村“解放前”与“解放后”数十年沧桑内涵,叙述人对亲历历史的记述,与其对非亲历故事的转述,汇合成莫言式“叙事流”——但这不过是小说叙述表层建构,究其内里,隐在的叙述意义则有两种指向维度:一为政治之维,一为生命之维。
“我姑姑是我大爷爷的女儿。我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他先是学中医的,参军后,跟着诺尔曼·白求恩,学会了西医。”姑姑万心既身受革命先辈的光荣馈赠,她本人也曾与“大奶奶老奶奶”一起被日军“扣作人质”,“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由此在革命政权的社会体统内享有优裕的政治资本。侄儿蝌蚪对姑姑革命家史的转述,实则是小说家莫言为其主人公铺设身世谱系,他以烈士后代的身份确认,就此将万心归纳于红色血统。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并非仅止于外在地勾画主人公政治身世谱系,其叙事更“别有用心”地强化万心对革命谱系的内在认同,她对自身红色血统的政治归属,具有高度意识自觉:“姑姑坚定地对我说:孩子,你什么都可以不相信,但一定要相信,你大爷爷是抗日英雄,革命烈士!英灵山上,有他的陵墓,烈士纪念馆里,展览着他用过的手术刀和他穿过的皮鞋。那是双英国皮鞋,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临死前赠送给他的。”
“英灵山”与“纪念馆”,政治地表构筑委实是万心所属革命谱系的法定簿册,父亲的“陵墓”、“用过的手术刀”以及诺尔曼·白求恩临终馈赠的“皮鞋”,则是其红色血统的文物实证;而无论是政治地表构筑抑或实证文物,它们均为革命谱系、红色血统的象征符号,万心个体生命即存活于此象征系统内,其存在意义由象征系统赋予。并且,在革命政权的体制结构内,红色后代万心本人也是革命的肉身符号,随身携带着革命的合法性权威,其泼辣性格不惟具有个性特质,且深潜政治正义的意识自觉。作为革命后代,万心显然具有革命英雄情结,她在乡村厉行推广“新法接生”、强力取缔“老法接生”,既有以科学破除传统习俗的知识学意义,更具革命斗争的政治学意义,她飞腿怒踢“老娘婆”的暴力行为,在其自我意识中、也在莫言叙述中,具有乡村革命斗争的谱系价值和暴力革命的历史命意。
莫言叙述的政治意指,其叙事功能一方面是为“我姑姑”日后奋身投入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人物英雄情结的性格逻辑依据(其间包含人物政治意识自觉),同时另一方面,则在叙事中为计划生育确定政治合法性与正义性。在万心意识认知中,计划生育具有革命政治的合法性:“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而在莫言叙事表现中,计划生育更具有社会实践的正义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蛙》的故事叙述,表达出对计划生育政治实践的价值肯定,其间贯穿政治正义的叙述立场。然而,饶有意味的是:小说叙事的生命意指,呈示出与政治意指、即政治正义迥异的价值判断。《蛙》的生命意指表现为叙事对生命伦理的关切与敬重,小说以“吃煤块”故事叙述开首,黑煤充饥的“反常”情节,凸显生命自我保护的伦理权利。有关乡村“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手足眼鼻耳眉肝胆等等)的叙述,在人名对身体的符号化意指间,表述着对生命的素朴关怀,既表现出民间生命伦理的思想特质,作家叙事也表露着对此的精神认同。“老奶奶”以“熬绿豆汤”为“大爷爷”祛病,传统食疗法传达着有关食物与肉身关系的民间意识。姑姑“私下里”自述“当年去平度城吃日本鬼子的宴席”:“山珍海味”,“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你还不吃?”——对食欲的肯定实则是对生命欲求的伦理认同,即此可见:革命叙事内搀和着民间生命伦理意念。
有关食物的叙述、尤其是对食欲的叙述表现,通常是莫言叙事生辉之处。推究叙述动源,分明有作家本人对大饥荒的早年记忆与切身体验;追究叙述立场,则可了然:莫言对食欲的艺术表现,揭见肉身与食物间自然关系,在肯定食欲正当性的同时,传达着对生命存活权利的伦理肯定。
叙事困境:政治正义与生命伦理的价值背悖
在具有高度整一性的国家体制内,“计划”委实是一个国家词汇与国家修辞,表征着国家意志的强硬规约;所谓计划生育,实则是国家意志对自然生育的强力干预。面对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民间传统及伦理信念,国家意志实施生育干预的实践途径,只能是对妊娠的强制预防与强行中止,“男扎”和“引产”则是此间行之有效的典范性操作技术。
身为“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姑姑,“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当姑姑以红色后代的政治自觉、革命激情与泼辣干劲,奋不顾身投入乡村计划生育实践,其意识深处实际将自己从事的工作,归纳进了与红色先辈一脉相承的革命谱系,现行的计划生育被想象建构为革命事业的历史继承。在政治正义意识支配下,即便邻里“连坐”、暴力逼迫,姑姑也做得轰轰烈烈,大义凛然,且表现出自我牺牲品格与献身精神,体现着革命谱系的英雄情怀。
但在生命伦理的叙述意指上,计划生育国策以及姑姑们在社会组织基层的实践,遭遇质疑与谴责。“我母亲”,姑姑的堂嫂,“摇摇头,说:自古到今,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人一辈子生几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这还用得着你们计划?我看你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母亲”对计划生育的否定意见,代表所有母亲乃至全体乡民社会对自然生育的推崇,其意义内涵非“传统陋见”所能涵盖,隐含生命敬畏的伦理意识。但在国家意志的威权面前,母亲们素朴的生命伦理意识势单力薄;为此,“我母亲”机灵征用革命谱系中“最高指示”为自然生育辩护:“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是活宝,有人有世界!”,“毛主席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却遭姑姑指责,称是“伪造”“语录”、“矫传圣旨”,并恐吓:“这在过去是要砍头的。”
厉行计划生育的姑姑万心,在乡民世界获得“妖魔”、“土匪”等骂名,遭受“不得好死”、“死后要上刀山,下油锅,剥皮挖眼点天灯”等恶咒,这显然与她红色后代的政治身份确认、及其内心世界英雄情结,构成巨大评价反差。在莫言的叙述中,乡民社会的谩骂与恶咒一方面表现出乡村民间的陋俗,另一方面,其更深蕴涵则表达着民间生命伦理对国家意志的无奈与绝望抗议。并且,与意识质疑及话语谴责同时展开的,则是乡民社会的行为抗争:“免费”发放的“避孕套要么被扔进猪圈,要么被当成气球吹起来,并涂上颜色,成了孩子们的玩具”;“挨家挨户发送女用避孕药”,但妇女们“抗拒服用”,即便“当场逼着”吞下,“一转身,她们就用手指或筷子探喉,将那药片吐出来”;“应运而生”的“男扎手术”“非常有利于妇女、手术简便、后遗症很少”,却同样“遇到了重重障碍”。
国家意志主导的计划生育政治实践,借体制力量强力推进。“公社党委”有关推行“男扎手术”的“两项决议”,一是“领导开始”,“干部带头”,一是对违抗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手段与专政铁腕既表征着、也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强制性,以姑姑为首的“公社计划生育小组”,具有调用乡村社会国家机器(公安、武装部及民兵)的政治权力,且“把当年游击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在国家意志及其专政铁腕面前,无论是王脚乡村泼皮式的歇斯底里反抗,抑或是肖上唇的“死磨硬扛”,均终归失败,作为“反面典型”,这两个乡村男子,最终均无奈接受了“男扎手术”。
莫言叙事表达的尖锐之处在于:他认同计划生育国策的政治正义性,但同时呈示国家意志在现实实施中的暴力性及其后果——“悲剧的诞生”。耿秀莲、王仁美及“袖珍美人”王胆三位“计划外”怀孕女性,她们的“非计划”死亡,于小说叙事中凸显悲剧蕴涵;而反复书写属性相同的死亡故事,无论是作家主观动机还是文本客观效果,均表现出对悲剧性的叙事强调。莫言叙事表达的深邃之处则在于:他在认同计划生育国策政治正义性的同时,又从生命伦理立场对此考量并提出质疑,政治之维与生命之维既为小说叙事双向意指,政治正义与生命伦理则对峙而成小说叙事的内在意义张力,它们呈现为背悖的价值判断,小说叙事就此表现出内部分离、乖违的价值倾向——在我看来,这是莫言的叙事困境,其根因是叙述对象(计划生育国策)的现实困境;而就文本蕴涵论,莫言的叙事困境构成其叙事深度。
《蛙》表现出政治正义对生命伦理的现实压抑,此种压抑源于国家意志及其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实践;就此而言,小说叙事中的压抑表现,实有社会生活的现实依据,莫言创作因此具有把握现实社会问题的叙事品格。
叙事反抗:生命伦理的反压抑象征
颇具吊诡的是:遭受政治正义压抑的生命伦理,在小说叙事中以艺术方式得以伸张,莫言叙事中既表现着现实压抑,又表达着反压抑意识,即:被压抑的生命伦理对政治正义的反抗。换言之,在社会实践中被压抑的生命伦理,在小说叙事中借艺术方式,反抗压抑——这是叙事对现实的反抗,也是叙事对现实的艺术超越。
《蛙》前半部,叙事整体风貌为写实,后半部趋向神秘与象征。叙事形态及风格的前后差异,造成小说形制的内在裂隙,整体建构包含引人瞩目的断裂——它或许会招致评论诟病,但在莫言,委实出于叙事表达需要:他对象征的征用并非出于纯艺术考量,神秘也决非仅有风格学意义,在《蛙》后半部叙事中,作为艺术要素的象征与神秘,实际表述着生命伦理的反压抑意指。
“蛙”无疑是小说象征系统的核心意象,它在莫言“叙事流”中段出场,第四部开首即是:“在我的印象中,姑姑胆大包天,这世界上似乎没有她怕的人,更没有她怕的事。但我和小狮子却亲眼见到她被一只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昏厥倒地的情景。”颇值寻思的是:“蛙”在叙事中出场便径直指向万心内心世界,剥揭出其间深潜的恐惧内容(“怕”),姑姑素常形象(“胆大包天”)也在此瞬间颠覆。
“吓”“昏”姑姑的,是“一只黑瘦的青蛙”。“黑瘦”的修辞形容,显然有拟人化的叙述暗示与叙事效果。“黑瘦的青蛙”被“白纸包裹”,由“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递到姑姑手里”——这是一出蓄意制造的恶作剧,与青蛙包裹在一起的,是仇恨与敌意,因此,恶作剧实为刻意报复。寻索姑姑内在心迹,这只“黑瘦的青蛙”使她联想起自己退休那晚醉酒之后,孤身行走“洼地”的经历,那是蛙群对她的恐怖攻击:先是“蛙声的包围”,“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继之,蛙群“波涛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坚硬的嘴巴在啄着她的肌肤”,“爪子在抓着她的肌肤”,“还有很多的青蛙牢牢地抓住她的衣服、头发,有两只用嘴巴咬住她的耳垂”,“像饥饿的娃娃叼着母亲的奶头”。
蛙群围攻姑姑的情节,显然是小说叙事中的精心设计,莫言汪洋恣肆的想像及重笔浓彩的烘托,非“写实”范畴所能涵盖而有彰著的神秘性。其间,“蛙”与“娃”的谐音修辞关系,以及描述过程中普遍而精细的拟人化,建构起叙事的象征意指:“蛙群围攻”其实是“群娃复仇”。并且,由“蛙群围攻”的神秘情节象征意指的“群娃复仇”,生长、蔓延至小说末端即第五部——“九幕话剧《蛙》”,“复仇”实际成为小说后半部叙事表现的基本母题。剧本“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娃’”——剧作家蝌蚪所作的命名阐释,“当然还可以”移用说明小说《蛙》的题名。“蛙”对“娃”的象征意指,在此更伸展至神话里的种族之母:“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对神话母亲原型的叙事征用与指涉,是小说象征手段的表征,而其深层意义蕴涵则是:在对自然生育天赋权利的指认中,伸张生命伦理的正当性。
“蛙群围攻”的神秘情节及其“群娃复仇”的象征意指,表述着姑姑万心的内心冲突:她自知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也“将数千名婴儿送进了地狱”,自己“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作为乡村计划生育的“领导者组织者”与“实施者”,姑姑的职业行为体现着政治正义(“计划生育关系到国计民生,是头等大事”),而其内心蛰伏着被压抑的生命伦理,它最终以强劲反弹的方式爆发,对抗压抑。“蛙”,或者说“娃”,其实一直就在姑姑内心,没有人注意“胆大包天”的万心灵魂底处的恐惧与脆弱,它源于其内心对夭亡的“群娃”的伦理记忆,是沉重的心灵罪感体认。
罪感体认既显示莫言叙事的心理深度,又表现出伦理拷问的内在蕴涵,并由此延伸出惩罚与拯救的叙事主题。在其故事谋划中,莫言将郝大手设计为姑姑的“救命恩人”:遭受“群蛙围攻”的万心“几乎是赤身裸体跑到了小桥上,与郝大手相逢”,“她喊了一声‘大哥,救命’,便昏了过去”,是郝大手用“绿豆汤”使她“脱皮换骨”,“闯过了这一关”,紧随其后便是姑姑与郝大手结婚。此间的奇遇设计凸显叙事的传奇性,婚姻安排除了万心“感恩”之外别无双方坚实的性格逻辑依据——即:它不是人物性格逻辑必然,而是作家叙述需要。其实,无论是两者的奇遇抑或结合,莫言叙事均在“写实”原则之外,即不是写实叙事,而是象征叙事。莫言在其叙事中没有向我们“敞开”郝大手的心灵世界,这是他有意而为的“屏蔽”,“民间工艺大师”就此被处理为文本中一个象征符号,正是在象征意义上,郝大手成为万心的“救命恩人”:“姑姑是将她引流过的那些婴儿,通过姑夫的手,一一再现出来”——这是万心的赎罪与自救之道。
因此,《蛙》是一部具有强烈罪感意识的小说,它在肯定当代中国生育政策的政治正义性的同时,又将这种政治正义性在叙事中悬置,且从生命伦理的维度拷问我们的灵魂。就此而论,莫言的叙事超越了现实政治考量,而具有生命本体追问的哲学沉思品格,《蛙》也就此成为当代中国的“罪与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