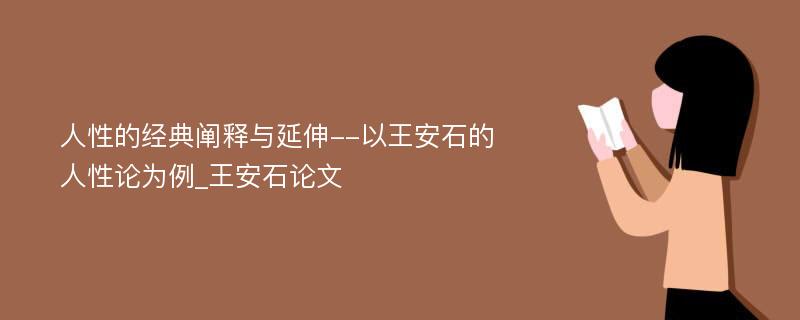
经典诠释与人性义理的伸展——以王安石人性论为个案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论文,义理论文,个案论文,王安石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性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话题,历代儒家都程度不同地有所关注与讨论。王安石论人性涉及性才、性情、性命等方面,本文拟由此三方面对其人性论展开讨论,希望能够准确把握王安石人性论的内容、特点及其意涵。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诠解、发展、充实儒家人性思想,与其独到的经典诠释理论与方法存在密切关联,因而本文亦将其列为考察、研究之任务。 一、性移才异 “性”、“才”这两个范畴在先秦就已进入儒家的视野。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①孟子的意思是,人若按其本有资质为之,即可以为善,因此,人若不为善,不是因为其本有的资质。因而孟子所谓“才”,是指资质或本性,也就是说,对孟子而言,“才”与“性”是一物。那么,在王安石这里,“性”、“才”含义及其关系是怎样的呢? 王安石认为,“性”是仁、义、礼、智、信五常,“才”是愚、智不移者。他说:“其所谓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谓也。才者,愚智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品,则孔子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是也。欲明其性,则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孟轲所谓人无有不善之说是也。”②就是说“性”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因而属道德范畴;“才”是指人愚智、昏明之等级,因而属知识范畴;这与孟子的说法不同了。他甚至说如果要讨论“性”,就得由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说开始,而讨论“才”则要从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说开始。王安石将“性”与“才”做德性与智性的区分应该是个突破。 可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什么意思呢?王安石说:“此之谓智愚,吾所云者,性与善恶也。恶者之于善也,为之则是;愚者之于智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后世圣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孔子作《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盖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与,惟孔子之智,虽游、夏不可强而能也,况所谓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③就是说,在道德层面即人性层面,上智下愚通过“习”发生转换;而在智识层面,上智下愚不可换位,即愚不可能转向智,智也不可能转向愚,因而所谓“上智下愚不移”是在智识范围内说的。那么,道德上的“上智下愚不移”又是什么意思呢?王安石说:“有人于此,未始为不善也,谓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为不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有人于此,未始为善也,谓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为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下愚,皆于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④就是说,只有不曾为恶而最终也没有作恶之人,从而不存在移向“中人”的情形(虽然不曾为恶最终还是为了恶,这就叫“移”),此谓上智;只有不曾为善而最终也没有作善之人,从而不存在移向“中人”的情形(虽然不曾为善最终还是为了善,这就叫“移”),此谓下愚。可见,王安石这里所理解的“上智下愚不移”,是根据人在德行上的最终表现(或善或恶)进行判断的,因而并不意味着上智下愚天生不可互换。既然是以道德的善恶规定上智下遇的内容,那么上智下愚便成为德性范畴,从而使“上智下愚”伦理化。因此,王安石服膺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说,乃是因为此观念可以支持其道德上的“上智下愚不移”论。 既然道德意义上的“上智”、“下愚”是可移的,那为什么又说它们不能互移呢?王安石说:“谓其才之有小大,而识之有昏明也。至小者不可强而为大,极昏者不可强而为明,非谓其性之异也。夫性犹水也,江河之与畎浍,小大虽异,而其趋于下同也。性犹木也,楩楠之与樗栎,长短虽异,而其渐于上同也。智而至于极上,愚而至于极下,其昏明虽异,然其于恻隐、羞恶、是非、辞逊之端则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轲之言,有才性之异,而荀卿乱之。扬雄、韩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说,混才与性而言之。”⑤就是说,“五常”对于上智者、下愚者是一样的,即智、愚皆具“五常”。但“才”与“性”是不同的东西,荀子、扬雄、韩愈正是因为困惑于“上智下愚不移”之说,将“性”、“才”混为一谈。而事实上,才有大小,识有昏明,小者不可强为大,昏者不可强为明,这不是性的差别,而是才的不同。性如水就下,如木上长,是事物的内在趋势。这样,所谓“不移”只是对智识而言,王安石就将“上智与下愚不移”与“性相近,习相远”做了圆融,从而克服了“上智下愚不移”成为其主张“性相近,习相远”的障碍。蒋维乔、杨大膺可谓准确地传承了王安石观点,他们认为:“至于上智、下愚不移,那不是从性的立脚点去说人类有上性下性,是从生理的立脚点去说人性虽可以由环境塑染,但在生理上,却有不能受环境塑染的人,这就是上智下愚不移。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智或愚,和他的脑成正比的。脑极大,就是聪明的人;反之,脑极小,就是极愚笨的人。猿猴没有人的智慧大,就是因为脑不及人大脑的大小,在母胎中就决定了,所以人的智慧也在母胎中决定,而环境不能增减脑的大小,也就不能移转人的智慧,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他们把这个道理看错,于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孔子的性纯可塑论,就一变为他们的性三品论。”⑥ 虽然“性”与“才”是有区别的,而且智识层面上智下愚不可移,但二者却存在密切关系。王安石说:“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者,生之质也,五常是也。虽上智与下愚均有之矣。盖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也。夫人生之有五常也,犹水之趋乎下,而木之渐乎上也。谓上智者有之,而下愚者无之,惑矣。仲尼所谓生而知之,子思所谓自诚而明,孟子所谓尧舜先得我心之所同,此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谓困而学之,子思所谓勉强而行之,孟子所谓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者也。”⑦就是说,作为人生来而具的本质,仁义礼智信“五常”人人都有,上智有,下愚也有,因而不能说上智有五常之“性”,而下愚没有五常之“性”。只不过,“上智”是生而知之者,“下愚”是困而学之者,因而它们所能开发出的“五常”之多寡是不同的。这表明王安石认识到智识对于道德的影响:愚昧的人虽有德性,但难以觉悟并显发出来,而聪明的人容易觉悟并能显发出来,这就是所谓“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⑧。也就是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⑨。 概言之,王安石基于“性相近,习相远”与“上智下愚不移”两个命题对“性”与“才”关系展开了一定程度的讨论。王安石认为“性”与“才”是两物,前者就善恶言,后者就智愚言;上智下愚都具有“五常”,但上智下愚所得不均,而这种不均并非天生的、永恒的,而是上智下愚的觉悟高低锐钝不同所致;因此人性上的“上智下愚不移”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智识上的上智下愚不移;人性上的上智下愚可以换位,乃是后天努力使然。换言之,“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⑩。这样,王安石通过对“上智下愚不移”做德性与智性的区分,从而纠正了才、性不分的错误观念,进而阐明德性的上智下愚借助外在条件可以实现转换的道理,由此回到他信奉的孔孟人性论:“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圣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轲,孟轲学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载于《语》。子思、孟轲之说,著于《中庸》,而明于七篇。然而世之学者,见一圣二贤性善之说,终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岂非惑于《语》所谓上智下愚之说与?噫,以一圣二贤之心而求之,则性归于善而已矣”(11)。 二、性情一体 王安石之前,儒家关于性情的讨论从没停止过,如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12)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13)《礼记·乐记》载:“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董仲舒说:“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14)李翱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也。”(15)可见,性与情关系自是儒家人性论必须观照到的课题。那么,王安石之于性、情关系有怎样的识见呢? 王安石说:“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此吾所以异于韩子。且韩子以仁、义、礼、智、信五者谓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恶焉而已矣。五者之谓性而恶焉者,岂五者之谓哉?”(16)在这里,王安石将“性”与“五常”的关系等同于“太极与五行关系”,“性”即是太极,而太极与五行关系是生与被生的关系,太极是本体,是生者,因而“性”之于五常,也是本体,是生者。韩愈的错误就是将“五常”视为“性”,并判其为恶。王安石认为,“性”之无善恶也表现在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都不能自洽上。就孟子言,他说:“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后出乎中者,有不同乎?”(17)就是说若按照孟子性善说,那就必须证明人没有怨毒之心,而且,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都是受外在影响而表现出来,这点没有差别,因此,如果在经验上无法证明一个人没有怨毒忿戾之心,就不能有人性善的判断。而荀子言性恶存在同样的问题。王安石说:“荀子曰:‘其为善者,伪也。’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为人果皆无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为埴,埴岂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乌在其为伪也?”(18)就是说,荀子言性善乃人为,那就必须证明人没有恻隐之心,而荀子本人也认为,如果不是土而是木,就不能做出“埴”来。既然不能否认恻隐之心的存在,就不能说善乃人为。因此,孟子不能证明人无怨毒忿戾之心,荀子也不能证明人无恻隐之心,那就说明他们的主张都存在逻辑上与事实上的矛盾,因而最终结论是“性无善恶”。 “性”与“五常”是“体”与“用”的关系,而且性无善恶,那么,善与恶由何而生呢?王安石说:“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19)太极是本体,其生出“五行”后,才有利害出现,因而太极不能以利害言之,即太极无利害。性与情的关系,等同于太极与“五行”的关系,性无善恶,“情”处才有善恶。而孟子、荀子或言性善或言性恶,所以王安石说自己不同于孟、荀。王安石说:“且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扬子之言为似矣,犹未出乎以习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20)既然只有“情”处才显出善恶,而“情”是“性”的表现,因而“性”无善恶。不过,这里隐含需要追问的问题:(1)既然“情”才有善恶,那么“情”何以为善,又何以为恶?(2)既然“情”可善可恶,那么使“情”可善可恶的条件是什么? 如上讨论不难看出,王安石所言性是体,且无善无恶,而情是用,且有善有恶,那么,无善无恶的性与有善有恶的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王安石说:“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21)就是说,喜、怒、哀、乐、好、恶、欲这些言情的东西,存于心而未发出时是性;而当它们发出来并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情。性是情的本体,情是性的末用,它们一个是未发,一个是已发,所以性情一体。王安石说:“彼曰性善无它,是尝读孟子之书,而未尝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恶无它,是有见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恶,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动而当于理,则圣也、贤也;不当于理,则小人也。彼徒有见于情之发于外者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恶也,因曰情恶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于情之发于外而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22)在这里,王安石清楚地阐述了性情关系:性是未发,情是已发,性本情用。这是儒家人性论的重要观念,喜、怒、哀、乐、好、恶、欲七情出于性,因而不能认作恶,这样就肯定了七情的合理性。由于接物而有善恶发生,合于理,为圣为贤,即善;不合于理,为小人,即恶。这里提出了情必须合于理的问题,因而善、恶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的。情之发于外既可能是恶,也可能是善,因而不能简单地“定情为恶”,这就为合理的情张目。王安石对人性的解释,透显着深厚的人文关怀。 由于性情一体,情由性出,因此君子养性之善,其情也善,小人养性之恶,其情也恶。所以,君子之所以是君子,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决定者是情,视其在情处的表现。王安石说:“盖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故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莫非情也。”(23)因此,不能将性归为君子、情归为小人,因为是君子还是小人要看其在“情”处的表现。王安石说:“彼论之失者,以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所谓情者,莫非喜、怒、哀、乐、好、恶、欲也。舜之圣也,象喜亦喜,使舜当喜而不喜,则岂足以为舜乎?文王之圣也,王赫斯怒,使文王当怒而不怒,则岂足以为文王乎?举此二者而明之,则其余可知矣。”(24)因此,小人君子之分,就在一个情字。不能将情性分离,性是君子,情是小人,这是不合实情的。足见“情”多么重要。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情”若被废,则性不能显现,就成了不能自明的怪物。王安石说:“如其废情,则性虽善,何以自明哉?诚如今论者之说,无情者善,则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须,犹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恶,则犹中与不中也。”(25)性情犹弓矢,所以是一体。因此,性由情显,体由用见,情若是被废除,则不能见性,不能见体,所以“性情一体”论在肯定情欲合理性同时对情欲进行了规范。 王安石将性比之太极,而且无善无恶,从而将性确定为无善无恶的本体;而无善无恶的本体必须有一个表现自己的“物”,这就是情,因而性与情是体用关系,是未发已发关系;已发的情因与外界接触而可能失其正,一旦失其正,便是恶,因而需要护情养性;护情既是不使失其正,又是使性得以健康呈现,因而情是不能废弃的;情由性而出,性无善恶,因而养性善者,其情亦善,养性恶者,其情亦恶。由是观之,君子小人的分别就看其在情方面的表现,其在情处为善,即为君子,反之,为小人。概言之,王安石确定了性情关系为本末体用关系,揭示了情在其相互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指出了性为君子、情为小人之判断在理论上的错误,强调了君子养性成善的重要。 三、以性正命 儒家对性命的关注有着悠久的传统。如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26)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27)董仲舒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28)可见,性与命在王安石之前就已有关注和讨论,对二者的含义也有所界定。那么,王安石思想中的“性”与“命”是什么含义呢?其对“性”、“命”关系的讨论又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王安石说:“天授诸人则曰命,人受诸天则曰性。”(29)就是说,天授予人的东西叫“命”,如天将天下授给帝王,而授予者(天)与接受者(帝王)是主客关系,这就叫“命”;将人生而有的东西叫“性”,如人之感官需求等,而且这里的“天”是虚设,人与天不存在主客关系。对人而言,天之授予行为是外在的,是可变的,即“天”授予谁、什么时候授予都是不确定的;而人承受者,是本有的,天生而就的。正所谓“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30)。概言之,“命”是指变化无常而不可控的必然性,“性”是指事物生来本有的规定性。但“性”、“命”关系之于人而言极为复杂,或者性服从命,或者命从属于性,或者性、命合作而相得益彰。所以说,性命之理远深而神秘,并且会发生不同结果,所以要正性命。所谓“性命之理,其远且异也。故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是圣人必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也”(31)。 那么,怎样才叫性命正呢?王安石说:“圣贤之所以尊进,命也;不肖之所以诛,命也。昔孔子怀九官、二伯之德,困于乱世,脱身于干戈者屡矣。遑遑于天下之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于旅人也。然则九官、二伯虽曰圣贤,其尊进者,亦命也。盗跖之罪浮于四凶、二叔,竟以寿死,然则四凶、二叔虽曰不肖,其诛者,亦命也。”(32)在这里,王安石对“命”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就是圣贤应该被尊进,不肖应该被诛杀,这就是“命”,即合乎公理才叫“命”,或者人道合乎天道才叫“命”。但在现实生活中,人道往往与天道相悖,表现为“命不正”,所以要正命,也就是使人道合乎天道。而“人道合乎天道”的命正现象,也就是“命行”。王安石说:“然命有贵贱乎?曰有。有寿短乎?曰有。故贤者贵,不贤者贱。其贵贱之命正也。抑贵无功而贱硕德,命其正乎?无憾而寿,以辜而短,其寿短之命正也。抑寿偷容而短非死,命其正乎?故命行则正矣,不行则不正。”(33)所谓“命行”,就是贤者贵、不贤者贱,这叫贵贱之命正。因此,无功而贵、硕德而贱,便不是“命行”,故不能说是命正;而无憾而长寿,以罪恶而寿短,便是“命行”,故是寿短之命正。按照这个逻辑,历史上尧舜时代四门无凶人,而比屋可封,表明那个时代“命行”,所以贵贱寿短之命是正。王安石说:“是以尧舜四门无凶人,而比屋可封,此其行贵贱寿短之命于天下也。降及文王兴,而棫朴之诗作,则士不侥幸,而贵贱之命正矣。成王刑措而假乐之诗作,则民不憾死,而寿短之命正矣。”(34)概言之,如果以无功为贵,以硕德为贱,这就不叫命正了,寿命也是如此。可见,王安石在性命论上所表达的价值立场,正体现了儒家的道义精神。可是,贤者贵、不肖者贱即“命正”是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正性命怎样完成? 如上所言,性命正就是贤者贵、不肖者贱,就是人道与天道合,就是“命行”。关于这点,王安石借助孟子、扬雄对性正、命正内涵做了更为具体的说明。他说:“孟子之所谓性者,独正性也;扬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扬子之所谓命者,独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35)就是说,孟子所言性只讲了“性正”方面,而扬雄所言性包括“性正”与“性不正”两个方面。王安石说:“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恶之性,且以羞恶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尽力乎善以充其羞恶之性,则其为贤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谓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以充羞恶之性,则其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扬子之兼所谓性者也。”(36)就是说,人好善恶恶,并努力为善去恶,此即孟子所言“性正”;而以逐利为目标,且没有止境,即扬雄所言“性不正”。因此,如果有人逐利而至不屑,扬雄必厌恶:“今夫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则扬子岂以谓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恶其失性之正也”(37)。因为这已是失性之正。孟子所言命,认为任何事象都由命定,即所谓“莫非命”;而扬雄主张“人为或不为”才是命。王安石说:“有人于此,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谓命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贵而贱,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扬子之所谓命也。”(38)有人才疏而贱、犯罪而死,原因在于自己不作为,而从命上说,属于命不正。孟子也把这种现象称作“命”。如果是另一种情况,依人的材质本可以贵却贱,按人的品德本可以生却死,这不是人力所能掌控的,而从命上说,属于命正,这就是扬雄所讲的“命”。如果有人听天由命而不努力,孟子必厌恶。 综上可以看出,性命正,就是使人道合乎天道,即所谓“命行”。那么,怎样使性命正?王安石说:“是诚君子志也。古之好学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由此而言之,则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君子虽不谓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为不肖,何以异于此哉?”(39)这就是说,如果在“命”的现象中有“性”,那么君子就不叫它“命”了。为什么?因为“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得其正,就需要人去正命,而“命”是客观的必然,“性”是主观的自由,因而“正命”必须诉诸“正性”,由于“正性”必然达到“正命”,所以“命”就不成其为“命”了。由此可看出,在王安石观念中,“性”不仅是人与生俱来的基质,更是一种内在的向善力量,正是这种向善力量无穷无尽的扩充与释放,使不正的命归于正。这正是王安石性命说的核心。 那么,如何正性命呢?首先是尽人事。王安石不信命,所谓“天命不足畏”。他说:“是以圣人不言命,教人以尽乎人事而已。呜呼,又岂唯贵贱祸福哉?凡人之圣贤不肖,莫非命矣!”(40)如上所言,所谓“命不正”,就是“贤者贱,不肖者贵”之现象,因而“正性”就是使“贤者贱,不肖者贵”转变为“贤者贵,不肖者贱”,所以王安石主张尽人事,尽人事也就是“正命”。那么,圣人怎样尽人事呢?王安石说:“以至人及草木,而天下之命其有不正乎?其后幽王有圣人之势,而不称以德。故君子见微而思古,小人播恶而思高位。诗曰:‘谋之其臧,则具是远。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夫有德者举穷,不德者举达,则贵贱之命行乎哉?抑小人进用而刑罚不当,故恶有所容而善斯以戮。诗曰:‘此宜无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复说之。’失是善者杀,不善者或生,则寿短之命行乎哉?此知命非圣人不行也。”(41)所谓贵贱之命行,就是“贤者贵,不肖者贱”,所谓寿短之命行,就是“善者寿,不善者短”,可是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而是“命不行”、“命不正”;而要颠覆这种现象,王安石认为只有寄希望于圣王。 其次是以人道合天道。王安石说:“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贤者治不贤,故贤者宜贵,不贤者宜贱,天之道也;择而行之者,人之谓也。天人之道合,则贤者贵,不肖者贱;天人之道悖,则贤者贱,而不肖者贵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则贤不肖或贵或贱。尧、舜之世,元凯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纣之世,飞廉进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汉、魏而下,贤不肖或贵或贱,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盖天之命一,而人之时不能率合焉,故君子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贵贱祸福之来,不能沮也。子不力于仁义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于诞谩虚怪之说,不已溺哉?”(42)在王安石看来,贤人治理不贤,而贤者贵、不贤者贱,这是天然的道理;但若贤愚贵贱属于选择的结果,则是人所为。因此,只有人为与天道相合,贤者才能贵,愚者才能贱。相反,天人之道相悖,就必然是贤者贱、愚者贵。那么,这里所谓天道是指什么?人为又是指什么?它们怎样才叫合?怎样才叫悖?“使贤者治不贤,故贤者宜贵,不贤者宜贱”,这叫天道;对天道进行人为的选择,就是人道。人的选择与天道相合,就是贤者富、愚者贱;相反,人的选择与天道悖,就是贤者贱、愚者贵。在这里,王安石进一步阐述了命与性的关系:贤愚,是人性的部分,富贵,是天命的部分;由贤愚到富贵贫贱,也就是从性到命,由性改变命,是可能的,但也是困难的。这就反映了王安石对于性虽然持积极的态度,但并不认为性是可以轻易成就的,不能不受命的影响,因而正命便成了他面对的主要课题。 再次,正命不能有违仁义。对儒家而言,“仁义”是其根本精神,对君子而言,“仁义”是其风骨,是其血脉。因此,由仁义而富且贵,心安理得;反之,心神不宁。因此,即便贤者不能富贵,即不能做到“命正”,但仁义在其中,亦足自慰。王安石说:“夫贵若贱,天所为也;贤不肖,吾所为也。吾所为者,吾能自知之;天所为者,吾独懵乎哉?吾贤欤,可以位公卿欤,则万钟之禄固有焉;不幸而贫且贱,则时也。吾不贤欤,不可以位公卿欤,则箪食豆羹无歉焉;若幸而富且贵,则咎也。此吾知之无疑,奚率于彼者哉?且祸与福,君子置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义,反仁义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义而祸,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于匡,彼圣人之智,岂不能脱祸患哉?盖道之存焉耳。”(43)贵与贱是地位的高低、身份的尊卑,这是天决定的;贤与不贤,就是你这个人好与坏,有无德行,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是可以由人决定的。就是说,人能否得到富贵,后天努力是前提,但最终能否成功,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这是个人所不能把握的,因为“命”在其中。但天决定的事,每个人也不是毫无争取的希望。概言之,“命”所决定者仍有“性”在,而“性”所决定者往往由于“命”而不能落实。然而,不管是贤能不幸而贫贱,还是不肖幸运而富贵,都不能与仁义相悖。就是说,违背仁义而得到的富贵,为君子所不取;合乎仁义而丧失富贵,君子不会在乎。这样,王安石将正性命与仁义结合起来,仁义成为正性命的依据,使其性命论所蕴含的儒家精神得以殷实、得以鲜明。 概言之,性与命都存在不正之情状,所以有正性与正命的任务;性是内在的、本有的,命是外在的、必然的;正命就是做到“贤者贵,不肖者贱”,因而可通过正性达到目的;正性就是扩充人的内在力量,就是尽人事,就是修行,从而认识、把握命,以达到正命。可见,王安石的“性”之内涵具有多层性:生来本有之性;究竟之性;扩充善能之性;理性调适之性。正是以内涵如此丰富的“性”,去引导、监督、完善“命”,使命归于正。因此,王安石通过性与命关系的讨论,展示了他对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思考,在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张力之间,主张通过正性以正命,注重主体内在力量对于外在命运的把握,强调内在自由对于外在世界改造与建构的能力与信心。因而可以说,发现并扩充性所内含的正命之力量,正是王安石在人性论上的又一独特贡献。 四、结语 本文以上从性才、性情、性命三个向度对王安石人性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析,同时展开了一定程度的讨论。基于上述讨论,或许仍可对王安石人性思想做如下延伸性思考。 (一)王安石人性论概要 王安石之于性才、性情、性命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讨论,在丰富儒家人性思想的同时不仅贡献了诸多建设性的观点,似也留下了某些可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1.理论内容。王安石究竟在哪些方面丰富了儒家人性论内涵?可以说俯拾皆是。在性才关系上,对性才做了道德与知识的区分,肯定了智识对于道德的积极意义;对“上智下愚不移”做了智识与道德内涵的分解,以疏通与“性相近,习相远”的关系;在性情关系上,他超越孟荀提出性无善恶论,而回到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说;又标举性情一体论,超越了性三品说与性善情恶论;在性命问题上,提出并解释了命、正性、正命、命行等概念,提出了正性以正命的重要观点。这些无不显示出王安石在人性思考上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他的系列主张与观点,都称得上是儒家人性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 2.人文意蕴。儒家关于人性的讨论,即建基于深切的人文关怀,王安石的人性思想忠实地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王安石认为上智与下愚所得到的五常是不等的,上智得之富,下愚得之寡,因而主张提升人的智识,从而肯定智识在人性上的价值。王安石认为,性情一体,情是性的表现,废情即不能认识性,即不能表现性,即是否定性,从而肯定适度情欲的意义;儒家认为性是本有,与生俱来,但王安石开发了“性”的主体性,内在于人的“性”是一种扩充善的力量,是人对自我的要求,从而引导、规范命,使命归于正,由此王安石将主体自由精神通过“正命”进行了充分的彰显与激励。 3.粗略之处。王安石关于人性的论述中,由于并没有从理论上对人性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因而存在可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第一,对人性的性质规定不确定:王安石一方面说性(五常)人人具有,另一方面又说性不能善恶言。第二,对“性”的地位不确定:有时性是太极,有时性又是五常,前后阐释,不统一。第三,混淆德性与智识,从而阻碍了智识的伸展。王安石以道德融于智识之中,从而将上智下愚的内涵实现了由智性向德性的转换,但以德性规定、判断智识,必然将人引向智识相反的方向,从而妨碍智识的发达。第四,人性观上呈贵族色彩。王安石虽然认为人人具有无常,上智下愚概不例外,但在五常的觉悟与开发上,只有先知先觉的圣人有资格;王安石强调“以性正命”,但真正能够正性命的只有圣人,可见,王安石的人性论仍然没有跳出贵族性窠臼。 (二)对儒家人性论影响 王安石讨论人性的文字并不多,然而,就是在那些有限的“绣针”式文章中,却让任何人不敢低估其在儒家人性论上的影响。 1.对儒家人性论的丰富与发展。王安石人性论在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人性理论。在性才关系上,他借助“上智下愚不移”命题的解释,指出就性而言,上智下愚可移;就才而言,上智下愚不移,这就相对积极地处理了上智与下愚的关系。在性情关系上,李翱等主张性善情恶说,王安石认为性情一体,肯定情的合理性,而性不能善恶言,从而超越了孟荀的人性论,否定了李翱的性善情恶说。在性命论上,王安石整合了孟子与扬雄的性命论,调动了“性”的主体性,激活了“性”的内在力量,从而将性、命所内含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加以处理。可见,王安石对于儒家人性论的确有了很大推动。 2.对新儒学人性主张的影响。王安石人性论不仅对前人的人性理论或观点进行了修正、丰富与提升,而且下启了新儒学的人性论。主要表现在:就性情关系论,王安石的观点是性情一体,性是未发,情是已发,善恶在情处。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对儒家处理本体之性与末用之情提示了方向,而其受益者就是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朱熹说:“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44)朱熹认为:“有这性,便发出这情;因这情,便见得这性。因今日有这情,便见得本来有这性。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恻隐、辞逊四端之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之意。”(45)朱熹还说:“盖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盖性之与情,虽有未发已发之不同,然其所谓善者则血脉贯通,初未尝有不同也。”(46)朱熹的这些话我想无需多解释,其受王安石性情一体论影响清晰而确实。因此,朱熹的“心统性情”论当可视为王安石性情说的修正与发展。再看性无善恶论(47),王安石认为,孔子所言“性相近,习相远”,并没有说性善性恶,而且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恶,都存在经验上与逻辑上的矛盾,因此,性无善无恶。这让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几百年之后的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48)。应该说,王阳明对“性”之性质的规定,可谓与王安石“同条共贯”。此外,王安石强调养性对于情的规范义,注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所谓养性之善则情善,养性之恶则情恶,王阳明则认为:“静时念念存天理灭人欲,动时念念存天理灭人欲”(49)。王安石开发了“性”所蕴含的能动性,强调正性以正命,即希望通过主体自身的完善解决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的矛盾,心学家陆九渊、王阳明都强调“心即理”,强调道德主体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人性论对于心学的发生与形成是有特殊作用的。 (三)经典诠释理论与方法 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的更新、丰富与发展,是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实现的,因而王安石丰富与发展儒家人性论实践中,必然表现出其经典诠释的态度、理论与方法。 1.综罗百经以视其通。在王安石观念中,所有的经书都值得尊重,都值得学习,表现为海纳百川的气量与胸怀,因而他在解释、发展儒家人性论的时候,对于所能掌握的人性观点与学说概不排斥。他说:“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50)正因为这样,儒、道、墨、名、法、佛等学派的人性主张与观点,他都有涉猎,都认真学习、研读、消化。当然,正如王安石所说,他对诸多人性学说与观点的涉猎,并不是盲目泛览而无所宗,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选择他所认同的人性思想,比如性无恶善论、性情一体论、正性以正命说等,都是在分析其他人性主张基础上形成的,从而达到“尽圣人故”以“明吾道”的目的。 2.超越文字以揭其义。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诠释,充分体现了其不拘泥文字而发掘意蕴的诠释理念。比如,他将“上智下愚不移”做德性与智识的区分,认为讲不移时,是就智识言,而讲可移时,是就德性言。王安石对孟子、扬雄的性命论进行解释的同时,创造性地对命、命正、命行、正性、正命等概念做了规定,使儒家性命论思想进到一个新的层次。这都表现了王安石解释经典依傍文字而又超越文字的特点。他引用孟子的话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为周者之所以讼也。”(51)这种以追求义理为宗旨的诠释方法,正表现出对传注方法的否定。王安石说:“孔子没,道日以衰息,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以无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传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学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52)在王安石看来,只有将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发掘出来,才能真正传承、光大圣人之学。 3.解经的标准与目标是人心。王安石对于儒家人性思想的解释,表现出了鲜明的以人心为宗的旨趣。比如,他对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否定,以凸显自己的性无善无恶论;他对“性三品”说与“性善情恶”论的否定,以凸显自己的性情一体论;他对孟子、扬雄性命说的解释,以服务于他的正性、正命主张。此外,王安石强调养性之善才能养情之善,强调“性”的主体性、扩充性,等等,都表明王安石在经典诠释上主体为宗的特点。王安石说:“余闻之也,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数在乎俎豆、钟鼓、管弦之间,而常患乎难知,故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辩说,诵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学,而乐于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恶夫非之者。乃烧《诗》、《书》,杀学士,扫除天下之庠序,然后非之者愈多,而终于不胜。何哉?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经虽亡,出于人心者犹在,则亦安能使我舍己之昭昭,而从我于聋昏哉?”(53)王安石以秦焚《诗》《书》、杀学士而不能淹没人心为例,阐明经典诠释的标准与目标都是人心。 4.以生命贯注诠解实践。王安石对于儒家人性论的理解与发展,贯注了生命原则。孔子有“性相近,习相远”说,又有“上智下愚不移”说,这弄懵了不少人,包括韩愈这样的大学者。王安石对这两个命题进行了生命性的解释。他将“上智下愚不移”做德性与智识的区分,从而打通了“上智下愚不移”与“性相近,习相远”,这不仅消除了荀扬董韩等的迷惑,而且对孔子人性思想实现了圆融。韩愈、董仲舒有所谓“性三品”说,王安石认为“习于善者为上智,习于恶者为下愚,一习于善,一习于恶,为中人”,这个表述的内涵在于:上智、下愚、中人的划分,是根椐主体习惯于善或恶的修行与实践时间的长短,因而突破了那种以所得“五常”多寡决定上智、下愚、中人的固定模式;由于“习”是动态的、可变的,从而规定了上智、下愚、中人的可移性,而突破了将上智、下愚、中人视为固定不变结构之僵化观念;由于“习”所强调的是主体的力量,确信主体对于人之德性高低的掌控能力,从而突破了“性三品”说中的先验性。可见,王安石在上智、下愚、中人的规定上,显示了其诠释思想的开放性。李翱有所谓“性善情恶”说,王安石认为性情一体,性是未发,情是已发,但二者是一物,因此,不能说性善情恶,并通过废情以保护性善,这完全支离了性情关系。情是性的延伸,是性的呈现,没有情也就废除了性,因而必须肯定情的存在,在肯定情存在的基础上考虑情不失其正的问题。可见,王安石的性情一体是将性与情视为生命整体,而不是偶设一个情并定之为恶,然后千夫所指,这完全背离了性情论本旨。正性命是儒学的一大课题,如何正性命也是王安石面对的难题。王安石将“正性”解释为“为善去恶”,解释为“扩充性而成善”,解释“正命”为“贤者贵,不贤者贱”,因而“正命”就是消灭“不公平的必然性”,如“贤者贱,不贤者贵”。而要消除“命不正”的情形,就必须“正性”,就必须尽人事,使人道合乎天道。可见,王安石对于“正性命”的解释也是洋溢着生命气象的。质言之,王安石之于儒家人性论的解释,即是生命精神的贯注,从而呈现动态活泼、生意盎然之气象。 概言之,王安石更新、丰富儒家人性思想是通过其理解与解释儒家经典完成的,而其理解与解释儒家经典实践中所表现的态度、所坚持的理论、所应用的方法是成就其人性论的前提。王安石以宽阔胸怀善待所有人性理论,以求得文字意旨作为解释方法,以人心作为选择人性主张并对其改造的根据,以生命性作为疏通、圆融所有人性论的基本路径,如此便使王安石诠释经典的理论与方法凸显出义理特质,而成为告别汉儒传注方法的重要标志,正所谓“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视汉儒之学若土埂”(54)。 注释: ①《孟子·告子上》。 ②王安石:《性论》,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临川集拾遗》第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页。 ③王安石:《原性》,载《王安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④王安石:《性说》,载《王安石全集》,第237页。 ⑤王安石:《性论》,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临川集拾遗》第五集,第283页。 ⑥蒋维乔、杨大膺:《中国哲学史纲要》,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48页。 ⑦王安石:《性论》,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临川集拾遗》第五集,第282页。 ⑧《孟子·告子上》。 ⑨《易传·系辞》。 ⑩王安石:《性说》,载《王安石全集》,第236页。 (11)王安石:《性论》,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临川集拾遗》第五集,第282页。 (12)《孟子·告子上》。 (13)《荀子·正名》。 (14)《春秋繁露·贤良策三》。 (15)《李文公集》卷二。 (16)王安石:《原性》,载《王安石全集》,第235页。 (17)王安石:《原性》,载《王安石全集》,第235~236页。 (18)王安石:《原性》,载《王安石全集》,第236页。 (19)王安石:《原性》,载《王安石全集》,第235页。 (20)王安石:《原性》,载《王安石全集》,第236页。 (21)王安石:《性情》,载《王安石全集》,第234页。 (22)王安石:《性情》,载《王安石全集》,第234~235页。 (23)王安石:《性情》,载《王安石全集》,第235页。 (24)王安石:《性情》,载《王安石全集》,第235页。 (25)王安石:《性情》,载《王安石全集》,第235页。 (26)《论语·宪问》。 (27)《孟子·尽心下》。 (28)《春秋繁露·贤良策三》。 (29)王安石:《性命论》,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临川集拾遗》第五集,第283页。 (30)王安石:《扬孟》,载《王安石全集》,第235页。 (31)王安石:《性命论》,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临川集拾遗》第五集,第283页。 (32)王安石:《对难》,载《王安石全集》,第239页。 (33)王安石:《性命论》,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临川集拾遗》第五集,第283页。 (34)王安石:《性命论》,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临川集拾遗》第五集,第283页。 (35)王安石:《扬孟》,载《王安石全集》,第234页。 (36)王安石:《扬孟》,载《王安石全集》,第235页。 (37)王安石:《扬孟》,载《王安石全集》,第235页。 (38)王安石:《扬孟》,载《王安石全集》,第235页。 (39)王安石:《对难》,载《王安石全集》,第239页。 (40)王安石:《对难》,载《王安石全集》,第239页。 (41)王安石:《性命论》,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临川集拾遗》第五集,第284页。 (42)王安石:《推命对》,载《王安石全集》,第238页。 (43)王安石:《推命对》,载《王安石全集》,第238页。 (44)《答何叔京》,载《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45)《性理二》,载《朱子语类》卷五。 (46)《答胡伯逢四》,载《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 (47)关于王安石人性性质的主张,学界聚讼不已。贺麟先生在《王安石哲学思想》中所做的解释可供参考(《贺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页)。 (48)王阳明:《传习录中》。 (49)王阳明:《传习录上》。 (50)王安石:《答曾子固书》,载《临川先生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78~779页。 (51)王安石:《庄周下》,载《王安石全集》,第233页。 (52)王安石:《书洪范传后》,载《王安石全集》,第301页。 (53)王安石:《虔州学记》,载《王安石全集》,第304页。 (54)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4页。标签:王安石论文; 孟子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人性论论文; 人性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宋朝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荀子论文; 天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