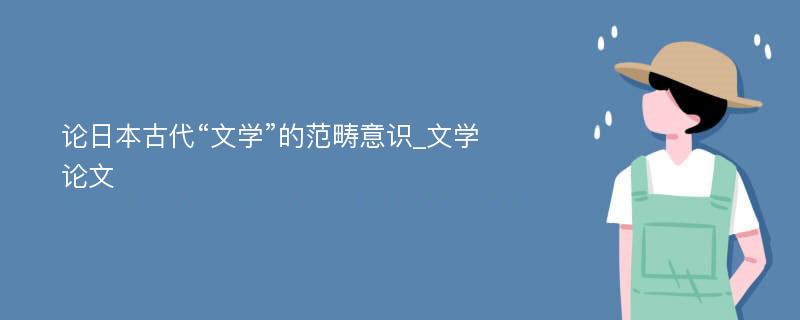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范畴论文,试论论文,古代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7)02-0208-03
时至今日,用汉字表记的“文学”概念通解为“语言艺术”,与西方通用的“Literature”相对应。但是,在“Literature”被翻译为“文学”之前,日本对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如何,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日本上代文学”、“平安文学”和“女流文学”等是共时性的,还是历时性的,它与中国的“文学”关系如何,也就是说,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是何时产生的,关于这些问题,日本学界关注已久,铃木贞美的《日本的“文学”概念》[1]92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加以梳理,以期引起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注意。
一、上代与中古的“文学”概念
一般认为,汉籍在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由百济博士王仁传入日本。其后,王仁等渡来人的子孙大多成为博士或宫廷的史官;雄略天皇重用渡来人,强化政权;继体天皇七年(513年)和十年(516年)则两次从百济引进五经博士,教授汉籍。推古朝(592-628年)以后,汉学进一步发达,儒教和佛教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种大规模引进外来文化的思潮中,儒学的文献经典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后,圣德太子积极引进佛教,并使其成为政治的中心,与儒教抗衡。在引进汉籍的过程中,“文学”这一概念也逐渐传到了日本。
在现存的日本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文学”一词的是《养老令》(718年),是对中国汉代官职“文学”的模仿,系指讲解经书的官员。相对而言,在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中则有“旋文学之士……”[2],系指一般的学问、尤其是儒学,直接秉承了我国六朝时期的一般学问和“文章”之学的观念。也就是说,在此时日本的“文学”概念中,《论语·先进》和《魏书·郑义传》中的“文学博士”、《汉书·先帝记》中的“文献经典”以及《晋书·官职名》中的“官名”之义,还是首当其冲的。譬如,《论语》中仅出现一次的“文学”,则与“德行”、“言语”和“政事”并举,文学的“文章博学”之义出于宋代的注释。因此,人们往往认为,此期的“文学”系指“学问,尤其是关于文献的学问”[3]。从汉代起教授帝王经书的职官称“文学”,各州府从事经书教育的教授也被称为“文学”。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历代职官表》援引《汉书·西域传》“诸大夫郎为文学者”,并附唐代颜师古注“谓为文学,言学经书之人”。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意指学习古籍,尤其指学习儒学的经书。
日本在接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概念的基础上,也有一些不同于中国的特色。这就是佛教的影响更大,同时亦不难发现神道思想的印迹。汉诗集《怀风藻》的64个诗人中有18人的名字出现在其后不久编集的《万叶集》中,这表明他们当时是既赋汉诗又咏和歌的。显然当时并没有在今天的“文学”概念的范畴上提出“诗歌”的概念。也就是说,汉诗与和歌不在“文学”之内。与“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梁书·刘勰本传》)的“文学”相比,显然,日本上古时代还缺少“诗”、“文”的范畴意识。
在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下,中古时代日本汉诗文的创作空前兴旺,先后出现了《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7年)和《经国集》(827年)等。此期经学的地位有所下降,学习《汉书》、《史记》、《三国志》以及《文选》的“纪传道”比较流行。“纪传道”俗称“文章道”,教授则为“纪传博士”或“文章博士”,学生为“纪传生”或“文章生”。在空海(774-835年)的《三教指归》和《遍照发挥性灵集》中,“文学”只被用在意指给亲王侍讲的官职名[4]。而在他的《文镜秘府论》中则有“文章”论,两卷专论“文笔十病得失”,显然深受六朝以降“文体论”的影响,也说明作为文章之学的“文学”概念已经传入了日本。
《古今和歌集》逐渐强化了“诗歌”的范畴意识。在纪淑望用汉文写的“真名序”中,宣称“不假外力,即可动天地、感鬼神、和夫妇、慰武士者,和歌也。”[5]可见,他模仿《毛诗大序》,原封不动地把中国诗歌的理想“拿到”日本的和歌上了。也就是说,此期还没有出现只有和歌才是日本的“文学”的想法,汉诗与和歌是属于同一范畴的。
在《枕草子》和《源氏物语》中都提到过“文”、“文集”等概念,而没有出现文学的概念。譬如,《枕草子》第197段:“文为文集、文选、新赋、史记、五帝本纪。”[6]
可见,在上代和中古时期,作为“文章之学”或“经史之学”的“文学”概念已经传入日本,但是并没有在意指汉诗、和歌和物语等的意义上流通开来。
二、中世与近世的“文学”概念
中世镰仓时期的《古今著闻集》(1254年前后)卷四题为“文学”,第一段从“伏羲造字”的中国神话传说开始,再到孔子弘扬“仁义礼智信”,从而使“文学”之道不断兴旺。“序”援引藤原孝范编《明文抄》(1232年前后)的“弘风导俗,莫由文尚,敷教训民,莫由学善”,强调“文”、“学”的作用,反映了平安时期“文学”作为“经史”之学和“文章”之学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古今著闻记》百科全书式的编辑体例中,“文学”位于“神祇”、“释教”、“政道忠臣”和“公事”之后,其后接“和歌”、“管弦歌舞”、“能书”和“术道”等,即标志着“文学”在平安朝后期的地位[1]109。
在《神皇正统记》下卷《后宇多天皇》中,则有“文学之方,于后三条之后,使闻如此之才”[7],亦非今日之“文学”。日本中世歌论和艺能论盛行,但并没有被纳入“文学”范畴。世阿弥(1383-1443年)的谣曲《老松》中出现了“文学”:“唐帝之时盛行文学,花增颜色味道超常。废文学则无味无色。”[8]这里的“文学”也只是在强烈意识到中国传统的基础上,专指“汉诗文”的。
由葡萄牙传教士编译的《日葡辞书》(1603年)中给文学(Bungaku)下的定义为“Fumi Manabu(文学ぷ)書物ゃ書状の立派な文体なざを学習すゐてと、またはその学問。(学文,学习书籍和文书的优秀文体,或指这方面的学问)。”可见,虽然传教士具有英语“Literature”的背景,但是亦没能完全摆脱“文章之学”的束缚。
日本近世独尊儒学,在藩校讲授儒学的教授被称为“文学”,不仅朱子学,一般儒学和学习汉诗的也被称为“文学”。当然,在儒学者的著述中对“文学”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伊藤仁斋《童子问》用为“依靠文献”的学问;石田梅岩《都鄙问答》用为“文章博学”之意;增穗残口《艳道通鉴》(1716年)的《神祇之恋·八》的“一生文学して志を遂げず(一生从事文学未遂志)”[9]的“文学”也是指儒学。可见,直至此期作为“文章之学”或“经史之学”的“文学”概念依然根深蒂固,还没有产生把“和歌”称为“文学”的范畴意识。
江村北海等编著的《日本诗史》(1771年)中,不时可见“文学”一词,如“文学衰退”、“帝业盛偕文学”都是“儒学”之意。但是当他用“经学文艺”、“儒术文艺”代替“文学”[10]54时,“文”与“学”则被对举,即变成了“经学=文艺”或“儒术=文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京都、镰仓僧侣为中心的汉诗文创作才被称为“五山文学”。五山僧侣在实践中把儒学和汉诗文区分开来,是其后江村北海“文”与“学”并举的重要依据。《孜孜斋诗话》(1805年)引用江村北海“時に干戈戦争の余に属し、文教地を掃ふ。況ゃ郷僻遠に処して、人、文学を知らず,(时属干戈战争之余,文教扫地。何况乡处僻远,人不知文学)。”[10]在这里,“文”与“教”、“文”与“学”并举。奉德川光圀(1628-1700年)之命于1657年开始编修的《大日本史》(1870年完成)中的“文学传”也具有“儒学”和“诗文”的双层含义。因此,18世纪江村北海笔下的“文学”即与今天通用的“文学”概念相同,这标志着那个时代“文学”范畴意识已经开始觉醒。
三、“文学”范畴意识的觉醒
近世以后,一部分以文学语言艺术为业的学人,逐步产生了文学类别的意识。津阪东阳(1767-1825年)在《夜航余话》中明确指出:和歌、俳谐虽然与汉诗在表现方式等方面有所差别,但是它们没有尊卑之分,同属于“诗歌”范畴。他对松尾芭蕉(1644-1694年)把汉诗唱和的方法运用于连歌创作大加赞赏[10]139与谢芜村(1716-1783年)也主张“俳谐尚用俗语而脱俗”,在方法上与诗相通[11]。芜村试图在“用俗”与“脱俗”的层面上,把作为“文学”传统的“雅”和“俗”对立秩序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在儒生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学”就是经学与诗学相结合的产物,传承于中国的雅的世界才是“文学”,与此相对,日本的和歌和平安时代的物语都是“俗”的游戏世界。
德川时代小说范畴意识也有所萌发。曲亭马琴(1767-1848年)在《近世物之本江户作者部类》中强调:“赤本、洒落本、中本、读本虽各有所差,然戏墨则一。”这就是比较鲜明的“部类”——戏作的范畴意识。其后,马琴亦有《和汉小说目录》与《近来戏作者变态沿革》等著述。《目录》的“和”部为《读本类书名抄》,“汉”部为《唐山稗史类书名抄》;“变态沿革”也就是“演变史”。可见,在马琴看来,小说等于读本类(日本)、稗史类(中国)。小说这一概念已经开始流通了[10]246。并且,马琴还有意识地把“物之本”的范畴意识延伸到对历史传统的表述:“所谓近世物之本,系物语草纸类(读本),应称之为物语之本。”[10]289他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读本的源头在于平安时代的物语。
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民族主义思想有所萌发,知识界试图摆脱儒学的束缚,在神道教的思想中寻找与儒、佛不同的东西。在这种大的思潮中,研究日本古典也蔚然成风。契冲(1640-1701年)的《万叶集》和《古今集》研究、贺茂真渊(1697-1769年)的《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研究都成就斐然,时称“国学”。本居宣长(1730-1801年)在研究《源氏物语》的《紫文要领》中旗帜鲜明地向儒佛发难:“儒有儒立足之本意,佛有佛立足之本意,物语有物语立足之本意。以此强证之于彼,必为附会之说。以和歌、物语立足之本意说是,才是正说。”[12]也就是说,和歌、物语的“本意”是“合人情之真情”,这与儒教的“灭人欲、存天理”是格格不入的;儒佛说教的是道德,和歌、物语所表达的是“文学”。可见,虽然此期“文学”概念还没有近代语言艺术的意味,但是本居宣长的思维方式已经比此前有了极大的飞跃,能够自觉地把“和歌”、“物语”等文学的“本意”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区分开来,实在是“文学”的一大进步,也标志着日本“文学”真正开始觉醒了。
总之,日本古代没有产生近代欧美文学意义上的“文学”的范畴意识。在西方的“Literature”传入日本之前,创作与读书阶层长期拘泥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以一般学问、尤其是儒学以及“文章”之学为“文学”的全部,而忽视了对真正的“文学”范畴的研究,从而长期把和歌、俳谐(俳句)、净琉璃、歌舞伎和戏作等排除在“文学”之外。但是,近世以后,随着文学者文学范畴意识的不断强化,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江村北海《日本诗史》把“文”“学”对举,发现了“五山文学”的历史传承;从芭蕉的连歌,人们发现了俳谐与汉诗可以并驾齐驱的关键之所在;从对戏作的综合认识,马琴发现了小说这一文学类别的基本构成;本居宣长自觉地把“和歌”、“物语”与儒佛的道德区分开来,标志着日本“文学”的一大进步。这些无疑都为日本近代接受西方的“Literature”概念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收稿日期]2006-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