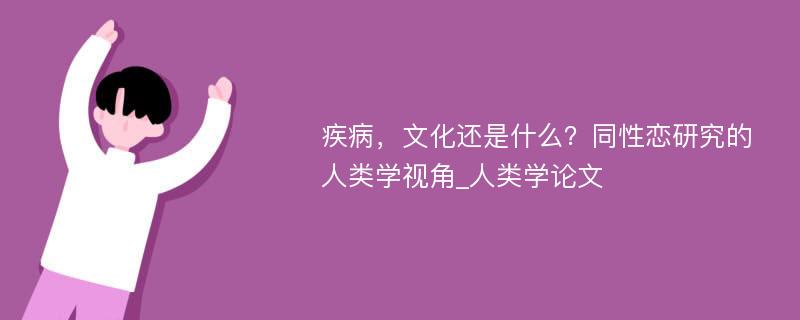
疾病、文化抑或其他?——同性恋研究的人类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同性恋论文,视角论文,疾病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2-0086-10
长期以来,“同性恋”在人类学史上是一个“禁忌”的研究命题,鲜有人类学家有勇气研究被高度污名化的同性恋行为。本文试图对人类学的同性恋研究进行理论回顾,从历时角度梳理主导范式的转换轨迹,从共时角度结合医学、性学、精神病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视角透视其他学科对于人类学同性恋研究的影响。
一、20世纪上半叶:游离于医学科学的边缘
20世纪前半叶是讲求本质主义的科学时代。“本质”问题是西方哲学的特有问题,它是一个重要的本体论问题。本质主义源自柏拉图,他认为本质就是永恒不变的形式,我们只能通过心灵(Minds)却不能通过感官去理解它们①。这就意味着本质是超越物质表象的终极所在,具有超越性、绝对性、普世性和确定性。这也是现代科学观的主导话语并在1960年代前占据主导地位。本质主义认为性意识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外在于文化与社会,来自于固有的、天生的趋力,而这本质与趋力指导着我们对性的认同②。
(一)本质主义对同性恋的观察
医学科学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有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1903-1925年,在这一阶段,性(Sexuality)不是完全独立的领域,而是和性别(Gender)一起受到控制,医生更感兴趣的是偏离的性别行为(Gender Behavior)③。第二次浪潮是在1934-1942年,医学科学占据了什么是道德的性、什么是偏差的性的发言权,性开始与生物学同义。医生成为决定哪些行为是该禁止的、哪些是被允许的权威。针对同性性行为,“逆转”(Inversion)的概念被发明出来,医生通过一系列测量,不仅可以诊断性逆转的症状,而且判定何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④。医学科学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由性别偏离和缺陷引起的病态,并利用其合法性介入了社会控制的领域,作为统治话语一直活跃到1950年代。
同样讲求科学性的是性学研究。在诸多性学家断定性逆转究竟是先天遗传或后天获得,是病态、退化还是变态的争论中,先天之说和变态之说逐渐占优势⑤。1940年代,性学家金赛里程碑式的同性恋和异性恋体验的从0-6的光谱式分析⑥,打破了以往科学家生吞活剥、非此即彼的性分类系统。金赛质疑以往调研的缜密性,并且反对没有经过充分的设计(样本代表性、调查技术等)和论证(缺乏男女比较研究、忽略教育程度不同等)就进行解释和得出一般结论的做法。金赛虽然看到了同性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特别文化的习俗影响所产生的行为,但他研究的总体观点仍旧是寻求“性科学”的方法去证明同性恋现象的生物学基础。
“性倒错”的说法更是全盘纳入精神病的范围中。最早的评估认为,性倒错是一种先天性神经退化的标志。这与一个事实相符,即医生们最初是在那些患有或者似乎患有神经症的人身上发现了性倒错⑦。由此吊诡的一个逻辑是,这些本应寻求解释的行为却被片面“诊断”为神经退化的精神病患者,将同性恋“治疗”成为异性恋成为目标。同时,医学和性学联手精神病学对同性恋行为进行治疗,包括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穆尔的联想治疗法和皈依宗教等手段。
总之,就同性恋这个命题,本质主义强调将生成(Becoming)还原为存在(Being),即根据永恒不变的东西去说明现象之变化的倾向。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基要主义(Foundationism)认识论,科学的支配原则深嵌其内。由此,本质主义将同性恋归结为科学中终可发现的本质,表现之一为不分具体时空和场景地还原为“性逆转”、大脑结构、激素和遗传因素,并据此构成对同性恋的全部“病态”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质主义强调“生物的相同性”,相信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并在认识论上认为其自身是对外在世界的真正的唯一的解释。那么在20世纪上半叶,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是,同性恋的污名从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转移到世俗社会和医学领域。一个耐人寻味的思考是,医学和性学对于“女性化男人”和“男性化女人”的科学诊断固化和束缚了公众对于同性恋的想象。在讲求实证主义的科学时代,在寻求绝对的超越性的科学时代,探寻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学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二)人类学:“犹抱琵琶半遮面”
人类学家Kath Weston在其影响深远的论文《家园人类学中的女/男同性恋研究》(Lesbian/Gay Studies in the House of Anthropology)中,简单梳理了20世纪上半叶有关同性恋的民族志研究,并认为总体意义上的性尤其是同性恋的民族志出版材料乏善可陈。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研究同性恋不符合学界的主流口味从而影响个人发展的因素有关,但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家整体性的社区调研中缺乏这一视角的观察。
伊文思·普理查德(Evans Pritchard)1940年代的研究显示,在阿赞德帝国,家中豢养的男孩越多,越会提升贵族家庭的财富和声望。这类被普理查德界定为Page Boy的男孩扮演了年长男性贵族的听差、知己和性伴的角色。当Page Boy成年后,年长贵族像对自己儿子般赠予他们结婚的聘礼,并用更年轻的男孩替代他们的位置⑧。作为贵族家户成员的阿赞德军人,借由阶层差异延伸出来的亲属系统为自己的同性恋行为找到了路径。“许多阿赞德战士和男孩结婚,并且指挥官不只有一个男妻。当他们结婚时,战士向男孩的父母支付长矛好像迎娶他们的女儿一样。”婚后,战士称男妻的父母为“岳父”“岳母”,同时履行其他亲属义务。战士和男妻互称“My Lover”,男妻随军征战,负责料理战士的生活起居。在男妻成年后,他们也将成为战士并迎娶属于自己的男妻。由此得出,同性恋或为一个男人成年的“过渡仪式”已然成为阿赞德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探讨蕴含于行为背后的权力、阶层、性别、亲属制度的结构性互动将对当时认为同性恋“变态”、“精神病”的学界大有意义。颇为遗憾的是,碍于医学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对同性恋达成共识的口诛笔伐,普理查德的相关研究在1970年代才敢于和得以发表⑨。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列维·斯特劳斯身上。他对祖尼印第安人进行结构分析时,忽略了Ko’lhamana的描述。在祖尼印第安文化中,Ko’lhamana指涉第三性人物(Third-gender)或双神人物(Two-spirit)。它在祖尼起源的神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借由它男性和女性、农业和狩猎在文化上得以区别。并且在复杂的庆典中,Ko’lhamana作为调解人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有这些,列维·斯特劳斯只字不提。在他眼中,Ko’lhamana仅仅被指涉成双性存在(Bisexual Being),也仅仅出现在祖尼神话中众多调解人的图表中⑩。在这里,Ko’lhamana被简化为一个名词,而其社会角色、生活方式,尤其是和北美印第安社会一脉相承的Berdache(11)传统一概隐而不论,这实质也体现出结构主义在同性恋问题上暗含的本质主义倾向,即以身份为中心的交换结构属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异性恋范畴,而同性恋却连用于交换的身份都不具备。
玛格丽特·米德1930年代对美洲游牧印第安人的性别和气质进行研究,她认为不顺应社会环境的个案类型是性别角色离轨的表现,这种离轨不是因先天缺陷就是因早期发育过程的偶然事故所致(12)。米德在承认同性恋行为有先天因素之外,更倾向于所处社会按照性别二分法的严格标准对于人格和气质的强行模塑(这样,同性恋就找不到认同),这也从文化视角为当时流行的“潜在同性恋”倾向提供了解释。笔者认为,所谓“潜在同性恋”的情境实质由他人的同质性促成,即社会成员趋同于所处社会认定的性别特征并在人际互动中有意强化,从而导致与公认性别特征不太相符的个体气质立刻凸现出来。由此,性别特征的同质性得到进一步认同和加强,而异质性的个体则对文化规定的自身气质产生怀疑和困惑以致丧失性别归属感,并对那些遵守性别规范的人产生影响。不可否认,米德顺应时代潮流,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她同时提出“病因”的文化解释——尤其是意识形态化的性别规范决定人格特征的文化——形塑同性恋的可能性,这在当时已跳出窠臼,虽是寥寥几笔,但从侧面起到为同性恋正名的作用。
客观地说,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对于同性恋研究的态度和经验性产出自相矛盾。这体现在:一方面人类学随波逐流,顺应学界趋势认为只有异性恋才符合社会期待的性规范,并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来看待(还谈不上研究)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这与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意义或价值形成对比。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显示,很多部落社会都接受同性恋,并将其作为生命历程中的必经阶段来认同。但研究者却因为“合法性”的问题,给这一鲜活的社会现象罩上了面纱。这证实了人类学在那个年代的同性恋研究领域中的困境,一种不能正视,继而退缩,从而被动,最终止步不前的困境。可以说,同性恋现象早已有之,诸种文化中的丰富记载远远早于医学科学给予它的“诊断”,但是自视为科学的人类学却把自身多向度的研究潜力抹杀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条退路中模棱两可的进路:一条是故步自封,对广泛收集的经验材料做蜻蜓点水式地“体验”,没有系统分析性行为发生的文化情境,而是更多地局限于个体层次,把同性性行为的发生归结为个人不能适应社会性别角色的期待。另一条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模型。分析人类学数据的理论模型直接来源于西方关于性的心理学概念,并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视同性恋为“变态”的模型对异文化中的同性性行为进行评估(13)。尤值一提的是,克鲁伯使用“同性恋的小生境”(Homosexual Niche)理论来解释北美印第安社会中的Berdache现象。他认为同性恋的产生是先天的、自然的,是超越历史和文化的大多数社会的共性,这种那个时代人类学家得出的普遍结论恰恰应和了前面提到的本质主义的科学论调。
二、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历史—文化建构成为关键词
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学会以邮寄投票的方式承认同性恋研究的合法性以及迅速启动相关研究和发展项目的重要性。虽然学科内部的反思性自我批评使人类学的视域不断扩大,然而对同性恋研究领域的职业抗拒仍旧持续着。
(一)文化的情境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同性恋的民族志研究略有增长,尤值一提的是,人类学家Herdt以及他的团队在同一个文化区——美拉尼西亚对制度化的同性恋给予细致而深入的关注。1986年,《人类学与同性恋行为》(Anthropology and Homosexual Behavior)出版,这是第一本集合了不同文化领域中同性恋经验研究的人类学论文集,直至今日仍是最有影响的介绍多种社会同性恋形态的研究。书中集合了巴西、墨西哥、印度、莱索托等非西方社会的同性恋民族志调查成果,检视了同性恋行为如何被非西方部落社会的文化所形塑,显示出这一群体如何被整合至社会系统并得到接受,从而为同性恋和同性恋研究的合法性提供经验佐证。
在综合大量民族志研究资料的基础上,Barry Adam认为同性恋是年龄、社会性别和亲属制度特殊结合的产物(14)。他归纳出两种同性恋模式:一种是注重男性成年后异性妻子和同性恋人共存的古代模式(Ancient Model)(15);另一种是注重男性自身再生产的美拉尼西亚模式(Melanesian Model)。古代模式中的性仅仅是权力的表征,而无所谓对象的性别和身份。有意思的是,发生同性恋行为的双方被界定为“接受者”和“提供者”,年龄因素介入表述,很多民族志材料发现年老的“提供者”寻找年轻的“接受者”满足另类志趣,并通过物质性补偿获得“接受者”的家庭和社会的认可。在美拉尼西亚模型中,与女性的接触被视为对男性气质的威胁和污染,因此需要举行仪式来使男性群体确认和重新生产男性自身。在这里,同性恋行为被仪式化了,并通过“精子”的象征意义完成男性对于自身和所属群体的认同。在《成长的甘薯和男人:一个Kimam男性仪式化同性恋行为的解释》中,J.Patrick Gray对于美拉尼西亚Kimam社会中甘薯神话和巫术的细腻描述令人沉醉。甘薯神话源于一个妇女生育了一个单臂单腿的男孩,这个男孩请求直立埋葬。若干年后,当坟墓被打开时,人们发现男孩已经变成了一个甘薯(16)。甘薯被赋予了与男性相关的成长、死亡、气质等多重意义和强大力量,并视女性为禁忌包括在甘薯仪式前避免与女性性交。男性的间接(通过在身体上涂抹年长男子的精子)和直接的性交被认为是男性力量的传递,促成男孩向男人的地位转变,并帮助维护所属Paburu的财富。此外,从莱索托的“母子”女性友谊——替代或伴随异性婚姻的女性支持网络,到尼加拉瓜的Machistas——发生男男性行为但不认同自己是同性恋身份,到不同时代巴西的性分类系统的人类学解释,这些研究不断向我们揭示同性恋的跨文化多样性。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同性恋的民族志研究已经脱离了病理学的轨道,转而重点阐述特定地理区域的特定文化如何组织和模塑同性恋行为。美拉尼西亚社会和北美印第安社会成为当时方兴未艾的同性恋民族志研究的两个经典案例。同时,其他地理区域的民族志材料的收集和描述力图拓展西方社会以外的视野,增强了文化地理学的含义。不同社会的民族志材料呈现同性恋多样性的同时也提出了疑问:生物学意义上的二元生理性别能否解释性别多元存在的现象?这实际牵引出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在西方世界的生理性别认识论发明和散播之前,关于性与性别的多线知识是如何在广阔的非西方社会生产出来的?
纵观这个时代的研究,文化模式成为关键词,关于性别角色、亲属制度和劳动力分工的意识形态在同性恋行为的建构中非常重要。在这里,行为成为一个环程的入点,借由它探寻与其相联的意义的不同领域。由此,我们看到上述研究所隐含的古代模型中“同性恋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美拉尼西亚模型中“同性恋作为群体分类的标准”、“同性恋作为成年礼”的意义。民族志文本中描述的同性恋行为并未作为性取向,甚至是性身份得到行为发生者的认同,这种行为只在人生某个特定阶段(如婚前)为了某种目的(如增强男性气质)而发生,即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发生。同时,同性恋行为又是一个终点。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对于社会的作用又在哪里?在某些社会(尤其是古代模型),我们看到性行为是变化着的,采取同性/异性性行为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团结和凝聚力的需要而随时调整,同性恋的存在不能动摇其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隐约让我们看到了功能主义色彩。
这个阶段,人类学家在为绘制“同性恋民族志地图”而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着迷于对各个区域的同性恋进行分类:如年龄—构架的、跨性别的、平等主义的等类型。他们还研究与其相关的领域:A.性建构的经济情境;B.亲属制度和家庭系统;C.性规则和社群的界定;D.国家和社会系统等。大部分研究都围绕社会和文化因素对性的形塑和建构,强调抽象的模式总结而非探索文化内部同性恋存在的多样性。
(二)社会建构论
宽泛地说,人类学关注文化的影响因素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这一范式一方面强调在模塑性行为和态度方面的文化和习得的角色,另一方面又看到性是被生物性决定的基本事实。在1970年代中期,一股更强调文化的和非本质主义的话语在人类学的外围——在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中——出现了,并渐渐形成社会建构理论(Social Construction Models)。总体而言,社会建构论强调相同生理行为拥有在不同社会中的重要性和主体意义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性在变迁的文化和历史时空如何被界定和理解。社会建构论的视域很广,包括性行为、性身份、性社群、性选择、性欲望和主体性等,并鼓励不同学科的讨论和参与。社会建构论和人类学的文化影响模式虽互有叠压,但人类学更感兴趣的是探求文化的无限可能。这一对于文化影响因素的强调,都是隐含在对“性”的广泛论述中:如性交、性高潮、前戏;性幻想、性差异、性别关系等(17)。这样的理论和叙述框架又使人类学具有下列颇有意思的特点:性(Sexuality)和性别(Gender)经常合并起来谈;性身份和性主体的意义在宏观领域和宏大叙述中被模糊了;对于文化态度的过于强调忽视了行为本身意义的解读。而这几个总括性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的论述中清晰
1.历史建构。虽然注重跨文化比较,特别是在历史的和政治的情境下,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阶段的人类学仍旧缺乏自己的理论来阐释同性恋行为和实践。人类学家Carole Vance呼吁一个批判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和历史分析,研究性别系统、性和权力之间的关系(18)。福柯在《性史》中,将同性恋行为从古代民法或教会法中的鸡奸到19世纪同性恋成为一个医学科学研究的“物种”(Species)的演变过程展示出来,揭示了社会用来对身体和性发挥作用的权力形式,认为性倒错的增长是一种权力形式干预身体及其快感的真实结果(19)。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克斯Weeks则对附着在同性恋身上的污名进行细致的解构。他的名作《出柜:英国的同性恋政治,从19世纪至今》(Coming out: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揭示了超越医学模型的同性恋自我表达,更重要的是“自我界定”的政治团体和关键个人的发展(20)。
由此看到,对权力也好,对社会也好,对文化也好,“主体性”的回应是福柯和威克斯共同强调的主题,而这正是人类学所缺乏的。人类学家往往从“客位”视角进行冷静、有效的观察和记录,而缺少文化持有者“主位”的声音。具体来说,这个阶段的研究注重报道人的社会角色,多与信仰、仪式和社会组织相联并探讨个人对社会整体的作用,而忽视其脱离异性恋框架的束缚,作为“主体”的性别、身份、情感、欲望和行为的批判分析和阐释。这个阶段的人类学虽已认识到文化情境对于同性性行为模塑的重要性,但仍旧停留在文化相对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论调上,这也是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尽管研究积累了足够支持详尽的类型学材料,但是很多地区的跨性别和同性恋的知识仍旧是碎片化的,对于性、性别的结合点及对意识形态主导的性别结构的回应并未做深入探索。
人类学“性”研究的新思考随之呈现:性的范式是什么?我们关于“自然的”性的设想是什么?想象和行动、个人和社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重新检视主流的性理论,必须对这些领域(性研究的社会历史、性驱动和能量、性边缘群体的经验研究、异性恋的社会建构)进行深入分析。这实则提出人类学新的理论追求,并期待跨学科合作。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几乎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提到福柯的重要贡献,福柯开创性的研究帮助学者发展理论框架,这不免折射出当时人类学学科认识论的转向。人类学的研究项目开始受到其他学科,诸如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的影响并逐渐加强跨学科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一批民族志作品已经有意识地将历史研究编织进他们的文本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Evelyn Blackwood的《印度尼西亚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的性犯罪》、Richard Parker的《赤道下:巴西的欲望、男同性恋和新出现的同性恋社群的文化》等。
但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学的学科革新者忽视了女性主义关于性别(Gender)和性(Sex)的积极探索。作为回应,Behar和Gordon于1995年编撰了一本《女性写文化》质问人类学文化批评中的作者政治(21)。一系列分支人类学的发展和反思性民族志作品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
2.性别人类学。从女性人类学向性别人类学的转向使人类学从最初的数据收集逐步转向理论化,并且从只关注女性转到研究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和男—女关系等领域(22)。尤为重要的是,女性从以前民族志材料中的否定角色转变成发声的主体,并且开始质疑性别研究的基础领域。
性别人类学是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它对性别的认识也是不断嬗递的。从早期的女性人类学强烈要求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区分开来,反对将性别简化为可见的外表和身体器官,而是将性别嵌入至特殊文化情境的意义系统中来理解;到1980年代提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均是在一套社会意义和实践中被建构的,性交和生殖不单单是生理过程,它们也是社会活动(23)。在此基础上,Errington在1990年代对生理性别和生物差异的社会建构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述。她尽力对“性别”(“Sex”)、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进行区分以达到其对性别的透彻理解和话语建构。相较而言,生理性别(Sex)指的是人类身体的二元生理特征,社会性别(Gender)指的是生理性别的不同社会文化建构。“性别”(“Sex”)不仅包括生殖器功能、生殖过程的生物学原理,又涵盖作为符号系统的生殖系统的复杂信仰。Errington认为,生理性别(Sex)是西方生物化学话语的产物,在世界大多数文化中,在本土或地方知识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没有生理性别(Sex),只有“性别”(“Sex”)(24)。笔者认为,“性别”(“Sex”)实质是人类学理论的一种分析策略,它建立在人类生殖的基础上,旨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理解和划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综合差别。Rosalind C.Morris则对社会性别(Gender)的研究更进一步,认为社会性别不是一个固定关系的结构,而是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主体建构的性身份一旦涉及最终归结到哪个范畴的性质堡垒,对待意识形态的批判就不具有免疫力了(25)。也就是说,性别人类学脱离执拗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极对立,开始关注规范的性/性别(Sex/Gender)系统和同一系统中实际存在的性的模糊、多元之间的冲突。通过非西方社会的“制度化的易装”民族志实践(26),性别人类学表达对性权力话语的抗拒,反对将性别判断的标准简化为可见的器官,从而忽略性存在的多样化状态。
性别人类学的发展颠覆了我们对于性别的假想。通过对女性主义的思考借鉴和前者身体力行地参与,人类学终于从想当然的性别二分法的窠臼中跃然而出;提请注意的是,社会性别创造出来是为了驳斥政治和权力场域中生理性别决定一切的合法性,但并不意味着这截然不同的两种范式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性别人类学不仅解构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固定化的主流模式,而且致力进行多元性知识的再生产。这在完成学科内在批评和反思的同时,无疑进行了一次华丽的转身,虽然有些实践矫枉过正,但其提供了一个未来的可预见的发展方向。这样的转变无疑给同性恋研究提供了一个便捷的语境,对性的多样化理解,尤其是对所谓正统的性别分类所不愿也不能解释的性的“模糊”状态,如易装实践、双性恋等提供了一个理解和继续研究的平台。同时,不断涌现的文化批判思潮为同性恋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如从社会建构论发展出来的酷儿理论将我们带入同性恋研究的另一个时代。
当同性恋者庆祝由于民权运动而带来的新身份和新自由的时候,当研究者们为研究的新转向和新成果产生喜悦的时候,1980年代初艾滋病的骤至为之前的努力和成就带来了阴霾,这些研究在“世纪瘟疫”艾滋病中得到了改变和考验。同时,同性恋研究又扩大了阵营,医学人类学家的参与和批判人类学的转向又为我们开辟了研究的新领域。
(三)艾滋病的侵袭和批判人类学的转向
在美国,艾滋病最初被命名为“男同性恋者免疫缺陷症”。其后,在艾滋病流行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艾滋病被视为“男同性恋者的瘟疫(Gay Plague)”。艾滋病流行初期,学界的专题研究更多地关注“出柜”(公开性取向)的男同性恋的疾病表述。在美国社会以外,艾滋病的流行已经超越了地域的想象。很多跨文化的调研成果一一登场。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艾滋病的不可治愈性和慢性传染病的特征加强了性与疾病的联系,从而使生物医学范式得以复活。生物医学和流行病学成为艾滋病防治话语的主导范式,其更重视艾滋病的易感和风险行为,缺乏对性尤其是边缘的性的亚文化的敏感性。然而,当行为干预在更广泛和多样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展开时,其“一刀切”式干预策略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质疑。这无形之间造成了一种困境,社会科学尤其是关注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学的参与成为不时之需。
人类学的参与也颇有趣味。从只关注个体人群中同HIV传播有关的性行为的经验事实,到1980年代末,人类学家提出了文化在塑造与HIV传播和预防相关的性行为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对行为本身的关注转向行为发生的文化情境以及组织这些行为的文化象征、意义和规则上(27)。这实质是对前面提到的社会建构论也好,文化影响模式也好的重复和回应,并无理论新意;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应用,即将更大规模的人类学家群体(如医学人类学)卷入到设计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地方预防和干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以社区为基础,具有文化敏感并且以适应性转变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为目的,致力于通过最终能够提升安全性行为的方式来重建集体意义。
然而出现的新问题是,仅仅从人的个性、由文化决定的动机和理解力去解释与健康相关的问题是不充分的,在很大程度上结构性的,如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显然也会建构性经历(因此也就包含性行为改变的可能)。特别是,相关研究已经强调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决定流行的状态和传播扩散中的核心角色,并且强调这些因素对有效的艾滋病干预项目遇到复杂的障碍负有责任。因此,对于结构因素中政治的和经济的分析的新关注——包括增加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和促进或阻碍减低风险的结构因素——成为现有人类学回应艾滋病流行的中心,这也是批判人类学的主旨所在,即在人类学的框架内,用政治经济的批判眼光解决问题。
由此,性别权力不平等、异性恋至上主义、跨性别、男男性工作者、少数民族群体中的男同性恋、被迫或诱使发生男男性关系的青少年男性、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以及男男性行为的污名与歧视等有关的脆弱因素与其他形式的结构性暴力(如贫穷、种族主义等)相互作用,构成了批判人类学在同性恋群体中解释和应用的场域。笔者感兴趣的是,在欧美国家将大量防治经费投入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东欧和中亚等艾滋病流行状况严重的地区和国家时,是否带来了控制疾病的“副产品”?即同性恋群体借由艾滋病防治平台争取权益,从而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参与结构性对话,并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关系。这里面涉及的全球化背景下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结构对疾病发生作用又反作用于结构的批判性产出,非西方的民族志对西方话语做何回应,均是值得探讨的发展方向。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酷儿政治及未来发展走向
从19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者开始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由此发展出来的酷儿理论在1990年代引起关注。“酷儿理论”(Queer)这一概念的发明权属于著名女权主义者Teresa de Lauretis,她创造这个词的本意是希望用它来取代无差别的单一名词——同性恋,以便将性的多重性放在它们各自的历史、社会的语境中去理解。在酷儿之前出现的术语Gay,实质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运动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革命”和政治色彩。酷儿的提出已经超越同性恋身份政治,它反对正统观念,质疑社会的“常态”,力图以一种无偏见的姿态去挑战现存的性规范体制。酷儿理论有四方面主要内容:挑战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男性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传统同性恋文化;联合边缘群体采取共同行动(28)。
(一)性别即表演
对性欲和性别挑战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巴特勒(Judith Butler)。这位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其代表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中,解构了女性主义理论(包括性别人类学)里存在的异性恋假设,对规范性欲对于少数所谓非规范的性别实践及其合法性的控制进行了抵抗。与其他女性主义学者不同,巴特勒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和对立不以为然,在她看来生理性别的二元性被建构成一个前话语的、先于文化的领域无非是为了维护异性恋制度的权力统治。她认为,“从定义上来看,生理性别一直显现的就是社会性别”(29)。同时,包括通过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欲等稳定化的概念确立的“身份”也是强制性异性恋通过文法操演和身体镌刻实践的结果。恰恰在这种单义的、一致的以及连续的“合法”话语里,那些不入流的性存在状态(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等)成为了制度的“幽灵”(spectres,巴特勒语)。尽管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幽灵”的存在令异性恋性别范畴的语言和逻辑捉襟见肘,但它被文化设定的性欲秩序和性别等级原则强令禁止,并通过律法的排除和控制来实现并固化异性恋霸权的想象。
巴特勒又进一步提出了“性别表演”理论。与福柯一样,巴特勒认为身体可以理解成一个媒介,更确切地说是一页白纸,这样它可以被历史和文化任意书写和铭刻,可以具有内部和外部的边界。身体成为可见的能指,法律、性别、灵魂都可通过在身体表面的在场或不在场的运作形成所指并反向生产和建构身体。这样,生产出来的行动、姿态与欲望实践大都可以解释为表演性的,其基点在于它们原本意图表达的本质或身份都是虚构,是通过身体符号以及其他话语手段制造并维系的。也就是说,性别及其表达的身份具有历史偶然性,不是自然化的个人本质属性,而是经由重复表演的行为而达成的意义建构。在此基础上,其一,巴特勒不以为然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均不是真实的存在(其真实由表演创造),它们作为异性恋管控实践的有力工具,只是一种社会暂时状态和一种“自然化”行为的幻觉效果;其二,“自然化”了的异性恋以及其他性少数人群(如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也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这实质是基础性的第一条思路的一个解释性出口。它们将性建立在一个不断改变的表演的系列之上,就是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异性恋需要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对立,而表演理论通过易装实践将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间性化了、模糊化了;从而凸显异性恋话语体系中“标准”和“身份”的脆弱。
(二)酷儿理论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酷儿理论对21世纪人类学的发展影响颇大。根据人类学家Boellstorff的研究,人类学的性研究现在通常是以酷儿政治的形式出现(30)。新世纪的同性恋研究已经超越1990年代民族志绘图式的研究视野,而是强调新方法和新理论。酷儿政治带着批判视角进入人类学的视野,提供重要认识并在以下方面产生影响:(1)重新思考社会性别图式,颠覆社会性别作为自然化的异性恋的评估标准。打破社会性别的两分体系,将社会性别视为多元的、流变的存在。避免将酷儿做性别化和性身份的定型和分类,它标识的是一种新型的生活状态。(2)酷儿的内涵包括男同性恋(Gay)、女同性恋(Lesbian)、双性恋(Bisexual)、跨性别(Transgender)定义的身体、情欲的实践和欲望并超越它们。酷儿人类学在不断扩大视域范围,将起初“不合法”的性(如恋物、虐恋等)整合至酷儿理论新出现的领域,并且提出使用Intersex代替目前普遍使用的“LGBT”(31)来涵盖多元的性。(3)从文化影响范式过渡到批判人类学范式。从关注特殊历史和文化情境中的同性恋生存状态转至在此基础上,接合到更广阔的论述领域——国家、政治、经济、宗教、移民、种族、殖民主义、贸易等对性的建构,尤其关注种族和阶级对性的建构。(4)改变男同性恋中心主义的支配地位,尤其是隶属于中产阶级的白人男同性恋中心主义的支配地位。酷儿理论尽可能包容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群。(5)在全球化背景下,探求与性相关的欲望、社群和设置的文化观念的地方形塑,尤其是全球化对空间意义的重新分配,地方逐步成为关注的重点所在。
四、总结性讨论
上面我们粗略勾画出人类学同性恋研究的百年理论轨迹,在整体性研究思路下我们看到四个发展阶段:(1)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深受本质主义话语的影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选择退避三舍或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模型来看待这个问题。(2)1960年代发轫的反思性自我批评使得性别尤其是同性恋研究获得了合法性。这个时代同性恋的民族志研究方兴未艾,并脱离病理学轨道,转而重点阐述特定地理区域的特定文化如何组织和模塑同性性行为。(3)1970年代开始,强调文化影响的模式在同性恋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正逢其道的社会建构论有所交叉。然而,人类学界对此问题的惯有冷漠使得文化持有者“主位”的声音隐而不论,这与社会建构论强调的“主体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学提出新的理论追求,期待跨学科合作,比如将历史研究、性别研究、艾滋病防治实践融入至同性恋视野。(4)1990年代,酷儿理论的兴起与人类学的发展有了合作的契机,这样一种交叉趋势在21世纪初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酷儿人类学分支,赋予人类学的同性恋研究更具批判性和颠覆性的研究视域。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今天,致力于同性恋研究的人类学者仍旧痛心地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将付出学术声望和职业限制的严峻代价。在我国,1949年后仍旧采取西方社会已经摒弃的病理学范式,社会和文化给予同性恋的高度污名和歧视使得同性恋群体隐匿于公众视野而难于获得观察。同样,针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也因为研究者的固有偏见或难于深入造成研究的延迟和数量的稀少,这种情况在人类学中尤为凸显。
与屈指可数的人类学作品相比,“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同性恋人群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近些年来,在与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合作实施艾滋病防治项目的过程中,男同性恋群体将防艾工作和人群本身的“赋权”诉求结合在一起,出版了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内部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2005)、《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2006)、《中国“同志”人群生态报告》(2008)等。这些作品多出自作家童戈之手。童戈先生虽不是人类学学者,但他的研究带有民族志的敏感性,并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发出“主位”声音,对社群发展状况进行论述和反思。上述情况实则激发脚步落后的人类学家放弃偏见,与文化持有者构成“互为主体”的格局,与相关学科加强学术交流,并通过“内”“外”合作分享和激发研究的多向性,提供人类学对于性存在多元状态的独到解释、研究探索和理论关怀。
注释:
①卢风:《两种科学观: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哲学动态》2008年第10期。
②[美]Jennifer Harding:《性与身体的结构》,林秀丽译,(中国台湾)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③Karin Martin的研究显示,医学研究女同性恋,是回应和抗拒20世纪初期的女权运动和女性选举权。相较于性行为而言,医生对于“性别”行为的偏离更感兴趣。
④Karin Martin.Gender and Sexuality:Medical Opinion on Homosexuality,1900-1950.Gender & Society.Vol.7,No 2,1993,pp.248-254.
⑤[英]蔼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7-198页。
⑥金赛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不是二元对立的两个系统,两者之间具有关联性。参见Alfred Kinsey,Wardell Pomeroy,and Clyde Martin.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W.B.Saunders Company,1949,pp.638-654.
⑦[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欲三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10页。
⑧Evans-Pritchard.The Azande.Oxford:Clarendon,1971.
⑨Joseph M.Carrier.Foreword.In Evelyn Blackwood.ed.,Anthropology and Homosexual Behavior,New York:Haworth Press,1986.
⑩Will Roscoe.Stranger Graft,Stranger History,Stranger Folks:Cultural Amnesia and the Case for Lesbian and Gay Studi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97,No.3,1995,pp.448-449.
(11)从外表上看非男非女,从某种意义上是两性结合的个体。具体表现为男子的服饰和行动与女性类似,反之亦然。
(12)[美]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宋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294页。
(13)Evelyn Blackwood.Breaking the Mirror:The Construction of Lesbianism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on Homosexuality.In Evelyn Blackwood.ed.,Anthropology and Homosexual Behavior,New York:Haworth Press,1986.
(14)Barry Adam.Age,Structure,and Sexuality:Reflections on the Anthropological Evidence on Homosexual Relations.In Evelyn Blackwood.ed.,Anthropology and Homosexual Behavior,New York:Haworth Press,1986,p.19.
(15)根据作者的描述,古代模型多存在于古代希腊、中国、拜占庭帝国和中古波斯帝国。
(16)J.Patrick Gray.Growing Yams and Men:An Interpretation of Kimam Male Ritualized Homosexual Behavior.In Evelyn Blackwood.ed.,Anthropology and Homosexual Behavior,New York:Haworth Press,1986,p.57.
(17)Carole Vance.Anthropology Rediscovers Sexuality:A Theoretical Comment.Soc.Sci.Med.Vol.33,No.8,1991,pp.878-879.
(18)Carole Vance.Gender Systems,Ideology,and Sex Research: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Feminist Studies.Vol.6,No.1,1980,p.141.
(19)[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5-45页。
(20)Joseph Bristow.Remapping the Sites of Modern Gay History:Legal Reform,Medico-legal Thought,Homosexuality Scandal,Erotic Geography.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46,2007,pp.117.
(21)Ellen Lewin and Willian L.Leap,Out in Theory:The Emergence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y.Urbana:Univ.Ⅲ.Press,2002,p.2.
(22)Kath Weston.Lesbian/Gay Studies in the House of Anthropology.In Annu.Rev.Anthropol.22:346,1993; Anne Siegetsleitner.Gender I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H.Tames Birx.Ed.SAGE Publication,2006,p.1031.
(23)Henrietta Moore.Understanding Sex and Gender.In Tim Ingold.ed.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Routledge,2002,pp.813-830.
(24)S.Errington.Recasting Sex,Gender and Power:A Theoretical and Regional Overview,in J.Atkinson and S.Errington ed.Power and Difference:Gender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5)Rosalind Morris.All Made Up:Performance Theory and the New Anthropology of Sex and Gender.In Annu.Rev.Anthropol.Vo.24,1995,pp.568-569.
(26)如前面提到的北美印第安社会berdache,南印度社会的hijras,泰国社会的kathoey等。
(27)Richard Parker.Sexuality,Culture,and Power in HIV/AIDS Research,In Annu.Rev.Anthropol.Vol.30,2000,pp.163-179.
(28)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9)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Routledge,2006,p.11.
(30)Tom Boellstorff.Queer Studies in the House of Anthropology.In Annu.Rev.Anthropol.No.36,2007,pp.17-35.
(31)L指代Lesbian女同性恋,G指代Gay男同性恋,B指代Bisexual双性恋,T指代Transgender跨性别。也有添加Q指代Queer和I指代Intersex,简称为“LGBTQ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