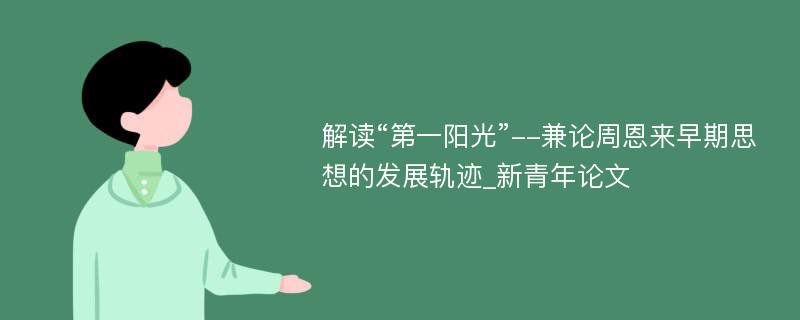
“一线阳光”解读——兼论周恩来早期思想发展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轨迹论文,思想论文,阳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9年4月5日,青年周恩来在日本京都岚山春游,写下的诗中有这样几句:|“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1〕对于这几句诗,研究周恩来的众多著述,都认为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喜悦。胡华、王建初早在80年代初就认为,周恩来“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光明’,‘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内心无限的欢欣和振奋。”〔2〕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也持此观点, 书中说:“就在这种‘潇潇雨,雾蒙浓’的艰难时刻,‘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刻理解它,但已在他面前燃起了新的希望,使他感到格外欣喜——‘真愈觉姣妍’。”〔3〕英国迪克·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中, 也持以上观点,认为“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象是给在他脚下这个新世界的一束光明,以及他发现了他是如何幸福。这是在第一首诗中穿云而出的‘一线阳光’。”〔4〕
本来,从一首诗中推断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就带有想象的因素,而数十种著述竟然都持此观点,我认为就值得研究了。可以说,这些推想的判断都是缺乏根据的。周恩来这首诗流露出来的欢快心情确实能表达出他某种政治思绪。这种思绪,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民主主义。我们通过周恩来写这首诗之前之后一两年的思想轨迹,完全可以得出一个较公允的结论。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我们从众多的材料中,还可以看到日本时期周恩来的其他心理因素。
一、周恩来从多元的庞杂的政治思想净化为一元的民主主义思想
1914年至1919年春,是周恩来在沈阳读书、天津读书、日本留学的三个时期。这几年的中国社会,正是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独裁统治从开始到覆亡、继之军阀混战不休的几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也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发展的时期,各种新思潮像雨后春笋般在中国扎根成长。作为一个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周恩来,一方面忧国忧民、伤时感怀,另一方面又以惊人的毅力吸收着各种思想,以期救国。
周恩来曾有教育救国和储金救国之行动。如1915年6 月他曾在天津救国储金团第二次会上发表过激昂的演说,他的讲话曾被一阵阵掌声所打断,可见他对这些活动的执著。对周恩来影响最深的政治思想,并非以上这些,而是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
青年周恩来的“军国主义”是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陆海军,以此与列强并雄,否则必任人宰割欺凌。1915年,他这一思想就体现得很充分。在《海军说》这一作文中写道:“军盛则国强,军衰则国弱,斯人人所奉为公理,百验不磨者也。”〔5〕他并进一步论证, 要想成为执世界牛耳的国家,保卫和平,非建立一支强劲的海军不可。
他也曾主张贤人政治。青年周恩来在国家多难之际,希望出现一个登高一呼,万民景从的英雄,借以使民族有一中心,使国运强盛起来。1915年冬,周恩来在其作文《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陈述了强邻交逼、国人昏昏的境况,追忆古代刘秀、宋太祖等英雄人物,呼吁,“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6 〕周恩来渴望着大英雄出世的心情,一直萦绕着他那颗救国之心。1916年,江苏淮安中学出版的《中学》刊物,刊有两首咏韩信钓鱼台的诗,前一首叹惜韩信没有功成名退,后一首却唱道:“谁知一掷渔竿后,忽地淮阴有伟人。”周恩来评论道:“其气壮矣,然较之前者,不啻上下床之别。”〔7 〕这里也体察出贤人政治的思想。在他《项羽拿破仑优劣论》的作文中,提出了两种英雄,一种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一种是造出时势的英雄。“二者相侔并举,以演成世界之进化,物质之文明。”〔8 〕他在这里主要赞扬的是造出时势的英雄。他认为,“设世无拿氏,法兰西革命,决不至迁延若是其长。而欧洲各帝国,亦必攘臂以助法王,回(恢)复旧业,使美之共和,不稍存于欧土,则十九至二十世纪,亦犹前之黑暗,又何至有新文明哉!”〔9 〕这里我们不必苛求周恩来头脑中没有树立一元唯物史观,只能看其追求社会解放的可贵思考。
周恩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沈阳读书时就有萌芽,他读了许多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从中汲取了这方面的营养。在南开,接触这方面的书籍就更多了。维新派、革命派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都读了一些,1915年,周恩来在短文《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中谈了他对共和政体的看法,论述了君主制元首和共和制元首之不同,以及共和制的理论渊源、权力之间的监督这些问题。1916年10月,他又在《中国现实之危机》的讲演中,用民主共和的原则分析了中国的事实,这说明周恩来已经能用一些民主知识解释一些社会现象。
从上述可见,青年周恩来救国思想是复杂的,他自己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来。本来他对共和制度有些向往,而现实假共和又促使他欣赏“军国主义”、“贤人政治”,以及教育救国、储金救国等。从总体上来看,他对贤人政治更亲切一些,是以贤人政治为主,杂以其它学说为辅的庞杂的政治哲学。
到1918年春,周恩来政治思想却有了明显的变化。
这一年的2月份, 他在苦闷彷徨之中看了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杂志,就好似发现新大陆那么高兴。他在15、16日两天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无限喜悦的心情,早晨看,晚上回来又看。他对《新青年》宣传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10〕在国内他也看过《新青年》,远远没有这么深的体会。因前几年接受和积累的政治思想太繁杂了。除旧布新,通过重读《新青年》,得到一种净化、宁静。他写道:“收练了几天,这个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错,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11〕2月17 日的日记更进一步说明了他喜从何来。“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以前的一切事体都看成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法国女优倍那儿常说自己是小儿,我今天借用他这句话,我看我自己现在实在是小儿了。哈哈!”〔12〕这些记述,似乎使人看到了一个活灵活现充满自信、充实、满面春风的青年。
这真是历史必然的偶然了。2月18日, 周恩来就抛弃了“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他回忆几年来的旧想法写道:“现在的中国人,多半是因为现在的政局全在几个武人手里拿着,从此往后很不容易从他们手里去接替他管理政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这两句话上,就发生了许多念头,以为将来的政局非励精图治,在军事上头着手,很不容易把这班相传不绝的‘北洋系’、‘士官系’推翻。有这一想法,于是‘军国主义’的念头非常坚固。……因此对于袁世凯的独夫政治、亲德主义,反加赞成,以为他死的是可惜了。对于政治,也是想去行那贤人政治的方法,排斥真正的民本主义。这种主义,差不多现在号称有见识的人,都是这么想,就是我也是这里头的一个人。然而细细的考究起来,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已招各国反对了。”〔13〕经过几年的探索、追求,特别是《新青年》的启发,终于使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这同时也说明,周恩来过去几年对于民主主义的掌握是初步的,是感性的、零碎的,对民主主义的信服还缺乏稳定性、坚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这中间需要一个关节点。这个关节点就是2 月份这几天重新阅读《新青年》的结果。前两年看《新青年》为何没有这个良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缺乏量变的积累。世界观的转变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2月20日, 周恩来在日记中继续记载了自己破除“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的思想。紧接着预备考高师,没有在日记中反映政治思想,只记载了一些生活琐事。
4月23日,周恩来看到了一本新出版的《露西亚研究》日本杂志, 其中有篇文章是记述俄国革命的。现在好多著作把他这一段日记作为其信仰社会主义的证明,其实远远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恰恰是他相信民主主义的证明。他在日记中概述了所学所思:俄国现在分为三个党派,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过激派,领袖是列宁,主张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派;社会革命党,里面又可细分为三派。“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14〕周恩来在这里明确写着列宁主张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这本应是新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而周恩来却没有从新制度的视角去认识,反而放过了这一本质的认识。他说:“总起来说,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主’两主义”。〔15〕(请注意我加着重号这句话)。这说明,前不久周恩来刚刚受到《新青年》的洗礼,民主的思想像春潮一样在心中奔涌,他用“民主”来裁判一切,其简直成了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政治原则,他对俄国革命的本质的认识恰似一步之遥。这一年的11月,先驱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意义。如果说李大钊这是新思维,那么周恩来的思维还停留在早期新文化运动、激进民主主义的水平上。如果说从1915年后,周恩来在政治哲学上逐渐积累民主主义的认识,那么这时,又在逐渐积累社会主义的认识。
5月19日,周恩来在新中会发表讲话, 再一次证明他已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斗士,还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影子,尽管这时离他在4 月下旬看到的俄国革命消息已近1月。他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 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族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的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16〕这一观点,正是他读《新青年》获得新知的结果,有些类似后来胡适讲的“全盘西化”了。这也说明,周恩来对西方民主已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从周恩来自己思想进程上说,这是一件大好事,使他排出了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并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活力与喜悦。
从上面几段叙述可见,1918年2月以后, 民主主义成为周恩来政治思考的主流意识。
那么,怎样理解周恩来在日本阅读了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呢?我认为他这是受《新青年》影响和启发,激励自己求“新思想”、“新学问”,去做“新事情”的表现。他还是以“自由”、“民本”为大宗旨,去理解这些新学说。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新思想肯定引起他的重视,成为他以后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基础,但至今没有发现他1921年秋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给以赞誉的片言只语。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这样一个常识,青年人认为某种学说有道理,对它产生兴趣,但不一定认为它就能救国,而立刻把它作为自己的宇宙观,并用它来指导一切。周恩来在沈阳读书时初步接触了民主主义,天津读书时较多接触了民主主义,并有了兴趣,但他的政治哲学还是“贤人政治”。而他在日本接触这些马克思主义也正好像当年接触民主主义一样,不但没成为主流,也没把其当作一门独立的新阶级的世界观,而是用“民本”与“自由”这些旧瓶装进来消化“社会主义”的新酒。
现在我们再回到周恩来岚山诗境的分析上面。
前面我曾分析《雨中岚山——日本京都》,如果反映了周恩来的政治思绪,只能是对民主主义的喜悦。实际上,只要细心一下,从周恩来同一天写的《雨后岚山》,更能证实我的论点。《雨中岚山——日本京都》看不出政治内容(人们推出对马克思主义喜悦另当别论),而《雨后岚山》政治思想则明朗一些。原诗是:|山中雨过云愈暗,|渐近黄昏;|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登高远望,|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云如带;|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17〕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所猛烈抨击的宗教教条,封建礼法,旧文艺,以及元老们,也成为《雨后岚山》讥讽的对象。有人可能说,“资本家”不是社会主义学说批判的对象吗?其实,新文化运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无情地批判过“资本家”。
综上所述可见,周恩来岚山心境如果用政治方面的因素去解释,那只能说,他已从多元的、庞杂的政治选择中奔向了单一的民主主义选择。
二、周恩来归国后一直以民主为原则,1920年狱中出现思想颤动,1921年秋才相信共产主义
周恩来1919年4月回国后, 好长一段时间坚定不移地用民主主义指导自己的言行。
5月上旬,周恩来就曹汝霖等人给南开捐款,校长准聘他为校董, 批评校长不讲民主,去接近十七八世纪,闹得人心离体。〔18〕
7月12日, 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中说:“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19〕(着重号系本人所加)《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第一期封面的左边中段又写着:“本民主主义发表一切主张”。和上一句只差“精神”二字。在报头的下面,周恩来又用大写的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20〕请注意前面“一切主张”和“箴言”这样的字眼。说明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周恩来,像欧洲启蒙思想家那样都用“理性”去裁判一样,他主张一切都用民主去裁判,任何事物,都要在民主的法庭面前,去认证自己的合法或非法。《新青年》民主的宣传在周恩来心灵中打下的烙印是异常深刻的。
伴随着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和挚爱,周恩来也在实践着个性解放。他呼吁着“革心”、“革新”,从思想中摒弃旧道德、旧文化价值观,塑造完美的、觉悟的新人。1919年9月,他和其他同事发起组织觉悟社, “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21〕他认为,只有人觉悟了,才能不满意旧的现状,去追求新的生活。
差不多一年后,周恩来尚在狱中,又写了首较长的自由诗,继续讴歌启蒙思想的价值观念。如:“女子的生计独立”、“精神独立的自由径路”、“女子的人权天赋”、“自由的故乡”、“自由的旗”、“女权”、“平等”、“推翻旧伦理”等等诗句,我们从这里可见,民主自由的精神这时还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在日本接触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材料却没有得到体现。
我们不仅要从思想材料考察周恩来对民主主义的态度,更应从实践影响上做些考察。周恩来从日本归国后不到两个月,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这无疑给他增添了民主的信心。山东马良镇压爱国运动,周恩来亲自参与了抗议和请愿,其中虽有波折,但最后北洋政府还是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们。周恩来恰在这期间把民主奉为“箴言”,用其指导言行。只是在1920年因“福州事件”举行抵制日货被抓入狱中,他的思想才发生波动。1922年他在致李锡锦、郑秀清的信中说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萌芽有两个原因,一则“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一则“出国后得了施山一封谈主义的信,引起我探求的兴趣。”〔22〕这封信中的两句话对研究周恩来早期思想非常重要。“颤动”,是对民主主义的波动、一丝怀疑,而施山谈主义的信,引起他探求的兴趣,这个“兴趣”是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注意。在日本接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那是从新知识的角度,而这时却从政治角度去认识马克思主义,所以兴趣很浓。通过以上材料也可分析,他在狱中讲了几次马克思主义恰恰也是从“新知识”角度去讲的,政治的因素是不多的,是朦胧的。在狱中其他难友讲的也是些新知识新学问。如国际国内时事、五四追忆及评价、演说学、新人生观、商界工界分析、自我修养等。因为觉悟社在《‘觉悟’的宣言》中规定发扬宗旨方法有四种,即“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23〕显然,狱中这些讲演活动属贯彻觉悟社宗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狱中的周恩来对民主主义发生了颤动,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这一年11月,周恩来乘“波尔多斯”号赴他梦寐以求的法兰西,准备进一步探求救国之道。当他来到英法不久,又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颤动”更甚了。中国究竟参照哪个国家去改造,各有哪些利弊,他又苦苦追寻着。在日本所见民主主义的阳光,似乎又被乌云所盖。这些情况明晰地反映在他1921年1月30日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 信中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24〕可见,这时周恩来还没有拿定主意,还在了解“诸道”,进行充分比较和选择。
周恩来根据学过的知识,再加上他两个月来对英国的观察,英国渐进式的变革是一个选择的对象;他早在日本就了解的十月革命的俄国也是一个选择和比较的对象。但他还没有从社会制度上认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依然停留在方法上对英俄进行比较。他认为,俄国革命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一洗旧弊,符合俄国国情;英国以其保守而整其步法,求渐进改革之效,也符英国国情。这两国之法,用哪一国之法,在中国也不行,只能“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25〕周恩来这一思路说明,俄国革命只是诸道中之一道,尚未从制度上、性质上、历史递进规律上去掌握它。
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迟至1921年秋才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1922年3月,他致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 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 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26〕周恩来不但对自己迟信共产主义找到了心理人格的原因,而且表示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不移。比其他共产主义者晚了一两年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这没有更多遗憾,相反,他饱尝了启蒙、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这对于在一个东方封建大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必要的课题。
老一辈革命家对五四前后自己思想历程的回顾,也是一种很好的旁证。邓颖超说:“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在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27〕曾是周恩来入党介绍人的刘清扬也回忆五四前后自己的思想,说:“那时我们都很幼稚,……没有一定的信仰。……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28〕这些回忆和看法,都具有时代共性。
三、解读岚山诗情不能用单一的政治思维
青年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政治化思维去评价周恩来的岚山诗情。作为年仅21岁的年轻人,身处异国他乡,他的政治前途、价值观念、家庭变故、经济状况,都会影响到情绪。前面我们详细考察了周恩来政治思想由复杂到单一,达到某种程度的宁静,这是他岚山春游产生愉快心境的原因之一。除此外,他还有如下一些因素:
(一)周恩来于1918年两次考学名落孙山,使强烈的领先意识无法实现,陷于极度苦闷之中,当他产生“返国图他兴”的思考和决定之后,心情豁然开朗,这是他岚山心境的因素之一。
(二)周恩来家境败落,亲人亡故,自己功业未成,无以为孝,使他哀痛不已,一旦决定回家,可以见到亲人,减轻心理压力,这也是产生岚山心境的原因之一。
(三)周恩来在日本经济上困苦不堪,想到自己回国后可以摆脱经济困境,也是产生岚山心境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周恩来1918年春较快地抛弃了庞杂的政治思想,汇聚于一元的民主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从此支配着他的行动。1920年狱中发生了“颤动”,1921年秋完成了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他在岚山那种愉快的心情是和彻底相信民主主义有关,也和他对个人前途重新设计有关。对青年周恩来“雨中岚山”这几句诗,不能用唯一的政治思维、单一的思维去解读。只有既用政治,又用生活的思维去解读,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注释:
〔1〕〔5〕〔6〕〔7〕〔8〕〔9〕〔10〕〔11〕〔12〕〔13 〕〔14〕〔15〕〔16〕〔17〕〔18〕〔19〕〔21〕〔23 〕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300、59、63、105、219、221、282、282、283、283、291、290、293、300~301、302、305、333、332页,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胡华、王建初:《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35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3〕〔27〕〔28〕金冲及:《周恩来传》(1998~1949)37、 46、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4〕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37 页, 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0〕《周恩来年谱》(1998~1949),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22〕〔24〕〔25〕〔26〕《周恩来书信选集》,49、23~24 、24、4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