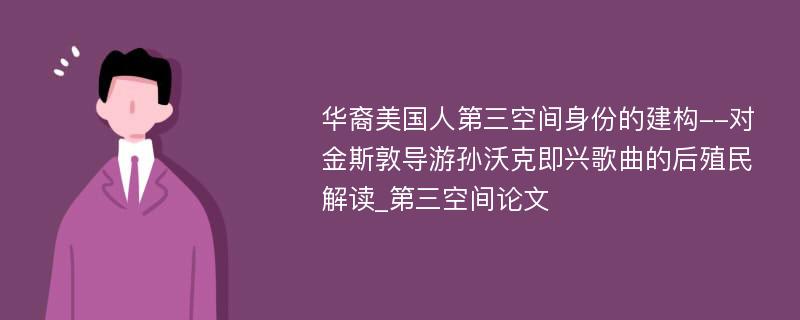
华裔美国人的第三空间身份建构——金斯顿《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的后殖民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即兴曲论文,美国人论文,华裔论文,身份论文,金斯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09)02-0075-06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09.02.1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经历了中美文化激烈的碰撞和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排斥,美国华裔作家开始重写其移民史,反思其生活现状,试图打破主流社会所强加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身份。然而在探求文化身份的艰难过程中,他们徘徊于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得其所。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深谙少数族裔作家所面临的困境与焦虑。基于对流散族群(diaspora)的研究,霍米·巴巴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东方和西方、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为多种文化并存状况下的身份构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第三空间”理论及其对华裔美国人身份建构的意义
在《文化的定位》中,霍米·巴巴提出了二元对立之外的知识与抗拒的“第三空间”——“既非这个也非那个(自我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1]28,即一个被书写出来的模糊混杂的空间,从而揭示穿越种族差异、阶级差异和文化传统差异的文化认同的“阈限”(liminal/liminality)。巴巴指出,第三空间通过“确保文化的意义和象征手段没有原始的统一或固定性”[1]37,使民族性、社群利益或文化价值的主体和集体经验得以被协商[1]2。
事实上,巴巴的“第三空间”是由“杂糅性”(hybridity)策略开辟出来的一块协商的空间。巴巴将杂糅性这个带有贬义性质的生物术语引入文化研究领域,并用于描述在政治对立或不平等的状况中文化权威的建构。他这样阐述杂糅的意义:“殖民杂糅不是一个发生学问题,也不是两个不同文化之间身份的问题,后者作为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重新加以解决。杂糅是一个殖民再现和个体化的问题(problematic),它颠倒了殖民主义否定的后果,使他者‘被否定’的知识进入支配话语,并离间了它的权威的基础——它的肯定的法则。”[1]114换言之,杂糅既是殖民话语生产的符号,同时又构成对殖民话语的颠覆。巴巴认为多种文化彼此混杂,并在跨越文化疆界的过程中进发新生的意义。通过这种混杂化的文化差异的协商,松动了文化本质主义的霸权,解构文化“本源”迷思;在殖民意识中发现、撕开裂缝,挑战殖民话语中的自我/他者、东方/西方、中心/边缘的严格分野,进而颠覆文化民族主义者对种族、血缘和语言“纯正”的盲目坚持,以对抗本质主义的偏见,挑战整体性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
在身份建构的问题上,传统的文化身份观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固定认同,即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后殖民话语拒绝这种始源性的固定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这也成为少数族裔打破主流社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文化刻板形象的理论依据。巴巴本人亦质疑在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带有拜物教性质的身份认同。他提出,今日文化的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而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处和疆界处有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in-between)的、杂糅的身份正在形成;所有流散的族裔(包括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只能处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即第三空间,在矛盾的冲突和传统中创造自己的身份认同。巴巴在这里旨在张扬一种少数族裔的独特的文化视角,“最真的眼睛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角(double vision)”,而“民族”文化也“越来越从被剥夺的少数族裔的视角生产出来”[2]。换言之,当一个人属于不同的文化,能够运用多种语言的时候,就不会被囚禁在一种语言、一种文化里,而是跟它们保持一定距离,去审视这些问题。这种距离感使得他能够将语言和文化看作一个整体,超越它们各自的文化束缚。华裔美国人作为少数族裔大家庭的一员,正如林英敏所言也身处“居间的文化”[3],彷徨于母国与移居国、母国文化与移居国文化之间;但同时亦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居间”的优势,摆脱中国身份或美国身份的纠缠,综合利用这两种文化话语,跟中西古今文化保持着对话式的关系;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状况下言说文化差异,重新检视个人认同、社群归属和国家建构的传统认知,创作出一种跨越种族之争、具有和平精神的全球身份。毫无疑问,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和杂糅理论给遭遇身份建构难题的少数族裔作家们带来了启示。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华裔作家之一,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关注处于“居间文化”的华裔的生存状态,通过展现在中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下所引发的文化的混杂性与多样性,挑战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白人性”美国定义,重新书写华裔美国人乃至美国的文化。
1989年的《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以下简称《孙行者》)为其创作生涯中的第一本小说。该小说把历史时空置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旧金山,将中国古典小说、西方文学传统以及美国流行文化三者杂糅并呈,叙述第五代华裔美国人的美国新经历。小说正如书名所暗示的,融合了美国嬉皮士精神、中国古典小说以及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想象,描绘华裔美国人经历中美两种不同文化互相纠葛的现象。“Trip”一词一语双关,它指代中国人由中国移民到美国的空间移动,暗示着各种不同疆界的跨越以及随之而宋的文化错置等漂泊离散(diasporic)经验,也隐喻华裔美国人在历史断裂、时空交错和文化变迁的新天地里,不断改变自己,发现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社群文化定位的历程。
二、在第三空间打破种族二元对立
爱德华·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统治,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西方的风格或方式。”[4]在西方的书写与东方文本之间,西方展现其意志力,用以统摄、宰制、决定东方文化再现的表现方式与内容。美国境内的东方民族也承受类似“东方主义”霸权的殖民效应。李磊伟(David Leiwei Li)研究中国人在美国的移民经验时提出了“美国的东方论述”(American Orientalist discourse)[5]。历史上美国主流社会通过文学艺术和大众传媒等手段,将亚洲人捏造为与白人完全相异的、落后的“他者”形象,从而在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方面将他们合法地排斥在外。华裔美国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当然逃脱不了主流社会的丑化与异化的命运。主流社会在将华裔陌生化、绝对化、他者化与妖魔化的处理过程中,逐步建构了等同于“白人性”(whiteness)的美国性(Americanness);与此同时,在包括华裔美国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和主流社会之间建立了无法逾越的界限。更为可悲的是,华裔美国人在被教导接受学习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语言文化和
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间接接受自己是落后愚昧种族的“事实”,进而自卑自轻,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归属。因此颠覆主流话语,重塑华人形象,言说文化差异成为华裔作家作品所关注的一个母题。
与大部分华裔作家不同的是,金斯顿并没有停留于对华裔所遭遇的痛苦经历的控诉。她在小说里开创了一个想象的第三空间,试图打破自我/他者、东方/西方以及边缘/中心的二元对立,揭示华裔美国人文化杂糅性(cultural hybridity)的本质,瓦解主流社会强加于华裔身上的刻板形象,以达成重新书写华裔美国人个人认同的目的。为此她塑造了一个充分体现杂化特征的美国华裔男性形象——慧特曼·阿新(Wittman Ah Sing)。
首先,慧特曼·阿新的命名由来便充满了巴巴式的杂糅模拟——一个美中结合再经改写的产物。主人公的“美国性”体现在他的名字——慧特曼(Wittman)上,这很自然令人联想到美国著名民族诗人——美国精神的缔造者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但是不难看出此慧特曼(Wittman)非彼惠特曼(Whitman)。慧特曼借自美国现代诗歌之父惠特曼(Walt Whitman),并有意无意地做了改写,去掉了其中的“h”,添加了一个“t”。金斯顿在一次采访中谈及该命名的缘由及意义:“慧特曼的父亲以‘最美国’的诗人之名为儿子命名,但却以有趣的方式拼写,那两个音节是华裔所独有的拼写习惯。我想在我的作品里将延续惠特曼的文学传统。……惠特曼为了赞颂所他倡导的现代人而写作,他为美国本身而歌唱。我为华裔美国人歌唱……”[6]金斯顿用华裔美国人自己的另类方式,对主流话语权威进行了无声的渗透、介入与干预:在跨越文化疆界杂糅模拟的过程中,对其进行解构与重构,重新书写华裔美国人的文化空间。
至于主人公的姓“阿新”,金斯顿欲通过这个包含多重涵义的杂糅名字,引发多重联想,借以多重寓意。她把哈特(Bret Harte)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笔下诈赌的“狡黠中国异教徒”(heathen Chinese)阿辛(Ah Sin)当作男主角的姓,并将这个带有屈辱含义的姓和代表“美国精神”的慧特曼名字并置,借以凸显美国社会对华裔美国人的歧视。还有学者认为阿新(Ah Sing)取自1855年致信给加州州长反对歧视华裔、争取华裔权益的诺尔曼·阿新(Norman Asing)[7],巧合的是也在1855年惠特曼出版了《草叶集》。由英文来看,Ah Sing又可以解读为“啊,唱吧”,与惠特曼的诗歌《自我之歌》(Songs of Myself)相得益彰。可见金斯顿欲借此姓氏暗示主人公是为华裔族群权益摇旗呐喊的先行者。事实上阿新既非姓也非名。“阿”字在中文里没有特别意义,只是一个广东方言里称呼的起头。“阿新”是早期华裔入境时,阴差阳错地被海关认可的姓氏。
金斯顿倒名为姓,把阿新当姓氏,也倒姓为名,把大诗人惠特曼这个英文姓氏当作阿新的名,倒置了原有的秩序,凸显了两种文化混杂协商过程中所产生的新命名,打破西方语言的霸权优势,使带有杂糅色彩的华裔语言也具有与西方语言相同的正当性。可以说,金斯顿通过主人公杂糅化的命名,在东西方文化相互杂糅的过程中,打破了二者的严格分野,在随之产生的暧昧的第三空间中重新定义华裔美国人的新文化身份。
慧特曼·阿新不仅在其命名上凸现了杂化的特征,他还是“猴王在当今美国的化身”[8]。在这里金斯顿将中国传统文化移植到了美国的文化语境中,把孙悟空协助唐僧西天取经的神话故事《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隐喻华裔移民定居美国的历史事实(Journey in the West):中美文化再次交融混杂,形成了一个表达身份和差异的阐释空间。慧特曼·阿新这只杂化的“猴子”,不是来自中国花果山的孙悟空,而是来自于旧金山的“山姆大叔”[7],游走于中美文化之间的“行者”(Tripmaster);他集理想、叛逆、自由和自信于一身,以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杂化演出,达到颠覆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形象和积极重塑华裔美国人的新文化认同的双重目的。
金斯顿不满华裔美国人被视为“失声”的他者,便塑造慧特曼这只喋喋不休的嬉皮猴子来颠覆此负面的形象。小说一开始,慧特曼不再是阴柔的、被禁声消音的传统华裔男性。他多言善辩,挑战“美国东方论述”的霸权宰制,指出中国人的体貌特征虽然与白人不同,但绝非外貌可憎、又聋又哑的怪物;华人身上也不乏美国白人的任何品质,而且更加可塑和全面,同时具有文化杂糅的本质,正如慧特曼父亲所说:“真正的中国人像印第安人、巴斯克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吉普赛人、菲律宾人。”[9]200慧特曼也以犀利的言辞批判主流社会的“模范少数族裔”的政治运作,揭穿主流社会借这种隐蔽的殖民政策再次“驯化”、“边缘化”华裔美国人的阴谋。他以一幅20世纪60年代美国“垮掉派”青年的姿态:蓄长发留络腮胡,磕药迷幻,嬉笑狂骂,从事不稳定不体面的工作,彻底颠覆主流社会强加在华裔美国人头上的“模范族裔”光环。
当然,“嬉皮猴子”慧特曼最像的还是那只拥有“七十二变”法力的孙悟空。《西游记》中孙悟空凭借“七十二变”法力,应对种种艰难险阻。《孙行者》中慧特曼的“七十二变”则使他挣脱任何本质主义身份认同的固囿。如同孙悟空可以拥有不同的化身一样,慧特曼的身份游动不止,他是经历民权运动的垮掉派,是在公车上朗诵经典的校园诗人,是百货公司玩具部门的售货员,是城市的失业者,是用杂糅式的中西文学传统重写华裔民族史的剧作家……他不停地变化,展现多面化的自己,呈现华裔美国人身份的流动性和杂糅性。多重性的“自我”彻底颠覆了主流社会对华裔美国人的僵化认识,化被叙述的客体为主动陈述的主体,转被压抑的小写的“我”(me)为自我肯定的“大我”(1),从而重建了自己的主体尊严,寻找到属于华裔美国人自我的文化定位。正如慧特曼大声宣布:“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战士要赢得西部、地球和宇宙。”[9]319为了追寻华裔美国人消失已久的英雄传统,慧特曼借用了中国古代甲骨文“我”字的书写中含有代表战斗精神的“戈”字,声言“我们是关公的子民”[9]319,从而打破了华裔美国人滞定化的文化属性(内向、服从、阴柔)。这种全新的“自我”通过中国古代象形文字在西方语境中迸发出一种全新的意义,一种属于华裔美国人的新的身份认同由此产生。
这种流动杂糅性的全新身份是两种文化越界协商所进发的新意,同时也使慧特曼和他的族群挣脱了“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中的族裔连字符(ethnic hyphen)的枷锁。连字符号的存在,对于华裔美国人而言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选择:不是被美国主流社会彻底同化,就是固守中国传统成为永远的他者。而连字符的去除,“‘Chinese’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American’就成了名词。这样,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就成了美国人的一员”[8]。
三、在“第三空间”建构华裔美国人新社群
“嬉皮猴子”慧特曼在追寻个人认同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垮掉派作家克鲁索“在路上”精神的虚空与无助。美国所称道的个人主义——“美国人自行其是。关系疏远,没有族人,崇尚个人。成功的美国人必须远离族人,远离伴侣,远离帮伙”[9]273,仅仅是适用于白人的生存哲学。对于游移在白人至上主义社会之外的“他者”,华裔美国人只有依靠他的族群的力量,并以此为依托才能找到他们真正的文化归属。
尽管中国移民定居美国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在美国社会却始终是隐性人口,他们从未真正占有空间。这种“不可见”性,正如巴巴引述葛兰西的概念时所言:“(他们不仅是一个受压迫的团体),而且缺乏自主性,从属于另一社会团体的影响或支配,完全没有自己的支配空间。”[1]59因此华裔社群只有争取、对抗既成的空间分布,披荆斩棘开辟属于一己空间,方能重新自我定位。
正是缘于对社群的渴望和“争回美国”的诉求,慧特曼找到了戏剧,他坚信“我们创造剧场,我们创造社群”[9]261。他以杂糅中西文学传统的即兴剧凝聚华裔美国人意志和力量,借表演自己族群的故事,唤醒集体记忆,带领华裔社群进入美国文学传统,从而介入美国主流社会,为华裔开辟新的生存空间。
慧特曼的剧团“美国梨园弟子团”(The Pear Garden Players of America)本身就是中西文化杂糅并呈的产物,以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演出”(interplay)来拒绝二元对立的绝对差异和对本源纯正的迷恋追求(nostalgia for the lost origin)。“梨园”本是中国人对戏剧的俗称,将中国的戏剧放在“西方”,无疑构成杂化的意象。它是金斯顿所致力建构的美国华裔族群文化的具体体现,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高度杂化的美国华裔族群的象征。这座西方梨园在演出过程中逐渐成为游移不定、具有无限可能的、颠覆性的第三空间,并在此孕育出新的文化感性(cultural sensibility)。
慧特曼的剧本多元杂糅,涵括中西文学传统,以互文(intertextuality)的方式将中国典小说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及不同源头的欧美文学作品与美国通俗文化混沌杂糅,互相僭越;时间横跨古今,剧情连接中西,架构雄浑磅礴,演员与观众以后现代的狂欢颠覆既有的秩序,共同演出自己社群的故事。休戚与共的情感交流唤醒久远的华裔英雄传统记忆,重拾失落的自尊与自信。
将所有“被遗忘的事物,被忽略的人物”[9]52统统纳入剧中,因为“任何与你偶然相遇的人们都是你的同胞”[9]223。慧特曼以这样民主开放态度为创作理念,让所有的人,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和阶级都参与演出,从而紧紧凝聚成一个坚实而无所不包(inclusiveness)的想象社群,意味着不能以传统的地理观念来区分群体,也不能以肤色、国籍来定义群体的成员。一个杂化的兼容并蓄的群体由此诞生,从而有力地粉碎了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社群之同质化、刻板化的建构。
西方梨园以集体的力量用戏剧描述“我们存在的事实”,并再次用“杂糅”为华裔美国人社群争取空间,重绘美国的想象地理空间。慧特曼所重绘的美国历史和空间是杂化而多源头的,从而颠覆美国源头的权威论述,建构了多元共存的新国家想象。中美地理历史在慧特曼的剧中杂糅并呈,中国的“珠江三角洲”[9]37和“长江的东吴”[9]172成为美国人初至美洲大陆的地方;慧特曼的祖先抵抗英国侵略者的虎门销烟正如当年美国人民抵抗英国殖民者的波士顿倾茶事件[9]323;歌颂华裔移民经验的歌,则是戏仿美国民谣O Susana,成为《金山之歌》[9]39;慧特曼的祖先和乘着五月花号来新大陆的欧洲人一样久远[9]39。金斯顿曾经概括美国华裔身份建构探求的尝试:“一部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就是一场争取美国人的战斗;我们不畏艰辛地为获取合法的美国公民而战。”[10]因此,慧特曼在他的独角戏中告诉他的同胞:“我站在这片土地上,我是属于这片土地 (美国),而这片土地也是属于我的。我不是地球另一面的东方人。”[9]326为此,华裔美国人必须认同他们为之奋斗和耕耘的土地,产生休戚与共的情怀,才能真正地为自己的族群开辟生存的空间。于是,当提起“革命”不再是1911年和1949年,那只能说明“你依旧是个新宋的人”[9]282,“1776年7月4日才是我们的革命纪念日”[9]282。
慧特曼执导的这部社群大戏,以即兴演出为媒介,介入多元族裔的文化遗产,借由文化记忆的再现和重新书写,重新定义美国的属性,使之成为华裔族群争取对抗既成的空间分布、重新自我定位的舞台。
四、结语
金斯顿这部充满后殖民主义文本色彩的小说和霍米·巴巴的主张相呼应:运用杂糅的策略,言说文化差异,解构文化本质主义,以语言为华裔的身份及其社群重新命名,再创华裔美国人新传统,争取文化空间,进而重绘美国立国的想象地理空间。一个跨越在此岸和彼岸的属于华裔美国人的精神家园由此而生。
收稿日期:2008-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