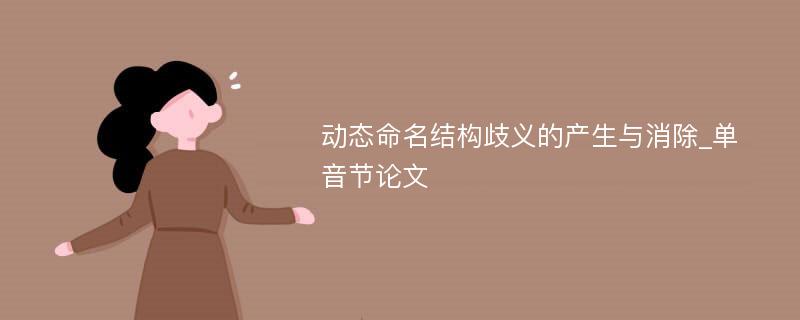
动—名结构歧义的产生与消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义论文,生与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动—名结构可以用来表达多种句法关系,最常见的是表示动—宾关系或定—中关系,但也可以用来表示存现关系以及表示频同动作频率或时段相关的动—补关系。同一个结构形式可以表达这么多的句法关系,必然会出现歧义。而汉语的形态标记又不很发达,产生歧义的几率似乎应该很大。不过,尽管像例(1)a那样的歧义结构并不罕见,像例(1)b和(1)c那样的非歧义结构却也大量存在,而且歧义结构和非歧义结构在形态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就说明汉语一定有某种机制防止动—名结构产生歧义,或者说可以消除某些动—名结构的歧义,而且该机制应该与形态标记无关。
(1)a.炒蛋 雇工 拖车 存款 走道 吊灯
b.炒锅 雇主 拖斗 存折 走廊 吊臂
c.炒股 雇人 拖粮 存档 走路 吊水
动—名结构产生歧义的原因以及消除歧义的办法,历来众说纷纭。目前占上风的说法是汉语的动—名结构以表示动—宾关系为主,在表示定—中关系时则受到很多限制,所以能表示定—中关系的动—名结构很少,有歧义的更少。文献中经常提及的有语义限制(朱德熙1982,邵敬敏1995,郭锐2002,李晋霞2003,李晋霞、刘云2003)、句法结构限制(顾阳、沈阳2001)和广义的韵律限制(吴为善1986、1994,张国宪1989、1997,端木三2000,冯胜利2000、2002、2004,王洪君2001)这几种。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汉语的句法既允许动—名结构表示动—宾关系,也允许其表示定—中关系,所以许多动—名结构是天生就具有歧义的。不过,具有某些特定句法地位的动词性成分和名词性成分组合时,往往只会形成特定的动—名结构,表示特定的意义,并不一定会产生歧义。即使是有歧义的动—名结构,由于受语义、韵律、语用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有时候也会失去部分意义,不再具有歧义。这些因素对动—名结构的合法程度只有相对的影响力,并没有绝对的否决作用,对于歧义的消除也只有相对的影响力。从句法同语义、韵律以及语用之间的互动关系着手,探讨各种因素在消除歧义时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汉语语法的特点。
一 句法因素对动—名结构的影响
动—名结构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句法关系。比如例(2)a和(2)b中的动词都属于一价,即通常所说的不及物动词,所以后面的名词短语只能理解为施事,而不是受事。这两个例子带有表示体貌的动态助词,应当理解为完整的句子,但句中的施事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语,也不表示被动意义,这类结构一般称为存现句。
(2)a.进水了! b.跑油了。
一价动词形成的动—名结构并非总是表示存现关系,有时候也会像例(3)a那样表示定—中关系,这样就必然会出现(3)b那样的歧义结构。
(3)a.来宾 b.来人
不过,歧义的出现同名词性成分的形式及其句法地位有关。只有当一价动词后面是光杆名词时,这种动—名结构才有可能出现歧义。如果像例(4)那样,名词性成分带有数量成分,或者像例(5)那样名词性成分受“的”字结构修饰,整个动—名结构就只可能表示存现关系。
(4)a.来一个人 b.跑三辆车
(5)a.来不相干的人 b.跑不值钱的车
另一方面,如果一价动词变成了“的”字结构的一部分,原来的动—名结构就不再会产生歧义,只能像例(6)那样表示定—中关系。
(6)a.来的人 b.跑的车
由二价动词形成的动—名结构也有类似的特点。只有当其中的名词性成分是光杆名词时,整个结构才有可能出现歧义,或者说才有可能既表示定—中关系又表示动—宾关系。如果名词性成分受“的”字结构修饰,带有数量成分,或者带有指示代词,整个动—名结构就只能表示动—宾关系。例(7)、(8)和(9)a、(9)b中的结构就都没有歧义。
(7)参考老师指定的文献 (8)烤刚买的红薯
(9)a.考三道题 b.提交两个议案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例(9)中的动—名结构作一些改动,将动词性成分放在“的”字结构中,得到的例(10)便不再能表示动—宾关系,而是只能表示定—中关系了。
(10)a.考的三道题 b.提交的两个议案
动—名结构的这些特性同内部成分的句法地位有关,也同汉语的句法结构要求有关。现代理论句法中有两种句法结构,表示两种最基本的句法关系。附加结构表修饰关系,核心—补足语结构表谓—宾、介—宾及存现等关系。附加结构的组成部分必须具有相同的句法地位,即词只能由词修饰,短语只能由短语修饰。核心—补足语结构中的核心必须具有词的地位,而补足语必须具有短语的地位,所以动—宾结构的“动”一定是动词,“宾”一定是名词性短语。
在现代句法理论中,短语指在句中充当主要成分的句法单位,性质取决于其核心成分,名词短语的核心一定是名词,而以动词为核心的一定是动词短语。短语可以只有一个核心,也可以由核心同其他成分按规则组成,所以有些可以充当核心的句法成分,如名词、数词、形容词以及一价动词之类,在单独出现时既可作为单个的词,又可作为短语,即只有一个核心的短语。
正因为如此,光杆名词在现代理论句法中便具有双重地位,既可以作为名词在复合词中充当成分,又可以作为名词短语在句子或其他短语中充当成分。单个的数词同样具有双重地位,但数量成分和名词的组合结构则具有短语的地位,即所谓的数词短语(NumP)(Li 1998)。单个的代词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但指示代词、量词和名词的组合是短语,即所谓的限制词短语(DP)(Abney 1987,Chomsky 1995)。另一方面,单个的动词中只有一价动词才会有双重地位,而真正的单个两价动词就只能是词,不会是短语。只有“的”字结构才一定是短语,只不过已经不再是动词短语,而是一个小句(石定栩2002),或者一个特殊短语了(司富珍2004)。
正因为词和短语有这些差别,缺乏形态标记的汉语同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动—名结构出现歧义。汉语的动词短语不能直接修饰名词性短语,只有“的”字结构才能修饰名词性短语,大部分动—名结构因此只能表达单一的句法关系。即由“的”字结构和名词性成分组成的结构只表示定—中关系,而由单个动词和名词性短语组成的动—名结构一定不表示定—中关系,只会表示存现、动—补或动—宾关系;只有例(1)a或例(3)b那样由单个动词和光杆名词组成的动—名结构才可能出现歧义,既可理解为单个动词和光杆名词构成修饰关系,又可理解为单个动词和名词性短语构成核心—补足语关系,既表示定—中关系又表示存现或动—宾关系。
二 影响动—名结构的语义因素和语用因素
由单个动词和光杆名词组成的动—名结构可能会产生歧义,但并非一定会出现歧义,比如例(1)b、(1)c和(3)a里的动—名结构就只能表示一种意义。所以还应该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或者限制某种意义的产生,或者规定由某种动词和名词组成的结构只能表示某种意义。
朱德熙(1982)按照语义把动词分为两类,即普通动词和名动词,并且指出只有后者才能直接修饰光杆名词,而“[普通]动词必须加上‘的’才能修饰名词。要是把[普通]动词直接加在名词前头,造成的就不是偏正结构而是动宾结构”。名动词是表示抽象意义的动词,如“调查”、“说明”、“支持”、“考虑”和“准备”之类,特点是既可以直接充当谓语,又可以放在“进行”、“加以”、“给予”、“予以”和“作”等虚化动词的后面充当宾语(朱德熙1985)。
朱先生的意思是说由于名动词具有名词和动词这一双重身份,动词性比较弱,所以能直接修饰名词而不至于造成歧义。他的另一个意思是说,当动词性比较强的普通动词出现在动—名结构中时,首选的意义只能是动—宾,所以“买卖房屋”、“交换货物”和“占领阵地”等结构都只能表达一种意思。
朱先生这里说的当然是二价动词。由一价动词形成的动—名结构一般不会表示动—宾关系,但有可能表示存现关系,所以依此类推的话,一价动词也必须加上“的”才能够修饰光杆名词。不过,一价动词直接修饰光杆名词的情况似乎十分常见。例如:
(11)飞鸟 跑车 游鱼 跳台 落点 笑声 卧姿 哭腔
(12)死亡地点 睡眠姿势 投降条款 失败原因 游行群众
由普通二价动词形成的动—名结构其实也是如此,不需要“的”而可以表示定—中关系的数量极多(邵敬敏1995),除了例(1)b之外,例(13)、(14)也较为常见。
(13)占领区 侵略军 检查哨 调和油 打击乐 印刷厂 混合物
(14)买卖合约 交换条件 监督单位 遗失车辆 羁押人员
不过,由二价动词组成的动—名结构的确有一部分只能表示动—宾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像例(15)那样有歧义的。这就说明朱先生的论断是有事实根据的,只不过归结得过于严谨,仅仅考虑了表示动—宾关系这一种可能性,而忽略了另外两种可能性。
(15)填鸭 汇款 烤烟 烧肉 编码 遗失证件 打印文件 交换学生
朱德熙(1982)的论断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去理解,即动词的语义对动—名结构是否会出现歧义有一定影响。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标记,修饰关系和核心—补足语关系最终都有可能形成动—名结构。也就是说,由动词和光杆名词构成的动—名结构既可能表示定—中关系,也可能表示动—宾关系或存现关系,这种结构从本质上说是应该有歧义的。不过,实际使用的动—名结构并不都具有歧义,应有的两个意义往往会被消掉一个,而导致固有意义被消除的因素很多,动词的语义便是其中之一。
比如说朱先生提到的名动词“调查”,语义上通常要求表示事件的名词性成分作补足语,所以“调查事故”和“调查事故原因”都表示动—宾关系。一旦动词后面出现了表示其他事物的名词性短语,不太可能作为“调查”的对象,整个动—名结构便有可能表示定—中关系,如“调查计划”、“调查期间”和“调查任务”等都是这样。
类似的情形在普通动词中同样存在。比如说,“攻占”不能跟在虚化动词后面做宾语,是个典型的二价动词。按照朱先生的说法“攻占”应该只能带宾语,而不能直接修饰光杆名词。事实上虽然“攻占阵地”和“攻占城市”多半会理解为动—宾结构,但“攻占时间”、“攻占方式”和“攻占部队”却都是可以接受的定—中结构。关键在于“攻占”要求表示地点的名词性成分作补足语,“阵地”和“城市”可以满足这一要求,而“时间”、“方式”和“部队”却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由前者和“攻占”构成的动—名结构可以表示动—宾关系,而由后者构成的动—名结构就只能表示定—中关系了(邵敬敏1995)。
显然,动—名结构的语义并非完全取决于动词的语义,而是还取决于动词和名词的搭配,特别是动词对补足语的搭配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双向选择性原则(邵敬敏1997)。如果动词对补足语的要求比较宽松,那么形成动—宾结构或者歧义结构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比方说,商品交易的范围现在越来越广,可以同动词“买卖”搭配做补足语的名词也越来越多,由“买卖”构成的动—名结构就以表示动—宾关系的或歧义的居多,能够表示定—中关系的就只有“买卖双方”、“买卖方式”和“买卖金额”等少数几个了。这些名词表示的事物通常都无法作为商品进行交易,所以用在动—名结构中不会表示动—宾关系。
有些名词性成分只用来表示人,而且通常是作为动作施事的自然人或法人,如“手”、“师”、“家”、“专家”、“商家”之类。由这些名词性成分和二价动词组合,形成的动—名结构就常常只能表示定—中关系,例(16)中的动—名结构因此都不会有歧义。
(16)突击手 核算师 批评家 盗窃能手 剽窃专家 制造厂家
除了动词和名词的语义搭配之外,语用因素也会对动—名结构能够表示的意义产生一定的影响。比方说“遗失”和“丢失”对补足语的搭配要求大致相同,而且都可以表示具体的动作,所以由这两个动词构成的动—名结构一般情况下会表示相同的关系,如“遗失收据”、“丢失收据”和“遗失皮包”、“丢失皮包”都表示具体的动作或事件,即表示动—宾关系。不过,具体的动作总是牵涉到具体的事物,如果相关的名词不表示具体的事物,而是表示类别或者事物的集合,动—名结构就不大可能表示具体的动作。比如“车辆”总是表示事物的集合,“丢失车辆”和“遗失车辆”不可能表示具体的行为或动作,也就很难表示动—宾关系。还有一些由文言文遗留下来的名词性成分,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表示常见的事物,在动—名结构中就很难表示动—宾关系,如“观众”、“储户”、“怨妇”等动—名结构便只会表示定—中关系。
当然,很难不等于绝对不可能。在特定的语用环境里,“遗失车辆”还是可以表示动—宾关系的,只不过不星表示具体的动作,而星抽象的动作,或者是某一类别的动作。比如香港警方有一条规定是“遗失车辆为严重失职”,表示特定的动作类别,而保险公司的要求“遗失车辆应立即申报”则表示抽象的动作。
另一方面,由于“遗失”也可以表示较为抽象的、作为类别的动作,其构成的动—名结构在某些语境中就会表示定—中关系。像“遗失款项三天后寻获”,和“遗失物品待领”中的“遗失”都明显是在充当定语。就算是“遗失证件”,也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才会表示动—宾关系,更常见的应该是表示定—中关系。
有些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动—名结构的实际意义。比如说“辅导”要求表示人物的名词性成分作补足语,“辅导老师”和“辅导学生”照理都应该可以表示动—宾关系。但是,由于老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的关系不对等,通常总是老师辅导学生,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前者更倾向于表示定—中关系,后者更倾向于表示动—宾关系。类似的社会因素也可以解释“治疗医师”和“治疗病人”,或者“管理干部”和“管理工人”之间的差别。“管理”表示的是一种权力关系,即上级管理下级。“干部”的级别有高有低,所以“管理干部”可以表示动—宾关系,即普通干部被更高层的人物管理,也可以表示定—中关系,即负责管理下属的干部。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工人通常处在权力阶梯的最下层,所以“管理工人”只能是动—宾结构,即工人接受管理。但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由“工宣队”的工人管理大大小小的干部,“管理工人”大概就可以理解为定—中结构了。
三 影响动—名结构的韵律因素
影响动—名结构语义的还有一个因素,即动词的音节数量。比如张国宪(1989,1997)及胡裕树、范晓(1995)就曾经提出,只有双音节动词形成的动—名结构才可能表示定—中关系,而由单音节动词构成的只能表示动—宾关系。不过,张国宪也承认有些例外,一是某些单音节一价动词可以充当单音节名词的定语,二是表示烹饪义的单音节动词可以在表示食物名称的动—名结构中充当定语。
近来有人从韵律规则对句法结构的作用着手(冯胜利2000、2002、2004,端木三2000,王洪君2001,李晋霞、刘云2003,吴为善1986、1994),对这一限制作了更为细致的描述,指出音节数量对动—名结构的影响会因其语义而变化。表示定—中关系时,双音节动词加双音节名词的2+2形式,单音节动词加单音节名词的1+1,双音节动词加单音节名词的2+1,或者是带有附带成分的单音节动词加名词的[1+1)+1都符合韵律要求,而单音节动词加双音节名词的1+2形式则不符合韵律要求。表示动—宾关系时,双音节动词加双音节名词的2+2形式,单音节动词加单音节名词的1+1,以及单音节动词加双音节名词的1+2都符合韵律要求,只有双音节动词加单音节名词的2+1形式不符合要求。
他们的理由是“建造房屋”、“建房”和“造房屋”都是能说的动—宾结构,但“建造房”或“建造屋”就不能为人接受。同样,“租住客人”、“租客”、“租住人”和“长租客”都是能说的定—中结构,而“租客人”或“住客人”都不是能说的定—中结构。韵律对各种结构都有限制作用,动—名结构自然也包括在内。
韵律限制的确反映了一定的语言事实,上面的这些例子也确实能够证明这些限制的存在。不过,问题在于音节数量也好,韵律要求也好,似乎都构不成严格意义上的限制。在现代语言学中,所谓的限制应该是没有例外的。比如汉语中不得出现被修饰成分在前修饰语在后的正偏结构,便是最典型的句法结构限制,任何违反这一限制的句法结构,都不能成立,无一例外。而动词音节数量对定—中结构的限制或韵律对动—名结构的要求,却都有大量的例外存在。
比如在表示定—中意义的动—名结构中,并不像张国宪(1989,1997)、胡裕树、范晓(1995)所说的那样必须由双音节动词充当定语,由单音节动词构成的定—中结构实际上数量极多,而且各种类型的都有。下面的例子都是由单音节动词和单音节名词构成的定—中结构。例(17)中的定语是一价动词,例(18)中的定语是二价动词,中心语是动词的施事,例(19)里的定语也是二价动词,但中心语是动词的受事,例(20)中的定语同样是二价动词,但中心语的句法地位各异,包括工具、地点以及其他不太容易说清楚的各种成分。
(17)死囚 浮云 入口 动感 渡口 飞艇 挂钟 滚筒 滑道
(18)雇主 窃贼 赌徒 读者 看客 考生 骑士 杀手 养父
(19)爱女 批件 插画 炒粉 存款 雕像 挂图 煎饼 贴花
(20)刮刀 烤箱 吸力 考题 驻地 堆栈 产量 唱法 运力
即使是采用较为狭窄的韵律限制,即主张只有1+2型的定—中结构才不符合要求(冯胜利2000,2002),例外也还是不少。下面例(21)-(23)里的动—名结构都表示定—中关系,而且修饰双音节名词的都是单音节动词,可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定—中结构不能说。
(21)飞将军 浮小麦 定滑轮 升结肠 活火山 叫蝈蝈 睡美人
(22)腌黄瓜 煸草头 炖蘑菇 冻豆腐 制首乌 炙甘草 镶红木
(23)代总统 仿牛皮 加速度 拖油瓶
既然有这么多1+2类型的定—中结构可以说,韵律限制的可靠性便要大打折扣了。不过,不能说的1+2定—中结构也的确不少,韵律限制又似乎并非一无是处。问题在于文献里讨论1+2型的定—中结构时,总是从2+2型的定—中结构开始,逐个减少“定”和“中”的音节数量,这同究竟有没有能说的1+2定—中结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2+2型定—中结构的缩减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牵涉到的因素很多(李晋霞、刘云2003,周荐2003),本文不打算涉及,留待以后另文讨论。
另一个问题源自韵律限制的适用范围。一般都主张韵律对1+2型的限制适用于所有定—中结构,而非仅仅针对动—名结构,即所谓的“辅重必双”理论(王洪君2001)。但事实上表示定—中关系的动—名结构和一般的定—中结构在这一方面有不小的差别。由名词和形容词充当定语的定—中结构为数极多(周荐2003),常见的有例(24)那样由名词充当定语的,还有例(25)那种形容词充当定语的。
(24)铁工厂 菜市场 人贩子 市政府 省机关 水资源 煤藏量 水薄荷 海百合 棉蚜虫 书蛀虫 角天牛 枪榴弹 钢结构 木栅栏 美舰队 儿皇帝 车把式 窑花子 电老虎 油耗子 蕨化石 油页岩 性知识 猪内脏 牛排骨 糖火烧 铅玻璃 铝合金 油葫芦 核潜艇 氢弹头 油码头 水罐车 脑外科
(25)小布伞 大高个 红小鬼 长竹竿 丑小鸭 新大楼 大红楼 破汽车 旧房子 大房间 好电影 高质量 红布条 黑衬衫 假奶粉 真翡翠 干木头 胖娃娃 短文章 薄棉被 热炕头 熟地瓜 厚毛毯 方瓷砖 远距离 热饽饽 冷饺子
相比之下,由动词充当定语的1+2型定—中结构似乎种类较少,常见的只有两类,一类是像例(21)那样由—价动词构成的动—名结构,通常没有歧义,只能表示定—中关系。另一类是例(22)那样由二价动词与其受事构成的动—名结构,通常都具有歧义,既可以表示动—宾关系,也可以表示定—中关系。而由二价动词充当定语修饰施事的,则很难找到,例(23)中列举了几个地位不太清楚的,其中的动词勉强可以算是二价,但中心语却又似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施事或受事,有些恐怕要算成与事或其他成分。
显而易见,由单音节动词充当定语的确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该限制并不完全取决于韵律要求,而是与动词的句法地位以及中心语和动词的句法语义关系密切相关。比较合理的作法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到朱德熙(1982)最初的设想,从动词性的强弱着手。单音节动词的动词性比较强(胡裕树、范晓1995),而双音节名词则是典型的名词,由这两种成分构成的动—名结构主要表示动—宾关系或存现关系。而双音节动词的动词性比较弱,由其构成的动—名结构往往既可以表示动—宾关系,又可以表示定—中关系。
另一方面,很多单音节的名词性成分在现代汉语中失去了自由地位,成了所谓的“成词语素”(陆俭明1988),不再能够单独成词,也就不再能够作为短语充当动词的宾语。由这类名词性成分构成的动—名结构,表示动—宾关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价动词构成的1+2型动—名结构主要表示存现关系,只有当动词和名词的语义搭配不太可能表示存现义时,像例(21)那样的动—名结构才有可能表示定—中关系。二价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名词构成的动—名结构主要表示动—宾关系,但有些语言环境会帮助这种结构获得定—中意义。比如在制造、中药、烹饪等行业中,常常用加工方式来区分产品,而加工方式又通常由动—宾结构表示,所以例(22)中的那些动—名结构既用来表示加工过程,又用来表示产品,这就形成了一大批歧义的动—名结构。这些结构的两种意义各有各的使用场合,很少会重叠,也就很少会造成误解。
由此可见,韵律要求对1+2型定—中结构的限制其实并不严格,反倒是单音节动词的句法地位对表示定—中意义的动—名结构有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时候会因为语用的关系而产生一些变化。
四 结语
关于动—名结构的合法性的讨论验证了当代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共识,即句法上的结构限制通常是不能违反的,不符合句法结构规则的成分必然不能说;但合乎句法规则的并不一定就能够说,因为语音、语义和语用的要求会将其中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筛选掉。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名词构成的动—名结构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讨论还证实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名言“说有易,说无难”。在考察语言现象的时候,一时找不到例证不等于永远找不到,更不能因此就轻易否定某一现象的存在。本文的讨论基于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基本信条,只有更好的理论才能取代原有的理论,而单靠反例并不能推翻现存的理论,应该尽力寻找能更好、更全面地解释语言现象的理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希望能有更多的同行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本文提出批评,使我们的认识能够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