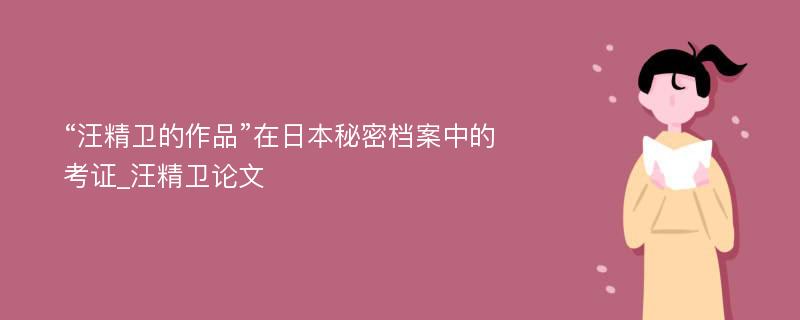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汪精卫论文,工作论文,秘档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降日问题,学界研究已经颇为丰硕。但是,日本对于汪精卫所报持的态度、所采取的政策是什么?这一政策又是如何演变的?迄今为止的研究还不能说完满。本文就是针对一份日本方面进行“汪精卫工作”的绝密文书而作的研究札记。
一
在汪精卫及其伪政权史的学术研究中,①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重要的课题。关于汪精卫与日本的关系,学界的各类著作中虽然均有所论述,但是迄今,也还只有一本在当年出版的、并非学术专著的小册子《汪精卫与日本》②以及1980年台湾吴学诚的硕士论文《汪伪政权与日本关系之研究》。关于日本与汪精卫的关系,除了黄友岚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版)略有涉及之外,迄今的代表性论文只有1997年11月于东京庆应大学召开的“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大陆的张振鹍先生的《日本与汪精卫》与台湾的陈鹏仁先生的《日本的对汪兆铭工作》。③前者以汪日之间的条约为主要考察对象,史料上的开拓不多;后者因主要依据影佐祯昭的回忆录,实际上还只是他本人的“汪精卫工作”而并非全部。
在上述有限的学术研究中,无论从汪、日之间的哪个方面,史料的问题一直是最大的制约因素:就中方资料而言,除了台湾的邵铭煌先生出自“大溪档案”的资料外,主要是中方当事人物在事后形成的、并不完整的忆述性资料;就日方资料而言,虽然有一些档案资料被有限地利用,但主要也是日本进行“汪精卫工作”的当事人物的忆述资料。中、日双方当事人物的资料固然重要,但是它们的局限性也是人所共识的。正由于各种中、日文的人物资料庞杂,难以梳理出清晰的脉络,以至于日本诱降汪精卫(汪精卫投降日本)的事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这无疑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因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在国内仅有的一些日本档案资料之外,发现和利用更多的同类资料,应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抗战初期日本官方 (政府、军部)与“民间人士”各方面都从事的“事业”,许多机关和当事人都有各自的记述与说法。那么,日本政府当时有没有统一的说法?这是关乎日本侵华国策的重要问题。
1947年9月,日本外务省文书课记录班整理了一套名为“支那事变”的《外交资料原稿》,共有八部,其中之第六部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经过”,内中之“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经过”,简要而系统地叙述了汪精卫自叛逃到成立伪国民政府的过程,并且附录了大量的外交史料。④外务省整理的这份资料,引起了中国学界灼注意:先是1963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收录的杨凡先生自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翻译的“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就是这份资料;⑤随后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也收录了上述资料。⑥但这份重要资料,仍然有其局限性:在形式上,它并非当时留下的第一手的“外务省记录”;在内容上,它也不是后来中文翻译所误称的“日本外务省向内阁的报告”,而只是战后外务省方面整理的资料而已。
当时的日本政府有没有这样的文书?带着这个线索和疑问,笔者2003——2004年于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期间,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昭和14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⑦与上述资料比较,这份绝密文书,则具有以下特点:
1.就发表的时间来看。1939年12月,日本方面正在由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与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最终于30日签订了被称为“日汪密约”的《关于日中新关系调整的协议》。这个“协议书”签订以后,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日本政府选择这个时机发表该文书,无异于将此前的“汪精卫工作”做一个自我的总结,即所谓的政府“自白”。
2.就发表的机关来看,是“内阁情报部”。 1937年9月25日,近卫内阁在前广田内阁“内阁情报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充、设立了“内阁情报部”,将分别属于内阁各省的情报与宣传等业务,进行了一元化的统一。该部门发表的资料,应该是综合了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部门的相关资料,而代表政府的声音的。由内阁情报部进行表述,无疑就可以统一日本各方的口径。因此,该文书具有权威性和全面性。
3.从“内阁情报部”同期发表的其他资料状况来看,这些资料多数是以内阁各省整理的资料为基础,而最后以“内阁情报部”的名义发表的。笔者因此判定这份文书应该属于外务省方面制作的;⑧而且后来外务省文书课记录班整理上述资料,也非常明显地又是以这份文件为蓝本的。
4.就发表的形式来看。这份文书的原件,不同于内阁情报部同时发表的其他“时局宣传资料”:不但标志有“绝密”的字样,而且没有统一的文书编号,并注明“不许复制”;并特别要求如果以后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文书,该文书必须予以销毁。拓务省在收到该文书后,1940年1月13日,大臣官房文书课长在致管理局长的信函中,强调指出:为了避免损害汪政权的自主独立性、并招致所谓傀儡政府之称号,对于该文书要尽量予以“绝密”的处理。⑨可见,它并非一份一般性质的文书。
有鉴于此,并考虑到迄今中、日学者在有关论著中均未利用过该文书,笔者拟对此进行一些考述与解读,以深入研究日本“汪精卫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
三
1939年12月内阁情报部发表的《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按照日本“汪精卫工作”的全过程,共分为六个部分。在其中大量隐晦的文字表述中,蕴藏着诸多日本诱降汪精卫、扶助其建立傀儡政权的重要史实。兹分别进行如下的解读(以下楷体字体部分,均为原稿之翻译)。
一、汪精卫逃离重庆以前
1.汪精卫运动的发端
汪精卫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当时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蒋介石副秘书长周佛海、江宁县长梅子 (应为“思”——笔者)平等人,主要纠合中坚的文武官员,策划与日本之间进行和平提携。
2.初期的进展情况
(1)本运动的目的是与日本提携、建设新东亚,因此,其纲领是排除共产主义、抗日主义,建立亲日的新生国民党政权,并且首先要实现与日本的和平。他们暗中策动蒋政权内部的要人,并与四川、云南等地军阀密切联系,以逐渐增加其同志。
(2)同时,我方自1938年夏以来,主要在香港及上海两地,与汪精卫方面的代表进行接触,探测其诚意与热情。11月中旬,我方在确认了汪精卫方面与日本提携、迈向重建新东亚的决心以后,表明了帝国对于汪精卫运动亦不惜予以支援的意向。随后,关于日中新关系的调整,提出了下述宗旨:“日中两国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同时,为了解放东亚于侵略势力、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在互相公正的关系基础上进行坚强的结合,发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关系,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目标”。
日本方面关于“汪精卫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的认定,是一个重要的史实和判断依据。这是因为,汪精卫集团之降日的所谓“和平运动”,他们自认为是七七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和平运动”的自然延续,而汪精卫则干脆把蒋介石也拉在了自己的对日求和阵营一边。⑩这是出于其政治目的“贴金”和“陪绑”。
诚然,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最高集团在抗日的同时,也进行了对日本的和平谈判,主要是在南京陷落前后,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而与日本进行的和谈。但是,这种和谈与汪精卫集团后来的对日“求和”是根本不同的,何况日本在攻占南京之后,又单方面终止了和谈。1937年12月21日,近卫文麿内阁决定了《关于日华和平谈判致德国驻日大使的复函》,提出了苛刻的谈判原则和秘密的谈判细目,并迫使中方接受。(11)1938年1月 11日,昭和天皇主持召开了日中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审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其中分别规定了中国中央政府求和、不求和的不同对策;关于中国中央政府求和的对策,继续沿用了近卫内阁的上述决定。(12)1月15日,在日本规定的最后答复期限,中国政府未答复,日本乃认定这是中国政府毫无诚意的表现,进而采取了中国政府不求和的对策。16日,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正能够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18日,又发表了一项“补充声明”:“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定该政府,更加强硬。”(13)近卫第一次声明,实际上是日本的断交与宣战书,随后,两国分别召回了自己的大使。日本单方面关闭了与国民党政府和谈的大门。
近卫声明以后,日本要寻求的“中国新政权”到底是谁?1月18日下午,近卫在会见内阁记者时,发出了如下的信息:“如果国民政府屈服、放弃过去的抗日政策,可以加入新政权。”(14)这是日本第一次表示对于国民政府的诱降政策。它在中国抗战阵营内部的一些不坚定分子中间,引起了对日“和平”的臆想。为了探询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2月25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派遣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潜访日本,到东京与日本高官秘谈。3月10日,董道宁回国,途中又去大连,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晤谈。董道宁此次赴日,探得了某些日本高官的“和平”底牌:影佐祯昭表示期盼中国有一大政治家出马;松冈洋右干脆明指这位大政治家就是汪精卫。(15)这极大地鼓舞了汪精卫集团。随后,就有了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为首的对日“和平”运动。因此,日本方面认为 1938年3月董道宁的访日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最初表现和开端。(16)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开始了协助汪精卫集团的上述和平运动,并以之作为其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方针。(17)
由此可见,汪精卫集团的对日“和平”运动,与国民政府短暂的对日和谈,完全是两码事;汪集团对日“求和”的根源,在于日本第一次御前会议以后的对华政策,而非中国抗战阵营内部的和战之争。这是一个来自日本方面的重要的史实认定。
徐州会战结束之际,近卫内阁进行了改造:5月26日,宇垣一成就任外相;6月3日,板垣征四郎就任陆相。军方出身的宇垣一成,是以“视情况取消1月16日声明”作为一个条件而入阁的。近卫内阁此次改造,实际上等于自我否定了其第一次声明。以此为契机,从6月开始,日本掀起了处理“中国事变”的高潮,企图在年内达成对华战争的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宗武于6月23日秘密东渡日本,在东京逗留了一个星期,与日本的首相、陆相及参谋本部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7月9日回国。高宗武此次私自赴日,得到的是日本方面亟思拉蒋介石“下马”,另推汪精卫上台的策略。(18)其实,这就是当时日本最高当局的旨意:7月8日,日本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决定了《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和《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虽然准备的是对于中国政府的两手策略,但实际上规定的是中国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7月15日决定的《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则是这个对策的表现。(19)
按照促成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日本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抓住了高宗武此人,从这年夏天开始,主要由军方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和香港两地,进行以最终诱降汪精卫为目的的“和平工作”,并将这一工作命名为“渡边工作”(“渡边”系高宗武的日本名字)。在陆军省起草、提交五相会议讨论通过的《渡边工作指导要领》中,日本方面明确提出了“支持汪精卫一派,以摧毁抗日政权”的目标。(20)通过这一工作,日本方面的目的是在继续探测汪精卫集团的“诚意”。因为与此同时,日本也突破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界限,继续与蒋介石集团进行“和谈”:外相宇垣一成主持了与孔祥熙的和谈;日本的“民间人士”也致力于与蒋介石集团的和谈。(21)
受到日本诱降政策的影响,武汉、广州沦陷之后,汪精卫集团的“求和”气焰更加嚣张。(22)到10月底,在重庆的汪精卫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令高宗武、梅思平作为其代表,到上海与日本方面的代表接触。(23)
日本在“中国事变”未能如期解决的情况下,被迫继续调整对华政策,转入了“政略进攻”时期。 11月3日,近卫发表了“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第二次声明,声称:“如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我方并不予以拒绝。”(24)这个自我否定的近卫第二次声明,就是日本加快诱降国民政府内部“和平”分子的对华新政策的信号。
随后,失望于蒋介石集团的日本,11月中旬,表明了对于汪精卫运动不惜予以支援的意向,并加快了“渡边工作”的步伐。11月12-14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今井武夫进行了秘密谈判。11月19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的“重光堂”继续密谈,于20日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并分别向日本政府和汪精卫进行了报告。如果说以前日本还在探测汪集团的和平诚意,被称为“重光堂秘约”的这个协议书的签订,使得日本方面最终确认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合作的决心。(25)
日本方面得到了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的工作报告后,11月30日,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在上述协议书的基础上,决定了《关于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提出了日中两国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对华政策目标。(26)日本对于汪精卫的政策,已经从以前的“谋略”正式上升为日本的国策。
与此同时,汪精卫在重庆得到了梅思平的报告后,12月1日,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答复日本:汪同意在上海的协议,拟于12月5日离开重庆,如果困难,延期到20日。日本方面4日答复:相约在汪精卫离开重庆后,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27)
汪精卫为什么逃离重庆、叛国投敌?一直是汪精卫研究中的重要环节,时人和后人多有论争,但这些论争几乎都是单从汪精卫一方来解读的。上述文书的记载及有关史实的解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来自日本的另外一个视角: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对华政策,以及近卫第一次、第二次声明的发表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就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因此,日本的诱降政策,应该是抗战初期怀抱民族失败主义的汪精卫集团投降的主因和动因。只要日本存在这样的政策,即使没有汪精卫,中国照样还会有李精卫、张精卫之流。
二、汪精卫逃离重庆及在河内的工作
1.逃离重庆
(1)与此同时,在重庆,伴随着该运动的发展,蒋介石方面的压迫也逐步增强。汪精卫一派,由于逐渐感到身边的危险,从事工作的核心人员自 12月上旬以来,就开始了将工作据点转移他处的实际准备;首领人物汪精卫于12月18日逃离重庆,经过昆明,到达了河内。至此,该运动进入公开化。
(2)恰在此时,近卫首相12月22日以谈话的形式,向国内外表明了关于调整日中关系的政府方针。
2.在河内的工作
(1)汪精卫12月28日向重庆政府发出了对日和平的建言,接着于12月30日发表了反共和平的声明,公开了他的上述建言,并向中外表明了他的主张。
(2)随后汪精卫继续在河内多次发表声明,阐述他的主张。同时,指挥香港、上海各地的同志,继续开展工作。
还在重光堂密谈时,汪精卫方面就向日本提出:在宣布“起事”以后的最初阶段,希望日方不要过分宣传对于汪氏等的支援,以免使汪精卫陷于“汉奸”的不利境地。(28)因此,在汪精卫逃离重庆到河内的时间里,除了近卫首相应约于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声明之外,这份文书只有汪精卫自己不断进行工作的记录,以证明这是他自己在搞的运动。
实际上,在汪精卫于河内公开投敌期间,日本方面尽管政局变动(1939年1月5日,平沼骐一郎内阁上台),但仍然延续了近卫内阁的对华政策,继续加强了第二期的“渡边工作”。除了军部和“民间”的力量之外,日本外务省、兴亚院等方面也开始了与汪精卫运动发生联系。日本方面之所以将这些工作暗中进行,或者做而不说,除了汪本人的上述要求之外,主要考虑是:“如果过早地暴露日本方面和汪精卫的关系,反而会使功名心强的中国人走到相反的方面去,因此,应将汪精卫和我方的关系,秘藏于当事人的心中,不使中国民众得知。”(29)所以,这期间,一方面是汪精卫的公开投敌,一方面是日本的若无其事。双方心照不宣,无需要特书了。
为了避免予国人以“汉奸”的形象,汪精卫在河内期间,主要策动西南的地方实力派,企图在重庆之外,建立自己的势力。但是,他错误估计了中国抗战的形势,“登高一呼”并没有产生轰动效应,反而受到了国内的挞伐和中国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日本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虽然部分重复了“重光堂协议”的内容,但在日军两年撤军这个汪精卫方面最为关心的重要问题上,却没有采纳。姗姗来迟的近卫第三次声明,由于是根据该御前会议的决定,也根本没有提及汪精卫方面所期盼的日本撤军的问题。对此,“重光堂会谈”的主要当事人高宗武开始对日本产生了怀疑,他甚至于建议日方最好以蒋介石收拾时局。日本由此对于高宗武也产生了怀疑,他们避开了高,而直接到河内与汪精卫接触,并且策划汪精卫逃出河内,前往上海。(30)
不可能得知日本第二次御前会议情况的汪精卫,从近卫第三次声明中也感觉到了日本态度的变化。但是,在自己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他也只好半推半就地继续投入日本的怀抱。
三、汪精卫逃离河内到来朝
1.逃离河内
然而,即使在河内,重庆方面的压迫仍然日益激烈,以至于心腹曾仲呜被暗杀。汪精卫等难以继续居住,乃于4月25日暗中逃离河内,5月8日到达上海,居住于租界外的我军警备区域内,其同志亦逐渐在上海集中。
2.汪精卫来朝
汪精卫到达上海后,认识到今后的工作除非与日本紧密联系、并在其支持下公开施策,否则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为此,他认为必须自己亲自来朝,与日本方面中央部门直接会面,坦承其理想,5月31日,携带了高宗武、周佛海、梅子[思]平等幕僚,来到了东京。
3.来朝中的行动
汪精卫在日本约二十日,其间,与平沼首相、近卫前首相、陆海军、外务、大藏各相进行了会谈,结果对于我方关于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意向,充分予以谅解,表达了诚意,并发誓将尽瘁于中央政府的建立工作。同时,他也感激于各大臣的鼓舞与激励,对于工作前途怀抱了更大的希望。6月18日,离开东京。
曾仲鸣被暗杀后,汪精卫在河内岌岌可危。日本首先决定到河内营救汪精卫。影佐祯昭回忆:板垣陆相命令他到河内营救汪精卫,影佐建议组成由陆军、海军、外务省、兴亚院、民间人士参加的集体行动;后来经过五相会议的决定,海军派遣了须贺彦次郎、外务省与兴亚院派遣了矢野征记,民间人士为犬养健。按照汪精卫的意见,他们把他营救到了上海。(31)可见,让汪精卫自河内逃亡上海,本是日本的国策行为。(32)
就汪精卫而言,他在河内,还有些可以与日本讨价还价的资本,但在他亡命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他的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了。而这本是日本方面所希望的局面。
到上海后,日本方面送给汪精卫一个“竹内先生”的日本人化名。由于可以面对面地直接进行“竹内工作”,日本先前的“渡边工作”也到此结束。
在日本人的工作下,汪精卫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认识到今后的工作除非与日本紧密联系、并在其支持下公开施策,否则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为此他选择了直接到东京上朝,与日本最高当局的人物会面。5月31日——6月18日,汪精卫在东京滞留近20日。为了有备而往,汪精卫在出发前的5月28日,就向日本单方面提出了他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33)
为了应对汪精卫的突然造访,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分别命令其驻华官员,迅速赶回东京与中央机构商讨对策。6月3日汇总了各方意见后,5日由板垣陆相向政府提出了方案。内阁于6月6日召开了“五相会议”,决定了《新中央政府的建立方针》,规定将来的中国“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成政权以及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构成,构成分子应该预先同意关于日中新关系的调整原则;同时,还决定了一份附件《“汪”工作指导腹案》,提出要使汪精卫服从日本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同时也要让他畅所欲言,“给予其前途光明和绝对被信赖的印象”。(34)日本政府匆忙之中作出的这个重大决定,并没有完全理会汪精卫的要求,而只是要他服从日本的方针,即汪精卫所不知道的去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而并非作为汪精卫逃离重庆之依据的“重光堂协议”,而且汪精卫也不是日本将来构筑中国“新中央政府”的唯一人选。
根据这样的方针,6月10——15日,日本现内阁的五相(平沼骐一郎首相、板垣征四郎陆相、米内光政海相、石渡庄太郎藏相、有田八郎外相),以及近卫前首相,分别与汪精卫进行了会谈(与板垣征四郎陆相会谈了两次)。为了让汪精卫有得而归,6月16日,五相会议就汪精卫事前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以及日本方面的意见,达成了“大致无异议”的谅解。(35)
汪精卫的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了。此前专注于从事“汪精卫工作”的日本参谋本部也认为:由于汪精卫此次访日,该工作进入了转折阶段,即由过去的“秘密策划”变为“公开策划”。(36)
四、从回国到前往广东
1.与临时政府、维新政府首脑的会谈
汪精卫回国途中,在天津与王克敏等临时政府的要人、在上海与梁鸿志等维新政府的要人,围绕收拾时局、建立中央政府问题,进行了会谈,恳请其予以合作。两方都表示了体谅汪的真意、合作以应付时局的意向。
2.在上海工作的进展
同时,汪派在上海,成功地将根据地设于公共租界内,为了公开推进其工作,将《中华日报》复刊,或者通过广播发表他们的主张,首先开展了活跃的舆论战。
3.访问广东
汪精卫继续前往广东,在华南派遣军的指导援助之下,从事华南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8月14日,离开广东回上海。
汪精卫自日本回国,踌躇满志,经过与华北、华中伪政权人物的面谈之后,7月9日,在上海的《中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两份文件《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敬告海外侨胞》,(37)这是他与国民党当局断绝关系、走向卖国投敌的“声明书”,也是向日本方面首次表明了他要收拾中国时局的态度。
7月14日,汪精卫授意褚民谊去拜访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科尔,认为自访问东京之后,他尝试进行“和平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对此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科尔则认为:汪精卫已经陷入了他所希望避免的罗网,实质上已经成了一名日本的囚徒。(38)这位第三国的旁观者一语道破汪氏的处境。
汪精卫组建伪中央政府的工作是艰难的。因为日本方面的既定方针,是并不以他为唯一的人选,也不是以他为主,而只是一个在华伪政权的联合体。因此,汪精卫也必须适应日本的需要,在努力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一方面继续做华北、华中的伪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的工作,一方面配合日本,拉拢吴佩孚,企图实现汪、吴合作。(39)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为了分裂、打击重庆政府,还要继续利用汪精卫最后的一点利用价值,以榨干其最后一滴血。那就是策动汪精卫南下广东进行“访问”,在日本华南派遣军的指导援助之下,从事华南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8月,汪精卫在广东,与华南派遣军司令官达成了协议,企图建立华南政权,主要是促使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与日军合作,并将这一运动扩大到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推翻重庆政府。(40)这些工作曾经是汪精卫在河内未完成的任务。汪精卫与日方达成工作协议后,本人先回到上海,继续协助日方指导华南工作。原来,日本在1939年2月占领了海南岛之后,继续伺机南进,而“华南工作”却是日本的薄弱环节。在这方面,汪精卫自有其特殊价值,日本人并未健忘。
五、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译略——笔者)
六、尔后工作的进展情况
1.对于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9月19日开始,历时三天,汪精卫在南京会见王克敏、梁鸿志,具体协商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问题,结果,三方决心更加紧密地合作,致力于建立新中央政府。
2.对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工作,大致看来进展顺利。
3.军事工作指向有反蒋倾向的非中央军,眼下正在努力开展之中。
4.此外,汪精卫在阿部内阁更迭之际,为了与我政府中枢进行联络协商,10月2日,派周佛海到东京。周佛海连日与政府要人进行会谈,再次确认了帝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之后回国。
帝国政府根据1938年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的方针,应对处理上述汪精卫方面的运动,决定所需要的指导方策以及帝国对于新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导汪精卫及其既成政府等。与此同时,为了建立新政权、保障其发达强化,帝国目前正在进行折冲之中。
1939年8月底9月初,汪精卫集团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伪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一中全会”。这期间,8月30日,日本的陆军大将阿部信行组阁。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当局决定了“不介入欧洲战争,致力于解决日华事变”的方针。为了加快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在吴佩孚出山渺茫(12月初,吴氏暴死于牙疾)、对重庆工作收效不大的情况下,被迫加快扶植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这是日本政策的重大变化,其重要表现就是促使其卵翼下的临时、维新两政府的首脑,与汪精卫展开合作。
汪精卫趁机继续向日本提出希望和要求。继6月15日他本人在东京提出《对日本实行尊重中国主权原则之希望》后,9月,他又提出了《有关新中央政府财政问题对日本方面的希望》、《希望日本方面考虑之种种事项》,并准备派周佛海携带这些文件,以庆祝阿部内阁成立为名义,赴日进行协商。(41)10月1日,周佛海与董道宁一起赴日,他还携带了汪精卫的大量亲笔信:致阿部总理及其他全体阁僚一封;致阿部总理、陆、海、外务、大藏各大臣每人一封;致近卫、平沼、米内、有田、石渡等前任大臣每人一封;致柳川总务长官、铃木政务部长各一封。如此大量携带的汪精卫亲笔信,简直就是汪与日本高层的第二次“笔谈”。日本方面则在9月30日就拟订了《关于周佛海的接待要领》,决定了“各大臣对于汪精卫方面迄今为筹建新中央政府的努力及其成果,表示慰劳”的方针,以及“帝国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政策并无变化,汪精卫方面不必疑虑”的应对要领。(42)周佛海在东京十几日,他与日本政府要人进行了会谈,再次确认了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支持决心。
周佛海回国之后,10月30日,日本兴亚院的连络委员会决定了对于汪精卫的上述全部要求与希望的答复文件以及《关于新中国国旗的文件》。11月1日,兴亚院会议决定了《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43)这些文件,表面上是在答复汪精卫的要求与希望,但实际上,是按照去年11月30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而确立的对于即将成立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政策。
按照上述文件,日本在上海开始了与汪精卫集团的正式谈判。11月1-12日,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日本“梅机关”,与以周佛海为首的汪精卫集团进行了关于调整日中国交原则的七次会谈。12月18-24日,根据海军省的训令,须贺彦次郎少将与周佛海之间,又进行了关于海南岛问题的六次会谈。在上述会谈的基础上,12月30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梅机关之间,签订了《关于调整日中新关系的协议书》,即“汪日密约”。这个条约,是在汪精卫政权尚未成立以前,日本强加给汪精卫集团的;汪精卫集团放弃了“重光堂协议”之后,又被迫签订了这个“卖身契”。
四
关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如何评价?迄今绝大多数的日本学者均认为这属于日本的“谋略”,中国学者虽不赞成,但也缺乏足够的论据,而台湾的著名专家陈鹏仁先生还认为:“日本对汪精卫的工作,始于谋略也终于谋略,只是汪和影佐祯昭之间相互欣赏的产物。”(44)通过对于上述文书的考述,笔者最后想指出的是:如果就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以及高宗武、周佛海、汪精卫等人物之间所进行的个人工作而言,可以说是日本的“谋略”;但是,如果就日本最高统治集团(政府与军部)与汪精卫叛国集团之间的关系而言,“汪精卫工作”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只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而已。对此,当时的日本官方就发表过如下的见解:
1939年7月12日,有田八郎外相致日本驻欧美各国大使的函:
自去年春天以来,主要由参谋本部秘密进行的通过汪精卫一派脱离国民政府而摧毁蒋介石政权的工作,自12月18日汪精卫成功逃离重庆而告一段落。……此后,该项工作终于发展为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工作的形式,因而作为我对华根本国策之一,在有关省、部的密切合作下,开展各项工作。(45)
1940年1月13日,拓务省大臣官房文书课长致管理局长的函:
对于汪精卫的工作,既具有作用于瓦解重庆政府的策略性质,也是自近卫内阁以来三届内阁所实施的最高国策的产物。为了理解这样的宗旨,故有本文书之制作。(46)
注释:
①1999年底以前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欧美学者的研究状况,有关专家曾经进行过详细的介绍:蔡德金:《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研究概略》,《中国研究月报》(东京)1996年2月号;余子道:《回顾与展望:建国以来的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邵铭煌:《台湾地区汪精卫政权史料与研究》,《中华民国史专题第四届讨论会报告论文》,台北“国史馆” 1997年12月版;许育铭:《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②青韦编,1939年8月版,出版地不详,上海图书馆藏。该书收录了37篇文章,从其全部内容来看,显然属于当时的宣传品,学术价值并不大。
③[日]卫藤沈吉编:《共生から敌对へ——第4回日中关系史国际》シンポヅゥム论文集》,东京东方书店2000年8月版,第547-596页。张振鹍的论文,后来又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 1999年第1期。
④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30:《支那事变关系一件》,第二十七卷。
⑤1964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汪精卫卖国投敌资料》(内部资料),收录的更加全面(第1-17页)。
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6页。
⑦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6.1.1.9:《支那事变之际新支那中央政府成立一件》,第一卷。
⑧1939年7月12日,有田八郎外相致日本驻英、美、德、法、意、苏各国大使的信函称:汪精卫工作有涉及军事机密之处,其内容望绝对予以保密;但是,今后将作为具体事实而公诸于世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6.1.1.9:《支那事变之际新支那中央政府成立一件》,第一卷)。可见,外务省当时已经准备在适当时机公布有关事实。
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6.1.1.9:《支那事变之际新支那中央政府成立一件》,第一卷。
⑩最明显的表现是汪精卫于1939年3月27日在河内发表的《举一个例》,把他的向日本求和,上推到1937年12月6日在汉口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会议的决定。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 156页。
(11)[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380-381页。以下简称《主要文书 (下)》。
(12)《主要文书(下)》,第385-386页。
(13)《主要文书(下)》,第386-387页。
(14)[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日新闻社1975年版,第479-480页。
(15)邵铭煌:《直蹈虎穴秘档——解读董道宁战时潜访日本刺探报告》,《近代中国》第137号,2000年6月。
(16)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30:《支那事变关系一件》,第二十七卷。
(17)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30:《支那事变关系一件》,第二十七卷。
(18)邵铭煌:《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秘档——东渡日记、会议记录、个人观感》,《近代中国》第129号,1999年2月。
(19)《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S487,S1110-27,第 184-185页。7月8日的决定,部分修改之后,又于7月12日正式决定。
(2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30:《支那事变关系一件》,第二十七卷。
(21)参见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孔祥熙和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谈判》,《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22)武汉沦陷前后,周佛海的思想变化最为显著,参见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上卷之1938年10-11月间;周佛海:《简单的自白》(1946年 9月于南京监狱),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4页。
(23)[日]今井武夫:《渡边工作的现状(1)》,1938年11月15日,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页。
(24)《主要文书(下)》,第401页。
(25)《主要文书(下)》,第401—404页。
(26)《主要文书(下)》,第405—407页。
(27)[日]今井武夫:《渡边工作的现状(3)》,1938年12月6日,《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97-298页。
(28)《主要文书(下)》,第404页。
(29)[日]今井武夫:《渡边工作的现状(4)》,1939年1月15日,《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04页。
(30)《渡边工作(第二期计划)》(1939年2月)、《渡边工作现地报告》(1939年5月15日,矢野征记),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 1.0.30:《支那事变关系一件》,第二十七卷。
(31)影佐祯昭作、陈鹏仁译:《我走过来的路(二)》,《近代中国》第110期,1995年12月。
(32)[日]户部良一:《汪兆铭のハノィ脱出をめぐって——关系者の回想と外务省记录》,《外交史料馆报》第19号,东京,2005年9月。
(33)《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64-69页。
(34)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30:《支那事变关系一件》,第二十七卷。
(35)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o.30:《支那事变关系一件》,第二十七卷。
(36)[日]《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12页。
(37)《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177-185页。
(38)《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科尔的私人记录》(1939年7月14日)、《克拉克·科尔从上海发至英国外交部的电报》(1939年7月24日)(FO676:410),[加拿大]大卫·巴雷特著,单富粮译:《英国外交档案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及汪政权的部分历史档案文件》,《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
(39)重庆市档案馆:《日、汪、蒋拉拢争取吴佩孚情报一束》(1939年),《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3期。
(4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6.1.1.8-3:《支那中央政权树立关系》,第四卷。
(41)《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408-415页。
(42)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6.1.1.8-5:《支那新政府树立关系一件(汪精卫关系)》,第一卷。
(4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30:《支那事变关系一件》,第二十七卷。
(44)陈鹏仁译著:《汪精卫降日秘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书后语。
(45)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6.1.1.9:《支那事变之际新支那中央政府成立一件》,第一卷。
(46)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6.1.1.9:《支那事变之际新支那中央政府成立一件》,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