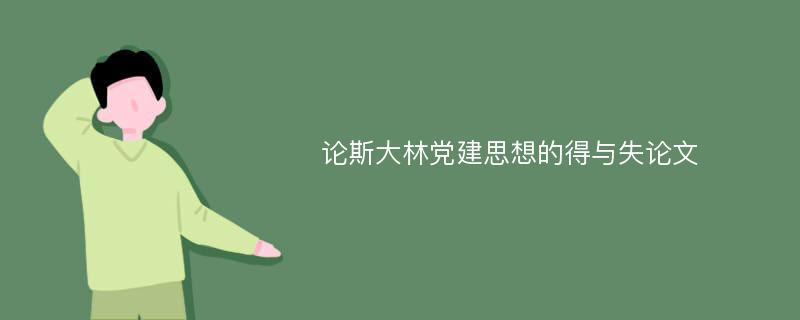
论斯大林党建思想的得与失
斯 钦
(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生工作处,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 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之一,对20世纪人类历史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极具争议性的领袖人物。在其担任苏联共产党领袖30年里,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也是这一理论的真正实践者。本文从得与失的视角评析斯大林的党建思想。斯大林比较全面正确地继承了列宁党建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较为系统的党建思想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实际相结合,进行了理论和制度创新,在执政党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效。同时斯大林党建思想中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离,革命思想压倒执政意识,混淆了“领导”与“执政”功能,党群关系紧张与变形等问题,这严重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斯大林党建思想的得与失,对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执政,怎样执政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斯大林; 党建思想; 得与失
斯大林的党建思想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产物。在继承列宁党建思想的基础上,斯大林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斯大林的党建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特征。
一、比较全面继承了列宁党建思想的同时 又有某些偏差与误解
作为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斯大林虽然继承和发扬了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但实际上二人之间关系非常复杂。甚至列宁在病逝之前还提出要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尽管未能成功,但这无疑给二人之间的关系平添了许多猜测。斯大林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最忠诚的学生,有人赞同,有人否认,更直接提出斯大林并不是列宁选定的最理想的接班人,甚至有人认为斯大林背叛了列宁[1]30-33[2] 19-36。但总体而言,尤其是在党的建设方面,斯大林对列宁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继承,不仅与同时代的其他所谓的“列宁的继承人”相比,还是与斯大林死后继承其位置的后来的几位继承者相比,都是他们难以望其项背的。有人说:“在领导苏共近30年的实践中,斯大林运用和发展列宁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执政党建设理论,大胆探索、不断突破,其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贡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3]
从某种角度而言,斯大林一生都坚持客观认识自己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把自己放在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的地位。从1905年与列宁见面后的20多年里,他一直是列宁忠诚的战友。斯大林在1924年1月26日全苏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4]169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坚持并丰富了列宁一系列的党建思想。在党的性质上,列宁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对此,党内外不少人对列宁提出了批评,但斯大林却坚持捍卫了列宁的这种看法。他指出:“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4]261斯大林坚定地支持关于在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指出这是列宁主义的精髓和核心所在,他说:“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4]398-399后来,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多篇文章里,继续进一步阐述并发展了列宁的党建思想,并提出了自己许多有见地的思想。比如在党的组织性质上,斯大林非常认同列宁关于党“并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5]252的论述。
在实践中,斯大林不仅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还对这个理论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列宁提出的,在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作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作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4]263可见,在继承列宁思想的基础上,斯大林把对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水平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可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斯大林都无愧于为列宁的接班人。
3.3.1 人体产热和散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在产热相对恒定的状态下,控制人体散热(传导、对流、辐射和蒸发)就具有重要意义,必要时采取主动加温措施以保证体温的恒定。本研究中,常规保温组虽然采取了一些的保温措施,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但这种作用比较微弱。由于术前用冷消毒液消毒皮肤,消毒液挥发时带走皮肤表层大量热量。同时,麻醉开始后,由于麻醉药和肌松剂的作用抑制产热和血管收缩作用,
在这一逻辑的推演下,“消灭富农”的口号不断升级,苏共对农民进行了无情的剥夺,并利用强大的政治压力把农民并入集体农庄。这直接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农业生产的大滑坡,造成了一系列悲剧,导致了苏联人口的减少。而且在“向资本主义进攻”的口号下,1930年联共(布)决定提前终止与外商签订的租让合同,彻底消灭国家资本主义因素。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造成了在党建思想上的严重滞后,不但不能适应现阶段的新任务,反而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斯大林不仅在党建理论上与列宁一脉相承,而且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体制建设上,他们也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正如吴恩远转引俄罗斯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中的一段话所指出的,苏联体制“基本成分是在1917-1920年间产生的,1920年经历了某些变化,在1930年代末期最终形成。这个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共产党是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党领导政府(苏维埃),承认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群众工会组织(工会、共青团等形式)被视作共产党影响非党群众的工具;权力镇压机构;国家机构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管理;党和国家的众多宣传机构力图使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8]14-15
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党建思想体系
三级管理机构是涉及到学校的各个学院、校办企业等,如学校后勤部门、车队、出版社、企业等。各个单位有一定的自主权,具有较大的资产处置权限。其基本职责主要有:(1)贯彻执行学校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同时制定适合本单位的管理细则与办法;(2)具体掌握本单位国有资产的分布情况,健全相应的国有资产档案,防止资产流失;(3)负责本单位的国有资产的培训使用和监督管理,提高资产利用率;(4)具体管理本单位国有资产的采购论证、维护、报废与变卖工作;(5)加强本单位科研成果的转换工作。
在党建的指导思想上,斯大林始终认为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他也指出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又必须是不断发展的,而不是故步自封的。在这里他特别突出了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出要按照列宁建党原则来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使苏联共产党在本质上成为一个战斗的、革命的、随机应变的无产阶级政党[4]60-261。此外,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工作思路和总体布局,他指出:“我们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任务是:(1)把党的理论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2)在党的一切环节中加强思想工作;(3)在党的队伍中不倦地宣传列宁主义;(4)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党组织及其周围的非党积极分子;(5)不要掩饰而要大胆地批评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6)不断地揭露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体系及其残余。”[9]341-342
斯大林在1937年《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中再三强调:“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11]129必须承认的是斯大林错误估计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把本来的矛盾扩大化,使苏联肃反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从6个方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进行了论述:“(1)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2)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3)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4)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5)党是意志的统一,与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6)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其来的。”[4]261-271通过对无产阶级政党特点的总结,斯大林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命题。这个命题不仅科学阐明了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而且提出了党建的内容、途径和方式。
自从2004年国内初步接触到机构知识库,我国高校图书馆在机构库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机构库的建设内容和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高校机构库的整体建设并不乐观,机构库要想健康发展,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和障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斯大林在《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和德国共产党党员赫尔措格的谈话)中,指出各国共产党要彻底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议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2)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5)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8)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9)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11)“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4]311-313
这些基本条件的提出,实际上细化了斯大林党建思想的基本原则,为党建工作提供了明确而又细化的可操作性方针和措施。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斯大林又对苏联共产党的党建原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明确和深化,还把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指导思想、革命胜利的方式、组织建设、工作作风、群众路线等六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党建方针和政策。
三、革命思想压倒了执政意识
斯大林的党建思想虽然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执政意识淡薄就是斯大林党建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虽然苏共早在十月革命中就已取得执政党的地位,但在潜意识上仍然把自己定位在“革命党”的认知层面,未能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斯大林建立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这是一个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与机会主义彻底决裂,在思想上和队伍上保持纯洁性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进的、有组织的战斗部队等等。他主张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要成功,必须要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来实现[10]134。在1937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上,赫鲁晓夫清楚地表达了斯大林这方面的思想,“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所以我们应该……动员全党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彻底消灭想阻止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阶级敌人、所有右和‘左’的残余和各种各样的其他机会主义者”[8]14-15。
由于纳入的文献样本量少,异质性检验则采取了I2检验的方法,该方法可以利用自由度修正计数对Q值的影响,而且数值大小不会随着数目变化而变化,异质性检验结果也更为稳定可靠。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无差异,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但鉴于本分析的样本量较少,结果有可能掩盖了一些潜在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对于后续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可能更应该关注药物联用后的安全问题。同时,由于文献质量不高,虽然进行了偏倚分析,但只限于发表偏倚,研究强度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建议应谨慎接受本研究结果,临床在利用此结果指导实际应用时,本研究仅作为参考。
斯大林不仅继承和丰富了列宁的党建理论,更重要的是他把马列主义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党建思想体系。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和谈话中,斯大林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党建理论,科学地说明了进行党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客观地总结了苏联党建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经验、方式及途径。这些论述从宏观上完成了对党建理论的阐发,初步形成了内涵博大精深的斯大林党建思想,其中的精华部分现在仍然被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遵循。
虽然苏联当时已经进入相对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但是在继续革命理念的指引下,苏联一边大规模开展工业化、五年经济计划、农业集体化等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搞政治运动。革命成为那个时代苏共特殊的烙印,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地使用“进攻”、“退却”、“阵地”、“堡垒”、“人民敌人”、“反党集团”等革命词汇。在斯大林的思想中,这些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庇护下成长起来,它们包括“耐普曼”和富农,并培植了他们党内的代理人布哈林集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革命对这些人发动进攻。
在革命特殊时期,有些做法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苏共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时,苏共所应考虑的不应该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而是应该考虑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执政的问题。列宁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对执政党建设进行系统的论述,因此斯大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理论上的阐述和回答。但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概述的党的6个基本特征,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执政党的地位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种种理论误导和实践错误。
“党是工人阶级部队”,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正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认识的那样,党的先进性并不是抽象、绝对的、固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变化的、动态的、历史的。列宁所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了一整套革命党所具备的原则、规章和纪律,堪称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典范。但苏共成为执政党后,革命不应该成为党政治生活的主题,探索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如何执政兴国、执政为民,党员干部如何利用好手中的权力,当一个合格的人民公仆,顺利实现一个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就成为执政党建设中毫无争议的主题。
在斯大林的党建思想中,我们没有看到这种转变的痕迹。他仍然主张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把党放在“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的位置。他主张党要领导本阶级的斗争,把党建设成“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队伍”,成为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最高组织形式,领导工会、共青团、苏维埃等非党组织同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旧社会势力做艰苦的斗争。同时为了斗争的需要,党内不允许其它派别组织的存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论述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六个特征中非常明显的一条主线就是党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以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作为主要任务,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在此基础上,斯大林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理论,为党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1926年《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斯大林又对党的领导权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他指出:“‘传动装置’、‘杠杆’、‘指导力量’综合起来就构成‘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列宁语),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日常工作就是依靠这些东西来实现的。”接着他又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作用。”[4]412-413总之,斯大林通过这一系列的文章,科学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这六个基本特征,不但没有反映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任务、目标及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的转变等重要内容,反而刻板要求以革命党的一整套做法搬用到执政时期来,一味强调党的任务是组织队伍,强化纪律,领导战斗,这是斯大林执政理念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12]91斯大林坚持认为“党的当前任务,党的日常工作的政治路线就是: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去反对它的阶级敌人”。提出,“不过还必须使大家不要把这一任务看作临时的、瞬息即逝的任务,因为在我们国内还有阶级、我们还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时候,加强无产阶级战斗准备这样一个任务就应该贯串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9]36。
在农业解决方案中,颇具前景的是创新型数字农业业务,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带来最佳用户体验并增加效率。数字技术的应用在每个地区的需求不一样,数字农业平台涉及的气候数据采集、病害诊断、解决方法推荐等,将会帮助农户更好种植,逐步达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愿景。
在二者的关系上,科索拉博夫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他认为:“毋庸置疑,斯大林认为他是列宁的学生和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承认这一点对他这样一个在个人生活中别无所求同时也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是最高的评价和荣誉。……斯大林一直缅怀列宁,尽管在列宁晚年,他与列宁的关系很复杂,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在领袖墓前发出的誓言。”[6]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不仅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列宁党建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党建思想。莫洛托夫认为,“斯大林不仅仅是列宁思想十分出色的普及者,不,毫无疑问,他还给列宁的理论增添了新的东西。”[7]339理论源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经验,所以不可能十分明确而又具体阐述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建设问题;列宁虽然领导了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但执政时间较短,相比而言,斯大林不仅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而且在理论上不拘陈规、大胆创新,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苏联党建实际情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推进到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斯大林党建思想的一大缺陷,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一味地用“革命”的手段和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教条地搬用马列主义,甚至超脱现实,树立一些不存在的“敌人”,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强制推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后果,必然会导致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给苏共确保执政地位留下了后患。
四、混淆了“领导”与“执政”的功能
虽然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本身所具有历史特征与理论特点也对后来的党建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领导”与“执政”功能的混淆,把个人权力和党的集体领导放在了对立的位置。这一关系的错乱,使其党建思想在一些方面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相对立,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误区。
“党的领导”、“党的执政”虽然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外在相似与内在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重大的区别。从词源学的角度,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在“党的领导”这个概念中,主体是共产党的实体组织,而客体则是人民群众。而在“党的执政”则不同了,执政一般是指“一个政党通过合法的途径在国家权力中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国家权力将自己的治国主张贯彻于国家的政务管理过程中的活动”[13]4-17。从这一概念而言,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委托”,而党则通过国家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群众作为授权者成为主体,是社会的主人,而执政党则成为客体,执政者成为人民公仆,党执政的合法地位需要得到群众拥护和认可才能有效。这对于任何一个存在的政权来说,它的统治都必须需要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一个政权维持长期有效的统治和进行有效治理,保持持久稳定的心理基础。
常书铭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措施保障,切实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领导。新时代对水土保持提出许多新要求,要充分认识做好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扛起水土保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政治责任,围绕新时代水土保持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考核,层层落实责任;要增强本领,强化队伍建设;要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要强化自律,持续改进作风,全力推动全省水土保持再上新台阶。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往往扮演两种角色,具备两种功能。作为领导者,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因此,共产党自然就具备了领导者的资格,也使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合法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党的领导地位不仅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人民群众的选择。对此,斯大林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过:“未必用得着证明:负有领导责任的党不能不考虑被领导者的意志、情绪和觉悟程度,不能不顾阶级的意志、情绪和觉悟程度。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以党的指示代替阶级的意志和行动。”[4]417但在另一方面,斯大林却强调党对政权的绝对领导,他认为:“在苏联,党的最高领导的表现就是没有党的指示,包括苏维埃在内的其它组织都不会做出任何一个政治或组织决定。”[4]415
实施目标管理以来,各科室有意识地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工作,成功申报千人计划学者、长江学者、青年拔尖人才。近几年,医院国家自然基金获得数、资助金额、SCI论文发表数均大幅上涨。2016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2017年,医院在中国科技影响力排行榜中居第33位,较上年上升2个位次。
强调党的领导本身没有问题,但党的领导应该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通过政治上、思想上对人民群体利益的满足而实现的,而不应存在“压制”或“强迫”的手段。而就人民群众与党的关系而言,党的领导只能体现在党服务于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绝不是强制人民群众服从。但在斯大林执政的30年间以及斯大林的著作中,几乎很难看到“执政党”、“执政”这样的词语,更没有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进行明确的阐释。领导人对该问题的漠视,也使当时苏联的学术界很少谈论这个问题。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时存在思想上的一个误区,因为苏联实行的是“一党制”,党的领导也被他想当然地等同于党的执政了。
斯大林对这两个概念的忽视和混淆,使得他一方面片面强调党实行对政府机关及工会等组织的政治领导,指出党的指示应该通过国家机关及群众组织的党员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却提出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要有党的指示,这就造成了在理论中对党政关系的认识混乱。由此可见的是,在实践中,党政职能日益混淆,国家机关的职权日益从属于党的领导机关,甚至形同虚设。这些问题不仅严重挫伤了政府部门的积极性,而且制约了党在国家重大问题中所应发挥的政治领导作用。
哈萨克族小伙阿合力是一名“三支一扶”大学生,他作为活动组成员全程参加了此次活动,在活动前他对每个游戏进行了了解和充分的准备工作。他高兴地说:“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对国学有了了解,也更加喜爱国学,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国语,跟周围的汉族朋友多交流,把国语学好”。□
毛泽东同志认为:“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而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道路不走是不可能的。”[14]548斯大林党建思想在苏联执政党建设中占据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地位,其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要吸取和避免的。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深刻指出:“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前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斯大林党建思想的经验教训固然有其特殊的时代烙印,但对当代执政者而言,更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加强制度建设,转变执政理念,夯实执政基础的丰富的理论遗产和实践经验。
[ 参 考 文 献 ]
[1] 郑异凡. 列宁和斯大林关系的历史真相 [J]. 探索与证明, 2010(7).
[2] 尹彦. 列宁之后有谁接班——比较研究列宁时期的托洛茨基、斯大林 [J]. 东南学术, 2004(6).
[3] 黄涛海.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共产党建设 [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4.
[4] 斯大林选集: 上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5] 列宁全集: 第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6] (俄)理·伊·科索拉波夫. 并不神秘的斯大林 [N]. 苏维埃俄罗斯报, 1998-01-15.
[7] (苏)费·丘耶夫.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M]. 王南枝,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2.
[8] 吴恩远. 苏联历史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9] 斯大林选集: 下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0] 斯大林全集:第1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1] 斯大林文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12] 周尚文, 等. 苏共执政模式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3] 张恒山.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1).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On Gains and Losses of Stalin ’s Party Building Thought
SIQIN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 Stalin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He has had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huma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lso he is a highly controversial leader.During his 30 years as the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h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 Engels and Lenin’s proletarian party theory. Also he was the true practitioner of the theory.This paper evaluates Stalin’s party building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ins and losses.Stalin inherited Lenin's party building thought comprehensively and correctly, and formed his own unique and systematic party building ideological system. Combining Marxism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Soviet Union, Stalin carried out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party.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Stalin’s party building thought, such as the sepa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revolutionary thought overwhelming ruling ideology, confounding the functions of “leadership” with “governance”, tension and deformation of party-masses relationship, which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image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weakened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the party.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studying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Stalin’s party building though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what banner to hold, what road to take and how to govern.
Key words : Stalin; party building thought; gains and losses
[收稿日期] 2019-03-22
[作者简介] 斯 钦, 男, 蒙古族,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A 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9)04--0005--05
DOI: 10.3969/j.issn.1001-7623.2019.04.001
【责任编辑 张晋海】
标签:斯大林论文; 党建思想论文; 得与失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