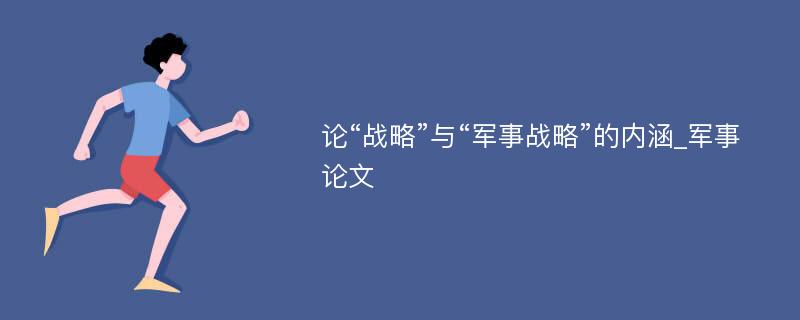
关于“战略”和“军事战略”内涵的浅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见论文,内涵论文,军事战略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化,我国的战略研究空前活跃,探讨战略问题的热潮迅速兴起,都在谈论国家战略、经济战略、政治战略、外交战略、科技战略、军事战略、环境战略,等等。“战略”一词不胫而走,广为流行。因此,对于“战略”的确切涵义进行深入探讨,已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性的问题,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学术分册对“战略”所下的定义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并将“战略”与“军事战略”等同起来。笔者认为这一定义有些过时和老化,需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加以修正。现就“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内涵发表一点浅见,与战略研究界的同行们商榷。
不能照搬60多年前的释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以及《辞海》、《军语》等权威性辞书关于“战略”的释义似均出自毛泽东主席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经典著作。毛主席在该文中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这样的说法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而写的。当时,红军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之中。以革命战争打破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毫无疑问成为当时我党我军全部工作的中心,研究和把握指导战争全局的规律,也就成了我党我军的根本战略任务。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在整个革命战争的年代内,情况都是如此。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我党我军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目标、手段和策略运用都在战争这个压倒一切的全局下有机地统一起来,当时的“战略”自然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战略”与“军事战略”也就难以分家。
然而,机械地把毛主席60多年前对“战略”和“战略学”所下的定义照搬并沿用至今,似不甚妥当。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就已由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也就是说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手段和战略力量建设以及战略方针和战略思想设计和运用也进行了方向性的调整。因此,早在建国初期,简单地把“战略”释义为仅仅研究战争问题,把“战略”与“军事战略”等同起来,已经不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迫近”的看法,肯定“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明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从而将内外政策的立足点真正转到和平建设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战略”乃至“军事战略”涉及的对象和范围已大大超过原来的定义规范,迫切要求对不合时宜的定义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改。也就是说,“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定义乃至战略研究和设计,也应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根据时间、条件、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认为战略仅仅研究战争问题的观点早已过时
从历史发展看,战略早已从单纯研究战争问题扩展到广泛的领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早已不仅仅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而是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宣传、外交、地理等诸战略力量和手段围绕总的国家战略目标的综合运用。这种变化不仅适用于我党我军从革命战争转入和平建设,而且在世界上带有普遍意义。
“战略”(strategy)一词的出现远可追溯到东罗马拜占庭时代。公元578年,东罗马皇帝莫里斯曾编了一本书, 名为《将道》或《用兵之道》(希腊文Strategicon),总结当时的战争经验教训, 用来教育他的高级将领(strategos)。当然,战略思想早于此已经存在, 公元前471~400年间,古希腊名将修昔的底斯曾著《伯罗奔尼撒战记》,是硕果仅存的最古老的西方战史,其中已有较完整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存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 春秋末期的孙武就著有《孙子兵法》,集我国古代用兵之道的大成,不仅是中国最早和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名著,也为世界各国战略界所推崇。《孙子兵法》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理论原则,至今仍保持着不朽的生命力。我国正式出现“战略”这一概念是在西晋时代(公元265~316年),当时的学者司马彪著有兵书,题名《战略》。
应当承认,从《孙子兵法》直到19世纪传统的古典“战略”概念,的确一直与“军事战略”别无二致,局限于研究战争的指导。19世纪,瑞士的约米尼和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总结拿破仑战争和其他欧洲战争的经验,写出了《战争艺术概论》和《战争论》等战略理论名著。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在《战争论》一书中写道:“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是对整个战争的筹划”;而“战术是对某一作战行动的筹划。”这里所指的“战略”实即“军事战略”。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武器的出现和战争样式的变化,战争空前复杂化。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表明,军事因素更明显地受制于经济、政治、科技、心理等非军事因素。这就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战略问题。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1895~1970年)的名著《战略论》,分析了2500年来的大量战例,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不仅提出了军事上的“间接路线战略”,主张把战斗行为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强调用各种手段出敌不意地震撼敌人,以达到不进行决战而制胜的目的;而且提出了“大战略”理论,将“大战略”或“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区分开,成为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大战略”或“国家战略”已不再是一个军事术语,更不只是一个战时概念,而上升为根本的治国之道。美国学者科林斯70年代中期撰写《大战略》一书,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基本定义是:“在平时和战时综合运用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的利益和目标”。这一定义与英国早已使用的“大战略”的内涵基本相同,都着眼于全面协调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以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军事战略也不仅仅是研究战争问题
毫无疑问,军事战略的中心是研究战争的规律,制定“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首先要解决何时、何地、同何种对手打何种战争等关键问题。然而,筹划战时行动并非军事战略的唯一任务。事实上,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对于和平时期如何发挥军事力量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如何增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安全效益和社会效益,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孙子兵法》中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已成为各国战略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核武器时代的“核威慑”、“常规威慑”和“多层次威慑”理论,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在和平时期如何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以确保国家安全目标和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和平时期应维持多大的常备军和多高的军费?如何部署军事力量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威慑”或“国家安全”效益?应当制定什么样的国防发展战略?军队应当如何编组、训练和演习?如何通过显示实力,配合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的运用,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如何发挥军事力量的国内功能?这一系列问题需要不断研究解决。
“军事战略”既是“国家战略”从属的工具,最终为国家安全目标和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服务,又是推行“国家战略”的最后手段,当经济、政治、外交、科技、文化、宣传等其他手段均已失灵,无法达成国家战略目标,无法维护国家安全甚至国家生存时,最后不得不诉诸军事手段的全面运用——战争。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论断“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过去适用,今后仍然适用。
战略的内涵不断扩展
实践表明,战略的内涵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不能不随战略环境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丰富和扩展。战略内涵的扩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战时战略”逐步向“平时战略”转化。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的两大主题。各国特别是各大国都认识到今后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逐步实现由“战时战略”向“平时战略”的过渡,由准备早打大打,转向以综合国力竞赛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就是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霸气十足的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出现连续90多个月的持续增长,与美国从“冷战战略”向“平时战略”转变分不开,从过去重点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转向目前以“经济安全”为中心分不开。克林顿政府正在推行的“塑造—反应—准备”新军事战略,就是建立在判断2015年之前美国不会有“全球性对手”和“全球性军事威胁”的基础之上,重点转向“塑造”对美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当然,这一新战略也不放弃必要时对外作出军事“反应”,如对伊拉克的频频动武,以及对未来可能出现新的全球性对手预做“准备”。
(二)从主要是军事家所关心的事变成政治家和各界普遍关心的事。“战略”走出以战争为中心的神秘殿堂,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内涵,已不仅是军事家的专利,除了“国家战略”成为政治家主要关心的事之外,各行各业都在纷纷制定自己的战略。一时间,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各种“战略”随处可见,出现了“战略泛滥”的倾向,把许多属于战术性、操作性的方法也上升为战略。从这一侧面,也证明弄清战略内涵的必要性。
(三)从方法、策略和手段的运用发展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关于“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的论述,实际上肯定了战略是一门科学,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一论断至今仍有指导意义。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定义只承认战略是一种“方略”,似有不足之处。事实上,战略的制定和决策过程,越来越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需要群策群力,仔细估量种种复杂的战略因素,全面地分析内外战略环境,力求在战略目标、战略力量和战略方针三个战略要素之间取得平衡。国家战略一经制定,将对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发挥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并在执行中经受检验,进行评估和修正。
(四)战略体系日益完备,趋向于多层次和多类别。英、美等西方大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开始分家,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而较为完整的战略体系的逐渐形成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以美国为例,在杜鲁门政府时期(1946~1952年),美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仍混然一体,都是“遏制战略”。直到1987年初,里根政府提出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的多层次和多类别的战略体系才正式形成。从美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一种上下一致、左右配合、地区协调、梯次配置的战略体系,按层次可分为: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按时间可分为:平时战略和战时战略,当前战略和长远战略;按内容可分为: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以及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外交战略、文化战略、军事战略,等;按地域可分为:国内战略和对外战略(国际战略),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等。当然,各项主要战略之下仍可细分。例如,军事战略可包括:威慑战略与实战战略;核战略与常规战略以及非常规战略;军事力量发展战略与军事力量运用战略;进攻战略与防御战略;陆、海、空军军种战略;大陆、海洋、空中与空间战略;欧洲、亚太、中东等地区战略;联盟战略,等。
战略和军事战略释义
综合战略概念的扩展,并参考若干其他国家的定义,“国家战略”似可作如下释义:“在平时和战时,综合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宣传、军事等一切战略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权益和价值观,推进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科学和方略。”
这一释义的特点是:(一)将平时置于战时之前,表明国家战略的运用重在平时;(二)使战略的三要素——战略目标、战略手段和战略方针——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综合发展并运用”,体现出三者之间的和各战略手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三)承认战略既是“方略”,更是“科学”,中心是研究和探求全局性的指导规律;(四)在国家的诸战略手段中,经济被排在最先,军事最后,一方面表明冷战后经济的重要性更形突出,另一方面表明了军事手段仍是其他手段失灵时的最后手段;(五)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可依照战略行为主体的不同和目标、手段的变化,参照“国家战略”定义,拟定其他战略的释义。例如:“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义似可为:“在平时和战时,综合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宣传、军事等一切战略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推进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科学和方略。”“军事战略”的定义似可为:“在平时和战时,通过维持、发展、部署、显示和使用军事力量,确保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科学和方略。”
(本文完稿于199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