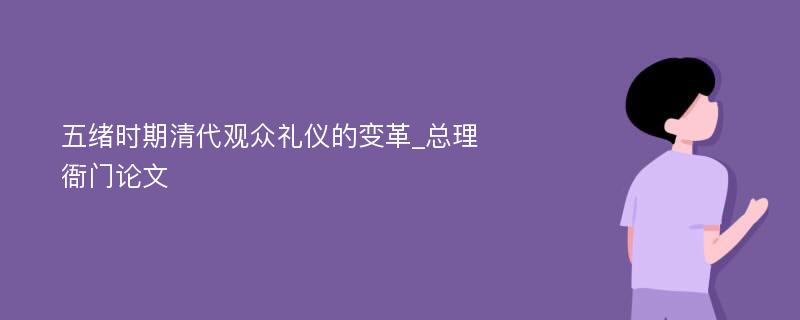
戊戌时期清廷觐见礼仪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廷论文,礼仪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变法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爱国救亡、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百年来,人们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但有关戊戌时期清廷觐见礼仪方面改革的问题,目前尚无文章论及。笔者拟就此略抒管见,以为引玉之砖。
一、传统礼制冰山的消解
数千年来,中国在世界上一直处于政治制度先进、经济发达、思想文化进步的地位,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与周围地区各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藩国家关系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伦理观念、礼仪制度等。按照传统的宗藩礼制规定,中国的官员是不得与外国及外国使臣私自交接的,即所谓的“人臣无外交”。除与中国建立有宗藩关系的外国使臣外,中国的封建帝王是不接见其他外国使臣的。某藩属国使臣若被允准觐见,则必须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近代以前,由于中西交通的不便与阻塞,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不了解世界大势,仍以传统的宗藩观念认识中外国家关系,将中国传统文化圈以外的一切国家,皆错误地看做是不知礼义的化外之夷。东渐而来的西方国家商人、殖民主义分子以及使团官员等,皆被视为向化输诚的“朝贡者”。
19世纪初,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纷纷来到中国国门之外,要求按照资本主义世界的模式与中国建立起国家关系和商务关系。清统治者仍以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些陌生者。最初,清廷对外国人采取不屑一顾的鄙夷态度,既不与外国人,也不与外国政府发生任何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满意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于19世纪40年代以战争的形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与之建立起不平等的国家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等国的全权代表即曾与清廷就觐见清帝及呈递国书之事进行过交涉。后来他们武装入侵北京,强行向北京派驻了公使。从此,中外之间围绕外国驻华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及呈递国书的形式问题展开了长期的礼仪之争,开始了中外外交礼仪艰难而曲折的从对接、错位,到趋同的过程。
1873年2月24日,即同治帝亲政的第二天,英、法、美、俄、 德等国外交公使,一改过去单独交涉而为公使团联衔照会总理衙门的办法,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并面呈国书的要求。3月5日,该公使团再次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入觐一事,“事情切要”,要求清廷与之商定有关觐见事宜。此时,清廷已无充足理由拒绝外国公使的觐见,由此开始了长达四个月之久的外使觐见清帝的礼仪交涉,其焦点是外国公使是否以跪拜礼觐见清帝。在此期间,中外照会往来,反复交涉,折冲辩难,最后以“简明节略”的形式,基本达成有关觐见的共识,但外国方面仍对其中某些条款表示“未足满恰”(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28页。)。
6月14日,清廷颁谕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 住京各国使臣呈请觐见,呈递国书一折,现在赍有国书之住京各国使臣,著准其觐见。”(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23页。)
1873年6月29日,日本国大使副岛种臣以作揖礼, 西方五国公使以鞠躬礼,在紫光阁觐见了清同治帝。
此次觐见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却可以说是自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后中外礼仪之争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清廷虽与外国公使团“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九,29页。),但最后仍是被迫屈从于外国的压力,第一次同意外国公使不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这不但改变了有清二百年以来列祖列宗之“祖制”,同时也改变了数千年来的华夏礼仪“旧制”。中国传统的礼制冰山开始崩塌,但中外之间在觐见礼仪问题上仍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首先是外国公使,特别是新任公使是否具有要求清帝尽早接见的权力。
1873年的觐见之后,外国公使团一直在要求清廷遵照各国惯例,随时接见外国新任驻华公使。而清廷则担心外国公使可能在觐见时提出各种非分之请,许之不可,拒之不便,故而声称:为维护觐见的郑重严肃性,觐见不可多行;外国公使新至中国,不得随来随觐,须如1873年五国公使同觐之例。
1890年,清驻英、法公使薛福成奏陈说:觐见属于交际的范畴,而具体的事务交涉则属于外交的范畴。西方各国皆“厚于交际”而“严于交涉”,“凡各国使臣初到,其君主无不接见慰劳数语,以示优待。使臣鞠躬而退,并不言及公事,此通例也”。外国公使对于“公见不言公事”的惯例,“断无不谙之理”(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九,10803页。), 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对外使觐见一事心怀疑惧。
薛福成的上述奏陈,基本上消除了清廷的隐忧,同时,外国公使又纷纷要求随时觐见。有鉴于此,光绪帝于1890年12月12日颁谕并照会各国公使,表示今后凡外国使臣来华,一律依国际惯例,尽快予以接见,接受国书。
1891年2月27日,经奕劻等奏准,“嗣后, 续到使臣,随到随见”(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附奏折》,外交类,59号。),而不是如1890年所说的“续到各使,按年觐见(即每年的正月岁见)”。自此,清帝随时接见新到任的外国公使,开始作为一种外交礼仪制度规定下来。从此,出现了清廷在外交礼仪方面向国际礼仪过渡接轨的新变化。
其次是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地点问题。
早在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 美等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清同治帝不久,即大呼不妙,颇有为清廷所愚的感觉。英国公使威妥玛提出,紫光阁乃清帝接见筵宴藩属国君主或使臣之地,各国使臣在此觐见清帝,有碍国体。其他各国使臣“为其摇惑,颇多未惬”,多次要求清廷变改觐见地点。
1890年春,德国公使巴兰德首先与总理衙门就此事进行实质性的交涉。各国公使所送的外交节略中也声称:“紫光阁觐见,因有视为不合宜之故,将来觐见、贺年,另指他处”(注:《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四,32—33页。)。同年10月,巴兰德再次向总理衙门提出:今后必须改变觐见地点,其要求“牢不可破”,而各国公使“亦皆附和其议”。为此,总理衙门上奏光绪帝说:“臣等俯查西国通例,使臣所至之国,以呈递国书为通好之据,视为至重,且外国之待使臣,无不亲接国书,加以优礼”。外国使臣此次要求改变觐见地点,只是“拘于成见,并非故意抗违,……措词尚属恭顺,……可否于使臣觐见之时,另易他处,俾释怀疑之见而纾就日之忱”。光绪帝朱批“依议”(注:《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四,32—33页。)。
最初,清廷选择了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奥匈帝国及英、德、比各国使臣都曾在此呈递过国书。但是,1894年法国新任驻华公使施阿兰来华后,向清廷主管外交事务的庆亲王奕劻提出:承光殿“不是位于皇宫以内”,表示自己将不去此殿呈递国书。当时,正值中日战争期间,清廷在外交上需要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因而很快同意将外国使臣觐见清帝的地点改在皇宫内的文华殿。
二、传统观念与现实的冲突
一种社会观念一旦形成,即会对人们产生长期的影响。在中国流行了数千年的“华夷之辨”、“天朝大国”等传统思想,虽在近代受到严酷现实的冲击和挑战,却仍充斥于部分封建统治者头脑之中;传统的礼仪制度虽已崩塌,部分封建统治者却仍企冀维持修复,表现为传统与现实的严重背离与冲突。
众所周知,早在1868年清廷就英国可能提出的修约问题展开讨论时,清廷内部即围绕外国公使是否可以觐见、以何种礼仪方式觐见清帝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讨论,甚至是争论。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广总督李鸿章、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人认为:既然西方各国并非中国属国,自不必在礼仪问题上苛求坚索,可以允许外国公使不行跪拜之礼。但许多顽固而腐朽的封建官僚坚持外国公使必须行跪拜大礼,方可觐见的传统礼制。
1873年清廷与外国公使团就外使觐见礼节进行交涉之时,清统治集团内部又有许多顽固的封建官员以传统礼制的忠实捍卫者自居、自责。翰林院编修吴大澄曾慷慨激昂地说:“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示以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他甚至以不避斧钺,勇撄龙鳞的气慨大呼:“朝廷之礼,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九,41—42页。),意即贵为天子的皇上,也无权更易中华传统礼仪。
1873年外国公使分别以鞠躬和作揖之礼觐见了同治帝,但在有关觐见的其他礼节问题上,清统治集团内部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面对外国公使的不断要求,光绪帝于1889年亲政后,在外使觐见礼仪问题上做了诸如清帝将依据国际惯例,尽快接见外国公使,接受国书等重大变革。这无疑是清廷摒弃传统礼仪,向国际外交礼仪过渡接轨的新举措。光绪帝的上述变革,主要是礼仪觐见程序的变革,而较少涉及觐见的具体礼仪形式,因此尚未引发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1898年4 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围绕接待亨利亲王的具体礼仪问题,清廷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首先,清廷在德国亲王入境后,应由何种级别的清廷官员前去迎接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898年2月8日,德国驻上海领事照会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于亨利亲王路过上海时,两江总督亲自迎送。刘坤一对此颇不以为然,致电总理衙门说:以前俄国亲王路经上海时,系派道员会同关道接待。此次德国亲王来沪,拟派藩司接待,“已较优异”,各国驻上海领事亦“颇以为然”,况且本人“近来多病,步履艰难,不胜此役”,要求总理衙门对德国的上述要求“坚持勿允”(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二十九,12页。)。
总理衙门所要面对的,不仅只是何人在上海迎送的问题,还要解决诸如德国亲王来华后所有路途中的迎送、所乘车轿的规制、至京后清帝的筵宴接见等一系列礼仪问题。为此,总理衙门致电前驻德公使许景澄,向其询问西国通例。许景澄复电说:“遵考西礼,亲王将到,派提督、副将、都司三员先迎于陆境,或舟次。主国亲王迎于车站,同车导至所舍客邸。君主即以是日延见,用客礼。旋偕至外殿内,亲王筵请其从僚。此后,辞行再见,或有事另见,无常例。所派官常值照料。出门则提督陪乘。送如迎礼。”(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二十九,22页。)亨利亲王来华后,清廷基本是按这一复电行事的。
其次,清廷内部在亨利亲王觐见的地点等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最初,清廷拟准亨利亲王乘轿进入东华门(按清制,文武大臣必须于东、西华门外下马、下轿,步行入宫朝见。只有经清帝特许的老臣或勋臣方可乘轿入宫),在毓庆宫内接见,然后于东配殿内设宴款待。但军机处各大臣多有反对。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翁同和认为:如此“优待极矣,然有窒碍”,并列举了诸如殿内供奉有孝敬皇后的御容,配殿极狭隘,无容席之地,乘轿进入宫门非礼等五条理由,表示坚决反对。光绪帝对翁同和的反对意见颇为不满,“皆驳之”,并怒责另一军机大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29页。)
1898年5月14日下午2点,亨利亲王乘火车到达北京的马家堡车站。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张荫桓、崇礼等人亲至车站迎接。亨利亲王乘坐绿呢加饰黄绊大轿(1901年议定《辛丑条约》时,外国公使争得了乘坐加饰黄绊绿呢轿进入清宫的权力),在奕劻等人的迎送下至德国驻华使馆下榻。清廷派内务府大臣负责接待照料。
5月15日中午,亨利在庆亲王及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的陪同下, 在颐和园的乐寿堂和玉澜堂先后觐见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清廷考虑到亨利亲王既是德国王子,又是现任德王之弟,“此次来华,有代(德)君相见之谊”,因此,不但光绪帝予以接见,慈禧皇太后亦破例“接待如礼”(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三十二,10页。)。光绪帝接见时,给其以“出御座相见,并于纳陛上赐坐”(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295页。)的优礼,使“亨利坐于右偏,有垫高杌”之上。随后,光绪帝向亨利亲王赠送宝星,设宴款待。应亨利要求,奕劻、李鸿章、翁同和为其题字。清廷设宴款待亨利一行时,采用了“洋乐”。(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47—48页。)
24日下午,亨利乘轿至西苑勤政殿,再次觐见光绪帝。“上御勤政殿,亨利入,摘帽鞠躬,向上立致国电,数语毕。上起立,命之前握手,赐亨利坐,略言谢彼主美意。”(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52页。)
清廷在接待亨利亲王时,虽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礼仪观念,给其以前所未有的外交礼遇,但与西方国家外交礼仪惯例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虽然光绪帝给其以纳陛赐坐的礼遇,但清廷不肯在其觐见慈禧太后时,也给予同样的礼遇。早在亨利亲王未到北京之前,清廷即拟定了慈禧太后“召见德王于乐寿堂,(站)立(觐)见”(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32页。)的礼仪规格。其后,德驻华公使海靖赴总理衙门,要求亨利于觐见慈禧太后时,能得到“赐坐”的礼遇。庆亲王奕劻当面予以拒绝。稍后,翁同和亦再次反对赐坐。为此,慈禧太后传谕:“若必欲坐,只得不见”(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41页。)。数日后,海靖提交了德国亲王觐见慈禧太后的礼节八条,其中一条为:“皇太后自愿赐见亲王,亦应赐坐。”庆亲王表示“此节殊办不到”,并在翁同和等人的支持下,派张荫桓至德国使馆,“与海靖声明,若必欲赐坐,皇太后即不能赐见”。(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43页。)中德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一直争论到5月14日夜,亨利亲王才表示妥协,同意“立见”慈禧太后。5月23日,光绪帝本准备在宫内再次接见即将离京的亨利亲王,翁同和“力言非体(制所宜)。……庆邸有(见)起,复言之”(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52页。),最后,终将接见地点改在了西苑。
由此可见,戊戌年时封建传统礼仪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反对变革传统外交礼仪的力量,首先是来自中枢决策机关的高级大吏,如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和等人。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系恋着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礼仪,而不管其是否适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需要。这一情况显示出清廷外交礼仪与世界的接轨将是何等的艰难,变革者需要具有何等的勇气与魄力。
三、与世界外交礼仪接轨的大胆尝试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进步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在百日维新运动中,光绪帝不但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作了重大的变革,在外交礼仪方面同样表现出了值得肯定的进取变革精神。其主要变革是:
第一,光绪帝决定给呈递国书的外国公使以更为优隆的礼遇。清廷原来拟定的觐见礼节规定:外国公使由清廷有关官员引领,“进文华殿中门,使臣一鞠躬;向前数步一鞠躬;至龙柱间正立一鞠躬。使臣致词,翻译译文各毕,使臣向前至纳陛中阶下,捧国电敬候。亲王一人由左阶下,接受国电,由中阶升至案前,将国电陈于案上,使臣一鞠躬。皇上答以首肯,示收到国书之意。使臣退回龙柱间原站立处。亲王一人在案左跪听皇上以国语传谕慰问。亲王一人由左阶下,至使臣站立处,用汉语传宣,翻译译述”(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附奏折》,缩微1552号。)。但在1898年4月3日讨论俄国公使巴布罗布呈递国书的礼节时,光绪帝主张俄使的国书不再由庆亲王于纳陛阶上、阶下来回转接呈递,而是由俄使直接“上纳陛亲递国电”。光绪帝的这一大胆礼仪变改,当即遭到翁同和的反对。4月5日接见俄使时,光绪帝令俄使上纳陛亲递国书,并“不以国语(即满语)传宣慰问”,而是变改祖制,“宣谕用汉语”。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礼仪变改。为此翁同和在日记中记述说:“此皆前所未有也。”(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29页。)
同年5月17日,光绪帝接见法国驻华公使毕盛时的礼仪变改, 更使翁同和等人惊异不已。光绪帝不但身佩宝星,“特命(法公使)上纳陛致颂词,……上亲宣答词,不令庆亲王传宣”,而且“翻译一人亦上,随递国书于案”。(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49页。)
第二,有鉴于清廷高级大僚对觐见礼仪变革的不理解和反对,光绪帝于1898年6月15日,即颁布变法维新的“明定国是诏”后的第4天,命总理衙门“将各国君后宗藩及特派头等公使来华,于皇太后及朕前接见款待礼节,务须参酌中西体制,详定章程,从优款待”之事,妥议具奏。7月1日,总理衙门上陈《遵议款接外宾参酌中西体制详定章程折》,同日“奉旨依仪”。由此加快了清廷与世界各国外交礼仪的对接过程和同化步伐。
关于款接外国君后及宗藩礼节,总理衙门诸大臣会议后在原则上一致认为:泰西各有约国家君后往来,“悉以敌体之礼相见,款之宫中,迓诸郊外”。由于泰西各国国情相近,“言语、居处、服食无异”,各国皇室间多有姻亲关系,彼此关系较为亲密。同时,各国君主所居宫室又多为楼房,“无重门之限”,因此相互间“款接良便”。而中国情形与西方各国颇多差异,因此在款接礼仪问题上“似难强同”。尽管如此,清廷亦应制定较为合乎西方通例的款接礼节,以尽东道礼宾之谊。为此总理衙门建议:
第一,将北京的某一王公旧府改建为国宾馆,以“备各国君后旅居之用,即王子、亲王亦可于此安憩”。国宾馆的“门楣依旧”,而其内部房室,则“酌照西式装修完美,陈设合宜”,清政府提供各种生活必须品,“凡百从丰”。
第二,外国君后来华后,清帝可设宴款待。款待地点,或在宫中,或在西苑,届时“请旨施行”。今后若仍有类似德国亨利亲王的某国亲王来华,“皇太后、皇上仍照此次款待礼节,毋庸另议”。
关于款待各国头等特派公使的礼节,总理衙门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如其带有国书,专为致贺皇太后、皇上而来,则“请皇太后、皇上均予接见”。
其二,如其仅为两国交涉之事而来,可按过去各使臣呈递国书之礼,由“皇上亲接国书,口敕答颂”;如系头等公使,则“请皇上立受国书,俾与二等公使有所区别”。如果外国使臣欲见皇太后,则可恭请太后懿旨,“届时,由御前大臣与臣等带领该使臣进殿俯首修敬,太后坐受”,亦可“量加慰劳,或赐以珍玩,以作优待之处”。
此时,清廷已认识到中国繁文缛节的传统礼仪,不但不能为清廷争得尊崇荣耀,反而经常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总理衙门在同一奏折中说:泰西各国君主视接见外国使臣为寻常之务,因而并无礼节单之类的东西,只是由专人“接导”。若逢国家重大庆典,也只是向各外国使臣分送一个通知单,“告以齐集宴会日期、服色”而已,其目的“并非律人以步趋、行立、鞠躬之烦”。今后中国遇有庆典,总理衙门亦“拟仿照编送”(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三十二,9 —10页。)。
四、余论
清廷,特别是光绪帝于1898年在外使觐见礼仪方面的变革,虽并非戊戌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但却同样具有值得肯定的进取意义。
首先,清廷觐见礼仪的变革,表现出中国方面的主动变改精神。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渐以来,中外在外交礼仪方面多次发生严重的纷争。到了19世纪末,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清廷在外交礼仪方面作出过许多重大变改。但这一变改并非中国方面通过对中外礼仪的比较、反思后的自我修正改良,而是迫于外国方面政治、外交压力,甚至是武力强迫,无奈退让的结果,带有极其鲜明的屈辱色彩。戊戌年清廷的上述礼仪变改,虽也具有一定的适应外国方面要求的因素,但更多的表现为中国方面为适应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客观需要,而主动变改传统外交礼仪的意识。例如,光绪帝准备变改清廷旧的礼仪形式,允许俄国公使“上纳陛亲递国电”时,翁同和表示反对说:“此次该使并无格外请索,似不必加礼。”光绪帝却认为:对于觐见礼仪的“此等小节,何妨先允,若待请而允,便后著矣,并有欲尽用西礼之语”(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29页。)。也就是说,清廷是此次觐见礼仪变改的主动者。
其次,清廷觐见礼仪的变改,表现出与国际外交礼仪惯例接轨的进步倾向。近代以降,清廷在外交礼仪方面虽也进行过某些变改,但就其变改的方向而言,更多的是向后看,尽可能多地维护传统旧礼仪(坚持传统礼仪与客观上维持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关系,非本文论说主旨,恕不赘言)。而戊戌年清廷的礼仪变改,则更多地注意到了如何与国际外交礼仪的对接问题。光绪帝在命总理衙门妥议日后外国“君后宗藩及特派头等公使”来华后的礼仪时,特别提出了“务须参酌中西体制,……从优款待,一俟议妥奏准,即行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并分电(清驻)各国大臣,令其一体知悉”(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三十二, 9—10页。)的原则,从而表现出较以前迥然不同的礼仪变改方向,与当时国内向西方学习的政治思潮保持了相同的运动方向。
其三,清廷觐见礼仪的变改,在某些具体的礼仪形式上,也特别注意与世界外交礼仪的对接。清廷曾力图删改传统外交礼仪中的繁文缛节,如前所述,总理衙门提出今后凡遇有清帝接见外使或遇国家重大庆典之时,不再向外国方面致送繁杂而又拘执僵化的礼节单,而仅是仿照外国送一普通的通知单。同时,清廷还仿照外国的待宾礼仪,在京城设立“国宾馆”等。
清廷,特别是光绪帝于戊戌年进行的外使觐见礼仪的变改,无疑是符合国际外交礼仪惯例的,因而值得肯定。但是,外交礼仪的变改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和力度,因此不应该是一种个人行为,更不应该带有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光绪帝在接见外使时,某些礼仪的变动,如让外国公使,甚至包括翻译直接登上纳陛致颂词,亲递国书,用汉语而不是满语致答词等,并未就此与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妥议讨论,而是带有强烈的我行我素特点和封建帝王极端专制独裁的色彩。翁同和在日记中记述说:事先只有总理衙门的张荫桓予闻其事,而身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和身为军机大臣、光绪帝师傅的翁同和本人事先“亦不知”(注:《翁文恭公日记》,三十七册,31页。)。这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虽无值得惊异之处,但在客观实践中,却将使具体负责清廷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诸大臣处于一种尴尬被动的地位,不利于清廷的对外交往与交涉。
戊戌政变发生后,百日维新期间的各种新政均遭扼杀,清廷又回复到过去那种极端顽固和保守的状态之中。同时,清廷和光绪帝在戊戌年进行的外使觐见礼仪的变革,也随之出现了逆转倒退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