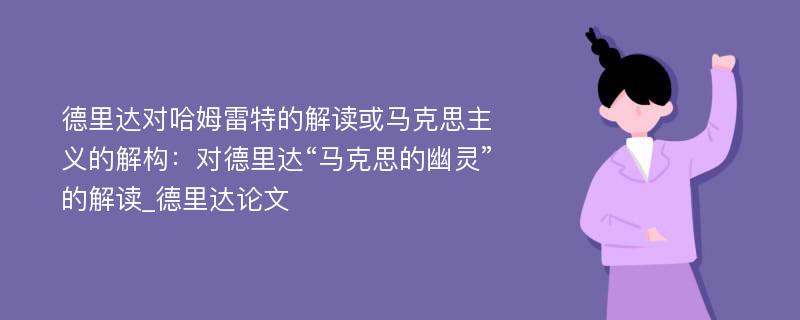
德里达版本的《哈姆莱特》或解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版本论文,德里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幽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5-0091-09
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早已是人人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但是德里达在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们》(尤其是在“马克思的指令”一章)①中给了它一个完全陌生化的、典型的德里达式的阅读,即一种挪用式的解读,抓住文本的几个细节、意象或文字片段,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演绎与连接,由此而让意义转换、扩展、游牧、播撒,直到使如此操作下的对象完全冲破了此前众多评述所构筑的各种阐释篱障,打开出人意料的话语和寓意层面。如此操作之下,他实际上将这部名剧变成了自己的戏剧材料,演绎了一场使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互相渗透、支撑和阐释的说教剧,表达了他本人批判与向往的双向理论运思。
他所批判的是各种版本的“终结论”和“本体论”,前者不仅有福山为美国式自由民主体制高唱赞歌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②还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祛除和围剿的叫嚣。后者不仅有机械论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教条主义,更有学者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谓的科学论调,他们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而将其变成了象牙塔中众多的哲学标本之一,从而消解了它的革命性、实践性。在以上批判的基础上,他向往的是,一种永未完结、总有未来、总有“希望” (promise)的社会空间和允许多元、异质、流变因素并存、因此永远不会走向物化、僵化或集权化的政治与学术空间。
正是在此种意图上,他用《哈姆莱特》剧中的鬼魂为隐喻,通过对莎翁和马克思的几个经典文本的交错解读,③勾勒了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幽灵系谱,演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徘徊学”(“闹鬼学”)(hauntology)或“幽灵政治学”(spectrapolitics)。这可谓一种马克思主义活力论、发展论或永久革命论,即对一种不断颠覆现实、开拓未来的精神的张扬,以对抗于“终结论”和“本体论”。在阐发这整个“幽灵诗学”(spectrapoetique)的同时,他也在分析着象征知识分子的哈姆莱特们、象征学者的霍拉旭们和象征具有指认情结之人的勃纳多和马西勒斯们与马克思这个“归魂”(revenant)人鬼情未了的各种关系,既批判传统知识分子,又呼唤新型知识分子。最后,他更借阐释和挪用《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五场结尾处的名句表达他自己这个解构王子对时代、对马克思关于“变革时代”的指令的思考。
在这整个过程中,他实际上构造了他的解构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以前者激活后者,用后者提升前者,使之成为能够介入当下政治、经济、学术问题的政治学,这也正是他对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何处去”、“马克思主义衰亡了吗”④的问题的有力回答。
一、鬼魂与恶魔,精神与幽灵
为了演绎一个马克思主义“徘徊学”,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中对《哈姆莱特》的借用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他最频繁使用的是第一幕第一场,在“厄耳锡诺。城堡前的露台”。正是在这个看似安然却充满诡异的场景中,被谋杀的前国王老哈姆莱特的鬼魂两次出现,却默默不语,直到见到哈姆莱特时,才带他避开旁人,向他陈述了丹麦国里所发生的“骇人听闻而逆天害理的罪行”,(莎士比亚:97)即他的叔父,现在的国王,是个阴险毒辣的弑君篡位者和丧尽天良的弑亲乱伦者。然后,鬼魂就给了哈姆莱特指令,让他“不要默尔而息,不要让丹麦的御寝变成了藏奸养逆的卧榻”,(莎士比亚:98)而要匡扶正义,重整乾坤。
在德里达看来,鬼魂的出现开启了一个关于复仇和正义的戏剧,如果没有鬼魂的出现,后面的一切事件都不可能,因为正是“闹鬼”(haunting)带来了指令,而发出指令也就是“闹鬼”的内容,鬼魂与指令,形式与内容,两者的结合,给哈姆莱特的心头压上了沉甸甸的责任,让他认识到,事情没有完结,历史没有终结,希望则在未来,但是行动迫在眉睫,鬼魂将会一直萦绕下去,成为一个永久的精神,敦促和激励自己尽早将指令付诸实施。
从这里德里达转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他认为,马克思的灵感来自莎士比亚,他也是将一个幽灵搬上历史舞台而开始了欧洲的伟大戏剧,这个幽灵的名字叫共产主义,对其出现的正式宣告在《共产党宣言》(1847)的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马克思:250)这个幽灵也带着一个指令,就是《费尔巴哈提纲》(1845)那著名的最后一纲(第十一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马克思:19)这个指令开启了另一场复仇和匡扶正义的伟大戏剧,即人类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推翻压迫、争取解放的伟大斗争。
正如老国王的鬼魂,这个幽灵在“还是旧欧洲的厄耳锡诺城堡”上一出现,(Derrida: 10)就引起了惊恐,它遭遇了“欧洲旧城堡中的一帮贵族和教士对它的驱逐,因为它是一种威胁”,因此那些人纠集起来,结成了神圣同盟,“想对令这些主子们彻夜难安的鬼魂发起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征战”,并梦想着用这样的驱逐带来历史的终结,让历史从此停留在资本主义体制,永世不变。(Derrida:40)
于是一时间里,欧洲被资本主义这个魔鬼所折磨,却任其寄居在自己的内部,有多少个革命的转折点都被它所消解,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实践,从莫斯科的审判到匈牙利的镇压,又如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嘲讽的波拿巴那样,也是以革命的名义反对革命,因为它并没有走向自由解放,而是走向了独裁、集权、专制,导致了社会、经济灾难,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种体制的惨败;20世纪80年代,又有推倒柏林墙、苏联解体等事件;而当下的全球化则更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甚或全球美国化了。于是美国自由民主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模式似乎就如日中天了,驱鬼的人们宣称:“马克思死了,共产主义死了,彻底死了,包括其希望、话语、理论、实践。于是可以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了,(Derrida:52)以至于如福山之流迟到的终结论者沉浸在一种欣快症里,继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的“终结”论之后,干脆摆出启示录派的架势,喊出了更多的终结,如“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甚至“最后的人”,因为在他看来,美国自由民主式的社会体制已经是人间天堂,也就是人类奋斗的终点了。
但德里达认为,资本主义,正如克劳狄斯,是个篡位者,异乡客,“并不因为长期住在欧洲人家里就不是陌生人”,(Derrida:4)主人或正统的魂灵正在归途中徘徊,虽然经历着各种遭遇,如追逐、祛除、指认、丧葬,变换出众多不同的形态,但他顽强地徘徊在归途上,这就是希望所在,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所在。所以尽管驱逐活动一直在进行,终结论老调也一直在重弹,但是马克思的幽灵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如老哈姆莱特王的“归魂”,带着指令又回来了,虽然他没有确定的到达日期,但他的徘徊是毫无疑问的,他如老国王的鬼魂一样,从面甲后面注视着他的继承人,让你虽不能确切指认,却不可抗拒地感到一种冥冥中的精神力量,一种弥赛亚的诉求,一种人类经验结构中最根本的愿望的召唤,而且他在眼下再次来“闹鬼”,更带来了一种紧迫感,原因就在于,当下的现状如日中天,这本身就是一种危机,德里达在这个问题上所持观点,用本雅明的语言来概括,即:“灾难——丧失了(革命的)机会;危急时刻——现状牢不可破;(真正的)进步——所采取的第一个革命步骤。”(Benjamin:474)
以这种危机感和迫切感,德里达从表面的“全球化新秩序”中却看到如被篡位者把持后的丹麦国里一样,隐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德里达历数出十大祸患(plagues),如:失业、无家可归、经济战争、贸易保护、外债、饥馑、军火工业和贸易,新一轮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黑手党和贩毒集团,国际法被某种意识形态所把控,等等,(Derrida:81- 84)并认为,悲惨不幸的名单还在扩大,所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执行他的指令,变革世界,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德里达在这里让人想起意大利社会学家法莱罗(Guglielmo Ferrero)对马克思的评价,法氏认为马克思具有末世想象力,只是他把基督教末日的善恶决战战场(Armageddon )搬到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借这个比喻,可以说德里达的善恶决战是在幽灵与恶魔之间,但他把结局无限延宕了,这是德里达的末世论,他强调这种末世论是区别于启示录、目的论或本体论的,因为他的末世论是一种“永久革命论”或“否定的乌托邦”,指的是永远不能满足于或锁定在任何当下,而要锲而不舍地颠覆、批判、超越,永远以“诗和思”的激情朝向未来,打开希望的空间(promise)。而他所说的启示录、目的论、本体论指的是各种论调的终结论,按照那种观点来看待当下的世界,世界已经完成与定格(déjà vu),不再需要未来和希望了。
德里达又称自己的末世论为“未来民主”,“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或者“非决定论弥赛亚”,(Derrida:65)即一种向未来和希望的永远的开放性或绝对的不封闭性。从这种意义上把握“马克思的幽灵”,便要既强调其永远不会到场,又看到其执著的徘徊,这也就是清醒地认识到,它是以一种不在场 (即非教条、非物化、非本体化)的方式的在场,且这种不在场不是否认,而是以极端的方式肯定和强调在一个被权力话语、意识形态把控的单向度社会中这种“徘徊不定”(即开放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这个层面,德里达用两个概念,精神与幽灵,来分解“马克思的幽灵”,他强调:“那精神,那幽灵,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强调这个差异。”(Derrida:6)作为精神,正如萨特的“虚无”,它打开可能性的空间,德里达又称这是一个他者,即不同于当下的差异、对峙、变革的力量,它凝视我们,关心我们,我们冥冥中知道它存在,因为它诉诸我们的欲望,但它的在场方式,却是流动性的,它蔑视语义学、本体论、心理学或哲学的指认,那么它必然打破镜像对称性,消解共时性,它永远不会被锁定在某个知识范式中,正如《哈姆莱特》中国王的幽魂,它是戴面甲或穿甲胄的,这些防护就是防指认、收编、物化的。但这种流动性、变换性、不确定性、未完成性并不是缺点,而正是精神的非凡品质,它不仅要求不断批判与变革现实,也要求理论不断自我批判和变革,以防僵化和教条化。德里达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早就一再表明自己的思想是有历史性的,这就为这种精神做出了榜样,德里达感叹:“谁这样做过?”(Derrida:6)正是在作为一种批判现实、并自我批判的精神的意义上,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要有某种马克思,要有他的天才,至少要有他的一种精神。”(Derrida:13)这里所强调的“某种”、“一种”就是批判和变革的精神。
对这个精神的忘却必然导致幽灵化,幽灵化又是什么?在这里德里达展开了他的幽灵系谱,首先,有那些“超自然、悖论性质的现象性,不可见物的狡黠的和无法把握的可见性,或一种可见物的不可见性”,(Derrida:7)前者就是使精神有了肉身或现象性,将之变成一种体制、一套法规、一种意识形态,如前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正相反,是使实体消失,代之以幻影(simulacrum),幻影本身又变成了一种非实体的感觉物或物化,施展魔力、导致异化,如《资本论》中所剖析的货币交易、市场价值、金钱等。此外,还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那类假革命、画皮、戏仿。再者,一旦权力掌控走向极端,还可能会召回恺撒的幽灵。最后,甚至还有马克思自己的幽灵,即马克思自己的本体论、决定论,因为在德里达看来,精神与幽灵的界限是如此微妙,一不小心则极其容易逾越,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圣麦克斯·斯德纳(St.Max Stirner)的精神决定论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物质决定论,因此产生了新的本体论、先验论、宿命论,封闭了其他可能性。马克思在驱除幽灵化时却陷入了自己的幽灵化中。德里达在阐述这一切时,亮出解构的主旨:解构并不是耶鲁批评家们按其“专家转型”( de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诺里斯:12)需要所演绎出来的那种文本批评方法,而是针对上述魑魅魍魉的意识形态批判。而这种解构的目的是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变革精神。
二、哈姆莱特与霍拉旭(勃那多,马西勒斯),传统知识分子与学者
在马克思的精神与幽灵的转换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作用不可忽略。德里达转引瓦莱里(Paul Valery)的《精神的危机》,将哈姆莱特看作代表着“看着千千万万个幽灵……思索着生与死的真理”的欧洲知识分子,(Derrida:5)这千千万万个幽灵即欧洲思想史上的先驱们,哈姆莱特在对待那些象征着精神遗产的骷髅时是不同于那几个掘墓人的,后者将他们仅看作“一件东西”,而哈姆莱特看每个骷髅都是“卓越的头颅”,并还记得“那个骷髅里曾经有一条舌头,它也会唱歌哩”,(朱生豪:162)即他的关注点是其内容和精神,而不是僵化的形式,如他抓住康德的头颅,知道他生成了黑格尔,抓住黑格尔的头颅,知道他生成了马克思,但是马克思应该生成什么?是否有未来?这是德里达的关注,但瓦莱里偏偏在此用了省略号,让马克思退场了,这意味着欧洲知识分子中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继承人。看来马克思只能成为“一件东西”了。
如此悲观和简单吗?哈姆莱特,霍拉旭 (或勃那多,或马西勒斯),掘墓人,即所有这些与亡灵打交道的人,他们有什么区别?或许这可以从瓦莱里所列举的与亡灵打交道时的三种态度(或三种关系、三个层次)来判断,简言之,即对之丧悼、听其言说、观其运作。所谓对之丧悼,即确认对象已死,并确认其身份、墓地,盖棺论定,德里达又称这种丧悼活动为本体论化和语义化,一旦如此,它便不再有歧义,也不再有发展或变化的余地,因此也不再是一种活跃的精神,而是典籍中的一项,哲学史中的一页,马克思则变成了许多哲学家中的一个,由此而变成一种中性化的、任何阵营都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它已经死亡,不再有任何危险。这无疑也是一种终结论。
所谓听其言说,即认为,它不仅只是一件东西,一个骷髅,它曾经有舌头,会唱歌或会言说,即它留下了生动的内容给后人阐释,由于这种阐释,产生了一大堆“马克思的儿孙们”。(Sprinker:213)
所谓观其运作,则与丧悼活动正相反,前提是认为魂灵还活跃着,是一种精神之精神,一种变革的力量,因此用一种期待的态度守望之。
先看作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哈姆莱特在这三个层面的哪一层?的确,在第五幕第一场,他不仅问掘墓人,那头颅是谁的,还要知道墓是谁的,这是为了确认以便丧悼。但是,又是他告诉那些人,这些骷髅是曾经言说的,并阐释其内容,同时他又是与鬼魂交流、视其为活的精神并执行其指令的人,但他所做的却是延宕、迟疑、不去确定、拖延行动。所以事情非常复杂,他并不纯粹。德里达无疑是不赞成第一个层面,对第二个层面则是包容的态度,认为每种阐释都是独特的,但反对任何一种阐释自称权威。对于第三个层面中的延宕和不确定,德里达给予了两种解释,从解构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他并不指责这种延宕,因为在他看来,“是或不是”(或“做或不做”,“生或死”),这的确是个问题,他甚至认为,问“A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个伪问题,因为不可能有一一对应,任何对应与同一都会导致某种僵化、物化,幽灵化,封锁了通往未来的道路,于是,从这个层面,哈姆莱特的延宕反而是他最宝贵的一面,他给幽灵继续徘徊的时空,让其精神运作。但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角度来看,这与霍拉旭(或马西勒斯)没有区别,都是在观看已然的东西,没有创新,没有行动,而这在德里达看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磨灭的教训。
综合来看,作为传统欧洲知识分子代表的哈姆莱特显然是不尽如人意的,但相比之下,作为学者的霍拉旭或马西勒斯们还有更糟糕的一面,即指认的欲望,霍拉旭和勃那多谈到鬼魂时都是用结论性的语言:“正像已故国王的模样”,(一幕一场)“这恰恰就是他穿过的甲胄”,(一幕四场)他们都认为让幽灵言说,倾听之并思索之,这是困难的,更不用说与幽灵共同言说,即用超越在场与不在场,实在与非实在,生命与非生命等二元对立的方式言说,因为这些传统学者们只相信本体论 (ontology),不相信闹鬼论(hauntology),即只相信确定性和在场性,不相信流动性,未然性,因此也就是拒绝了可能、希望、未来,而追求锁定当下,形成权力,当这种追求达到极致时会产生一种语言或知识的暴力,如德里达所描绘的:马西勒斯让霍拉旭这个“有学问的人”去招呼鬼魂,“质问它,审问它,更准确地说,是去向那个还在的东西提问……,于是霍拉旭……两次以专横又谴责的态度命令它说话(‘我命令你说话……说呀,说呀,我命令你,快说!’……拦住它,马西勒斯。)”(莎士比亚:82,84)(Derrida:12)所以德里达说要对这种幻觉的、神秘的马西勒斯情结保持警惕,这之所以是幻觉和神秘的,是因为这是一种极度膨胀的主观臆断、主体意识和同一性思维,它将他者、差异、异质、不对等都看作自己的猎物,必须同化与收编才感到完满。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它们曾经是极端对立的阵营,却走向同样的独裁与专制,就在于它们始于这同一意识形态。
德里达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中最醒目的东西的彻底忘却,即作为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幽灵是徘徊的、永不停息的“闹鬼”,德里达说“这是第一个父亲般的角色,既强大有力,又无实在在场,一个比人们快乐地称作活生生的在场的东西要更为真实的幻觉或幻影”。(Derrida:13)而这种不断自我更新、敦促变革的榜样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树立的,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再版序言中就根据新的局势变化,声明《宣言》的某些内容已经过时,且考虑对整个体系的颠覆与重构,德里达将这种自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之精神,这也正是他所理解的“指令”的精神:变革,当机立断,不可延缓。但德里达认为这首先需要的是,用超越学者式的方式来阅读和讨论马克思主义,所以指令所要求的首先是思维范式的变革。
于是德里达期待这样一个新型学者的产生:“某个白天、某个夜晚或若干世纪之后,会有另一个‘学者’出现,后者最终必定能够——在在场与不在场、实在性与非实在性、生命与非生命的对立之外——思考那幽灵的可能性,思考作为可能性的幽灵”,(Derrida:12)这个“可能性”就是面向未来或希望的开放性。
三、颠倒的时代与脱节的指令,解构与正义
这样一个学者的出现,其实不需要等到若干世纪之后,他早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德里达本人,他正是以超越二元对立之外的运思来思考时代、责任、未来。在这个层面他所借用的是哈姆莱特在第一幕结束时所发出的那著名感叹:“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O cursed spite,/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Shakespeare:679)(“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或时间或时代脱节或错位了。该诅咒的命运,却让我负起这重整乾坤的责任!”)。⑥德里达将之一分为三来演绎自己的运思。他认为,这句话的第一部分不仅命名了哈姆莱特的时代,也命名了当今世界、甚至历史本身的特点和机会,而最重要的是,它更命名了“重整乾坤”这个指令的性质。第二部分命名了这样一个时代本身无法规避的悲剧。第三部分命名了责任。
对第一部分,德里达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将之看作是对时弊的写照,认为哈姆莱特如是说,就揭露了“一个脱节、错位、出轨、颓败、惨败加颓败、错乱、无序、疯狂”的时代,但是德里达眼中的哈姆莱特并不因此而消沉为一个抑郁王子,反而由于如此彻悟时代的弊端而打开了“诗与思的洞天”,(Derrida:18)即他开始超越现实,与“鬼魂”共谋,思考如何实施“指令”,以便“重整乾坤”,改造世界,也就是说,哈姆莱特认识到,当“颠倒混乱”达到那种极端状态时,就正如黎明前的黑暗,意味着曙光和希望就在前面,给重新开始带来了机会。从这里,德里达开始第二个层面的阐释,即“颠倒混乱的时代”也就是脱节、错位的时代,历史“按部就班”的进程将在这里急刹车,让位于新纪元,这里德里达呼应着本雅明半个多世纪之前在“神学—政治断章”和“暴力论”等文章中所表达的同样观念,⑦即历史与救赎虽然是两个相反的极端,却正可以因其之间的张力而激发革命,也就是说,历史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走得越远,越远离人类自古以来所追求的理想,也就越暴露其矛盾与困境,因此就越使得救赎的需要迫在眉睫,本雅明把这种断裂叫做“弥赛亚式的断开”(the messianic caesura),德里达所用语言也与本雅明极其相似,他说:“当时代出了毛病,对于他者,这种断裂,这种‘出了毛病’所产生的失调,不正是良善、或至少是公正所必需的吗?断裂不正好就是他者的可能性吗?”(Derrida:22)
于是德里达从哈姆莱特对自己时代的命名和彻悟中也找到言说当下时代的寓言,即,正如“丹麦国里有些见不得人的事”,全球化的世界新秩序里同样也“出了毛病,已经破败不堪……每况愈下”,德里达借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画家的话说,“一天不如一天了”。并以画家的方式给这个世界画了一幅“黑板画”,表明这些画面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被擦除的,这些画面便是他归纳出的那十大“祸患”(plagues),整幅画的题目就叫“颠倒混乱的时代”或者“糟糕透顶的今日世界”。(Derrida:78)这也意味着这个世界需要改天换日,德里达正是从这个视角产生哈姆莱特式的思想飞跃,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制造的世界新秩序的幻象,看到马克思的幽灵带着指令归来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如日中天的全球化语境中,在终结论响彻世界的时代里,德里达正如哈姆莱特“无论在戏剧中还是在历史中都不会知道‘完满结局’的平静”,(Derrida:29)反而更清楚地看到“闹鬼”,感到鬼魂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精神,冥冥中给了自己“重整乾坤”、“改造世界”的重托。
但这个“重整”与“改造”的指令究竟是怎样性质的?应如何理解与继承?带着这些问题,德里达随即进入第三个层面的运思,即“指令”的“非共时性/非同一性”性质。这也是一种脱节,总与自身脱节,这指的是,在世界或历史变幻的风云中,这样一个指令本身的性质是非物化、非教条化、非本体化的,它是一种活的精神,不断自我更新、自我扬弃,永葆批判与颠覆的锋芒与锐气,因此它所强调的改造、行动也必然是一种“永久革命”意义上的不断变革与进取。对这样一个指令的继承,就不能将之作为一个哲学典籍来收藏,也不可将其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异质成分同一起来,而是尊重与保持其异质性、流变性,并批判与选择,唯有如此,才可保持它的“游魂品质”,即使之发挥作用,而不是成为僵尸,德里达借用言语行为论术语,称这为维护它的“诉行性”(performativity)。
德里达援引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马克思的三种声音》,把这种态度称为“政治的声音”,它所针对的是“应答”的声音和“科学”的声音,所谓“应答”的声音,即给问题一个答案,将之本体化,变成政治性结论,“夜以继日地哄骗意识”。(Derrida:30)所谓“科学”的声音,则是另一种本体化操作,它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大学的课程,将马克思的著作列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伟大经典之一,用哲学—语文学的方式来研究,而马克思则被看做了一个与别人无区别的哲学家,不属于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属于任何政党。由此马克思主义被解政治化、中立化、去革命性,去威胁性,它不再是一个指令,而是一个理论流派。但所谓“政治的声音”正与上述声音相反,用德里达所引用的布朗肖的话来说,
它能使每一种声音短路。它不再带来任何意义,而带来一个号召,一个暴力,一个决裂的决定。……它甚至要求革命恐怖,建议不断革命,并总能指明,革命不是最终的必然性,而是一种紧迫性,因为革命的特征,如果它能开启和穿越时代,就是毫不耽误地提供紧迫性,使自己作为永远在场的要求而存在着。 (Derrida:33)
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本雅明意义上的“革命”或“纯暴力”,它可以颠覆“事情就这样发生下去”的已然状态,开启一个新纪元,因此它不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是“急刹车”。而布朗肖之所以在其《哲学的终结》中说,哲学精神却在哲学自身的终结中、葬礼中热烈欢呼、欣喜若狂,引导着自己的葬礼队伍缓缓而行,也是因为这种终结是终结了目的论、本体论,而开始了“闹鬼论”,因此也就打开了未来。布朗肖称这是哲学在死亡中的升华。德里达认为布朗肖的论述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深刻,以一种既审慎又令人炫目的方式散发着理智的光芒”,他对此“完全认同”。(Derrida:16)从这个视角,德里达特别提醒读者,哈姆莱特正是在幽灵要他发誓执行指令的那一刻高喊,“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或时间脱节错位”,借此德里达也是再次强调时代和指令的性质。
但是哈姆莱特又诅咒自己的命运,这又是为什么?在德里达看来,哈姆莱特所诅咒的是,他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必须用复仇和惩罚来匡扶正义,才能复兴一个已经失去的时代。换言之,他是为正义而出生、而存在,但是他必须通过灭杀来实现所谓法律上的公正,而他对此无法选择,因为历史已经先他而存在,这是他的出身创伤,所以他诅咒他的出身和命运,就如同约伯诅咒那个见证了自己出生的日子。但他这样诅咒时,实际上也诅咒了那个以法律为标示或作为法律历史的历史,他的出身本身就证实了当今世界的“本源性腐败”,(Derrida:22)无怪乎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
在这里德里达就涉及第三个部分,“重整乾坤”,他向往建立与上述完全相异的时空,那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某一天、不再属于历史的某一天、或者说救世主即将降临的某一天,可以最终摆脱复仇的命运,不仅是摆脱,而且是要在源头上使那一天成为与复仇的命运全然无关的一天,成为完全异质的一天”,(Derrida:21)这既是一个比记忆本身还要古老的时间(人类的夙愿),又是一个未来的时间(尚未实现的理想),两者之间的断裂,便是当下。德里达借海德格尔对《阿那克斯曼的箴言》的阐释进入对这个断裂的思考,并提出“对嵌合的思考也就是对指令的思考”,即思考如何从现在着手向着美好未来奋斗。这个美好未来将是超越法律的正义社会,即美好的事物将是一种赠与,不是用暴力、惩罚、新一轮权力去换取,同时不仅超越任何对立,也超越市场、恩赐、交易、商品。
但是,德里达的下一个问题是,这个礼物由谁来给予?谁拥有它?如果谁将这种状态当作别人没有,而需要由自己给予,这岂不是又有一种危险,即把正义又刻写在在场的符号下,正义本身又成为一种主导权力?但真正的正义应该是解除这一切的。在此,德里达再次强调解构的真正意义,即只有解构创造了真正达到正义的条件,因为解构是一种“荒漠般的弥赛亚”,(Derrida:28)它对“荒漠”、或者“深渊”、“虚无”、“缺场”的强调和运用,正是对权力、僵化、神化、封闭、终结的抵抗,为多元异质能够共存、为无尽的可能、因此也为未来打开空间。德里达版本的正义从横向维度上追求消解总体化、本体化、幽灵化,从纵向维度上追求即将到来的民主、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而不是民主的将来或共产主义的将来。他又称这是一种极端的弥赛亚诉求,一种“新国际”,其绝对开放性程度被强调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即,这是一个朝向未来的“我们”,是“无结盟关系”的新联合,因此“无组织、无政党、无民族、无国家、无财产”,德里达最后称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他重整乾坤、取代“世界新秩序”中的国际法的乌托邦计划。(Derrida:29,85,86)
这个乌托邦是一个与当下不同的他者 (other),正在到来,但绝对不可预测其确切日期,德里达用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话说,与这个他者的关系,就是正义。在他的鬼魂系谱中,这个他者叫arrivant,⑧即正在到来的归魂,或希望与未来,因此也必然是迫使当下不断变革的力量,这就是“一个脱节的指令”的指归,也是解构的目的,在这点上,德里达认为解构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异名同体,解构不可能产生在前马克思主义时代,同时解构又是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的更新、尤其是对它的激进化。而这种解构的立场才是知识分子“重整乾坤”的责任所在。
注释:
①本书的英译本全名为: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rning,and the new interna tional。其中第一章“injunctions of marx”可为全书的微缩、理论框架和逻辑前提。
②F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Free Press,1992).它的出版曾在全球学术界和政治界引起轰动,已经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
③在谈金钱与商品的幽灵性时,德里达转引马克思所用的《雅典的泰门》中的片段,在谈权力欲望时提到《麦克白》与《裘力斯·恺撒》中的幽灵。马克思的文本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第一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纲)。
④1993年4月22日至24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赛德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世界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出席,会议的主题是“Whither Marxism? Global Crisi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对“Whither Marxism?”中的“Whither”一词德里达从字面和声音两个层面来理解,即whither/wither,于是这个问题不仅是“Where is Marxism going”(“马克思主义何处去”),它还是“Is Marxism dying?”(“马克思主义衰亡了吗”)(见该书第X iii页的“note on the text”),他围绕这两个问题为会议做了两场讲座,讲座材料后整理为《马克思的幽灵们》一书。
⑤德里达把马克思的这种变革精神视作其精髓(批判精神、实践价值、行动性),认为理解和继承这个精神是个责任,并说他这个讲座不是为了构造学术或哲学话语,而是为了不逃避这个责任,并就这个责任之本质提出几个假设供讨论。这是他这部著作的主旨。(详见Derrida:51)
⑥译文根据对德里达应用这句话的理解做了调整。
⑦德里达正是在谈到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时提到本雅明,另外在被认为是《幽灵们》的前文本的“Force of Law: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中,他也引本雅明的“暴力论”为依据,见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ed.by Drucilla Cornell et al,Routledge,1992)中的第一篇。
⑧见Derrida:28,65,168,181等。这是德里达自己造的一个词,在英译本中保持原样,没有翻译。德里达将弥赛亚、他者、正义、归魂联系起来说:“……the messianic:the coming of the other,the absolute and unpredictable singularity of the arriyant as justice.”(Derrida:28)
标签:德里达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本体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