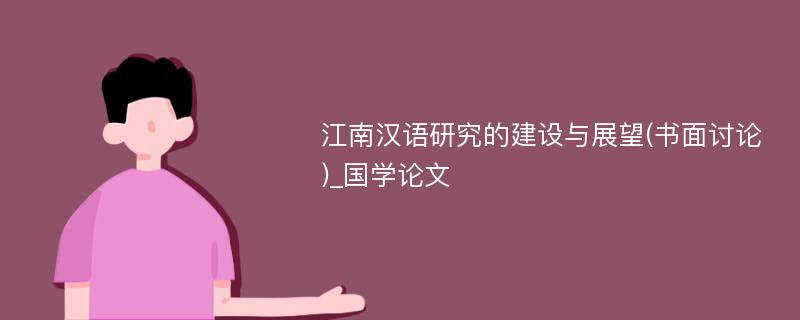
江南国学的构建与展望(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江南论文,国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学是北方文化的产物,也是以北方与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学术的独特反映与表现形态。但早在春秋时代就传播到江南地区,并历史地形成了具有独特学理内涵与精神性格的江南话语谱系。在一些民间珍藏的家谱中,还可以看到齐鲁等地的居民早在西周初年就开始南迁江浙一带,说明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要比我们一般设想的历史开端要更早。这是我们提出江南国学的经验基础与学术背景。在以后漫长的中国思想与文化史上,日益成熟的江南国学不仅对北方儒学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增殖与价值多元化,同时,以经济与文教发达的古代江南社会为中心与根据地,江南国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生态。由于缺乏江南国学理念以及相对独立的学科支撑,以往关于江南国学的正面研究很少,而相关研究不是从属于江南区域的经济、宗教、社会史、文学艺术研究,就是淹没在江南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中,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江南国学固有的独特形态与本质。随着江南文化研究在当代的不断升温,如“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曾被列为2005年中国学术界十大热点,如《光明日报》推出的“儒学与都市文明对话”(其中涉及儒学的地域性问题),以及与江南传统文化相关的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出台等,直接推动了整个社会和学术界对江南国学的关注与研究。特别是在国家推广汉语文化、国学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以“江南国学”为总体学科框架,以传统的文史哲学科的“江南研究”为支撑学科,积极吸收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当代新兴学科的知识与研究技术,建设一门具有重要地方经验与当代世界价值的新兴人文社会学科,正在被迅速地提到学术议事日程上来。而当代以上海为首位城市的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精神文明与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则为江南国学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江南国学在学科构架上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江南国学理论研究。对于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建设,基本理论体系的建设首当其冲,是一切具体的学术研究与精神生产的基础,直接决定着各种经验事实与经验性知识如何构成与再现,所以,不是一般零碎的、偶然的经验事实与知识积累,而是先于它们的观念、理论与框架才具有更为重要与优先的地位。要想创建一门具有系统的理论范畴、独立的学科属性与重要的应用价值的江南国学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是我们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弱项,在对象的属性与范围、基本的结构与层面、目的与意义缺乏起码界定下进行的研究,其结果通常有二:一是大家一直纠缠在概念内涵大小、术语是否精确等琐碎辩论中,无法在学理上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和推动学科建设的深入发展;二是由于问题、对象、范围与目的“不明”,在进行了许多的经验研究与讨论之后,人们多半会发现自己讨论的是一个无法讨论的“伪命题”或无法界定的“宏大对象”,更有甚者则会因此而怀疑与否定某一门学科是否可以成立。这是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研究而导致的必然后果,因为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认识与研究提供基本的技术手段、分类原则与解释框架,使在经验层面上与其他事物相互缠绕、混沌一团的研究对象呈现出来。如江南国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清理出它特有的概念范畴与内在层次、知识谱系与话语系统、历史源流与演变规律,以及与齐鲁儒学或其他地区儒学的差异等。这些都是江南国学得以成立、具有学科合法性以及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进展,可以为整理与研究江南国学文献提供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解释框架,使这一重要的国学资源的个性特征、内在本质与人文价值大白于世。
二是江南国学文献与历史研究。江南地区自古就以经济与文教的发达著称于世,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区域文化与独具个性的学术传统。这是江南国学得以提出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与历史资源。由于中国文化在自然地理上分布与发展的差异,使得江南与北方和中原在文化形态与学术生产上有很大的不同。其核心的表现在于,如果说北方文化的深层结构源自齐鲁文化中的政治—伦理要素,那么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则在于江南社会中的经济—审美要素。与齐鲁文化相比,除了物质生活的富裕、文化教育的发达之外,江南文化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诗性文化。在江南诗性文化中,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这是古代江南民族对中华文明最独特的贡献。江南国学的特质与特色与江南诗性文化息息相关,源自北方与中原的国学正是因为受到江南诗性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脱离了它质朴木讷的政治—伦理形态,开辟出清新、细腻以及在思维上更加抽象与纯粹、在感受上富有人情与美感的新体系。在异常复杂的历史与学术史的演进中,这一新体系生产与存留了大量的文献资源,它们在叙事、学理、旨趣、精神、气质等方面既与北方国学相关,同时也由于江南生活方式与文化生产模式的影响而生成了新的本质与重要特征。如古代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三者发展得比较和谐,为个体的感性机能、审美心理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这是在江南地区容易出现戴震那样的“怀疑论者”、顾炎武那样的“职业化学者”,以及李贽一类的儒学异端人物的根源。相反,在经济生产条件较差、政治军事动荡不断的北方与中原,学者很容易把学术研究理解为政治经济斗争的工具,而对“纯思辨”、“纯学术”、“纯抒情”的东西则很难认同与理解。所谓北方学者多守成醇厚,而江南学者多喜标新立异,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江南国学文献与历史研究,不仅可以为传统文史哲的“整理国故”提供新的学科生长点,同时对实现当代国学研究的多向与全面发展也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资源。
三是江南国学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学以致用”,这是江南国学研究的实践应用层面,也是在国家推广汉语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江南地区城市文明建设等相关政策背景下的直接产物。江南国学文化遗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这主要得力于大自然与江南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良性循环,秀丽山川因“得诗人之助”而倍增其人文内涵与气象。人与自然在古典文化背景下的相互交流与和谐生态,使各式各样的国学文化遗产在江南大地上蔚为大观。以人文地理论,如陈亮在永康县东北五十里方岩开创的五峰书院,如方孝孺曾受聘讲学的宁海西南三十里的“前童”村。以主体精神论,如绝食而死的刘宗周,余英时称他为“宋明理学的最后一位大师”,牟宗三的评价更高,说“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随时表而出之,是学问,也是生命。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亦亡”。对这些国学文化积淀深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空间进行保护、修复与开发,既是展示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同时也可以通过现代创意与设计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这对于江南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保护的层面讲,主要是在学术研究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挖掘、抢救至今已湮灭不闻或濒于灭亡的江南国学文化遗产,编制江南国学文化遗产名录,使其纳入各省、市、城镇与乡村的非物质遗产保护计划中,并研发它们在当代都市化背景下的生存与发展战略。就开发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以文化创意与文化产业为战略框架实现江南国学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它既可以是按照时代需要对江南国学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再生产,也可以是对被遗忘了的一人一事一物的发现、修葺与景观化。前者如与“北方圣迹图”工程相呼应,研发“江南儒学的文化线路”,全面展示儒学在江南大地上的历史与精神行程。后者如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他曾定居南昌开坛讲学,是儒家学术与文化在江南地区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他在南昌的墓就在东湖之滨,今南昌二中内。正如白居易在李白墓前所写:“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今天还有几人会知道这位在江南大地上传播儒家薪火的先行者呢?
江南国学新学科建设,既是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整体战略框架的一部分,也是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当代长三角地区的一种重要学术实践。江南国学文化不仅在历史上构成了这一地区的精神核心,同时也在“软实力”的层面上直接影响着当代江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江南国学的深入研究与不断探索,不仅有助于推动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的学术转型,提升与释放人文社会科学服务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的水平与能力,同时,江南国学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再生产,对上海及长三角的旅游业、文化产业发展也可作出直接的贡献。此外,江南国学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上的探索与经验,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国学研究、精神文明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资源产业化等,也将会产生一些重要而积极的示范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