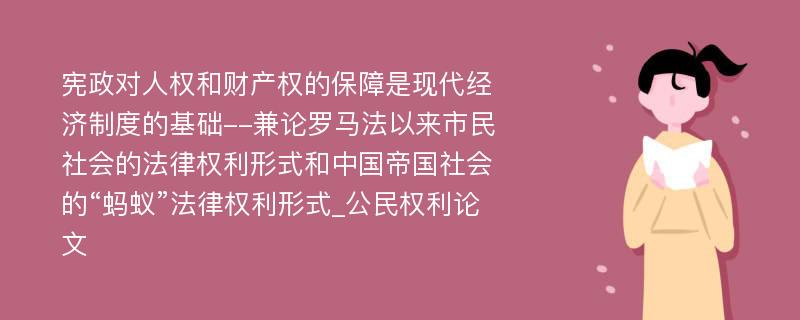
为什么宪政对人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兼论罗马法以来公民社会法权形态与中国皇权社会“蚁民”法权形态的迥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权论文,蚁民论文,形态论文,社会论文,皇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不久杨小凯先生逝世的令人惋惜,不仅是因为他作为出色经济学家而未竟其志,更由于他近年尤其致力于阐扬宪政政体保障公民人权和财产所有权的制度意义,而这项他 没有完成的努力正是当今中国所亟须。去年,他在一篇题为《土地产权与宪政共和》的 短文中说:
大家都尊重财产,就有一个保险在里面。我丢了权力不怕,因为我的财产不会被别人侵犯。这样,人就变得文明了,不会抓了权不放的。这在西方是一个传统,……不像中国古代,丢了权,皇帝可以把你的家产抄没,没有这种事。丢了权就丢了权,你就不当官了。地产还在那里,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是政治共和的一个基础。……因为权利不清的时候,老就想抢人家的,因为抢不算抢。我白拿你的,也不算偷。那大家当然都想拿。地产不清的时候,人就不文明。而且,这个时候,有权的人可以任意解释,说我这样做就是对的。政治上就变成你死我活了,这个政治共和就搞不起来。(注:《南方周末》2003年5月22日,第23版。)
本文用这段文字作为开头,一是因为杨先生把这个关乎我们无数小民百姓身家性命(更关系着能否在中国建立起现代经济制度)的道理叙说得至简至明;二是因为,这个道理还远远没有成为我们社会遵行的基本法理和准则。且不说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对国民人权和财产所有权的侵犯随处可见,即使是学术界,上述的道理也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所以经常有相反说法热闹一时。
下面就通过介绍和质疑这样一种当前比较流行的说法,以引出对本文标题所示主题的讨论。此种理论认为:在皇权中国这一迥异于宪政及其产权形态的制度框架之内,近现 代性质的经济方式仍然可以建立起来;至少,明清时代经济史曾经证明中国具有根据内 生的制度逻辑建立现代经济方式的充分可能;而且因其路径有别于“西方化”,遂有着 特殊的价值;尤其在今天,对此价值的弘扬更有着“反对西欧中心主义”的意义。
一、当下流行的一种经济史观对宪政及其产权理论的挑战:“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
旨在说明直到明清时代,皇权中国的制度环境一直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使其得以领先于世界经济的新潮理论,近来可谓层出不穷。比如前两年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译本(出版时不少学者对其格外推重),此书认为:所有关于西方国家现代先进地位是因为近代以来理性精神的建立、制度创新和工业革命等等结论,都是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以来世人炮制的“欧洲中心论”的妄说。因为自中古以后,世界经济就存在着一个完整的产业分工和多边贸易体系,众多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国内经济都充分依赖于这个体系;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国家,则一直是这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它们因为制度更为理性、生产更为发达等原因走在了世界的前头。相反,依附于这个体系的落后欧洲国家则长期处于入超地位,因此只能依靠向东方国家输出美洲白银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直到17世纪,中国的领先地位才因为白银供应的突然匮乏而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于是一直搭乘东方快车的西方才借机将昔日的中国挤下,并占尽了近代以来世界的先机。
随后,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中译本又在2003年出版,该书认为:直到18世纪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上面,中国经济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的区 别(注:[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中文版序言》,“通过最近两年的讨论已完全站住脚的观点是: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 他一些地方(显然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 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 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 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第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中国所以没有 能够走上类似英国工业式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中国不具备英国那样地理位置优越的 煤矿、不具备英国那样能够提供棉花、木材、谷物等集约产品的殖民地(注:详见史建 云:“《大分流》带来的启示”。(http://www.guoxue.com/jjyj/trgj/dfl.htm))。更 值得提及的是,此书中译本出版之前,经济史学界就对此书的内容以及与其相呼应的学 术观点做了充分的褒扬,比如北京大学一位学者说:
弗兰克、彭慕兰,还有王国斌,他们形成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学派”,是研究中国史的。比较起来,王国斌的研究……不仅有经济数据,还把国家的形成,各种体制、制度也考虑在内。……我非常欣赏他的一个论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分成一个个阶段延续下来的,政府是一个系统,但应用到地方同样也是一个系统,所以中国的政令便于执行,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他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他是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衡量,不仅是王国斌,有些法国汉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中国政治的特点是爱民、救民、教民,……王国斌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共空间去发表意见,但它有别的东西,把这一部分 研究出来,这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走的道路吗?(注: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在2001年12月 7日“中国经济史论坛”上的发言,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中国经济史论坛会 议记录》(http://www.guoxue.com/jjyj/trgj/hyjl.htm))(引文中的黑体均为本文作者 所标,下同——注)
褒扬中国皇权社会经济制度的同时,则认为近现代经济制度在欧洲的创立只是因为一种偶然,而并不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历史必然性:
王国斌向欧洲中心论提出挑战,认为欧洲的“主导作用无论在空间或时间方面都被夸大了”。他同意朗德斯的论点是:西方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进行了巨大改造;但他指出这只是最近200年的事,与欧洲传统文化无关,它的成就是一种不正常的断裂。(注: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见《经济史论坛》网 络版(http://www.guoxue.com/jjyj/trgj/pw.htm))
在反对“欧洲中心论”名义下,判定中国传统经济(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制度环境“绝不是专制主义”,判定中国可以通过迥异于宪政及其产权制度的方向而走出另一条“道路”,类似看法还有很多(注:详见史建云:“《大分流》带来的启示”,《经济史论坛》网络版http://www.guoxue.com/jjyj/trgj/dfl.htm;李军等:“‘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这当然说明此种经济史观的不容忽视。
二、与宪政及其产权形态完全悖逆的专制制度环境导致了中国经济史上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人们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题目下面,对于能够证明中国在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中期(16世纪)以后太湖流域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史料做了穷尽式的发掘,以期证明在皇权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按照中国经济内部固有的轨迹本来也能够自发地产生近现代经济制度;而这几乎成为定论的结论今天仍然被看作是《白银资本》、《大分流》等的先声或同调。
但是这些老的和新的结论似乎都忘记了,皇权中国的城市,其性质与欧洲的“自由市”完全不同,因为所有中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首要功能,都是作为皇权体系大网上的一个个凝聚和传导权力的网结,这给城市经济规定了两个最重要的特质:第一,城市经济的模式必然被置于皇权体制的控御之下,这不仅表现在官营、禁榷等统治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在两千年中始终极为强大,而且即使是城市民营经济,在整体上也必须首先以服务于皇权制度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前提;宋代著名民谣所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行在”即皇帝住所——注)卖酒醋”,就生动地形容了政治发迹与经商发迹,两者都要仰赖于皇权这共同的核心。第二,由于城市经济首先服务于统治权力,所以从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分工与规模化、统治者所卵翼之寄生人群的激增、奢糜消费风俗的形成等等,所有这些启动城市经济繁荣的路径,都是以统治权力对全社会的超强控制和权力消费的急剧膨胀为前提;而一旦这种以残酷掠夺弱势群体为前提的“繁荣”达到了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承载极限,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发生雪崩式的倒塌,一度繁盛的城市经济也就随之被周期性的流民造反或统治者间的战乱扫荡殆尽,其必然结果就是城市遭到毁灭性焚掠、人口锐减、工商业者流离失所和被大量屠杀,社会结构回落到专制权力的强度与社会利益相对平衡、但经济总量和生产水平大大萎缩了的低谷,并重新开始下一周期的盛衰轮回——也就是说,在 皇权政体及其“一治一乱”的运行周期中,任何一定时段和内“商品经济”的繁荣都因 为出于“权力经济”大背景的制约,所以它非但不可能导致近现代经济制度的产生和确 立,相反连长期保持传统经济形态的平稳运行都从来是不可能的。
那么,上述“权力经济形态”与皇权社会中小民人身和财产法权形态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在中国皇权社会,对子民人身和财产权益的规定源于这样的法理:皇帝乃是代表至高无上的“天”而拯救、抚育和统治天下万民,因而子民的一切人身和财产最终只能归属于皇权,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百姓)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等等(注:(唐)柳宗元:“为耆老等请复尊号表”,《柳宗元集》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而由于亿万子民人身和财产权益根本不具备禁止统治权力阑人的“权界”,所以其一旦面对权力,则一切“市场行为”就立刻被完全扭曲。
概括起来,明清时代统治权力对市场的扭曲除了秦汉以来历朝沿袭的禁榷(盐铁茶酒等各种高额利润的商品禁止民间经营而由官府、甚至是由皇帝亲幸垄断专营)制度、官营手工业在相当大程度上无偿占用最优质经济资源等等之外,至少包括这样一些刺目的方面:其一,统治者依仗威势,在与商户的交易中用强买强卖、拖欠货款、贵卖贱买、名 为购买实为强占等等手段大量渔利;其二,权力集团中从上到下的各级成员都蜂拥经营 商业、并利用政治特权(甚至是司法和特务权力)而最大限度地攫取商业垄断利润;其三 ,因为没有人身和产权方面的保障,所以商人阶层只能“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以使自 己安身立命和征得商业经营的出路;其四,皇权“恶税”制度给包括城市经济在内的整 个国民经济带来灭顶之灾;其五,权力集团公开、大规模地掳掠工商阶层和百姓们的财 产。
因为统治权力对市场的凌驾通过上述“五管齐下”的方式而在16—17世纪达到空前程度,所以对其说明需要很大篇幅,笔者只能另外撰文详细介绍。这里只以统治者掳掠工商阶层时的极端横暴酷虐为例,说明在皇权社会的法权制度统治之下,工商阶层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是何等卑微,因而使任何局部和一时的经济规模扩展,最终都只能落得悲剧性的结局。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热衷于以明代中后期(嘉靖、万历以后,即16世纪以后)为例,说明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了如何可观的发展。而实际上,恰恰是以此时为标志,专制权力对于工商阶级的掠夺达到了空前恶性的程度,比如万历皇帝朱翊钧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即经济钦差)前往全国各地搜刮百姓,尤其是掳掠商人富户的财产:
(万历二十八年,即1600年)户部尚书陈蕖题:“迩自言利,小人奏收商税,(税使)一到地方,狼吞虎噬,截索等于御夺,搜括甚于抄封。商旅裹足,民心思乱。”(注:《明神宗实录卷》卷三百四十六,645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以学者们经常用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如何发展”的纺织业状况为例。我们说,在16世纪前后的制度环境中,不论纺织业一度有过怎样的发展,但是其转瞬之际的衰落却无可避免。比如,据户部尚书赵世卿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对北京、河西务(“河西务”为当时督察漕运事务的衙门,设在今天津武清县)、山东临清、江西九江、江苏淮安等南北众多商业枢纽地的调查统计,可以清楚地知道统治权力恣睢暴虐对这一产业的毁灭性摧残:
在河西务关,(当地人)则称:“税使征敛,以至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馀名,今止三十馀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谓沿途税使抽罚折本, 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段(缎)店三十二座,今关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 ,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在淮安关,则称: “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挨捉,商畏缩不来矣。”其他各关,告穷告 急之人,无日不至,不敢一一陈渎。……税使之害,尤有甚于(商人)跋涉风涛者,则苛 征猛于虎之说也。”(注:《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六,万历三十年九月,7073页。)
赵世卿这里所用“挨捉”一词,非常准确地说明了税监衙门对商人们实施的,乃是拉网式的追剿。而在当时“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注:《明史》卷三百十五,“宦官·二”,780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的大潮之下,类似恶果不仅举目皆是,而且由于统治权力网络的高度发达,其威势更是人们无可逃于天地之间:
近日御题黄纛,遍布关津;圣旨朱牌,委亵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 市,丝粟皆空。(注:《明史》卷二百二十三,“王士昌传”,5878页。)
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巷陌,……商旅不行,货物不聚。(注:(明)沈鲤:“请罢矿税疏”,《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三,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清乾隆四十六年刻本,1896—1899页。)
而同时受到戕害剥夺的,则更包括作为工商业基础的国计民生,甚至是百姓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经济条件。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富者贫,贫者死”(注:《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傅好礼传”,6168页。);“矿税流毒,宇内已无尺寸净地”(注:(明)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卷六,“陈增之死”条,17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注:《明史》卷二百二十六,“丘橓传”,5936页。)
此时权势者对于民间工商业的摧残和掠夺,更是凭着空前野蛮的方式而实现的,由此而最充分地展示出日益专横的政治体制和法权制度加之于经济形态之上的牢笼是何等狰狞。比如朱翊钧派出专门掳掠富商的特使程守训,凭着皇帝授予的无限威势,对江苏、浙江、安徽等江南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进行了挖地三尺式的搜刮,其手段之残暴令举世胆战心惊:
武英殿带衔中书程守训密旨访各处富商,搜求天下异宝。……(其侍从)旋盖车马,填塞街衢。首有金字钦命牌二面,继有二牌,一书:“凡告富商者,随此牌进”;一书:“凡官民人等,怀藏瑰宝者,随此牌进。”四介胄士骑执之。其他戈矛剑戟,拥卫如卤簿。臣为之色夺。又抎立京棍仝治为中军,另踞一船,逻卒数百辈,爪牙甚设,每日 放告,专合四方积滑,揭首匿名鬼状,平空架影,今日械一人,曰:“尔富而违法!” 明日系一人,曰:“尔家藏珍宝!”……凡稍殷实者,即罗而织之。其初逮也,不遽讯 也,铁索锁项,三木曳身,令过都历市,遍使观者股栗,而后就讯。舟次设水牢,于舟 中昼夜浸之,绝其食饮,……非法刑阱,备极惨毒。其人求死不得,无奈倾家鬻产,跪 献乞命,多则万金,少亦不下数千。如仪真监生李良材、南京盐商王懋佶、淮扬江、高 、汪、方、全诸家,立见倾荡丧身,人心汹惧,弃家远窜。而守训方饱于仪扬,又扬扬 去之金陵、之太平、之芜湖、之徽州,且声言向苏杭矣。……其号于人曰:“我天子门 生,奉有密旨,部院不得考察,科道不得纠劾!”(注:《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七,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五月,6467—6469页。)
这里值得留意的,不仅是权势者可以捕风捉影(“平空架影”)地随意诬告商人违法,并以刑讯、囚禁示众、逐户杀戮等各种“备极残毒”的手段勒索无数的商人,而且这种威势因为直接受命于“天子密旨”,所以是任何司法和监察机构都根本不能干涉的(注:关于专制权力日益不受制约的制度原因,详见拙文:“明代中后期法律文化的逆现代性”,《明史论丛》第2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同样惨目的例子在当时的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史料中随处可见,比如广东税使李凤及其爪牙陈保等人凌虐敲诈县令、抚按等大小官员,同时纠集海匪劫掠和杀戮沿海商人,其凶恶程度甚于倭寇:
罗织善良,钳制命吏,召集海盗,架使大船,截海商,登岸劫杀。在在见告,惨于夷寇,波水为红!(注:《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六,万历二十八年四月,6461页。)
在这种商业阶级连其最低限度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都永远无法获得制度保障的环境中,市场机会的平等、商业资本投资的广泛自由、国家公权对贸易的保障服务等等更高一级的“市场权利”,就更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种政治体制和法权制度中,任何优质的经济资源,不仅完全不能如彭慕兰等人所说的那样为经济形态向现代的发展提供的支撑,相反却由于统治权力的极端专横而成为了天下百姓(特别是工商阶层)杀身灭家的祸端,典型的例子比如税监陈增以盗掘矿产的罪名诬陷敲诈富户,仅仅三天之中就拘捕了五百多人(注:《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吴宗尧传”:“中官陈增以开矿至,……诬富民盗矿,三日捕系五百人。”(6177页)),所以当时人只能泣血哀陈:
天下富室无几,……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罄矣!”(注:《明史》卷二百二十五,“李戴传”,5919页。)
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挖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百家,杀人莫敢问!(注:《明史》卷三百五,“陈增传”,7806页。)
这类例子说明,抛开制度环境而以为只要具备了某些经济资源就可以保证社会发展的看法,是与事实完全悖逆的。
而统治权力专制性对经济和社会极大戕害更有令人毛骨竦然的例子,比如福建税监高采不仅网罗流氓充当打手、敲诈百姓、扣压抄没商人的货物、杀戮商人、焚烧民居,而 且成批地剖解活生生的儿童,取出他们的脑髓来为自己制作恢复性功能的药物:
原奏官魏天爵、林宗文百计媚采,由是得幸。忽进一方云:“生取童男女脑髓,和药饵之,则阳道复生,能御女种子。”采大喜,多买童……(注:(明)张燮著:《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条,265页,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明万历刻本。)(原书下有缺页— —注)
这种以往只有在文学家杜撰恶魔行径的神话小说中才能一见的暴行,竟然在17世纪前后依靠中国权力制度而完完全全成为了现实;并且在西方宪政影响来临之前,此种权力 制度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过任何真正的质疑,更没有提出过任何可以切实取而代之的政治 和社会制度设计(因此传统的中国思想家们,两千年间只能在是否应该恢复“井田制” 之类问题上打转儿(注:希望通过恢复“井田”等古制以遏止专制皇权对万民的克剥朘削,而此乌托邦在现实中又万难实现,关于中国传统制度学家们这种幼稚的设计及其始 终无法走出的两难困境,详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一”,35—36页 ,“十通”本。))。所以假使我们说,如此局面的笼盖之下竟然能够萌芽和发展出近现 代经济和社会形态,竟然能够赢得“中国人自己走的道路”之类莫大荣誉,那不是天大 的笑话吗?
三、罗马法以来公民社会的法权形态与中国皇权社会“蚁民”法权形态的迥异及其制度结果
说明上述“权力经济”模式及其制度基础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这套法权和法理体系乃是整个中国皇权社会的骨架,而且更因为它们恰恰是与推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有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法权制度完全逆向的。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制度得以产生的原因时说:
尽管(世界)各个地方都一直有着市民的市场特权、公司、行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城乡法律差异,但是公民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却从未存在过……(注: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可见对于近现代制度体系来说,最为关键乃是“公民”法权(首先是其人身和财产的权利,随之而来的是其参与和决定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权利)制度体系的建构。显而易见,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将亿万国民死死规定为“蚁民”和“草民”的中国政体之中,不具备任何向新的法权形态过渡的制度路径;所以我们在17世纪通俗小说的描写中看到,经商多年的商人在官老爷面前跪述的竟然是这样的法理:“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这蝼蚁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赐!”(注:《醒世恒言》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那么这种将天下万民视如无比轻贱的“蝼蚁”,将他们一切所有统统归之于皇恩和官 恩“所赐”的法权形态,它与宪政法权形态之间的巨大差别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知道,西方世界走出中世纪进程所凭借的最重要制度资源之一,就是罗马法所确立的那样一套能够使国民私有财产得到确认和保障的法权和法律制度,所以恩格斯赞扬罗马法“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也说:
罗马法学家所制定的关于经济关系的规则是具有更为直接的经济重要性的学说。他们几乎无限度地支持私有财产的权利,保障签订契约的自由,超过了当时条件所认为适当 的程度。……(因此)罗马法,则构成资本主义的法律学说和制度的重要基础。(注:[英 ]埃里克·罗尔著,陆元诚译:《经济思想史》,第37—38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可见罗马法体系所确立的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古典时代而为近现代社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基础。
如果对比罗马法定义公民及其财产的法权形态与中国皇权定义其“子民”人身和财产归属的法权形态,其间差别之巨大以及这个区别必然导致制度方向的迥异,就可以一目了然:首先,罗马法对于所有权之来源的判定是以“自然法”为根据,于是一切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天赋的人身权利,享有通过“先占”、“契约转让”等方式而占有财富的权利(注:详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第八章“财产的早期史”、第九章“契约的早期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而在这种根据“自然法律和理性”所确立的法权制度之上,绝对不可能如中国那样,还有“皇恩”、“大救星”这无比神圣的终极性所有者和恩庇者。所以以自然法为基点,罗马法体系对公民所有权构建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方面,即公民所有权之“绝对性”、以及每个公民获得和占有财富权利的天然平等。也正因为罗马法的这两大准则具有超越古典时代的伟大地位,所以其法理意义在继承了罗马法的现代民法体系中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比如《拿破仑法典(法国民法典)》(1804年)第544条明示:“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紧接着的545条又明示:“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也就是说,每个公民之所有权的不可侵犯不容质疑;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由代表这 一利益的公权机构对其加以某些不得已的限制,也必须是在事前和公正补偿的前提下, 这种限制才可能是合法的。
其次,罗马法的形成本身,就是人们通过权力博弈而赢得公民权益的一个经典范例。以《十二表法》这部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为例,罗马实行共和以后,依然是由贵族祭司团执掌法律,法律的主要内容也还是不成文的习惯法,由此而使平民的利益在诉讼中受到巨大的损害。于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由平民发起成文法运动,力图“用制定法律明文来限制贵族的专横与压迫。”公元462年,由平民中产生的、其职责主要在于保护平民利益、限制贵族官吏专横的“护民官”特任悌留士·亚尔萨倡议,由平民组成委员会,起草法律。而贵族以平民不懂法律为由对此倡议坚决反对。此后平民始终坚持自己的诉求、连续八年选举亚尔萨连任护民官,终于至公元前454年,贵族与平民相互妥协而达成协议:立法委员会由贵族担任,但所拟订的法律必须经由贵族和平民有产者组合 而成“百人团会议”批准方能生效。在派人赴希腊研究梭伦法律制度之后,于公元前45 1年由百人团会议选举贵族十人,负责起草成文法律,完成后经百人团会议通过、并经 营元老院批准,在法庭公布并刻于十块碑板之上;因为感到其内容仍不完善,遂于该年 底另选十人(据说其中有平民当选),制定了补充性法律条文,再刻于两块碑板之上,与 前十块合称“十二表法”,而该法典的颁布标志着平民在私法范围内已经争得了与贵族 平等的地位(注:详见周楠:“十二表法”,载周楠、吴文翰、谢邦宇著:《罗马法》 ,第362—363页、373页,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由此可见,《十二表法》首先在 法理的根据和立法程序的启动这第一级制度平台上,就是通过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反复博 弈而直接肯定着双方的利益诉求及相关的法权。人们评价这种权力博弈的巨大意义:
“十二表法”的建立与巩固完全是罗马共和国建立不久与平民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在这个使罗马跨入伟大民族之列的历史过程中,斗争的坚决、妥协的明智、平民的成熟、贵族的开明,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成文法的制定把法律从贵族垄断的秘藏变成了直白的文字,因此明显有利于平民。但另一方面,制定与阐释法律仍然依赖于贵族的德性与智慧。整部“十二表法”的基本内容也可以说是混合了有利于贵族的古老习惯与有利于平民的较新规定。在罗马法漫长的衍生史中,对“十二表法”的阐释越来越偏向两阶层之间的平等。按照维柯,这意味着“十二表法”体现了一种新的礼法——以平等(aequitas/equity)为特征的人道自然法。而在西塞罗看来,罗马法表明了罗马的政体 是贵族与平民共同统治、并且结合了王政因素的“均衡政体”……共和国的首席思想家 自豪地宣称,在诸政体之中,均衡政体是最可取的:“因为一个国家中必须有最高的王 政因素,某些权力则应授予上层公民,而某些事物又应该留给民众来协商个决定。这样 一种宪制(constitution)首先提供了某种高度平等……其次,它具有稳定性,”(西塞 罗,《国家》,第一卷,45)可以说,罗马法的背景就是以上下阶层的相互承认为自然 法前提的均衡政体。没有这种礼法—政制背景,一切宪政、民法典均不可能。(注:丁 耘:“罗马法何以可能?”,《读书》2003年第12期,第57—63页。)
可见,上下阶层相互承认对方的权益界限为自己权力所不能阑入,这个前提不仅保证了公民个人所有权的地位,而且更使宪政、法治、均衡政体的建构成为可能;而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法理根据、立法原则、立法程序等等法律体系的一切重要方面均为皇权所绝对垄断(所以法律总是被直截了当地称为“王法”和“官法”),是完全不同的(注:详见拙文:“‘王法’‘官法’与宪政法理的根本分野”,《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02年第7期。)。
正因在罗马法体系中,从平民到贵族、甚至皇帝等一切人,他们在作为财产所有者时所遵循的是保障“私人所有权”的统一法权制度和法理逻辑,所以“分立”的、不为政府威权所主宰的财产权利才成为可能;更进一步,这种财产权也才能通过近代产业体系而扩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即如哈耶克所说明的:
地中海地区是最早承认个人有权支配得到认可的私人领域的地方,这使个人能够在不同团体之间发展出密集的商业关系网。……“希腊—罗马的世界从本质上说显然是个私人所有权的世界,从几亩耕地到罗马贵族和皇帝的巨大领地莫不如此,也是个私人贸易和制造业的世界。”(芬利,1973:29)……同样,就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而言,可以说资本主义—和欧洲文明—扩张的起源和产生的理由,是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更为强大的政治统治下,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城市里,最后是在治理宽松的英格兰,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而不是军阀的统治下,近代的产业制度才得到了发展。保护分立的财产,而不是政府主宰其用途,为密集的服务交换网络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一网络形成了扩展秩序。(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致命的自负》,第二章“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第28—3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而对于说明本文主题尤其有意义的是,哈耶克又根据李约瑟的研究成果而特别指出,与“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一个私法楷模”形成最鲜明反衬的,恰恰是以中国皇权为代表的亚洲制度:
这些政府(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相似,但其权力却超过了欧洲)也有效地抑制了私人的首创精神。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中华帝国,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麻烦时期”,文明和精巧的手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反叛或脱离常规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因为它一心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秩序。(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致命的自负》,第二章“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所以正是在中西的这个鲜明的对比之下,哈耶克对宪政政体中财产所有权法理和相关政治哲学原则(如洛克所说的“没有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大卫·休谟在《英格兰史》中所强调的“分立的财产权得到承认,显然标志着文明的开始;……把国家强盛的原因归功于政府干涉财产的权力受到限制”等等)的重申(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 译:《致命的自负》,第二章“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第33—34页,中国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缔结禁止侵夺他人财产的契约如何导致了财产权和正义理念 的诞生,“划定财产、稳定财物占有的公约,是确立人类社会的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 件”等等对于财产权与社会正义之间关系的论述,详见休谟:《人性论》第三卷,第二 章第二节“关于正义和财产的起源”。),才尤其显得醒目。
如世人所熟知,不论是在欧洲社会和法律制度发展史中,还是从洛克、休谟、康德等以后的宪政思想体系中,确立禁止侵夺他人财产的所有权准则、并进一步建立起以充分保障这种所有权制度为基本目的的公共权力和国家形态,都是宪政政体的基础。比如早在中世纪的英国,因为供养了国王的军士等原因而被授予土地的人,他们所享有的“土 地保有权”并非仅仅表现在某一时段内对财产的支配,而是更主要地表现在他们能够通 过法律制度确认自己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是领主所不可侵犯的;所以其法律权利,是与那 些使用领主的土地,因而“土地上无权利可言,无法庭可言”的“非自由土地保有人” 完全不同的:
自由的土地保有人受国王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得到一种国王的令状,以约束领主使其正确对待他们;自由土地保有人与领主之间的争议将在一个(比庄园法庭)级别更高的 、自由土地保有人自己本身就是法官的法院中来处理。(注:[英]S·F·C·密尔松著, 李显东等译:《普通法的历史基础》,第1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法律史证明,从13世纪起,“土地的占有和权利”在英国普通法中的意义,就已经与罗马法中的这些概念的内涵“逐渐趋于一致了”,所以“权利变成了某种类似领主权的抽象的极端的东西。”(注:[英]S·F·C·密尔松著,李显东等译:《普通法的历史基础》,第12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另外,对于确立财产权更具意义的,是欧洲封建时代国王与其封臣之间具有那种不成文的、由习惯法所规定的义务关系,即封臣要效忠于国王、向其缴纳赋税和提供军事服务;而同时,国王也有义务保证其封臣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特别是双方这种义务关系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如果其中一方要求习惯之外的权利,或拒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则被视为违法行为,对方有权以解除契约关系相对抗。”(注:程汉大著:《英国政治制度史》,第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所以国王如果无视甚至践踏贵族的财产权利,则不仅势必引起强烈的反抗、而且尤其将引发人们更加明确、强化法权和契约关系的要求,以此而有效实现对王权专横欲望的限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王约翰即位以后,滥用对领主的权力,他增收赋税、未经由贵族和骑士组成的“大会议”批准即没收贵族的封地、迫害教士并掠夺他们的财产、以取消对自由城市的特许状为要挟而对城市增税。而这些滥用权力对各个阶层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很快就遭到了贵族、教会和城市平民一致的反抗,在武装抗暴的威慑之下,约翰不得不在1215年接受地方贵族的要求而签署《大宪章》,从而确认了在宪政史上一系列经典性的法律准则,其中包括:不经法庭的合法程序,不得任意对国民逮捕、监禁、褫夺财产、驱逐出境;没有可靠的证据,不得对国民进行司法审判;承认教会选举自由;保障贵族和骑士采邑的继承权;国王不得违例加征赋税;重申对伦敦等城市享有自由权利的承认,等等。
正因为具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后来宪政思想家对于国民财产权法律地位的强调,才那样的直接明了,比如洛克所反复申明的:
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在物质对象上所施加的劳动)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注: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篇,27节,第19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注: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篇,124节,第77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绝对统辖权,无论由谁掌握,都决不是一种公民社会,它和公民社会的格格不入,正如奴役地位与财产制格格不入一样。父权只是在儿童尚未成年而不能管理他的财产的情况下才会存在;政治权力是当人们享有归他们自己处理的财产时才会存在;而专制权力是支配那些完全没有财产的人的权力。(注: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篇,174节,第107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而这种使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从中世纪那种“奴役地位”、“绝对统辖权”的状态中 解脱出来,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首要条件,即如亚当·斯密概括的: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服务。……按照自然自由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52—253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可见他是把“完全解除”君主权力对于私人产业的介入,作为“自由自然制度”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
值得强调的是,国民的财产权在国家法律和法理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私人权益的保障,相反,以此为起点而开启的,是一种通过保障“国民个体安全”进而推进到保证“社会安全”的宪政之路,所以早在古典公民国家中,公民个体安全与公共利益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已经清晰地显露出来:
在罗马法和日尔曼法的初期,有着一种颇为简单的理想:维持治安,亦即满足社会对一般安全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在罗马法的古典时期及其成熟时期中,上述那种简单的理想为另一种理想所取代,亦即通过社会制度的安全,换言之,通过满足社会制度中的社会利益的安全,间接地维持一般安全。中世纪后期,由于人们接受了查士丁尼的法律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所以上述那种有秩序地维系社会现状的理想渐渐地也成了这一时期的理想。(注:[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 史解释》,第44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至洛克等人以后确立的近代宪政主义准则就更是如此,比如在康德关于权利的思想中,财产权甚至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即“财产权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制度,它的作用来源于一系列的规则”;(注:李梅著:《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学研究》,第221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所以康德说:“根据自然状态中个人权利(私法) 的诸条件,就可以得出公共权利(公法)的公设。”(注:康德著,沈叔平译:《法的形 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134页,并详见此书第一部分“私人权利(私法)”与 第二部分“公共权利(公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类似的意思,拿破仑在讨论《 法国民法典》时说得更清楚:“个人如何处分其宝石或图画意义甚小,但是个人处分其 土地的方式事关整个社会,这正是社会需要制度规则并对其处分权加以限制的理由。” (注:引自[英]F·H·劳森、B·拉登著,施天涛等译:《财产法》,第118页,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再比如费希特强调,作为国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基本人权 必然延伸的,乃是公民对立法权等政治权利的享有:
在他看来,能够生存是一切人的绝对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正如自由通常应受到国家的保障一样,这种目的也应受到国家的保障。……但是,要真正使生存权得到可靠的保障,公民还必须具有另一种更高的权利,那就是政治上发挥自由能动性,使自己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成为国家的立法者……(注:梁志学著:《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第1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可见在宪政法理体系中,公民的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乃是通向他们不可剥夺地具有立法、管理国家等等公共权利的基石;而宪政制度对于国民这些权利的保障,也是每个公民发挥自己的道德潜能的前提,所以“私法”与“公法”两大体系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撑的密切关联性,本身就是宪政最重要的内容和根本性的内在逻辑(注:所以康德把“公共正义”的内涵定义为“保护的正义、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133页);直到罗尔斯仍然强调,宪政对于国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乃是每个国民实现道德完善的基础:“立宪政体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将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这些道德能力,并随着他们这样做而使他们在整个生活过程中充分发展这些道德能力。”([美]约翰·罗尔斯著,万俊人译:《政治自由主义》,第215页)而与上述法理相反的,则是居身于权力专制性恶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下,人们就只能越来越普遍地通过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等践踏社会正义和蔑视社会道德的路径来维系、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而使社会发展完全悖逆于宪政和法治的方向,详见拙文:“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5期连载),“再论明代流氓文化与专制政体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流氓政治与张铁生现象”(《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也正因为如此,宪政法理这种从国民私有财产权地位的确立进而通向公民社会公法体系的逻辑路径,恰恰就与中国皇权政体的法理逻辑(从规定子民们“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出发,进而确立大救星“统天御宇”、“广有四海”、“代天养民”等无限的普世威权),形成了鲜明对照。
总之,不论是从中国两千多年“蚁民社会”的法权形态及其发展方向,还是从罗马法 以来公民和宪政社会的法权形态及其发展方向来看,其实都不难明白“为什么宪政对公 民人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如果将这两者加以对比,则问题的 结论就更加昭然无隐。当然,对上述结论更直接的印证决非“纸上得来”,因为这个问 题关系最为深切的,无疑还是我们今天现实中的制度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