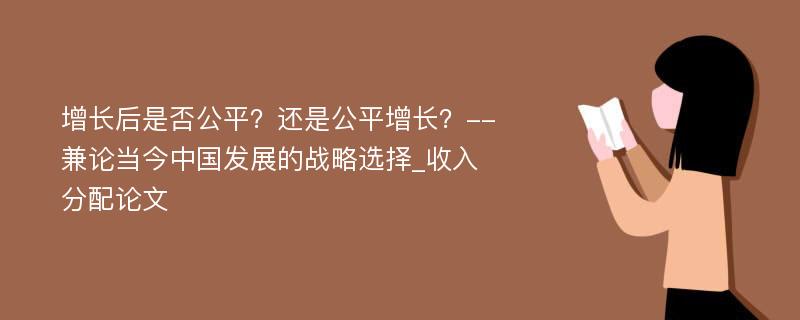
是要增长后的公平?还是要公平中的增长?——也谈当今中国发展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论文,发展战略论文,也谈论文,当今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768(2000)04—0006—04 自从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诞生以来,经济学家用了大量笔墨来检验“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以及从理论上说明经济增长是怎样影响收入分配的;而收入分配是如何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并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少数几个理论,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暗含了不均等的收入分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并一度使“先把面包做大,再来分割面包”的发展战略甚嚣尘上)。近年来,这种现象得到很大的改观,许多文献都在强调收入公平分配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也在从以增长为中心转向兼顾公平的增长。本文旨在剖析两种不同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并期望能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抉择提供一点帮助。
一、增长后实现公平——早期发展理论的应有之意
从所周知,在有关效率与公平的争论中,存在效率公平对立论和效率公平依存论两大流派。其中,在效率与公平对立论中,又有效率优先论与公平优先论之分。将均等分配视为效率的天敌,主张在增长之后再考虑分配问题是效率优先论者的核心思想。
持效率优先论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贯主张“自由是效率诞生的基础,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是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只有坚持市场经济的这种自由,资源配置才会有效率”,而追求收入的均等分配则会损害自由,其结果必然是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遭到破坏,并在最终损害经济增长。这些经济学家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市场是天然的平等派,公平、经济增长都可以在市场运行中自发地形成和实现;相反,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试图人为地将业已公平分配给每个人的收入进行再分配,这无疑是在破坏“公平”。“公平”被破坏后,就会窒息市场机制的激励功能,使人们丧失不断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和压力,并最终阻碍经济增长。
此外,新制度学派早已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为什么要提出界定产权?最重要的依据是这样能够增加经济效率,至于应当如何界定产权以及这种产权的界定是不是建立在收入差距很小的基础上并不重要。换句话说,收入差距有多大不必太在意,“清晰的产权”才是最重要的。以此推论,政府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排他性,以保证产权交易和市场竞争的自由,从而促进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相反,政府若是想方设法去侵犯人们的产权、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势必要防碍经济效率的提高。
至此,我们能清楚地看出效率优先论者的核心观点:即收入分配过于均等不仅未必符合公平的原则,而且还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至于政府“不患寡而患不均”那就更加不可取了。
如果说自由主义理论主要说明了“收入差距太小会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话,那么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则更象在不断“倾诉”一种“不公平的增长观”,即收入差距的扩大还能促进经济增长。
早在50年代,纳克斯和纳尔逊就提出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根源是:人均收入水平过低导致储蓄与投资不足,而储蓄与投资不足又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反过来导致人均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发展中国家极容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或“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之中。那么,如何才能解决此问题呢?刘易斯提供的“答案”是:要实现发展中国家(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增长,只有使收入分配发生有利于现代部门的变化。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必须牺牲均等分配来促进经济增长。60年代诞生的费——拉尼斯模型同样隐含着这样的政策含义:任何试图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努力都可能因抑制了经济增长和减少了就业而给穷人带来了更大的不利。
“倒U型”假说的提出,无疑对这种“不公平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50年代到70年代,经济学家运用不同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基本证实了“倒U”现象的存在,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坚信,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且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对于一个亟待发展的低收入国家,既然公平与效率“二者不可得兼”,那自然是舍公平而取效率。如约翰逊指出:“对希望迅速增长的任何欠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平等的成本都是巨大的……所以,一个渴望取得迅速增长的国家过于强烈地坚持旨在保证经济平等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政策,似乎是不明智。”(注:H.G.Johuson."Pianning and the Marke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Repainted in Money,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George Allen and Unwin,1962.p.159.)
“不公平增长论”还有一个更诱人的理念,即增长是实现平等的必要条件。就象艾哈德所指出的那样,“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辨国民财富的分配,倒不如集中所有的人来增加国民财富要明智得多;何况争辨不休往往会走入歧途,耽误国民收入的增长。有了一个较大的蛋糕,就不难让每个人分得较大的一份,如果只有一个较小的蛋糕,尽管讨论了怎样分法,总不能使每个人多得一点”。(注: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中译本)。)正因为如此,“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就在20世纪中期受到极度的推崇。
二、在公平中实现增长——近期理论与政策的基本取向
“不公平增长理论的要义”是认为公平分配与经济效率无法协调,80年代以来,这种观点逐渐受到批判;相反,“在公平中实现经济增长”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么,提倡“为了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不宜过大”的主要依据究竟何在呢?
(1) 在坚持公平与效率对立的学者中,以美国经济学家罗尔斯为代表持公平优先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分配不均会损害工作热情,降低工作效率。他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均等一定会导致个人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或者说结果的不平等将会导致和加深起点的不平等。原因很简单:在市场经济中,金钱与权力常常是可以互换的。收入差距一旦扩大,获得更多金钱的那些人很可能获得更大的权力,而权力的不均等又能成为收入财富进一步扩大的源泉。这一切意味着:收入差距扩大后,收入和财富的多寡常常不能取决于人们的努力程度;然而,人们付出的努力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他们的工作热情就会大打折扣。当这种情况普遍发生时,经济效率的降低也就不言而喻了。相反,缩小收入差距,使分配较为公平,往往可以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2) 收入分配不均,会影响低收入者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其实,无论经济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收入差距问题最尖锐的矛盾并不在差距本身,而在低收入者所能达到的最低生活标准。如果低收入者的温饱问题岌岌可危,这部分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便十分有限,这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人口的平均素质。从经济增长本身来看,虽然在现有的劳动者既缺乏知识又缺乏技术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常规资本也能获得某些增长,但增长质量肯定是比较低的。因此,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人力资本投资的迅速提高,但要大规模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没有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不可能的。东亚奇迹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快速普及初级和中级教育,雁而在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受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启发,近来许多经济学家注意到: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收入分配对增长的影响,而不是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些文献着重从政治机制来论证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①收入越不平均,低收入阶层的寻租活动就越多,威胁产权的人也就越多。产权受到威胁后,投资者的信心就会大挫,投资减少了,经济增长自然要受到破坏。②AIcsina& Pcrotti 1997年对71国所作的实证研究发现,过高的收差距会造成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影响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的计划,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③由于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中低收入者较多,因而主张采取高税收的人就越多(穷人总希望税收高一些)。税率一旦上升,投资和经济增长就要大受影响。
(4) 收入分配不均会通过市场规模(总需求)来影响经济增长。早在古典经济学时代,西斯蒙第就指出了收入分配通过总需求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因为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是用于储蓄,而穷人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因此收入分配过于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就会使整个社会的积累过多,而总消费需求不足,最终必然导致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生产过剩局面,从而防碍经济增长的实现。相反,收入均等分配除了可以提高穷人的收入以外,还能增加社会总需求和消费,调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促进经济增长。最近,墨菲等人用新经济增长的分析工具提出了一个新的工业化模型。在这模型中,墨菲等人指出,工业化进程主要由工业品的市场规模决定,而收入分配对市场规模的大小有重大影响;并指出分配不均是阻碍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为分配过度不均,就会导致有能力购买工业品的人数过少,此时采用报酬递增的工业化技术就会因无法弥补固定成本而无利可图,而缺少报酬递增技术,工业化自然无路可走)。
事实上,于1994年1月召开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人们所听到的大部分声音是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更不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因为,80年代以来,所有的非洲、拉美国家,贫富差距都极大地拉大了,两极分化程度超过了发达国家;然而它的经济并没有被“刺激”上去,而是越“刺激”越糟,社会也发生了动乱。相反,一些亚洲国家比较注意缩小贫富差距,经济却发展得较快。新加坡政府更是明确提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收入差距保持在最小限度”。
美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南希·伯索尔女士和威廉斯大学教授理查德·萨伯特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平经济学”的思想。他们在《再论贫富不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一些亚洲国家的经验证明,“贫富不均的加剧并不一定是经济成功的副产品。如果政策得当,就能既缩小贫富差距,又提高经济增长率。”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加快同收入更加平等这两者并不矛盾,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近二三十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出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三、中国发展战略的抉择
在饱受“平均主义之煎熬”后,我国郑重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这是考虑到“过多地奢求公平将会抑制效率、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之后作出的正确抉择。事实上,这种分配原则与“不公平增长”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确实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小平同志所设想的那样:“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屠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注: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在“平均主义”已经被驱逐出历史舞台后,我们实在不能重回“极端平均主义”那条“乌托邦大道”了;然而我们能否由此得出分配不均是经济增长之前提的结论呢?回答是否定的。只要我们能清醒看到“公平增长论”取代“不公平增长论”已是当今分配理论与政策的发展趋势,能正确认识到收入差距过大将给效率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就不会为“平均主义越少,经济效率越高”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丧失警惕。
在我国工业化初期,由于资本积累不足,要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除了牺牲一定的公平外,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因此,“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出台,本身就包含了很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告别短缺并迅速走向较严重的相对过剩,消费需求不足正在严重制约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此时,经济增长正期待收入分配能为之提供更大的市场而不是资本积累。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重提缩小收入差距,绝不仅仅是涉及公平问题的思考,而是事关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能否顺利实现的现实抉择。
有的人总是抱着“倒U”假说不放,总是把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看成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寄希望于把“把面包做大”后再来解决分配问题。其实,库氏的“倒U型”假说之所以被我国理论界逐渐接受并广为流传,个中原由除了此假说本身的“魅力”外,还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分配政策的出台有关。事实上,“倒U型”曲线常常用来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政策的合理性。有人甚至指出,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与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假说不谋而合吗?
笔者认为,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阶段,运用“倒U型”曲线来分析问题时要保持相当的警惕:一方面,从统计方法看来,与六、七十年代所不同的是,近年来,“倒U”假说的存在性及稳定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许多研究发现,支持库兹涅茨假说的实证研究不仅使用了不适当的数据和指标(Ram 1998),而且使用了不恰当的回归方程(Ram 1995)。另一方面,从理论上看,“倒U型”假说也有许多可疑之处:①“倒U型”理论的前提是古典经济学,即经济近乎于自由放任。而在一个经济运行受政府强烈干预的国家,其结论能否成立有待思考。事实证明,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不符合“倒U型”假说。②库兹涅茨提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情况,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国际环境、历史文化有着极大差距的国家,其理论的适用性也需要探讨。③“倒U型”曲线更多的是一种实证描述,它本身并不能得出市场机制最终可以自发实现公平与增长的结论。库兹涅茨不过是多一次强调,在发展的初期,市场经济的作用会使收入差距扩大,而在发展的中后期,随着政府干预的增多,收入差距会缩小。
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重视政府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而且能够将收入差距长期控制在较低又有别于平均主义的水平;而我国在饱受平均主义的煎熬后,一度对“收入差距扩大”放松了警惕,对收入差距可能为经济增长带来种种不利更是有些认识不足。日本经济学家南亮进曾经语重深长地指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收入差距拉大了,对此中国经济学界似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是分配过分失衡的确是个必须警惕的危险倾向。中国许多人对收入分配前景持乐观态度,主要是依据库兹涅茨假说,从日本来看,本世纪20、30年代,分配极不公平,但现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其收入分配也趋于均等,甚至比美国还均等,这似乎恰好应验了库氏假设。但是人们没有想一想:日本何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使分配由不均等转向了比较均等的状况?当时在美国占领军强制下,日本实行了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成立工会等重大改革,这样在农村解决了土地占有严重不均问题,在城市缓解了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倾斜、贫富悬殊的弊病,结果迅速实现了分配均等化。这表明,收入分配均等化不能指望自然发展机制,而必须注重制度改革的作用,在发展的同时改善分配格局。(注:南亮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难题》,载《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
毫不夸张地说,确有部分漠视收入差距扩大的人“见猎心喜”,不假思索地拿“倒U型”假说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进行辩护,这无疑是自欺欺人的。他们往往尽力让人相信,“收入差距扩大没有关系,这只是暂时现象,库兹涅茨早就告诉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它自然会逆转”,这无非是在给人们提供一种心灵上的安慰,让他们在差距迅速扩大面前麻木不仁;他们还要让政府相信,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更不能干预,否则就会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显然又是非常有害的。正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理事詹姆斯·斯佩恩在1996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所说:那种“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振兴要通过加剧不平等现象才能实现”的说法,是一种“危险的神话”,现在“应当结束这种危险的神话”了。
收稿日期:2000-0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