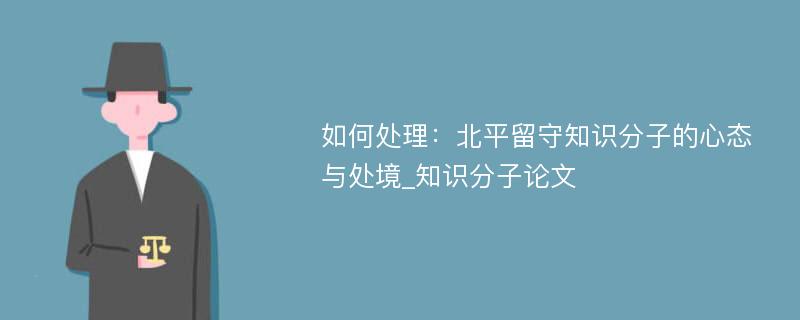
何以自处: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境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平论文,境遇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4-0096-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411 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对沦陷区知识分子的探讨日渐为学界所关注,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地域选择、政治倾向与著述转变等层面。①当然,有时对这一群体的心态和境遇,不免存在着“倒放电影”式的论列与评判。②故而,对沦陷区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交际形式、生存压力与著述环境等问题,仍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笔者不揣简陋,以身处“笼城”北平的知识分子群体为探讨对象,对此问题加以申说。 一、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对于战争之下北平城如何得以保存的问题,北平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主张即出现了分化。部分学者如江翰、马衡、徐炳昶等,出于保存北平古物的考虑,发起了北平为“文化城”的运动。但提倡者主张的北平不驻兵、撤出军事装备,成为不设防城市,被视为有利于日本侵略,从而遭到了傅斯年、鲁迅等人的极力反对。傅氏颇为痛心地说:“北平学者出此下策,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③(P429)在劝说无效后,他还向蔡元培等人写信申明立场。④七七事变后,北平知识分子在留守与南迁的问题上,态度也多有不同。随着大部分学人选择离开,作为留守于北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家的抗战前途、个人的出处去就等问题上,政治心态颇为复杂而微妙。 北平沦陷后,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北平将来的局势,不免存有截然两途的认识。乐观必胜论者以胡适、潘光旦等为代表。胡适即认为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之人,他看到李方桂因国难家愁而滞留北平时,就劝说道:“啊呀!你怎么还在这里?不走等甚么?”⑤(P62)催促其出国留学。而对于那些决意留守北平的学人,他也勉励道:“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⑥(P168、174)潘光旦也抱持着相近的态度,他在作别妻女离平南下之时即预见到:“敌人鉴于我民族实力之不可侮,国际正论之不可拗,及时悔祸,还我河山,则团聚之期,当亦不远也。”⑦(P8)部分知识分子在家人暌隔、国土沦丧之际,仍能相互勉励、弦诵不绝,亦可见他们对中国抗战前途抱有必胜信念的乐观心态。 然亦有学者对抗战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如吴宓在日记中记述道:“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又言“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⑧(P219)吴宓一度也有留守北平之心:“盖宓之意向,欲隐忍潜伏,居住北平,静观事变,置身局外,苟全性命,仍留恋此美丽光明之清华、燕京环境,故不思他去,不愿迁移,不屑逃避。”⑧(P192)后来,时局骤变,他也不得不改变初衷,选择了离城南下。沈从文的心态与吴宓颇有些类似,他初意与城共存亡:“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⑨(P236)但其后来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因资金匮乏而滞留于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叹道:“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⑨(P239)战争似乎并未阻碍部分人对于娱乐享受的热爱,这也使得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顿生愤懑与悲凉之情。 久居沦陷之城的知识分子对于个人际遇、国家前途所持有的心态也颇为复杂,愤懑悲戚、感慨自伤、自嘲自谴各有不同。执教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邓之诚在日记中感慨道:“卢沟桥事变迄今六周年矣!战事了结不知何日,伤今怀古,感慨无穷,瞻念前途,但增悲怛,我怀如此,天意谓何,触笔酸辛,聊识冤愤,不欲人知,自伤而已。”⑩时局不明,学人观国土收复无望,其悲戚心情,并非个案。旧派学人傅增湘面对危局,与友人张元济的信函中则言:“我辈高年,遇此国难,则身家之计亦无从顾及矣。”(11)(P357)困居北平、聊司笔札的谢国桢致友人杨树达的信中坦露了自己的心境:“事变后地方尚称安靖,但消息沉闷,不得朋友消息,夏日冗长,惟以读书自谴而已。”(12)(P79)在沉闷与压抑的政治氛围下,学者们的自伤、自嘲与自谴,也反映了这一留守群体五味杂陈的内心感受。 沦陷区知识分子在出处去就问题上,其个人抉择也颇具意味。有些学者在恪守师道尊严与民族大义之间选择了微妙的平衡。如周作人的弟子俞平伯,在1939年周氏“落水”接受伪职后,即选择与之疏离以保持自身气节。周作人本欲让俞平伯代燕京大学课程,却被弟子委婉拒绝:“一则功课非素习,以前从未教过,亦难于发挥”;“二则接先生之席,极感难继,恐生徒不满意”;“三则去年事变后,即畏涉远西郊”。(13)(P264、265)俞平伯对其师之请婉辞不受,所言“畏涉远西郊”,表为托词,实为持守节操、维护自身清白也。此后的日子里,俞平伯虽有为朋友、亲戚谋职之事请托于周作人,但其个人却能在沦陷之下的北平城始终守持民族大义于不坠,这种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沦陷区知识分子在学术倾向上虽或相近,而政治抉择有时却截然相异。当时的读书人在“真金入火之时”,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压力,群体间难免出现分化,可谓是:“遗老犹应愧蜂蚁,故人半已化豺狼。”(14)(P354)尤其部分留守北平的清朝“遗老”们,战前因与民国政府扞格不入而消极避世;北平沦陷后又日渐活跃于政学两界,某些人还有屈节事伪之嫌,此种情状可谓是当时政治乱象中的又一抹灰色调。 二、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交际 北平沦陷后,留守的知识分子为保持民族气节,多离群索居;其原有学术交谊方式,如拜访论学、聚谈相讨、办报论政等,在日伪的政治高压下变得难以为继。严苛的政治审查与迫害,知识分子处于自身生存与民族大义的双重压力之下,学人之间的交际活动因此变得颇为谨慎。 1.战时中日学人的交往 20世纪20、30年代,大批日本学人来到北平,如鸟居龙藏、桥川时雄、松崎鹤雄等,与罗振玉、邓之诫、陈垣、傅增湘等多有学术交谊。北平沦陷后,在社会舆论、道德评判乃至保守节操的压力下,这一交往变得极富敏感性,“民族大义与学术无国界形成相当程度的紧张”。(15)如何处理纯粹的学术交往和坚守民族大义的关系,成为当时部分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抉择。 以松崎鹤雄而言,与陈垣在战前多有函札往还,请益不断。北平沦陷后,这种正常的学术交谊却随之发生了些许变化。他在一封与陈垣的信函中言:“顷者敝国学界仰慕高风,频属弟问先生之阅历、著述书目,能听其请,赐示先生自叙传及大著书名,则弟当冒风趋谒函丈。奉教到贵校教员细井先生处,拟为此请,未知先生无由请谒也。”(16)(P226)函中所言“教员细井”,乃细井次郎,1939年被派至辅仁大学,名为教员,实则监察校务。(17)(P113)松崎鹤雄欲请陈垣作一自传,但因正在两国交兵之时,他心中又不免忐忑。所言“先生谢俗,不敢冒渎”,大概深知陈垣的高风亮节,料想他必定不愿在此时与日本人交往也。 除陈垣外,松崎鹤雄与北平的其他中国学人也多有交往,邓之诚便是其中之一。(18)《五石斋札记》中对此多有记述。如1943年9月21日:“访松琦深谈,谓颇忧其国濒亡。”(12)(P127)可见,日本虽为侵略之国,然其学人亦有亡国之忧。松崎也曾有向邓氏索要“自叙”之举,初被婉拒,“而坚请不已,乃略叙生平不慕荣利及为学之方以答之”。(12)(P144)抗战胜利后,松崎鹤雄被民国政府敦促返国,但他因久居北平对中国颇怀眷恋,于是写信向邓之诚倾诉不愿离开之意。邓氏又请陈垣代为说情:“松崎柔甫不欲行,将被敦迫就道。顷以书来,辞甚凄苦,未知先生能转托友人为之缓颊否?”(16)(P385)然而,“缓颊”最终未成,松崎被迫选择回国。 另一位日本学者桥川时雄,与北平学人也多有交往。他战前主办“文字同盟社”,编辑发行月刊杂志《文字同盟》;又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因报酬丰厚,平津一带学人多被延聘。1940年,桥川编写《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一书,述及中国学人概况甚详。傅增湘为之作序曰: 子雍桥川君自东瀛来,久居燕京,相知十余年矣。嗣以从事东方文化总会,与余过从尤数。其为学也勤,其治事也勇,其接人也和以挚,盖智力强果而才识开敏之士也。近岁以来,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汲汲以征文考献为务,交游益广,阅见益博,凡故都耆宿,新学英流,靡不倾身延接,气谊殷拳,而吾国人士亦多乐与订交而争为之尽力。(19) 此序作于“庚辰夏六月”,即1940年夏。文中言“久居燕京,相知十余年”,则又知相互交谊之深;中国学人中“凡故都耆宿,新学英流,靡不倾身延接”,亦可知当时中日学人交往范围之广。 又如,曾在北平多所大学执教的汉学家鸟居龙藏,其与洪业等人多有交谊。北平沦陷后,日本人以文化交流为由,强令燕京大学增加一名日本教员。此举遭到了学者们的反对,最终妥协的结果是,聘请鸟居龙藏担任客座教授。校长司徒雷登回忆道“鸟居龙藏博士只提出了一项条件,就是我们得保护他,使他不受日本军事当局的压力。我们向他保证说,只要他留在校园里就行,这事容易办到”;他则表示“既然成了燕京的人,就永远属于燕京”。(20)(P126)鸟居龙藏为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拒绝了所有日本方面的帮助,更不愿接受日本军部的控制和救济,生活日渐陷入困顿。 毋庸讳言,战争之下中日知识分子的交往不免附有强烈的政治含义,且战时日本学人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学术组织中浓重的侵略意图,使得后世学人看待这一问题时多以“文化侵略史学”涵括之。然而,对于北平沦陷区中日学人交往的研究,除了前述视角之外,似亦应回归到当时学术社群交往的情景中做具体分析。可以说,在纯粹学术自由与紧绷的政治张力之间,如何达到客观而公允地评述、论析,是诚可思之的问题。 2.战时中国学人的交往——以陈垣与傅增湘的关系为例 沦陷之后的北平学人多以闭门谢客、潜心著述的形式来保持民族气节,期间学人的交往也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身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其个人遭遇及与傅增湘的关系,颇值得关注。 可以说,陈垣与傅增湘交谊甚笃。傅增湘任教育部总长时,陈垣任教育部次长,傅氏下野后,陈氏接任他做护理部务,掌管大印,相当于代理总长。抗战时期,傅增湘出于诸多原因而留守北平,从事古籍的收藏与整理,心境不免消沉。他在与挚友张元济的信函中称:“祸难方殷,兵戈满地,我辈乃孳孳以考史拾遗为事。真所谓乾坤一腐儒也。”(11)(P359)此间,傅增湘因参与东亚文化协议会(21)并任要职颇遭时人诟病,被视为节操有亏。但是,对于傅增湘与陈垣的关系,后世的论述不免有些失实之处。 陈垣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 陈先生拒不见客,敌人老是麻烦他,要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这名义上是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汉奸组织)他拒绝;敌人要他出来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同盟会会长,他也坚决拒绝。(22)(P41) 孙金铭《坚持对日斗争的陈垣校长》一文对此记述道: 日寇成立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请他作副会长,说这是大东亚最高的文化机构,每月薪资几千元。他义正词严地说:“不用说几千元,就是几万元我也不干!”当他听到日寇拟改请某人出任时,他和这人是老朋友,便连夜去找这位朋友,希望不要答应此事。到了朋友家里,才知道已经答应了,老校长闻后拂袖而去,从此再也不和这位朋友来往。(23)(P51) 事实上,上述所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据史料记载,陈垣所辞“东亚文化协议会”的职务应为副会长,而非会长。此会首任会长为汤尔和,1941年改由周作人继任,“定章是有两个副会长,一个是中国人,即傅增湘,另一个则由日本方面担任,即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平贺,始终没有变换”。(24)(P159)由此可知,上述陈垣的这位老朋友应为傅增湘无疑。而孙金铭所言“从此再也不和这位朋友来往”,则又非实情。观《陈垣来往书信集》所录,陈垣与傅增湘往来函札达45通。傅增湘任“副会长”后,双方亦有4通信函往来。前三封为纯粹学术性探讨,时陈垣发现《魏书》缺页,并校勘补辑,傅增湘索要此页的临摹本,故有函札。抗战胜利后,傅氏患疾,陈垣亲去探望,并写信安慰:“偶阅竹汀自撰年谱,言五十七岁忽得风痹之疾,两足不能行动,目入夜不能见物。然《通鉴注辨正》、《疑年录》、《金石文跋尾》、《元艺文志》、《十驾斋养新录》等均撰次在患风痹之后,尊恙区区,当可以竹汀为例也。”(16)(P66)信中,陈垣借清代乾嘉名宿钱大昕(号竹汀)晚年虽遭遇风痹之症仍著述不辍的精神来宽慰傅增湘,实见老友间情谊之笃。 可以说,北平沦陷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其交往空间与战前相比显得更为逼仄、狭小,如何在出处去就上保持民族大义于不坠,是他们时刻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一忐忑不安的心境下,中日学人和中国学人之间的往来、交际变得更为谨慎也在情理之中。 三、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反抗 七七事变后,北平留守学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在经济生活上,因战时物价腾贵,学人们多四处兼课,甚而易稿、卖书、典当家产以维持生计。在撰述方面,他们倡导有意义之学,多以暗讽、隐喻等撰述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反抗。 辅仁大学是当时学者们聚集的一个中心。因为有德国教会背景的缘故,学校得以在沦陷区存留。那些滞留北平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便纷纷涌入辅仁大学。(17)(P113)因之,这里也成了知识分子潜在抵抗的营垒。陈垣致北平市教育局的公函中即言:“代理文学院长董洗凡、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等为抵制敌伪奴化教育,秘密组织文教协会,奠定地下工作,又与英千里及教授并附中教员等三十余人被捕,迨三十四年七月始次第开释。”(25)(P532)日伪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逮捕使得留守者们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潜在危险。 战时流徙于西南的陈寅恪——因未身处危机四伏的“笼城”——对北平留守者所面临的困境颇多隔膜,曾致信陈垣曰:“北方秋季气候最佳,著述想益宏富。”(26)(P133)言辞中竟不免有些艳羡之意。陈寅恪认为,与南迁学人相较,北平学人既无迁徙流亡之苦,又有书籍可供撰述之资,似应多有著述。然而,留守者的苦痛又非他人所能感同身受。抗战胜利后,陈垣对前来探望的郑天挺感叹道:“我八年没有出门了!”(27)(P552)这种长期枯坐书斋、难与外界交流的孤寂心情,也是留守知识分子无法纾解的苦闷和痛楚。 当时,书信成为学者们互致问候的重要方式。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人对北平知识分子的书信检查日渐严密。作为学界翘楚的陈垣,为避免受到监视和迫害,不得不在信函中欲言又止、顾虑重重。他在1943年底与弟子方豪的信中言:“书收到,敬颂道安,不一一。”今人或不识其缘由,方豪则阐释道,1944年“是先生和辅仁大学处境最险恶的时期,教职员被捕极多,陈先生不能不为学校着想而稍加谨慎了”。(28)(P93)陈垣在与三子陈约的家书中说得更为直白:“乱世家书,凡关于碍检查之字样,均应回避。删去六个字示例。我不说明,汝终不明白。”(28)(P742)可见当时文禁的严苛。当时往还信函因检查而多有迟滞数月者,以致陈垣也不免有“若千山剩人之能声闻邻国也”的感叹了。(28)(P201)“千山剩人”乃明朝遗民、著名诗僧,入清后被流放盛京,禁止外出。陈垣身处政治高压的北平城,数月不得书信,不免有类似的屈身受辱之感。1943年以来,陈垣所撰短篇《北宋校勘南北八史诸臣考》《黄东发之卒年》《李志常之卒年》,皆纯粹考证之作。他从当时颇有寓意的“遗民”之学转而归复纯粹的学理性考证之学,实与当时日渐严酷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1944年初,日军逮捕了英千里、赵光贤、叶德禄等人,陈垣亦有遭受缧绁之虞,故其以文喻意、激励学人的做法,似亦有因之而暂停的痕迹。 具体到写作环境,陈垣亦多艰苦之状。在撰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时,陈氏曾感叹道:“事变以来,五年之间,四易其居,道释二藏,已各斥其一。即有公家图书馆可借,然供求苦不相应”;所谓“禁其为自由之国’民,未尝禁其为忠信笃敬之人也,未尝禁其为危行言逊之人也”,(25)(P107)此非单纯言古,而是藉史影射日本人的禁锢与迫害。战后,陈垣在辅仁大学开学典礼上言:“我们处在沦陷区域,国旗拿不出来,国歌亦唱不响亮,甚至连说话都要受限制了,为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以往的八年是由不动声色的黑暗世界中度过来的。”(25)(P530)故而,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实是借助史学典籍来补偏救弊,正人心,彰士气。 另如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在北平沦陷期间,张星烺不变其初志,任劳任怨,在敌人压迫之下,仍慨然肩起为国育才之宏任。每论国事,其多抱乐观,以日美势力相较,释生徒之忧戚。(29)困居围城之际,张星烺笔耕不辍,在《中德学志》等刊物中撰述、翻译了大量文章。 著名学者谢国桢(字刚主)在友人纷然南下避难之际,却毅然选择北上,在沦陷之域过着书斋式的生活。他在1943年除夕感慨道:“这几年来,我一个人坐在书斋内,常常这样的想,当年认识的好朋友,多半都流散了;有些朋友又都很忙,我又怎好意思去找他。只有躲在角落里,过我仰事俯畜平凡的生活。我不禁失笑。我真成一个商人了。”(30)(P757)在岁寒时节、风雪满庭之际,谢刚主枯坐书斋,追忆当年师友唱和,其孤寂怅惘之情跃然纸上。 其他学人如顾随,在北平沦陷后,即将家中大量宣传、记述抗日的书籍和资料予以焚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执教的燕京大学解散,日军搜捕更甚,他又被迫将自己词集中有关抗日的文字撕下烧毁。(31)(P107、124)对于这种孤寂困苦的生活,顾随在一次祭扫鲁迅的墓地后感慨道:“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绝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32)(P470)为维持生活,顾随亦兼课于中法大学、中国大学,所撰诗文颇重“诗心”,忧国忧民。这种压抑、愤懑的生活境况也使得部分学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钱玄同在北平城沦陷不久即因蛰居抑郁而赍志长逝。而辅仁大学教授余嘉锡,其书房原名“读已见书斋”,抗战后则题为“不知魏晋堂”;在与友人信中自署“钟仪”,以春秋时楚国之俘自喻;其著述自题为“武陵”,以逃避秦乱的逸民自比,寓意不言自明。 在潜心著述之外,生存问题成了困扰学人们的头等大事。学人余嘉锡杜门著述,“淡薄自持,不亏操守。每至饔飧不继时,辄卖书以易米”。(33)(P377)留守北平的学者们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实为普遍现象。当时敌占区北平的很多大学教授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晓市”卖掉自己心爱的图书,换得粮店配售的每天187克的混合面,维持生命得以不死。(34)(P287)学人邓之诚因微薄薪金难以维系丁口众多的家庭,亦处于囊空如洗、为生计发愁的境地。最终,他不得不典卖珍贵藏书。其日记曰:“托松琦代卖《锡珍手稿四种》,可得千金,已略有成说。”归家之后,邓氏摩挲古籍,竟又有些恋恋不舍,“宁饥死亦不欲出手也”。(35)邓氏虽为书痴,然而迫于生计,不数日仍将此书售卖。售书所得,买“稻米六十斤,费一百十四金。于是寒家十四口,两月无忧矣”。(35)典卖书籍是当时留守学人维持生存的不得已之举。上述皆为有教职的学人,其生活尚如此艰苦,有难以为继之虞,那些脱离于高校、无以谋生者,其艰辛又可想见矣。 不仅如此,在日伪的严苛统治下,北平留守知识分子还面临着政治恐怖的压力。为此,他们在表面上虽然呈现出一种避言政事,甚而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姿态,实则多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潜在抵抗形式。1938年俞平伯为徐北汀所临《溪山清远图》题诗言“承平风景依稀见,莫问残山故国秋”(36)(P306)即是这一心态的反映。又如抱疴数载、以衰病之躯滞留燕都的钱玄同,对日军驻兵北大校园、太阳旗贴于自家门首之事,看似轻描淡写地寥寥数笔叙于日记中,实则心境异常愤懑,以致在翻阅《亭林诗集》时,不禁“辛酸泪下”。(37)(P1335)同样,困守孤城的黄宾虹身患白内障之疾,依然恪守民族大义,拒绝事伪,在日常生活与交流中,更多是“在艺言艺”,在信函中也少有言及政治问题。诚如他与友人的信函中所言:“事变淹留,蜷伏尘市,日与古纸摩挲,如世外也。”(38)(P101)困居孤城,日事笔墨,足不出户做学问,也实属当时沦陷区学人的无奈之举。 总之,留守知识分子们注重“诗心”,提倡“有意义之史”,这种藉历史典故影射当下的做法,彰显了他们在政治暴行与生存艰难的双重压力下对个人尊严和道德底线的恪守。与国统区知识分子畅快淋漓的爱国表达相比,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抵抗形式更为多元化:有人选择行动上的政治抗争,也有人选择消极避世的自我放逐,更有人选择枯坐书斋式的道德坚守。当然,在生存频受威胁的境况下,政治沉默与道德抗争似乎成为了留守知识分子普遍采用的方法。 四、结语 随着日本对北平城的占领成为一种常态,留守知识分子们曾怀有的尽快收复故都的热切期望日渐冷却、沉寂,甚至变得迷惘。他们所面临的除了生存之忧外,更多的是一种个体抉择上的无所逃遁与内心情绪上的无处安放。傅增湘在校勘《金兰集》的跋文中即感叹:“城邑既为墟莽,乡里尽化崔苻。亦欲避地苟全,而无山可入,无田可耕,环顾四方,有蹙蹙靡骋之叹。”(39)(P972)傅氏这种愤懑不已而又难以言说的心情,也是当时留守者们所遭遇的共同困境。 那么,对于沦陷区北平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境遇,学界何以在较长时期内缺少应有的关注呢?首先,部分当事人的沉默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身处沦陷之城北平,许多学者过着隐忍苦守的生活。“落水”的周作人曾言:“最初我是主张沉默的,因为有如徐君所说在沦陷区的人民都是俘虏,苦难正是应该,不用说什么废话。”(40)(P719)当然,“落水者”周氏此言无疑含有自我辩白、开脱罪责之意。但这里暂且抛开周氏的屈节事实和政治立场不论,只借用其中所提到的所谓甘愿受难和主张沉默的心态。实际上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的促使下,许多留守学人在后来的追述中多将这段经历有意无意地抹去。 其次,抗战胜利后,留守于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不免有一种不甚自信的心态,他们也需要同人对其操守的承认与彰显。部分人对此颇能报以同情之心。史家缪钺在《著史于夷狄之朝之不易也》中论道:“有中国人士,误陷虏中,不甘事伪朝而拔身南归者,其人虽贤,魏收亦没其善而妄加恶辞,是则可已而不已者也。”(41)他借史事表达了对那种非黑即白道德评判的不满。黄炎培亦言:“诸公羁滞陷区,以湛冥之姿态,扶持正义,维系人心,其处境之艰,用心之苦,无日不在同人怀念与钦敬之中。”(42)(P72)与普通民众相比,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肩负着更多的道义责任,他们通过历史撰述来借古喻今,委婉而隐晦地表达民族正义与国家认同。然而,受制于当时的舆论环境和意识形态,后世的评判不免忽视了他们复杂而纠葛的心路历程。 最后,在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话语下,留守者们也面临着爱国不力的指责和压力,或许这也是他们避而不谈的一个原因。一部分留守者因其爱国方式的隐蔽性,在抗战胜利后的道德审判中有一种不被理解的苦痛;另一部分人因埋首故纸堆与保持政治沉默而招致道德上的非议;更有个别人因对道德操守的底线不自知而抱憾终身。 [收稿日期]2015-11-25 注释: ①相关研究以对沦陷区上海、北平的探讨较为详实。傅葆石(Fu Poshek)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从历史阅读文本出发,重塑了文人群体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的夹缝中所作出的不同抉择。李斐亚(Sophia Lee)的博士论文Education in Wartime Beijing:1937-1945(Ph.D,UMich,1996),论述了北平沦陷区的高等教育和文人团体。另有北京大学袁一丹的博士论文《北平沦陷时期读书人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2013),论述了身陷北平之读书人的进退出处与表达方式,以及这一群体所遭遇的政治伦理困境。 ②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新史学,2003(4). ③王汎森,潘光哲.傅斯年信札·第一卷[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④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上)[J].传记文学,1963(5). ⑤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⑥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⑦潘光旦著,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日记[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⑧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6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⑨沈从文著,张兆和主编.沈从文全集·第18卷·书信[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⑩邓之诚著,邓瑞整理.五石斋文史札记·八[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2). (11)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尺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杨树达著,杨逢彬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13)周作人、俞平伯著,孙玉蓉编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4)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二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15)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J].中国文化,2007(24). (16)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7)对于细井次郎在辅仁的表现,教师启功曾有记述:“日本侵略者不敢接管或干涉辅仁大学的校务,只派一名驻校代表细井次郎监察校务,而这位日本代表又很识相,索性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并没给学校带来什么更多的麻烦。为此日本投降后,陈校长还友好地为他送行,真称得上是礼尚往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了。”参见启功.启功全集·第9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8)邓瑞.邓之诚与松崎等的友谊[N].南京大学报,2007-01-10. (19)[日]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M].东京:株式会社名著普及会,1982. (20)[美]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泽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21)[日]小林澄兄.东亚文化协议会[N].三田评论,1938-10-01. (22)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C]//.陈智超.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23)孙金铭.坚持对日斗争的陈垣校长[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24)周作人.“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C]//.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3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25)陈垣著,陈智超编.陈垣全集(第22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26)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7)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8)陈垣著,陈智超编.陈垣全集(第23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29)万心蕙.沦陷期间之张星烺先生[J].文讯,1946(9). (30)谢国桢著,谢小彬、杨璐主编.谢国桢全集(第七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 (31)闵军.顾随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2)顾随.顾随全集4·日记书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3)周国林.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34)张承宗等.百年青峰[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35)邓之诚著,邓瑞整理.五石斋文史札记·六[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4). (36)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十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 (37)杨天石.钱玄同日记·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8)上海书画出版社,浙江省博物馆.黄宾虹文集·书信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39)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从不说话到说话[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41)缪钺.著史于夷狄之朝之不易也[N].益世报·文史副刊,1942-11-26. (42)黄炎培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9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