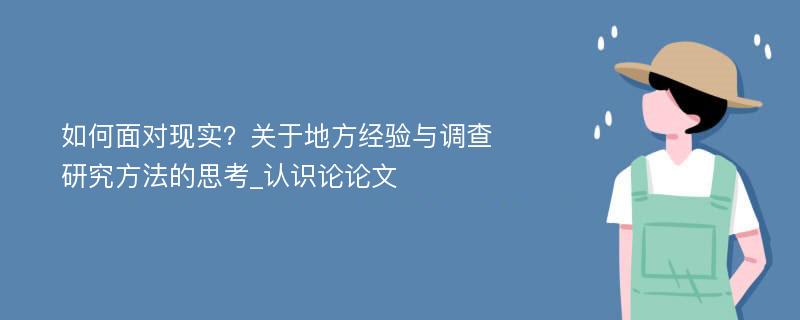
如何朝向事实本身?——调查研究的本土经验及其方法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调查研究论文,朝向论文,本土论文,事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与策略:调查研究的本土经验
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作为社会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式之一,它不仅在大陆社会学界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台湾、香港等地区也相继出现了社会科学调查的热潮(苏耀昌、边燕杰、涂肇庆,2001)。可是,热潮出现的同时,往往也是调查研究被误识和滥用较多的时候。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批华人学者有意识地对调查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学术反思。这些反思涵盖了调查研究的多个环节。首先,就概念(变量)操作化环节而言,往往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理论前提或预设,另一种则是具体指标有问题,不能准确测量需要研究的内容。第一种情形在大陆尤为明显。刘少杰(2001)在对1988-1998年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131份调查报告的分析中发现,这些研究报告有“明确的理论前提”的仅占29%。边燕杰(2001)对此也发表看法,认为这种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些研究者往往误将学术性调查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民意调查,在问卷设计之初便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理论问题的考察。有学者发现,在台湾社会变迁的基本调查中,问卷中的有些题目并不理想,有些意义不明或相当复杂,有些效度不高,也有些题目在社会科学意义上不够充实,甚至在形式上可能有社会赞许性或习惯性反应趋向(瞿海源,2001:58)。
其次,在问卷设计环节上,可能存在“无回应率”或“懈怠选项率”偏高的现象。有些时候,由于调查对象对研究课题不感兴趣或不明白为何被问及许多繁琐而又不知有何作用的问题,往往在一些题目上没有作答(陈应强,2001:101)。受访人的受教育水平、城乡、地域属性和年龄也对无回答水平有比较稳定的影响(严洁,2006)。此外,自填式问卷中答案顺序的不同排列,可能也会影响调查对象的回答(风笑天,2008)。
第三,在实施抽样环节上,抽样方案的精确性并不代表抽样结果的科学性。在社会急剧变迁的中国,人口流动性日渐增强,住址时常变更,各个社区的变化情况很大。所以在抽样实施时,尽管我们初期的抽样方案可能比较细致,但是到了现场却发现很难严格地执行下去。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根据户籍所在地确定调查对象的研究中,抽样实施的难度往往会增加。此外,如果事先没有非常细致地了解各个社区的居住状况,在抽样的具体实施中,往往会损失一些预先设定的样本。这在访问式问卷调查中尤为明显。
第四,在资料收集中,调查对象自身及其所处环境的限制会对调查资料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调查对象自身因素的限制包括两方面:一是调查对象的自身文化素质或生理特征的限制;二是调查对象存在“心理二重区域”,也就是“说假话”的问题(李强,2001)。调查对象所处环境的限制,是指调查对象由于身处某一特定环境,比如高档住宅小区内,或在特定行业工作。研究者如果试图将他们作为调查对象,那么必须要运用适当的行政资源或其他形式的帮助方可获得所需资料。这样一来,由于行政资源的利用或者其他形式的帮助存在,资料收集的质量就可能受到影响。
针对上述这些调查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从事社会研究的华人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经验总结并提出解决策略。边燕杰和李路路(2004)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试图将本土化关怀与社会学理论的一些普适性关怀结合起来,培育和发展调查研究的理论导向,解决问卷设计中理论不足,或指标体系的“水土不服”问题。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城市部分)中,他们特别将“关系”的本土化关怀和社会网络的普适性概念相结合,使“关系”进入社会网络分析的测量体系。刘少杰(2001)针对大陆问卷设计缺少理论前提的情况指出,大陆的调查研究应当选择一些切合大陆社会现实的理论指导自己的问卷设计。这些理论的选择首要前提就是对大陆社会性质及其特点的判断。大陆社会的伦理性不仅决定着指导大陆社会学调查的理论观点和概念框架应当有自己的特殊性,而且决定着大陆社会调查的认识论方法不仅应模仿实证科学的认知方法,还应吸纳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一些理解论方法。蔡禾从结构式访问的调查研究总结中发现,“语境”问题也是影响问卷调查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预设的非充分满足性,即我们假设调查对象回答这个问题时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并不准确或没有考虑到,而致使调查对象丧失语境,难以回答问题。此外,语境的压迫性和语境的熟悉性也会影响到调查员收集调查资料的质量。因而,他主张对调查员进行系统的培训以保证资料收集的质量(蔡禾,2004)。
至于抽样实施的困境,梁玉成(2004)针对中国城市社会调查研究中PPS抽样法和地图抽样法的局限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虽然PPS抽样无法解决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问题带来的困难,但如果在PPS中逐级逐步求精,采取自加权的方法,求得各级各类子抽样单元的加权数,既能减少需要收集资料的数量,又不违反PPS原则而实现了最终抽样单元的等概率入样原则。不过这是以政府的有效协助为前提的。地图法抽样虽然不需要面对PPS抽样方法的尴尬,但却要面对城市人口分布的非均匀特性,城市人口分布密度的极端不平均,会使得随机抽样具有难以估计的误差。不过他认为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削减这种负面影响,即以中心的高密度作为抽样单元规模的指标,在图中作PPS抽样,同时对人口密度高的格子加大抽取样本量。
对资料收集中调查对象的“心理二重区域”问题,李强(2001)从自己的调查研究经验出发,认为至少可以从选题适宜性、心理与风俗习惯、询问方式、测谎问题设置、调查场景控制和人为解释等六个方面着手解决。边燕杰对此作了一些补充,认为“心理二重区域”还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人对同一问题讲假话的程度差异;此外,同一个地区,具有不同年龄、性别、教育、身份等特征的人,由于对政治和社会结构压力的感受不同,可能也会影响他们说假话的程度。
诚然,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本土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学者们上述经验总结也是多元的。他们多是从具体研究实践中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多的是强调一般的程序和具体策略性措施。这种务实的做法非常有助于调查研究方法在本土运用的经验积累和发展。不过,我们在探求社会事实的过程中,除了注重这种实践经验的积累外,还须重视方法论的反思。
二、超越“主义”之争:方法论反思
虽然方法论在我们刚起步阶段可以权宜性地“悬置”,当到了一定阶段就需要反思,且这种反思不能等同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实证主义相对于方法论是个更大的概念内涵,其不仅包含方法论,还有作为方法论认识基础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给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当然包括调查研究方法)的人戴上实证主义的帽子未必适合。谢宇就声称自己并非一个实证主义者,而是一个实用经验主义(pragmatic empiricism)者(谢宇,2004:58)。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时至今日,调查研究的方法论与其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多少有点分离了。其实,这种分离并非实证主义的专利,西方各类“主义”,如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主义、批判主义等也已发生了较大的流变。它们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立场往往不再泾渭分明,甚至开始互相渗透和包容,出现了整合建构论和实在论的哲学思想(吉尔德·德兰逖,2005:147-150)。也正因为如此,法国的后实证主义倡导者布东(Raymond Boudon)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存在很多虚假的方法之争,首当其冲的就是理解(Verstehen/Understanding)和解释(Erklaren/Explanation)(雷蒙·布东,1987:1-14)。从所戴的“主义”的帽子来看,理解应是诠释主义的方法,解释则是实证主义的方法。但在实际运用中,根据不同的议题两者有着不同方式的结合。
因此,我们在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中,完全可以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用墨守西方既往的各种“主义”藩篱,画地为牢。我们更应该结合具体研究议题中每个环节所牵涉的方法论层面进行经验总结,借用和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养分。比如借助现象学社会学对日常生活的情境分析方法和认识论要素,加强调查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阶段对社会事实的理解和把握,或者更敏锐地发现调查研究中的局限和问题。这可从调查研究的概念(变量)操作化中予以实施。为避免抽象叙述,举一个案例进行说明。在国内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一项调查在变量操作化中将社会支持网操作化为四个变量,即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张文宏、阮丹青,1999)。其中财务支持网成员选择的标准是,“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以及“您觉得对自己经济支持很大的人有哪些”。由于作者在文中的量表设计部分,只对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两个变量的操作化给以说明,未对“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给予相应的说明。所以仅从文中的分析结果来看,财务支持网统计表的数字显示,农村居民被访者提到配偶的仅为4.1%,城市被访者提及的也只有5.6%,与西方同类调查结果相去甚远,这样的指标设置可以商榷。在西方国家中,这一指标可能比较适用,但在中国使用,却未必能真实地反映作为网络成员的配偶在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
首先,从财产权观念来看,中国的夫妻间个体财产权观念比较弱。在中国家规礼制中只有家庭财产权观念,没有个体财产权观念,这从日常生活中的“私房钱”可以得到说明。为什么认为夫妻间个人保留一定钱财算是“私房钱”呢?因为在多数中国的夫妻眼中,在“夫妻共同体”的集体财产之外,保留自己个人钱财方便己用是游离家庭之外的私心。尽管这种私房钱数量通常比较有限,但在行为上也不被提倡。夫妻共知共有的财产,仍是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现在核心家庭是主体,故在此讨论的仅是核心家庭)。对于这主要部分的财产,既然是夫妻共有,则使用财产就不是“借”,而是“拿”。“借”是针对外人的,而不是发生在家人之间。因此普通居民向自己配偶“借钱”的概念很弱,尤其是需要“借一大笔钱”时,更不可能想到向自己的配偶借。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个人财产权观念的普及深入,中国夫妻间这种“公共财产权”的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向“收入独立,支出协议”类型转变(邓伟志、徐榕,2001:108)。那时,这一指标可能也会适用于中国的个人社会支持网的调查研究;但在当前则难以适用。
其次,从日常生活来看,夫妻间的财产所有权关系难以厘清。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在此只能简单地加以说明。第一,单从家庭的功能而言,中国家庭目前具备赡养、孩子教育、经济等多种功能。夫妻的结合,即意味着家庭的建立。夫妻在家庭中会有不同分工,以履行不同的家庭功能,诸如获取财富、抚养教育小孩、赡养老人、料理家务等。由此,夫妻在家庭中的贡献也各有侧重点。即使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中,也很难说,丈夫在外所挣钱财是其私人所有。如果这样,妻子则应该得到在赡养老人或抚养教育孩子及家务劳动中的工作报酬。第二,夫妻创造财产时的共同行动使得收获的财产难以分清。这一点在中国大部分农村比较显著。家庭是很重要的生产单位,自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来自耕种责任田的财富,往往是夫妻共同劳动的结果(邓伟志、徐榕,2001:81)。即使流动的农民工,也常常是“夫唱妇随”,夫妻商店、夫妻手工作坊很多,要明确区分夫妻各自财产困难重重。第三,理财的方式和习惯,仍然使得个人财产权难以独立于“夫妻公共财产权”之外。当前,以夫妻关系为主的家庭,其理财方式主要是“收入合一,支出统管(或协商)”,这样,要划清夫妻各自的财产有点勉为其难。
可以说,由于日常生活中有这种难以厘清的财产权,夫妻间难以产生向对方借一大笔钱的行为,更多的可能是夫妻双方共同使用财产。因此,无论是从夫妻间财产权观念而言,还是从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权关系来观察,这一“财务支持网”所使用的指标,难以真实地体现配偶在个人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至少还应该有其他指标的辅佐方可。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则可以说,这种变量操作化忽视了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及由此而生的行动预设——换成舒兹(Alfred Schutz)的现象学社会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忽视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所积累的“手头现有知识”(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社会网络理论尽管有其适用性的一面,但这毕竟是一种“二阶建构”(second order constructs)的知识,财务支持只是基于此上的一个统计概念(变量)。众所周知,统计概念并不能超越特定时空场域而有着普遍且客观的有效性。它是特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孕生品,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直就沉重地负载着特定哲学人类学预设的观念包袱。如果缺乏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统计概念的内涵,则包含着误用与滥用的危险(叶启政,2006:171)。因而,这一统计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理解,要看中国的被调查者在“一阶建构”(first order constructs)的常识中渗进了多少“二阶建构”的知识,或与国外的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间存在多少共通之处。如果在被调查者的常识中没有类似国外社会现实中的夫妻财产权观念(意识),就不会采取从自己配偶那儿“借钱”的行动,也不会将从配偶那里“拿”钱视作“借”钱。所以他们也不会在面对“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的问题时提及自己的配偶。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居民财务支持网的操作化过程中借用现象学社会学的认识论有助于对事实本身的把握。首先可以在概念操作化之前提醒自己,借钱行为是一种有意义的行动。然后在分析这一行动中注重其主观意义及其生存的社会情境,即要了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财产权观念和相应的互动关系,由此来确定我们概念测量时所选用的指标能否接近他们日常生活的实际,并被他们所理解。此时,不管代表诠释主义传统的现象学社会学是否从本体论上将日常生活世界界定为主观世界,我们都已从其认识论的有关知识二阶构造中获得了启发,明确了这一统计概念在本土运用中的局限,找到了对其进行操作化的方向。其实,在调查研究的其他环节中也可以根据具体研究问题的需要,利用有益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资源,提升调查研究的质量。西方已有学者尝试将此付诸实践,并有效地探究了家长支持与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Hossler & Vesper,1993)。
三、如何朝向事实本身
上述这种对调查研究方法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进行整合改造的尝试并不是妄想通过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改造,将其作为一种普适的研究方法推向一家独尊的地位。其实任何想将研究活动定于一尊的努力,不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有害的(黄瑞祺,2005:63)。这种做法只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追问如何朝向事实本身的过程中,不宜墨守西方既往的各种“主义”藩篱,将调查研究的方法论与本体论和认识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尽管它们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关联),以致形成抽象经验主义的习气,抑制了方法论的发展(米尔斯,2001:61)。当然,这并不表明方法论可以完全与本体论和认识论相剥离,或者我们要奉行一种虚无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方法论作为告诉人们在从事研究时应该怎么做的理论,主要探讨研究的基本原则、逻辑、假设和程序等问题。本体论则是人们关于被认识对象本身是什么的思考。认识论是人类认识外在世界的努力。方法论与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和距离,但也有着较密切的关联。库恩曾用科学哲学的语言阐明了这一状况,即关于事实的科学研究通常只有三个焦点,即确定重要事实,理论与事实相一致,阐明理论。这三个焦点既不经常也非永远地泾渭分明(托马斯·库恩,2003:23-31)。
面对这种困境,现象学果断地进行了突破。这一突破的最大贡献可能在于向自柏拉图提出永恒世界(world of being)与形成世界(world of becoming)以来的二元对立本体论提供了转向的可能,即从二元对立结构转向互动共存的二维结构。就社会学而言,从胡塞尔到舒兹,再到伯格(Peter Berger)和拉克曼(Thomas Luckmann),现象学的不断介入为其提供了具有严格基础并多元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他们认为生活世界和有限意义域的社会世界①可以相互建构的论断,在其后的认识论整合中显示了影响。建构实在论(constructive realism)就是典型代表。这些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为调查研究方法提供了更为自由宽松的方法论反思空间。它可以根据具体研究议题所处的社会情境,或暂时“悬置”本体论和认识论,或从周围有用的知识论中找到切合的概念和解说词。这对雷德尔(Layder,1998:133,177)而言,无疑是为建构调适理论(Adaptive theory)提供了好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依据。调适理论将朝向事实本身的努力放在了调适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上。它在方法论上奉行演绎与推断并驾齐驱的策略,在本体论上兼容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认识论上奉行既不采取实证主义也不采取诠释主义的立场(也不是悬置)。如果说雷德尔的努力还停留于理论设想或建构阶段,克雷斯维尔(Creswell,1994:173-185)则已开始以菜单式的陈述阐明怎么做一项定量与定性方法相混合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者可以选择实用主义知识观,采取并行三角互证或顺序性探究等策略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和文本。
由此看来,西方世界在面对如何朝向事实本身的议题中,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论整合方向。方法论与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也获得了相应的选择与组合空间,形成了自己相应的知识论体系。调查研究方法早已不再只是尊奉实证主义,它还从建构实在论中获得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新据点。这也为西方近些年来日趋增长的定量与定性混合型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Research Consensus)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托马斯·库恩,2003:14)。西方社会科学为此付出了上百年的时间,而且仍面临着新的危机。所以如何朝向事实本身仍将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我们也必将长时间地面对这一议题,但我们没必要让西方学术史上出现的众多的虚假方法论之争在中国重演。我们可以暂时“悬置”陷入“主义”藩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直接面向实践,寻求方法论的拓展空间,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或对象,尝试利用本土或西方经验研究中有益的元理论命题或假设。
注释:
①与其对应的是知识结构的两重性:一阶建构的常识和二阶建构的构识(constru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