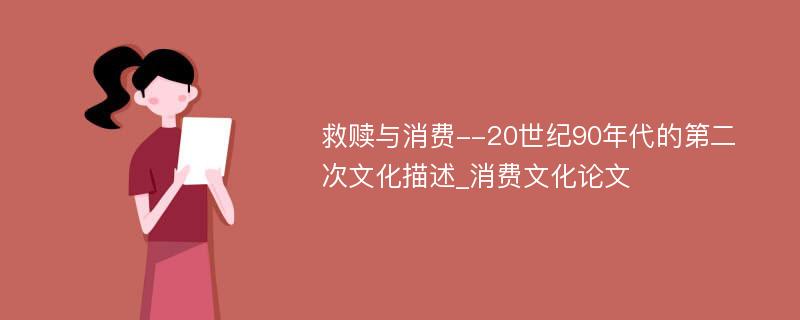
救赎与消费——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毛泽东
或许八、九十年代之交最引人瞩目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便是“毛泽东热”。这无疑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与特定的公共空间之初现、禁忌的重申与对禁忌的消费、主流话语重述与政治窥秘欲望等等彼此对立、相互解构的社会文化症候群。换言之,这是另一个有趣的多重话语的共用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1990年的“毛泽东热”在此后虽盛况略减,但始终持续,直到1993年对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纪念活动中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共用空间中,由多媒体介入、多中心发出的“毛泽东热”,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次对“文化毛泽东”的书写。这是一次重构与戏仿,一次意识形态运作与对意识形态的消费。
事实上,即使作为一种经典的主流话语的运作方式,毛泽东形象也不仅呈现为对革命经典叙事、或曰再现国家的初始“创伤情境”的“民族叙事”的单纯复制,而呈现为一种新叙事策略,一种在偏差与错位中,对神圣、对革命经典叙事话语的重述与重构。类似情形不仅呈现在九十年代重要的“革命历史巨片”或曰“主旋律”电影(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之中,而且更为清晰地呈现在众多的以毛泽东为主角传记题材的故事片、电视连续剧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主流话语运作方式的革命历史叙事、领袖叙事,与作为公共空间初现的、来自与市民阶层的“毛泽东热”,并不是一个彼此对立冲突的话语系统,或中心与边缘间的文化及话语权力间争夺与对抗。事实是,早在八十年代末年,在毛泽东形象再度为主流话语和革命经典叙事所借重之前,市民社会中的“毛泽东热”已初露端倪。似乎是作为一种新的时尚与流行,毛泽东的面像(间有周恩来的画像)——曾作为神圣的标准像的一幅已作为悬挂饰物,开始悄然取代了汽车司机们曾热衷的毛绒玩具、送香瓶(作为“洋气”——想象中的西方情调)、倒福挂坠(传统的平安祈福),大量出现在轿车的前窗上。继而出现了同样图饰的BP机皮套、手表底盘、防风打火机外壳。颇有风靡一时之势。并非如某些海外论者所强调的,这单纯地表达了某种不满或政治抗议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八十年代之交,对“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允诺,再度唤起了一种“大跃进”或曰乌托邦的热望。而整个八十年代,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热气球则以不断的加速度持续升腾。当想象与现实间的鸿沟于九十年代初的清晰显影之时,无疑带来了极为强烈的失望与不满;同时对上层腐败的不断曝光,则加深着这种失落与不满;那么,“毛泽东热”的初现与极盛,确乎有着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经典神话重述的政治与现实意味。它指称着一条想象的救赎与回归之路。同时,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症候,正向人们揭示出一种转型中的大陆中国社会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心态:那便是在一个渐趋多元的、中心离散的时代,人们对权威、信念的不无深情的追忆;以及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线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不无戏谑、亦不无伤感的回首;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来自民间的、对英雄与神话的呼唤;一个正在丧失神圣与禁忌的民族,对最后一个神圣与禁忌象征的依恋之情。它间或寄予着在重写中救赎记忆的愿望。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毛泽东热”在民间的兴起,意味着人们对社会“安全”感与信托感的渴求,对一个并不富足但是(至少在理论上与想象中)没有饥饿与未知威胁的时代的记忆。然而,为大部分论者所无视或忽略了的,正是“毛泽东热”初起之时,毛泽东形象的“载体”。显而易见,汽车、BP机、防风打火机,于彼时,正是作为时尚的象征、消费主义的能指;于是,与其说这是某种清晰自觉的政治行为,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政治潜意识的流露:政治权力与消费主义的置换与合流;同时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与消费化的趋向,正在以不无调侃与亵渎的形式,在实现着对禁忌与神圣的最后消解。
而八、九十年代之交,在“毛泽东热”之中,在数以千万计的出版物与音像制品之中,形成了热点中的经久不衰热点的,是权延赤以跟随毛主席多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录形式所著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此外尚有同一形式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以及《红墙内外》、《领袖泪》、《卫士长谈毛泽东》等等多种与《走下神坛》内容大同小异的版本流行于世)。此书仅第一版便发行十万册,并且在四、五年间一版再版,畅销不衰(姑且不提多种盗印本与改写本)。有趣之处在于,《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不仅成为一本极端成功的畅销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毛泽东热”的基调,成了这一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的题解。而这本为数百万人争相购买并为之热泪盈盈的作品,事实上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主流话语及话语策略转换中最为成功的一例。“走下神坛”,正是这一次“毛泽东热”的真义之一。如果参照宋一夫、张占斌先生的见解①,将五十年代的“毛泽东热”视为一次“造神”运动的开始,将六十年代的“毛泽东热”视作“造神”运动近于疯狂的峰值;那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毛泽东热”则是一次“由神而人”的叙事或曰重述的过程。尽管在此之前有过类似形式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但在《走下神坛》一书中,毛泽东第一次呈现在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呈现在夫妻、父子、饮食起居的场景之中。一个伟人,但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痛苦,在性情中、在情理中。一个因超越了普通人而必须比普通人承受更多、更大痛苦的个人。甚至是一个因伟大而孤独、乃至无助的个人。许多新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此书中被赋予了个人化、性格化的动因与解释。万民领袖,但也难出人伦常情。于是,当人们捧读此书时,他们因新的获知,在某种全新的悲悯与原宥之情中,重温并重写了一份敬仰之情。《走下神坛》一书因之而成了几乎所有涉及当代史的“革命历史巨片”及毛泽东传记片、电视连续剧必须的素材读本,几乎每部类似的影视作品都必然包含了取材于此书的情境与细节。在某种相对低调处理的、情感化、个人化的叙事语调中,重写的历史场景再次要求着读者、观众(人民?)的理解、原宥与分担。从某种意义上说,《走下神坛》一书,不仅为诸多的“主旋律”电影提供了新的素材、叙事策略、语调与距离,而且成了此后盛行的关于毛泽东的畅销书的写作、出版及购买必须参照的蓝本。诸如《毛泽东传》、《我眼中的毛泽东》、《生活中的毛泽东》、《1946-1976毛泽东生活实录》、《毛泽东的儿女们》、《毛泽东逸事》、《毛泽东轶闻录》、《走近毛泽东》,如此等等,均首版数万、数十万册不等,并遍布各大城市的书店、书摊,成功畅销。与此同时,伴随着“毛泽东热”,六十年代及其“文革”歌曲在电子音乐伴奏、流行歌手的演唱中再度流行。以《怀念你,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湖北音像出版社,张咪、杨宗强演唱)为主题,全国各大音像出版社出版了数百种毛泽东颂歌、语录歌的录音盒带和CD②。这是一次真正的流行,在经典的高音喇叭的有线广播中,在电台、电视台、在形形色色的演唱会、综艺类节目,在卡拉OK厅、KTV包房、在家庭卡拉OK的热烈中,在露天的群众舞场和昂贵的高档舞厅。对年轻人,这是一种新鲜的时尚,对中年以上的人们,它是一份跨越了四十年的、亲切、稔熟的、“个人”的回忆。1993年,法国钢琴家克莱德曼访华,在北京于容数万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出,他的拼帖式的、极为优雅而兼有滑稽剧表演的演出风格,他在中国名传遐迩的细腻而煽情的《秋日的私语》,固然引起青年观众极大的热情,但只有当“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全场才真正进入了狂热的状态。
如果说,围绕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权力话语以新的叙事策略、语调,在一次由神而人的叙事过程中,试图再度整合“讲述(重述)神话的年代”③,而在市民社会中则在一种“新”的时尚中表达了他们的现实情绪,安全感需求;那么,九十年代初年,两桩一度沸沸扬扬的花边新闻、热门话题,则揭示出另一个时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意义。一则是彼时为各种娱乐、消闲性书刊争相刊载、转载的某近年来专事扮演领袖的特型演员在全国各地的综艺类文艺晚会上索取高额出场费,并偷税漏税的花边报道;另一则是关于六、七十年代最为重要且著名的作曲家李劫夫的女儿状告几个音像出版社盗用李劫夫作品、侵害其署名权、著作权的跟踪报道。此案以原告胜诉、其中两个出版社公开道歉并赔款而告结束。尤其是在后一例之中,生产于六、七十年代的、曾作为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及意识形态工具的文化制品,在这桩署名权、著作权的诉讼案中,剥落了其作为社会共有、“精神财富”的“惯性”想象及指认方式,显露出其作为私有财产的价值与价格。这两则花边揭示了在“毛泽东热”的背后,一个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毛泽东热”极盛的1990年至今,这已然是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一度为人们作为愚昧与极权产物的而鄙夷的毛泽东像章,此时成了极有价值的个人收藏品,并重新制作、销售;各类当年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袖珍《毛选》四卷合订本、毛泽东像以极为昂贵的价格出现在外国游客、旅居者出没的场所;“文革票”早已在集邮界一炒再炒,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品;甚至“文革”中的各类油印小报,也已奇货可居。如果说,“毛泽东热”的产生有着其且深刻、且多元的社会、文化、心理成因;那么,它的极盛与流行,同时包含着当代中国政治揭秘/窥秘的消费、供求关系于其中。它确乎是一次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同时是一次极为典型的生产/消费过程,一份极有中国特色的消费主义文化时尚。其中主流话语与消费主义文化彼此冲突、又彼此借重,互相解构又不断合流。如果说,九十年代主流叙事所借重的一个“由神而人”的过程,再度试图由神圣、膜拜、敬畏或敌视而为理解、悲悯与原宥,从而实现新的文化整合;那么,为这一策略始料不及的是,这份悲悯情怀也将抹去神圣偶像的最后光环。如果说,“拆毁的殿堂还是庙,扯下来的神像还是神”;那么,在“毛泽东热”之中,消费禁忌、记忆与意识形态的热浪却有力地消除着“殿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神圣的超越与市民之红尘间沟壑。或许可以说,这是又一处中国大陆特有的、重叠在一起的黄昏与黎明,又一次时代的终结与开始。
1993年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中央电视台在毛泽东故乡韶山举行的大型文艺演出,似乎是一个有趣的例证。文艺演出的前半部分,是壮观的合唱队演出的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颂歌联唱,气势磅礴,雄风犹在,再度显示社会主义合唱艺术的恢宏与魅力。但在为这一特定的时刻谱写的童声独唱中却出现了这样的词句:“我问妈妈他是谁?/妈妈说:他是天上的云,/他是墙上的灯,/他是勇敢的老山鹰,/他是勤劳的小蜜蜂。”在对“文化毛泽东”的多元而又共同的书写中,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演变、一次全新的权力更迭与转移正在发生。
“原画复现”
在消费记忆、意识形态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中,“文革”时代的特定产物:知青群落、知青文化与写作、以及关于知青的话语演变与更迭成为另一个丰富的文化/消费文化的症候群。
从某种意义上说,盛行于八十年代后期的“知青文学”这一称谓,不仅指称着一个特定的作家群落,指称一种特定的被叙事件,而且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多重缝合的叙事样式,一个极为特殊的、为多元决定的话语所穿行的文化空间。它是无虚饰的告白,又是心灵的假面;是伤痕的展露,也是精神财富的炫耀;它是一代人特殊记忆的书写、删改、补白或虚构,同时是“寻根”——对民族文化记忆痛苦绝望的追寻与质疑;它是先锋文学间或涉足的场景,也是女性写作不时介入的空间。一如八十年代的历史文化反思运动,实际上是夭折的政治反思文化的伸延或曰其转喻形式;而“知青文学”无疑继“伤痕文学”、“反思小说”之后,直接负载着沉重的、令人难于负载的文革/现实政治记忆。
然而,不同于“伤痕文学”或“反思小说”,知青文学这一特定的话语空间,包容着远为繁复的情感与陈述。与其说这是另一种控诉,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无限萦回的怀念与追忆;与其说这是一份忏悔,不如说它更近似于一份光荣与梦想的记录;与其说这是某种历史的沉思,不如说它是不能自弃、不能自己情感立场。于是,“知青文学”似乎作为一种特例、一次特许,联系着文革记忆、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微妙的错位与汇合。事实上,从《绿夜》到《大林莽》,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金牧场》,甚至《麦秸垛》与《岗上的世纪》④,典型的或不甚典型的知青小说始终以青春有悔、但无悔青春的、痛楚的、但昂扬或低回的基调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话语相错位。然而,它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特例,获得一种特许,正在于它是以一种强烈的情感而非理性的姿态固执着一份遭重创、但不自悔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激情。这无疑是曾为、而且至今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嘉许的精神与叙事基调。事实上,就知青小说而言,它与其说是拒绝清算文革时代,不如是拒绝清算自己的青春记忆。如果说,米兰·昆德拉将六十年代东欧的文化态势描述为“一代人清算自己的青春”⑤,那么,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似乎是相反的情形。对于在文革十年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的一代人说来,“向‘四人帮’讨还青春”、或“从我们的年龄中减去十年”的口号显得太过轻松与廉价,而清算、否定自己的不寻常的青春则太过残酷、绝望。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大众更渴望的是想象性地、以“恶梦醒来是早晨”式的话语,告别这段陡然成为历史的不堪记忆,并在为了忘却的欢笑中强化一种“重新开始”或新生的幻觉;如果说,不断获得轰动效应的“伤痕文学”,是在虚构的英雄与温情中,试图从历史中拯救个人;那么,知青文学所追求的,则是从历史的灾难、劫掠与罪恶中救赎自己——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于是,他们几近绝望地尝试将自己的青春记忆从历史和关于历史的话语中剥离出来。这无疑是一种徒劳。于是,一种浸透了创楚的理想主义激越,使知青一代,以及知青文学在不期然之间不仅与经典主流话语相汇合,而且与五十年代人的“痛苦的理想主义”相呼应。但正是在那一不断的剥离之中,在对青春记忆、或曰一代人的自我价值绝望的救赎之中,关于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陈述,渐次侵入了个人主义的话语——尽管囿于集体主义的情景、现实与规定。
时至八十年代后期,知青文学以及关于知青一代的表述,已不仅作为一个为多元决定的、为多重话语所穿透的文化空间,而在渐次裂解中成为一个多元的话语场。其中一部分终于加入了主流话语,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而另一些则在渐趋鲜明的实用主义文化与现实中,因其对信念的固执、因其理想主义的纯净与脆弱,而成为所谓失败者与被弃者的陈述;其中最为极端的,则以某种狂热的文化英雄主义激情,在与主流话语不断的遭遇与错位之中,渐次蜕变为一种边缘。事实上,在八十年代的十年中,曾投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代人,已通过不同的渠道(主要是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登上并逐渐入主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舞台;而在文化舞台上,这一代人则已然成为八十年代精英文化的主部与中坚。此间关于所谓“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话语不断衍生、增殖,实际上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化”的实践。这一时期的一部介乎于纪实与虚构之间的作品:老鬼的《血色黄昏》,不期然成了八、九十年代文化断裂的一个标识,同时成了连接这一新断裂带的一座浮桥。作品自传、近于日记式的叙事语调,叙事人与人物无间离的合一与认同,使《血色黄昏》呈现出一种赤裸、酷烈、几近狰狞的“原画复现”的特征。在这幅复现出的、文革与知青岁月的画面中,显露出理想主义话语中特定的、庞杂的内容物与填充物以及其间必然包容的暴力与残酷;英雄主义在现实遭遇中的重创与萎琐;个人主义的绝望反抗与挣扎,却是为了朝向“集体”的认可与接纳。几乎是一个时代、一代人所遭遇的全部悖论情景,一处不断奔突逃离却去而复返的“鬼打墙”。但这一切只是无遮蔽地呈现在一个无反省的、或曰拒绝反省与忏悔的个人回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屡经延宕、终于面世的作品,成了众多的知青写作的底本,成了稔熟、绚烂的著名画卷于色彩剥落后复现出的一幅原画。它显然不同于“伤痕”、不同于“反思”与“寻根”,它只是一阕个人的话语,它只是以一种赤裸、或曰赤诚的陈述(于不期然之间完成了由英雄主义的社会理想向文化英雄主义的转换),在要求着“集体”/社会对个人英雄行为——将屈辱、放逐作为考验来承受的个人、理想的纯净与赤诚予以追认。似乎是为某种青春情感的固执而索取的必须的代偿。
记忆的“价格”
然而,有趣之处在于,《血色黄昏》在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并一版再版之时,它所唤起的,并非对作品无反省、拒绝忏悔的盲目与狂热的触目惊心,而在一幅复现的原画所突然涌出的一股强烈的怀旧与留恋的热浪。事实上,《血色黄昏》比此前诸多的知青文学及关于“第三代”、“第四代”的话语更为直接地引动了一代人的记忆与“正名”的渴望。于是,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另一番热烈景象之旁,在《现代艺术展》的轰动之畔,《魂系黑土地》——大型图片、实物展在历史博物馆隆重开幕。一个并非偶合的时间和地点,表明了此一代人固执于自己的青春记忆与记录、顽强而曲折地试图进入历史的时刻与线路。同样拒绝忏悔的、“青春无悔”的主题再次应和着一种悲壮、激进而盲目的“世纪之战”的主旋。继发的一次跨越八、九十年代的、持续的对“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的追忆、讴歌,继《血色黄昏》和《魂系黑土地》展览之后,大量关于知青运动的回忆录、报告文学、准“历史”写作,制造了一种新的畅销书类型和新的畅销书作者。其中引人瞩目的有:《大草原启示录》、《中国知青潮》、《中国知青部落》、《风潮荡落——中国知青运动史》等数十种作品。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症候,其中始终深刻地持续着一种关于“青春无悔”——对青春记忆、自我和历史的确认、一种已然入主社会舞台的力量所推动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实践,和“血泪记忆”——反思、控诉、质疑历史的精英主义文化实践之间的论争与冲突。然而,后者明显地迅速处于劣势。这不仅在于前者无疑为某种主流话语所支持,而且潜在以经济实用主义的宏观政治经济学以及持这一立场者的经济政治实力为前提。同时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的主要趋向相汇合,它应和着中国大陆特定的政治窥秘渴求,成为即将奔涌而出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先声。从某种意义上说,刚好是历史控诉类型的写作者(或者说,是这一立场之表象的攫取者)更为成功地将所谓知青历史的写作转换为书写暴力、乃至色情的绝佳载体之一。与此相伴随的是盛极一时、几为时尚的“知青返乡热”。显而易见,这并非《南方的岸》、或《心灵史》⑥式的回归,而更近乎于某种衣锦还乡式自我印证,或者是一种新型的旅游项目的兴起。在这一领域,消费主义文化再度以消费意识形态的方式崭露头角。
这一知青、“老插”怀旧与复现青春记忆的文化症候与社会时尚,于九十年代的北京、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潮头中被直接转换为一种消费方式与消费时尚。九十年代初,在北京不同的繁华地段,出现了名曰“黑土地”、“向阳屯”、或“老插酒家”的中、高档酒店、饭庄。始作俑者别具匠心地设置了一盘盘土坑,令食客们盘腿围坐炕桌,而且供应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宽粉条炖肉、贴饼子、棒茬粥、蚂蚁上树、老虎菜,当然亦不乏各式东北风味的精美菜肴。即使是乡野风味的“粗茶淡饭”同样价格可观。开业伊始,“黑土地”、“向阳屯”等等门庭若市,别是一番热闹辉煌。它们不仅一时间制造了一种新的时尚,一个极为流行、时髦的社交场所,而且实际上在鲁菜、粤菜、川菜一度流行之后制造了东北菜的知名与流行。一如四处张贴的“老插酒家”的征联启事云:“这是老插们怀旧、寻梦的理想场所。”在昔日知青(或曰其中的“成功者”)找到了“怀旧、寻梦”、相聚之地时,他们所获得的已不再是复现的“原画”或记忆中的时光,而是被复制、被出售的表象、仪式与“味道”、某种消费方式而已。一种明码标价的“记忆”。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黑土地”餐馆中独辟一壁令当年的“北大荒人”的人们在此放置他们各自的名片。其中故不乏各界名流,但最为多见的是名目繁多各类尚不见经传的贸易、物业、房地产、广告或各种名目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名目与头衔。于是,不无悲壮的、黑土地上的历史记忆与现代都市的交际方式,激情、感伤的怀旧追忆情怀与功利主义现实目的,对“无悔青春”的想象性重返与奋斗成功之路(以金钱与消费为绝对及唯一尺度)的展露与认证,便不无“后现代”意味地缝合、或曰拼帖在一起。一个新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与现实甚至超越了八十年代由“北大荒精神”到“大碗茶奇迹”的转换⑦。
而此间,李春波的一曲风靡全国、流行城乡的《小芳》,似乎作为一个更为有趣的例证,标明了一个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发生与发展。作为一首“后知青”歌曲,《小芳》以直白的词句、简单的曲调,在模仿并改写了当年的知青歌曲。一洗当年的激情、忧伤与无望,《小芳》轻松而不失真情,浅直却不乏诚挚。这显然不是一幅复现的“原画”,而更像是一种“黑土地”、“向阳屯”式的越味与消费。与其说它是一份痛苦的追忆,不如说它是一份因距离而获得的安全感,更近于某种优越与奢侈。但更为有趣的是,这首为了流行/消费而制造出来的通俗歌,确乎流行全国、盛极一时,但它却不是以其制作者预期的原因、预期的方式流行开来的。如果说《小芳》的初衷,是以“有一个女孩叫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帮我渡过那个年代”来加入那个消费记忆、安全而优越地回首青春岁月的时尚;那么其始料不及的是,真正使歌曲获得流行的,却是另一类人、另一种成型中的社会空间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小芳》直白、简单而诚恳的风格所吸引、为歌中那留着长辫的、朴素的农村少女所感染的却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涌入城市的、离土离乡的农民,和对中国农村只拥有想象性体验的新一代都市人。《小芳》在这些新的都市边缘人和都市青年中大受其欢迎。对遥远旧日的轻松回眸,为当下身受的情感所取代。与此同时,毋须记忆的铺陈,一个传统的少女形象,加上滥殇于通俗歌曲中爱情情境,满足了都市边缘人的文化需求,同时满足了都市青年的某种心理匮乏;而直白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则作为一种别致的趣味,应和着一种不无调侃心态中的返朴归真的愿望。没有人在意诸如“帮我度过那个年代”一类有着特定所指的词句。于是,李春波的又一首成功的流行歌便成了为这一特定消费需求而制造的《一封家书》,不再借助回忆或想象的由头,而成了一个极为寻常、或曰日常化的情境,一封最为普通家信。甚至不再保留最为简单的歌词韵脚,这一次,他直接以口语入歌,以“此致敬礼”一类的套话,在城市民工、类民工心目中唤起此情此景、形同身受的感受,而在都市青年中则传递出一种反讽、一种无聊与洒脱。不再为诸多不平、不甘中的追忆、反思、正名或“让历史告诉未来”等等式的超越性目的所赘,仅仅是一种状态的呈现,一种对“新状态”文化的构成与加入。于是,李春波的歌曲和艾敬的《我的1997》⑧等等一起,形成了本土通俗音乐的一个重要类型:城市民谣。都市与消费开始取代对意识形态与记忆的消费,以其渐趋成熟形态占据着新的文化空间。
一个未死方生的时代。一次再次地,人们在消费与娱乐的形式中,消解着禁忌与神圣、消费着记忆与意识形态。一个不再背负着不堪重负的未来固然令人欣喜,一个不仅拥有官方说法的前景亦使人快慰;但一个全然丧失了禁忌与敬畏的时代是否便是一幅乐观主义的图景?我仍然只有描述的权力与可能。
注释
①宋一夫、张占斌《中国:毛泽东热》,北岳文艺出版社,1951年5月第一版。
②1992年3月止,畅销的关于毛泽东的录音盒带还有12种:分别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颂歌献给毛泽东——永恒的怀念》,中国音乐音像出版社,《大救星》,扬子江音像出版社,《太阳红》,武汉音像出版社,《毛泽东颂歌》,《北斗星》,海南音像出版公司,北京音像出版公司,《中国歌潮——毛泽东》,广东音像出版社,《万众齐唱——红太阳》,太平洋音像出版公司,《毛泽东颂歌大联唱——红太阳》,中国长城音像出版社,《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语录歌曲》,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
③美国电影理论家汉德森语,对于一部叙事性作品的意义说来,“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译文刊于《当代电影》,1987年第5期。
④张承志《绿夜》,《金牧场》,孔捷生《大林莽》,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雨》,铁凝《麦秸垛》,王安忆《岗上的世纪》。
⑤前波兰作家米兰·昆德拉《笑忘录》。
⑥孔捷生《南方的岸》,张承志《心灵史》。
⑦80年代曾一度宣传了几个自东北建设兵团返城的知青,从卖“大碗茶开始”,终于成就了又一番大事业。
⑧艾敬的《我的1997》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它同样在一种极为口语化、歌谣化风格中,将间或被称之为“大限”的1997——香港回归放置在艾敬的个人际遇之中,它由是面不再呈现一个历史的时刻:“我的1997你快来吧”,只为了“我也可以去香港。”
标签:消费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血色黄昏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