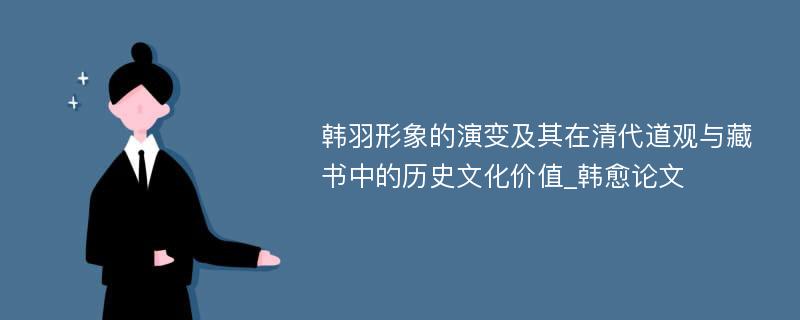
清代道情、宝卷中韩愈形象的演变及其历史文化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情论文,清代论文,历史文化论文,韩愈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152-05
清代有关“湘子仙话”的道情、宝卷中融会了韩愈的故事。没有“湘子仙话”,韩愈故事的承载、演绎和传扬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然而反过来,没有“度文公”的情节,“湘子仙话”也必将失去它应有的丰富和趣味:二者可谓彼此依托,相映成趣。进一步说,韩愈故事在道情、宝卷中虽然是因依“湘子仙话”而存在和传扬的,韩湘子这个人物之于韩愈故事的情节的推进、环境的展开和脉络的走势,都至关重要而不可缺少;但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以韩愈为中心再来品阅这些俗文学中的“湘子仙话”,则韩湘子便成为韩愈故事中的陪衬人物了。笔者关注这些“湘子仙话”讲唱文学,重点就在于探讨其中的韩愈故事与韩愈性格,而这种探讨对于“韩学”的研究也很有意义。
一、有关“湘子仙话”的清代道情、宝卷版本考略
清代有关“湘子仙话”的道情、宝卷本子很多,比较重要的,笔者认为有4种:《九度文公道情》《蓝关宝卷》《白鹤传》和《湘子传》。现略述如下:
《九度文公道情》版本较多,名称也不一致。有清咸丰九年己未(1859)经纶堂刻本和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公志堂刻本以及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永州大雅堂刻本《新编韩湘子九度文公道情全本》。其中,公志堂本国家图书馆有藏,大雅堂本吉林省图书馆等有藏。吉林省图书馆还藏有长沙芸香阁订正、积经堂梓清末刻本《韩湘子九度文公道情全本》,以及民国初年重镌《监本九度文公道情》和石印本《韩湘子九度文公十度妻》,版心亦均为《新编韩湘子九度文公道情全本》。又有清刊本《新编韩湘子九度蓝关道情全本》,内容与《九度文公道情》一致,馆藏不详。《九度文公道情》一般为上中下三卷,有“出身过继”“议婚成亲”“韩愈责侄”“训侄遇师”等共23节,最后一节为“走雪得道”。
《蓝关宝卷》又名《绣像韩湘宝卷》,题“云山烟波钓徒风月主人撰述”,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据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刊本重镌,上海翼化堂藏版,吉林省图书馆等有藏本。内容有“韩会求子格苍穹,钟吕湘江度白鹤”等共18回,最后一回为“全家证果朝王阙,玉旨褒封大团圆”。
《白鹤传》又名《韩仙宝传》,版心为《新刻韩仙宝传》,光绪九年癸未(1883)重刊,版存保宁府观音堂,上海图书馆有藏本。内容有“白鹤童思凡受贬,仙芦柴惹祸投胎”等共12回,最后一回为“林英度归观音座,婶母度为土地婆”。
《湘子传》又名《湘祖成仙传》《元阳宝传》《韩祖成仙宝卷》等,版心为《新镌韩祖成仙宝传》,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京都斌魁斋据道光元年辛巳(1821)刻本刊刻,泽田瑞穗旧藏,现藏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又有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新刻《湘子全传》经元堂藏版及光绪八年壬午(1882)上浣榴峰道士题本,版心均为《新镌韩祖成仙宝传》。《湘子传》内容有“出身过继,三天鹤临海投舍”等共24回,最后一回为“满门成仙,无相城六合归根”。
“湘子度文公”的故事,原是从晚唐五代宋时古小说中演绎而来。到元代,出现了杂剧《韩湘子三度韩退之》(纪君祥)、《韩湘子三赴牡丹亭》(赵明道)、《韩退之雪拥蓝关》(同前)以及南曲戏文《韩湘子三度韩文公》(佚名)、《韩文公风雪阻蓝关》(佚名)等。虽然均已佚失,但从戏剧题名可以推断,“湘子度文公”故事在元代就已经成形了。明天启三年(1623),长篇白话小说《韩湘子全传》(杨尔曾)面世,《蓝关宝卷》情节内容与这部小说高度一致,当是据以改编的。而此前最晚到明万历元年至万历二十年(1573—1592,即《金瓶梅》万历本出现的时期),就已经有“韩文公雪拥蓝关”的道情在民间演唱,因为《金瓶梅》第六十四回有这样的描述:“……子弟鼓板响动,递了关目揭帖。两位内相看了一回,拣了一段《刘智远白兔记》。唱了还未几折,心下不耐烦,一面叫上两个唱道情的去,打起渔鼓,并肩朝上,高声唱了一套‘韩文公雪拥蓝关’故事下去。”
有研究者还考论,道情《说唱十二度韩门子》(已佚)与《韩湘子全传》有渊源关系①;而现存《韩湘子九度文公道情全本》情节内容上与《韩湘子全传》及《蓝关宝卷》有不少相异之处,却与其他宝卷如《白鹤传》《湘子传》等基本一致,可知此《道情全本》与《说唱十二度韩门子》原非一个系统,却又与《白鹤传》《湘子传》等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总之,历时地看,道情和宝卷固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元曲及明代小说、传奇等同类题材作品的影响;而共时地看,这些俗文学(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作品)在其形成和流传的过程中也难免互相渗透、彼此吸纳,因此才造成了这些俗文学文本面貌类同而实际上又互有差异的复杂状况。
在内容情节上,上述道情、宝卷又都把“度文公”作为重头戏,在韩愈与湘子的冲突和互动中,演述了一个又一个精彩故事。并且,道情、宝卷里的韩愈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又不同于晚唐五代宋时期的古小说,与明代小说、戏曲也互有异同。
二、清代道情、宝卷中的“心气”韩愈
韩愈《送侯参谋赴河中幕》有云:“尔时(按指自己年轻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所谓“心气”,中医学指心的生理功能;而从心理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说,“心气”就是志气、正气。有理想愿望,有责任担当,高度自信,持正不阿,是谓有“心气”。这种“心气”近乎孟子所标榜的“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所谓“浩然之气”,是一种贯注了极高的道德修养后表现出的宏大志气、风发意气、凛然正气。清代的道情、宝卷——主要是“蓝关走雪”以前——就再现了一个拥有宏大壮盛“心气”的韩愈。
首先,这个韩愈热衷功名,心怀高远。道情、宝卷中的韩愈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读书人,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科举成名,进而寻求建立功业,以光耀门楣。因此,他努力寻求科第出身是极其自然的。不仅如此,当他功名在身以后,又要请“高明先生”教导年仅7岁的湘子。于是《九度文公道情》和《白鹤传》中,韩愈让人叫湘子出来,先要“问他几句”,“看他志气如何”。《湘子传》还和这两个本子一样,安排了韩愈在请先生之前苦心孤诣训导湘子的细节。这些本子中,韩愈不厌其烦地历数甘罗、姜子牙、孟夫子、朱买臣、班超、窦燕山、苏老泉事迹,勉励湘子向这些功名昭著的前贤学习,通过“十年寒窗辛苦”以求“书中荣显”。这一方面固因大哥韩休临终托孤义不容辞,一方面也是取决于韩愈自己向来所奉行的价值和所坚持的高度的自我期许。而这样的情节恰是古小说及明代小说、传奇所没有的。
其次,这个韩愈刚肠嫉恶,正气凛然。如前所述,“南坛祈雪”情节中,《九度文公道情》把3年“长安大旱”归因于宪宗的“无道”,特别是韩愈领受祈雪御旨时心下想的竟是“君王无道,于臣何干”,无疑较明清其他俗文学作品凸显了韩愈耿介刚正的性格。当然,“官贬潮阳”的情境更集中体现了韩愈的这种性格。事实上,道情、宝卷除了《蓝关九度道情》②以外,均笔调沉重地描述了韩愈“谏迎佛骨”所遭遇的险恶场面;《蓝关宝卷》还与《韩湘子全传》一样大段抄录了韩愈《谏迎佛骨表》原文(有删改)。然而如前所述,《九度文公道情》《白鹤传》则更加表现了韩愈对宪宗的怨恨与不满:
[山坡羊]罢了!老天,老天!韩愈本是个护国忠良,君王不听良言语。……[驻云飞]珠泪满腮,恼恨君王听残(谗)言,无故摘(谪)贬潮阳县。(《九度文公道情·摘贬潮阳》)
想我韩愈官拜礼部尚书,也不是尸位素餐,也曾替圣朝除些弊患。虽不比稷契皋夔,伊周望散,赤胆忠肝,也不像曹操的奸谋诡计。到今番好可怜,为块骨头就要斩了英雄汉。难道不怕天,难道无神鉴?(《白鹤传》第十回)委屈里透着意气,愤懑中带着直气。“直气”者,正气也。王建《寄上韩愈侍郎》诗就赞韩愈为“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气折王侯”。文天祥《发高邮》诗亦自许曰:“我今载南冠,何异有北投。不能裂肝脑,直气摩斗牛。”所不同者,文天祥的“直气”在为国效死的决心中显现,韩愈的“直气”则在忠而见黜的悲愤中透出。
“尔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原是韩愈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精神状态的。看来历史上的韩愈对孟子的“丈夫”人格及其所倡导的“养吾浩然之气”倍加赏誉和推崇,并非偶然。而实际上,“心气壮”又何止是韩愈早年的精神状态?元和五年(810)韩愈42岁,由国子监博士改授河南县令,因惩不法军人触怒留守郑余庆;七年(812)45岁,因“妄论”柳涧事由尚书职方员外郎复降为国子博士;九年(814)47岁,吴元济反,朝臣多主招抚,韩愈上《论淮西事宜状》力驳之;十二年(817)50岁,以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裴度行军司马讨吴;十四年(819)52岁,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王公士庶竞相膜拜,百姓烧顶灼臂事佛以致破产。韩愈上表力谏,触怒宪宗,被贬潮阳;穆宗长庆二年(822)55岁,奉使镇州宣抚叛军,说王庭凑归顺朝廷……这些都说明,其实历史上的韩愈始终都保持了一种壮盛的“心气”。这也是道情、宝卷中的韩愈“心气”的历史依据。
当然,道情、宝卷中的“心气”韩愈也有另外一面: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这自然是集中体现在他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上。谏迎佛骨,是由于韩愈认为佛骨是“假宝”,且于“文武忠良”不利;攘斥道教,则一是因为两个道人(钟吕二仙)哄湘子抛弃学业离家出走,二是因为韩愈在官贬潮阳之前基本上不相信神仙的存在。因此,尽管越到后来他对湘子诸多“神功”的“解说”越显乏力甚至十分可笑,可他就是“死硬”到底,拒不认输,反而刚愎自用,气焰骄横,动辄大骂“游方野道”,或命人将来者(扮成道人的湘子)“与我拿下,打他四十”。尤其是每当湘子要他随其出家修行,他的反应总是异常激烈,多次将其赶走。这种粗暴的态度既是韩愈真性实情的表露,同时也是他骄傲自大心理的写照。
三、清代道情、宝卷中的“性情”韩愈
《庄子·缮性》曰:“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性情”,指人的禀性和气质,亦即人的个性、情感中最真实的东西。庄子把这种“性情”看成是人先天带来的最可宝贵的禀赋与资质,而反对文饰与博学,认为那样就毁坏了质朴之风,淹没了纯真之心,才导致人民的惑乱。古往今来,就有一种所谓“性情中人”,他们质朴真率,随性而动,不矫情,不做作,不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性格、思想和好恶。经典文人如屈原、司马相如、嵇康、陶渊明、李白、苏轼、徐渭、曹雪芹等就都是这样的人。
史上韩愈无疑也属于“性情中人”,这充分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韩愈“食不择禁忌”③,晚年家居比较随便,常穿“白布长衫紫领巾”④;没钱时赊账饮酒,有钱了就大兴土木,所谓“清俸探将还酒债,黄金旋得起书楼”⑤;他因侄子即将离去而与之“盘宴”一昼夜依依难舍⑥;更有甚者,朋友张籍来看他,二人“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⑦,竟然废寝忘食地闲谈了一个月;他“气厚性通……与人交,始终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无主者十人。幼养于嫂郑氏,及嫂殁,为之朞服以报之”⑧;他“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而为师”,招来“群怪聚骂”,被诬为“狂”⑨;他“因使过华”,遇华阴令柳涧被劾,贸然替柳开脱,致使自己被指“妄论”而由职方员外郎贬回国子监。⑩又据韩愈《上张仆射书》,他受徐州节度使张建封之邀,前去充任幕僚,初到徐州就对其“晨入夜归”的上班制度不满而致书于张,说如果这样的话,他“必发狂疾”,干不好工作,建议每天“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以“使不失其性”。张建封应该是采纳了韩愈的建议,才使韩愈虽然此时常抱怨怀才不遇,但还是留任了一二年。
道情、宝卷虽未出现上述生活细节,但其中的韩愈仍然是一位“性情中人”,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坦直疏率,胸无宿物。史上韩愈“常惋佛老氏法溃圣人之堤”(11),而以儒家道统自许;道情、宝卷中的韩愈对待仙道的态度却是几经转变。起初,韩愈对仙道并无成见。《蓝关宝卷》承袭《韩湘子全传》,说湘子出生3年不曾说话,吕师与钟师扮作阴阳先生,拿一粒丹药给湘子吞服,湘子便能开口叫“叔父”,二师则“化道清风而去”,致使韩愈感慨“这二位恐是仙家所化”。此后韩愈于洒金桥邀钟吕二仙所扮道人回家,留其在睡虎山教湘子读书。在《九度文公道情》和《白鹤传》中,韩愈听了二道“遍读书史”的自诩后,还称赞其是“一翻疯话,又是一翻真语”,“一翻训词,又是一翻玄妙”,这才决意请二道做了湘子的老师。只因后来得知二道并未教导湘子读书上进,反而诱其学仙,整天唱渔鼓道情,使韩愈大失所望,怒将他们赶走。而在“南坛祈雪”和“湘子上寿”中,湘子也扮作道人前来,韩愈一方面居高临下,态度简单粗暴;另一方面也因多次亲历和目睹湘子“神功”与“仙术”而不由自主地与之接近和周旋,直至“蓝关走雪”时才改变态度,接受仙道思想,情愿随湘子修行。如此一波三折,完全是韩愈的胸怀坦荡、心底无私所致,绝非有意而为。即便是在湘子“仙术”前拒不认输,也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看法充满信心,并不认为自己有改变观点的必要。同样,当湘蓝二仙所化番僧进献佛骨,满朝文武“大家默默都无言,只有韩愈逞高见”。《九度文公道情》以及《白鹤传》《湘子传》还将韩愈表奏佛骨不祥的情节改为韩愈坚执二僧所献乃“假宝”,不可能是真的“西方佛骨”的观点,结果被宪宗以“欺君”之罪下令处斩,改贬潮州。这实际上是有意淡化了史上韩愈固有的反佛立场和态度,从而使受众更能感知到这个人物的心直口快、胸无城府。
二是随性任真,雅俗不拒。道情、宝卷中的韩愈,可谓朝堂之高,一言九鼎,堪为栋梁重臣;居家之严,蓄内抚孤,洵是德馨恩崇。因此,这个韩愈在人前显露的就纯是一派天真,根本不需要装腔作态、矫情饰行。换句话说,高朋满座、优雅谈吐,或者骄尊傲物、盛气凌人的韩愈,是真的;哭天喊地、濒死改道,或者贪财好吃、俗不可医的韩愈,也是真的。特别是后者,往往给人印象深刻。由于已经有了前面志得意满之韩愈的比衬,“官贬潮阳”后的韩愈虽然最终“得道升仙”,却更像是一个祸福无常、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蓝关宝卷》中的韩愈,面临斩刑及流贬潮阳,心惊胆战,痛哭流涕。此时的韩愈,若论“心气”固是大不如前,但其所发散出来的“地气”却更加浓厚了,因而其所蕴聚的人性的魅力也更加强烈了。至于《九度文公道情》和《白鹤传》中韩愈在蓝关由于“雪打风吹昏花眼”而“枯梅认作一个人”的细节,更使广大普通受众也仿佛置身于一种万死投荒、凄惶无助的人生窘境,而与作品中的韩愈发生无可避让的心灵的碰撞和情感的共鸣。当然,朝堂上忠肝义胆、正言厉色的韩愈,转瞬间竟跟平常人一样在飞来横祸面前几至“精神崩溃”不堪言状,恐怕要让一班专门喜欢围观“超级英雄”临难不惧、慷慨赴死的好事者大失所望了。
其实,道情、宝卷中韩愈性格最有趣的看点,还在于他贪财好吃、俗不可医的一面。此正是这些作品与相关明代小说、戏曲最大的不同之处。特别是《九度文公道情》和《白鹤传》《湘子传》中韩愈故事的结局,迥异于《韩湘子全传》《升仙记》而颇具喜剧色彩。韩愈的那一番贪恋人间富贵享乐的所谓“真言”,的确是把他不可救药的凡心俗情和盘端出了(12),正所谓“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13)。从作者和写手的角度说,这无疑是最后完成了将韩愈“世俗化”的过程。这一方面更加拉近了韩愈与广大受众之间的距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亲和力量;另一方面又给那些幻想做神仙却又不愿放弃世俗享乐的凡夫俗子勾画出一个效法的样板,吸引更多命里注定成不了神仙的普通人去相信所谓“神仙道化”的天方夜谭。然而韩愈的这番“真言”对于“仙缘”浅薄似笔者之流来说,却难免油然而生一种滑稽风趣之感。特别是《九度文公道情》中,韩愈去做“南京都土地”是被恨铁不成钢的铁拐李“一拐棍将他打下南天门”的,就更让人在粲然一笑之余,觉得这个韩愈反倒更加讨人喜欢。其实,这个韩愈放弃官复“卷帘大罗仙”的机会,而更乐得当个远离权力漩涡、微不足道却衣食无忧逍遥自在的“土地爷”,又充分说明他的“大俗”中原是带着“大雅”的,绝非一般庸碌无为、不求上进之流所可比肩。
四、余论
关于历史人物的形象,近年来学界有“三种形象说”(“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和“四种形象说”(“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历史记录中的人物”“后世解读的人物”“读者接受的人物”)。这两种说法似乎都忽略了“文学形象”或“后世解读的人物”其实也是“接受的历史形象”。因为能够进入文学作品的历史人物,他们对后世的影响所及首先就是作家,然后才是作家笔下的由历史人物演绎出来的文学人物对于广大受众的影响。后世作家运用文学的手段演述历史人物的故事,宣扬和传播了历史人物;尽管这个历史人物在作家的笔下早已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异,但这正好表明作品中的文学形象是作家对相应历史人物接受的结果。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把进入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分为“真实的历史形象”(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记录的历史形象”(史书记载的人物)和“接受的历史形象”(包括“文学形象”和主要受文学形象影响的“民间形象”)三个层面。其中,“记录的历史形象”应该与“真实的历史形象”基本吻合,但由于史家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已经不完全是历史真相了;而“接受的历史形象”更不可能与“真实的历史形象”完全相同,但也不排除二者之间总要存在着某些外在与内在的联系。
清代道情、宝卷中的文学人物韩愈之于历史人物韩愈,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一方面,它们在前代文学——特别是俗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虚拟了有关韩愈的许多故事和细节,作为后世作家与写手解读和接受历史上韩愈的一种“精神桥梁”;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中的韩愈又与历史真实及史书所载的韩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文论及“‘心气’韩愈”与“‘性情’韩愈”的历史依据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研究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也是有助于对历史人物本身的感知和认识的。特别是要研究后世人对历史人物的接受,其所塑造的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的价值就更大。因为这种文学形象不仅是作家和写手接受历史人物的精神收获的物化形态,更重要的是,它将深刻影响广大受众心目中相关历史人物形象(即“民间形象”)的产生和完成。即是说,“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虽然同属于“接受的历史形象”,但二者出现的前后次序不同,而且前者显然对后者有着极大的“导向性”甚至“规定性”。在废名短篇小说《文公庙》中,王大奶和她的孙女就“都喜欢‘韩湘子度叔’的唱本,孙女儿唱,祖母听,‘韩湘子度叔’上面有‘韩文公’,而且,‘谪贬潮阳路八千’”。可见文学形象韩愈在普通百姓中间的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类似这种有关韩愈多重形象与社会影响的研究,目前在学界还有很大的留遗空间,亟须研究者来弥补这个缺憾。
收稿日期:2013-09-16
注释:
①吴光正:《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宗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中华书局,1996年,第359—360页。
②光绪十三年(1887)跋刊,版心为《蓝关九度》,16卷,泽田瑞穗旧藏,现藏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此本没有正面描述“谏迎佛骨”情境,而只在“走雪”卷开头由韩愈追叙一过。
③⑧(唐)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6462、6461—6462页。
④(唐)韩愈:《赛神》,《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1页。
⑤(唐)王建:《寄上韩愈侍郎》,《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56页。
⑥(唐)韩愈:《人日城南登高》,《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44页。
⑦(唐)韩愈:《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32页。
⑨(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5813页。
⑩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3559—3560页。
(11)(唐)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并序》,《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7040页。
(12)《白鹤传》中,韩愈被湘子接到天上,登凌霄殿听封。玉帝封韩愈“原职(卷帘大将)在驾前”,可韩愈并不领情谢恩,“登时玉帝龙颜怒,‘贬他酆都受熬煎!’”湘子替叔父求情,玉帝勉强给了韩愈一个“南京都土地”的职位,韩愈则连忙磕头谢恩。湘子不解,韩愈吐露“真言”道:“卷帘职分真清淡,玉帝驾前不敢言。我爱南京都土地,猪羊鸡酒用不完。”还让湘子“快快去接你婶母,同到南京受香烟”。眼见叔父还是“贪图口腹”,湘子勉强依允:“就做土地也不凡。”
(13)(宋)苏轼:《于潜僧绿筠轩》,《三苏全书》(第七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