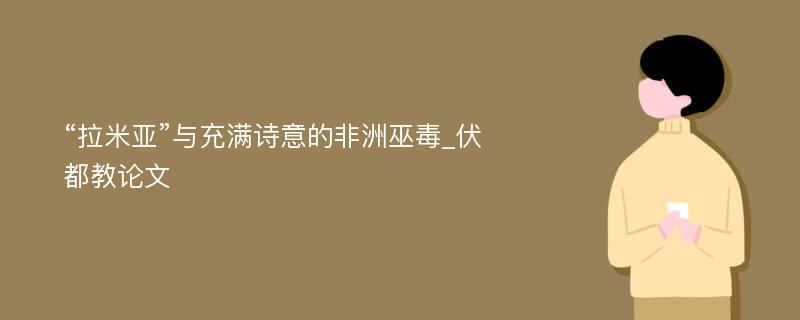
《拉米亚》与诗化的非洲伏都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拉米亚论文,伏都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伏都教(Voodoo)是一种主要在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尤其是海地流行的宗教,由罗马天主教仪式原理和达荷美奴隶的泛灵论和魔法结合而成;其中一个至高的上帝统治着包括地方神、监护神、神化的祖先及圣者的万神殿,他们与信徒在梦境中、梦幻之境和宗教仪式的领地进行交流。济慈通过对这一信仰的理解和演绎,创作了长诗《拉米亚》,对以蛇类信仰为核心的伏都文化的文学和政治意义进行了阐释。
二、济慈的“消极才能”说和拉米亚的蛇类意象:白与黑
1.长诗《拉米亚》的最后一幕是最精彩的高潮。在年轻的里修斯和拉米亚的婚礼上,秃顶的哲学家阿波罗尼专注的盯住新娘,揭示了新娘并非善良少女的秘密,从而彻底搅乱了婚礼:
……
诡辩家的眼睛/有如枪尖,刺穿了她的全身,/锐利,无情,彻底,猛烈;她按/无力的 纤手所能表示的那般,/示意他保持沉默;但徒劳无补,/他目光直直的一看再看——不 !/“一条蛇!”他应声喊到;话音未止,/她发出惊恐的惨叫,便永远消失……[1](P269 )
阿波罗尼的眼光锐利如矛,刺入蛇妖的心脏,也映射着济慈一直在思索的诗人角色问题。1818年,济慈在写给理查德—伍德豪斯的信中说:“令道德高尚的哲人吃惊的,会使玩世不恭的诗人欢喜。……一名诗人是生存中最没有诗意的,因为他没有自我—他要不断的发出信息,去填充其他的实体。”[2](P214)变色龙是19世纪欧洲探险家和旅游者发现的非洲固有的爬行动物,美丽而神秘。通过把作为诗人的自己和变色龙联系,济慈给自己的“消极才能”说赋予了色彩与内涵,一种“身处不确定性、神秘和怀疑之中,但仍对一知半解心满意足”的状态。
关于艺术家性格的探索,是济慈长久以来的兴趣所在。他曾在给弟弟们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注意到莎士比亚的品质是那些文学大家所应有的,这种品质叫negative capability(中译一般作“消极才能”,但也有“天然接受力”等说法)。济慈自己是这 样解释的:“一个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的、神秘与疑惑的境地,而不急于去弄清事实 与原委。”[2](P59)其后济慈把柯勒律治作为莎士比亚的反例:“譬如说吧,柯勒律治 由于不能够满足于处在一知半解之中,他会坐失从神秘堂奥中攫获的美妙绝伦的真相。 ”[2](P59)济慈对柯勒律治的理解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透过济慈谨慎选择的言辞,他 的想法大致可以归纳为:所谓艺术家的“消极才能”,是区别于理性主义精神的。理性 主义者总是急于用清晰而简单的逻辑去整理一切,使一切都变成一堆冰冷僵硬的“事实 和理由”。而艺术家则应“不求甚解”,只为对象完整具体的面目所迷恋和激动,逼真 地把握对象,保留其全部丰富、复杂和神秘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济慈的话里隐含着 一个意思,即艺术家要听任自己被对象本身的美所征服。济慈当时是这样表述的。“对 一个大诗人来说,对美的感觉压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或者进一步说,取消了一切的考 虑。”[2](P59)
所以,1819年济慈开始创作《拉米亚》时,他自然而然的选择了一个神秘的蛇女—她 藏匿于异邦的丛林之中,准备化身为人。对于济慈而言,拉米亚的神秘有三重意义:1) 她是蛇;2)她是女人;3)她源于非洲。济慈创作常用的Lempriere's Classical Dictionary解释为:“拉米亚”是“非洲的某种怪物。它们拥有女人的脸与胸部,其余 部分则与蛇类似。它们引诱陌生人近前,然后吞食之。尽管它们没有语言能力,但其嘶 嘶声却令人赏心悦目。”拉米亚的神秘特性,充分激发了济慈的想象力。同时,诗人发 出了警告:英国对于非洲传统魔法的理解和占有,可能对于两种文化都是毁灭性的。
2.1818—1820年,即济慈创作、发表《拉米亚》之时,济慈对非洲文化学习者和神秘 的非洲风俗表示了极大的兴趣。1819年1月,他写给弟弟乔治的信中提到了一篇描述“ 非洲王国的发现”的旅游札记。
欧洲人早就对恐怖的非洲习俗有所知晓,但济慈在信中强调:把人体作为无私的供品却是两种文明遭遇的结果。对于济慈,文化交流促生的故事,定会公然挑战约定俗成的个性,接近一种“消极才能”。非欧遭遇的故事,充满了神秘、不确定性和疑虑。它不尽是欧洲的,又不尽是非洲的,是一种处于“青须公”小说和“事实”之间的东西。非欧碰撞不仅包括了文化和宗教,还伴随着政治—领土占领和经济利益。因此,一种文化个性之所失,另一种则会有所得。
3.《拉米亚》开篇便被这种黑白争斗所充斥。诗作处于征服史之初,英国的仙女精灵把“森林神和山林水泽女神驱逐出茂林”,而“仙王奥布朗辉煌灿烂的王冠、节杖、用露珠做扣子的披风翩翩,还没有吓走牧神和林中女仙”。在济慈的叙述中,这些征服染上了白色:原本具有黑皮肤传统的森林之神,被奥伯朗征服;而后者的名字源自拉丁文albus(意即“白色”)。诗作早期的白色背景,和拉米亚的黑色相映。她同时是普洛塞嫔(冥后)(Proserpine)和欧律狄刻(Eurydice),而黑肤色无疑是来自宙斯的利比亚情妇。更甚者,如同伊尼亚斯的黛多(Aeneas's Dido)一样,济慈笔下的拉米亚也因为和白人文化的亲密接触付出了巨大代价:白人文化把她变成了“致命的白色”从而彻底毁灭 了她。
为避免我们把这种激烈碰撞看作是自然或偶然的,济慈把诗作的“原始征服”描述为浪子之神的利己行为。赫耳墨斯自己前去找寻“可爱的女神隐秘的床第”。他从山谷飞到山谷,从树林飞到树林,专心于“多情的偷窃”,试图找寻那看不见的女神;而后者的自由毋庸质疑是和她的不可见性紧密相连的。在上演这一征服剧时,济慈利用了探险旅行家们—他们声称,尽管其行为难免涉及“多情的刺探”和“偷窃”,但控制非洲的基本途径还在于揭露并拥有它的秘密。例如,苏格兰之非洲探险家巴克(Mungo Park,1 771—1806)就充分表达了“探察一个未知国家产品的激情期望”。巴克发誓,自己的孜孜探求将“使国人熟知非洲地理”,因而“把新的财富开放给国人的雄心和工业”。
看起来,和所有实业家一样,济慈也获益颇丰。拉米亚和里修斯的婚礼,是济慈遍览群书所获的最丰厚收益。拉米亚的婚礼舞会上,充盈着对巴克和博笛作品的舶来意象。“如同林中空地,大厅通向两排棕榈和两排车前草/它们的枝干由一方伸展至另一方/遮掩着回廊”。这种蓄意模仿恰恰就是博笛描述的天蓬掩映的山谷:“繁盛掩映的,是松树、芦荟和百合;丰富夹杂着的是棕榈、香蕉树、车前草和番石榴树”。但济慈决非仅仅是对热带植物进行简单的移植—博物学家和殖民主义者繁多的植物纲目在济慈处有所收敛。拉米亚婚礼大厅的魅力—其繁盛简直统领了诗作的第二部分—在阿波罗尼面前烟 消云散。济慈用非洲探险家的方法对阿波罗尼进行调整:“以规则和界限打破一切奥秘 /扫荡那精怪出没的天空和地底/拆开彩虹/正像它不久前曾经/使身体柔弱的拉米亚化为一道虚影。”
4.然而,济慈尝试在自己诗化的“规则和界限”内捕获拉米亚的魅力,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描述可以真实刻画非洲而不会有损其生命?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示,欧洲人通过探险作品或者诗歌,基本上设计了一种致命的占有程式。例如蛇(或大毒蛇),被博笛、约翰—史德曼中尉(Captain John Stedman)和约瑟夫—里奇(Joseph Ritchie)等科 学作家归类为非洲的自然风景,因此不仅可以捕猎,亦可作解剖标本。博笛用极其标准 的博物学家口吻说,非洲变色龙可挖掘、可归类、可拥有。
在《拉米亚》中,济慈亦利用了这一变色龙形象,但目的却不同。济慈的诗作对读者而言是一个充满歧义的难题(Gordian knot),因为和博笛不同,济慈之所以揭露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她免于被别人占有。赫耳墨斯首次注目这条蛇妖,就发现她是一个华丽无比的东西:
……
她状似色彩缤纷的难解的结,/一身斑点,或朱红,或金碧,或蓝色;/身上的条纹像斑马,斑点像豹,/眼睛像孔雀,全是深红色线条;/浑身是月亮的银光,她呼吸的时刻,银光就溶化,或增强,或把光泽/同幽暗的织锦画面交织在一起……[2](P242)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诗节是非洲传奇的翻版,但它同时也强调了拉米亚的破坏性演变:“一旦独处,那蛇便开始蜕变”。她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原色,仅用白色的皮肤和人形遮掩—这是她进入喧嚣的科林斯市的通行证。自此,济慈赋予其以美丽,但却从未停止过对蜷缩在皮肤下的蛇妖的暗示:“哈,蛇啊!一点不假,她不是蛇类”。济慈笔下,她既是蛇,又不是。他诠释的蛇妖,是一种演化,其过程削弱了游记作家和诗人(所谓的)占有本质,而这一本质在博笛的作品甚至华兹华斯的《序曲》中描述的是那么确信无疑。
济慈通过《拉米亚》宣告:探险和征服问题与诗歌的想象力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在其诗作的“广阔无垠的境域”(《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调用探险家/殖民主义者的“规则和界限”,济慈暗示:诗歌的演化可与文化差异互动而不毁灭它。通过拉米亚,济慈对强加在一块土地上的主权思想心生疑虑。他意识到,用“一般事物的单调目录”去描述“非洲之沙”,或者将非洲变色龙的演变放在科学作家的静止观察或殖民政府的占有眼神下,就等于完全毁灭了它们。
三、伏都教之蛇类意象渊源与《拉米亚》
济慈认为,拉米亚的蛇类本质和它的象征意义本身就是文化的交际和互动。对西方读者而言,拉米亚的形象象征着基督教传说中善言的爬虫和它带到世界的邪恶。而济慈笔下的拉米亚又同时是女人,这自然是夏娃和恶魔心肠的毒蛇的结合(尽管在中国,白蛇娘子也同时具有女人与蛇这两类性质,意象却完全不同)。
1.在19世纪早期的非洲和加勒比社会中,蛇是含有丰富意义的。很多欧洲游记把非洲描述成一个天堂,但对于蛇在非洲神教中的中心地位却了解很少。摩洛—圣莫利(M.L.E .Moreau de SaintMery)1797—1798年间曾详细描述了伏都女巫带领下的“蛇教”,强 调了蛇的非欧洲特点。但是,在浪漫主义时期所有的欧洲文学作品中,非洲人和西印度 群岛人赋予蛇类的意义常被当作神经无常的表现。自然而然的,蛇类崇拜成为奴隶强有 力的法宝,却成为白人永久的头痛。
浪漫主义时期关于奴隶贸易的辩论中,非洲人和蛇通常会一起出现。发行甚广的小册子《黑人奴隶制度的辩解,或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非人道之辩解》(An Apology for Negro Slavery:or the West India Planter Vindicated from the Charges of Inhumanity(1786)就把蛇类崇拜作为维护奴隶制的原因之一:“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 人是十足的无知、偶像崇拜和野蛮。他们崇拜蛇和其它野兽,以为这样它们就不会伤害 他们”,似乎非洲人的蛇类崇拜只是对邪恶的尊崇。很快,那些“信仰蛇类、爬虫,接 受邪神”的非洲人就变成了西印度群岛奴隶——他们“除了信仰魔鬼(obeah),一无所 信。”
蛇类崇拜之所以变成对白人种植园主的永久威胁,关键在于其神秘性。布赖恩—爱德 华斯(Bryan Edwards)在其1819年版的畅销书《西印度群岛史》中,尝试用欧洲人的常 识去解释奴隶们的崇拜活动。他发现,就词源而言:
“蛇在埃及语中叫Ob,或者Aub。Obion也是蛇的埃及名称。摩西用上帝的名义禁止犹太人探究邪恶的Ob,《圣经》中译作Charmer,Wizard,Divinator,或者aut Sorcilegus。恩多(Endor)女人被叫做Oub或者Ob,译作Pythonissa(女祭祀,女巫);Oubasois是Basilisk(蛇怪)/Royal Serpent的名字,是古代非洲的神灵。”
爱德华斯很不明智的把蛇类作为两种背道而驰的文化的共享符号。在蛇类的象征意义上,他把欧洲人和非洲人放在一起,而又承认不同领域含有的不同价值。基督教《圣经》中的蛇是魔鬼,而非洲人尊崇的蛇却放射着多产与生命的光辉。有些欧洲人(包括爱德华斯)将蛇类崇拜斥为无稽之谈,其他人则宣称:练习者可以施以符咒,使种植园爆发传染病灾难。
英国人对蛇类崇拜的具体功能知之甚少,但他们自然而然的将之与奴隶暴动、叛乱和其他危险举动联系起来。很多岛屿甚至制定法律,设立“蛇教审判”来干涉人们的信仰。济慈作品中的非洲蛇类意象,或许会使读者回忆起约翰—史德曼游记中描述的蛇类崇拜。史德曼把这些场景描述为:“神谕女巫”表演的“美人鱼舞蹈”:
“她在一群人中间又跳又转,速度惊人的快,直到口吐白沫,倒地痉挛。女巫发作期间发号施令,围观者则言听计从;但她经常命令人们去杀掉主人或逃往森林,所以这些聚会便极其的危险”。
史德曼的描述和摩洛所谓的“神灵通过蛇类附体蛇女”相近:
“突然,他拿起装蛇的盒子,置之于地,而蛇就开始攀附女巫之身。神物一到她的脚下,她马上就神灵附体。她浑身抽搐,手舞足蹈,而神灵就通过她的口开始说话了”。
而事实上,这种痛苦的意乱情迷正是拉米亚魔力演变的特点:
……
一旦独处,那蛇便开始蜕变,/她体内妖精的血液疯狂的流转,/她口吐白沫,被撒满 白沫的青草,/在甜而剧毒的唾珠下立即枯凋;/受到剧痛的折磨,她两眼凝固,/灼热 ,光泽,阔大,而睫毛全枯,/闪烁着磷光和火星,没一颗阴凉的泪珠。/色彩透过她全 身而燃烧成炽红,/她因沉重的痛苦而抽搐,扭动……[2](P246—247)
女巫通过蛇被神灵附体,这彻底迷惑了欧洲人。例如,女巫通过被占有而充满力量的同时,根据摩洛的说法,她“易于产生更加激烈的兴奋”,较其他练习者发出狂乱的呓语(MI:67)。这些奴隶固有的宗教崇拜的矛盾,解释了拉米亚的不连续性。她的化身就具有意义:作为一条“悸动的蛇”,她首先被困墓中;然而她同时又同赫耳墨斯神关联,以蛇杖为证,竟然也施展诊疗奇迹。她同时处于自由和奴役之中,体验着“自由的克制”/“禁锢的自由”;而济慈在《恩底弥翁》中称此为进入“魔法世界的伟大钥匙(great key to all the mazy world/Of silvery enchantment)”。在自己的“蛇狱” 中,拉米亚可以将自己的灵魂送到任何地方:从海神珠亭到喧嚣人间。
2.事实上对欧洲人而言,蛇类崇拜的最为不解之处,在于其同时具有解放和束缚练习者的能力,即摩洛所谓的“同时是控制和盲从的系统”。摩洛、史德曼等人忧心忡忡的自相矛盾,正存在拉米亚的心中。她的巫术在很多意义上宣告着她的自由。她蜕掉彩色的蛇皮和黑色的血统,拥有了白色的胳膊、白色的脖颈和温柔的嗓音。拥有了白色,她拥有了社交。白色美人赢得了里修斯的爱情:他给予她机会从茅屋小舍登上大雅之堂,从“茅庐之爱”升级为“宫廷之爱”。然而,这样的自由却仅仅在于强调了拥有的奴役作用。就像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一样,拉米亚亦一直为放弃自我而困饶。矛盾的中心有可能在奴隶们的现实生活中找到答案:只有通过对控制力量的完全屈从,一个人才能获取力量和优势。西印度群岛巫术的关键,奴隶们的毁灭性问题,和拉米亚的最终问题都是一个:一个人一旦为白色的躯体所攫取,放弃自我的可能性就无休无止。
对西印度群岛和西非人而言,白色的攫取就意味着邪恶和死亡。博笛在谈到他亲眼目睹的阿善堤宗教仪式时说:“他们吐一点液体在地上,作为对巫神的供品。他们从椅子上起身,随从立刻由侧翼护驾,以妨白色的恶魔对主人不利。”而对于英国人所知的黑白魔鬼之别,约翰—亚当斯上尉(Captain John Adams)描述更为清晰:在英国,邪恶可能是黑色的;而对于黑人,邪恶永远是白色。在济慈的诗中,阿波罗尼的秃顶就意味着白色,而他那邪恶的、召唤魔鬼的眼睛,更证明了英国式占有(British possession)的系统的因而是毁灭性的一面。他到达宴会时,拉米亚就要和里修斯结成连理。而阿波罗尼那心平气和的脚步、耐心的思虑和苛刻锐利的眼神终于把可怜的拉米亚化为乌有。
为了躲避这种“白色恐怖”,奴隶们的宗教仪式总在暗中进行。根据爱德华的记录, 牙买加的奴隶们在仪式上遮掩一块“神秘幕帐”,以避免为白人所知。而摩洛也亲见了Saint-Domingue宗教信奉者们的神圣誓言。为掩种植园主的耳目,仪式就这样在半夜里进行。在《拉米亚》中,济慈同样描述了一个“隐居”的蛇女,使用类似的夜幕笼罩着。整个故事都在夜幕中,从暗淡的夜幕,到黑夜,到午夜。诗作和拉米亚同时出现在“灿烂”一日的黑夜,而拉米亚结婚,被揭露,最终消融。
3.济慈志在赋予这一西方故事(无论《圣经》版还是希腊版)以新鲜的异国(非洲)情调。因此,他在利用非洲素材成就个人计划方面还是和博笛等人类似的。就此而言,他们的确掌握了所谓的“自然魔法”。然而,济慈的境遇较之旅行家或殖民主义者们却更加复杂:他不但掌握,而且被掌握。济慈选择了一个有着非洲渊源又具有西印度群岛魔法的弱势角色,颂扬了一种与殖民方法相左的非洲力量:不是占有者,而是被占有者;不是展示力量,而是隐藏力量;不是通过可视的全景,而是活跃在黑暗之中。
四、结束语
1819年9月写给伍德豪斯的信中,济慈试图将《拉米亚》诠释为读者被蛇类故事给占有的诗篇:“可以肯定,其中之火定可攫取人心”。济慈迫使读者通过掌握拉米亚的故事和她与非洲/西印度群岛宗教传奇的密切关系掌握这一诗篇。但不仅是读者掌握诗作,诗作也掌握读者。他们尝试通过一个不息的过程来认识拉米亚:她变换于女神和凡人之间;蛇类与人类之间;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可见与不可见之间;自由和束缚之间;占有与被剥夺之间。
果不其然。读《拉米亚》后一个月,伍德豪斯仍感济慈的诗作余音绕梁,于是写信给济慈的出版商们。具体而言,他思索的问题是:济慈是如何穿梭在主题之间,把灵魂赋予他所见、所感和所思的物体从而“由这一物体代言,而他的自我,除了机械部分,被彻底消灭”。伍德豪斯的问题(肯定出乎济慈意料)集中在,诗人作为人是如何被剥夺了自我的。伍德豪斯结论道:“作为人,他有自我;而作为诗人,他不必”。因此,济慈利用拉米亚通过非洲的神秘传奇展现诗化的想象时,正是他的殖民特权可以在“神灵的梦中”占有和剥夺非洲的:远离鞭笞,远离锁链,远离糖料种植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