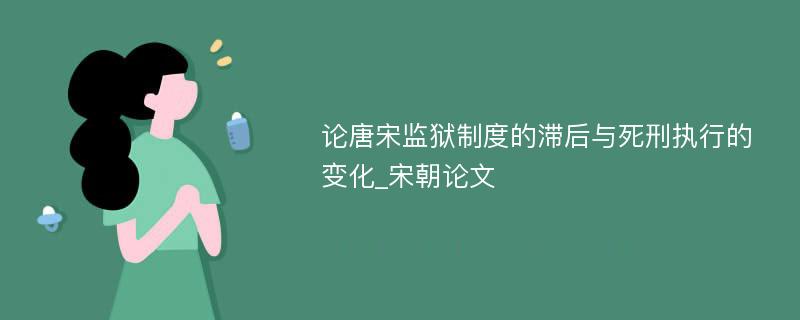
论唐宋时期监狱制度的滞后与徒刑执行方式的变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徒刑论文,监狱论文,时期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6)04—0071—06
徒刑是中国古代法典规定的基本刑罚之一,列于“五刑”,在唐宋时期,见于官方的法典《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然而,自中国古代法律之肇始直到唐宋时期,都没有建立近代意义上的监狱制度,当时的监狱只是关押犯罪嫌疑人、诉讼中的理亏人和死刑待决犯人的“禁系之所”。北宋末年,蔡京建立“圜土”制度(即于劳役之处建立禁系之所)的尝试被后人否定。唐宋两代分别用“流徒徙边”和“折杖法”来解决徒刑的执行问题,直到元代才产生近代意义的监狱制度的雏形。同时,就唐宋时期的徒刑而言,居作制度也发生了改变,即由以服务皇家为中心的宫廷居作,更多地转为以服役于国家军队和作坊为主,这使得罪囚的法律地位有了些许的改变,也是法制逐渐国家化的表现。
一、唐宋监狱制度的设置及职能
(一)国家监狱的建制扩大
秦汉的徒刑普遍被认为是城旦舂、鬼薪之类。但从其实质去考察,其实是一种“配”,即有年限的强制劳役。如汉惠帝诏:“城旦谓旦起治城,妇人不预外徭役,具舂作米,四岁刑;鬼薪,取薪给宗庙者,白粲令择米,皆三岁刑。”(《古今合壁事类备要·外集》卷一九,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5年)古代的徒刑以奴辱的形式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如汉唐的配没“掖庭”,即为宫廷之奴婢,但确实是《唐律》中的法定刑罚(如针对反逆缘坐之家属者)。凡配没掖庭者,几乎是终身为奴,除非遇到类似唐太宗的特制恩赦。正如唐代王延龄《秋宵读书赋》之所感慨:“长门幽绝恨欲死,掖庭一去无还期。”(《古今图书集成·学行典》卷九五《读书部》,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1884年)宋初,申国长公主为尼,掖庭嫔御随出家者三十余人,朝野作诗褒美之(宋代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在宋代,宗室妇女亦往往因为“作过”而被迫“披剃”出家,并规定一年以后才允许归本宗与其亲妇人及所生子女相见,但不能留宿,每月不得超过一次。(《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卷四七八元祐七年十月癸卯条,中华书局,1990年)《新唐书·百官志三》“大理寺”条记载:“贵贱、男女异狱”。即使到宋代,《庆元条法事类》(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90年)卷七五《断狱令》仍规定:“诸妇人在狱以倡女伴之,仍与男子别所。”在“良贱有别”的古代社会,罪囚的法律地位大致如此。本文谈及的徒刑执行的变异主要是由于古代法制中“狱”的观念以及监狱的状况,还有“禁系”与一般意义上徒罪的关系。
《周礼注疏》卷三四:“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可见,“狱”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其中包括了对犯罪嫌疑人的禁系和关押。如“诏狱”,是指由皇帝下旨缉拿,由法司(一般是御史台)禁系、审理,不经过大理寺初审、刑部详覆,把审判结果呈报给皇帝的案件。
唐宋时期,监狱制度的建制确实有明显的扩大趋势,但制度都很不完善,不适于以“居作”(劳役惩罚)为核心内容的徒刑的执行。从唐代的“徒流徙边”到宋代的“折杖法”蠲徒入杖,都是这一问题的表征。《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卷六规定:
凡京都大理寺、京兆·河南府、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县咸置狱。(原注:其余台、省、寺、监、卫、府皆不置狱。)
以上是唐代理想而规范化的制度。确实,在唐代,如果六部(包括刑部)欲系人讯问,皆须系于地方的监狱。
……(宪宗时)度支(户部)有囚系阌乡[笔者:阌乡在今河南省西部]狱,更三赦不得原。(白居易)又奏言:“父死,絷其子,夫久系,妻嫁,债无偿期,禁无休日,请一切免之。”奏凡十余上,益知名(《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中华书局,1976年)。
古代法制中的“囚”是由“狱”和“讼”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案件所涉及的债务问题,是“讼”的问题,在古代也适用监狱这种国家强制力来解决问题。即已被官府指认有犯罪嫌疑或者在“讼”中理亏并被无限期地禁系于监狱的人,都被称为“囚”,也都是会赦时原免的对象,这与死罪待决和流罪徙边的人在法律地位上极其相似。相比较之下,这种疑罪的囚徒和败诉的人在执行方式上反而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徒刑犯人。
唐代的监狱还有御史台狱和神策军狱。前者由于君权的膨胀,后者由于宦官的僭越。
(贞观时),李乾祐为(御史)大夫,始置狱。由是(御史)中丞、侍御史皆得系人。(玄宗时),(崔)隐甫执故事,废掘诸狱。……(《新唐书》卷一三○《崔隐甫传》)
(代宗)永泰中,神策军都虞候(刘)希暹讽(鱼)朝恩置狱北军,阴纵恶少年横捕富人付吏考讯,因中以法,录资产入之军,皆诬服冤死,故市人号“入地牢”。(《新唐书》卷二○七《宦者列传上》)
众所周知,武则天统治时期,御史台不但能系人,还能以审理案件为口实任意刑人。据《文献通考》等文献,宋代的御史台设有东西二狱。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谈到南北朝时的御史台只有弹劾职能,没有审判职能,而自唐以后的御史台把弹劾和审判集于一身,很难实现司法公正。吕先生的论点姑置不论,由皇权及皇帝的近臣(宦官)权力的恶性膨胀而衍生出的日益庞大的监狱体系,确实成为对官员和百姓而言异常恐怖的专政机构。
宋代的监狱体系有所扩充,更显庞大,而且管理严密:
官司之狱:在开封,有府司、左右军巡院;在诸司,有殿前、马步军司及四排岸;外则三京府司、左右军巡院,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宋史》卷二○一《刑法志三》,中华书局,1985年)
再加上大理寺狱、御史台狱,宋代的监狱既然足够多,为什么不能很好地执行徒刑呢?这与中国古代对监狱职能的界定有关。王谦之的《临海县狱记》称:“官师察夫不直不正与夫强而不令者,置之于狱……筋骨一治而终身创。”周朝端在《重建黄岩县狱记》称:“民习赂而轻犯法,狱犴充斥,县多不理。……而况丽于狱者,非皆狠戾犯法者,追胥之愆,诖误之累,间多有之……”(宋代林表民《赤城集》卷八,四库全书本)。足见,监狱是缉捕、关押和审判机构,“……狱之生杀予夺,其根乃在于县,自州至朝廷咸取成焉”。
笔者认为,唐宋时期乃至其以前的监狱不可能是刑罚的执行机构,至少不是徒刑的执行机构,而只是缉捕、关押和审判机构,禁系期间对“囚”的施刑也是出于审判目的的拷问而已。
(二)地方监狱的发展滞后
县狱作为初级的审判机关,其职守甚重。从总体上说,宋代官方对监狱的建设是投入不足的。地方官如果能修缮监狱,则被认为是德政,流芳后世。如元祐五年(1090),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公事游师雄“完郡县之狱,且授以唐张说《狱箴》,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观”,其事见铭于墓志(宋代张舜民《画墁集·补遗·游公墓志铭》,扬州:江苏广陵古籍,1983年)。宋代王谦之的《临海县狱记》记载钱温伯任临海县令时,“顾县狱岁久庳陋,倾侧风雨,燥湿之不时,而疾疠间作”,捐金五十余万,重修县狱。而钱温伯是“本乡‘提刑君’之长子,‘提刑君’在本乡号‘丈人行’”。捐金修狱,并非县令之本职,往往是当地豪绅的一时义举。如周朝端在《重建黄岩县狱记》中记载“黄岩壮邑……县狱且百年,风隤雨败,久弗及整。”(宋代林表民《赤城集》卷八,四库全书本)这恰是宋代县狱废怠的写照。由是,“形势户”私置监狱,滥用私刑之风也因之而起。如《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五《断狱令》申戒:
形势之家辄置狱,具而关留人者,徒二年。情理重者,奏裁。许彼关留人越诉。
从总体而言,唐宋时期,扩大了中央监狱体系,造成了淫刑滥罚;而地方监狱则发展严重滞后。其弊端集中体现在禁系之“囚”, 瘐毙情况严重。 元丰二年(1079)正月,苏轼上《乞医疗病囚状》,主张将瘐毙之责委以小吏和医人(《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二,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元祐七年(1092),刑部“遂分每禁二十八人以上,死一人者,更不开具。即是今后应系囚处岁禁二百人,许破十人狱死。”(《长编》卷四八一元祐八年二月壬子条)嫌疑之人,身婴缧绁,瘐毙比例之高,足见中国古代监狱制度之黑暗。于是,宋廷倡导以“狱空”为美政:凡治所内监狱疏决罄尽者,朝廷奖挹优渥。于是,欺隐邀功者有之;从速断决,铸成冤狱者亦当有之(参见《宋会要辑十稿·刑法》四之八五)。
二、唐宋监狱制度的发展
——“圜土”制度的尝试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在《宋元时代的法制和审判机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中华书局,1992年)一文中指出:“一般说来,拘禁犯人使之劳役的做法,即使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也有其客观上的困难。”诚然,宫崎市定先生的观点是基于唐代的流徒徙边和宋代的编管、刺配等强制劳役的刑罚手段而发的。据宫崎市定先生考述:“到了元代以后,才在配流场所建造了监狱。”如是,北宋末年,关于“圜土”制度的尝试就显得弥足珍贵。
元代人富大用著的《古今合壁事类备要·外集》卷二○载:“狱者,所以察究情伪者也,其始也作于皋陶,……历代所不废。今考其制为刑,圜象斗墙,曰圜墙,扉曰圜扉,总而名之曰圜土。”同时,又规定了枷杻和暑月洗涤之制。又规定:“凡囚以故逃亡及自杀伤、伤人者,徒一年;自杀、杀人者,徒二年。”这里提到的“徒罪”在宋代应该以“折杖法”执行。在对监狱职能的界定时,说:“鞠问审断,并不许违程”,且“州委法司,县委佐官,五日一申本司(提点刑狱),催促、结绝”。
据《文献通考》,元丰年间,苏颂建议请依上古圜土之制,“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夜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稽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宋徽宗崇宁三年,宰相蔡京令诸州复置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且“视罪之轻重以为久近之限,许出圜土充军,无过者纵释。”崇宁五年(1106)罢之,大观元年(1107)复置,四年(1110)又罢之。南宋的葉适评价说:“……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配隶者有奔亡困踣之患”。(《文献通考》卷一六八《刑七》,中华书局,1986年)葉适言“加役流”,其实是指宋代的编管、刺配之法的弊病。宫崎市定先生也认为:“圜土之建在自由刑(徒刑)上堪称是新的尝试。”但后世多因蔡京其人而诋毁其“圜土”之法,就连葉适也没有正面褒美之。
北宋末年的“圜土”的意义重大之处在于,使古代徒罪的执行方式更加趋近于现代刑法意义上的自由刑,符合了古代刑罚制度“流徒合一”的发展趋势,以至于近代没有流刑这一刑种了。而现代不少法史学家在研究《唐律》等法典时,把徒刑冠之以“自由刑”的帽子,实质上没有区分古代的徒刑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刑在概念和实质上的区别。又因为蔡京是臭名昭著的奸臣,学者们对圜土之制的历史评价也有失公允。
三、“居作”刑罚的变异与罪囚法律地位的改变
“居作”是唐代法定的监禁加劳役的刑罚方式,同皇权与官奴婢制度息息相关。笔者试设此议题,也旨在论证皇权司法与官僚司法的演变趋势,通过对罪犯法律地位的解析,以期论证法制由皇家之“私器”逐渐到天下之“公器”的演变趋势。
西汉之制,在皇帝诏准的前提下,“死罪欲就宫者听之”,即死罪减等的人下蚕室,宫刑之后而服役于宫室(参见《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 中华书局,1962年)。南朝刘宋在其都城建康设立了廷尉法狱和建康狱,还有在尚方署中设立了居作场所,“尚方”原只是“主作手工作、御刀剑、玩好器物及宝玉作器”的官署,尚方的囚徒也“婴金屦校”而劳作。这是后来唐代在将作监、少府监执行居作之法的渊源①。
唐代继续把直接服务于皇室确定为立居作之法的主旨:
武德四年(621),诏裴寂等更定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 三岁至两岁半悉为一岁。居作者,著钳若校。京师隶将作,女子隶少府缝作。旬给假一日,腊、寒食一日,毋出役院。病者释钳、校,给假,疾差(瘥),倍(通‘赔’)役。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饍。”(《文献通考》卷一六八《刑七》)
另外,《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96年)卷三《名例律》规定:“工、乐、杂户及太常音声人,犯流者,二千里决杖一百,一等加三十,留住俱役三年……其妇人犯流者,亦留住,流二千里,决杖六十,一等加二十,俱役三年。”这里的“留住”即居作,即妇人犯流罪时的代替刑,而杖罪与流罪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代替也是《唐律》的既定原则,因为工、乐、杂户与妇女的“留住”更有利于国家和宫廷杂役的解决。
此外,唐代的“配没掖庭”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终身的“居作”。掖庭本意上是“宫中旁舍”,嫔妃所居,别于正宫。《后汉书》:“婕妤以下,皆居掖庭”。“配没掖庭”在唐代多适用于犯奸罪的品官妻妾和官员的“别宅女妇”。武周时,郎中裴珪妾赵氏因与人奸,没入掖庭。(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一,中华书局, 1979年)殿中侍御史王旭对“别宅女妇”滥施酷刑,有罪妇言:“苦毒而死,必诉于冥司;若配入宫,必申于上。”王旭惭惧。(《朝野佥载》卷二)可见,“配没掖庭”直接服役于皇室,且带有明显的奴辱性质。与宫刑为内侍一样,只要君主专制存在,类似的刑罚就必然存在。宋代文献关于“配没掖庭”的记载较少,仅说明宫人的数量少而已②。唐代前期,由于行用太广,而每遭非议。开元年间,少府监张廷珪上言,名为《论别宅妇女入宫第二表》:
检贞观、永徽故事,妇人犯私,并无入宫之例。准天授二年敕,京师(长安)、神都(洛阳)妇女犯奸,先决杖六十,配入掖庭。至太极修格,已从除削,唯决杖六十,仍依法科罪。(请从《太极格》)……。(《全唐文》卷二六九,中华书局,1985年)
天授二年敕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官员的自尊心,同时也体现了以京城为中心立法,以皇室和宫廷利益为核心的倾向。终唐之世,“配没掖庭”之法没有废止,而是更广泛地适用于反逆缘坐的惩罚中。
以上是唐代“居作”之法的基本内容。毋庸讳言,这种法令带有明显的奴役色彩。宋初,仅在很短的时期内仍然行用居作之法。但地点不是将作监、少府寺、司农寺或掖庭,而是一些官营的作坊。
(宋初)御史台上言:“伏见大理寺断徒罪人,非‘官当’、‘赎铜’外,送将作监役者。其将作监旧充内作使……比来工役,并在此司。今虽有其名,不复役使……欲望令大理寺依格式断遣罪人后,并送付作坊应役。”从之。自后,命官犯罪当配隶者,多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其所死特贷者,多决杖黥面,配远州牢城,经恩量移,即免军籍。(《长编》卷八,宋太祖乾德五年二月癸酉条)
相比之下,唐代与宋代的“居作”在施行的地点上大为不同,即是以皇城为服役的核心向以国家服役为目的的转变。并且,宋代旋即废除了居作之法,而代之以执行于地方的刺配和编管。这诚然是统治者疆域观念的重大进步,也促进了法制的官僚执行制度和“法者,天下公器”原则的确立。应该指出,宋代并没有因之而消弭奴婢制度,宋代偶尔也有没为官奴婢的情况,但官奴婢的服役地点不止限于京畿。如熙宁四年三月,为惩治庆州叛兵,令“其亲属当绞者,论如法;没官为奴婢者,其老、疾、幼及妇女配京东、西,许人请为奴婢,余配江南、两浙、福建为奴,流者决配荆湖路牢城……诸为奴婢者,男刺左手,女右手,余亲属皆释之……”(《长编》卷二二一),这是北宋历史上罕有的没为奴婢的刑罚之执行,从文意上看,没为奴婢在量刑上重于配某州牢城。
宋代的刺配按轻重大致分为刺配本城、牢城和重役军分,其轻重之别也部分地体现在道里远近。“配”不是独立的刑罚方式,只是流徒二刑的一种执行制度[1]。这恰恰说明“刺配”是律条中流刑的变异形式,而这种变异是包含了徒刑和杖刑内容的变异,因为在徒刑的执行中,服刑的犯人或徙边,或配于掖庭、作坊或皇室的寺观,皆以“配”称。“配”本身的含义就是强制劳役于某处,所配之处所也林林总总。宋初规定,出产茶的州县,“民辄留及卖鬻计直千贯以上,黥面送阙下,妇人配为铁工。”(《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丁未条)元祐年间,依荆湖南路提刑司曾建言,将犯刺配的罪人与裁汰的厢军一并“于钱监工役”,从事铸钱的劳作。(《长编》卷四六四元祐六年八月庚子条)京城的将作监、太常寺按照律条规定是执行徒罪的男女犯人服刑的地方,分别名隶匠籍和乐籍。但在实践中有很多流罪的犯人也因为需要在彼服刑。在宋代人的观念中,刺配无疑是流罪在执行中的加重。朱熹说:“古时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编管样。是唐、五代方始黥面……”(《朱子语类》卷七九,中华书局,1994年)
我们不妨做这样的结论,没为奴婢或其他任何带有奴辱意义的“居作”都不是宋代的常法。因为在《长编》这样卷帙浩繁的史料中仅有一例。如前述,宋代的流罪原免者称“即免军籍”。再结合前面对于北宋末年“圜土”制度及宋代枷杻制度的论述,则有下文之结论。
由唐代到宋代,综观徒流罪的执行方式以及“居作”等劳役制度的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从地点上,由内廷的将作监、少府寺、掖庭和司农寺向作坊和诸州以及边镇的牢城转移;从对服刑罪人的法律身份界定上,由至重者为皇室的奴婢到至重者为国家的牢城军人。这种对罪囚法律身份的不自觉的重新界定,仍然是以“良贱有别”为社会背景的;从奴婢到军人,刑罚的奴役色彩淡化,劳役色彩却加强了。尽管宋代的罪囚的实际状况并不尽人意,甚至可以说杌陧种种,但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却体现了人文精神和社会进步。这是皇室利益向国家利益的让步,也是法律制度必然成为的“公器”的趋势使然。
四、“流徒徙边”与“折杖法”对监狱制度发展的间接影响
唐宋时期的监狱制度的不发达与徒刑执行的弱化是刑罚制度演变的表征。而探究其原委,在于“流徒徙边”与“折杖法”的演变和改革。
“五刑”之中,变通最多者当属徒、流二刑,其中,又以流、徒刑的变通使用最为广泛。在《唐律》的最初规定中,流和徒的执行方式都是力役:
诸流徒囚役限内而亡者(犯流、徒应配即移乡人未到配所而亡者,亦同),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等。(《唐律疏议》卷二八《捕亡律》)
流刑的变通形式也是徙边充军。而唐代前期,已经有了罪囚充军的尝试,并且适用的对象是犯赃的官员。敦煌出土的《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记载:
流外行署、州县离任,于监主犯赃一疋以上,先决杖六十;满五疋以上,先决一百:并配入军。如当州无府,配侧近州断后一月内,即差纲领送所配府,取领报讫,申所司。赃不满疋者,即解却。虽会恩,并不在免军及解免之限。东在都及京犯者,于尚书省门对众决;在外州县者,长官集众对决。赃多者,仰依本法。(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卷一九《格》中华书局,1989年)
同宋代的刺配相比,则《神龙散颁刑部格》尚未规定黥面和徙边,颇类宋代的邻州编管。这种规定自然较之律条为重,既不符合“轻刑”的主张,也有违优容仕宦的原则,必定行之难久。但“充军刑”却为“徙边”开了先声。
另外,唐宣宗在《科吴湘狱敕》中,特旨处李克“决脊杖十五,配流天德”,刘群“决臀杖五十,配流越州。”(《全唐文》卷八一)唐宣宗时,已经产生了类似宋代的配流。
徒罪在唐末也开始以徙边的方式执行,也与古代监狱的职能有关,即监狱不是徒刑犯人服刑的地点。就唐宋两代而言,是审而未结的人犯(犯罪嫌疑人)皆系于狱。唐制:凡禁囚皆五日一虑焉(虑,谓检阅之也。断决讫,各依本犯具发处日月,别总作一帐,附朝集使,申刑部)。(《唐律疏议》卷一,三《名例律》),监狱制度不完善,难以容纳数千罪囚。所以,唐代后期每遇战事,就以罪人徙边,以解燃眉之急,以至后来使之制度化。
应该补充的是,无论是唐代的流人,还是宋代的刺配、编管的犯人,都不是囚禁在监狱中服刑。因为当时的监狱不以此为主要职能。他们主要是为官府佃种或服兵役。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赦书节文:“应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粮种,俾令耕田,以为生业。”(《文献通考》卷168《刑七》)
这与宋代沙门岛流人的生存和服役方式极为类似。
因为“折杖法”仅是名义上取缔了流刑。按文献,编管至重者为一千里,其次为五百里、邻州、本州,一般配合“折杖法”行用附加的杖刑。在《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一般“编管”的附加刑是“杖一百”(也按宋太祖时期确立的“折杖法”执行臀杖二十)。古代的刑罚都带有奴辱的色彩,“编管”也概莫能外。
首先,宋代和唐代比较,杖的大小有所改变。《唐律疏议》卷二九《断狱律》规定:“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依《唐令》:“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五厘。”唐宣宗大中七年敕:“法司断罪,每杖脊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全唐文》附《唐文拾遗》卷八)宋太祖于建隆四年颁布《宋刑统》时,同时规定了“折杖法”,也为此承袭了后周显德五年的杖制,即杖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得过二寸,厚及小头直径不得过九分(《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宋仁宗天圣七年,又以杖制轻重无准,“诏无过十五两”。这个标准总体上使杖的规格略大于唐制的讯囚杖,同时取消了唐代的笞杖和讯囚杖,实行了划一的杖制。“折杖法”既行,大大减少了用杖的数量,原则上把笞、杖、徒、流之刑罚合并为杖刑和徒刑。根据建隆四年的《宋刑统》卷一《名例律》的规定及《文献通考》卷一六七《刑六》的补正,“折杖法”对徒流的执行方式的改变可以概括为如下:
徒刑:三年改为杖脊十五;二年半改为杖脊十八;二年改为杖脊十七;一年半改为杖脊十五;一年改为杖脊十三。
流刑:加役流改为杖脊二十,配役三年;三千里改为杖脊二十,配役一年;二千五百里改为杖脊十八,配役一年;二千里改为杖脊十七,配役一年。
在流刑的执行方式发生如是改变以后,逐渐于元代在配役之所产生了类似近代意义上的监狱制度,而北宋末年蔡京推行的“圜土”之制,即正规的近代意义上的监狱制度之雏形。
总之,中国古代监狱制度发展的一般动态是由“禁系拷讯之所”发展成为具有类似近代意义上的徒刑执行机构。唐宋时期的监狱正处于这一演变发生的交替时期,但对于当时的司法实际需求而言,监狱制度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因此导致了徒刑执行方式的种种变异。
收稿日期:2006—01—16
基金项目:本文承蒙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9—12世纪中西制度文明比较研究”课题之赞助。
注释:
① 参见姚潇鸫:《刘宋监狱新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但笔者认为将作监、少府监不是执行徒刑的监狱,而是流徒罪犯和官奴婢的劳役场所,尚方亦然。尚方是定罪后配役劳作的场所,而不是“狱”。如《宋书·张畅传》载张畅因被胁迫参加了南郡王义宣的叛乱,被俘后先下廷尉论罪,定罪后即“配左右尚方”服刑。
② “配没掖庭”的居作之罚具有为皇室服务的特殊性,偶尔会因此亲近皇帝,反奴为主。如唐宣宗生母孝明郑太后,先是逆臣浙西节度使李錡之姬妾,没入掖庭后为郭太后侍儿,为唐宪宗亲幸,生宣宗,“为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又七年薨。”(见唐裴廷裕:《东观奏记》卷上,扬州,广陵古籍影印本,1983年)
标签:宋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古代刑罚论文; 历史论文; 唐朝论文; 文献通考论文; 唐律疏议论文; 新唐书论文; 全唐文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