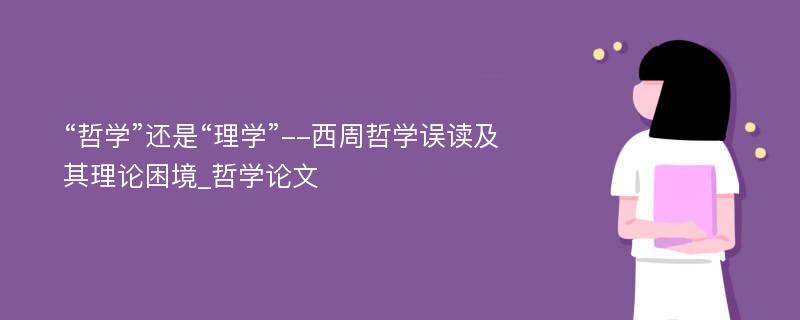
“哲学”抑或“理学”?——西周对Philosophy的误读及其理论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周论文,误读论文,理学论文,困境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的人是日本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西周(1819—1897)。他最初把Philosophy译成“希哲学”,后来为了解释这个新概念,又以“希贤学”加以说明,而最终作为学术用语在日本固定下来的是“哲学”。在采用“希哲学”或“希贤学”翻译期间,西周曾多次把这门学问与“理学”或“性理学”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西周最初接触Philosophy时,曾把它理解为与儒学中的宋明理学基本相同的学问。虽然他也感到其中有“大相径庭”处,但仍然将其与“性理学”类比。根据西周的《百学连环》可以看出,西周注意到儒学与西学中这门学问的不同主要在于:“此哲学在东洲称作儒学,儒学的根源自邹儒以来学者,其孔孟学派虽连绵相续却无变革。不像西洲学者那样,自古其学连绵相传,却各自依据自己的发明讨伐前人学说,唯采用不可动摇之处。所以不断推陈出新”。(《西周全集》第4卷,第169页)因此,他指出:“宋儒存在着虽有追求性理哲人却无自己著作,唯在圣贤经传中加入自己学说的问题”,“汉儒达不到卓绝在于泥古二字”。(同上,第183页)日本学者藤田正胜认为,这应该就是西周没有使用“理学”而创造“哲学”一词翻译Philosophy的原因所在。(藤田正胜,第10页)
然而,对于西周不采用“理学”而自创“哲学”一词翻译Philosophy的原因,如果仅仅追究至此,也就是说仅指出儒学与西学的这些表面特点的不同,不再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东西方的学问会存在这样的差别,其根源究竟何在等问题,就不能发现西周翻译Philosophy时存在的对于西方哲学理解上的缺陷,也就无法把握东西方学问所存在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本文拟从分析西周翻译Philosophy概念时的困惑和徘徊入手,探讨其理解上的局限,以为认识明治学术界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反思的向度。
一、“希哲学”、“希贤学”与Philosophy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最初传入日本是与基督教进入日本同期。麻生义辉、熊野纯彦等人只是指出大约在公元1549年前后。(参见麻生义辉,第22-25页;熊野纯彦编著,第9页)但是,藤田正胜的近期论文已经对时间和文献有了具体的指认:他认为Philosophy最初进入日本应该是在1519年,岛原加津佐印刷出版的《圣人桑托斯工作之记载》(サントス(聖人)御作業の内抜書)一书中多次出现“ヒィロゾヮィァ”(philosophia,哲学)与“ヒィロゾホ”(philosopho,哲学家)的概念。(参见藤田正胜,第6页)西周最初接触到哲学这门学问的确切时间虽不能确定,但是,在他于1861年为津田真道的《性理论》一书撰写的跋文、1862年前往荷兰之前给好友松冈邻的信,以及他为蕃书调所准备的哲学讲义中可以看到,这期间他已经开始关注这门学问。但在这个时候,他把 Philosophy理解为与“儒学”相同的学问。比如,他在给松冈的信中谈到:“小生最近得以了解西方之性理学、经济学等学问之一端,大为惊叹其乃公平正大之论,而觉悟到与以往所学汉说存在大相径庭之处……只是其所言ヒロソヒ之学,简述性命之理不轶于程朱之学,本于公顺自然之道……”根据此信不难看出,他把Philosophy理解为“西方之性理学”,虽然感到两者之间“大相径庭”,但将其看成与“性理学”同类学问是事实。不过,即使这样,西周还是把Philosophy翻译成“希哲学”,即使自己生造新词,也不愿采用“理学”或“性理学”来翻译。他为《性理论》所作的跋文如此,为蕃书调所准备的“讲义”也是如此。在“讲义”中他还解释道:“从毕达哥拉斯这个贤人开始使用ヒロソヒ这个词……据说语意为爱好贤明。与此人同时代有苏格拉底这个贤人继承使用此语……称自己为ヒロソヮル,语意为爱好贤德之人(=爱智者),与所谓希贤之意相当。”(《西周全集》第1卷,第16-17页)显然,在这里西周为了解释“爱好贤德之人”,使用了“希贤”这个单词。到了他从荷兰留学回来,在明治初年办私塾“育英舍”时,其所讲授的《百学连环》中,就直接说:“ヒロソヒ一直译亦可称为希贤学”。(同上,第4卷,第146页)
西周将Philosophy译成“希哲学”进而又以“希贤学”来解释,最初来自于他对Philosophy原意的理解。在西周所掌握的荷兰语中,据说除了直接使用外来语“Philosophie”之外,还有“Wijsbegeerte”即“爱智学”这种翻译,这使西周首先受到“爱智学”荷兰语译的影响,当然同时也受到了周敦颐“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一句话的启发。对于“希贤”一词源于周敦颐,西周在《百学连环》中有明确解释。(参见同上,第145页)根据藤田的论文,津田也使用了“希贤者”、“求圣学”、“希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所以藤田认为,这种翻译有可能是西周与津田两人交流的结果,而不会是其中某一位独自思考的产物。(参见藤田正胜,第8页)
从这种译语的来源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西周等把Philosophy与性理学等同理解的问题。周敦颐所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周敦颐集》,第28页),应该与其“圣可学”(同上,第40页)思想结合起来理解,这容易让我们想起程颐的一句话:“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二程集》,第318页)其实,周敦颐在这里揭示了士人求学的三个阶段,存在着三种不同层次的“希求”主体,同时也包含与之相对应的三个不同层次的“希求”对象,即:圣人以天地之理为希求对象,为人生最高境界;贤人则以圣人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士人则只能以贤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和崇尚的对象。①西周等人却把这三者混淆了,特别是把士人与贤者混淆了。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的身份与等级的区分。“士”在古代是职业读书人,读书做官是士的本职工作。更进一步,“士”既是职业身份,又是文化精神,士人以贤哲之人为目标,所谓“见贤思齐”,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但这只是第一层次的追求。当“士”上升、抵达“贤哲”境界之后,作为贤哲之人,其更高的目标是成圣,以圣人作为自己的更高境界;而只有圣人才能悟道,以道即“天(理)”为探索对象,并寻求与之达到一如境界。津田把“求圣学”与“希贤学”、“希哲学”等同理解,西周认为Philosophy就是“希贤学”等,这显然是把Philosophy之“爱智”的含义与周敦颐的“希贤”之意等同,从而既混淆了“士”与“贤”、“圣”的区别,也混淆了“爱智”与“希贤”的本质不同。根据西方哲学中关于哲人对于真知的追求,应该是“希天”的境界才是与之相匹配的,因为只有“圣人”才与古希腊认定的“哲人”境界相似,这两者才属于同样层次的存在,而“贤人”、“士人”还不是“真知”的爱好者,还不具备古希腊意义的“爱智者”的境界。然而,即使儒学中所谓的“圣人”与西方哲学的“哲人”在境界上相似,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哲人只是“爱智者”,而儒学之圣人却是“有智者”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贤人”的存在层次才是对应的。可是,从古希腊哲学意义来看,儒学中的“贤人”、“士人”都只是“臆见的爱好者”,与“真知的爱好者”即“爱智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样,由于儒学与Philosophy存在本质的不同,两者是不具备类比性的。西周在翻译Philsophy时,如果对这种情况有所把握,势必会陷入对应性译语的困境。
既有很高的汉学素养又可以用汉文写作的西周,不可能不理解周敦颐原文的意思,所以他对 Philosophy以“希贤”的意思来解释,显然是由于没有真正理解古希腊所谓的Philosophy的本质内涵所致。正是这种理解上存在的问题,才会导致他在解释Philosophy时让“希哲学”、“哲学”、“性理学”三者相互诠释,以致出现认识上既强调此又顾及彼、既努力想区别二者又总把二者等同视之的结果。比如,他在《复某氏书》中说:“大概孔孟之道与西之哲学相比大同小异,犹如东西彼此不相因袭而彼此相符合”(《西周全集》第1卷,第305页),而在《开题门》中表述得更为明确:“东土谓之为儒,西洲谓之为斐鹵苏比(ヒロソヒ一),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同上,第19页)。这里所谓的“大同小异”、“其实一也”,都说明了西周把东方的“儒学(理学)”与西方的“Philosophy”等同和混淆的问题。
二、Philosophy的两种含义
一般认为,西周通过“理学”来解释Philosophy是由于当时知识界普遍接受的是“理学”,而利用已有的知识来说明陌生的Philosophy这门学问是一种传播上的需要,也就是说,他并非不了解两者的不同。然而,只要我们进一步对照他的其他文献,就不难发现其根本原因还不在这里。Philosophy在古希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如果把这两者混淆了,不理解哲学意义上的Philosophy的真正内涵,那就势必会出现把Philosophy与中国的儒学,更确切地说与宋明理学等同理解的结果。
可以发现,西周把Philosophy翻译成自造的“希哲学”一词,并不是由于他把握到了西方之“爱智学”与东方之“理学”的本质区别,而是仅仅为了区别两种不同地域的学问。比如,他在《生性发蕴》中注释“哲学原语”时表明了这种理由,他说:“尽管可以采取直译的方式将之翻译成理学、理论之类,但是由此却会过多地引发与他者之间的混淆,故而如今翻译为哲学,与东洲之儒学一分为二”。(同上,第31页)可见,他仅仅是为了区别西学与儒学之“东洲”与“西洲”的不同才采用了“希哲学”,而不是出于区别两种学问本质不同的考虑。
根据藤井义夫的考证,古希腊在哲学这门学问诞生之前或同时期,也存在着日常意义和哲学意义两种不同的与Philosophy即“爱智慧”相关的用语现象。(藤井义夫,第1-12页)比如,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的梭伦与留迪亚国王克罗伊索斯的对话中出现的Philosopheon(寻求智慧),以及修昔底德的《战史》中伯利克勒斯在战殁者演说中赞扬雅典人热爱智慧时使用的Philosophoumen(热爱智慧)等,都是这种用法的例子。而在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中,最初采用这种用法的是赫拉克利特,在他的残篇中有“爱智慧的人们(philosophoi andres)必须是诸多事物的探索者”这种表达。不过,在这些文献中出现的与Philosophy有关的概念,都只是一般教养中好学、求知欲等日常意义,并不具备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爱智内涵。哲学意义的Philosophy自毕达哥拉斯始,而苏格拉底赋予了其具体内涵。这种哲学发展史在学术界已成共识,前面谈到的西周在最初的“讲义”中以及后来在《百学连环》中解释Philosophy时,都沿袭了这一观点。毕达哥拉斯用“奥林匹亚的比喻”说明“爱智者”的含义,他把人的超越现实功利的、自由探索事物本质的求知活动,置于人的其他一切活动之上,从而赋予了哲学意义的Philosophy的本质内涵。然而,毕达哥拉斯所揭示的哲学意义的“爱智”只是突出一种精神性的意义,究竟这种“爱智”寻求怎样的“知”的问题并不明确;这个问题只有到了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的宣言开始,才有了丰富而具体的内容。
苏格拉底把知识分为“人的智慧”与“善美之知”两种(プラトン,弁明21D、23A)。人的智慧指的是作为人一般所能达到的知识,如医术、航海术、手工艺技术等,这些无疑对于人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有用的知识。然而,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如何活得更好,如何达到幸福。根据苏格拉底的理解,人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对于善美之知的把握是最根本的条件。他认为“幸福”(Eudaimonia)与“行善”(Eu prattein)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人要获得真正的幸福离不开从善的行为。而人要行善,就需要善美知识。(同上,饔宴204E-205A)于是,关于善美之知的追求,就自然成为人活着的第一重要的知识追求。可问题是,苏格拉底的知识标准与一般的理解不同,他追求的是一种不含任何杂质、任何逻各斯都驳不倒的真知,那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认识高度,即所谓“普遍定义”。正是源于这个标准,他真正继承了古希腊人的精神传统,指出所有的人都是“无知”的存在,人充其量只是一个“爱智者”,而不可能达到“有智者”的状态。显然,这种哲学意义上的“爱智”中所要求的“知”的状态,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知道”、“认识”,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求知欲、好学,而是一种彻底的求知、求证的质疑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哲学中权威是不存在的,一切经典都只是人们质疑、批评的对象,哲学史上不可能有永世的圣典存在。于是,西方哲学史当然会成为一种“各自依据自己的发明讨伐前人学说……所以不断推陈出新”的历史。
西方哲学的这种本质特征,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把泰勒斯作为哲学始祖这一认识中得到印证。在泰勒斯之前,存在过古埃及文明,也存在过辉煌的神话文明,然而,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没有把这些作为哲学的起源,而是把泰勒斯的探索作为哲学的开始?这与从泰勒斯开始的求知的特点有关。因为古埃及文明所有的知识都是建立在现实的功利目的之上的,比如医学知识发达来自于制造木乃伊的需要,而数学知识与建造金字塔以及丈量尼罗河流域广袤的土地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现实的某种需要促成了某个领域的学问发达,这种学问只要现实目的达到就行了,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这是受制于现实、非自由的学问追求。而泰勒斯之前的希腊神话文明中关于世界的理解,是建立在故事性虚构(Mythos)基础之上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缺少对于认识对象的质疑精神,只是无条件地赋予神创造世界之先在性和超越性权威,且不容质疑,一切从信仰开始;这些都与亚里士多德所认定的哲学这门学问的本质格格不入。
然而,从泰勒斯开始的学问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学问只是想知道而求知,“想知道”本身就是目的,求知自身就是求知的目的,没有任何现实性功利的追求。比如他们追问世界的始原(arche)是什么,这个世界保持如此和谐有序的状态其原因何在,世界万物与这种作为始原的存在是怎样的关系等等。这种求知行为由于超越了现实功利,因而是一种自由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探索所得出的结论不具备权威性,允许质疑、批判;追求更为客观、合理的答案是这种探索的共同目的。它与古埃及文明中从现实功利出发的学问追求不同,与神话文明中盲目相信权威、不容质疑的接近宗教的缪多斯(Mythos)之主观想象也不一样,乃是一种全新的求知求智精神。这种精神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一切从怀疑出发之求证求真的逻各斯精神。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把泰勒斯作为西方哲学始祖的根本理由,也是西周所说的西方哲学能够“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根据上述西方哲学的本质特征,哲学意义的Philosophy中所要求的“知”,以及“爱智者”与“知”的可望可即却不可得的关系,显然与宋儒之“性理之学”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虽然“圣人”在儒家思想中是一种高不可攀的世界之传道立法者,可是自孟子始“人皆可成圣”的思想成为传统认识,到了宋代周敦颐提出“圣可学”、进而程子的“圣可学而至”(《二程集》,第577、578页)的阐述,逐渐为人之“成圣”指明了道路,最终发展到明儒进一步提出“满街人都是圣人”(《传习录》卷下,见陈荣捷,第213页)的极端。在他们的思想中,圣人之“格物致知”最终是可以抵达“知”天地万物的大境,也就是说人可以从“爱智者”逐渐到达“有智者”的高度。周敦颐所揭示的士之“希贤”、“希圣”到“希天”三种希求阶段,就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具体阐述。因此,在儒家的“性理学”之形而上学中,日常意义的“爱智”与哲学意义的“爱智”是没有区别的,西方哲学中最根本的“知”的问题在这里也是含糊不清的,更没有对人的认识作“知识”(Episteme)与“臆见”(Doxa)的严格区分。对于这些问题,可以说自西周、津田开始乃至整个明治日本的学界,基本上都没有清醒的认识。③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周在翻译Philosophy时在用语选择上出现的徘徊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麻生义辉肯定“西周助、津田真一郎等创造的‘希哲学’,是深刻探究的产物……其创造新词的思索和努力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麻生义辉,第47页),但是,在Philosophy一词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重要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三、西周对于“Philosophy”及其“知”的理解局限
前文说过,西周在留学之前即文久二年(1862年)为蕃书调所准备的“讲义”中,已经把 Philosophy翻译成“希哲学”,并以“希贤”诠释“希哲”的意思。如果考虑到当时进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文献极其有限,西周可能是通过“兰学”的一些资料接触到了西方哲学,那么,他在认识上存在的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他从荷兰留学归来,在明治初年创办的“育英舍”中讲授《百学连环》时,却仍然沿袭这种理解,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了。
在《百学连环》中,西周这样解释Philosophy这个概念:
Philosophy这个词之philo是英文的Love(爱),而sophy则为wisdom(智)。其语义为希求热爱贤哲。
哲学(ヒロソヒ一)也有称之为理学、或者穷理学。
始称此学为ヒロソヒ一(Philosophy)的人是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即为以希求热爱贤哲、自己想成为贤哲之意所命名。
……希腊有Socrates(苏格拉底)这个人,最初以称之ヒロソヒ一为喜好使之(得以)确立。
作为ヒロソヒ一的含义,正如周茂叔已经说过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那样的意思,因此ヒロソヒ一直译亦可称为希贤学。(《西周全集》第4卷,第145-146页)
《百学连环》中见到的关于Philosophy的解释,比之前的“讲义”内容详细,也是人们所引用的关于西周的“哲学”一词解释的最基本的文献。然而,我们能够发现,其中与从前不同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明确将Philosophy作为合成词,即由philo和sophia两个部分构成,不像“讲义”中源于荷兰语“Wijsbegeerte(爱智学)”的影响而译成“希哲学”;(2)“希哲学”的翻译不再出现,而是直接使用“哲学”,但是仍然以“希贤”之意解释,最后明确表示可以直译成“希贤学”;(3)明确表明“希贤”之意来源于周敦颐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句话;(4)指出“哲学”也有翻译成“理学或者穷理学”的。
从上述(1)中,我们知道西周此时已经弄清了Philosophy在希腊语中的语义。从(2)中,可以知道西周此时已经不再使用“希哲学”而直接使用“哲学”,此时的其他文献中关于Philosophy的旁注中也只使用“哲学”。上述(3)说明了“希贤”的来源,而这一点在以前的“讲义”中并不明确。上述(4)表明出现了“穷理学”的译法,因为此时西周已把Psychology即现在的“心理学”翻译成“性理学”,故不便再用“性理学”翻译Philosophy,而换成了“穷理学”。但这并不意味他已经放弃初期把性理学与Philosophy相对应的认识。
从上述情况看,西周留学荷兰之后,不但没有改变最初关于Philosophy的理解,相反更加坚定了把Philosophy与儒学中的理学进行对应性理解的认识。正如人们所熟知,西周在荷兰留学时期,正是荷兰处于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哲学盛行的时期,通过欧普佐梅尔(C.W.Opzoomer)引进的法国的孔德、英国的边沁、穆勒等人的哲学在荷兰盛极一时。虽然西周是否直接受教于欧普佐梅尔并不清楚,但他对于欧普佐梅尔的重视可以从他带回国的藏书中得到确认。实证主义哲学是当时西方哲学界的主流,这是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兴起所带来的崭新思潮。而由亚里士多德奠定的西方哲学体系中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形而上学在此时逐渐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追求,进而把实证主义运用到人生论的领域,这也是当时学术的新倾向。虽然西周在荷兰期间似乎也倾心过康德哲学,但他最终接受的还是康德的《为了永远的和平》而不是其批判哲学,从而使西周的哲学始终没有脱离实证主义经验论的范畴。(参见麻生义辉,第59-65页;桑木严翼,第17-20页)
无论实证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注重的都是经验知、实践知而不是理论知。经验知正是古希腊柏拉图哲学所揭示与批判的属于臆见认识的东西,这种“知”只是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二哲学”而不是“第一哲学”。相反,在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哲学看来,古典形而上学中所追求的所谓“第一哲学”之关于“存在”的理论知,与宋学中“理”的探究一样,都只是一种观念性空理而不是即物性实理。所以,西周认为实证主义哲学以前的西方哲学都是“空理上的学问”④,这也是明治初年的知识界把程朱理学、阳明学之“格物致知”都归入“空理”的原因之所在。
西周当时对于“知”的理解,我们可以从《百学连环》的“总论”中看到端倪。(《西周全集》第4卷,第13-17、43-47页)在这里,西周对于学、术、观察、实践、知、行等概念作了详细解释。其中对于“知”的来源的解释是:“知源于五官感知所发,是由外及内的东西。”这与我们一般对于“知”的理解并没有多大区别。然而西方哲学所追求的“理论知(真知)”并非源于感觉器官,而是理性探索的结果,其与西周所解释的“观察”(theory)、即“所谓观察,指的是万事极其理”密切相关。西周虽然认识到“观察”产生“单纯之学”,是“对于理的论述”,但他在这里仅仅把“理”作为一种“关系”中的存在进行把握,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观察”之theory是需要脱离五官感觉的认识活动,属于纯粹理性的认知范畴,叙述内容却在中途转向对“温故知新”与“知行”关系的说明,这显然放弃了对于“感觉知”与“理性知”、即“实践知”与“理论知”的辨别,于是,想要在这里找到Philosophy中所包含的“真知”与“臆见”之间的严格区分是不可能的。而他在该书中介绍“理体学(本体论,Ontology)”时,把“有”和“体”相对应,指出“理体学”之论并非论述其形,而是论述“真性(本质属性、本性,essential attribute)”;“所谓真性一切事物都有,但唯有一个名称的时候,是其终极的东西……大凡万物各有一种名称,要知道其终极,就需要知道其原因”。(同上,第153页)这里虽然谈到了对事物“原因”的把握,似乎可以看成已经脱离了五官感觉,然而,他在此文之后仍然用“童子”、“杖”、“犬”三种实物比喻“体”的存在,以此说明诸“体”之间的关系,这说明他对于“知”的来源问题的看法,依然停留在“源于感官认识”的层面。所以桑木严翼指出:西周哲学的“方法服从于自然科学的精神方法,其学风倾向于经验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诸思想”。(桑木严翼,第21-22页)这种脱离形而上学的哲学倾向,不仅西周如此,也是整个明治初期知识界的一种普遍倾向。为此,桑木进一步指出:“明治初期的哲学倾向,一言以蔽之,是以非形而上学的人生哲学作为根本,直接受到西方的实证主义经验论的影响”。(同上)
这样,受过良好汉学教育、对宋明理学具有很高素养的西周,由于接触西方哲学时受到的是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的洗礼,所以他在理解philosophy这门学问时,容易把Philosophy与宋儒的理学进行对应认识。虽然他也常常谈及两者有所不同,但只是简单地把“理学”断定为“空理”,仅此一言以蔽之,无法从根本上把握两者不同的本质所在⑤。西方哲学之形而上学所探索的“存在(有)”,与宋儒所追求的天地万物之“理”在西周看来基本属于同样的存在。尽管他把“体”理解成“有”,却只是将其作为“性”来把握。西周认为:“西方如汉学理这个字不是别的……是口头无法说明的存在……无论心里怎么思考,还要更进一步思考到极致,以此谓之理。”(《西周全集》第4卷,第147页)这里显然是把“理”作为纯粹的思维对象来把握,符合宋儒关于“理”的理解。他在《尚白劄记》中解释“ァィデァ(ィデァ,idea)”时说:“此语今译作观念,看成好像其与理字没有什么关系。其深处是与宋儒所指之理,呈现理之同一意味的语言”。(同上,第170页)然而,宋学之“理”,若从存于天地而言,只相当于希腊语的“摄理”(tuche);若在事物内部,只与亚里士多德的“内在形相”(eidos)相似;若从人的行为来看,只是一种“当为”(dein),相当于德语的sollen,而西方哲学的探索却要抵达赋予这些“必然性”、“本然性”存在依据的“存在本身”(auto kath’hauto),“存在本身”才是Philosophy的最高对象和终极目标。而“存在本身”并非一种思维性存在,而是一种真实存在(ontos on),与宋学之“理”不是等同的存在,只是在认识与把握上都需要通过纯粹思维才能把握。“理”与“存在”的共同点只是都与以思维把握有关,但在根本上却有重大区别。儒学中的“理”内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它与万物属于连续性的存在,人通过“格物”可以“致知”,达到对于它的把握,这是儒学之“理学”的立场。但西方哲学的“存在”,虽然属于世界万物的存在依据,却不在万物之中,而是超越于万物而独立之存在,与万物之间是非连续性的,因而人的探索可以无限接近它,却不能完全把握它从而达到“真知”。由于西方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之经验论立场的哲学否定这种超越性的“存在”,于是接受了这种哲学的西周,把Philosophy与“理学”对应类比、甚至等同理解就不奇怪了。
通过以上的梳理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西周采用了新造词汇“希哲学”翻译Philosophy,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西方哲学传统中对“知”的形而上学的独特追求,故只能从儒学中寻找“希贤”、“求圣”等与Philosophy之“爱智”表面含义相近的概念进行诠释,而没有意识到周敦颐的“希贤”之“希”的含义并无古希腊人那种彻底的求证求真的质疑、探索精神,也没有发现“贤”字虽然有“贤哲”之意,但与古希腊的Philosophy中所追求的“智慧(真知)”根本不同;这就决定了西周在翻译Philosophy时,只能在“理学”的框架内对二者进行对应性说明,从而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和误读。此其一。其二,由于西周在引进Philosophy概念时,所接触和接受的是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这使他不能从古希腊哲学的源头来理解西方哲学的传统,即不能从哲学最本质的“知”的独特性来把握Philosophy,而只能从其自身的汉学素养出发,简单地指出东西方学问之不同在于东方是“空理”,西方(近代)是“实理”;由于东方探讨“空理”,所以儒学不能抵达真理,只是重复于经典文献的诠释。这样一来,东方理学与“实际”相对的“空”,与西方古典哲学对“存在”本体无限探索之“空”的根本区别,就被进一步模糊和混淆了。不仅西周如此,与西周同时期的津田也是如此,甚至整个明治时期的日本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都是如此,即没有认识到西方哲学最本质的“知”的追求与儒学的根本不同,才是两者呈现出“泥古”与“革新”之不同的根源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讲,西周对Philosophy的误读就成了一种宿命,在所难免。
注释:
①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荀子·哀公》),指出了人之圣、贤、君子、士、庸人等不同层次的存在。“圣人”作为最高的存在,是需要修为而达到的境界。当然,“圣人”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是发展的,但人可以“成圣”的思想自孟子以后即成为儒家圣人观的基础。周敦颐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应该放在儒家关于士、君子向学求贤直至“成圣”的思想中来把握。
②如荀子说:“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荀子·哀公》)程颐也说:“圣人,生而知之者也。”(《二程集》,第578页)
③西周在《百学连环》中,虽然也谈及“臆断”(prejudice)与“惑溺”(superstition)的问题,并指出“臆断与惑溺是学者最忌讳的地方,要获得真理必须规避这两种病灶”(《西周全集》第4卷,第29);在《生性发蕴》中也触及到了智者与苏格拉底的不同,但都没有进一步论述哲学所追求的“知”与一般意义的“知”即“臆见”的本质区别。日本学术界对于西方哲学中“知”的问题加以重视并取得富有成果的研究,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初“ヘラス会”(希腊会)出现之后的事,此后,日本对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进入全新阶段,其中田中美智太郎的研究成果意义重大。
④与“空理上的学问”相对的是“实理上的学问”(Positive Philosophy),此学源于法国人孔德以及英国人边沁、穆勒。此三人以前都是空理上的学说,自孔德始初至实理上的学说。(参见《西周全集》第4卷,第181页)西周认为,“大凡一般学者若不入实际都涉空理。学者需要进入实际。”(《西周全集》第4卷,第21页)也就是说,只有关于具体事物和实践探索的理论才是实理,观念上的学术文章都是空理。
⑤对于西周接受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学术界一般都从明治国家的现实需要的角度来理解,当时日本社会的“经世致用”的需要让西周选择了经验论的立场。然而,这只是表面的原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对于 Philosophy并没有达到本质的认识。如果他完全把握了Philosophy的真意,就不会把“理”与“idea,相、理念”等同理解。也正因此,他才会认为孔德之前的哲学也都是与宋明理学一样的“空理”学问。
标签:哲学论文; 理学论文; 周敦颐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文化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