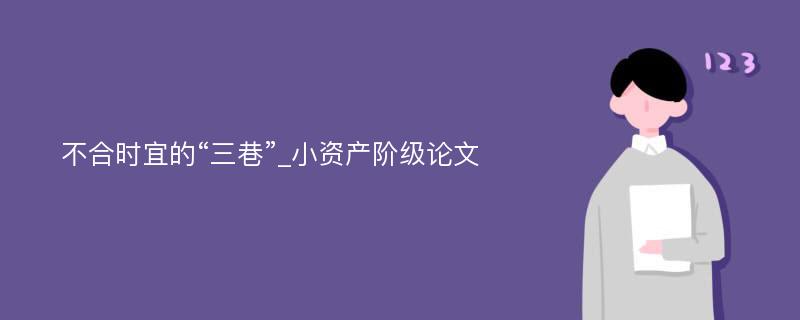
生不逢时的《三家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不逢时论文,三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964(2008)04-0007-05
最近几年中,重评“十七年文学”与反思新时期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两个热点①。有的学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试图扭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断抬高新时期文学、贬低“十七年文学”的倾向;有的学者仍然坚守启蒙的价值立场,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新时期的结论;有的学者则认识到,现在既不能简单回到十七年,也不能简单重复新时期,因此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细读上,试图从文本角度揭示出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文学生产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以此发掘“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细读当代文学作品,是不应忽视欧阳山的《三家巷》的。这部5卷本长篇小说,创作时间长达27年之久,跨越两个历史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中,《三家巷》和《苦斗》因大胆表现人情人性,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在新时期淡化政治、告别革命、肯定人情人性的潮流中,作者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作品的后3卷(《柳暗花明》、《圣地》和《万年春》),却未能得到文坛的一致认可。艺术革新者们认为这些作品太僵化、太保守了,较为保守的学者则把它作为维护革命文学传统、反对文艺新潮的重要武器。从这部作品以及有关它的评论,我们有可能同时展开对两个时期的文艺批评的反思,有可能揭示出两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不合时宜的成长小说
《三家巷》采用了十七年中流行的革命成长小说的写作模式,即通过人物的成长讲述历史的发展过程、论证历史的发展规律。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中,这类小说是保证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复杂性的重要手段。只有在这种写作模式中,作家才能兼顾革命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才能获得书写人物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因素的权利。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较为稳健的批评者正是从维护人物的真实性与丰富性的角度为周炳的缺点辩护。蒋荫安等人肯定作者对周炳的缺点的描写:“周炳身上的这些缺点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而逐渐泯灭的,我们认为这样的描写是深刻的。因为它不但为周炳以后的性格发展留下广阔的余地,更重要的是使这个形象更真实更生动而不致简单化。”[1]黄秋耘明确反对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随意拔高人物:“一个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一定要符合他自身的逻辑,符合客观现实的规律。不管作家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高出于书中的正面人物多少倍,他也没有权利代替书中的正面人物去思索、去感受、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周炳还远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一个像金刚钻般坚强、明朗的无产阶级斗士,在他的心灵深处,还残留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感伤的情绪,……直到《苦斗》最后一页,周炳只不过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的革命者形象,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共产党员。”[2]楼栖也肯定了欧阳山的良苦用心:“作者有意把他摆在最复杂的环境中,让他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作品结束时,周炳的性格还未十分定型,但比出场时却已成熟些了,作者的意图很清楚,显然要给《一代风流》后4卷留下发展的余地。可惜这个意图没有得到一些人的理解,有的评论文章把周炳的性格当作一个定型化了来评论,未免显得性急了些。”[3]
应指出的是,即便是肯定周炳的批评家,也很难完全摆脱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制约。比如,楼栖一方面批评性急的评论家把周炳当做定型化的人物来批判,另一方面又抱怨周炳成长的过程太缓慢,“他在矛盾中前进,在斗争中发展,但作者有意让他多受煎熬,性格发展得很有节制”,“作者仿佛有意把周炳的性格扣在笔下,不让他向前发展”[3]。其内在逻辑是:人物成长过于缓慢,是不能反映出无产阶级思想战无不胜、摧枯拉朽的威力。蔡葵认为:“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正确的描写和评价这样的人物,真正写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怎样逐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和发展过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是,当周炳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形象时,作家对于这样的人物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作出如何的评价。”[4]言外之意是只能以批判的而非赞美的态度来描写成长中的人物形象。章里、易水等人则批评作者更多地让周炳在革命斗争的实践(挫折与磨难)中成长,没有把周炳成长的动力归功于党的领导和教育:“作者过多地把自己的这个人物放在生活斗争中去考验,使他在生活斗争中做出应有的结论,逐步成长;而比较地(并不是完全没有)忽略了周炳这个人物成长过程中党如何给予正面教育的描写。”[5]从这些批评中,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对革命成长小说的成长速度、价值评判、以及成长模式的制约。
1964年之后,意识形态领域掀起“兴无灭资”风暴,为了追求百分之百纯洁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长中的人物形象已无安身立命之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完全丧失了进入文学作品的资格。许多批评者夸大了周炳思想中的小资产阶级因素,忽略了其成长的过程,把他看做一个停滞不前的小资产阶级形象:“虽然周炳的性格在《苦斗》的结尾还没有最后完成,尚有待于在以后几部作品中继续发展;但就目前出版的这两部作品的描写,周炳显然还只是一个带有不少弱点的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值得歌颂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4]
在前2卷中,周炳尚未成长为时代所期待的成熟的革命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其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保证了作品的审美性,这在当时却很难得到激进意识形态的认可。在不少感染了意识形态洁癖的批评者看来,周炳的思想杂质实在太多了,“周炳在革命斗争中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在爱情上的恋爱至上主义和唯美主义,都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品质水火不相容的。把这些东西看成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些‘缺点’,看成‘次要的方面’,可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上容纳而还不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要混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6]。
在革命成长小说中,成长者必须不断剔除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为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期待的那种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因此人物越是成长其性格便会越单纯、简单、干瘪。在作品后3卷中,这种困境逐渐呈现出来:周炳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在共产党员金端的引导下,对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进行了检讨,终于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练,经过延安思想整风,周炳彻底告别了个人主义,完全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来思考和行动,成为一个坚定的集体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战士。周炳终于成熟了,但时代却不需要这种成熟的英雄了,新时期所需要的,是从集体中剥离出个人,是肯定个人的主体性。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周炳的思想变得单纯了,但时代却不需要单纯的人了。在新时期关于“复杂人物性格”和“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大讨论中,不难看出当时文坛对复杂人物形象的强烈期待,对发掘人物性格的非理性层面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极端反叛情绪。不少艺术革新者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大力肯定前2卷中的周炳而极力否定后3卷中的周炳。
二、爱情与政治的纠缠
如何评价《三家巷》中的爱情描写,也是争议较多的问题。1964年后,欧阳山被宣判为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至上主义者。进入新时期,许多人认为这种观点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是政治上的无限上纲。这种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由于受到“拨乱反正”的政治情绪的影响,它未能很好地揭示出作品被批判为宣扬爱情至上的内在逻辑,也不利于准确认识那个时代文学批评的内在症结。
当时对《三家巷》爱情描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爱情描写太多太滥,“把爱情写成了一条龙,把政治写成了一条虫”[7]。有人曾粗略统计了一下,“书中情人近二十对,三角恋爱五六起,还有三四人同时追求一人的场面;而那位‘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书中的主人公周炳,则是一个被七个女人追求着的‘美男子’”。“作者特意在周炳的周围安排了许多表姐表妹,让他在姑娘堆里厮混,整天陷在个人感情的漩涡中爬不出来,革命斗争都被‘哥哥妹妹’挤掉了。很难设想,周炳这样的人还能革命”[6]。其二,周炳未能处理好政治和爱情的关系。“一个革命者应该永远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但书中的周炳却恰恰相反,他在若干次的恋爱中都把爱情凌驾于革命之上”[6]。“他从事革命的动力是爱情,爱情的得失成了他革命情绪高低的标尺:爱情顺利,革命情绪就高涨,脑袋顶着了天;失去了爱情,情绪就一落千丈,陷于绝望而不能自拔”[8]。有人认为他领导的“十大寇”在震南村所进行的斗争,都不是真正的阶级斗争,而是保护美人的斗争,胡杏、胡柳、何娇等人一有危险,这些“美人的保镖”就不顾一切地盲动,以革命的力量去冒险[9]。其三,作品夸大了爱情的力量,以超阶级的爱情调和阶级斗争。“从作品的实际描写来看,周炳的逢凶化吉,化险为夷,难道不多半是由于陈家小姐的石榴裙的保护?可是在现实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哪里会有这样的事呢?一副漂亮的面孔就能成为抵御敌对阶级刀剑的盾牌?反动统治阶级空虚而无聊的妇女的情欲就能拦阻对革命者的血腥镇压?就算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过这样的个别事例,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只会感到耻辱和恼怒,一个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作家就应该更从本质上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暴露,表彰革命者的坚贞节气。可是在《三家巷》和《苦斗》中,作者的态度却分明是为主人公又庆幸又得意,并且企图引导读者也向往这种被黄色的恋爱所‘保护’的‘革命’”[7]。
重读作品,我们不能说这些指责是完全歪曲作品的“无限上纲”,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是一个政治高于爱情的年代,文学中的爱情必须是以政治本位的爱情,必须通过爱情诠释政治,而不能喧宾夺主,这恐怕才是作品被批判为爱情至上的根本原因。在新时期人道主义复苏的潮流中,爱情服从于政治的文化逻辑逐渐被瓦解,爱情的政治和阶级属性逐渐被淡化,以爱情为本位的爱情描写逐渐增多,从爱情、婚姻和家庭角度反思革命历史,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在这一文艺新潮中,《三家巷》、《苦斗》中的爱情描写得到广泛认可,欧阳山也被看做那个年代少有的敢于突破爱情禁区的作家。但作者并没有顺应批评界的行情而加大爱情描写的分量。恰恰相反,在《三家巷》后3卷中,爱情描写的篇幅大为减少了,从早期的热烈奔放转变为冷静沉着,从浪漫、感伤、放纵转变为理性的节制。周炳已成为一个革命事业至上主义者,爱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大大降低,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何守礼频繁地示爱和追求,周炳总是千方百计地回避。他还站在民族、国家和理性的立场上奉劝何守礼:“有帝国主义在,有国民党在,一个人谈什么恋爱呀,结什么婚呀?”“你应该让感情的列车在理智的轨道上奔驰。如果能够这样子,那么你到处都可以畅通,精神上得到宁静,不会觉得痛苦,也不会再受煎熬了。”可想而知,在一个非理性主义逐渐崛起的年代,在一个信奉跟着感觉走的年代,这种理性化的爱情注定是不受欢迎的,当时就有不少批评家义愤填膺地指责周炳在延安的爱情不够大胆、不够热烈。这显然给欧阳山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他不得不从历史真实的角度为自己辩护:延安时代的青年过的“是一种高度政治性的生活,也是高度理智的生活,很少有个人的感情宣泄,平时过的是高度有组织的集体生活,一切活动都是集体的,反对任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描写恋爱也很难表现,绝对没有那种卿卿我我、情意缠绵的形式”[10]。
客观地讲,欧阳山既没有像十七年的许多作家那样,把爱情与政治简单等同起来,以政治排斥爱情,使爱情失去其自然属性和人性内涵,也没有像新时期的许多作家那样,把爱情与政治简单对立起来,以爱情排斥政治,使爱情失去其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他在处理爱情与政治的关系时,有意识地在二者间保持着一定的弹性和张力。这主要表现在周炳与区桃、陈文婷,周炳与胡柳、陈文英,周炳与胡杏、何守礼之间的情感纠葛上。周炳与出身底层的区桃、胡柳、胡杏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吸引与被吸引的关系,她们是推动周炳走向革命的动力。作者肯定这种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爱情,并通过这种爱情的悲剧来谴责反革命的政治。区桃牺牲后,周炳陷入了精神危机;胡柳牺牲后,周炳化悲痛为力量,产生了更强烈的战斗激情;在延安,周炳与胡杏始终把革命事业放在首位,把爱情深埋在心底。这显然是从爱情角度描写周炳在政治上的成长的。周炳与出身资产阶级和地主官僚家庭的陈文婷、陈文英、何守礼之间的情感关系,则是一种诱惑与被诱惑的关系,这种情感是周炳走向革命的阻力。在这种类型的情爱描写中,更多地展示了爱情的自然属性和人性内涵(嫉妒、仇恨、肉欲等),显示出作者对政治与爱情问题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也是围绕着周炳的成长而展开的:周炳在坚定的政治理想的支撑下,成功地从陈文婷缠绵的爱情中突围,战胜了陈文英赤裸裸的肉体诱惑,摆脱了何守礼任性的反复纠缠,最终与胡杏走向了爱情与革命相一致的婚姻,这无疑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述周炳在政治上的成长过程。
三、五四话语与革命话语
在十七年中,《三家巷》、《苦斗》被批判为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也并非空穴来风,欧阳山在当时并未彻底否定五四精神和人道主义。陈文雄、何守礼、李民魁、张子豪、周金、周榕等人,都曾是思想单纯的青年,他们在五四思潮的鼓动下,积极探索民族和国家的出路,有的倾向于实业救国,有的倾向于商业救国,有的倾向于国家主义,有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有的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共同盟誓永远互相提携,为祖国富强而献身。欧阳山对这些热血青年无疑是有所肯定的。对于深受人道主义熏陶的陈氏兄妹,作者虽然对其局限性有所批评,但并没有完全否定,信仰基督教人道主义的陈文英既慈善又虚伪,整天奔波劳碌,“替那些贫穷和不幸的人服务”,在贵妇人的慈善会议上,她极力主张抚恤救济那些赤色的孤儿寡母,“为了这一点,她的嗓子哑了,她的苍白的脸蛋发红了,她的圆圆的大眼睛甚至贮满了泪水”[11]517。她天真地相信:“如果人人都信仰和平,就不但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人与人之间也没有欺凌侮辱,仇恨凶蛮了;如果人人都信仰博爱,社会上就不会有贫富不分,尊卑之分,幸与不幸之分了。”[11]524当胡杏受到非人的虐待时,陈家姐妹轻飘飘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丝毫无助于改变胡杏的命运,但坚信“人道、博爱、自由、平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的何守礼,却能挺身而出,为胡杏鸣冤叫屈,并愤怒揭发何家的罪恶;陈文娣“虽然也觉着这世道越来越崎岖不平,但是她的人道主义信念却是不肯放弃”,当何守仁决定派兵镇压震南村的革命斗争时,她坚决反对这种封建主义的野蛮行为。
从整体上来讲,作者是在革命的立场上来讲述五四的,每当涉及到五四话语与革命话语的关系时,他总是刻意强调革命优越于五四的权威话语。随着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激化,那些满腔救国热情的五四青年,很快就依着他们的阶级出身、阶级立场的不同而分化了。陈文雄、何守礼、李民魁、张子豪等人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和誓言,背叛了五四精神,纷纷融入到腐败的社会体制中,周榕、周炳则坚持、继承并发展了五四精神,加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这无疑是以文学的方式诠释毛泽东的权威论断:“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去了。”[12]700
从陈文雄与周泉,陈文娣与周榕、何守仁,陈文婷与周炳、宋子廉等人的爱情描写,也可看出作者对五四话语的反思和批判:满口人道主义的陈文雄,与立志要做自由、独立的新女性的周泉胜利结婚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五四精神的胜利,但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并非平等的,而是以一方屈从于另一方为代价的,陈文雄利用金钱和地位,轻而易举地把周泉变成一个不能自由飞翔的小鸽子,使其失去了个人主体性,整整昏睡了15年,直到陈文雄自杀她才从睡梦中醒来。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陈文娣和周榕以私奔的方式飞出三家巷的牢笼,宣告他们“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这种绝对自由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在经济贫困和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陈文娣开始退缩,她极力反对周榕参加革命:“为了证明我是一个‘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为了爱情和自由,我不怕任何障碍,我什么都能够做出来,但是在政治上,我怀疑你是偏了一点。”[13]183这位五四时代的自由女神很快变成了自由的诅咒者,她开始羡慕那些盲婚的农村女性。她最后和周榕分道扬镳,嫁给了何守仁,过起了养尊处优、醉生梦死的阔太太的生活。周榕在评价自己失败的爱情时说:单凭着对爱情的信念是不足于获得爱情的胜利的,“我总以为‘五四’精神会指引她前进,但是现在看来,‘五四’精神并不可靠”[13]289。这正是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化逻辑。在追求爱情自由上,陈文婷似乎要坚决一些,但她也是“‘五四’精神并不可靠”的文化逻辑的阐释者。为了获得周炳的爱情,她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当革命风暴来临时,她就开始退缩了,她想法设法地阻挠周炳参加革命,劝他不要和自己的买办家庭过不去,劝他和她一起读书,组建一个柔情脉脉的小家庭。这实际上是两种话语的尖锐对抗,她所进行的是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后来在家人的包办下,陈文婷嫁给了腐化堕落的官僚宋子廉,在糜烂的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最终以自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进入新时期,不少激进的思想、艺术革新者有意识地淡化了五四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把它简化为个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把五四时代看做是知识分子主体性觉醒的年代,并以此为标准反思和批判革命历史,以文学的方式讲述启蒙压倒救亡、革命压抑个人(知识分子)的故事。在这股文艺新潮中,欧阳山并未随波逐流,没有按照艺术革新者的逻辑去讲述革命历史,而是以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体验,同时展开对五四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反思。在《圣地》中,他采用了一种论辩体的形式,集中探讨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纪律、人情与原则的关系问题。在极力强调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年代,作者没有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写作,他并不完全认同张纪文、何守礼站在五四的立场上质疑革命(抱怨在延安没有言论、通讯和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胡杏在作品中承担着沟通、协调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功能,她一方面批评工农干部杨生明、吴生海不信任知识分子,批判过火的抢救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另一方面又批评张纪文、何守礼自命清高、不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肯定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在极力张扬个人主体性的年代,欧阳山没有完全肯定个人主体性,在他看来,个人主体性是很难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划清界限的。在周炳离开延安前夕,他奉劝何守礼、李为淑、张纪贞、张纪文等人在集体生活中不要筑起一道防线保护个人,在革命的大家庭中不要放纵个人,在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中不要神化个人。这完全可以看做是欧阳山与思想和艺术革新者们的对话。
正是这种价值立场,把欧阳山推向了文艺新潮的对立面。在批判朦胧诗现代派、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他都是坚守四项原则的急先锋,这自然会给人一种极端保守的印象。因此,尽管他(类似的还有刘白羽、贺敬之、丁玲、魏巍、臧克家、艾青、杨沫、曲波等人)在新时期仍然笔耕不辍,却很难得到思想和艺术革新者们的认同,只能反复慨叹自己生不逢时。
注释:
①代表性的论著有:李扬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程光炜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王尧的《“重返八十年代”与文学史论述》(《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