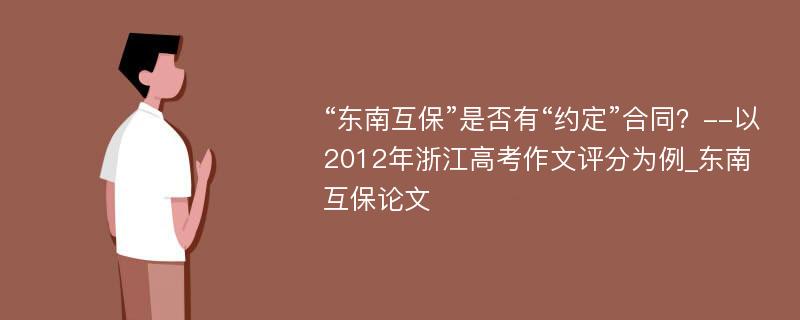
“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以2012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为例论文,高考作文论文,东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3)11-0162-10
一、问题的提出
义和团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当北方战事方兴之际,南方诸省与外国交涉,使所辖区域自外于战场,从而造成了“东南互保”的局面,这怪诞一幕,不仅在当时为世人所瞩目,事后也引发长久争议,历史与价值的辩论相互纠缠,聚讼至今,尤有余声。当下研究对“东南互保”的评价已趋多元,而对于基础史实的认定,却似仍遵循一套固定模式,凡论及“互保”成立之由,多列举“条约”或“章程”一二三云云,并加诸“议定”、“订立”、“签约”一类按语,读者因之形成约款既成事实的印象。
追溯源头,这一说法可谓其来有自。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赵凤昌对“中外会议”场景有过详尽记述,至于会议结果,则几无保留地给出“两方签约散会”一说。①后世研究者在处理此问题时,或将回忆等同信史,径引成说,或由结果推论前因,不暇追究事实之有无,以致凭印象形成的某类“常识”广为传播。修纂于民初的《上海县续志》,叙述“互保”要角之一、上海道余联沅之生平,称其“禀承南洋大臣,与各国领事议定东南互保约款”。②20世纪60年代,相关研究文献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谓“这一纸卖身投靠的文书使侵略者深感满意”,但亦承认“订立互保约款”的前提。③80年代以降,研究者对此事件的观感已然发生变化,不过,在相信文件经过“正式签订”这一点上,观点似仍贯其旧。④廖一中等撰《义和团运动史》记“东南互保”事:“(1900年)6月26日……经过双方谈判,当日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⑤读者众多的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最近一个版本谓“刘、张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共同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此处“共同炮制”一语,尽管措辞不甚严谨,但引申义还是很明确的。⑥90年代出版的多卷本《上海通史》同样采纳这一种观点,相应表述为“经过谈判,当天议定”。⑦至2006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还是沿用了“正式签署《东南互保章程》共九条”这样貌似确凿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⑧
其实,“东南互保”究竟有无“议定”约款,还是个问题,对此提出异议者且不乏其人。约半个世纪前,丁名楠先生已明确指出“‘中外保护章程’最后是没有订立的”,他强调中外间协商者为“章程”,并非“条约”,由于外国领事“拒绝签字”,归于无果。⑨这一看法被80年代出版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所继承。⑩刘天路进而注意到,中方所拟章程有着鲜明的“限制列强行动”的内容,这是造成列强对签约取消极态度的主因。(11)不过,这类观点在国内学界似未引起充分重视,前引多种著述不断重复旧说,即是显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缘于惯性驱使,众论易为成见所囿;另一方面,“拒绝签字”说的论证尚欠完善——主要强调妨碍订约的外部因素,对中方本身交涉行为几无着墨,至于“互保”谈判究竟以何种方式收束,也语焉不详。相对而言,以李国祁、王尔敏为代表的台湾学者,对“互保”过程的研究更以细密见长,实证风格突出,他们承认中外会议“始终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发生了良好的效果”,但当天并未就互保章程达成共识,也无正式结果可言。(12)林世明所著、至今唯一一部关于“东南互保”的研究专书,认为中外前后经历三次会议,而最后达成者“根本不是一种‘条约’”。(13)2000年纪念义和团运动一百年时,有论者为“东南互保”研究史做总结,仍将“盛宣怀、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与各国领事订立约款”和“列强各国拒绝正式签约”两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并列,莫衷一是。(14)
事实上,“互保”交涉并非一蹴而就,中间经历了若干曲折的阶段,讨论“议约”或“签约”,必须将视野从某个单一时间点拓展至更长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外互动频繁,列强国家各怀心事,而中方内部,包括直接负责交涉的盛宣怀、余联沅等人亦有行动不同步处。本文拟由先行研究较少注意的角度切入,再审“东南互保”问题,尤其对交涉情节做具体考察,进而落实“议定”说之有无。目的不仅为修正某些既有的、似是而非的历史认知,也希望通过史实重建,为理解那段特殊时期中外交往的实态提供助益。
二、“中外会议”前双方筹备
当华北义和团骤兴,作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的上海亦不复平静。面对外国军事干预的压力,驻沪中国电报总局督办盛宣怀与周边幕僚聚议筹画,发出首倡“东南互保”的声音。1900年6月23日,盛氏分别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香帅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由此明确提出中外互保的办法。(15)至迟不晚于6月25日,张之洞、刘坤一均已复电赞同,授命上海道台余联沅出为“与各领事订约”,盛宣怀“帮同与议”,另分派道员陶森甲、沈瑜庆赴沪与议。(16)盛、余二人受命后,迅即约请驻沪各领事于6月26日齐集会议,旋获响应。接下来的问题,就要放到谈判桌上解决了。
从江、鄂总督确认“互保”立场,到中外代表坐下来正式谈判,进展神速,中间相隔不过短短一天。6月25日当天,上海道与领事团两方面都在为会议做最后准备。就晚清外交体制论,通商口岸地所驻道台,兼任海关监督,同时负有处理涉外事宜之责。上海道余联沅的官位等级与领事品级相埒,经授权出为议款,系外交上直接负责之人。盛宣怀名义为协助上海道,并无明确职权,他也自谦“局外暗昧”(17),一开始做出过一番推让的姿态,实则“互保”具体操作仍由其主导,相关两个核心文件——“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均由盛、余合作完成。
前一章程草案原为五款,余联沅先于6月25日拟议,包括江、鄂地方力任保护洋商教士,禁造谣言,严拿匪徒,及限制外舰入江诸条目。(18)刘坤一以为“均可行”,但须补充保护制造局、吴淞炮台两条,并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一层列入,藉此划分彼此权责。(19)章程最终由盛宣怀修订完成,内容扩展为九款,其中第一、二款交代“中外保护”的一般性原则,第三款说明江、鄂总督在辖区内所负责任,第四至第九款则全部针对外国而言,除最末两款对外国人(侨民、游历者、传教士)活动有所规定外。主要是为限制列强在长江流域可能发起的军事行动,而各款“措词皆预留后步”,以备各领事驳议。(20)这份定名为“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的文件,也就是后来习惯上所称、而语义不尽准确的“东南互保约款”。
另鉴于上海租界的重要性,章程第二款加有附件,即“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分十款,对华洋两界治安权责做出了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民由华官保护,严拿流氓、土棍,添募巡捕,在城厢内外昼夜巡逻,租界周围由中国军队常川驻守,等等。(21)
如稍加留意,可发现中方预拟的两个文件都以“章程”命名,而它们实际具有某种条约协议的属性。“章程”(regulations),一般指技术性的特别机构的组织法规定要采纳的那些章程,有些章程有时自身可以构成一项条约文书。一国同意受条约的约束可用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书、批准、接受、认可或加入,或任何其他同意的方式来表示。(22)从国际法角度看,“章程”的生效,可以通过双方签署或者换文来实现。余联沅在初拟条款后,也曾请示应否聘请“律法官”,即律师,张之洞复以“请酌办,不必商”。(23)由此可见,对此次会议中方立意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订定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款。
与此同时,上海领事团也在进行紧张的准备。6月25日下午各国领事召集会议,法国总领事白藻泰(Bezaure)率先提出,如中方代表获得总督的全权授命,各领事也应具同样权限,从而达成谅解,将该总督辖区视为中立地域。这一意见得到了日本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等多数与会者的附和。地位敏感的英国总领事霍必澜(Pelham Warren)也没有异议,只是建议可进一步扩大中立地范围,将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各省也包括进去。(24)白藻泰等急于使长江地区中立化,是为避免战争扩大,也包含压制英国的意图,而霍必澜扩大中立地至法、日等国在华势力圈,也明显带有反制意味。将中外双方的会前筹备工作比较起来看,可以发现,各国领事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确立和平基础,避免战争波及南方省区,但这一点被限定了前提:在他们的预期中,将与东南督抚达成的,不过是的在局部地域内有效的、类似谅解备忘录的东西,而非对各自权责做出具体规定的条款。所以,领事团一开始就没有(也无意)像中方那样提出一个一揽子方案,当后来看到这个方案,甚至还包括许多约束性的内容,其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会议现场
6月26日下午3时,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在会审公廨(25)举行会议,盛宣怀以江、鄂公请的“帮办”名义出席。关于会议情形,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颇有绘声绘影的描述:
旋得各省复电派员来沪,盛即拟约八条,予为酌改,并加汉口租界及各口岸两条,共成十条,并迅定中外会议签约之日。其会议之所,即在新建会审公廨。盛既不在签约之列,对外即不便发言,又虑沪道余联沅向拙于应对,即为定中外会议座次,外人以领袖领事在前,以次各领事,中则以沪道在前,盛以太常寺卿为绅士居次,与余道坐近,再次各省派来道员。先与余约,倘领事有问,难于置答者,即自与盛商后再答之,庶有转圜之地。议时领袖系美国古纳总领事,果因五月二十五日上谕,饬全国与外人启衅,开口即云:“今日各省派员与各国订互保之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办否?”此语颇难答,遵办则此约不须订;不遵办,即系逆命,逆命即无外交,焉能订约?余道即转向盛踟躇。盛告余,即答以今日定约,系“奏明办理”。此四字本公牍恒言,古领向亦解之,意谓已荷俞允,即诺诺而两方签约散会。(26)赵凤昌非列席者,所记不是出于亲见,这段话中有明显错误。领事团领袖系葡萄牙总领事华德师(Valdez),而非美国人古纳(Goodnow)。会议当天,江、鄂指定代表沈瑜庆、陶森甲尚在南京,并未到沪。(27)不过,会议进程中盛宣怀“指授沪道”的作用,应该不是夸大。中方在会上提出的两份章程,实际当天上午才由盛拟议完毕,当晚余联沅去函云:“顷蒙指授机宜,多费清神,感佩无既。长江保护章程及上海租借[界]章程,请饬各抄一份,掷交去手,是所拜祷。此事如有确耗,亦乞略示为叩。”(28)可见他在会前未及掌握新改章程的全部文本,其程度大概了解大意而已。
再,所谓“双方签约散会”,也与事实不符。日本领事小田切的记录,属外交报告性质,可靠性相对较高,据其记载,余联沅在会上首先发言:
目前南北消息断绝,朝廷意旨未明,刘、张总督不论北方情势如何,力任保护长江一带外人生命财产,为防止中外间相互误会,特派我等与各国领事会议,协商保护章程。如此章程获各国政府同意后,由各领事调印生效,两总督在任之期,不论朝旨如何变化,必恪守章程,极力维护地方和平之局。(29)上述发言主旨在于代表江、鄂总督表明诚意,相应提出预拟的章程草案,希望在当天正式签署生效。领袖领事华德师代表各国回应,不过重申了6月20日大沽海军的联合声明,即列强在中国北方用兵,仅针对义和团及反对他们进军北京救援本国同胞的人,决无其他用意,进而表示如长江一带平静无事,各国将不会采取军事举动。(30)对于章程条文,各领事的态度则有相当大的保留,多数意见认为条款设置于己不利,不愿接受这样一个带有“自我约束”性质的协议。会后,盛宣怀向刘、张报告说:
奉岘帅、香帅电,帮同余道顷与各领事会议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悉遵两帅电示。各领事驳论多端,当告以督抚允认真保护,必须各国允兵船、炮台、制造局三款,方免误会生事。彼虑军火接济北匪,尚无法坚其信,兵船非许其各口添数只,亦必不允。现允照水师提督二十四文义照会余道,若长江内地无乱耗,各国决不派兵干预等语。(31)章程第五(兵船)、六(炮台)、七(制造局)各款,限制列强军事行动,本是中方注意所在,也最多引起外人非议。借当天会议,双方有机会互陈立场,彼此有所谅解,但事实上并未形成正式结果,故不存在“签订”一说。
第二天(6月27日),领事团决议作一共同声明,由领袖领事照会上海道,其文录下:
昨承贵道与盛京堂面述,两江、两湖制台诚意实力保护地方安静及保民命财产,倘有匪徒滋扰受损,愿为担承各节。各领事闻命欣慰,嘱转道谢悃。某等兹欲使两位制台得知,前在大沽各西国合兵,提督曾出告示谓,此次用兵实为专攻团匪,及阻挠救脱在京及他处遇险之西人而已。并欲申明,我各国之政府前时、现今均无意在扬子江一带进兵,不独一国不如此做,合力亦不如此做,为此布达。(32)该声明实际将昨日会议答言书面化,并未对中方所拟章程作直接回应。6月28日,余、盛会晤华德师,催问章程可否得到各国赞同,后者表示“宗旨均合,条目须酌”,仍不肯给出确切答复。(33)按前揭林世明书谓“互保”交涉共经历了三次中外会议,即6月26日、6月28日、7月7日三次。此说不确。实际上,盛、余和各国领事真正坐在谈判桌上合议仅有一次,即6月26日初次会议,其后交涉均是以照会往来和非正式拜访形式完成的。
至此,“互保”交涉的第一会合结束。就刘坤一、张之洞的本意而言,想把“互保”落实到约款,明文载定中外义务,目前结果显然与其初衷有所距离。此后,他们一面将章程内容知照各国政府,希望尽快获得批准;(34)一面指令上海道与领事团协议,以便尽快在上海签署定约。附带提及的是,当时清廷以“招拳御侮”为主旨的上谕已抵上海,继而又有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京被戕的消息传来,群情震动。余、盛等致力于安抚弥缝,严控消息扩散,以使“即外人传闻,亦是疑似之间,不足以为据”。(35)刘、张等地方大员则达成默契,一面将谕旨秘而不宣,一面向驻沪领事保证“无论北事如何,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36)东南督抚企图将“互保”局面以契约形式固定下来,但客观上随着时局演变,交涉进程已更加复杂化了。
四、由“签约”到“换文”
刘坤一、张之洞等原以为章程很快能完成签署程序,但对手方却未肯轻易就范,尽管多数国家原则上赞同东南省份实行“互保”,但于正式订约,均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这缘于有些规定限制了它们在长江的活动,同时也与北方战场形势的显著变化相关。各国政府的立场势必影响本国驻沪领事的态度,上海交涉因之变得更为艰难。(37)第一次会议后数日,余联沅与盛宣怀就如何答复领事团6月27日照会往复函商,二人目标一致,都在说服各领事尽快签约,而行事方法则稍有区别。余联沅计划再约领事聚议,讨论章程条目,争取在会上达成协议。其7月1日致函盛宣怀谓:
据鄙见,此事总宜请各领事会议,方可使彼无猜,万不可有一毫令之怀疑(如一国有意见,则事不成矣),致误全局。如我公以为然,即乞示复,以便敝处致函领袖领事,定时会议,届时再请鼎力维持,俾无陨越,是为至叩。现仍拟十点钟先谒,恭求指授一切也。如与一国有商议之事,派员往商,方不著痕迹。如沅与我公往,则人皆耳目之矣。英、美两国虽已定往,可否改订?尤为感祷。(38)作为直接负责交涉的地方官,余联沅持公事公办的立场,避免因赴领馆私议而授人口实,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盛宣怀安排分别拜会各国领事,他也不表赞同,坚持“总应会议,以示无私,若排拜几处,岂不惹别国见怪?”(39)
相对而言,盛宣怀则少顾忌,反而有意识利用身份便利,调用各种私人关系,有时甚至撇开余联沅单独行动。7月1日当天,他先后走访英、美、日三国领事,解释目前一系列突发事故,并将总督来电出示,作为“仍照原议办理”的证据。(40)当晚,盛宣怀发电刘坤一、张之洞:
顷与英、美、日各领事面商,拟由道照会领事云:前议尚未声明将来如何办法之处,诚恐北方衅端更大,东南人心动摇,自应彼此再为声明:“无论以后北事如何变端,上海及长江、苏、浙内地,如各国政府允仍照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运兵,两位总督亦允能干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各国在各省之人民财产”等语。并已将两帅断不更易之电交阅,各领允即电外部。请速电余道赶办照会,并请会电各驻使,愈速愈好。(41)当时情况下,就保护章程条款一一征求承认,已是很困难的事情。盛宣怀转而一面要求上海道余联沅发出照会,以宣示刘、张的声明;一面动员各领事向本国申请授权,从而达到以换文确立“互保”原则的目的。查万国公法:“两国立约,所应遵守之责,不拘式款如何,有明言而立者,有默许而立者,均当谨守。明言者,或口宣盟词,或文载盟府,或两国全权大臣盖关防于公函,或两国互行告示及互换照会,俱可。”(42)所谓“换文”(exchange of notes),即指当事国双方通过互换外交照会,就彼此关系事项达成协议,“它是两国政府用以缔结条约的简易形式。换文的生效通常无须批准,但在国际法上一向属于条约的性质”。(43)上引电文中,盛宣怀已预拟致领事照会稿,而江、鄂两处交换意见后,均复电赞成。(44)至7月2日,余联沅奉命向领事团照会如下:
6月27日来函敬悉,当即电达刘、张两督宪。兹奉两江总督刘复电如下:“无论北事如何,总当与香帅一力担承,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本官昨已将此项答复电文通知贵总领事。今复得刘督宪来电:“领袖领事华德师来函已阅。前议尚未声明将来如何之处,诚恐北方军务愈紧,东南人心摇动,自应彼此再行声明:“无论以后如何,上海及长江、苏、浙内地如各国政府允仍照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运兵,两总督亦允能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各国在各省之人民财产。”特此奉达,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赐复为祷。以便照禀。若是刘、张二督宪亦将知会其他诸省督抚,于所辖府州县按此约定,一律照行。该照会系盛宣怀拟稿基础上形成,文中未再涉及具体章程条款,而仅要求各国确认“无意在长江一带运兵”的意思。它作为6月27日领事团来照的复文,是标志“东南互保”交涉由议约向“换文”转变的重要文件。不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此前一天(7月1日),余联沅还曾经发出过另一件盛宣怀未曾与闻的照会:
两江总督刘、湖广总督张力任保护上海及长江内地,一意保全中外商民人命财产。兹奉两督宪之命,本官特拟保护章程九款,相应译成外文,呈交贵总领事,并请转知各国领事,恳赐俯允。又贵总领事前日照会:“倘两位制台能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外国人民之权利,我各国之政府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进兵,不独一国不如此做,合力亦不如此做。”本官已谨呈刘、张两督宪及江苏鹿[传霖]抚台。兹奉两江总督刘复电:“此间并未奉有宣战谕旨,无论北事如何,总当与香帅一力担承,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特此奉达,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为祷。(45)这一文件在过去研究中一直未被提及。那么,前后两件照会,究竟关系如何?查7月1日余联沅致盛函云:“顷奉环示祗悉。荩筹周密,钦佩莫名。并呈代拟照会稿,至为妥善。惟辰刻已嘱福茂生至各领处探询,归来即商拟一照会送去,大致与尊指相同,但不及我公之前后周到,歉仄之至。刻因前所陈拟稿尚未就绪,现嘱福茂生至尊处陈明一切,随后即诣求诲也。”(46)“福茂生”,即福开森,时供职于南洋公学,为盛宣怀幕僚。(47)余联沅碍于身份,不便随意活动,便委托福开森居间联络,探询各领事意向,而当天照会提及“保护章程九款”,仍意在催复,希望完成签署程序。此照会发出后,余联沅才得知盛宣怀拟以“换文”结束交涉的意向,故有以上这番解释。次日,又奉到刘坤一电谕,遂按照盛意再度缮发照会,其中不再言及章程,也回避了议约一说,目标已经退而求其次。
五、“换文”实现
盛宣怀对英、美、日三国领事的走访,达到了一定效果。日本领事小田切对“换文”持一种积极态度,致电本国政府请求授权,在响应盛宣怀提议之外,他更强调的理由是:在东南诸省维持稳定秩序,对保障日本商业利益关系重大,而利用中方急于换文的心理,正可善为操纵,借为扶植政治上的势力。(48)7月2日,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发出训令:
关于7月1日来电,帝国政府对此协定案固无异议,惟目前各国正采取共同一致之行动,该协定必须由清国官吏与所有关系国领事共同缔结,贵官应待有关各国领事均获得其本国政府之认可后,方可与清国缔结协定。(49)7月3日,再度训令:
关于7月2日本官电信,此际贵官不仅只与二三国领事,而必须与所有关系国领事协同一致行动,此点希特别注意。又,相信其他国家领事对此次协议亦表欣然。据贵官来电推察,盛宣怀等清国官吏不独与贵官及英、美两国领事从事交涉,或与他国领事亦有订有协议。(50)日本政府对“互保”原则表示赞成,但坚持以各国一致行动为前提,故指示小田切须谨慎从事,避免有过于露头的举动。训令中所谓的“二、三国领事”,即针对英、美而言。
英国是在长江流域拥有最多利益且最具权势的国家。早在6月中旬,英国总领事霍必澜即试探将本国海军舰队开入长江内地,遭到刘坤一、张之洞等婉拒。尽管后来坐到了谈判桌前,参与“互保”交涉,但作为出兵论的始作俑者,霍必澜并不甘心罢手;英国政府亦不愿订立约款,约束自身行动,这一态度在批复保护章程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51)交涉进入“换文”阶段后,霍必澜的态度仍显得消极,他坚持为使上海不致受到攻击,有必要在当地驻扎一支强大的部队。(52)相较而言,美国领事古纳最早表现出配合的姿态,6月26日会议后,他向华盛顿报告说:
自此次会议以后,这些省份的总督和巡抚们很积极地预防困难,而且假若困难发生的话,准备随时应付它。长江流域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村庄都有中国当局的布告,命令维持和平并且承认外人的权利及保护其财产。这一地区较小城市的传教士向我报告的信息,是令人鼓舞的。(53)
当中方提议换文,古纳也予以积极反应,于7月2日致电表示:“昨拟声明,无论北事如何变乱,上海及长江苏浙内地照前保护,英、美、俄、法各外部回电照允,即日签字照会。请督抚迅速出示,照约保护,因宣战已揭晓,恐有一处蠢动,致碍此约。”(54)古纳谓美国以外多国政府已同意签字的信息,不尽确,但他要求各省出示安民,很快得到回应。盛宣怀、余联沅互商后,随即禀请总督饬行;(55)刘、张等迅速布置地方,付诸实施。(56)
同时,领袖领事华德师致电刘坤一,提出一项特殊要求:“请拣定一员,操全权代表贵大宪与领事公会商办机务,以归简捷。”(57)这样就发生了中方代表全权身份问题。按国际法规定,缔约主体为国家,外交代表须由国家元首或中央政府授给全权资格(full powers),签字才具有相应的效力。(58)而余联沅等人的行为,仅奉地方长官行政指令,未经中央外交授权,因此不具有国际法上全权身份。外交最重程式,尤其强调交涉代表的对等原则及授权程序的完善性,领事团将谈判对象性质的含混处一下挑明,使地方督抚颇感觉难办。盛宣怀提出自己的见解:
各国现以长江、苏、浙一带之事,专责总领事办理,请两帅会电公派余道以全权与各领事会商办事,宣承命无不竭力相助。但两国交涉,必凭一人为主,已与余道议定,凡公事均归余道列名。照章应请两帅径电领袖华领事,即照香帅(张之洞—引者按)阳电之意,并应索该领袖全权文凭,与余道互易。兹事重大,乞两帅另给印文与余道及宣,以示各国为信。(59)该电要求江、鄂两总督颁给余联沅、盛宣怀授权“印文”,惟正式外交场合,仍推余为主;同时反过来向领袖领事勘验全权证书,作为互议凭证。在刘、张看来,“余道系地方官,各领信服,盛心细识优,可以相助”,均为可信用的人选,但担心“外间派全权,似未妥”。(60)李国祁指出,“江、鄂两督仅为地方首长,所倡导的互保办法仅是一时的权宜,并非中国政府的意旨。其本身已有违法的嫌疑,何能再授予盛宣怀、余联沅的全权?”(61)从国际法角度看,刘、张并无出具全权证书的资格,他们的授权实质只能代表其个人,或代表其总督辖区的权力,如径以“全权”名义公开交涉,那确乎有自视为政府的嫌疑了。现实的政治风险,还是让两人选择谨慎从事,最后发给余、盛印文,避开了“全权”字样,而改用“即与本大臣本部堂面商无异”。(62)
至7月5日,领事团仍未予照复。当天,盛宣怀赴南京面见两江总督刘坤一,此行目的是为应对清廷谕令停还洋款的危机,而他临行前,仍不忘“与各领订[六月]十二日(7月8日)回沪”,并切催复照。(63)盛氏的亲信赵凤昌后来回忆此事:“六月中旬刘督与盛电,奉廷寄约至宁见面,电问何事,坚不预泄,更使人不测,然不得不往。盛因邀予同行,予向病暑,却之,心则颇歉,梅生偕去,讵见后,即示廷寄,乃饬停还洋款,即商定置不奏复,可见庙谟之如儿戏也。”(64)盛宣怀对这一时机加以运用,显示了机敏灵活的交涉手段,王尔敏对此评价为:“不仅掩盖了一个重大事件的泄漏,使各领事相信,他的南京之行是为了解决签约问题而奉电召的,同时加速完成了这项保约。”(65)
时因换文交涉迟无进展,而北方战事已愈演愈烈,上海领事团预感形势危急,于7月5日决议由各领事向本国政府致电如下:“局势极为严重。义和拳运动正在发展;如果天津的联军不能制止它,那么,它将扩大到华中和华南,并成为全国性的运动……由此看来,有必要派遣一支部队制止其发展,并且支持总督们维持秩序。”(66)又因德使克林德遇害消息已被证实,德国对华态度趋向强硬,不仅表示“江、鄂两督拟订各节,碍难径允”,且有“在华应办事宜归统将主裁”等威胁之言。(67)鉴于上述情势,余联沅深感束手,只好向盛宣怀求援。7月7日,盛宣怀由南京匆匆赶回上海,喘息未定,即接到余联沅来函:
闻我公归,亟欲趋谒。兹奉手示,须密查案据,谨当遵候驺临。领事复文未来,因德领未遽允,赖公大力转圜,叩祷。手复敬请勋安。名正肃。十一日午刻。(68)
当日,盛、余两人即向领事团展开游说。为打破僵局,故不得不稍示强硬,“当即向各领事开导,既有去文,若无复文,两督何以凭示各省?且今日必要复文,以免误会”。(69)在中方一再要求下,“各领申刻会议,美领拟三稿,德领只允签复”,会后,领袖领事华师德正式照复余联沅:
本领袖领事承各国领事之嘱,答收贵道西历七月初二日来文,相应照复贵道,请将本领袖领事西历六月二十七日函致贵道,即视为答复七月初二日来函之文。理合照复。(70)其意在“声明不改原议”,不过重申前次照会,并未增加任何实质性内容,然在形式上,算是对换文交涉做了一个收束。中方原希望订约的目标没有达到,不过和平局面却基本得以维持,“东南互保”在事实上已然形成了。
六、结语
盛宣怀在上海首倡“东南互保”,并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响应,中方的交涉目标起初设定为“订约”,在沪代表也拟议了具体章程及其附件的草案,寄望于中外双方签字生效。相关的两份核心文件均以“章程”命名,在当时语境中可以与约款等同视之。一方面,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经双方批准的章程,具备与条约同等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几位“互保”的主事人在外交因应的同时,也有着政治面的缜密思虑:初拟条款之际,盛宣怀就已进言:“惟兹事体大,各条措词必须得体,留事后进呈地步”;(71)在向朝廷备案问题上,张之洞亦坚持如下主张——“只可言章程,不可用约字”。(72)尽管中方所拟章程以慎重出之,力求周全,但由于列强政府基于本身利益考虑,以及战争形势不断变化,章程细目并未被接受,交涉的主题渐由“签约”向“换文”转移。也就是说,中方不再追求以契约形式将章程法律化,转而通过互换照会达成某些和平性质的协议。从国际法角度来说,“换文往往言明签署后立即生效而不需要经过批准,在国家间需要迅速缔结和执行协议时,这种形式是特别方便的”。(73)对中方而言,可以说是灵活的权宜之计,实则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为面对僵局时不得不然的一种妥协。而领事团在公布和平告示、确认全权身份等要求一一得到满足后,并由于中方一再坚持,最终以复照形式申明,各国在利益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将不在长江流域用兵的基本精神。
本文的考察面,相对偏重于“互保”交涉过程的中方一侧,尤其对直接负责谈判的盛宣怀、余联沅等人言行、策略着墨较多,实际上,在对手方一侧,不仅列强政府之间有着持续的博弈互动,驻沪各领事对于“互保”的态度亦不乏有差别与变化。(74)“东南互保”之所以成立,发生在上海的交涉及其结果固然重要,各国互为牵制、莫敢先发的均势同样为不可忽视的因素。通过前文考订,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此次交涉的主线,并对此前在学界以及历史教科书当中误为“常识”一个史实作出修正,即“东南互保”没有“议定”或“签署”所谓的约款,而仅以换文形式达成了中外保护的谅解。就“互保”范围而言,原来只限于两江和湖广总督所辖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五省,后又加入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其中福建倒是唯一的、真正经中外签约而实现“互保”的省份。闽督许应骙事后对盛宣怀表示“敝处早经会各领事力任保护,与江、鄂不谋而合”,其行为与上海交涉相仿,但就交涉结果论,则具有更完备的法律形式。(75)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东南互保”是一个包含了复杂原因和曲折过程的、动态的历史事件,而并非仅牵涉两个“章程”是否签字的问题。为今人所乐道的章程文本有其阶段性的意义,却很难用它来代表整个事件的面貌。以换文告终的“互保”交涉,对中外双方都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但利益损害相对更大的,仍然是中方。对列强而言,拒签约款意味着在享受保护的同时,保留了将来自有行动的余地,而不必担负条约义务。尤其视长江利益为禁脔的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军事干预的计划,最后英军登陆上海,以及法、德、日军接踵而至的事实,令本来抱有期待的中国人大失所望。稍后,日本强行出兵厦门,也是一次效仿英国而功败垂成的冒险。这一系列来自外部的冲击,尽管没有整体动摇“互保”格局,但清楚印证了列强国家对待中国的野心和傲慢,也提示了在中外权势失衡的前提下“互保”的脆弱性质。
注释:
①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载《人文月刊》,第2卷,第5期,1931年。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88—294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本文所引皆据此版本。
②吴馨等修,姚文枬等纂:《上海县续志》卷十五《名宦》,第82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18。
③王明中:《义和团运动中英国与“东南互保”》,载《南京大学学报》1964(3—4),收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4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④谢俊美:《“东南互保”再探讨》,载《档案与历史》,1986(2);金家瑞:《论“东南互保”》,载《福建论坛》,1989(5)。
⑤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第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⑥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第四版)》,第3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⑦熊月之、袁燮铭:《上海通史(第3卷)·晚清政治》,第2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⑧张海鹏主编,马勇著:《中国近代通史(第4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第47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⑨丁名楠:《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所谓“东南互保”》,《大公报》,1952年2月28日,收入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⑩丁名楠、张振鵾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129-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刘天路:《“东南互保”述论》,见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2)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13·庚子拳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三章“均势思想与东南互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
(13)林世明:《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
(14)黎仁凯:《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载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第190页,济南,齐鲁书社2000。
(15)《寄李中堂、刘岘帅、张香帅电》(《愚斋存稿》卷3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第84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时间原注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研究著作多据此展开论述。此日期实系误植,查该电韵目为“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发电时间应在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日本学者藤冈喜久男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参见氏著《张謇と辛亥革命》,第97页,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1985。
(16)《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9页;《寄余晋珊观察》,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寄江鄂刘张两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见《愚斋存稿》卷36,第845页。
(18)五条内容具体如下:一、长江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及两湖督宪张切实保护。二、长江一带兵力足使地方安静,毋须各国派兵船入江帮助,业已出示禁造谣言,严拿游勇会匪。三、东南江海各口岸,如需兵力协防,由中国督抚相机随时函商各国办理。四、长江一带洋商教士,即由中国南洋大臣刘及两湖督宪张力任保护,若有疏虞惟地方是问。五、各国如不待中国督宪函商,竟自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起衅,毁坏洋商教士产业人命者,事后中国不认赔偿。(《余道来电并致江宁督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申刻到,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1页)
(19)《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见《愚斋存稿》卷36,第846页。
(20)《盛宣怀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68—97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按,两份章程的中、英文本收录于多种文献,王尔敏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参看其《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13·庚子拳乱》,第168页,注4。
(22)[英]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杨立义译,第2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关于“章程”有效性及其生效方式的研究,并可参考郭卫东:《〈江南善后章程〉及其相关问题》,载《历史研究》,1995(1)。
(23)《致上海盛京堂、余道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1页。
(24)《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領事代理ョリ青木外務大臣宛·秩序維持ニ付各國領事ト協議方劉張両総督ヘ提議ノ始末並仏領事ョリ両総督管下ヲ中立トナス提議ニ付請訓ノ件》,明治33年年6月25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77-478页,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6。小田切解释这里所用的“中立”一词,并非就其严密的固有意义而言,而是特指在指定地域内避免战争的意味。
(25)1868年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成立,简称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英文名为Mixed Court),初设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首理事衙门内,1899年移至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191号)新厦。
(26)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90页。
(27)《复张制军》,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见《刘坤一遗集》,第6册,2567页。
(28)《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酉刻,王尔敏、吴伦霓霞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49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29)《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領事代理ョ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南清秩序維持協定ノ解訳ニ関スル領事会議决議ノ報告ノ件》,明治33年6月27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80页。
(30)应大沽方面高级司令官的请求,上海领事团于6月23日将此声明出示。该文本见《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领事团的布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5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1)《寄粤宁苏鄂皖各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见《愚斋存稿》卷36,第846页。
(32)《寄粤李中堂、宁刘宫保、鄂张制台、苏鹿中丞、皖王中丞》,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见《愚斋存稿》卷36,第847页。同照会另一译本,可参看《驻上海各国领事致余联沅函》,《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93页。
(33)《寄江鄂刘张二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见《愚斋存稿》卷36,第850页。
(34)《收南洋大臣刘、湖广总督张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到,吕海寰:《庚子海外纪事》,第43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35)《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酉刻,载《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0页。
(36)《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余道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亥刻发,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8-8049页。
(37)前揭丁名楠论文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均有“7月13日领事团正式拒绝签字”的表述,未见引据,出处不详。
(38)《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卯刻,载《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4页。
(39)《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十二钟,载《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4页。
(40)《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領事代理ョリ青木外務大臣宛·秩序維持ノ協定、李劉張三総督承認並右協定ノ公文交換方盛宣懷ョリ請求ニ請訓ノ件》,明治33年7月1日,《日本外交文書· 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87页。
(41)《寄江鄂刘张两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见《愚斋存稿》卷36,第856页。
(42)惠顿:《万国公法》,第8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3)周鲠生:《国际法》下册,第5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44)《致上海盛京堂、余道台,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子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63页;《刘坤一致余联沅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07页。
(45)《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領事代理ョリ青木外矞大臣宛·长江沿岸ニ各国ョリノ出兵見合方ニ盛宣懷ョリ各領事宛協定請求並右ニ対スル領事会議ノ状况報告ノ件》,明治33年7月6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94—495页。按,两照会均系据英文文本回译。
(46)《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申刻,载《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5页。
(47)福开森(John.C.Ferguson,1866—1945),生于加拿大,入美籍,1887年以传教士身份赴华。先后在镇江、南京工作,创办汇文书院,佐两江总督刘坤一办理外交得力,“经历派办交涉事件,莫不实心相助为理”。(《洋员办事得力分别请奖片》,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117页)1896年应盛宣怀之聘,参与创建南洋公学,任监院。后为《愚斋存稿》作序,自述与盛氏交往始末。参看《愚斋存稿》卷首,第44—45页。
(48)《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領事代理ョ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南清秩序維持協定公文交換方ニ付禀申ノ件》,7月2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88页。
(49)《青木外務大臣ョリ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領事代理宛·南清秩序維持協定締結時期ニ付回訓ノ件》,7月2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88页。
(50)《青木外務大臣ョリ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領事代理宛·南清秩序維持協定ニ付各國領事ノ協同措置方斡旋ニ関シ訓令ノ件》,7月3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90页。
(51)戴海斌:《“东南互保”之另面——1900年英军登陆上海事件考释》,载《史林》,2010(4)。
(52)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June28,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24,edited by Ian Nish,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139.
(53)Mr.Goodnow to Mr.Crider,June29,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00,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gting Office,pp.249-250.
(54)《寄各省督抚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愚斋存稿》卷36,第857页;《美国总领事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酉刻到,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4页。
(55)《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申正、初七日七点一刻,《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5、357页;《余道来电并致江宁督署》,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六日亥刻到,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4页。
(56)《刘坤一致余联沅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09页;《致上海盛京堂、余道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巳刻发,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2页。
(57)《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到,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2页。
(58)[英]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第87页。
(59)《寄江鄂刘张二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愚斋存稿》卷36,第859页。
(60)《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午刻到,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7页。
(61)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68页。
(62)《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午刻到、初十日申刻到,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7、8081页。
(63)《盛宣怀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06页。按,六月初四日(6月30日)清廷上谕:“现在统筹战备,迭经谕令各省筹饷练兵,共保疆土。惟库款支绌,饷项艰难,既与外洋决裂,所有各省认还洋款,著即暂行停解,听候部拨,移充军饷。”(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64)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91页。“梅生”,何嗣焜(1843—1901),字梅生,江苏武进人,时为南洋公学总办。
(65)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13)·庚子拳乱》,第150页。
(66)《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68页,胡滨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
(67)《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82页。
(68)《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午刻到,《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8页。
(69)《盛宣怀上宁、鄂督署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407页。又据日本领事小田切报告:“据由南京归来之盛宣怀对本官所言:第一,刘坤一数日前接奉与排外诏敕意义相似之上谕,为此颇感苦虑;第二,关于6月27日各国领事与刘、张代表缔结之协议,刘坤一希望各国政府通过各领事速予正式照会;第三,对于驶入长江之少量军舰,刘坤一已示默允。(《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ョ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排外詔勅ニ対スル劉総督ノ苦慮並秩序維持協定ノ批准及各国ョリ沿江派艦見合方ニ関スル同総督ノ希望等報告ノ件》,明治33年7月7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500页)
(70)《寄江鄂刘张二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愚斋存稿》,卷37,第868页。
(71)《盛宣怀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89页。
(72)《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42页。
(73)[美]劳德派特修订:《奥本海默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第325页,石蒂、陈健译,商务印书馆,1972。
(74)戴海斌:《外国驻沪领事与“东南互保”——侧重英、日、美三国》,载《史林》,2011(4)。
(75)《闽督许筠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见《愚斋存稿》卷36,第858页。1900年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等与俄、美、日、法、英、荷兰、德七国驻福州领事签署《相互保护约章》,共计8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