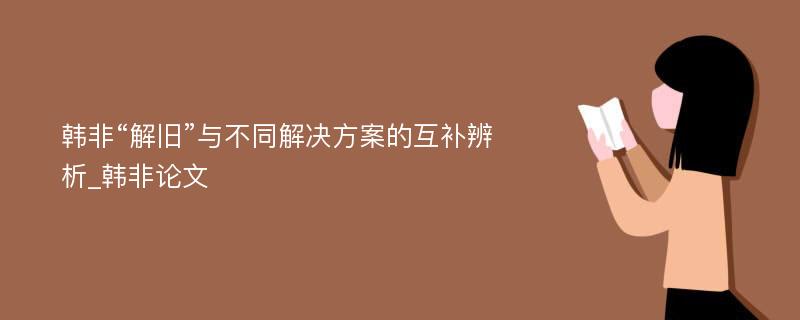
韩非《解老》异解补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解补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老子之《道德经》,哲理玄深,文辞亦“微妙难识”。因此,最早解释此经的韩非的《解老》,自然为历来学者所重视,据之解老亦颇多见。文章认为,韩解虽然有其参考价值,可是其解往往与本意乖异,故宜加辩别。对此,作者已有文阐述。本文则再引举明显之事例作进一步论述,以明此说非为诬妄。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赞又云:“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司马迁认为韩非的学术思想虽源自老子,却并未得其深远之旨。我们姑且不论司马迁此说是否有扬老贬韩之嫌,但他以为韩非所得,与老子本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是无可非议的。司马迁这话是就韩非的整个学术思想说的,但注意到韩非著作中有直接阐解《道德经》的《解老》、《喻老》两篇,所以应该说,它也是包括此两篇而说的。笔者认为,司马迁这话对于我们研读《解老》、《喻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韩非在认识上有此差异,再加之《道德经》本身文辞的“微妙难识”,他在阐解时会出现异解就势所难免了。即以《解老》而言(《喻老》另文论述),其所解违异本意之处可谓触目皆是,令人疑惑不解。固然,其中有的或许是想借老成说,但大多并非如此。由于《解老》在研究老子《道德经》上居于较重要的地位,而事实上,也确有学者在解释《道德经》时即据引韩之异解为说,致使老子本意不明。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撰写了《韩非〈解老〉异解辨》(刊载于《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6期)一文, 然意犹未尽,故再为补辨,以伸愚见。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道德经》五十四章:“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解老》云:“人无愚智,莫不有趋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来。得于好恶,怵于淫物,而后变乱。所以然者,引于外物,乱于玩好也。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而今也玩好变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圣人不然:一建其趋舍,虽见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谓‘不拔’;一于其情,虽有可欲之类,神不为动,神不为动之谓‘不脱’。为人子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
老子之意是,善于建国者其国他人不能夺取,善于执政者其政权不会脱手,由于国祚永保,故子孙祭祀可世代不绝。那么,怎样才是“善建”、“善抱”呢?我们参照他章,可以略明其意。二十九章云:“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六十四章云:“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二十二章云:“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于此可知,其所谓“善”,正在能“无为”、“无执”、“不争”。建国者,虽“建”而以“无建”处之;执政者,虽“抱”而以“无抱”处之,则自然“无失”而“善胜”,且莫能与争。
韩解之异是:(1)将所“建”指为“趋舍”,即“取舍”, 将所“抱”指为“神”,即精神,这就与老子之意不合。老子虽略而不言所“建”所“抱”之对象,但由其下接“子孙以祭祀不辍”一句,即可知其并非泛泛之言。我们知道,老子其时失国丧权者颇多,故其五千言多以君主为视角(如云“治天下”者,“治国”者,“侯王”、“王公”、“万乘之主”、“上”等)而论其利害得失,则此处似不应舍此而别求他意。况且,“建”指建国,其意固当;“抱”者,《广韵》曰“持也”,故作执政解,亦无不当。(2)其对“善建者不拔, 善抱者不脱”与“子孙以祭祀不辍”两句之关系的理解亦与老子相异。老子在后句特用一“以”字,表明其为因果相承之关系。韩非则以为前句只在陈述圣人之“趋舍”与“神”能不被外物引离的一般道理。但如此解释,显然不能与后句相承接,于是他不得不加上“体此道”一层意思作过渡,再引出后句,这就割裂了原本周密的语意。
韩解虽与老子原意相违,却为近年出版的一些《道德经》译解著作所采取,以至认为韩解反映了奴隶社会宗族之间斗争的社会现实〔1〕。可见其所造成的影响。
2.同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解老》云:“身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乱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2〕之固也。治家者,无用之物不能动其计,则资有余, 故曰:‘修之家,其德有余。’治乡者行此节,则家之有余者益众,故曰:‘修之乡,其德乃长。’治邦者行此节,则乡之有德者益众,故曰:‘修之邦,其德乃丰。’莅天下者行此节,则民之生莫不受其泽,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老子之意是,其自身能达到此种“善”的境界,那么,他的虚静寡欲谦下之德才纯真;其家、乡、国、天下都能达到此种“善”的境界,那么,他的德就发扬光大了。所谓“修之”之“之”,承上文之意,无疑当指“善”之境界而言;而所谓“余”、“长”、“丰”、“普”,则不过是发扬光大的变通说法而已。
韩解之异是:(1)将“修之身”解为身具“此道”, 即“外物不能乱其精神”,与老子所指违异。(2 )将“其德乃真”与其下“其德××”四句之“德”,一概以“得”意作解,亦与老子本意不合。此外,我们体会老子“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五句,其所以要由身而家、而乡、而国、而天下如此排列,无非想以此说明“其德”之作用的渐次扩展,故五个“德”字无疑是同义的。而韩非之“得”意,不仅所指无定,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如:以身言指“精”之“积”,以家言指“资财”,以乡国天下言又指“民”,全无定着。再如:以乡国天下言,在前指得民,在后却指民得资财,可谓自乱其例。
3.同章:“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解老》云:“修身者以此别君子小人,治乡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适观息耗,则万不失一。故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老子之意是,以自己心目中达到如此“善”之境界而有纯真之德的人、家、乡、国、天下,来观察当今之人、家、乡、国、天下。据此,即可明白天下何以会至于今日之地步。意为皆因背离“善建”、“善抱”之道而无纯真之德所致。
韩解之异是:(1 )将“以身观身”解为以“修身者”之是否合于“此道”来区分君子小人,不仅“修身”之意全乖,且别出区分君子小人之意,亦为原意所无。(2)将“以家观家,以乡观乡, 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解为(治家)治乡治邦莅天下者,若各自能从是否做到“无用之物不能动其计”这一角度去考察其家、乡、邦、天下之所以兴衰,就会获得正确的认识。此解不仅与老子原意大相径庭,而且将是否做到“无用之物不能动其计”视为家、乡、国、天下所以兴衰的根源,亦甚为悖理。
4.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
《解老》云:“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之意是,即使治理大国,亦当如烹煮小鲜一般简易省事。小鲜,敦煌辛本作“小腥”,盖指小虾小鱼之类。因其极为细小,故烹煮前无须逐一清洗,烹煮时,亦无须翻动即成。河上公注云:“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靡也。”此喻若以“无为”治国,即可致治。
韩解之异是:(1 )不辨老子用“小鲜”为喻而突出其“小”之用意,故认为“挠”是必要的,所忌只在“数挠”,这就与老子“无为”之寄意相异。(2)老子以“烹小鲜”为喻, 其意并非在论其色泽是否可取。韩非从色泽角度论其效果,这是与他作为法家学者而凡事注重功利有关的。所谓“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云云,其意显然。
5.同章:“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解老》云:“民犯法令之谓民伤上,上刑戮民之谓上伤民。民不犯法则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谓上不伤人。故曰:‘圣人亦不伤民。’”
老子之意是,圣人以道莅治天下,使得鬼也不灵验了;不是鬼不灵验,而是它的神灵不伤害人;不仅它的神灵不伤害人,圣人也不伤害人。
韩解之异是:(1)将圣人之“不伤人”归结于“民不犯法”, 此纯为其自生之意,与老子之以为出于其治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迥异。(2)以为“圣人亦不伤人”是相承“民不犯法”、 “伤上”而言,此亦纯为其自生之意,与老子之相承鬼“其神不伤人”而言乖异。
6.同章:“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解老》云:“上不与民相害,而人不与鬼相伤,故曰:‘两不相伤。’民不敢犯法,则上内不用刑罚,而外不事利其产业。上内不用刑罚而外不事利其产业,则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积盛。民蕃息而蓄积盛之谓有德。凡所谓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乱。精神乱则无德。鬼不祟人则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则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之谓有德。上盛蓄积而鬼不乱其精神,则德尽在于民矣。故曰:‘两不相伤则德交归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归于民也。”
老子之意是,鬼之神与圣人两者皆不伤人,故功德全归于圣人。
韩解之异是:(1)以为“两”是指“上与民”、 “人与鬼”两种关系,“不相伤”意即不相互伤害。而老子之所谓“两不相伤”,是承鬼“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而言,谓两者皆不伤人。“相”在此代指“人”。(2)其言德尽归于民,与老子相背。老子之意是, 因圣人治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故功德全归于圣人。退而言之,即如韩非所言,民既赖圣人之德,“盛蓄积而鬼不乱其精神”,怎么又成为德之所归呢?二章云:“圣人处无为之事……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老子关于功德归于圣人之见解,曾多处言及,可为佐证。韩非归德于民之说虽不合老子本意,但因其说在先,故后人往往有袭其说者〔3〕。
7.四十六章:“罪莫大于可欲。”
《解老》云:“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奸起则上侵弱君,祸至则民人多伤。然则可欲之类,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祸莫大于可欲。’〔4〕”
老子之意是,罪过没有比企图贪有之动念更大。老子主张“寡欲”、“无欲”,故视贪有之欲望为莫大之罪过。
韩解之异是:其所指“可欲之类”,为有害法治者,与本意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8.同章:“咎莫憯于欲得。”
《解老》云:“故欲利甚于忧,忧则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则失度量,失度量则妄举动,妄举动则祸害至。祸害至而疾婴内,疾婴内则痛,祸薄外则苦。苦痛杂于肠胃之间,则伤人也憯,憯则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于欲利。故曰:‘咎莫憯于欲利’。〔5〕”
老子之意是,没有比贪得而遭受灾祸更其痛苦。
韩解之异是:(1)将“咎”作“自咎”解,谓自己追究罪过, 而老子绝无此意。前二句云:“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与此句内容一致而句式一律,说“罪”、“祸”,皆无“自罪”、“自祸”之意,可为佐证。(2)将“憯”理解为身体上的疾痛, 而不知老子主要是指精神上的痛苦说的。(3)变乱了原句词语的表意结构, 故其解极其别扭怪异。
9.六十七章:“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解老》云:“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又云:“故临兵而慈于士吏则战胜敌,慈于器械则城坚固。故曰:‘慈,于战则胜,以守则固。’”
老子之意是,在上者若能以慈心对待百姓,即希望他们能安居而反对杀人的战争,则当战争之手段在‘不得已而用之’之时,他们反而会勇于战斗,达到战胜守固之成效。此正合于相反而相成之理。
韩解之异是:对于谁“慈”、谁“勇”,所指与老子或依或违,自相矛盾。如在前二者均指圣人,以为圣人出于慈心,虑事合道,故勇于行事;在后则分别指主帅与士吏,以为主帅慈于士吏,得士吏之勇,故能得胜,将一贯之意作了肢解。至于云“慈于器械则城坚固”,将“器械”也作为“慈”之对象,并以为此即老子“慈,以守则固”之意,则更与本意相隔千里。
10.同章:“俭故能广。”
《解老》云:“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是以举之曰:‘俭故能广’。”
老子之意是,以俭约自处,反能成其广有。此亦合于相反而相成之理。六十六章云:“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与此意相近。
韩非从三个方面来阐解其意,然皆违背原意:(1 )以“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作解。然而老子云:“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则他岂会教人“俭用其财”去达到“家富”?况且,“家富”未必可以“广”言,更无论“俭用其财”未必可致“家富”。(2 )以“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作解,谓爱惜体内之“精(神)”,固守之而不使外淫,则可致充盈。此已如前文所述,纯为韩非自创之说,与老子无涉。何况,即如所云,“精盛”又怎能以“广”言?(3 )以“人君重战其卒”则可致民众国广作解,谓君主爱惜士卒,使之慎重出战,即可使人民众多,国土广大。这分明是武力扩张意识的反映,与本意已南辕北辙。
求解老子《道德经》之本意,可谓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程。笔者上述之解意,不过是管窥之见。韩非之《解老》,是为研究《道德经》者所必览,然对其作全面之检讨,以笔者之孤陋寡闻,似寡有其人,故此文之作,诚为抛砖引玉,有望于识者。
注释:
〔1〕见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古棣、周英:《老子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引意亦见后者。
〔2〕高亨《韩非子补笺》云:“慎”当为“惪”, 即“德”本字。
〔3〕魏源《老子本义》解此章,全录《解老》。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等,亦取其德归于民之说。
〔4〕“祸”当作“罪”,韩引误。俞樾《老子平议》、 刘师培《老子斠补》说。
〔5〕“欲利”当作“欲得”,韩引误。刘师培说。
